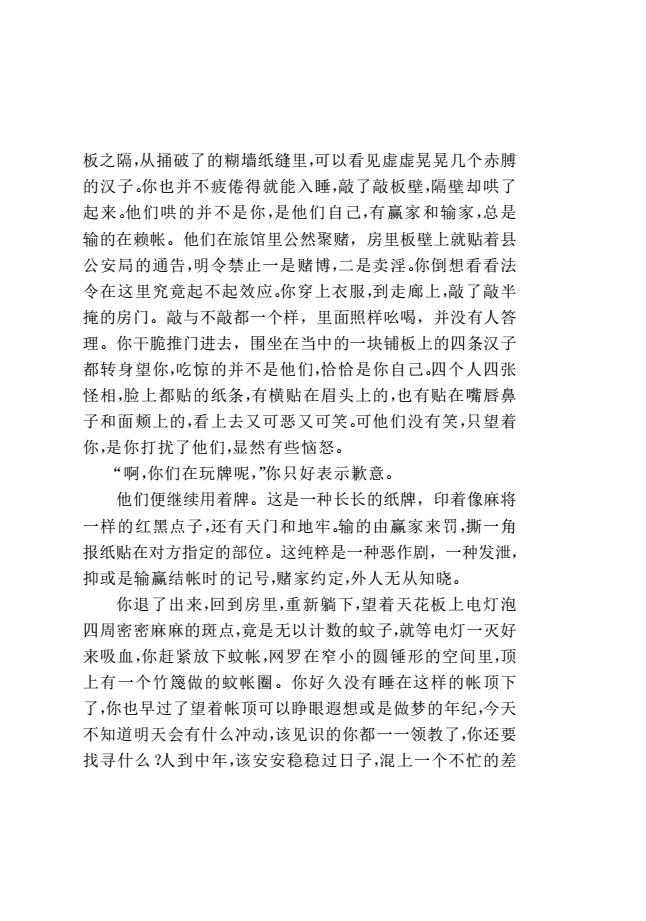
板之隔,从捅破了的糊墙纸缝里,可以看见虚虚晃晃几个赤膊 的汉子。你也并不疲倦得就能入睡,敲了敲板壁,隔壁却哄了 起来。他们哄的并不是你,是他们自己,有赢家和输家,总是 输的在赖帐。他们在旅馆里公然聚赌,房里板壁上就贴着县 公安局的通告,明令禁止一是赌博,二是卖淫。你倒想看看法 令在这里究竞起不起效应。你穿上衣服,到走廊上,敲了敲半 掩的房门。敲与不敲都一个样,里面照样吆喝,并没有人答 理。你干脆推门进去,围坐在当中的一块铺板上的四条汉子 都转身望你,吃惊的并不是他们,恰恰是你自己四个人四张 怪相,脸上都贴的纸条,有横贴在眉头上的,也有贴在嘴唇鼻 子和面颊上的,看上去又可恶又可笑。可他们没有笑,只望着 你,是你打扰了他们,显然有些恼怒。 “啊,你们在玩牌呢,”你只好表示歉意。 他们便继续用着牌。这是一种长长的纸牌,印着像麻将 一样的红黑点子,还有天门和地牢。输的由赢家来罚,撕一角 报纸贴在对方指定的部位。这纯粹是一种恶作剧,一种发泄, 抑或是输赢结帐时的记号,赌家约定,外人无从知晓。 你退了出来,回到房里,重新躺下,望着天花板上电灯泡 四周密密麻麻的斑点,竞是无以计数的蚊子,就等电灯一灭好 来吸血,你赶紧放下蚊帐,网罗在窄小的圆锤形的空间里,顶 上有一个竹篾做的蚊帐圈。你好久没有睡在这样的帐顶下 了,你也早过了望着帐顶可以睁眼遐想或是做梦的年纪,今天 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冲动,该见识的你都一一领教了,你还要 找寻什么?人到中年,该安安稳稳过日子,混上一个不忙的差
板之隔,从捅破了的糊墙纸缝里,可以看见虚虚晃晃几个赤膊 的汉子。你也并不疲倦得就能入睡,敲了敲板壁,隔壁却哄了 起来。他们哄的并不是你,是他们自己,有赢家和输家,总是 输的在赖帐。他们在旅馆里公然聚赌,房里板壁上就贴着县 公安局的通告,明令禁止一是赌博,二是卖淫。你倒想看看法 令在这里究竟起不起效应。你穿上衣服,到走廊上,敲了敲半 掩的房门。敲与不敲都一个样,里面照样吆喝,并没有人答 理。你干脆推门进去,围坐在当中的一块铺板上的四条汉子 都转身望你,吃惊的并不是他们,恰恰是你自己。四个人四张 怪相,脸上都贴的纸条,有横贴在眉头上的,也有贴在嘴唇鼻 子和面颊上的,看上去又可恶又可笑。可他们没有笑,只望着 你,是你打扰了他们,显然有些恼怒。 “啊,你们在玩牌呢,”你只好表示歉意。 他们便继续用着牌。这是一种长长的纸牌,印着像麻将 一样的红黑点子,还有天门和地牢。输的由赢家来罚,撕一角 报纸贴在对方指定的部位。这纯粹是一种恶作剧,一种发泄, 抑或是输赢结帐时的记号,赌家约定,外人无从知晓。 你退了出来,回到房里,重新躺下,望着天花板上电灯泡 四周密密麻麻的斑点,竟是无以计数的蚊子,就等电灯一灭好 来吸血,你赶紧放下蚊帐,网罗在窄小的圆锤形的空间里,顶 上有一个竹篾做的蚊帐圈。你好久没有睡在这样的帐顶下 了,你也早过了望着帐顶可以睁眼遐想或是做梦的年纪,今天 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冲动,该见识的你都一一领教了,你还要 找寻什么?人到中年,该安安稳稳过日子,混上一个不忙的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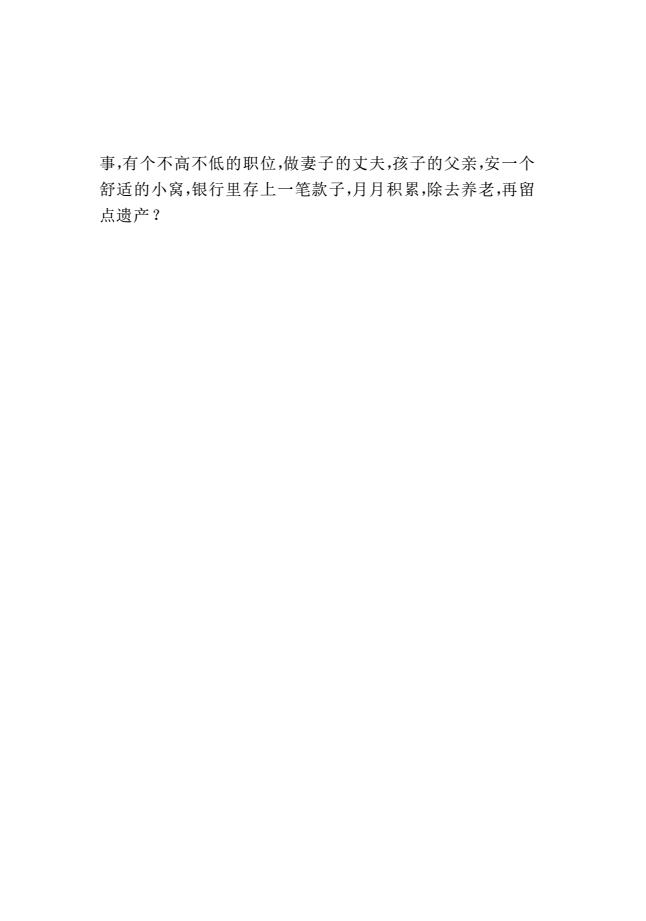
事,有个不高不低的职位,做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安一个 舒适的小窝,银行里存上一笔款子,月月积累,除去养老,再留 点遗产?
事,有个不高不低的职位,做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安一个 舒适的小窝,银行里存上一笔款子,月月积累,除去养老,再留 点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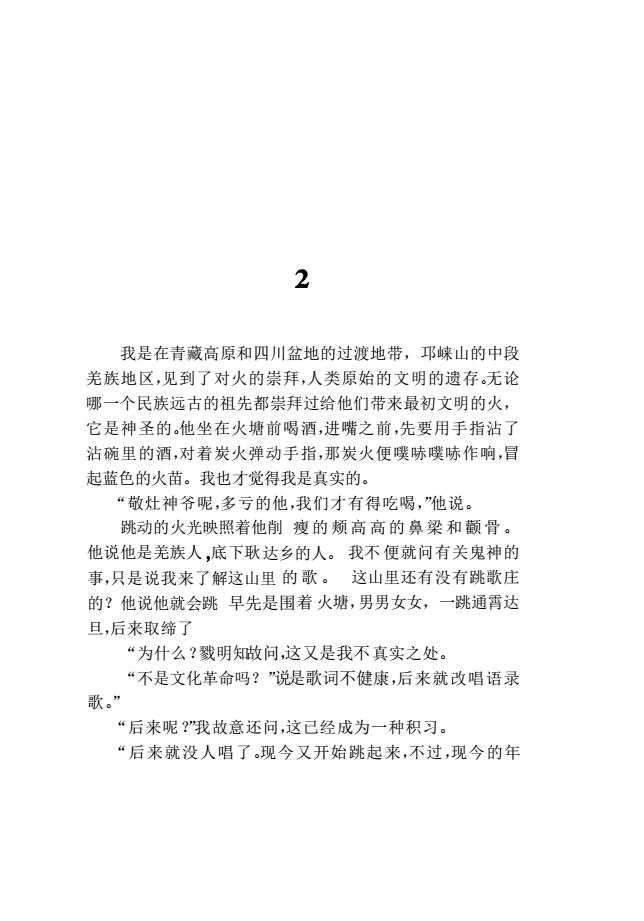
2 我是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邛崃山的中段 羌族地区,见到了对火的崇拜,人类原始的文明的遗存。无论 哪一个民族远古的祖先都崇拜过给他们带来最初文明的火, 它是神圣的。他坐在火塘前喝酒,进嘴之前,先要用手指沾了 沾碗里的酒,对着炭火弹动手指,那炭火便噗哧噗哧作响,冒 起蓝色的火苗。我也才觉得我是真实的。 “敬灶神爷呢,多亏的他,我们才有得吃喝,”他说。 跳动的火光映照着他削瘦的颊高高的鼻梁和颧骨。 他说他是羌族人,底下耿达乡的人。我不便就问有关鬼神的 事,只是说我来了解这山里的歌。这山里还有没有跳歌庄 的?他说他就会跳早先是围着火塘,男男女女,一跳通霄达 旦,后来取缔了 “为什么?戮明知做问,这又是我不真实之处。 “不是文化革命吗?”说是歌词不健康,后来就改唱语录 歌。” “后来呢?”我故意还问,这已经成为一种积习。 “后来就没人唱了。现今又开始跳起来,不过,现今的年
我是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邛崃山的中段 羌族地区,见到了对火的崇拜,人类原始的文明的遗存。无论 哪一个民族远古的祖先都崇拜过给他们带来最初文明的火, 它是神圣的。他坐在火塘前喝酒,进嘴之前,先要用手指沾了 沾碗里的酒,对着炭火弹动手指,那炭火便噗哧噗哧作响,冒 起蓝色的火苗。我也才觉得我是真实的。 “敬灶神爷呢,多亏的他,我们才有得吃喝,”他说。 瘦 的 颊 高 高 的鼻 梁 和 颧 骨 。 便就问有关鬼神的 这山里还有没有跳歌庄 早先是围 男男女女,一跳通霄达 真实之处。 跳动的火光映照着他削 他说他是羌族人 底下耿 我不 事,只是说我来了解这山里 的?他说他就会跳 旦,后来取缔了 “为什么? “不是文化革命吗?” 康,后来就改唱语录 歌。” “后来呢?”我故意还问,这已经成为一种积习。 “后来就没人唱了。现今又开始跳起来,不过,现今的年 戮明知故问,这又是我不 说是歌词不健 达乡的人。 的 歌 。 着 火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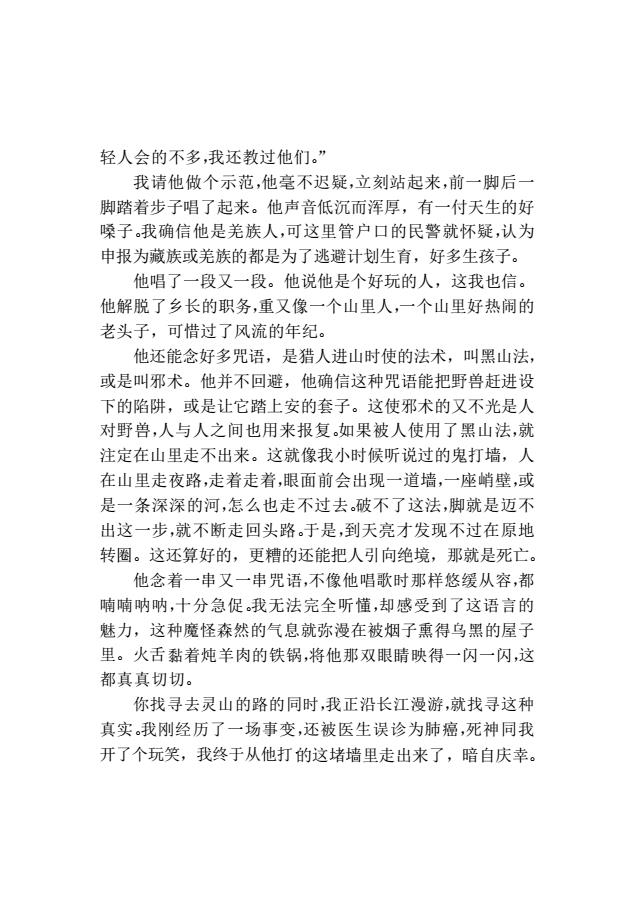
轻人会的不多,我还教过他们。” 我请他做个示范,他毫不迟疑,立刻站起来,前一脚后一 脚踏着步子唱了起来。他声音低沉而浑厚,有一付天生的好 嗓子我确信他是羌族人,可这里管户口的民警就怀疑,认为 申报为藏族或羌族的都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好多生孩子。 他唱了一段又一段。他说他是个好玩的人,这我也信。 他解脱了乡长的职务,重又像一个山里人,一个山里好热闹的 老头子,可惜过了风流的年纪。 他还能念好多咒语,是猎人进山时使的法术,叫黑山法, 或是叫邪术。他并不回避,他确信这种咒语能把野兽赶进设 下的陷阱,或是让它踏上安的套子。这使邪术的又不光是人 对野兽,人与人之间也用来报复。如果被人使用了黑山法,就 注定在山里走不出来。这就像我小时候听说过的鬼打墙,人 在山里走夜路,走着走着,眼面前会出现一道墙,一座峭壁,或 是一条深深的河,怎么也走不过去。破不了这法,脚就是迈不 出这一步,就不断走回头路。于是,到天亮才发现不过在原地 转圈。这还算好的,更糟的还能把人引向绝境,那就是死亡。 他念着一串又一串咒语,不像他唱歌时那样悠缓从容,都 喃喃呐呐,十分急促。我无法完全听懂,却感受到了这语言的 魅力,这种魔怪森然的气息就弥漫在被烟子熏得乌黑的屋子 里。火舌黏着炖羊肉的铁锅,将他那双眼晴映得一闪一闪,这 都真真切切。 你找寻去灵山的路的同时,我正沿长江漫游,就找寻这种 真实。我刚经历了一场事变,还被医生误诊为肺癌,死神同我 开了个玩笑,我终于从他打的这堵墙里走出来了,暗自庆幸
的这堵墙里走出来了,暗自庆幸。 轻人会的不多,我还教过他们。” 我请他做个示范,他毫不迟疑,立刻站起来,前一脚后一 脚踏着步子唱了起来。他声音低沉而浑厚,有一付天生的好 嗓子。我确信他是羌族人,可这里管户口的民警就怀疑,认为 申报为藏族或羌族的都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好多生孩子。 他唱了一段又一段。他说他是个好玩的人,这我也信。 他解脱了乡长的职务,重又像一个山里人,一个山里好热闹的 老头子,可惜过了风流的年纪。 他还能念好多咒语,是猎人进山时使的法术,叫黑山法, 或是叫邪术。他并不回避,他确信这种咒语能把野兽赶进设 下的陷阱,或是让它踏上安的套子。这使邪术的又不光是人 对野兽,人与人之间也用来报复。如果被人使用了黑山法,就 注定在山里走不出来。这就像我小时候听说过的鬼打墙,人 在山里走夜路,走着走着,眼面前会出现一道墙,一座峭壁,或 是一条深深的河,怎么也走不过去。破不了这法,脚就是迈不 出这一步,就不断走回头路。于是,到天亮才发现不过在原地 转圈。这还算好的,更糟的还能把人引向绝境,那就是死亡。 黏 他念着一串又一串咒语,不像他唱歌时那样悠缓从容,都 喃喃呐呐,十分急促。我无法完全听懂,却感受到了这语言的 魅力,这种魔怪森然的气息就弥漫在被烟子熏得乌黑的屋子 里。火舌 着炖羊肉的铁锅,将他那双眼睛映得一闪一闪,这 都真真切切。 你找寻去灵山的路的同时,我正沿长江漫游,就找寻这种 真实。我刚经历了一场事变,还被医生误诊为肺癌,死神同我 开了个玩笑,我终于从他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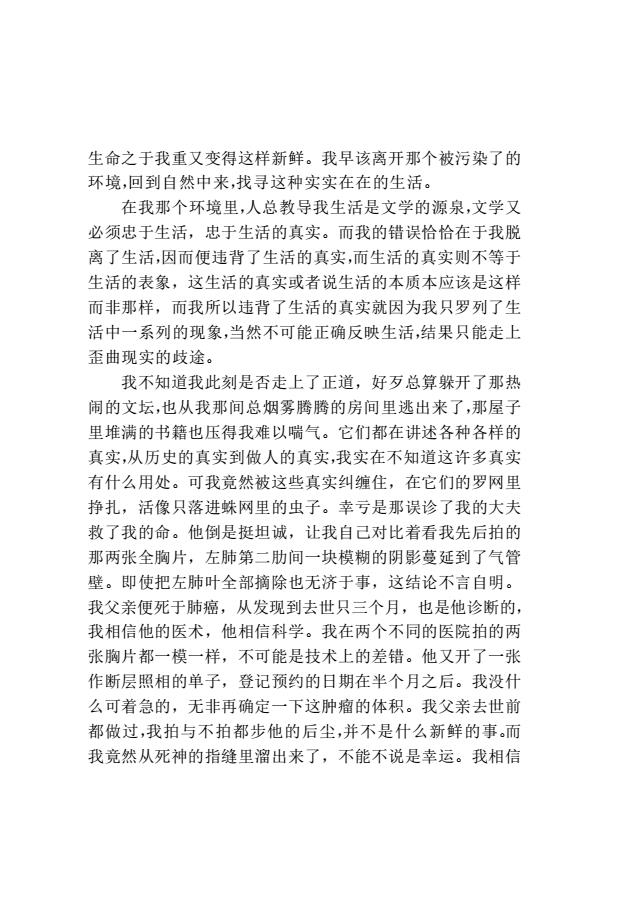
生命之于我重又变得这样新鲜。我早该离开那个被污染了的 环境,回到自然中来,找寻这种实实在在的生活。 在我那个环境里,人总教导我生活是文学的源泉,文学又 必须忠于生活,忠于生活的真实。而我的错误恰恰在于我脱 离了生活,因而便违背了生活的真实,而生活的真实则不等于 生活的表象,这生活的真实或者说生活的本质本应该是这样 而非那样,而我所以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就因为我只罗列了生 活中一系列的现象,当然不可能正确反映生活,结果只能走上 歪曲现实的歧途。 我不知道我此刻是否走上了正道,好歹总算躲开了那热 闹的文坛,也从我那间总烟雾腾腾的房间里逃出来了,那屋子 里堆满的书籍也压得我难以喘气。它们都在讲述各种各样的 真实,从历史的真实到做人的真实,我实在不知道这许多真实 有什么用处。可我竞然被这些真实纠缠住,在它们的罗网里 挣扎,活像只落进蛛网里的虫子。幸亏是那误诊了我的大夫 救了我的命。他倒是挺坦诚,让我自己对比着看我先后拍的 那两张全胸片,左肺第二肋间一块模糊的阴影蔓延到了气管 壁。即使把左肺叶全部摘除也无济于事,这结论不言自明。 我父亲便死于肺癌,从发现到去世只三个月,也是他诊断的, 我相信他的医术,他相信科学。我在两个不同的医院拍的两 张胸片都一模一样,不可能是技术上的差错。他又开了一张 作断层照相的单子,登记预约的日期在半个月之后。我没什 么可着急的,无非再确定一下这肿瘤的体积。我父亲去世前 都做过,我拍与不拍都步他的后尘,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而 我竞然从死神的指缝里溜出来了,不能不说是幸运。我相信
生命之于我重又变得这样新鲜。我早该离开那个被污染了的 环境,回到自然中来,找寻这种实实在在的生活。 在我那个环境里,人总教导我生活是文学的源泉,文学又 必须忠于生活,忠于生活的真实。而我的错误恰恰在于我脱 离了生活,因而便违背了生活的真实,而生活的真实则不等于 生活的表象,这生活的真实或者说生活的本质本应该是这样 而非那样,而我所以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就因为我只罗列了生 活中一系列的现象,当然不可能正确反映生活,结果只能走上 歪曲现实的歧途。 我不知道我此刻是否走上了正道,好歹总算躲开了那热 闹的文坛,也从我那间总烟雾腾腾的房间里逃出来了,那屋子 里堆满的书籍也压得我难以喘气。它们都在讲述各种各样的 真实,从历史的真实到做人的真实,我实在不知道这许多真实 有什么用处。可我竟然被这些真实纠缠住,在它们的罗网里 挣扎,活像只落进蛛网里的虫子。幸亏是那误诊了我的大夫 救了我的命。他倒是挺坦诚,让我自己对比着看我先后拍的 那两张全胸片,左肺第二肋间一块模糊的阴影蔓延到了气管 壁。即使把左肺叶全部摘除也无济于事,这结论不言自明。 我父亲便死于肺癌,从发现到去世只三个月,也是他诊断的, 我相信他的医术,他相信科学。我在两个不同的医院拍的两 张胸片都一模一样,不可能是技术上的差错。他又开了一张 作断层照相的单子,登记预约的日期在半个月之后。我没什 么可着急的,无非再确定一下这肿瘤的体积。我父亲去世前 都做过,我拍与不拍都步他的后尘,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而 我竟然从死神的指缝里溜出来了,不能不说是幸运。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