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台湾研究集刊 No.12007 (总第95期) TAIWAN RESEARCH QUARTERLY General No.95 台湾问题: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两难议题 林冈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030) 摘要:台湾问题是困扰中美关系的一大难题。美国基于维护台湾海峡两岸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 利益考虑,试图对双方采取平衡交往的双轨政策。但这一政策却因美国国内不同利益团体的作用,选 举周期的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海峡两岸的政治角力,不时地受到冲击,发生周期性的变化。 美国对华政策的周期摇摆性,不利于维持台海现状。1995-1996年的海峡危机和2003-2004年岛内公投、 制宪、正名风潮,与美方未能妥善处理台湾这一难题,给台北发出错误信号就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美国对台政策:两岸关系:中美关系:台湾难题:战略模糊:战略清晰:中程协议 中图分类号:D837.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07)01-0045-06 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困扰中美关系的一大难题ilem m a)。对华盛顿来说,这一难题在于其不能从 美方的单方面利益出发,同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予以外交承认,而只能二者择其一。1979年美国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与台北保持实质但非官方的关系,坚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既定原则,与两岸平衡 交往,对台海一旦发生战争时美方是否军事介入,采取“战略模糊”(strategic am bigu ity)的政策。近年美国 在处理台湾难题上的做法有了一些变化。如果说,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有关“三不”的表态与中方对李登辉 访美的强烈反弹有部分关联的话,那么,布什总统在2003年对台北领导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的示警, 则是为了防止岛内以“公投”和“宪改工程”为着力点的“独立”势头的持续发烧。四在华盛顿-北京-台北 三方的既定关系框架中,台北本是最不重要的角色,但近年来却采取了“以小搏大”,力图改变现状的进攻 谋略。台北的论述是,台湾无意改变现状:而所谓的现状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理应得到国际 承认,并在“宪政”的意义上予以“正名”。台北企图通过“外交”突破和自我宣示摆脱一中框架约束的冒 险举措,促使北京和华盛顿达成维护台海现状的默契。中方在福建沿海加强导弹部署,以此吓阻台独势头。 美方则推行一项积极外交(aggressive diplom acy)策略,反对台湾片面推进法理独立。 本文从政策演变的历史角度,考察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台湾难题,并以此推论其对台政策的未来走向。美 国对华对台政策的两难境地的根源何在?美国能否在台海事务中维持平衡交往和前后一致的政策?台海现 状能否得到维系?美国对台海战争的可能反应,是否已由战略模糊转为战略清晰(strateg ic clarity)?以下将 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 一、台湾难题之由来 台湾问题始终困扰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在中美建交之初,美国“认知”(acknow ledge)到中方有关世界上 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既定立场,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作者简介:林冈,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985工程”二期台湾研究创新基地成员。 ·45·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45· 台湾问题: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两难议题 林 冈*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030 ) 摘 要:台湾问题是困扰中美关系的一大难题。美国基于维护台湾海峡两岸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 利益考虑,试图对双方采取平衡交往的双轨政策。但这一政策却因美国国内不同利益团体的作用,选 举周期的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海峡两岸的政治角力,不时地受到冲击,发生周期性的变化。 美国对华政策的周期摇摆性,不利于维持台海现状。1995-1996 年的海峡危机和 2003-2004 年岛内公投、 制宪、正名风潮,与美方未能妥善处理台湾这一难题,给台北发出错误信号就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美国对台政策;两岸关系;中美关系;台湾难题;战略模糊;战略清晰;中程协议 中图分类号:D8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07)01-0045-06 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困扰中美关系的一大难题(dilemma)。对华盛顿来说,这一难题在于其不能从 美方的单方面利益出发,同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予以外交承认,而只能二者择其一。1979 年美国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与台北保持实质但非官方的关系,坚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既定原则,与两岸平衡 交往,对台海一旦发生战争时美方是否军事介入,采取“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的政策。近年美国 在处理台湾难题上的做法有了一些变化。如果说, 克林顿总统在 1998 年有关“三不”的表态与中方对李登辉 访美的强烈反弹有部分关联的话,那么,布什总统在 2003 年对台北领导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的示警, 则是为了防止岛内以“公投”和“宪改工程”为着力点的“独立”势头的持续发烧。[1]在华盛顿-北京-台北 三方的既定关系框架中,台北本是最不重要的角色,但近年来却采取了“以小搏大”,力图改变现状的进攻 谋略。台北的论述是,台湾无意改变现状;而所谓的现状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理应得到国际 承认,并在“宪政”的意义上予以“正名”。台北企图通过“外交”突破和自我宣示摆脱一中框架约束的冒 险举措,促使北京和华盛顿达成维护台海现状的默契。中方在福建沿海加强导弹部署,以此吓阻台独势头。 美方则推行一项积极外交(aggressive diplomacy)策略,反对台湾片面推进法理独立。 本文从政策演变的历史角度,考察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台湾难题,并以此推论其对台政策的未来走向。美 国对华对台政策的两难境地的根源何在?美国能否在台海事务中维持平衡交往和前后一致的政策?台海现 状能否得到维系?美国对台海战争的可能反应,是否已由战略模糊转为战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以下将 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 一、台湾难题之由来 台湾问题始终困扰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在中美建交之初,美国“认知”(acknowledge)到中方有关世界上 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既定立场,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 作者简介:林冈,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985 工程”二期台湾研究创新基地成员。 No.1 2007 General No.95 2007年第1期 (总第95期) 台湾研究集刊 TAIWAN RESEARCH QUARTER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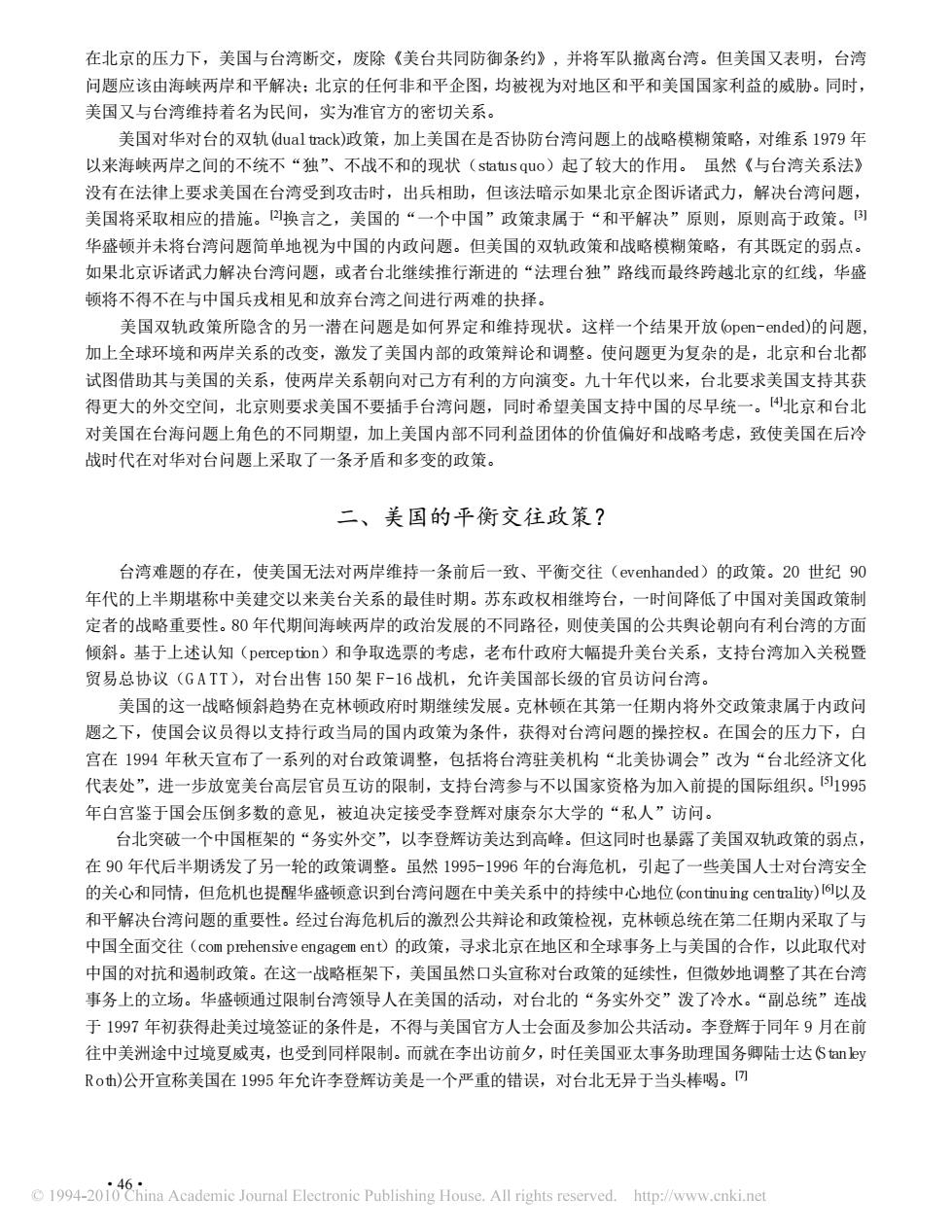
在北京的压力下,美国与台湾断交,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并将军队撒离台湾。但美国又表明,台湾 问题应该由海峡两岸和平解决:北京的任何非和平企图,均被视为对地区和平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同时, 美国又与台湾维持着名为民间,实为准官方的密切关系。 美国对华对台的双轨dual track)政策,加上美国在是否协防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策略,对维系l979年 以来海峡两岸之间的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现状(status quo)起了较大的作用。虽然《与台湾关系法》 没有在法律上要求美国在台湾受到攻击时,出兵相助,但该法暗示如果北京企图诉诸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美国将采取相应的措施。换言之,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隶属于“和平解决”原则,原则高于政策。) 华盛顿并未将台湾问题简单地视为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美国的双轨政策和战略模糊策略,有其既定的弱点。 如果北京诉诸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或者台北继续推行渐进的“法理台独”路线而最终跨越北京的红线,华盛 顿将不得不在与中国兵我相见和放弃台湾之间进行两难的抉择。 美国双轨政策所隐含的另一潜在问题是如何界定和维持现状。这样一个结果开放open-ended)的问题, 加上全球环境和两岸关系的改变,激发了美国内部的政策辩论和调整。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北京和台北都 试图借助其与美国的关系,使两岸关系朝向对己方有利的方向演变。九十年代以来,台北要求美国支持其获 得更大的外交空间,北京则要求美国不要插手台湾问题,同时希望美国支持中国的尽早统一。北京和台北 对美国在台海问题上角色的不同期望,加上美国内部不同利益团体的价值偏好和战略考虑,致使美国在后冷 战时代在对华对台问题上采取了一条矛盾和多变的政策。 二、美国的平衡交往政策? 台湾难题的存在,使美国无法对两岸维持一条前后一致、平衡交往(evenhanded)的政策。20世纪90 年代的上半期堪称中美建交以来美台关系的最佳时期。苏东政权相继垮台,一时间降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制 定者的战略重要性。80年代期间海峡两岸的政治发展的不同路径,则使美国的公共舆论朝向有利台湾的方面 倾斜。基于上述认知(perception)和争取选票的考虑,老布什政府大幅提升美台关系,支持台湾加入关税暨 贸易总协议(GATT),对台出售150架F-16战机,允许美国部长级的官员访问台湾。 美国的这一战略倾斜趋势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继续发展。克林顿在其第一任期内将外交政策隶属于内政问 题之下,使国会议员得以支持行政当局的国内政策为条件,获得对台湾问题的操控权。在国会的压力下,白 宫在1994年秋天宣布了一系列的对台政策调整,包括将台湾驻美机构“北美协调会”改为“台北经济文化 代表处”,进一步放宽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限制,支持台湾参与不以国家资格为加入前提的国际组织。1995 年白宫鉴于国会压倒多数的意见,被迫决定接受李登辉对康奈尔大学的“私人”访问。 台北突破一个中国框架的“务实外交”,以李登辉访美达到高峰。但这同时也暴露了美国双轨政策的弱点, 在90年代后半期诱发了另一轮的政策调整。虽然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引起了一些美国人士对台湾安全 的关心和同情,但危机也提醒华盛顿意识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持续中心地位(continu ing centrality).向以及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经过台海危机后的激烈公共辩论和政策检视,克林顿总统在第二任期内采取了与 中国全面交往(com prehensive engagem ent)的政策,寻求北京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与美国的合作,以此取代对 中国的对抗和遏制政策。在这一战略框架下,美国虽然口头宣称对台政策的延续性,但微妙地调整了其在台湾 事务上的立场。华盛顿通过限制台湾领导人在美国的活动,对台北的“务实外交”泼了冷水。“副总统”连战 于1997年初获得赴美过境签证的条件是,不得与美国官方人士会面及参加公共活动。李登辉于同年9月在前 往中美洲途中过境夏威夷,也受到同样限制。而就在李出访前夕,时任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陆士达Saey Ro)公开宣称美国在1995年允许李登辉访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台北无异于当头棒喝。可 46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46· 在北京的压力下,美国与台湾断交,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并将军队撤离台湾。但美国又表明,台湾 问题应该由海峡两岸和平解决;北京的任何非和平企图,均被视为对地区和平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同时, 美国又与台湾维持着名为民间,实为准官方的密切关系。 美国对华对台的双轨(dual track)政策,加上美国在是否协防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策略,对维系 1979 年 以来海峡两岸之间的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现状(status quo)起了较大的作用。 虽然《与台湾关系法》 没有在法律上要求美国在台湾受到攻击时,出兵相助,但该法暗示如果北京企图诉诸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美国将采取相应的措施。[2]换言之,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隶属于“和平解决”原则,原则高于政策。[3] 华盛顿并未将台湾问题简单地视为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美国的双轨政策和战略模糊策略,有其既定的弱点。 如果北京诉诸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或者台北继续推行渐进的“法理台独”路线而最终跨越北京的红线,华盛 顿将不得不在与中国兵戎相见和放弃台湾之间进行两难的抉择。 美国双轨政策所隐含的另一潜在问题是如何界定和维持现状。这样一个结果开放(open-ended)的问题, 加上全球环境和两岸关系的改变,激发了美国内部的政策辩论和调整。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北京和台北都 试图借助其与美国的关系,使两岸关系朝向对己方有利的方向演变。九十年代以来,台北要求美国支持其获 得更大的外交空间,北京则要求美国不要插手台湾问题,同时希望美国支持中国的尽早统一。[4]北京和台北 对美国在台海问题上角色的不同期望,加上美国内部不同利益团体的价值偏好和战略考虑,致使美国在后冷 战时代在对华对台问题上采取了一条矛盾和多变的政策。 二、美国的平衡交往政策? 台湾难题的存在,使美国无法对两岸维持一条前后一致、平衡交往(evenhanded)的政策。20 世纪 90 年代的上半期堪称中美建交以来美台关系的最佳时期。苏东政权相继垮台,一时间降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制 定者的战略重要性。80 年代期间海峡两岸的政治发展的不同路径,则使美国的公共舆论朝向有利台湾的方面 倾斜。基于上述认知(perception)和争取选票的考虑,老布什政府大幅提升美台关系,支持台湾加入关税暨 贸易总协议(GATT),对台出售 150 架 F-16 战机,允许美国部长级的官员访问台湾。 美国的这一战略倾斜趋势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继续发展。克林顿在其第一任期内将外交政策隶属于内政问 题之下,使国会议员得以支持行政当局的国内政策为条件,获得对台湾问题的操控权。在国会的压力下,白 宫在 1994 年秋天宣布了一系列的对台政策调整,包括将台湾驻美机构“北美协调会”改为“台北经济文化 代表处”,进一步放宽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限制,支持台湾参与不以国家资格为加入前提的国际组织。[5]1995 年白宫鉴于国会压倒多数的意见,被迫决定接受李登辉对康奈尔大学的“私人”访问。 台北突破一个中国框架的“务实外交”,以李登辉访美达到高峰。但这同时也暴露了美国双轨政策的弱点, 在 90 年代后半期诱发了另一轮的政策调整。虽然 1995-1996 年的台海危机,引起了一些美国人士对台湾安全 的关心和同情,但危机也提醒华盛顿意识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持续中心地位(continuing centrality) [6]以及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经过台海危机后的激烈公共辩论和政策检视,克林顿总统在第二任期内采取了与 中国全面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的政策,寻求北京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与美国的合作,以此取代对 中国的对抗和遏制政策。在这一战略框架下,美国虽然口头宣称对台政策的延续性,但微妙地调整了其在台湾 事务上的立场。华盛顿通过限制台湾领导人在美国的活动,对台北的“务实外交”泼了冷水。“副总统”连战 于 1997 年初获得赴美过境签证的条件是,不得与美国官方人士会面及参加公共活动。李登辉于同年 9 月在前 往中美洲途中过境夏威夷,也受到同样限制。而就在李出访前夕,时任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陆士达(Stanley Roth)公开宣称美国在 1995 年允许李登辉访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台北无异于当头棒喝。[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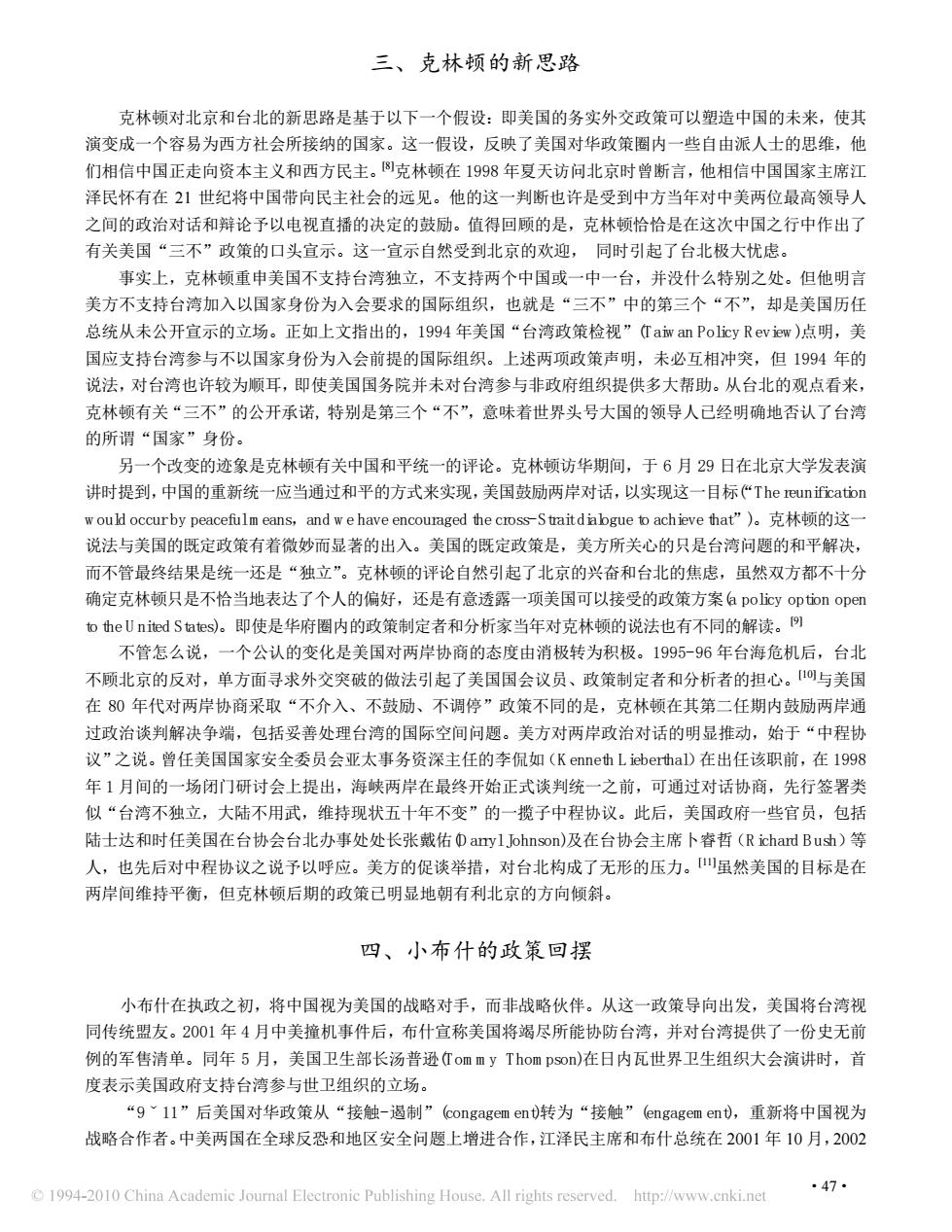
三、克林顿的新思路 克林顿对北京和台北的新思路是基于以下一个假设:即美国的务实外交政策可以塑造中国的未来,使其 演变成一个容易为西方社会所接纳的国家。这一假设,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圈内一些自由派人士的思维,他 们相信中国正走向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8克林顿在1998年夏天访问北京时曾断言,他相信中国国家主席江 泽民怀有在21世纪将中国带向民主社会的远见。他的这一判断也许是受到中方当年对中美两位最高领导人 之间的政治对话和辩论予以电视直播的决定的鼓励。值得回顾的是,克林顿恰恰是在这次中国之行中作出了 有关美国“三不”政策的口头宣示。这一宣示自然受到北京的欢迎,同时引起了台北极大忧虑。 事实上,克林顿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并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他明言 美方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身份为入会要求的国际组织,也就是“三不”中的第三个“不”,却是美国历任 总统从未公开宣示的立场。正如上文指出的,1994年美国“台湾政策检视”Taiw an Policy Rev iew)点明,美 国应支持台湾参与不以国家身份为入会前提的国际组织。上述两项政策声明,未必互相冲突,但1994年的 说法,对台湾也许较为顺耳,即使美国国务院并未对台湾参与非政府组织提供多大帮助。从台北的观点看来, 克林顿有关“三不”的公开承诺,特别是第三个“不”,意味着世界头号大国的领导人已经明确地否认了台湾 的所谓“国家”身份。 另一个改变的迹象是克林顿有关中国和平统一的评论。克林顿访华期间,于6月29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 讲时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应当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美国鼓励两岸对话,以实现这一目标(“The reun ification w ould occurby peacefulm eans,.and w e have encouraged the cross-Straitdiabgue to achieve that''”)。克林顿的这一 说法与美国的既定政策有着微妙而显著的出入。美国的既定政策是,美方所关心的只是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而不管最终结果是统一还是“独立”。克林顿的评论自然引起了北京的兴奋和台北的焦虑,虽然双方都不十分 确定克林顿只是不恰当地表达了个人的偏好,还是有意透露一项美国可以接受的政策方案a policy option open to the U nited States))。即使是华府圈内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当年对克林顿的说法也有不同的解读。) 不管怎么说,一个公认的变化是美国对两岸协商的态度由消极转为积极。1995-96年台海危机后,台北 不顾北京的反对,单方面寻求外交突破的做法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政策制定者和分析者的担心。©与美国 在80年代对两岸协商采取“不介入、不鼓励、不调停”政策不同的是,克林顿在其第二任期内鼓励两岸通 过政治谈判解决争端,包括妥善处理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美方对两岸政治对话的明显推动,始于“中程协 议”之说。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的李侃如(K enneth L ieberthal)在出任该职前,在l998 年1月间的一场闭门研讨会上提出,海峡两岸在最终开始正式谈判统一之前,可通过对话协商,先行签署类 似“台湾不独立,大陆不用武,维持现状五十年不变”的一揽子中程协议。此后,美国政府一些官员,包括 陆士达和时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张戴佑①anylJohnson)及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R ichard Bush)等 人,也先后对中程协议之说予以呼应。美方的促谈举措,对台北构成了无形的压力。山虽然美国的目标是在 两岸间维持平衡,但克林顿后期的政策已明显地朝有利北京的方向倾斜。 四、小布什的政策回摆 小布什在执政之初,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对手,而非战略伙伴。从这一政策导向出发,美国将台湾视 同传统盟友。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后,布什宣称美国将竭尽所能协防台湾,并对台湾提供了一份史无前 例的军售清单。同年5月,美国卫生部长汤普逊个om m y Thom pson)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演讲时,首 度表示美国政府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立场。 “9~I1”后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遏制”(congagem en t)转为“接触”(engagem ent),重新将中国视为 战略合作者。中美两国在全球反恐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增进合作,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在2001年10月,2002 ·47·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47· 三、克林顿的新思路 克林顿对北京和台北的新思路是基于以下一个假设:即美国的务实外交政策可以塑造中国的未来,使其 演变成一个容易为西方社会所接纳的国家。这一假设,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圈内一些自由派人士的思维,他 们相信中国正走向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8]克林顿在 1998 年夏天访问北京时曾断言,他相信中国国家主席江 泽民怀有在 21 世纪将中国带向民主社会的远见。他的这一判断也许是受到中方当年对中美两位最高领导人 之间的政治对话和辩论予以电视直播的决定的鼓励。值得回顾的是,克林顿恰恰是在这次中国之行中作出了 有关美国“三不”政策的口头宣示。这一宣示自然受到北京的欢迎, 同时引起了台北极大忧虑。 事实上,克林顿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并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他明言 美方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身份为入会要求的国际组织,也就是“三不”中的第三个“不”,却是美国历任 总统从未公开宣示的立场。正如上文指出的,1994 年美国“台湾政策检视”(Taiwan Policy Review)点明,美 国应支持台湾参与不以国家身份为入会前提的国际组织。上述两项政策声明,未必互相冲突,但 1994 年的 说法,对台湾也许较为顺耳,即使美国国务院并未对台湾参与非政府组织提供多大帮助。从台北的观点看来, 克林顿有关“三不”的公开承诺, 特别是第三个“不”,意味着世界头号大国的领导人已经明确地否认了台湾 的所谓“国家”身份。 另一个改变的迹象是克林顿有关中国和平统一的评论。克林顿访华期间,于 6 月 29 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 讲时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应当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美国鼓励两岸对话,以实现这一目标(“The reunification would occur by peaceful means,and we have encouraged the cross-Strait dialogue to achieve that”)。克林顿的这一 说法与美国的既定政策有着微妙而显著的出入。美国的既定政策是,美方所关心的只是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而不管最终结果是统一还是“独立”。克林顿的评论自然引起了北京的兴奋和台北的焦虑,虽然双方都不十分 确定克林顿只是不恰当地表达了个人的偏好,还是有意透露一项美国可以接受的政策方案(a policy option open to the United States)。即使是华府圈内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当年对克林顿的说法也有不同的解读。[9] 不管怎么说,一个公认的变化是美国对两岸协商的态度由消极转为积极。1995-96 年台海危机后,台北 不顾北京的反对,单方面寻求外交突破的做法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政策制定者和分析者的担心。[10]与美国 在 80 年代对两岸协商采取“不介入、不鼓励、不调停”政策不同的是,克林顿在其第二任期内鼓励两岸通 过政治谈判解决争端,包括妥善处理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美方对两岸政治对话的明显推动,始于“中程协 议”之说。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出任该职前,在 1998 年 1 月间的一场闭门研讨会上提出,海峡两岸在最终开始正式谈判统一之前,可通过对话协商,先行签署类 似“台湾不独立,大陆不用武,维持现状五十年不变”的一揽子中程协议。此后,美国政府一些官员,包括 陆士达和时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张戴佑(Darryl Johnson)及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等 人,也先后对中程协议之说予以呼应。美方的促谈举措,对台北构成了无形的压力。[11]虽然美国的目标是在 两岸间维持平衡,但克林顿后期的政策已明显地朝有利北京的方向倾斜。 四、小布什的政策回摆 小布什在执政之初,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对手,而非战略伙伴。从这一政策导向出发,美国将台湾视 同传统盟友。2001 年 4 月中美撞机事件后,布什宣称美国将竭尽所能协防台湾,并对台湾提供了一份史无前 例的军售清单。同年 5 月,美国卫生部长汤普逊(Tommy Thompson)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演讲时,首 度表示美国政府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立场。 “9ˇ11”后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遏制”(congagement)转为“接触”(engagement),重新将中国视为 战略合作者。中美两国在全球反恐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增进合作,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在 2001 年 10 月,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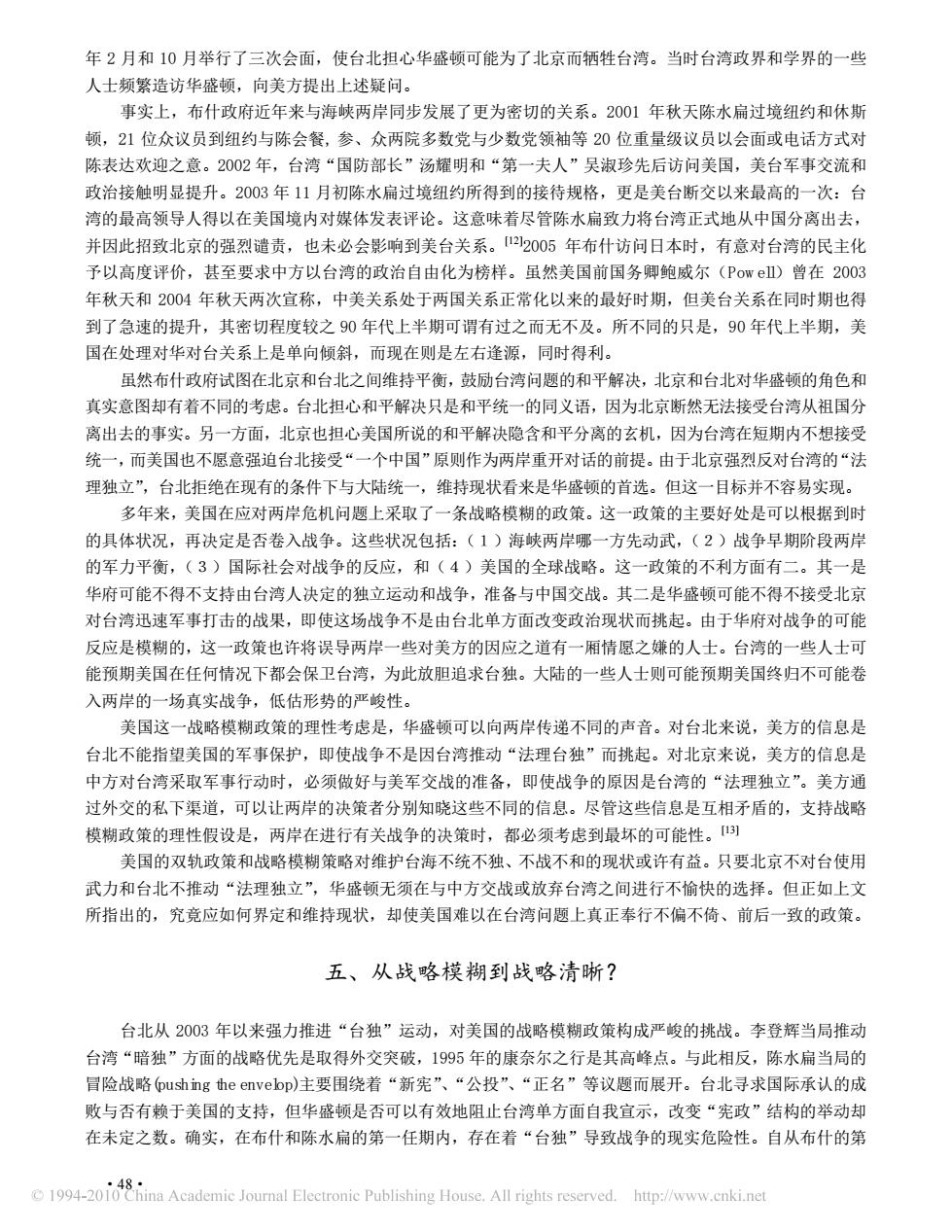
年2月和10月举行了三次会面,使台北担心华盛顿可能为了北京而牺牲台湾。当时台湾政界和学界的一些 人士频繁造访华盛顿,向美方提出上述疑问。 事实上,布什政府近年来与海峡两岸同步发展了更为密切的关系。2001年秋天陈水扁过境纽约和休斯 顿,21位众议员到纽约与陈会餐,参、众两院多数党与少数党领袖等20位重量级议员以会面或电话方式对 陈表达欢迎之意。2002年,台湾“国防部长”汤耀明和“第一夫人”吴淑珍先后访问美国,美台军事交流和 政治接触明显提升。2003年11月初陈水扁过境纽约所得到的接待规格,更是美台断交以来最高的一次:台 湾的最高领导人得以在美国境内对媒体发表评论。这意味着尽管陈水扁致力将台湾正式地从中国分离出去, 并因此招致北京的强烈谴责,也未必会影响到美台关系。22005年布什访问日本时,有意对台湾的民主化 予以高度评价,甚至要求中方以台湾的政治自由化为榜样。虽然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Pow)曾在2003 年秋天和2004年秋天两次宣称,中美关系处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好时期,但美台关系在同时期也得 到了急速的提升,其密切程度较之90年代上半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只是,90年代上半期,美 国在处理对华对台关系上是单向倾斜,而现在则是左右逢源,同时得利。 虽然布什政府试图在北京和台北之间维持平衡,鼓励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北京和台北对华盛顿的角色和 真实意图却有着不同的考虑。台北担心和平解决只是和平统一的同义语,因为北京断然无法接受台湾从祖国分 离出去的事实。另一方面,北京也担心美国所说的和平解决隐含和平分离的玄机,因为台湾在短期内不想接受 统一,而美国也不愿意强迫台北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重开对话的前提。由于北京强烈反对台湾的“法 理独立”,台北拒绝在现有的条件下与大陆统一,维持现状看来是华盛顿的首选。但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实现。 多年来,美国在应对两岸危机问题上采取了一条战略模糊的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好处是可以根据到时 的具体状况,再决定是否卷入战争。这些状况包括:(1)海峡两岸哪一方先动武,(2)战争早期阶段两岸 的军力平衡,(3)国际社会对战争的反应,和(4)美国的全球战略。这一政策的不利方面有二。其一是 华府可能不得不支持由台湾人决定的独立运动和战争,准备与中国交战。其二是华盛顿可能不得不接受北京 对台湾迅速军事打击的战果,即使这场战争不是由台北单方面改变政治现状而挑起。由于华府对战争的可能 反应是模糊的,这一政策也许将误导两岸一些对美方的因应之道有一厢情愿之嫌的人士。台湾的一些人士可 能预期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保卫台湾,为此放胆追求台独。大陆的一些人士则可能预期美国终归不可能卷 入两岸的一场真实战争,低估形势的严峻性。 美国这一战略模糊政策的理性考虑是,华盛顿可以向两岸传递不同的声音。对台北来说,美方的信息是 台北不能指望美国的军事保护,即使战争不是因台湾推动“法理台独”而挑起。对北京来说,美方的信息是 中方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时,必须做好与美军交战的准备,即使战争的原因是台湾的“法理独立”。美方通 过外交的私下渠道,可以让两岸的决策者分别知晓这些不同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是互相矛盾的,支持战略 模糊政策的理性假设是,两岸在进行有关战争的决策时,都必须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 美国的双轨政策和战略模糊策略对维护台海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现状或许有益。只要北京不对台使用 武力和台北不推动“法理独立”,华盛顿无须在与中方交战或放弃台湾之间进行不愉快的选择。但正如上文 所指出的,究竞应如何界定和维持现状,却使美国难以在台湾问题上真正奉行不偏不倚、前后一致的政策。 五、从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 台北从2003年以来强力推进“台独”运动,对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构成严峻的挑战。李登辉当局推动 台湾“暗独”方面的战略优先是取得外交突破,1995年的康奈尔之行是其高峰点。与此相反,陈水扁当局的 冒险战略push ing the envelop)主要围绕着“新宪”、“公投”、“正名”等议题而展开。台北寻求国际承认的成 败与否有赖于美国的支持,但华盛顿是否可以有效地阻止台湾单方面自我宣示,改变“宪政”结构的举动却 在未定之数。确实,在布什和陈水扁的第一任期内,存在着“台独”导致战争的现实危险性。自从布什的第 48·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48· 年 2 月和 10 月举行了三次会面,使台北担心华盛顿可能为了北京而牺牲台湾。当时台湾政界和学界的一些 人士频繁造访华盛顿,向美方提出上述疑问。 事实上,布什政府近年来与海峡两岸同步发展了更为密切的关系。2001 年秋天陈水扁过境纽约和休斯 顿,21 位众议员到纽约与陈会餐, 参、众两院多数党与少数党领袖等 20 位重量级议员以会面或电话方式对 陈表达欢迎之意。2002 年,台湾“国防部长”汤耀明和“第一夫人”吴淑珍先后访问美国,美台军事交流和 政治接触明显提升。2003 年 11 月初陈水扁过境纽约所得到的接待规格,更是美台断交以来最高的一次:台 湾的最高领导人得以在美国境内对媒体发表评论。这意味着尽管陈水扁致力将台湾正式地从中国分离出去, 并因此招致北京的强烈谴责,也未必会影响到美台关系。[12]2005 年布什访问日本时,有意对台湾的民主化 予以高度评价,甚至要求中方以台湾的政治自由化为榜样。虽然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Powell)曾在 2003 年秋天和 2004 年秋天两次宣称,中美关系处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好时期,但美台关系在同时期也得 到了急速的提升,其密切程度较之 90 年代上半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只是,90 年代上半期,美 国在处理对华对台关系上是单向倾斜,而现在则是左右逢源,同时得利。 虽然布什政府试图在北京和台北之间维持平衡,鼓励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北京和台北对华盛顿的角色和 真实意图却有着不同的考虑。台北担心和平解决只是和平统一的同义语,因为北京断然无法接受台湾从祖国分 离出去的事实。另一方面,北京也担心美国所说的和平解决隐含和平分离的玄机,因为台湾在短期内不想接受 统一,而美国也不愿意强迫台北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重开对话的前提。由于北京强烈反对台湾的“法 理独立”,台北拒绝在现有的条件下与大陆统一,维持现状看来是华盛顿的首选。但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实现。 多年来,美国在应对两岸危机问题上采取了一条战略模糊的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好处是可以根据到时 的具体状况,再决定是否卷入战争。这些状况包括:(1)海峡两岸哪一方先动武,(2)战争早期阶段两岸 的军力平衡,(3)国际社会对战争的反应,和(4)美国的全球战略。这一政策的不利方面有二。其一是 华府可能不得不支持由台湾人决定的独立运动和战争,准备与中国交战。其二是华盛顿可能不得不接受北京 对台湾迅速军事打击的战果,即使这场战争不是由台北单方面改变政治现状而挑起。由于华府对战争的可能 反应是模糊的,这一政策也许将误导两岸一些对美方的因应之道有一厢情愿之嫌的人士。台湾的一些人士可 能预期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保卫台湾,为此放胆追求台独。大陆的一些人士则可能预期美国终归不可能卷 入两岸的一场真实战争,低估形势的严峻性。 美国这一战略模糊政策的理性考虑是,华盛顿可以向两岸传递不同的声音。对台北来说,美方的信息是 台北不能指望美国的军事保护,即使战争不是因台湾推动“法理台独”而挑起。对北京来说,美方的信息是 中方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时,必须做好与美军交战的准备,即使战争的原因是台湾的“法理独立”。美方通 过外交的私下渠道,可以让两岸的决策者分别知晓这些不同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是互相矛盾的,支持战略 模糊政策的理性假设是,两岸在进行有关战争的决策时,都必须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13] 美国的双轨政策和战略模糊策略对维护台海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现状或许有益。只要北京不对台使用 武力和台北不推动“法理独立”,华盛顿无须在与中方交战或放弃台湾之间进行不愉快的选择。但正如上文 所指出的,究竟应如何界定和维持现状,却使美国难以在台湾问题上真正奉行不偏不倚、前后一致的政策。 五、从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 台北从 2003 年以来强力推进“台独”运动,对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构成严峻的挑战。李登辉当局推动 台湾“暗独”方面的战略优先是取得外交突破,1995 年的康奈尔之行是其高峰点。与此相反,陈水扁当局的 冒险战略(pushing the envelop)主要围绕着“新宪”、“公投”、“正名”等议题而展开。台北寻求国际承认的成 败与否有赖于美国的支持,但华盛顿是否可以有效地阻止台湾单方面自我宣示,改变“宪政”结构的举动却 在未定之数。确实,在布什和陈水扁的第一任期内,存在着“台独”导致战争的现实危险性。自从布什的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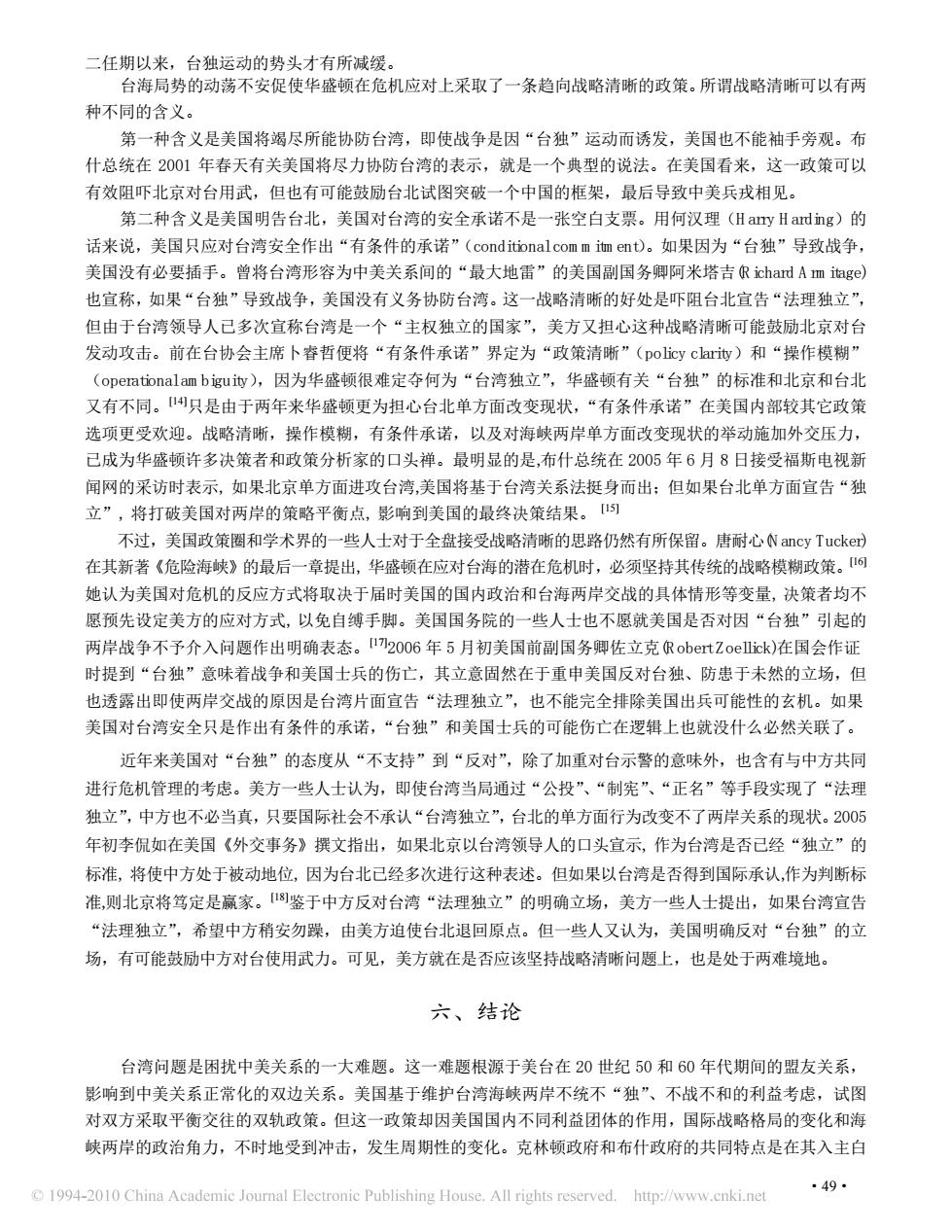
二任期以来,台独运动的势头才有所减缓。 台海局势的动荡不安促使华盛顿在危机应对上采取了一条趋向战略清晰的政策。所谓战略清晰可以有两 种不同的含义。 第一种含义是美国将竭尽所能协防台湾,即使战争是因“台独”运动而诱发,美国也不能袖手旁观。布 什总统在2001年春天有关美国将尽力协防台湾的表示,就是一个典型的说法。在美国看来,这一政策可以 有效阻吓北京对台用武,但也有可能鼓励台北试图突破一个中国的框架,最后导致中美兵戎相见。 第二种含义是美国明告台北,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不是一张空白支票。用何汉理(Hany Harding)的 话来说,美国只应对台湾安全作出“有条件的承诺”(conditionalcom m itm ent)。如果因为“台独”导致战争, 美国没有必要插手。曾将台湾形容为中美关系间的“最大地雷”的美国副国务卿阿米塔吉尔ichard A m it恤ge) 也宣称,如果“台独”导致战争,美国没有义务协防台湾。这一战略清晰的好处是吓阻台北宣告“法理独立”, 但由于台湾领导人己多次宣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美方又担心这种战略清晰可能鼓励北京对台 发动攻击。前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便将“有条件承诺”界定为“政策清晰”(policy clarit)和“操作模糊” (operationalam biguity),因为华盛顿很难定夺何为“台湾独立”,华盛顿有关“台独”的标准和北京和台北 又有不同。4只是由于两年来华盛顿更为担心台北单方面改变现状,“有条件承诺”在美国内部较其它政策 选项更受欢迎。战略清晰,操作模糊,有条件承诺,以及对海峡两岸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举动施加外交压力, 己成为华盛顿许多决策者和政策分析家的口头禅。最明显的是,布什总统在2005年6月8日接受福斯电视新 闻网的采访时表示,如果北京单方面进攻台湾,美国将基于台湾关系法挺身而出:但如果台北单方面宣告“独 立”,将打破美国对两岸的策略平衡点,影响到美国的最终决策结果。[) 不过,美国政策圈和学术界的一些人士对于全盘接受战略清晰的思路仍然有所保留。唐耐心N ancy Tucker 在其新著《危险海峡》的最后一章提出,华盛顿在应对台海的潜在危机时,必须坚持其传统的战略模糊政策。( 她认为美国对危机的反应方式将取决于届时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台海两岸交战的具体情形等变量,决策者均不 愿预先设定美方的应对方式,以免自缚手脚。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人士也不愿就美国是否对因“台独”引起的 两岸战争不予介入问题作出明确表态。12006年5月初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尔obertZoellick)在国会作证 时提到“台独”意味着战争和美国士兵的伤亡,其立意固然在于重申美国反对台独、防患于未然的立场,但 也透露出即使两岸交战的原因是台湾片面宣告“法理独立”,也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出兵可能性的玄机。如果 美国对台湾安全只是作出有条件的承诺,“台独”和美国士兵的可能伤亡在逻辑上也就没什么必然关联了。 近年来美国对“台独”的态度从“不支持”到“反对”,除了加重对台示警的意味外,也含有与中方共同 进行危机管理的考虑。美方一些人士认为,即使台湾当局通过“公投”、“制宪”、“正名”等手段实现了“法理 独立”,中方也不必当真,只要国际社会不承认“台湾独立”,台北的单方面行为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现状。2005 年初李侃如在美国《外交事务》撰文指出,如果北京以台湾领导人的口头宣示,作为台湾是否已经“独立”的 标准,将使中方处于被动地位,因为台北已经多次进行这种表述。但如果以台湾是否得到国际承认,作为判断标 准,则北京将笃定是赢家。8鉴于中方反对台湾“法理独立”的明确立场,美方一些人士提出,如果台湾宣告 “法理独立”,希望中方稍安勿躁,由美方迫使台北退回原点。但一些人又认为,美国明确反对“台独”的立 场,有可能鼓励中方对台使用武力。可见,美方就在是否应该坚持战略清晰问题上,也是处于两难境地。 六、结论 台湾问题是困扰中美关系的一大难题。这一难题根源于美台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期间的盟友关系, 影响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双边关系。美国基于维护台湾海峡两岸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利益考虑,试图 对双方采取平衡交往的双轨政策。但这一政策却因美国国内不同利益团体的作用,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海 峡两岸的政治角力,不时地受到冲击,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共同特点是在其入主白 ·49·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49· 二任期以来,台独运动的势头才有所减缓。 台海局势的动荡不安促使华盛顿在危机应对上采取了一条趋向战略清晰的政策。所谓战略清晰可以有两 种不同的含义。 第一种含义是美国将竭尽所能协防台湾,即使战争是因“台独”运动而诱发,美国也不能袖手旁观。布 什总统在 2001 年春天有关美国将尽力协防台湾的表示,就是一个典型的说法。在美国看来,这一政策可以 有效阻吓北京对台用武,但也有可能鼓励台北试图突破一个中国的框架,最后导致中美兵戎相见。 第二种含义是美国明告台北,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不是一张空白支票。用何汉理(Harry Harding)的 话来说,美国只应对台湾安全作出“有条件的承诺”(conditional commitment)。如果因为“台独”导致战争, 美国没有必要插手。曾将台湾形容为中美关系间的“最大地雷”的美国副国务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 也宣称,如果“台独”导致战争,美国没有义务协防台湾。这一战略清晰的好处是吓阻台北宣告“法理独立”, 但由于台湾领导人已多次宣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美方又担心这种战略清晰可能鼓励北京对台 发动攻击。前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便将“有条件承诺”界定为“政策清晰”(policy clarity)和“操作模糊” (operational ambiguity),因为华盛顿很难定夺何为“台湾独立”,华盛顿有关“台独”的标准和北京和台北 又有不同。[14]只是由于两年来华盛顿更为担心台北单方面改变现状,“有条件承诺”在美国内部较其它政策 选项更受欢迎。战略清晰,操作模糊,有条件承诺,以及对海峡两岸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举动施加外交压力, 已成为华盛顿许多决策者和政策分析家的口头禅。最明显的是,布什总统在 2005 年 6 月 8 日接受福斯电视新 闻网的采访时表示, 如果北京单方面进攻台湾,美国将基于台湾关系法挺身而出;但如果台北单方面宣告“独 立”, 将打破美国对两岸的策略平衡点, 影响到美国的最终决策结果。 [15] 不过,美国政策圈和学术界的一些人士对于全盘接受战略清晰的思路仍然有所保留。唐耐心(Nancy Tucker) 在其新著《危险海峡》的最后一章提出, 华盛顿在应对台海的潜在危机时,必须坚持其传统的战略模糊政策。[16] 她认为美国对危机的反应方式将取决于届时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台海两岸交战的具体情形等变量, 决策者均不 愿预先设定美方的应对方式, 以免自缚手脚。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人士也不愿就美国是否对因“台独”引起的 两岸战争不予介入问题作出明确表态。[17]2006 年 5 月初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在国会作证 时提到“台独”意味着战争和美国士兵的伤亡,其立意固然在于重申美国反对台独、防患于未然的立场,但 也透露出即使两岸交战的原因是台湾片面宣告“法理独立”,也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出兵可能性的玄机。如果 美国对台湾安全只是作出有条件的承诺,“台独”和美国士兵的可能伤亡在逻辑上也就没什么必然关联了。 近年来美国对“台独”的态度从“不支持”到“反对”,除了加重对台示警的意味外,也含有与中方共同 进行危机管理的考虑。美方一些人士认为,即使台湾当局通过“公投”、“制宪”、“正名”等手段实现了“法理 独立”,中方也不必当真,只要国际社会不承认“台湾独立”,台北的单方面行为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现状。2005 年初李侃如在美国《外交事务》撰文指出,如果北京以台湾领导人的口头宣示, 作为台湾是否已经“独立”的 标准, 将使中方处于被动地位, 因为台北已经多次进行这种表述。但如果以台湾是否得到国际承认,作为判断标 准,则北京将笃定是赢家。[18]鉴于中方反对台湾“法理独立”的明确立场,美方一些人士提出,如果台湾宣告 “法理独立”,希望中方稍安勿躁,由美方迫使台北退回原点。但一些人又认为,美国明确反对“台独”的立 场,有可能鼓励中方对台使用武力。可见,美方就在是否应该坚持战略清晰问题上,也是处于两难境地。 六、结论 台湾问题是困扰中美关系的一大难题。这一难题根源于美台在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期间的盟友关系, 影响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双边关系。美国基于维护台湾海峡两岸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利益考虑,试图 对双方采取平衡交往的双轨政策。但这一政策却因美国国内不同利益团体的作用,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海 峡两岸的政治角力,不时地受到冲击,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共同特点是在其入主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