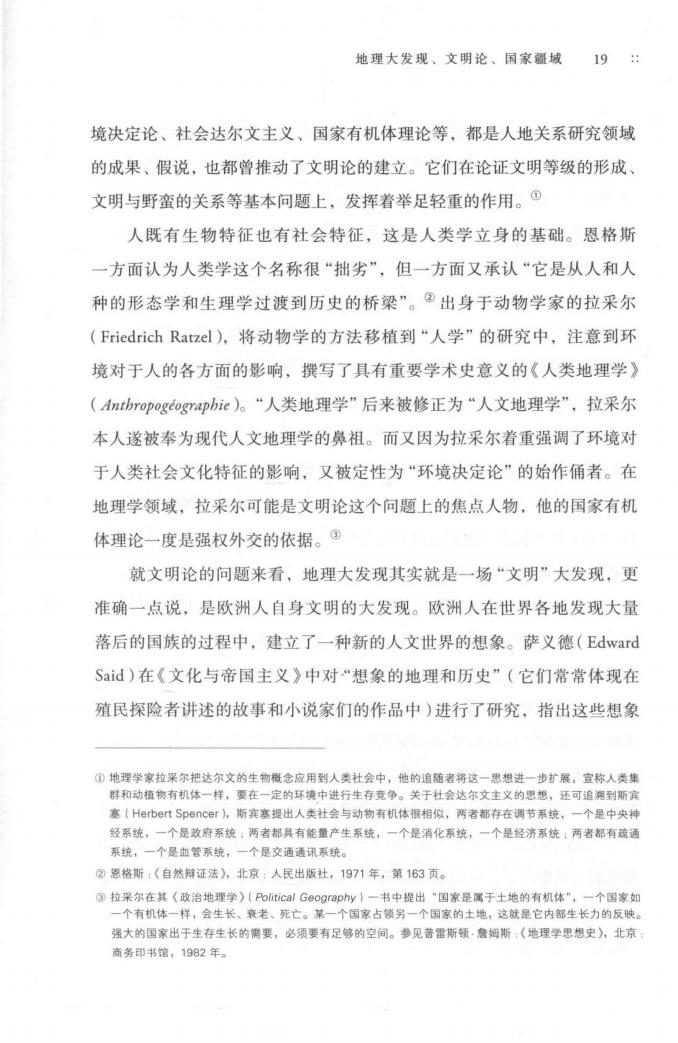
地理大发现、文明论、国家疆域19 境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有机体理论等,都是人地关系研究领域 的成果、假说,也都曾推动了文明论的建立。它们在论证文明等级的形成、 文明与野蛮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既有生物特征也有社会特征,这是人类学立身的基础。恩格斯 一方面认为人类学这个名称很“拙劣”,但一方面又承认“它是从人和人 种的形态学和生理学过渡到历史的桥梁”。®出身于动物学家的拉采尔 (Friedrich Ratzel),将动物学的方法移植到“人学”的研究中,注意到环 境对于人的各方面的影响,撰写了具有重要学术史意义的《人类地理学》 (nthropogeographie)。“人类地理学”后来被修正为“人文地理学”,拉采尔 本人遂被奉为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鼻祖。而又因为拉采尔着重强调了环境对 于人类社会文化特征的影响,又被定性为“环境决定论”的始作俑者。在 地理学领域,拉采尔可能是文明论这个问题上的焦点人物,他的国家有机 体理论一度是强权外交的依据。⑧ 就文明论的问题来看,地理大发现其实就是一场“文明”大发现,更 准确一点说,是欧洲人自身文明的大发现。欧洲人在世界各地发现大量 落后的国族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新的人文世界的想象。萨义德(Edward Sad)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对“想象的地理和历史”(它们常常体现在 殖民探险者讲述的故事和小说家们的作品中)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想象 ①地理学家拉采尔把达尔文的生物概念应用到人类社会中,他的追随者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扩展,宜称人类集 群和动植物有机体一样,要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生存竞争。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还可追痛到斯宾 寒【Herbert Spencer),斯宾寒提出人类社会与动物有机体很相似,两者都存在调节系统,一个是中央神 经系统,一个是政府系统:两者都具有能量产生系统,一个是消化系统,一个是经济系统:两者都有疏通 系统,一个是血管系统,一个是交通通讯系统。 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63页。 ③拉采尔在其(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一书中提出“国家是属于土地的有机体”,一个国家如 一个有机体一样,会生长、衰老、死亡。某一个国家占领另一个国家的土地,这就是它内部生长力的反映。 强大的国家出于生存生长的需要,必须要有足够的空间。参见普雷斯领,雕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年

20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 会通过把本土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夸张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欧洲 人虽然在波涛汹涌的大洋上历尽艰辛,但这些“发现”的成就以及由此产 生的对于人类世界的新的想象,令他们对自身鹤立鸡群的感觉是何等之好。 反之,“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存在的方式”。⊙ 殖民地的人民,在威武强大的欧洲船舰面前,确认了自己的野蛮与落后。 于是,一部新的世界历史被掀开,一类新的民族国家关系被建立。 随着文明一野蛮(未开化)这一对概念的普遍运用,将世界整理为文 明差异进而是文明等级的思想理论迅速发展。这个逐步形成的更具普遍意 义的新型文明一野蛮理论,依托新的全球地理观,而将整个人文空间时间 化、历史化。人类社会的空间多样性是固有的,而在进化理论(进步主义) 中,将空间差异整理为时间(历史)差异,即文明进化程度的差异。(人 类学家、社会学家总结的几大社会形态被理解为全人类必然履行的历史过 程。)人类社会似乎没有真正的空间差异,而只有时间(进化)差异。文明 理论是一种新的历史眼光。 虽然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并不是一个新的观念意识,在古代中国、古代 罗马都曾流行“华夷之辨”、“文野之辨”之类的观念。然而,此时的文明一 野蛮分野与古典的文野之辨有着十分不同的内涵和结论。古典的文野之辨, 文明一方对于野蛮一方,除了要“怀柔远人”、“边境晏安”之外,基本别 无所求,更恨不得以长城永久隔限其往来(中国和罗马帝国都修过长城)。 而此时的文明一方对于野蛮一方,却要侵入、统治、剥夺。马克思、恩格 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经济的角度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 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 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所有支那长城、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前言”第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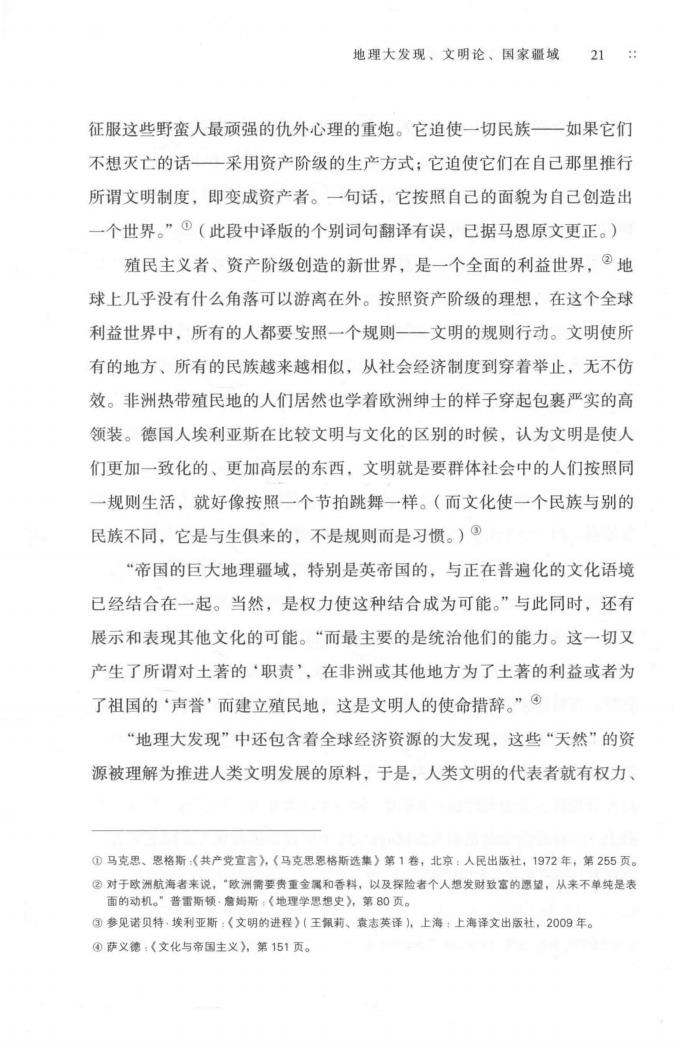
地理大发现、文明论、国家疆域21 征服这些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一如果它们 不想灭亡的话一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 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 一个世界。”①(此段中译版的个别词句翻译有误,已据马恩原文更正。) 殖民主义者、资产阶级创造的新世界,是一个全面的利益世界,®地 球上几乎没有什么角落可以游离在外。按照资产阶级的理想,在这个全球 利益世界中,所有的人都要安照一个规则一文明的规则行动。文明使所 有的地方、所有的民族越来越相似,从社会经济制度到穿着举止,无不仿 效。非洲热带殖民地的人们居然也学着欧洲绅士的样子穿起包裹严实的高 领装。德国人埃利亚斯在比较文明与文化的区别的时候,认为文明是使人 们更加一致化的、更加高层的东西,文明就是要群体社会中的人们按照同 一规则生活,就好像按照一个节拍跳舞一样。(而文化使一个民族与别的 民族不同,它是与生俱来的,不是规则而是习惯。)© “帝国的巨大地理疆域,特别是英帝国的,与正在普遍化的文化语境 已经结合在一起。当然,是权力使这种结合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还有 展示和表现其他文化的可能。“而最主要的是统治他们的能力。这一切又 产生了所谓对土著的‘职责’,在非洲或其他地方为了土著的利益或者为 了祖国的‘声誉’而建立殖民地,这是文明人的使命措辞。”© “地理大发现”中还包含着全球经济资源的大发现,这些“天然”的资 源被理解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原料,于是,人类文明的代表者就有权力、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5页。 ②对于欧洲航海者来说,“欧洲需要贵重金属和香料,以及探险者个人想发财致富的哪望,从来不单纯是表 面的动机。”普雷斯顿·詹蝠斯:《地理学思想史),第80页。 ③参见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王佩莉、囊志英译),上海:上海泽文出版社,2009年。 ①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第1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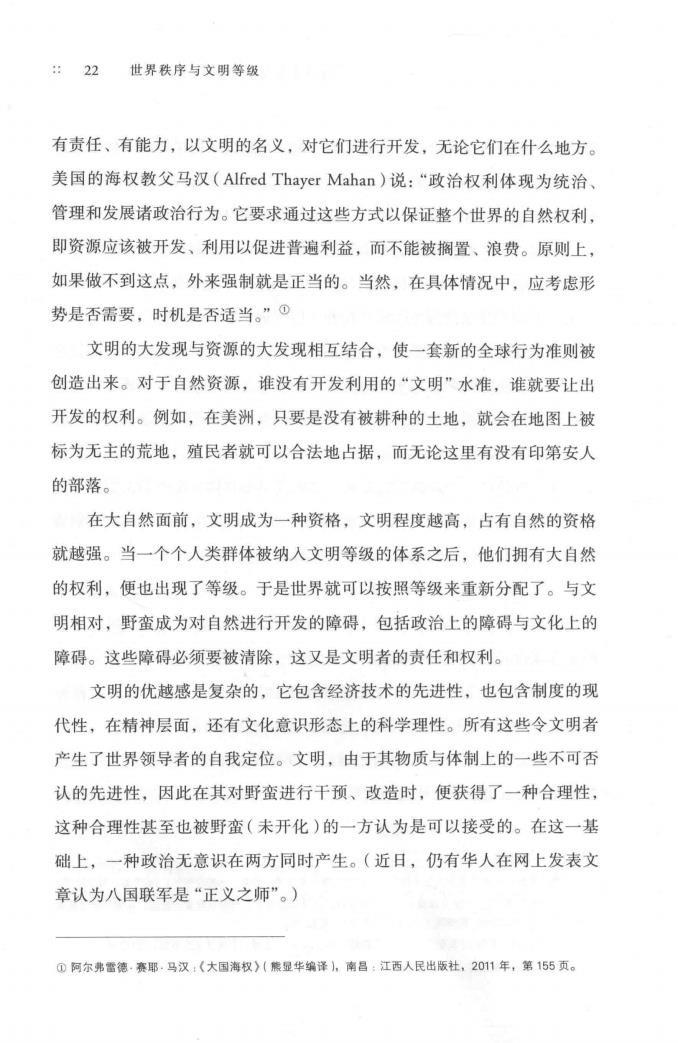
:22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 有责任、有能力,以文明的名义,对它们进行开发,无论它们在什么地方。 美国的海权教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说:“政治权利体现为统治、 管理和发展诸政治行为。它要求通过这些方式以保证整个世界的自然权利, 即资源应该被开发、利用以促进普遍利益,而不能被搁置、浪费。原则上, 如果做不到这点,外来强制就是正当的。当然,在具体情况中,应考虑形 势是否需要,时机是否适当。”⊙ 文明的大发现与资源的大发现相互结合,使一套新的全球行为准则被 创造出来。对于自然资源,谁没有开发利用的“文明”水准,谁就要让出 开发的权利。例如,在美洲,只要是没有被耕种的土地,就会在地图上被 标为无主的荒地,殖民者就可以合法地占据,而无论这里有没有印第安人 的部落。 在大自然面前,文明成为一种资格,文明程度越高,占有自然的资格 就越强。当一个个人类群体被纳入文明等级的体系之后,他们拥有大自然 的权利,便也出现了等级。于是世界就可以按照等级来重新分配了。与文 明相对,野蛮成为对自然进行开发的障碍,包括政治上的障碍与文化上的 障碍。这些障碍必须要被清除,这又是文明者的责任和权利。 文明的优越感是复杂的,它包含经济技术的先进性,也包含制度的现 代性,在精神层面,还有文化意识形态上的科学理性。所有这些令文明者 产生了世界领导者的自我定位。文明,由于其物质与体制上的一些不可否 认的先进性,因此在其对野蛮进行干预、改造时,便获得了一种合理性, 这种合理性甚至也被野蛮(未开化)的一方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在这一基 础上,一种政治无意识在两方同时产生。(近日,仍有华人在网上发表文 章认为八国联军是“正义之师”。) ①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大国海权)(熊显华编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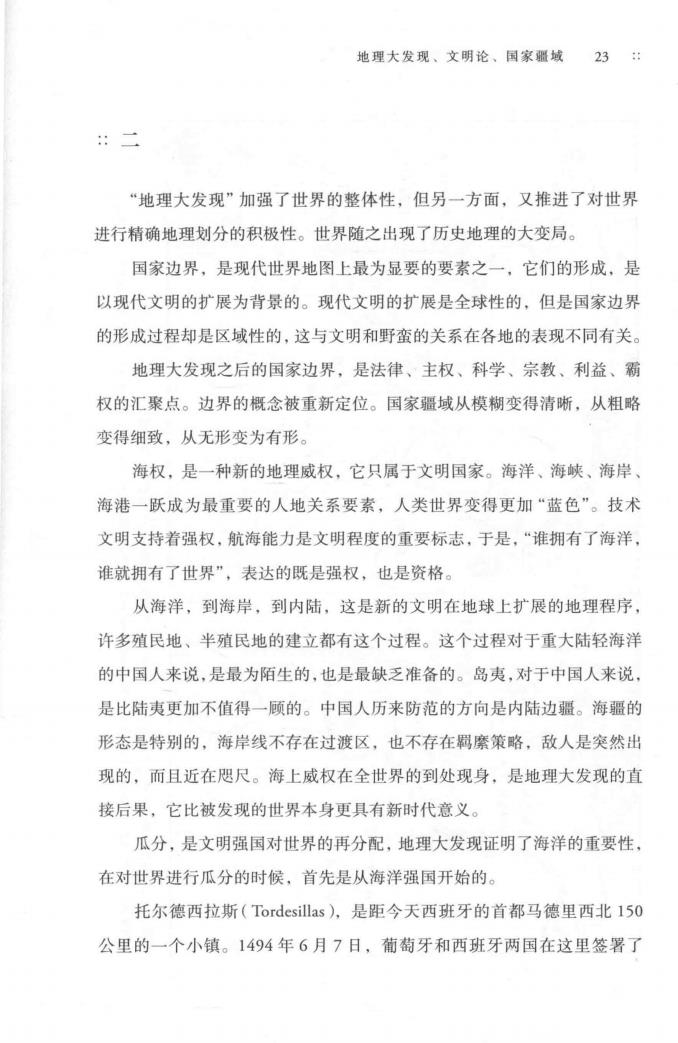
地理大发现、文明论、国家疆域 23 ∷二 “地理大发现”加强了世界的整体性,但另一方面,又推进了对世界 进行精确地理划分的积极性。世界随之出现了历史地理的大变局。 国家边界,是现代世界地图上最为显要的要素之一,它们的形成,是 以现代文明的扩展为背景的。现代文明的扩展是全球性的,但是国家边界 的形成过程却是区域性的,这与文明和野蛮的关系在各地的表现不同有关。 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国家边界,是法律、主权、科学、宗教、利益、霸 权的汇聚点。边界的概念被重新定位。国家疆域从模糊变得清晰,从粗略 变得细致,从无形变为有形。 海权,是一种新的地理威权,它只属于文明国家。海洋、海峡、海岸、 海港一跃成为最重要的人地关系要素,人类世界变得更加“蓝色”。技术 文明支持着强权,航海能力是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于是,“谁拥有了海洋, 谁就拥有了世界”,表达的既是强权,也是资格。 从海洋,到海岸,到内陆,这是新的文明在地球上扩展的地理程序, 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建立都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对于重大陆轻海洋 的中国人来说,是最为陌生的,也是最缺乏准备的。岛夷,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比陆夷更加不值得一顾的。中国人历来防范的方向是内陆边疆。海疆的 形态是特别的,海岸线不存在过渡区,也不存在羁縻策略,敌人是突然出 现的,而且近在咫尺。海上威权在全世界的到处现身,是地理大发现的直 接后果,它比被发现的世界本身更具有新时代意义。 瓜分,是文明强国对世界的再分配,地理大发现证明了海洋的重要性, 在对世界进行瓜分的时候,首先是从海洋强国开始的。 托尔德西拉斯(Tordesillas),是距今天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西北150 公里的一个小镇。1494年6月7日,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在这里签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