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版序言 对于一个几乎毕生都在从事比较政治与法律制度研究 的作者来说,看到自已的著作被翻译出版,因而使得一批新 的读者能够阅读,那真是对他的最大奖赏。当我为英语读 者所进行的比较由来自不同文化区域的学者观察时,必然 会被赋予一种新的意义;对于新的读者来说,我所使用的某 些方法或许是陌生的。 就本书而言情况尤为如此,因为它主要不是写给那些 博学的专家(尽管他们有国别差异,但却都属于一个拥有共 同概念的学者群体)阅读的,它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法律学与 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至少在美国,本书并没有试图为法 学院的大学生们提供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需要其备的 实用知识。相对而言,这些大学生中极少有人研究外国法 律制度,只是那些准备从事某些特殊法律职业的学生方对 他们感兴趣的外国实体法律制度加以研究,我的这本书试 图在法律科学的一个部门,即法律社会学领域内进行一些 开掘,在一段时间里,无论是法学院,还是政治学系,都忽略 了这门学问,尤其是当其课程设置主要是为了培养和提高 ▣13

比较法律文化 学生的职业技能的时候。 本书始于这样一个假定(它不仅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接 受),即法律与政治是相互依赖的,要对二者有真切的理解 有关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知识是不可缺少的。在第一章里 我解释了为什么我相信与政治文化相类似的法律文化概念 对于从比较的角度阐明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富于 成果的。 在中国,法学研究的复兴,法律教育的高速发展以及中 国与外国学者及法律家之间不断扩大的交往都是近十年间 引人注目的变化。如果本书能为中国的法律学生开阔视野 有所贡献,那将是我最大的满足。近年来颁行的法典和法 规构成了中国崭新的制度与法律结构,新一代学生的使命 就在于赋予它们以勃勒生机。比较研究永远不应该导致盲 目地模仿外国的模式。但是,对外国的积极或消极经验的 全面了解以及客观评价却很有必要,它将有助于人们分析 在自己国家中所通到的一些问题。 无论何时何地,法律的发展都不会完全停滞不前。要 紧跟制度的变化,并对演进中的时代精神(Zeitgeist),也就 是使制度得以操作的那种精神予以准确的评价,像本书这 类著作就必须不停地修订。在某些时候,不同国家间的法 律文化会呈现出愈来愈大的差异,而在另一些时候,它们之 间的趋同性又会十分明显。但是在这本19?4年即中国的 .14

中文版序曹 “文化大革命”时代写的书所涉及到的国家中,没有哪个发 生过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剧烈而意义深远的变化。在过 去的10年中,我总是要向阅读我这本书的学生们声明,书 中关于中国法的论述大多已与现实不符,甚至我在书中的 尝试性结论:“至少在目前,中国的法律文化的确是自成一 格的。”也颠值得怀疑了。对于中文版来说,这要引出相当 多的问题。两位译者和我都同意不对原文的内容邮以改 变。因为整本书中相当多的地方涉及社会主义以前,以及 1949年以后阶段的中国法律,它们都需要参照“文化大革 命”以来所发生的事件面加以修正。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势 必要打破全书的结构。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这里有必要简略地谈一下我作为 一个外国学者、一个远非中国法律专家的比较法学者对这 本书出版以来的新发展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绝不是对 今日中国法律生活与制度的一个全面的,甚至也算不得是 一种批评性论述。我只是试图运用比较法律文化的功能的 和历史的方法(如同本书所使用的那样)来估价目前变化的 主要趋势。 “文化大革命”中,成文法典的废奔以及“资产阶级法律 机构”的摧毁给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提供 了一次繼痛的法律教育。那个时代向人们表明,要实现现 代化,法律制度是保证实现社会、经济目标所绝对必须、不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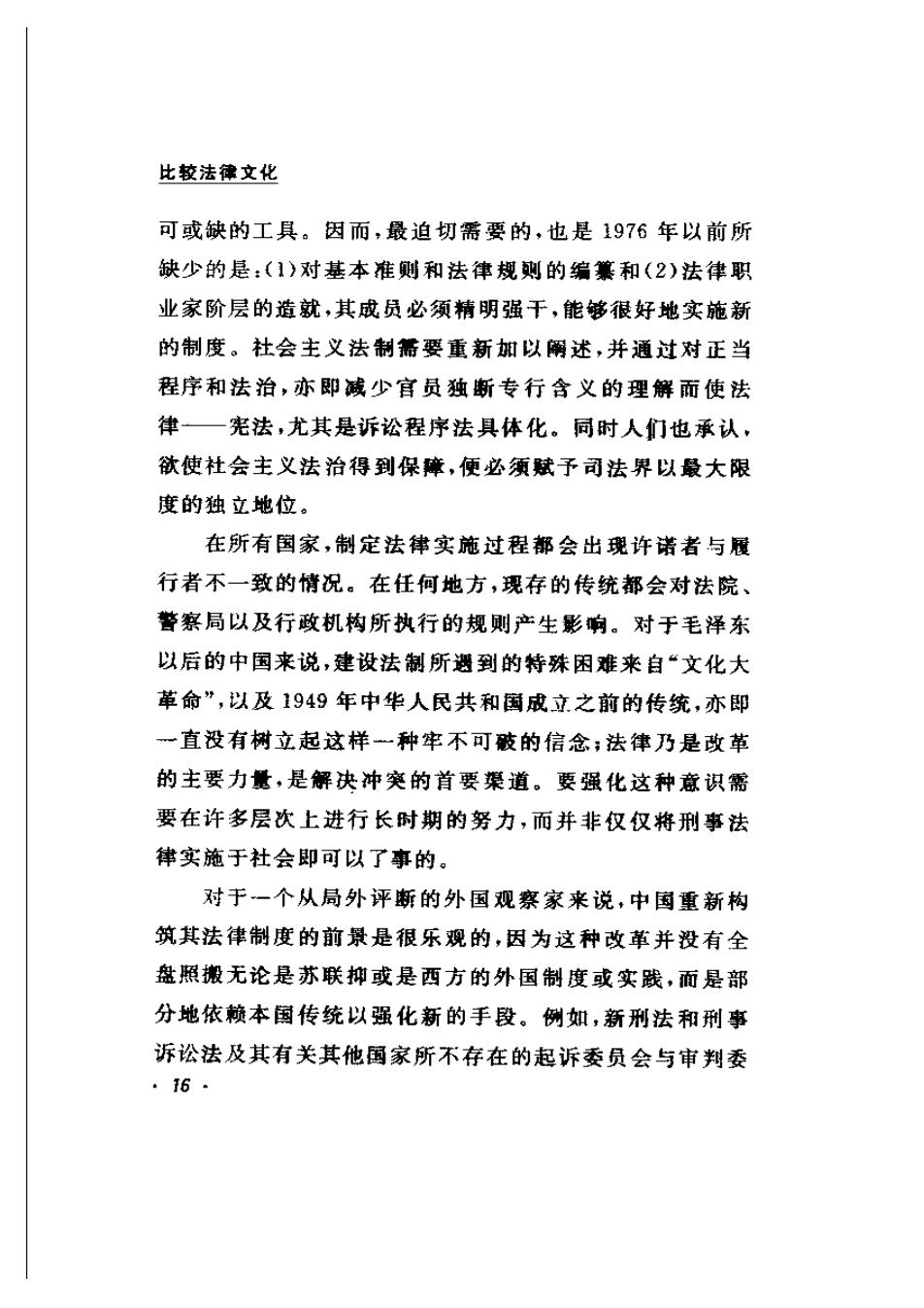
比较法律文化 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最迫切需要的,也是1976年以前所 缺少的是:(1)对基本准则和法律规则的编纂和(2)法律职 业家阶层的造就,其成员必须精明强干,能够很好地实施新 的制度。杜会主义法制篇要重新加以丽述,并通过对正当 程序和法治,亦即诚少官员独断专行含义的理解而使法 律一宪法,尤其是诉讼程序法具体化。同时人们也承认 欲使杜会主义法治得到保摩,便必须赋予司法界以最大限 度的独立地位。 在所有国家,制定法律实施过程都会出现许诺者与履 行者不一致的情况。在任何地方,现存的传统都会对法院、 普察局以及行政机构所执行的规则产生影响。对于毛泽东 以后的中国来说,建设法制所遇到的特殊困难来自“文化大 革命”,以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传统,亦即 一直没有树立起这样一种牢不可破的信念:法律乃是改革 的主要力量,是解决冲突的首要渠道。要强化这种意识需 要在许多层次上进行长时期的努力,而并非仅仅将刑事法 律实施于社会即可以了事的。 对于一个从局外评断的外国观察家来说,中国重新构 筑其法律制度的前景是很乐观的,因为这种改革并没有全 盘照搬无论是苏联抑或是西方的外国制度或实践,而是部 分地依赖本国传统以强化新的手段。例如,新刑法和刑事 诉讼法及其有关其他国家所不存在的起诉委员会与审判委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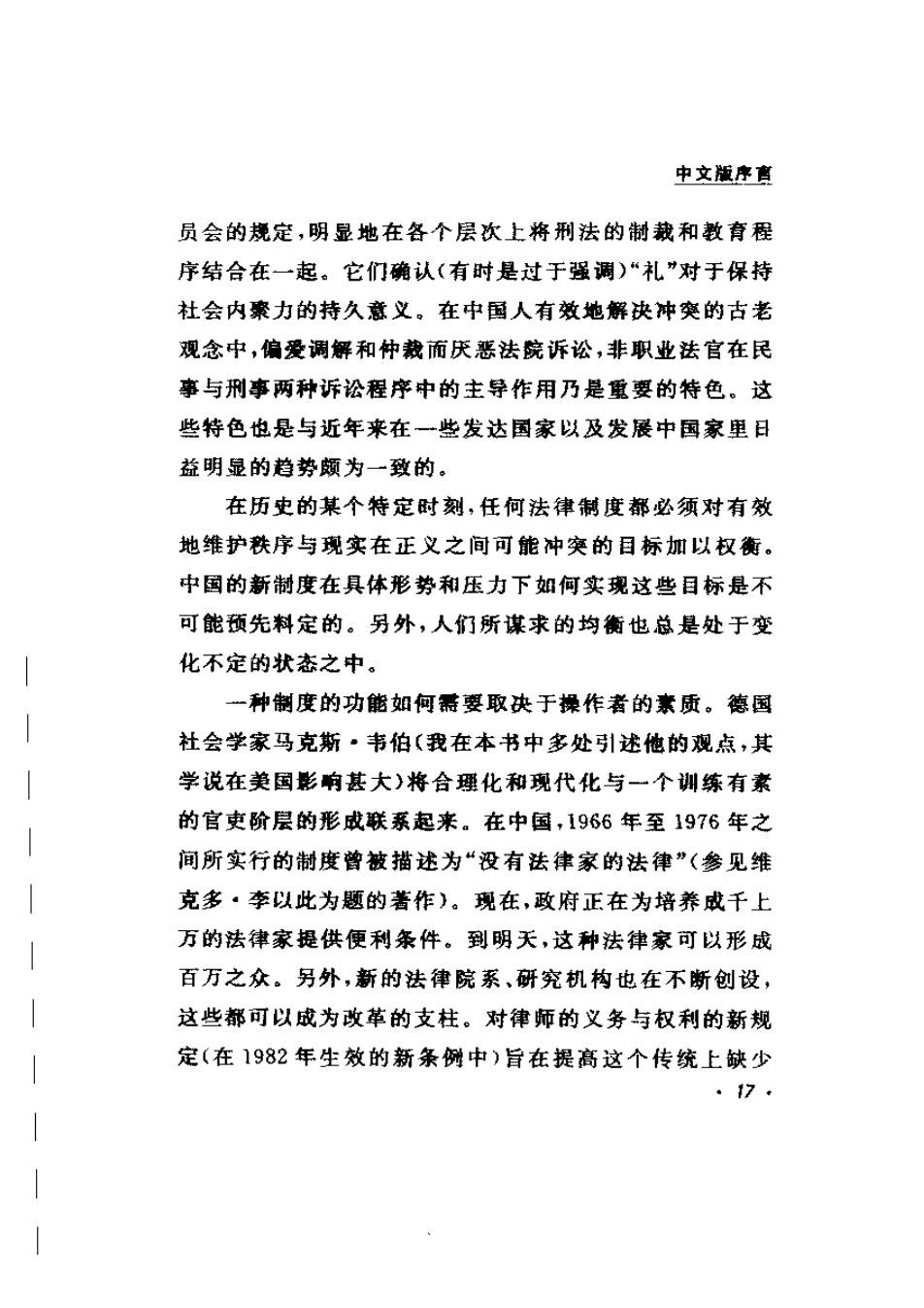
中文版序直 员会的规定,明显地在各个层次上将刑法的制裁和教育程 序结合在一起。它们确认(有时是过于强调)“礼”对于保持 社会内聚力的持久意义。在中国人有效地解决神突的古老 观念中,偏爱调解和仲裁而厌恶法院诉论,非职业法官在民 事与刑事两种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乃是重要的特色。这 些特色也是与近年来在一些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里日 益明显的趋势颇为一致的。 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刻,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对有效 地维护秩序与现实在正义之间可能冲突的目标加以权衡。 中国的新制度在具体形势和压力下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是不 可能预先料定的。另外,人们所谋求的均衡也总是处于变 化不定的状态之中。 一种制度的功能如何需要取决于操作者的素质。德国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我在本书中多处引述他的观点,其 学说在美国影响甚大)将合理化和现代化与一个圳练有素 的宫吏阶层的形成联系起来。在中国,1966年至1976年之 间所实行的制度曾被描述为“没有法律家的法律”(参见雏 克多·李以此为题的著作)。现在,政府正在为培养成千上 万的法律家提供便利条件。到明天,这种法律家可以形成 百万之众。另外,新的法律院系,研究机构也在不断创设, 这些都可以成为改革的支柱。对律师的义务与权利的新规 定(在1982年生效的新条例中)旨在提高这个传统上缺少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