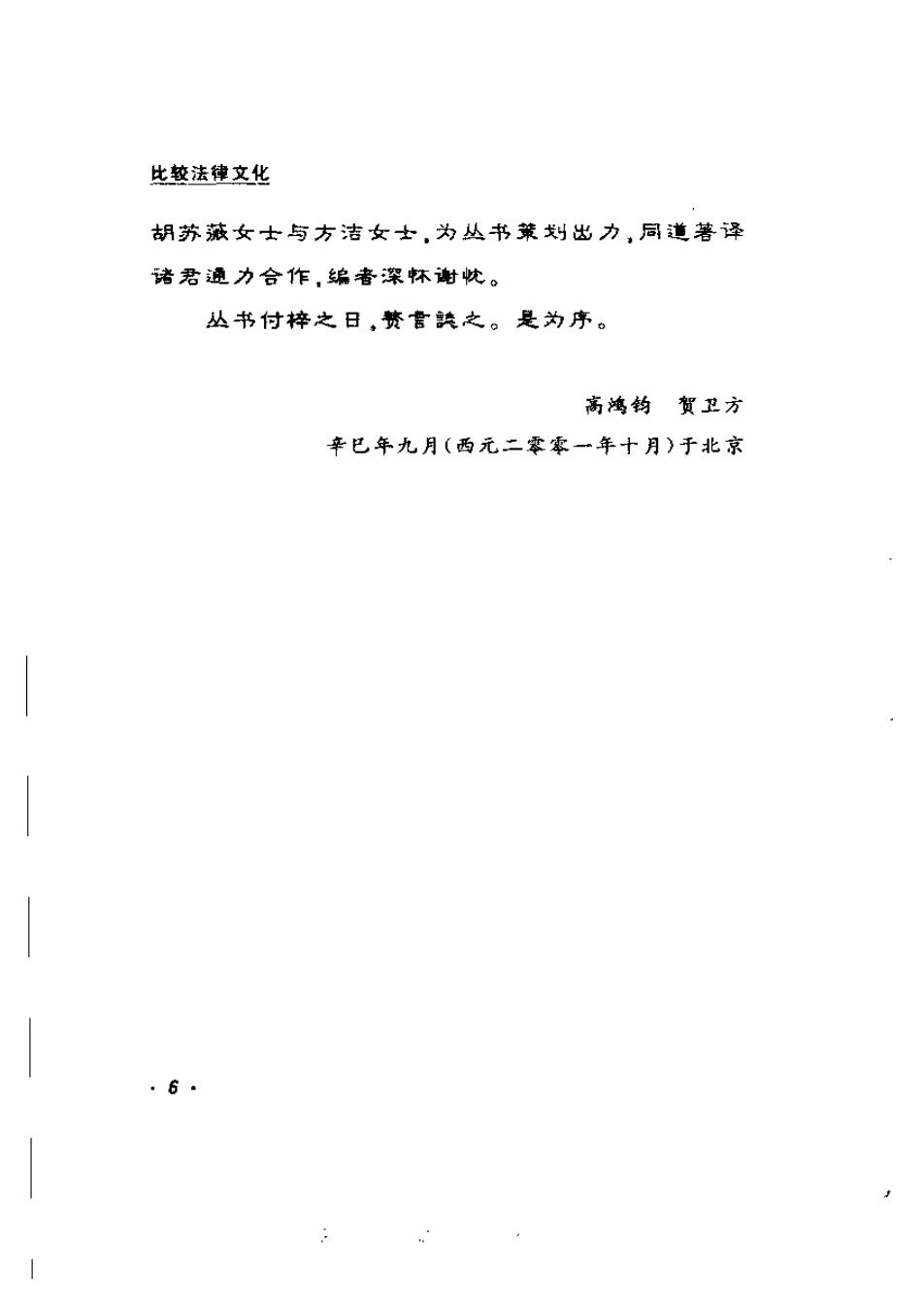
比较法律文化 胡苏滋女士与方洁女士,为丛书策划出力,局道著译 诸君通力合作,编者深杯谢忱。 丛书付梓之日,焚官关之。是为序。 高鸿钧贺卫方 辛巳年九月(西元二零零一年十月)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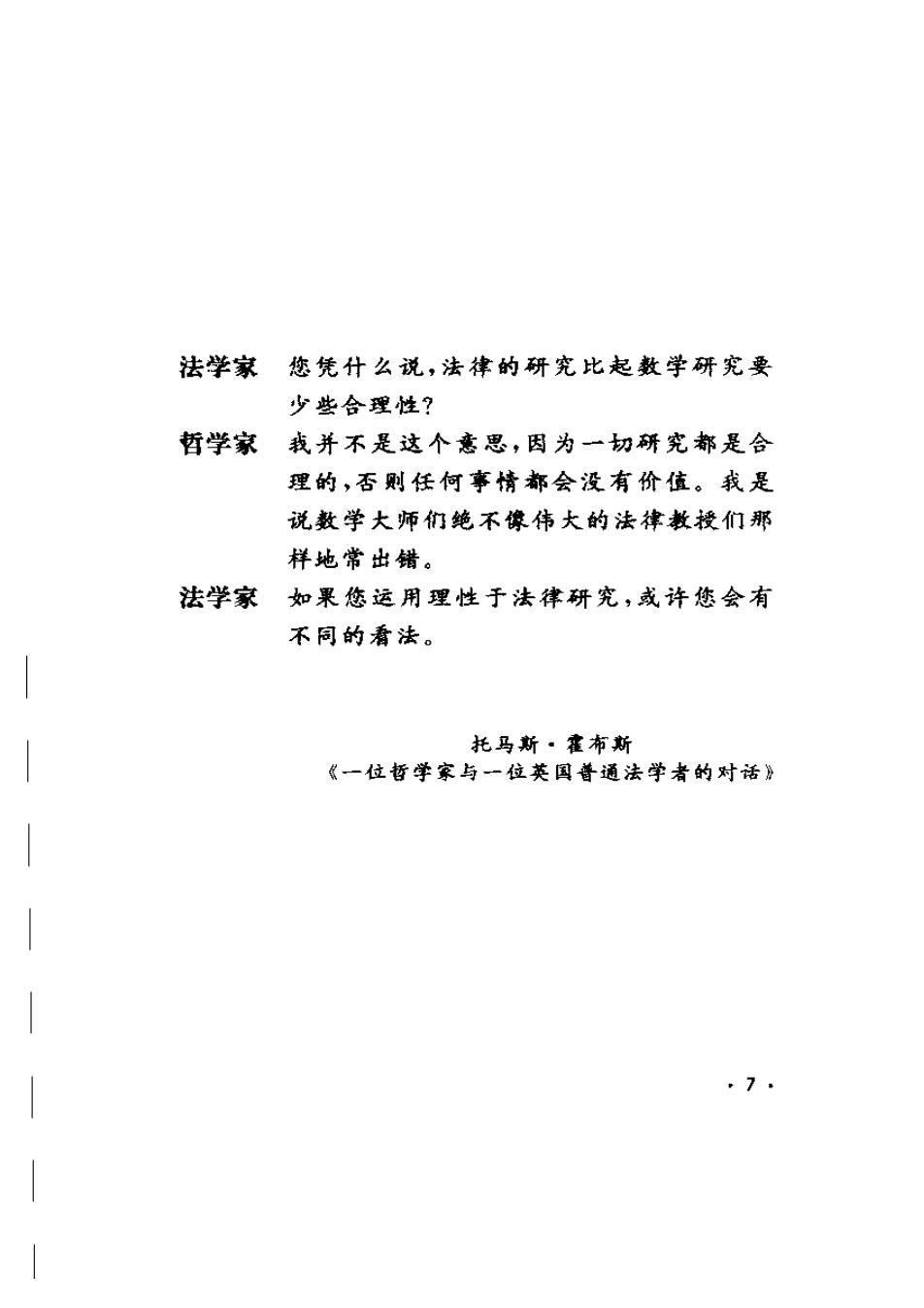
法学家您凭什么说,法律的研究比起数学研究要 少些合理性? 哲学家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一切研究都是合 理的,否则任何事情都会没有价值。我是 说数学大师们绝不像伟大的法律教授们那 样地常出错。 法学家如果您运用理性于法律研究,或许您会有 不同的奢法。 托马斯·霍布斯 《一位哲学家与一位英国普通法学者的对话》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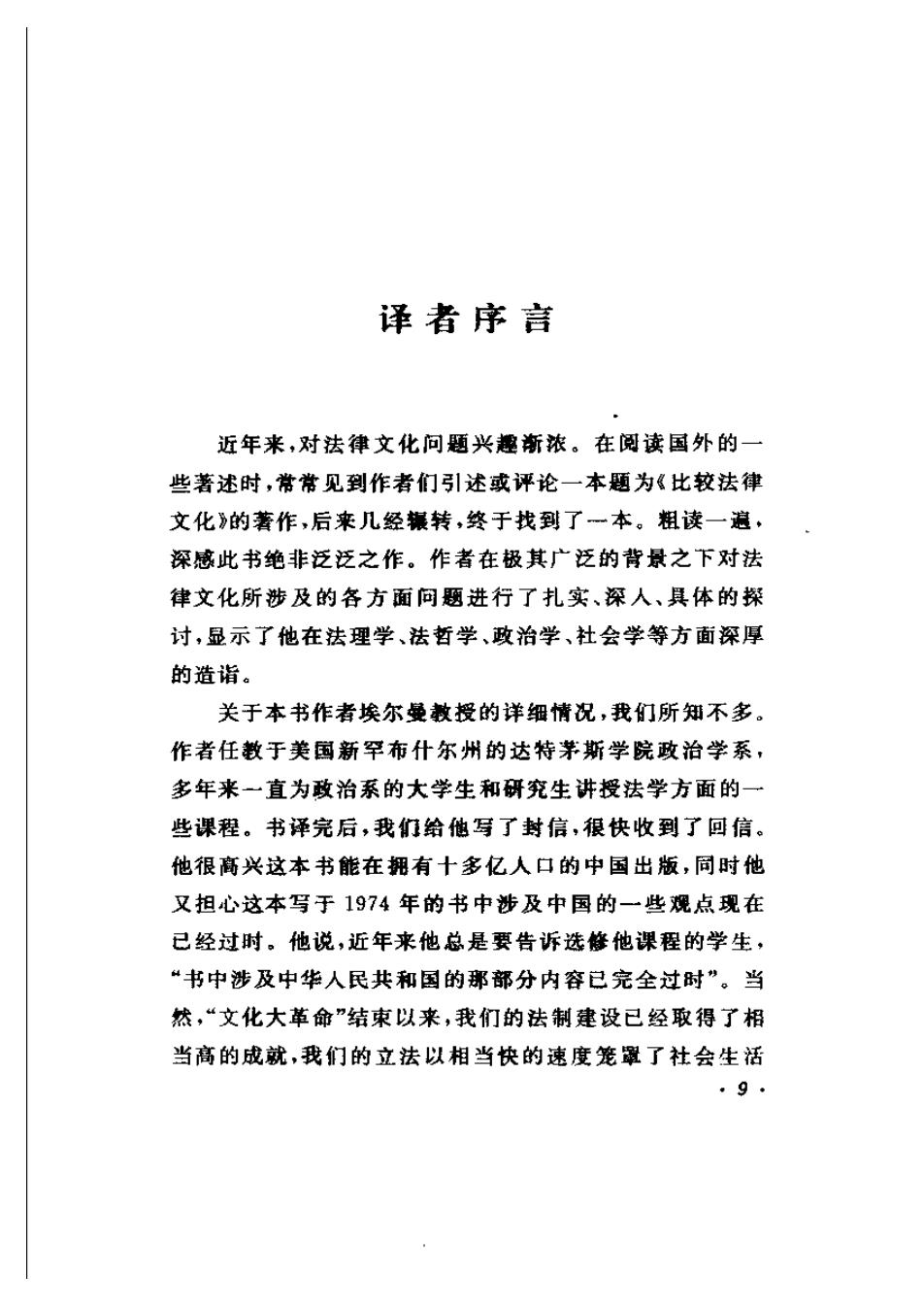
译者序言 近年来,对法律文化问题兴趣渐浓。在阅读国外的一 些著述时,常常见到作者们引述或评论一本题为《比较法律 文化》的著作,后来几经振转,终于找到了一本。粗读一遍, 深感此书绝非泛泛之作。作者在极其广泛的背景之下对法 律文化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扎实、深人、具体的探 讨,显示了他在法理学、法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深厚 的造诣。 关于本书作者埃尔曼教授的详细情况,我们所知不多。 作者任教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政治学系, 多年来一直为政治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讲授法学方面的一 些课程。书译完后,我们给他写了封信,很快收到了回信。 他很高兴这本书能在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出版,同时他 又担心这本号于1974年的书中涉及中国的一些规点现在 已经过时。他说,近年来他总是要告诉选修他课程的学生, “书中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部分内容已完全过时”。当 然,“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我们的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相 当高的成就,我们的立法以相当快的速度笼罩了社会生活 ·9✉

比较法律文化 的许多方面,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也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 个重要内容。但是,在那如火如茶的“文化大革命”中,即使 是一个中国人,又有谁能预料到数年之后会出现如此伟大 的历史性转折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但是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完全走上法治的轨道,这也是一 个事实。埃尔曼教授在他的书中曾引用一位“在伦敦受过 教育的大陆中国法学家”的话:“你们西方人的烦恼在于你 们一直未能超越你们称之为‘法治'的初期阶段。.而中 国却,总是知道,要治理一个社会单凭法律是不够的。两干 五百年前她便知道这一点,今天她仍然知道这一点。”如果 我们的着眼点不是在口号而在实际的话,我们得承认,今日 许多中国人骨子眼里仍然是格守着“这一点”的(至于“这一 点”的是非功过当然又是另一个重大问题)。由此言之,这 本书里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见解便没有 失去其现实意义。 我们不打算对这本书的内容进行过多的评论。翻译与 批评之间或许天然有些不和谐。翻译是细活,它着重具体、 细节,它可以见木不见林,不像批评家那样需有大处着眼之 手笔、高屋建瓶之气派。译者过多地对其译作品头论足,不 仅是越权,而且也常无意中暴髯自己的弱点。不如将那些 恢宏的议论、精到乃至严苛的批评留给原书作者、批评家和 读者。 我们要向粱君治平深表谢意。他向我们提供了原书,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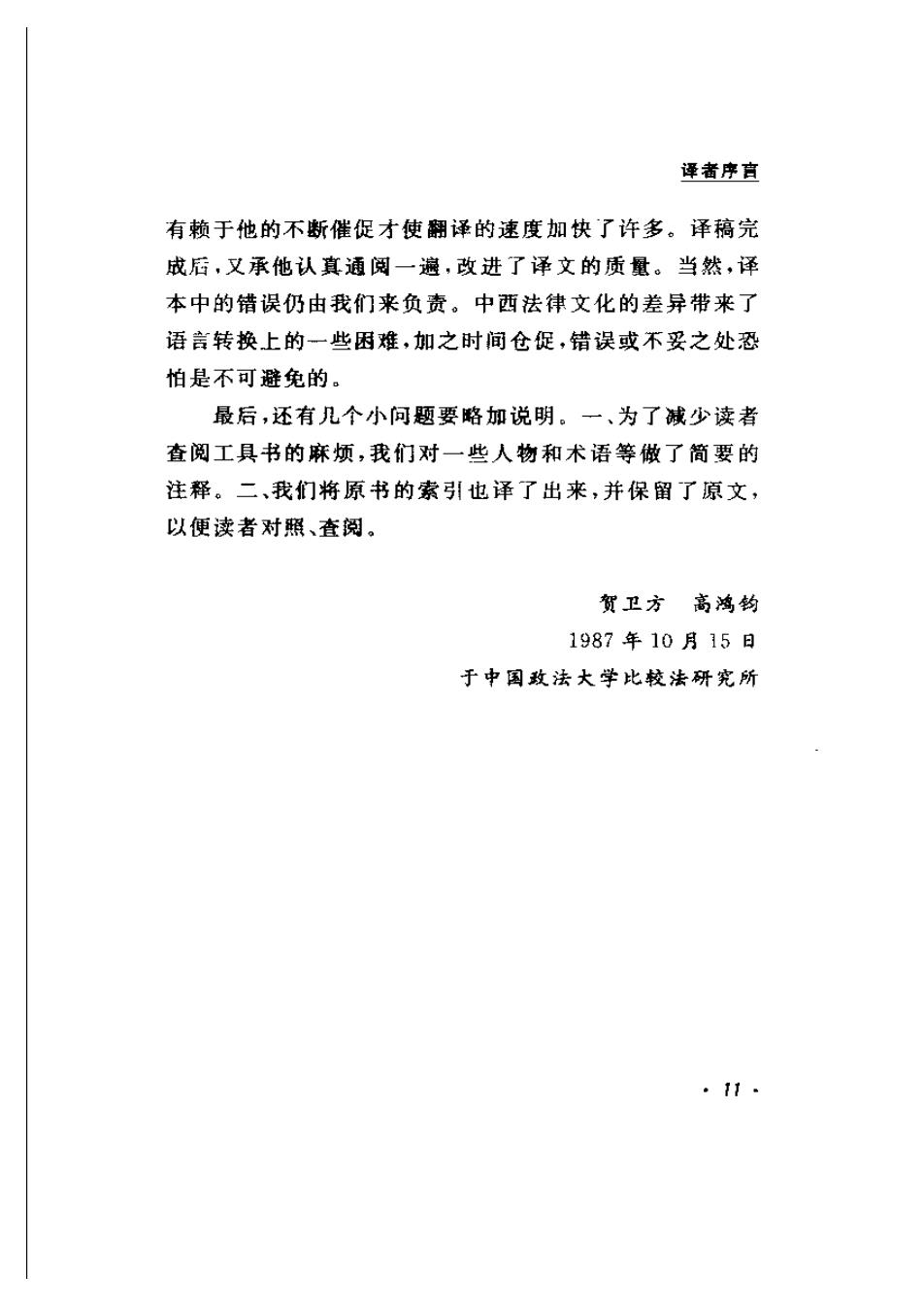
译者序直 有赖于他的不断催促才使翻译的速度加快了许多。译稿完 成后,又承他认真通阅一遍,改进了译文的质量。当然,译 本中的错误仍由我们来负责。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带来了 语言转换上的一些困摊,加之时间仓促,错误或不妥之处恐 怕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还有儿个小问题要略如说明。一、为了诚少读者 查阅工具书的麻烦,我们对一些人物和术语等做了简要的 注释。二、我们将原书的索引也译了出来,并保留了原文, 以便读者对照、查阅。 贺卫方高鸿钧 1987年10月15日 于中国玫法大学比校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