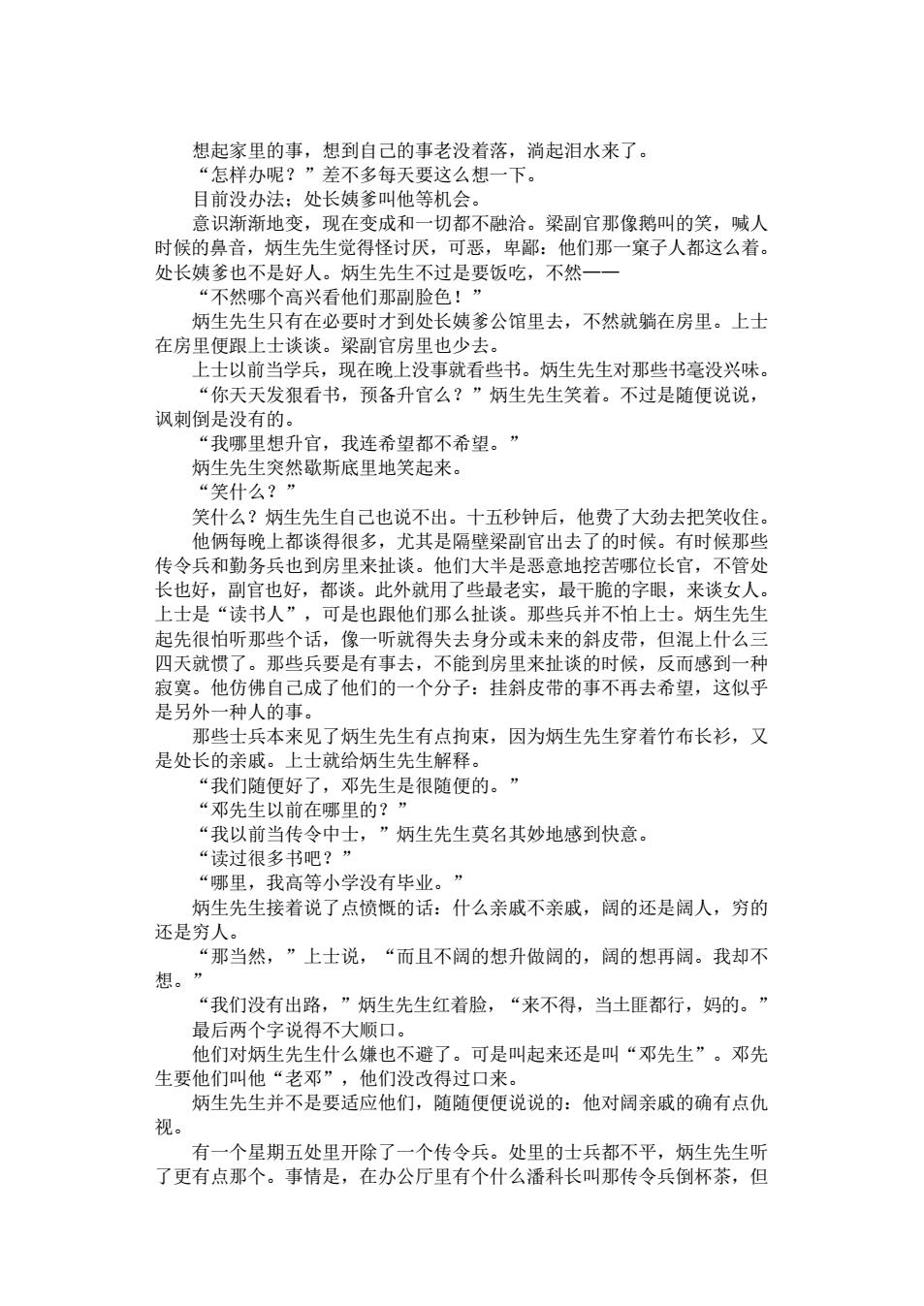
想起家里的事,想到自己的事老没着落,淌起泪水来了。 “怎样办呢?”差不多每天要这么想一下。 目前没办法;处长姨爹叫他等机会。 意识渐渐地变,现在变成和一切都不融洽。梁副官那像鹅叫的笑,喊人 时候的鼻音,炳生先生觉得怪讨厌,可恶,卑鄙:他们那一窠子人都这么着。 处长姨爹也不是好人。炳生先生不过是要饭吃,不然一一 “不然哪个高兴看他们那副脸色!” 炳生先生只有在必要时才到处长姨爹公馆里去,不然就躺在房里。上士 在房里便跟上士谈谈。梁副官房里也少去。 上士以前当学兵,现在晚上没事就看些书。炳生先生对那些书毫没兴味。 “你天天发狠看书,预备升官么?”炳生先生笑着。不过是随便说说, 讽刺倒是没有的。 “我哪里想升官,我连希望都不希望。” 炳生先生突然歇斯底里地笑起来。 “笑什么?” 笑什么?炳生先生自己也说不出。十五秒钟后,他费了大劲去把笑收住。 他俩每晚上都谈得很多,尤其是隔壁梁副官出去了的时候。有时候那些 传令兵和勤务兵也到房里来扯谈。他们大半是恶意地挖苦哪位长官,不管处 长也好,副官也好,都谈。此外就用了些最老实,最干脆的字眼,来谈女人。 上士是“读书人”,可是也跟他们那么扯谈。那些兵并不怕上士。炳生先生 起先很怕听那些个话,像一听就得失去身分或未来的斜皮带,但混上什么三 四天就惯了。那些兵要是有事去,不能到房里来扯谈的时候,反而感到一种 寂寞。他仿佛自己成了他们的一个分子:挂斜皮带的事不再去希望,这似乎 是另外一种人的事。 那些士兵本来见了炳生先生有点拘束,因为炳生先生穿着竹布长衫,又 是处长的亲戚。上士就给炳生先生解释。 “我们随便好了,邓先生是很随便的。” “邓先生以前在哪里的?” “我以前当传令中士,”炳生先生莫名其妙地感到快意。 “读过很多书吧?” “哪里,我高等小学没有毕业。” 炳生先生接着说了点愤慨的话:什么亲戚不亲戚,阔的还是阔人,穷的 还是穷人。 “那当然,”上士说,“而且不阔的想升做阔的,阔的想再阔。我却不 想。” “我们没有出路,”炳生先生红着脸,“来不得,当土匪都行,妈的。” 最后两个字说得不大顺口。 他们对炳生先生什么嫌也不避了。可是叫起来还是叫“邓先生”。邓先 生要他们叫他“老邓”,他们没改得过口来。 炳生先生并不是要适应他们,随随便便说说的:他对阔亲戚的确有点仇 视。 有一个星期五处里开除了一个传令兵。处里的士兵都不平,炳生先生听 了更有点那个。事情是,在办公厅里有个什么潘科长叫那传令兵倒杯茶,但
想起家里的事,想到自己的事老没着落,淌起泪水来了。 “怎样办呢?”差不多每天要这么想一下。 目前没办法;处长姨爹叫他等机会。 意识渐渐地变,现在变成和一切都不融洽。梁副官那像鹅叫的笑,喊人 时候的鼻音,炳生先生觉得怪讨厌,可恶,卑鄙:他们那一窠子人都这么着。 处长姨爹也不是好人。炳生先生不过是要饭吃,不然—— “不然哪个高兴看他们那副脸色!” 炳生先生只有在必要时才到处长姨爹公馆里去,不然就躺在房里。上士 在房里便跟上士谈谈。梁副官房里也少去。 上士以前当学兵,现在晚上没事就看些书。炳生先生对那些书毫没兴味。 “你天天发狠看书,预备升官么?”炳生先生笑着。不过是随便说说, 讽刺倒是没有的。 “我哪里想升官,我连希望都不希望。” 炳生先生突然歇斯底里地笑起来。 “笑什么?” 笑什么?炳生先生自己也说不出。十五秒钟后,他费了大劲去把笑收住。 他俩每晚上都谈得很多,尤其是隔壁梁副官出去了的时候。有时候那些 传令兵和勤务兵也到房里来扯谈。他们大半是恶意地挖苦哪位长官,不管处 长也好,副官也好,都谈。此外就用了些最老实,最干脆的字眼,来谈女人。 上士是“读书人”,可是也跟他们那么扯谈。那些兵并不怕上士。炳生先生 起先很怕听那些个话,像一听就得失去身分或未来的斜皮带,但混上什么三 四天就惯了。那些兵要是有事去,不能到房里来扯谈的时候,反而感到一种 寂寞。他仿佛自己成了他们的一个分子:挂斜皮带的事不再去希望,这似乎 是另外一种人的事。 那些士兵本来见了炳生先生有点拘束,因为炳生先生穿着竹布长衫,又 是处长的亲戚。上士就给炳生先生解释。 “我们随便好了,邓先生是很随便的。” “邓先生以前在哪里的?” “我以前当传令中士,”炳生先生莫名其妙地感到快意。 “读过很多书吧?” “哪里,我高等小学没有毕业。” 炳生先生接着说了点愤慨的话:什么亲戚不亲戚,阔的还是阔人,穷的 还是穷人。 “那当然,”上士说,“而且不阔的想升做阔的,阔的想再阔。我却不 想。” “我们没有出路,”炳生先生红着脸,“来不得,当土匪都行,妈的。” 最后两个字说得不大顺口。 他们对炳生先生什么嫌也不避了。可是叫起来还是叫“邓先生”。邓先 生要他们叫他“老邓”,他们没改得过口来。 炳生先生并不是要适应他们,随随便便说说的:他对阔亲戚的确有点仇 视。 有一个星期五处里开除了一个传令兵。处里的士兵都不平,炳生先生听 了更有点那个。事情是,在办公厅里有个什么潘科长叫那传令兵倒杯茶,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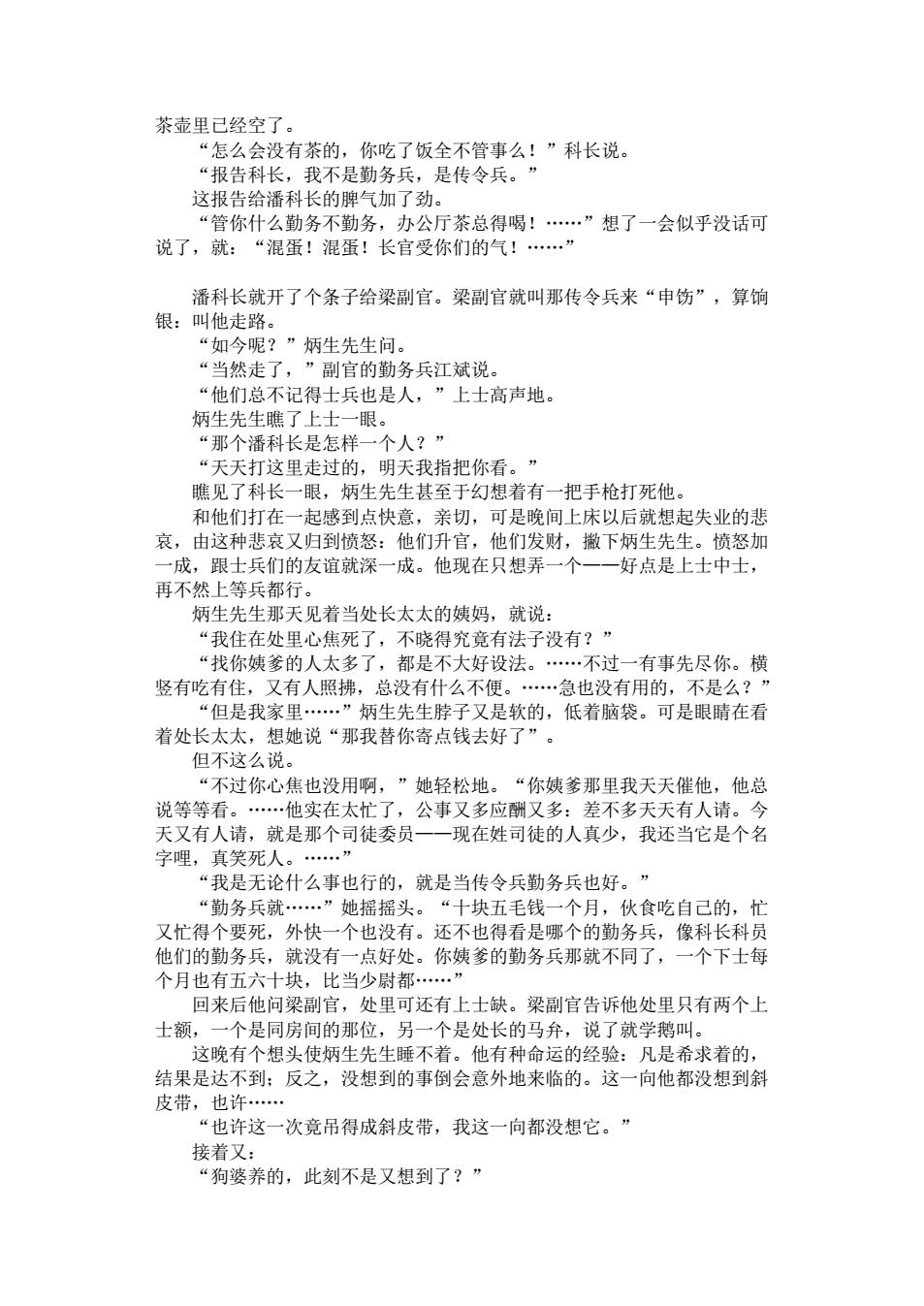
茶壶里己经空了。 “怎么会没有茶的,你吃了饭全不管事么!”科长说。 “报告科长,我不是勤务兵,是传令兵。” 这报告给潘科长的脾气加了劲。 “管你什么勤务不勤务,办公厅茶总得喝!…”想了一会似乎没话可 说了,就:“混蛋!混蛋!长官受你们的气!…” 潘科长就开了个条子给梁副官。梁副官就叫那传令兵来“申饬”,算饷 银:叫他走路。 “如今呢?”炳生先生问。 “当然走了,”副官的勤务兵江斌说。 “他们总不记得士兵也是人,”上士高声地。 炳生先生瞧了上士一眼。 “那个潘科长是怎样一个人?” “天天打这里走过的,明天我指把你看。” 瞧见了科长一眼,炳生先生甚至于幻想着有一把手枪打死他。 和他们打在一起感到点快意,亲切,可是晚间上床以后就想起失业的悲 哀,由这种悲哀又归到愤怒:他们升官,他们发财,撇下炳生先生。愤怒加 一成,跟士兵们的友谊就深一成。他现在只想弄一个一一好点是上士中士, 再不然上等兵都行。 炳生先生那天见着当处长太太的姨妈,就说: “我住在处里心焦死了,不晓得究竞有法子没有?” “找你姨爹的人太多了,都是不大好设法。…不过一有事先尽你。横 竖有吃有住,又有人照拂,总没有什么不便。…急也没有用的,不是么?” “但是我家里…”炳生先生脖子又是软的,低着脑袋。可是眼睛在看 着处长太太,想她说“那我替你寄点钱去好了”。 但不这么说。 “不过你心焦也没用啊,”她轻松地。“你姨爹那里我天天催他,他总 说等等看。…他实在太忙了,公事又多应酬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请。今 天又有人请,就是那个司徒委员一一现在姓司徒的人真少,我还当它是个名 字哩,真笑死人。…” “我是无论什么事也行的,就是当传令兵勤务兵也好。” “勤务兵就…”她摇摇头。“十块五毛钱一个月,伙食吃自己的,忙 又忙得个要死,外快一个也没有。还不也得看是哪个的勤务兵,像科长科员 他们的勤务兵,就没有一点好处。你姨爹的勤务兵那就不同了,一个下士每 个月也有五六十块,比当少尉都…” 回来后他问梁副官,处里可还有上士缺。梁副官告诉他处里只有两个上 士额,一个是同房间的那位,另一个是处长的马弁,说了就学鹅叫。 这晚有个想头使炳生先生睡不着。他有种命运的经验:凡是希求着的, 结果是达不到:反之,没想到的事倒会意外地来临的。这一向他都没想到斜 皮带,也许… “也许这一次竞吊得成斜皮带,我这一向都没想它。” 接着又: “狗婆养的,此刻不是又想到了?
茶壶里已经空了。 “怎么会没有茶的,你吃了饭全不管事么!”科长说。 “报告科长,我不是勤务兵,是传令兵。” 这报告给潘科长的脾气加了劲。 “管你什么勤务不勤务,办公厅茶总得喝!……”想了一会似乎没话可 说了,就:“混蛋!混蛋!长官受你们的气!……” 潘科长就开了个条子给梁副官。梁副官就叫那传令兵来“申饬”,算饷 银:叫他走路。 “如今呢?”炳生先生问。 “当然走了,”副官的勤务兵江斌说。 “他们总不记得士兵也是人,”上士高声地。 炳生先生瞧了上士一眼。 “那个潘科长是怎样一个人?” “天天打这里走过的,明天我指把你看。” 瞧见了科长一眼,炳生先生甚至于幻想着有一把手枪打死他。 和他们打在一起感到点快意,亲切,可是晚间上床以后就想起失业的悲 哀,由这种悲哀又归到愤怒:他们升官,他们发财,撇下炳生先生。愤怒加 一成,跟士兵们的友谊就深一成。他现在只想弄一个——好点是上士中士, 再不然上等兵都行。 炳生先生那天见着当处长太太的姨妈,就说: “我住在处里心焦死了,不晓得究竟有法子没有?” “找你姨爹的人太多了,都是不大好设法。……不过一有事先尽你。横 竖有吃有住,又有人照拂,总没有什么不便。……急也没有用的,不是么?” “但是我家里……”炳生先生脖子又是软的,低着脑袋。可是眼睛在看 着处长太太,想她说“那我替你寄点钱去好了”。 但不这么说。 “不过你心焦也没用啊,”她轻松地。“你姨爹那里我天天催他,他总 说等等看。……他实在太忙了,公事又多应酬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请。今 天又有人请,就是那个司徒委员——现在姓司徒的人真少,我还当它是个名 字哩,真笑死人。……” “我是无论什么事也行的,就是当传令兵勤务兵也好。” “勤务兵就……”她摇摇头。“十块五毛钱一个月,伙食吃自己的,忙 又忙得个要死,外快一个也没有。还不也得看是哪个的勤务兵,像科长科员 他们的勤务兵,就没有一点好处。你姨爹的勤务兵那就不同了,一个下士每 个月也有五六十块,比当少尉都……” 回来后他问梁副官,处里可还有上士缺。梁副官告诉他处里只有两个上 士额,一个是同房间的那位,另一个是处长的马弁,说了就学鹅叫。 这晚有个想头使炳生先生睡不着。他有种命运的经验:凡是希求着的, 结果是达不到;反之,没想到的事倒会意外地来临的。这一向他都没想到斜 皮带,也许…… “也许这一次竟吊得成斜皮带,我这一向都没想它。” 接着又: “狗婆养的,此刻不是又想到了?

一想到斜皮带,斜皮带的事多半又没望。 “他们哪里会替我诚心找事。诚心找还找不成么,一个中将处长?… 我的事情,他们只说说风…风…风什么话的。” 炳生先生记得“下江人”对这些话有个专门名词,叫风什么话,但中间 那个字怎么也想不起。 他叹了口气。 可纪念的一天。 这天天气不算好,可是时气好。梁副官告诉炳生先生:处里出了个司书 缺额,处长说给炳生先生补。 “以后你就可以安心了。…拿到薪水不过要请客哩,哈哈哈。” “五哥说的是真的么?”炳生先生的声音打颤。 “狗哄你。…你快些写个履历吧,姨爹说的。履历片子这里有。” 炳生先生抖着手指接了履历片,逃似地出了房门。 忽然又站住: “是准尉是少尉?” “本来是个少尉,不过把你补起来还不晓得是少尉准尉。横竖下面的话 炳生先生没有工夫听,一腿跨到自己房里。他当然希望是少尉:比准尉多十 块龙洋。但是,他又想,准尉也行,总而言之是斜皮带。… 一身的血在狂奔,心脏上有三百条蜈蚣在爬着的样子。额头上沁出了十 来点汗。 “呃,真热!” 突然发现了手里拿着的件把东西:才记起是来写履历的。“怎样写法呢!” 为郑重起见,先打个稿子给梁副官看。 出身:“高等小学堂肄业。” 经过职务:“曾任传令中士,须至履历者。” “要不得要不得,”梁副官尽捧着肚子学鹅叫。 炳生先生茫然了。 “要怎样写呢,我不会写啊。” 梁副官给他改了一下:什么中学毕业,又是什么机关里的书记。又把学 堂的“堂”改做“校”。 “人家不会查么?”炳生先生问。 “哪里有人来查。” “五哥你说咸板鸭好还是烧鸭子好?” “做什么?”那个愕然地。 “我想送姨爹一点人情。” “那又何必,不过烧鸭子比板鸭子好。” 炳生先生手发抖,履历写得怪费劲。 “五哥你说房子呢,房子怎样办?” “你住的房子么?自然把你搬到办公厅旁边职员室里去。” “啊呀真热!”拿袖子揩揩额头。 就在当天,江斌把炳生先生的睡觉行头,从上士室搬进职员室。同房间 的是薛先生,中尉收发
一想到斜皮带,斜皮带的事多半又没望。 “他们哪里会替我诚心找事。诚心找还找不成么,一个中将处长?…… 我的事情,他们只说说风……风……风什么话的。” 炳生先生记得“下江人”对这些话有个专门名词,叫风什么话,但中间 那个字怎么也想不起。 他叹了口气。 可纪念的一天。 这天天气不算好,可是时气好。梁副官告诉炳生先生:处里出了个司书 缺额,处长说给炳生先生补。 “以后你就可以安心了。……拿到薪水不过要请客哩,哈哈哈。” “五哥说的是真的么?”炳生先生的声音打颤。 “狗哄你。……你快些写个履历吧,姨爹说的。履历片子这里有。” 炳生先生抖着手指接了履历片,逃似地出了房门。 忽然又站住: “是准尉是少尉?” “本来是个少尉,不过把你补起来还不晓得是少尉准尉。横竖下面的话 炳生先生没有工夫听,一腿跨到自己房里。他当然希望是少尉:比准尉多十 块龙洋。但是,他又想,准尉也行,总而言之是斜皮带。…… 一身的血在狂奔,心脏上有三百条蜈蚣在爬着的样子。额头上沁出了十 来点汗。 “呃,真热!” 突然发现了手里拿着的件把东西:才记起是来写履历的。“怎样写法呢!” 为郑重起见,先打个稿子给梁副官看。 出身:“高等小学堂肄业。” 经过职务:“曾任传令中士,须至履历者。” “要不得要不得,”梁副官尽捧着肚子学鹅叫。 炳生先生茫然了。 “要怎样写呢,我不会写啊。” 梁副官给他改了一下:什么中学毕业,又是什么机关里的书记。又把学 堂的“堂”改做“校”。 “人家不会查么?”炳生先生问。 “哪里有人来查。” “五哥你说咸板鸭好还是烧鸭子好?” “做什么?”那个愕然地。 “我想送姨爹一点人情。” “那又何必,不过烧鸭子比板鸭子好。” 炳生先生手发抖,履历写得怪费劲。 “五哥你说房子呢,房子怎样办?” “你住的房子么?自然把你搬到办公厅旁边职员室里去。” “啊呀真热!”拿袖子揩揩额头。 就在当天,江斌把炳生先生的睡觉行头,从上士室搬进职员室。同房间 的是薛先生,中尉收发

“从此以后…”炳生先生老这么想着。 这么想着一直到夜里:老睡不着。外面下着毛毛雨。里面是薛中尉收发 一个劲儿尽打鼾。炳生先生又觉得热,小褂裤象发霉似地潮着。 “从此以后…” 少尉还是准尉可不知道,可是为得怕希望太大而有幻灭的悲哀之故,炳 生先生从准尉着想。三十二块钱:伙食十块,自己用十块,寄娘老子十块, 还有两块一一按月储蓄。不,这还不是急务。第一得支几块钱做套灰布衣, 买根斜皮带,斜的!脚上这双军用皮鞋还是当中士时期穿的,太不成话,所 以新皮鞋也是急务之一。军帽五毛钱一顶:可是踌躇着,还是厚边的好,还 是薄边的好。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挂横皮带的瞧见自己就得“敬礼”。他回乡去的时候,也挂 斜皮带,用额头看人。…一想起前几天还说过就是当传令兵勤务兵都行, 脸上发起烧来。 第二天很疲倦。张开眼。薛先生已经在刷牙了。 炳生先生不大自在:薛先生是中尉:中尉与准尉之比,等于准尉与中士 之比。…可是马上又想开了,薛先生起码有三十多岁,自己才二十七:到 了三十几,不见得连一个中尉都爬不上。 “薛收发今年贵庚?” “十八。” “不是,我问你贵庚,”最后两个字说得非常响亮。 “是啊,我今年十八岁。” 炳生先生几乎跳起来。可是镇定住自己,打个呵欠,表示他没听见那句 话。 下午三点钟,一个含有最重大的意义的三点钟,一个平常跟炳生先生打 笑的传令兵到房里来,手里一个大信封。 “恭喜邓先生。请你盖个私章。”掀开一本簿子。 炳生先生先用发疟疾似的手去接了大信封,擦擦眼睛瞧它的左角上一条 字。他集中全生命的力去辨“尉”字上面那两个字的差别。 右令少尉司书邓炳生准此 再瞧一遍:“少”!一一一点不含糊。 “怎么来得那样快,那东西?”他去问梁副官。 “这里处里的公事,你没看见么。还要呈请部里正式下委。” “呈请不准呢?” “没有不准的。你放心到差好了。” 马上就到差,马上认得许多同事:自然都是挂斜皮带的。在办公厅里呢, 有批士兵伺候着,这批士兵就是炳生先生以前在上士房里跟他们天天打在一 起的。 “这有些讨厌,”炳生先生想。 他后悔他不该以前跟他们太放肆,失掉几成现在的斜皮带身份。还有更 糟的是,他告诉了他们,什么高小没毕业的,什么当过传令中士。… “他们一定看我不起,不当我长官看待
“从此以后……”炳生先生老这么想着。 这么想着一直到夜里:老睡不着。外面下着毛毛雨。里面是薛中尉收发 一个劲儿尽打鼾。炳生先生又觉得热,小褂裤象发霉似地潮着。 “从此以后……” 少尉还是准尉可不知道,可是为得怕希望太大而有幻灭的悲哀之故,炳 生先生从准尉着想。三十二块钱:伙食十块,自己用十块,寄娘老子十块, 还有两块——按月储蓄。不,这还不是急务。第一得支几块钱做套灰布衣, 买根斜皮带,斜的!脚上这双军用皮鞋还是当中士时期穿的,太不成话,所 以新皮鞋也是急务之一。军帽五毛钱一顶:可是踌躇着,还是厚边的好,还 是薄边的好。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挂横皮带的瞧见自己就得“敬礼”。他回乡去的时候,也挂 斜皮带,用额头看人。……一想起前几天还说过就是当传令兵勤务兵都行, 脸上发起烧来。 第二天很疲倦。张开眼。薛先生已经在刷牙了。 炳生先生不大自在:薛先生是中尉;中尉与准尉之比,等于准尉与中士 之比。……可是马上又想开了,薛先生起码有三十多岁,自己才二十七:到 了三十几,不见得连一个中尉都爬不上。 “薛收发今年贵庚?” “十八。” “不是,我问你贵庚,”最后两个字说得非常响亮。 “是啊,我今年十八岁。” 炳生先生几乎跳起来。可是镇定住自己,打个呵欠,表示他没听见那句 话。 下午三点钟,一个含有最重大的意义的三点钟,一个平常跟炳生先生打 笑的传令兵到房里来,手里一个大信封。 “恭喜邓先生。请你盖个私章。”掀开一本簿子。 炳生先生先用发疟疾似的手去接了大信封,擦擦眼睛瞧它的左角上一条 字。他集中全生命的力去辨“尉”字上面那两个字的差别。 右令少尉司书邓炳生准此 再瞧一遍:“少”!——一点不含糊。 “怎么来得那样快,那东西?”他去问梁副官。 “这里处里的公事,你没看见么。还要呈请部里正式下委。” “呈请不准呢?” “没有不准的。你放心到差好了。” 马上就到差,马上认得许多同事:自然都是挂斜皮带的。在办公厅里呢, 有批士兵伺候着,这批士兵就是炳生先生以前在上士房里跟他们天天打在一 起的。 “这有些讨厌,”炳生先生想。 他后悔他不该以前跟他们太放肆,失掉几成现在的斜皮带身份。还有更 糟的是,他告诉了他们,什么高小没毕业的,什么当过传令中士。…… “他们一定看我不起,不当我长官看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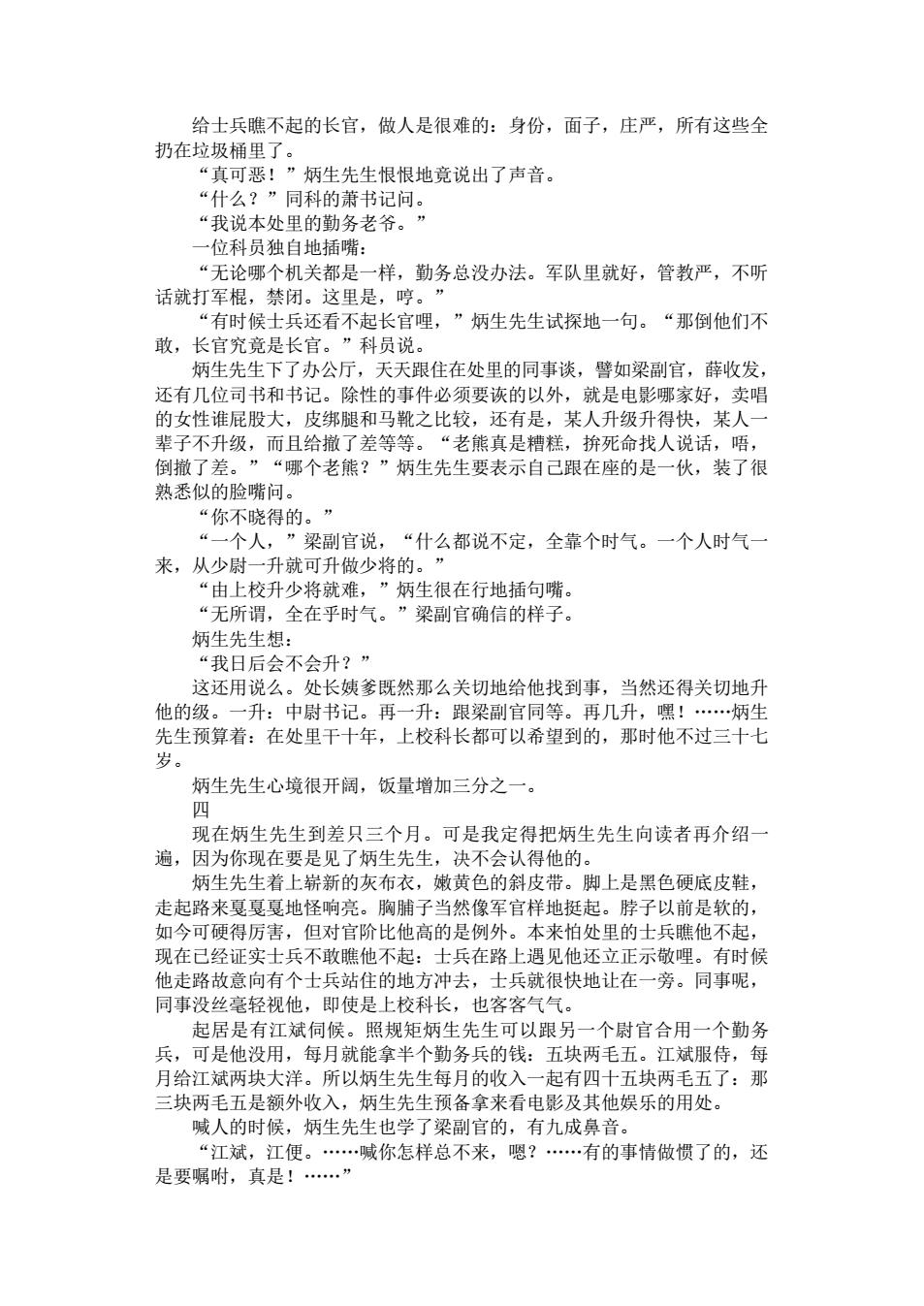
给士兵瞧不起的长官,做人是很难的:身份,面子,庄严,所有这些全 扔在垃圾桶里了。 “真可恶!”炳生先生恨恨地竟说出了声音。 “什么?”同科的萧书记问。 “我说本处里的勤务老爷。” 一位科员独自地插嘴: “无论哪个机关都是一样,勤务总没办法。军队里就好,管教严,不听 话就打军棍,禁闭。这里是,哼。” “有时候士兵还看不起长官哩,”炳生先生试探地一句。“那倒他们不 敢,长官究竟是长官。”科员说。 炳生先生下了办公厅,天天跟住在处里的同事谈,譬如梁副官,薛收发, 还有几位司书和书记。除性的事件必须要诙的以外,就是电影哪家好,卖唱 的女性谁屁股大,皮绑腿和马靴之比较,还有是,某人升级升得快,某人 辈子不升级,而且给撤了差等等。“老熊真是糟糕,拚死命找人说话,唔, 倒撤了差。”“哪个老熊?”炳生先生要表示自己跟在座的是一伙,装了很 熟悉似的脸嘴问。 “你不晓得的。” “一个人,”梁副官说,“什么都说不定,全靠个时气。一个人时气一 来,从少尉一升就可升做少将的。” “由上校升少将就难,”炳生很在行地插句嘴。 “无所谓,全在乎时气。”梁副官确信的样子。 炳生先生想: “我日后会不会升?” 这还用说么。处长姨爹既然那么关切地给他找到事,当然还得关切地升 他的级。一升:中尉书记。再一升:跟梁副官同等。再几升,嘿!…炳生 先生预算着:在处里干十年,上校科长都可以希望到的,那时他不过三十七 岁。 炳生先生心境很开阔,饭量增加三分之一。 四 现在炳生先生到差只三个月。可是我定得把炳生先生向读者再介绍一 遍,因为你现在要是见了炳生先生,决不会认得他的。 炳生先生着上崭新的灰布衣,嫩黄色的斜皮带。脚上是黑色硬底皮鞋, 走起路来戛戛戛地怪响亮。胸脯子当然像军官样地挺起。脖子以前是软的, 如今可硬得厉害,但对官阶比他高的是例外。本来怕处里的士兵瞧他不起, 现在已经证实士兵不敢瞧他不起:士兵在路上遇见他还立正示敬哩。有时候 他走路故意向有个士兵站住的地方冲去,士兵就很快地让在一旁。同事呢, 同事没丝毫轻视他,即使是上校科长,也客客气气。 起居是有江斌伺候。照规矩炳生先生可以跟另一个尉官合用一个勤务 兵,可是他没用,每月就能拿半个勤务兵的钱:五块两毛五。江斌服侍,每 月给江斌两块大洋。所以炳生先生每月的收入一起有四十五块两毛五了:那 三块两毛五是额外收入,炳生先生预备拿来看电影及其他娱乐的用处。 喊人的时候,炳生先生也学了梁副官的,有九成鼻音。 “江斌,江便。…喊你怎样总不来,嗯?…有的事情做惯了的,还 是要嘱咐,真是!…
给士兵瞧不起的长官,做人是很难的:身份,面子,庄严,所有这些全 扔在垃圾桶里了。 “真可恶!”炳生先生恨恨地竟说出了声音。 “什么?”同科的萧书记问。 “我说本处里的勤务老爷。” 一位科员独自地插嘴: “无论哪个机关都是一样,勤务总没办法。军队里就好,管教严,不听 话就打军棍,禁闭。这里是,哼。” “有时候士兵还看不起长官哩,”炳生先生试探地一句。“那倒他们不 敢,长官究竟是长官。”科员说。 炳生先生下了办公厅,天天跟住在处里的同事谈,譬如梁副官,薛收发, 还有几位司书和书记。除性的事件必须要诙的以外,就是电影哪家好,卖唱 的女性谁屁股大,皮绑腿和马靴之比较,还有是,某人升级升得快,某人一 辈子不升级,而且给撤了差等等。“老熊真是糟糕,拚死命找人说话,唔, 倒撤了差。”“哪个老熊?”炳生先生要表示自己跟在座的是一伙,装了很 熟悉似的脸嘴问。 “你不晓得的。” “一个人,”梁副官说,“什么都说不定,全靠个时气。一个人时气一 来,从少尉一升就可升做少将的。” “由上校升少将就难,”炳生很在行地插句嘴。 “无所谓,全在乎时气。”梁副官确信的样子。 炳生先生想: “我日后会不会升?” 这还用说么。处长姨爹既然那么关切地给他找到事,当然还得关切地升 他的级。一升:中尉书记。再一升:跟梁副官同等。再几升,嘿!……炳生 先生预算着:在处里干十年,上校科长都可以希望到的,那时他不过三十七 岁。 炳生先生心境很开阔,饭量增加三分之一。 四 现在炳生先生到差只三个月。可是我定得把炳生先生向读者再介绍一 遍,因为你现在要是见了炳生先生,决不会认得他的。 炳生先生着上崭新的灰布衣,嫩黄色的斜皮带。脚上是黑色硬底皮鞋, 走起路来戛戛戛地怪响亮。胸脯子当然像军官样地挺起。脖子以前是软的, 如今可硬得厉害,但对官阶比他高的是例外。本来怕处里的士兵瞧他不起, 现在已经证实士兵不敢瞧他不起:士兵在路上遇见他还立正示敬哩。有时候 他走路故意向有个士兵站住的地方冲去,士兵就很快地让在一旁。同事呢, 同事没丝毫轻视他,即使是上校科长,也客客气气。 起居是有江斌伺候。照规矩炳生先生可以跟另一个尉官合用一个勤务 兵,可是他没用,每月就能拿半个勤务兵的钱:五块两毛五。江斌服侍,每 月给江斌两块大洋。所以炳生先生每月的收入一起有四十五块两毛五了:那 三块两毛五是额外收入,炳生先生预备拿来看电影及其他娱乐的用处。 喊人的时候,炳生先生也学了梁副官的,有九成鼻音。 “江斌,江便。……喊你怎样总不来,嗯?……有的事情做惯了的,还 是要嘱咐,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