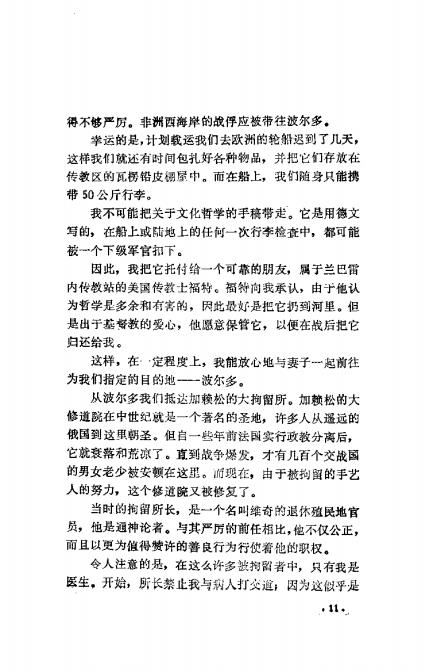
得不够严厉。非洲西海岸的战俘应被带往波尔多。 孝运的是,计划载运我们去欧洲的轮船迟到了几天, 这样我们就还有时间包孔好各种物品,并把它们存放在 传教区的瓦楞铅皮彻屋中。而在船上,我们随身只能携 带50公斤行李。 我不可能把关于文化哲学的手稿楷走。它是用德文 写的,在船上或陆地上的任何一次行李检在中,都可能 被一.个下级军官扣下。 因此,我把它托付给一个可靠的朋友,属于兰巴雷 内传数站的美国传教士福特。福钓向我承认,由于他认 为暂学是多余和有害的,风此最好是把它扔到河里。但 是出于恭督教的爱心,他恩意保管它,以便在战后把它 归还给我。 这样,在·定程度上,我能放心地与妻子一起前往 为我们指定的目的地一一波尔多。 从波尔多我们抵达加赖松的大拘留所。加赖松的大 修道酰在中世纪就是一个著名的圣地,许多人从遥远的 俄国到这里朗圣。但自一些年前法国实行政教分离后, 它就衰落和荒凉了。直到战争爆发,才有几百个交战国 的男女老少被安在这里。而现在,由于被拘留的手艺 人的努力,这个修道院又被修复了。 当时的掏留所长,是一个名叫维奇的退休殖民地官 员,他是通神论者。与其严厉的前任相比,他不仅公正, 面且以更为值得赞许的善良行为行使着他的职权。 令人注意的是,在这么许多波拘留者中,只有我是 医生,开始,所长禁止我与剂人打女道;因为这似乎是 11+

为官方所指定的拘留所医生一当地一位年迈的乡医 一的取责。几个星期之后,所长认为在拘留所内发挥 我这个医生的作用是正确的。他提供给我两个房间,一 间供我行医,一间则让我和我安子起居。 这样我丈成了医生,空余下来的时间,则用于写作 (文化和伦理》。我想,我也许不再能得到图在兰巴雷内 的原稿了,就凭记忆写下了这部著作的架婴。 1918年春季,根据米自巴黎的命令,我妻子和我y 被带往法国圣雷米省的专为阿尔萨斯人设置的拘留所。 为了留住我这个医生,加赖松的拘留所长徒劳地请求搬 销这个命令。圣雷米的拘留所也设在一个被遗弃的修道 院中。由于那里已有一个医生,因此开始我没什么事, 能整天写我的(文化和伦理,。在拘留所堙换了住院医生 之后,我就成了那里的医生,只是工作址没有加赖松那 里这么大。 为我妻子而感到十分高兴的是,我们在1918年7月 中旬得到通知,所有阿尔萨斯入将和被拘图在德国的法 国人交换。几天之后,我们将经过瑞士回到阿尔萨浙的 故乡。 经拘留所的检查人员检查盖章后,地们允许我们带 走我在加赖松和圣雷米写下的类于《文化和伦理?的纲 要。直到那时我才放心,在回家的路上它再也不会被夺 走了。 在斯特拉斯堡,市长让我担任市民医院的助理医 生,我榆快地接受了。同时,我又成了圣尼古拉较堂的 讲道者。由于教堂的阿尔萨斯牧师过分的德意志信念,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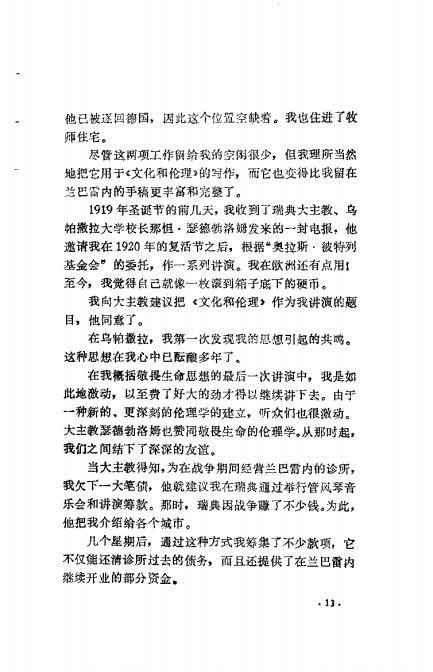
他已被遂回德国,因此这个位谊空皱着。我也住进了牧 师住宅。 尽管这两项工作阴给我的空闲很少,但我理所当然 地把它用于<文化和伦理的写作,而它也变得比我留在 兰巴雷内的乎稿更丰富和完整了。 1919年圣诞节的前几天,我收到了瑞典大主教、乌 帕撒拉大学校长那但·恶德勃洛姆发米的一封电报,他 邀请我在1920年的复活节之后,根据“奥拉斯·彼特列 基金会”的委托,作一系列件演。我在欧洲还有点用肛 至今,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枚滚到箱子底下的硬币。 我向大主数楚议把《文化和伦理,作为我讲演的题 目,他同意了。 在乌帕撒拉,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思想引起的共鸣。 这种思想在我心中已酝酸多年了。 在我概括敬畏生命思想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我是如 此地微动,以至费了好大的劲才得以跳续讲下去。由于 一种新的、更深刻的伦理学的建立,听众们也很激动。 大主教瑟德勃洛姆也赞同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从那时起, 我们之间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当大主教得知,为在战争期间经背兰巴霜内的诊所, 我欠下一大笔做,他就建议我在瑞典通过举行管风琴音 乐会和讲諛筹款。那时,瑞典因战争障了不少线。为此 他把我介绍给各个城市。 几个期后,通过这种方式我筹集了不少款项,它 不仅能还清诊所过去的债务,而且还提供了在兰巴蕾内 张续开业的部分资金。 +13+

我回到斯特拉斯堡不久之后,就收到了邮寄来的 《文化和伦理>的第一蒂,即我托付给兰巴岱内传较士福 特的那些手稿:这样,我也能利用文化和伦理的最初 构想来最后确定这都著作的文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在欧洲的首次逗留期间,有 机会在牛神,剑桥、哥本哈根和布拉格大学举行了多次 讲旗,用述《文化和伦理的思想。这些地方的人们表现 出对它的兴趣和理解。我能够感受到,人们肯定这种得 到透御论证的伦理学优于其他各种伦理学。 在我关于敬设生向伦理学的话中,我经常所到: 我的思想其实是圣弗兰西斯科·冯·阿西斯(1182一 1226)思想的复话。对此,我自已认为也是如此。从我 的大学时代起,我就是这个圣徒的最深刻思想的敬仰者。 他早就宜告,人类与生物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正是来 自天国的福音。但是他的听众认为,这只是是敬的诗数 而已,并不试图在地球上实现这一福音。这样,这一福 音就寂静和魔蔽地保存在由弗兰西斯科建立的敏团的度 信中。 而在做畏生命的伦理中,这种思想则是一种要求彻 底实现的人类思想。 (4) 1923年初,(文化和伦理的文稿可以付印了。但到 哪里去找出版者呢?实在没有什么好的指望。在德国, 当时人们都热中于斯宾格勒吸引人的、文笔出色的著作 414

西方的没蕃)。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文化历史地产生、 历史地繁荣、历史地衰落和死亡。这种悲刷性的思考方 式,符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精棹。斯宾格勒并不 研究文化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描述文化的历史命运, 那时,我怎样才能把我的真正地论证伦理和文化的 尝试公诺于众呢?我没有勇气为出版这部著作而去与任 何一个出版者联系。 艾米·马丁太太,她是一个与我关系密切的早迸的 阿尔萨斯牧师的遗捕,帮助我处理信件往来。她在前往 燕尼黑访问朋友时,要求我把手稿交给她。她试图在那 里找一个出版者。但是,她没热人。因此,当她路过贝 克出版社的书店时,就走了进去并要求和经理谈话。与 她见面的是经理代表阿尔贝斯先生。马丁太太向他表达 了自己的愿望:她要为我的文稿找一个出版者。阿尔贝 斯先生接受了文稿,浏览了第一页后说:“用不着审阅, 我们决定出版这一著作。阿尔贝特·史杯泽对我们并不 是一个陌生人. 贝克正好也是斯宾格物关于文化问题著作的出版 者。这样,我就结识了斯宾格勒。我们没有争斗,而是 或了朋友,作为朋友,我们就文化观点进行了辩论。 <文化和伦理出版于1923年,阿尔贝斯先生和我也 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5) 1924年2月,我间到了兰巴雷内。在那里,我仍保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