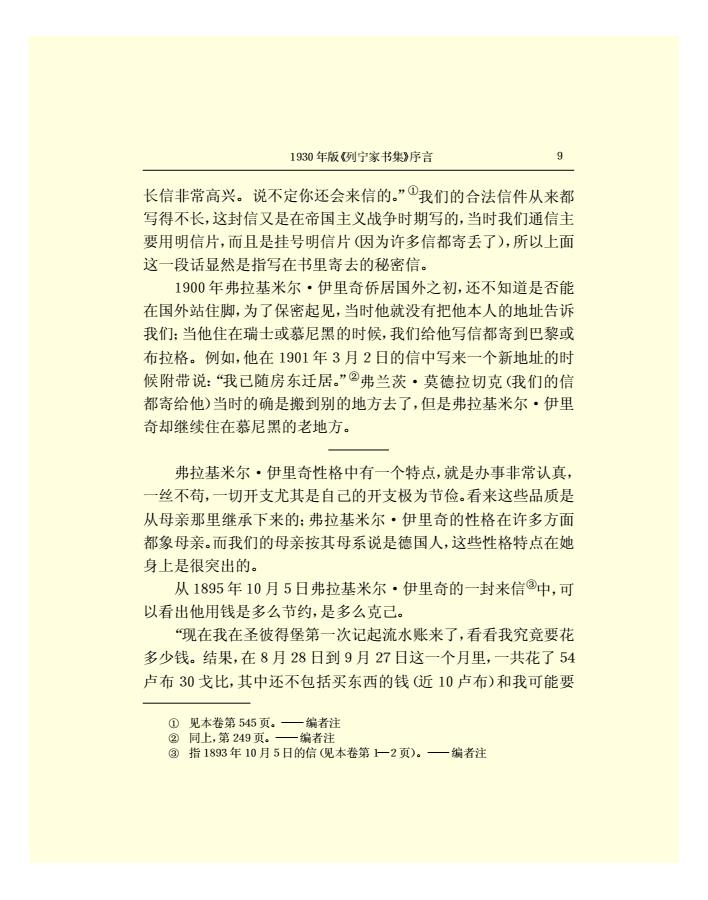
长信非常高兴。说不定你还会来信的。”①我们的合法信件从来都 写得不长,这封信又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写的,当时我们通信主 要用明信片,而且是挂号明信片(因为许多信都寄丢了),所以上面 这一段话显然是指写在书里寄去的秘密信。 1900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侨居国外之初,还不知道是否能 在国外站住脚,为了保密起见,当时他就没有把他本人的地址告诉 我们;当他住在瑞士或慕尼黑的时候,我们给他写信都寄到巴黎或 布拉格。例如,他在1901年3月2日的信中写来一个新地址的时 候附带说:“我已随房东迁居。”②弗兰茨·莫德拉切克(我们的信 都寄给他)当时的确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 奇却继续住在慕尼黑的老地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性格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办事非常认真, 一丝不苟,一切开支尤其是自己的开支极为节俭。看来这些品质是 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性格在许多方面 都象母亲。而我们的母亲按其母系说是德国人,这些性格特点在她 身上是很突出的。 从1895年10月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封来信③中,可 以看出他用钱是多么节约,是多么克己。 “现在我在圣彼得堡第一次记起流水账来了,看看我究竟要花 多少钱。结果,在8月28日到9月27日这一个月里,一共花了54 卢布30戈比,其中还不包括买东西的钱(近10卢布)和我可能要 1930年版《列宁家书集》序言 9 ① ② ③ 指1893年10月5日的信(见本卷第1—2页)。——编者注 同上,第249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545页。——编者注
长信非常高兴。说不定你还会来信的。”①我们的合法信件从来都 写得不长,这封信又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写的,当时我们通信主 要用明信片,而且是挂号明信片(因为许多信都寄丢了),所以上面 这一段话显然是指写在书里寄去的秘密信。 1900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侨居国外之初,还不知道是否能 在国外站住脚,为了保密起见,当时他就没有把他本人的地址告诉 我们;当他住在瑞士或慕尼黑的时候,我们给他写信都寄到巴黎或 布拉格。例如,他在1901年3月2日的信中写来一个新地址的时 候附带说:“我已随房东迁居。”②弗兰茨·莫德拉切克(我们的信 都寄给他)当时的确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 奇却继续住在慕尼黑的老地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性格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办事非常认真, 一丝不苟,一切开支尤其是自己的开支极为节俭。看来这些品质是 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性格在许多方面 都象母亲。而我们的母亲按其母系说是德国人,这些性格特点在她 身上是很突出的。 从1895年10月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封来信③中,可 以看出他用钱是多么节约,是多么克己。 “现在我在圣彼得堡第一次记起流水账来了,看看我究竟要花 多少钱。结果,在8月28日到9月27日这一个月里,一共花了54 卢布30戈比,其中还不包括买东西的钱(近10卢布)和我可能要 1930年版《列宁家书集》序言 9 ① ② ③ 指1893年10月5日的信(见本卷第1—2页)。——编者注 同上,第249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545页。——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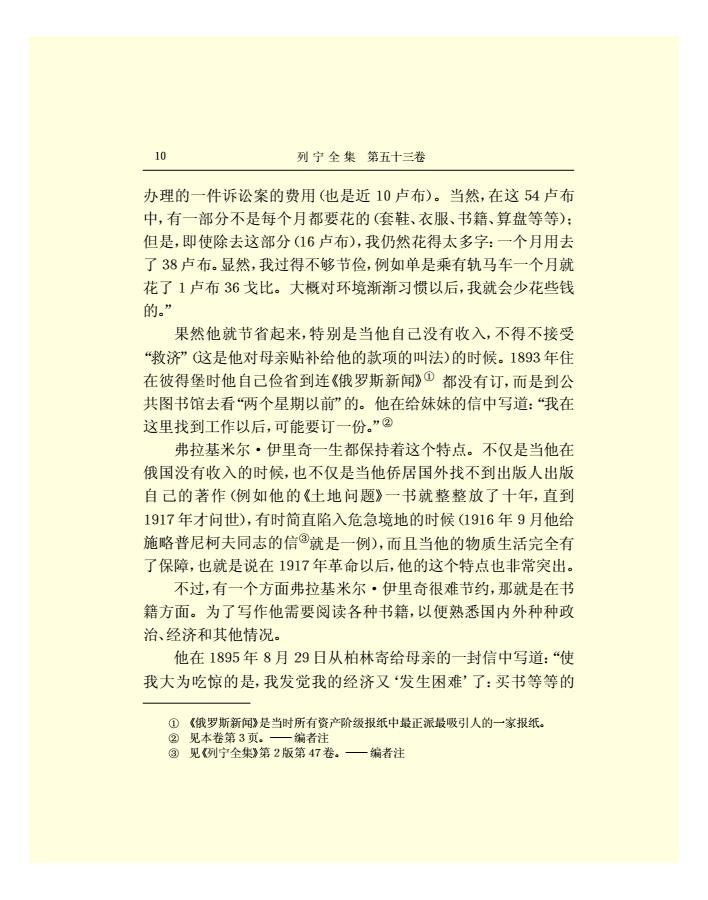
办理的一件诉讼案的费用(也是近10卢布)。当然,在这54卢布 中,有一部分不是每个月都要花的(套鞋、衣服、书籍、算盘等等); 但是,即使除去这部分(16卢布),我仍然花得太多字:一个月用去 了38卢布。显然,我过得不够节俭,例如单是乘有轨马车一个月就 花了1卢布36戈比。大概对环境渐渐习惯以后,我就会少花些钱 的。” 果然他就节省起来,特别是当他自己没有收入,不得不接受 “救济”(这是他对母亲贴补给他的款项的叫法)的时候。1893年住 在彼得堡时他自己俭省到连《俄罗斯新闻》① 都没有订,而是到公 共图书馆去看“两个星期以前”的。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在 这里找到工作以后,可能要订一份。”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生都保持着这个特点。不仅是当他在 俄国没有收入的时候,也不仅是当他侨居国外找不到出版人出版 自 己的著作(例如他的《土地问题》一书就整整放了十年,直到 1917年才问世),有时简直陷入危急境地的时候(1916年9月他给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信③就是一例),而且当他的物质生活完全有 了保障,也就是说在1917年革命以后,他的这个特点也非常突出。 不过,有一个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难节约,那就是在书 籍方面。为了写作他需要阅读各种书籍,以便熟悉国内外种种政 治、经济和其他情况。 他在1895年8月29日从柏林寄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使 我大为吃惊的是,我发觉我的经济又‘发生困难’了:买书等等的 10 列 宁 全 集 第五十三卷 ① ② ③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 编者注 见本卷第3页。—— 编者注 《俄罗斯新闻》是当时所有资产阶级报纸中最正派最吸引人的一家报纸
办理的一件诉讼案的费用(也是近10卢布)。当然,在这54卢布 中,有一部分不是每个月都要花的(套鞋、衣服、书籍、算盘等等); 但是,即使除去这部分(16卢布),我仍然花得太多字:一个月用去 了38卢布。显然,我过得不够节俭,例如单是乘有轨马车一个月就 花了1卢布36戈比。大概对环境渐渐习惯以后,我就会少花些钱 的。” 果然他就节省起来,特别是当他自己没有收入,不得不接受 “救济”(这是他对母亲贴补给他的款项的叫法)的时候。1893年住 在彼得堡时他自己俭省到连《俄罗斯新闻》① 都没有订,而是到公 共图书馆去看“两个星期以前”的。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在 这里找到工作以后,可能要订一份。”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生都保持着这个特点。不仅是当他在 俄国没有收入的时候,也不仅是当他侨居国外找不到出版人出版 自 己的著作(例如他的《土地问题》一书就整整放了十年,直到 1917年才问世),有时简直陷入危急境地的时候(1916年9月他给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信③就是一例),而且当他的物质生活完全有 了保障,也就是说在1917年革命以后,他的这个特点也非常突出。 不过,有一个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难节约,那就是在书 籍方面。为了写作他需要阅读各种书籍,以便熟悉国内外种种政 治、经济和其他情况。 他在1895年8月29日从柏林寄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使 我大为吃惊的是,我发觉我的经济又‘发生困难’了:买书等等的 10 列 宁 全 集 第五十三卷 ① ② ③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 编者注 见本卷第3页。—— 编者注 《俄罗斯新闻》是当时所有资产阶级报纸中最正派最吸引人的一家报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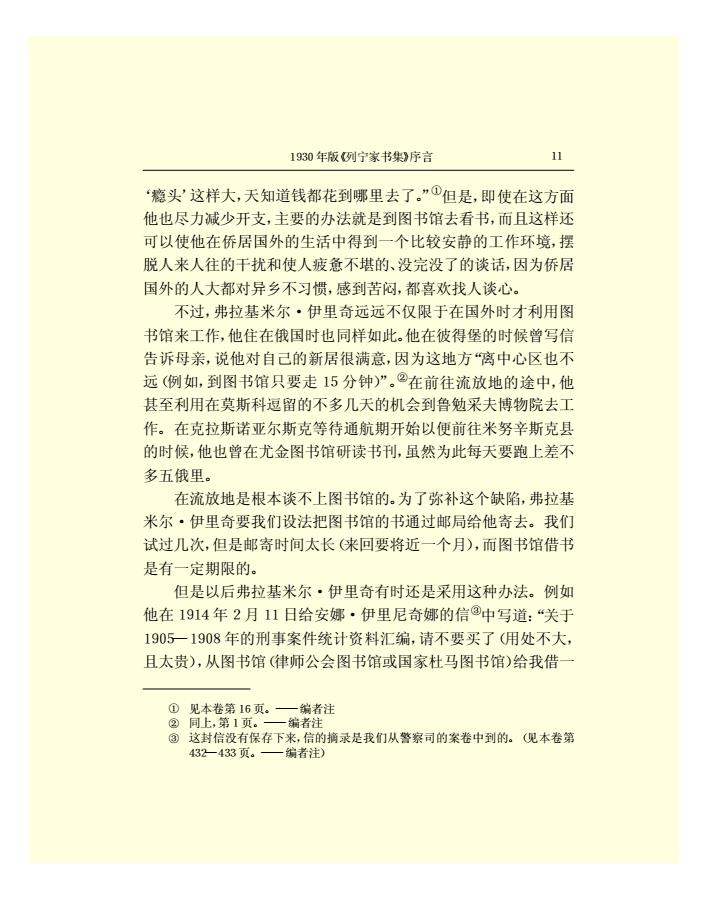
‘瘾头’这样大,天知道钱都花到哪里去了。”①但是,即使在这方面 他也尽力减少开支,主要的办法就是到图书馆去看书,而且这样还 可以使他在侨居国外的生活中得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工作环境,摆 脱人来人往的干扰和使人疲惫不堪的、没完没了的谈话,因为侨居 国外的人大都对异乡不习惯,感到苦闷,都喜欢找人谈心。 不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远远不仅限于在国外时才利用图 书馆来工作,他住在俄国时也同样如此。他在彼得堡的时候曾写信 告诉母亲,说他对自己的新居很满意,因为这地方“离中心区也不 远(例如,到图书馆只要走15分钟)”。②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他 甚至利用在莫斯科逗留的不多几天的机会到鲁勉采夫博物院去工 作。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待通航期开始以便前往米努辛斯克县 的时候,他也曾在尤金图书馆研读书刊,虽然为此每天要跑上差不 多五俄里。 在流放地是根本谈不上图书馆的。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弗拉基 米尔·伊里奇要我们设法把图书馆的书通过邮局给他寄去。我们 试过几次,但是邮寄时间太长(来回要将近一个月),而图书馆借书 是有一定期限的。 但是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还是采用这种办法。例如 他在1914年2月11日给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信③中写道:“关于 1905—1908年的刑事案件统计资料汇编,请不要买了(用处不大, 且太贵),从图书馆(律师公会图书馆或国家杜马图书馆)给我借一 1930年版《列宁家书集》序言 11 ① ② ③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信的摘录是我们从警察司的案卷中到的。(见本卷第 432—433页。——编者注) 同上,第1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16页。——编者注
‘瘾头’这样大,天知道钱都花到哪里去了。”①但是,即使在这方面 他也尽力减少开支,主要的办法就是到图书馆去看书,而且这样还 可以使他在侨居国外的生活中得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工作环境,摆 脱人来人往的干扰和使人疲惫不堪的、没完没了的谈话,因为侨居 国外的人大都对异乡不习惯,感到苦闷,都喜欢找人谈心。 不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远远不仅限于在国外时才利用图 书馆来工作,他住在俄国时也同样如此。他在彼得堡的时候曾写信 告诉母亲,说他对自己的新居很满意,因为这地方“离中心区也不 远(例如,到图书馆只要走15分钟)”。②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他 甚至利用在莫斯科逗留的不多几天的机会到鲁勉采夫博物院去工 作。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待通航期开始以便前往米努辛斯克县 的时候,他也曾在尤金图书馆研读书刊,虽然为此每天要跑上差不 多五俄里。 在流放地是根本谈不上图书馆的。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弗拉基 米尔·伊里奇要我们设法把图书馆的书通过邮局给他寄去。我们 试过几次,但是邮寄时间太长(来回要将近一个月),而图书馆借书 是有一定期限的。 但是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还是采用这种办法。例如 他在1914年2月11日给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信③中写道:“关于 1905—1908年的刑事案件统计资料汇编,请不要买了(用处不大, 且太贵),从图书馆(律师公会图书馆或国家杜马图书馆)给我借一 1930年版《列宁家书集》序言 11 ① ② ③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信的摘录是我们从警察司的案卷中到的。(见本卷第 432—433页。——编者注) 同上,第1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16页。——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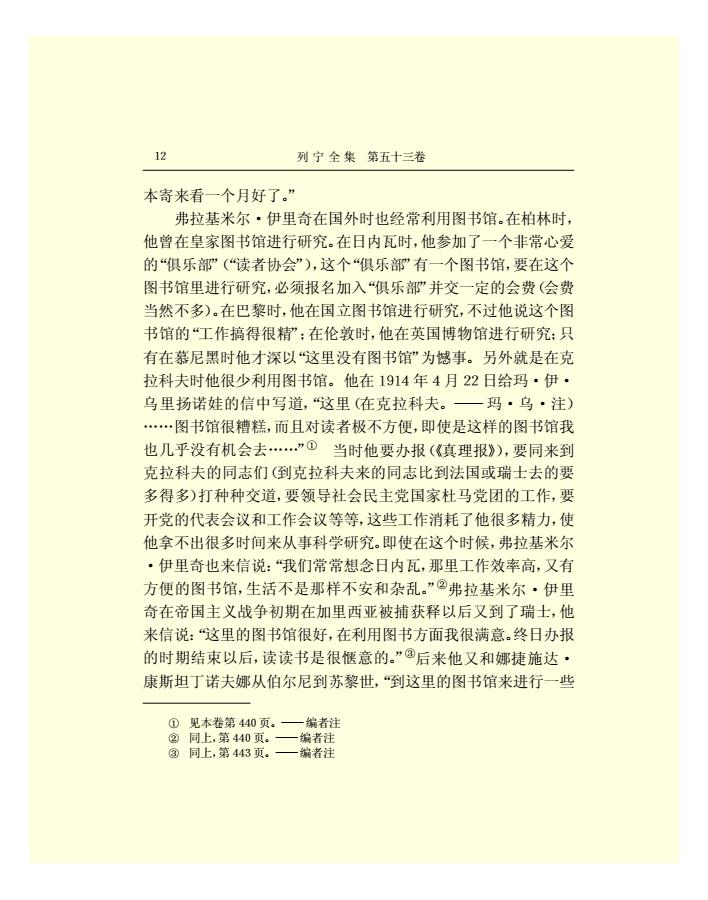
本寄来看一个月好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国外时也经常利用图书馆。在柏林时, 他曾在皇家图书馆进行研究。在日内瓦时,他参加了一个非常心爱 的“俱乐部”(“读者协会”),这个“俱乐部”有一个图书馆,要在这个 图书馆里进行研究,必须报名加入“俱乐部”并交一定的会费(会费 当然不多)。在巴黎时,他在国立图书馆进行研究,不过他说这个图 书馆的“工作搞得很精”;在伦敦时,他在英国博物馆进行研究;只 有在慕尼黑时他才深以“这里没有图书馆”为憾事。另外就是在克 拉科夫时他很少利用图书馆。他在1914年4月22日给玛·伊· 乌里扬诺娃的信中写道,“这里(在克拉科夫。—— 玛·乌·注) ……图书馆很糟糕,而且对读者极不方便,即使是这样的图书馆我 也几乎没有机会去……”① 当时他要办报(《真理报》),要同来到 克拉科夫的同志们(到克拉科夫来的同志比到法国或瑞士去的要 多得多)打种种交道,要领导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的工作,要 开党的代表会议和工作会议等等,这些工作消耗了他很多精力,使 他拿不出很多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即使在这个时候,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也来信说:“我们常常想念日内瓦,那里工作效率高,又有 方便的图书馆,生活不是那样不安和杂乱。”②弗拉基米尔·伊里 奇在帝国主义战争初期在加里西亚被捕获释以后又到了瑞士,他 来信说:“这里的图书馆很好,在利用图书方面我很满意。终日办报 的时期结束以后,读读书是很惬意的。”③后来他又和娜捷施达· 康斯坦丁诺夫娜从伯尔尼到苏黎世,“到这里的图书馆来进行一些 12 列 宁 全 集 第五十三卷 ① ② ③ 同上,第443页。——编者注 同上,第440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440页。——编者注
本寄来看一个月好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国外时也经常利用图书馆。在柏林时, 他曾在皇家图书馆进行研究。在日内瓦时,他参加了一个非常心爱 的“俱乐部”(“读者协会”),这个“俱乐部”有一个图书馆,要在这个 图书馆里进行研究,必须报名加入“俱乐部”并交一定的会费(会费 当然不多)。在巴黎时,他在国立图书馆进行研究,不过他说这个图 书馆的“工作搞得很精”;在伦敦时,他在英国博物馆进行研究;只 有在慕尼黑时他才深以“这里没有图书馆”为憾事。另外就是在克 拉科夫时他很少利用图书馆。他在1914年4月22日给玛·伊· 乌里扬诺娃的信中写道,“这里(在克拉科夫。—— 玛·乌·注) ……图书馆很糟糕,而且对读者极不方便,即使是这样的图书馆我 也几乎没有机会去……”① 当时他要办报(《真理报》),要同来到 克拉科夫的同志们(到克拉科夫来的同志比到法国或瑞士去的要 多得多)打种种交道,要领导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的工作,要 开党的代表会议和工作会议等等,这些工作消耗了他很多精力,使 他拿不出很多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即使在这个时候,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也来信说:“我们常常想念日内瓦,那里工作效率高,又有 方便的图书馆,生活不是那样不安和杂乱。”②弗拉基米尔·伊里 奇在帝国主义战争初期在加里西亚被捕获释以后又到了瑞士,他 来信说:“这里的图书馆很好,在利用图书方面我很满意。终日办报 的时期结束以后,读读书是很惬意的。”③后来他又和娜捷施达· 康斯坦丁诺夫娜从伯尔尼到苏黎世,“到这里的图书馆来进行一些 12 列 宁 全 集 第五十三卷 ① ② ③ 同上,第443页。——编者注 同上,第440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440页。——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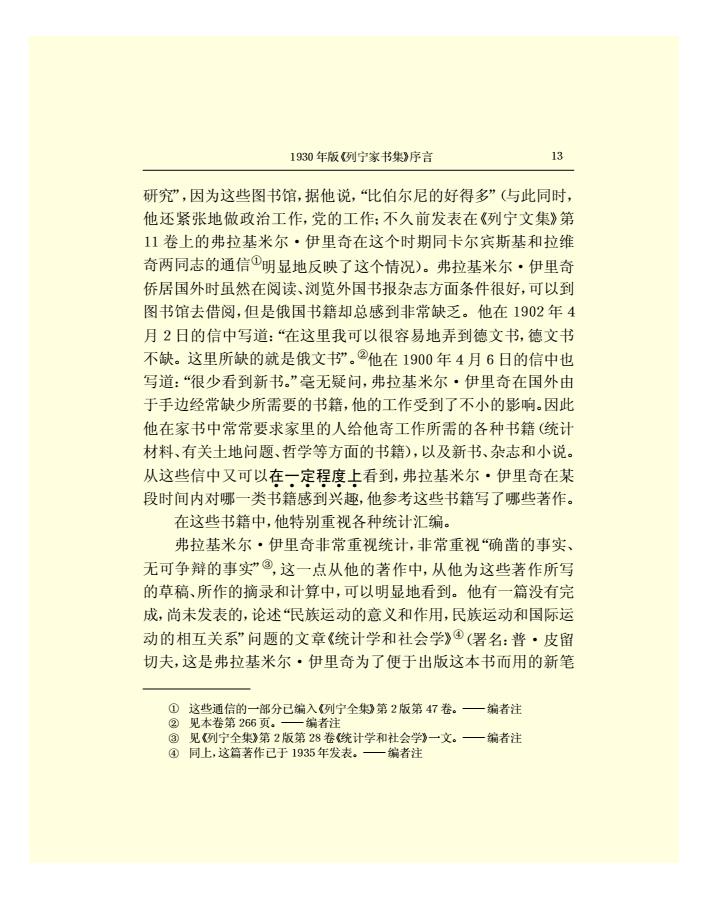
研究”,因为这些图书馆,据他说,“比伯尔尼的好得多”(与此同时, 他还紧张地做政治工作,党的工作;不久前发表在《列宁文集》第 11卷上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个时期同卡尔宾斯基和拉维 奇两同志的通信①明显地反映了这个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侨居国外时虽然在阅读、浏览外国书报杂志方面条件很好,可以到 图书馆去借阅,但是俄国书籍却总感到非常缺乏。他在1902年4 月2日的信中写道:“在这里我可以很容易地弄到德文书,德文书 不缺。这里所缺的就是俄文书”。②他在1900年4月6日的信中也 写道:“很少看到新书。”毫无疑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国外由 于手边经常缺少所需要的书籍,他的工作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因此 他在家书中常常要求家里的人给他寄工作所需的各种书籍(统计 材料、有关土地问题、哲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新书、杂志和小说。 从这些信中又可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某 段时间内对哪一类书籍感到兴趣,他参考这些书籍写了哪些著作。 在这些书籍中,他特别重视各种统计汇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统计,非常重视“确凿的事实、 无可争辩的事实”③,这一点从他的著作中,从他为这些著作所写 的草稿、所作的摘录和计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有一篇没有完 成,尚未发表的,论述“民族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民族运动和国际运 动的相互关系”问题的文章《统计学和社会学》④(署名:普·皮留 切夫,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了便于出版这本书而用的新笔 1930年版《列宁家书集》序言 13 ① ② ③ ④ 同上,这篇著作已于1935年发表。——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统计学和社会学》一文。——编者注 见本卷第266页。——编者注 这些通信的一部分已编入《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编者注
研究”,因为这些图书馆,据他说,“比伯尔尼的好得多”(与此同时, 他还紧张地做政治工作,党的工作;不久前发表在《列宁文集》第 11卷上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个时期同卡尔宾斯基和拉维 奇两同志的通信①明显地反映了这个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侨居国外时虽然在阅读、浏览外国书报杂志方面条件很好,可以到 图书馆去借阅,但是俄国书籍却总感到非常缺乏。他在1902年4 月2日的信中写道:“在这里我可以很容易地弄到德文书,德文书 不缺。这里所缺的就是俄文书”。②他在1900年4月6日的信中也 写道:“很少看到新书。”毫无疑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国外由 于手边经常缺少所需要的书籍,他的工作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因此 他在家书中常常要求家里的人给他寄工作所需的各种书籍(统计 材料、有关土地问题、哲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新书、杂志和小说。 从这些信中又可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某 段时间内对哪一类书籍感到兴趣,他参考这些书籍写了哪些著作。 在这些书籍中,他特别重视各种统计汇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统计,非常重视“确凿的事实、 无可争辩的事实”③,这一点从他的著作中,从他为这些著作所写 的草稿、所作的摘录和计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有一篇没有完 成,尚未发表的,论述“民族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民族运动和国际运 动的相互关系”问题的文章《统计学和社会学》④(署名:普·皮留 切夫,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了便于出版这本书而用的新笔 1930年版《列宁家书集》序言 13 ① ② ③ ④ 同上,这篇著作已于1935年发表。——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统计学和社会学》一文。——编者注 见本卷第266页。——编者注 这些通信的一部分已编入《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