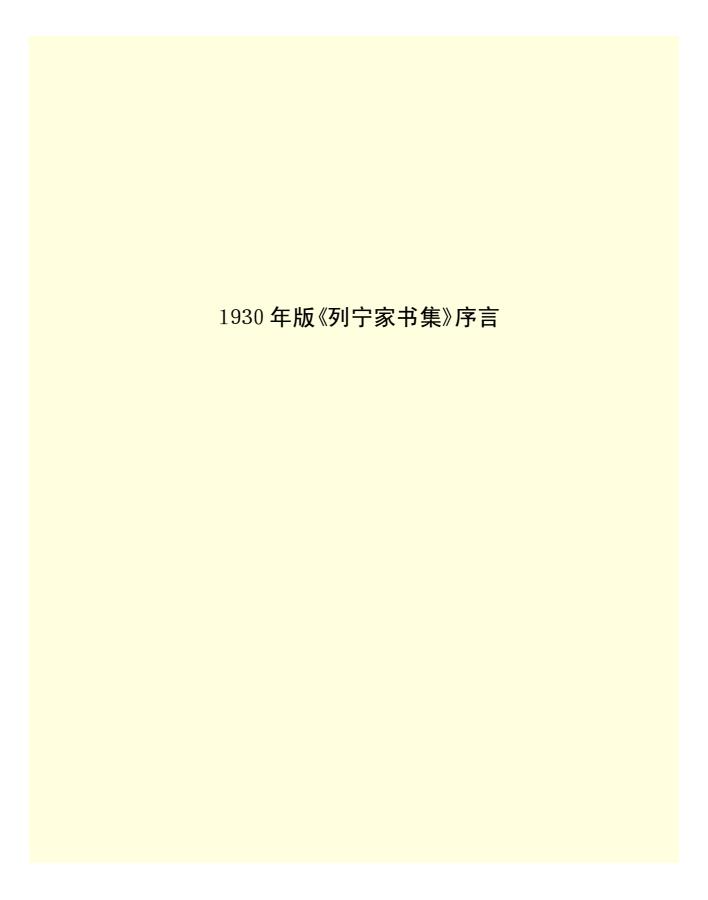
1930年版《列宁家书集》序言
1930年版《列宁家书集》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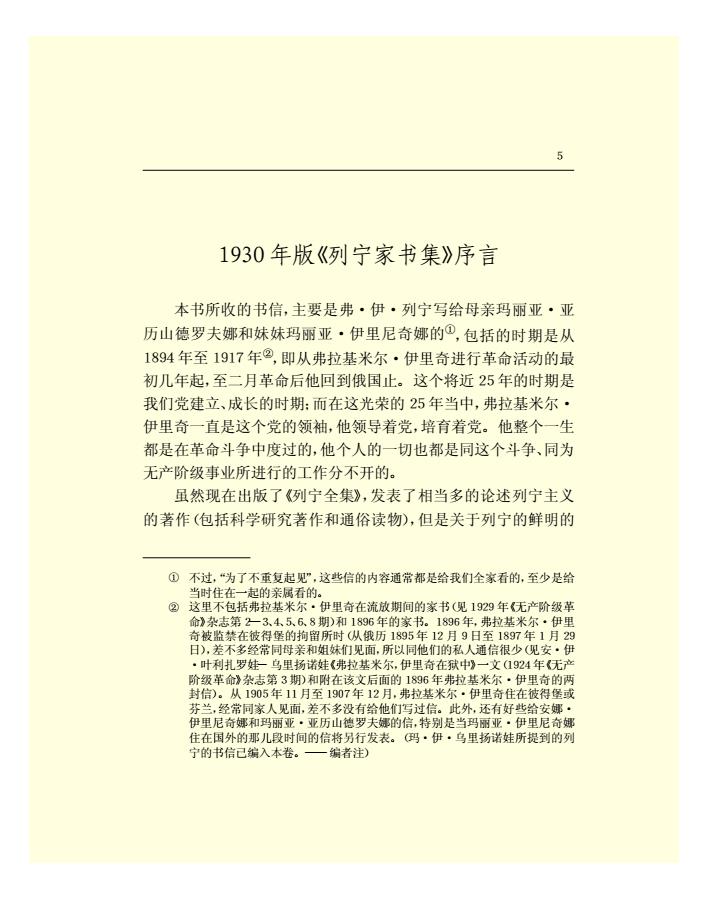
1930年版《列宁家书集》序言 本书所收的书信,主要是弗·伊·列宁写给母亲玛丽亚·亚 历山德罗夫娜和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①,包括的时期是从 1894年至1917年②,即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行革命活动的最 初几年起,至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俄国止。这个将近25年的时期是 我们党建立、成长的时期;而在这光荣的25年当中,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一直是这个党的领袖,他领导着党,培育着党。他整个一生 都是在革命斗争中度过的,他个人的一切也都是同这个斗争、同为 无产阶级事业所进行的工作分不开的。 虽然现在出版了《列宁全集》,发表了相当多的论述列宁主义 的著作(包括科学研究著作和通俗读物),但是关于列宁的鲜明的 5 ① ② 这里不包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流放期间的家书(见1929年《无产阶级革 命》杂志第2—3、4、5、6、8期)和1896年的家书。1896年,弗拉基米尔·伊里 奇被监禁在彼得堡的拘留所时(从俄历1895年12月9日至1897年1月29 日),差不多经常同母亲和姐妹们见面,所以同他们的私人通信很少(见安·伊 ·叶利扎罗娃- 乌里扬诺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狱中》一文(1924年《无产 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和附在该文后面的1896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两 封信)。从1905年11月至1907年12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彼得堡或 芬兰,经常同家人见面,差不多没有给他们写过信。此外,还有好些给安娜· 伊里尼奇娜和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特别是当玛丽亚·伊里尼奇娜 住在国外的那儿段时间的信将另行发表。(玛·伊·乌里扬诺娃所提到的列 宁的书信已编入本卷。—— 编者注) 不过,“为了不重复起见”,这些信的内容通常都是给我们全家看的,至少是给 当时住在一起的亲属看的
1930年版《列宁家书集》序言 本书所收的书信,主要是弗·伊·列宁写给母亲玛丽亚·亚 历山德罗夫娜和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①,包括的时期是从 1894年至1917年②,即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行革命活动的最 初几年起,至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俄国止。这个将近25年的时期是 我们党建立、成长的时期;而在这光荣的25年当中,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一直是这个党的领袖,他领导着党,培育着党。他整个一生 都是在革命斗争中度过的,他个人的一切也都是同这个斗争、同为 无产阶级事业所进行的工作分不开的。 虽然现在出版了《列宁全集》,发表了相当多的论述列宁主义 的著作(包括科学研究著作和通俗读物),但是关于列宁的鲜明的 5 ① ② 这里不包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流放期间的家书(见1929年《无产阶级革 命》杂志第2—3、4、5、6、8期)和1896年的家书。1896年,弗拉基米尔·伊里 奇被监禁在彼得堡的拘留所时(从俄历1895年12月9日至1897年1月29 日),差不多经常同母亲和姐妹们见面,所以同他们的私人通信很少(见安·伊 ·叶利扎罗娃- 乌里扬诺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狱中》一文(1924年《无产 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和附在该文后面的1896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两 封信)。从1905年11月至1907年12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彼得堡或 芬兰,经常同家人见面,差不多没有给他们写过信。此外,还有好些给安娜· 伊里尼奇娜和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特别是当玛丽亚·伊里尼奇娜 住在国外的那儿段时间的信将另行发表。(玛·伊·乌里扬诺娃所提到的列 宁的书信已编入本卷。—— 编者注) 不过,“为了不重复起见”,这些信的内容通常都是给我们全家看的,至少是给 当时住在一起的亲属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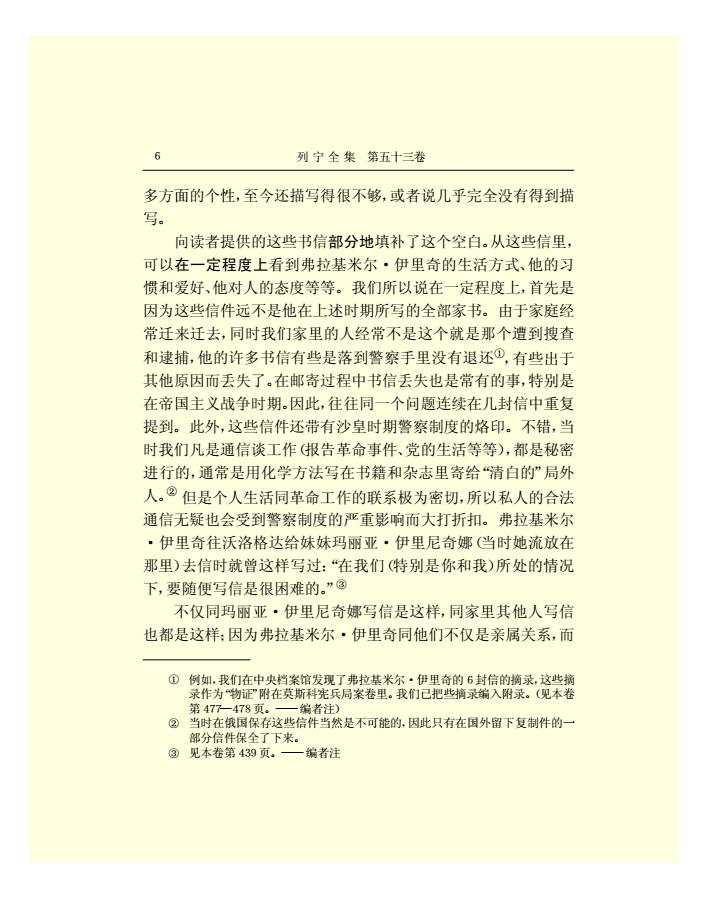
多方面的个性,至今还描写得很不够,或者说几乎完全没有得到描 写。 向读者提供的这些书信部分地填补了这个空白。从这些信里,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活方式、他的习 惯和爱好、他对人的态度等等。我们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是 因为这些信件远不是他在上述时期所写的全部家书。由于家庭经 常迁来迁去,同时我们家里的人经常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遭到搜查 和逮捕,他的许多书信有些是落到警察手里没有退还①,有些出于 其他原因而丢失了。在邮寄过程中书信丢失也是常有的事,特别是 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因此,往往同一个问题连续在几封信中重复 提到。此外,这些信件还带有沙皇时期警察制度的烙印。不错,当 时我们凡是通信谈工作(报告革命事件、党的生活等等),都是秘密 进行的,通常是用化学方法写在书籍和杂志里寄给“清白的”局外 人。② 但是个人生活同革命工作的联系极为密切,所以私人的合法 通信无疑也会受到警察制度的严重影响而大打折扣。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往沃洛格达给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当时她流放在 那里)去信时就曾这样写过:“在我们(特别是你和我)所处的情况 下,要随便写信是很困难的。”③ 不仅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写信是这样,同家里其他人写信 也都是这样;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他们不仅是亲属关系,而 6 列 宁 全 集 第五十三卷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439页。——编者注 当时在俄国保存这些信件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在国外留下复制件的一 部分信件保全了下来。 例如,我们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6封信的摘录,这些摘 录作为“物证”附在莫斯科宪兵局案卷里。我们已把些摘录编入附录。(见本卷 第477—478页。——编者注)
多方面的个性,至今还描写得很不够,或者说几乎完全没有得到描 写。 向读者提供的这些书信部分地填补了这个空白。从这些信里,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活方式、他的习 惯和爱好、他对人的态度等等。我们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是 因为这些信件远不是他在上述时期所写的全部家书。由于家庭经 常迁来迁去,同时我们家里的人经常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遭到搜查 和逮捕,他的许多书信有些是落到警察手里没有退还①,有些出于 其他原因而丢失了。在邮寄过程中书信丢失也是常有的事,特别是 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因此,往往同一个问题连续在几封信中重复 提到。此外,这些信件还带有沙皇时期警察制度的烙印。不错,当 时我们凡是通信谈工作(报告革命事件、党的生活等等),都是秘密 进行的,通常是用化学方法写在书籍和杂志里寄给“清白的”局外 人。② 但是个人生活同革命工作的联系极为密切,所以私人的合法 通信无疑也会受到警察制度的严重影响而大打折扣。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往沃洛格达给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当时她流放在 那里)去信时就曾这样写过:“在我们(特别是你和我)所处的情况 下,要随便写信是很困难的。”③ 不仅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写信是这样,同家里其他人写信 也都是这样;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他们不仅是亲属关系,而 6 列 宁 全 集 第五十三卷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439页。——编者注 当时在俄国保存这些信件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在国外留下复制件的一 部分信件保全了下来。 例如,我们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6封信的摘录,这些摘 录作为“物证”附在莫斯科宪兵局案卷里。我们已把些摘录编入附录。(见本卷 第477—478页。——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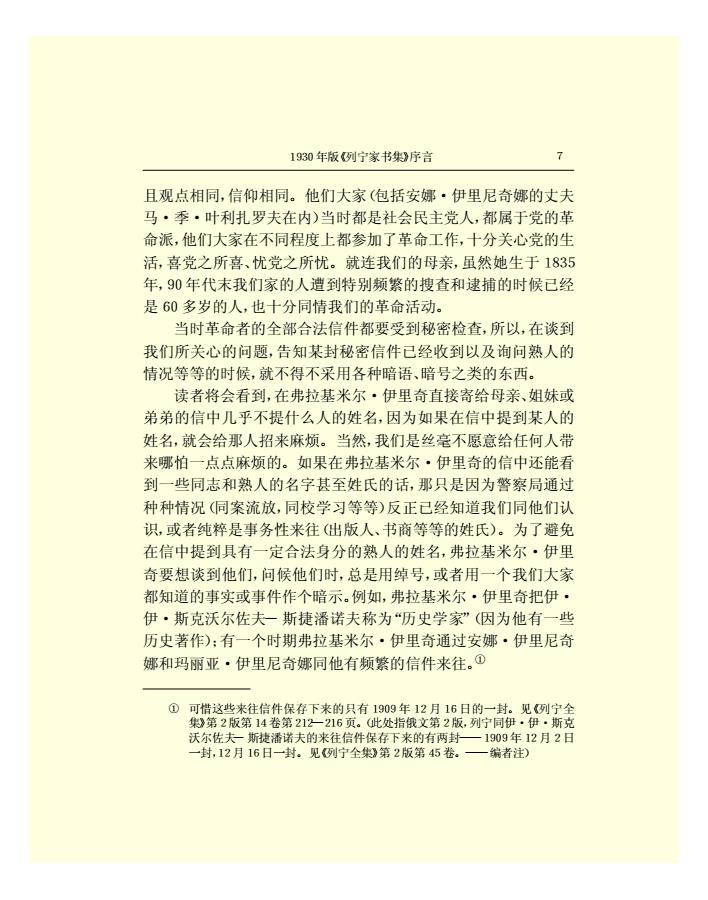
且观点相同,信仰相同。他们大家(包括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丈夫 马·季·叶利扎罗夫在内)当时都是社会民主党人,都属于党的革 命派,他们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十分关心党的生 活,喜党之所喜、忧党之所忧。就连我们的母亲,虽然她生于1835 年,90年代末我们家的人遭到特别频繁的搜查和逮捕的时候已经 是60多岁的人,也十分同情我们的革命活动。 当时革命者的全部合法信件都要受到秘密检查,所以,在谈到 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告知某封秘密信件已经收到以及询问熟人的 情况等等的时候,就不得不采用各种暗语、暗号之类的东西。 读者将会看到,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直接寄给母亲、姐妹或 弟弟的信中几乎不提什么人的姓名,因为如果在信中提到某人的 姓名,就会给那人招来麻烦。当然,我们是丝毫不愿意给任何人带 来哪怕一点点麻烦的。如果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中还能看 到一些同志和熟人的名字甚至姓氏的话,那只是因为警察局通过 种种情况(同案流放,同校学习等等)反正已经知道我们同他们认 识,或者纯粹是事务性来往(出版人、书商等等的姓氏)。为了避免 在信中提到具有一定合法身分的熟人的姓名,弗拉基米尔·伊里 奇要想谈到他们,问候他们时,总是用绰号,或者用一个我们大家 都知道的事实或事件作个暗示。例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伊· 伊·斯克沃尔佐夫- 斯捷潘诺夫称为“历史学家”(因为他有一些 历史著作);有一个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安娜·伊里尼奇 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同他有频繁的信件来往。① 1930年版《列宁家书集》序言 7 ① 可惜这些来往信件保存下来的只有1909年12月16日的一封。见《列宁全 集》第2版第14卷第212—216页。(此处指俄文第2版,列宁同伊·伊·斯克 沃尔佐夫- 斯捷潘诺夫的来往信件保存下来的有两封——1909年12月2日 一封,12月16日一封。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编者注)
且观点相同,信仰相同。他们大家(包括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丈夫 马·季·叶利扎罗夫在内)当时都是社会民主党人,都属于党的革 命派,他们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十分关心党的生 活,喜党之所喜、忧党之所忧。就连我们的母亲,虽然她生于1835 年,90年代末我们家的人遭到特别频繁的搜查和逮捕的时候已经 是60多岁的人,也十分同情我们的革命活动。 当时革命者的全部合法信件都要受到秘密检查,所以,在谈到 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告知某封秘密信件已经收到以及询问熟人的 情况等等的时候,就不得不采用各种暗语、暗号之类的东西。 读者将会看到,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直接寄给母亲、姐妹或 弟弟的信中几乎不提什么人的姓名,因为如果在信中提到某人的 姓名,就会给那人招来麻烦。当然,我们是丝毫不愿意给任何人带 来哪怕一点点麻烦的。如果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中还能看 到一些同志和熟人的名字甚至姓氏的话,那只是因为警察局通过 种种情况(同案流放,同校学习等等)反正已经知道我们同他们认 识,或者纯粹是事务性来往(出版人、书商等等的姓氏)。为了避免 在信中提到具有一定合法身分的熟人的姓名,弗拉基米尔·伊里 奇要想谈到他们,问候他们时,总是用绰号,或者用一个我们大家 都知道的事实或事件作个暗示。例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伊· 伊·斯克沃尔佐夫- 斯捷潘诺夫称为“历史学家”(因为他有一些 历史著作);有一个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安娜·伊里尼奇 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同他有频繁的信件来往。① 1930年版《列宁家书集》序言 7 ① 可惜这些来往信件保存下来的只有1909年12月16日的一封。见《列宁全 集》第2版第14卷第212—216页。(此处指俄文第2版,列宁同伊·伊·斯克 沃尔佐夫- 斯捷潘诺夫的来往信件保存下来的有两封——1909年12月2日 一封,12月16日一封。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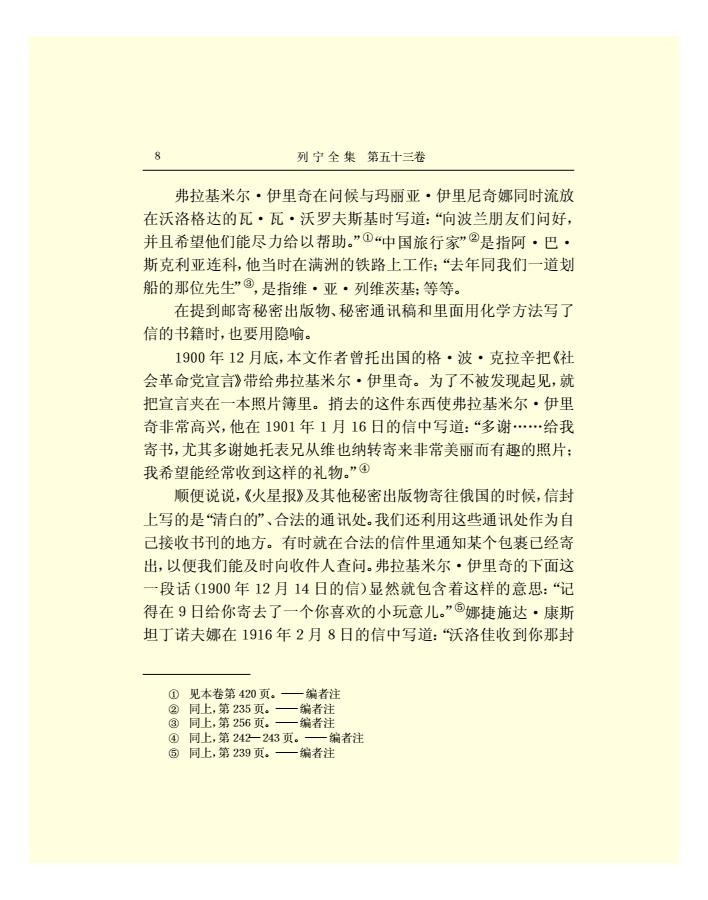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问候与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同时流放 在沃洛格达的瓦·瓦·沃罗夫斯基时写道:“向波兰朋友们问好, 并且希望他们能尽力给以帮助。”①“中国旅行家”②是指阿·巴· 斯克利亚连科,他当时在满洲的铁路上工作;“去年同我们一道划 船的那位先生”③,是指维·亚·列维茨基;等等。 在提到邮寄秘密出版物、秘密通讯稿和里面用化学方法写了 信的书籍时,也要用隐喻。 1900年12月底,本文作者曾托出国的格·波·克拉辛把《社 会革命党宣言》带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了不被发现起见,就 把宣言夹在一本照片簿里。捎去的这件东西使弗拉基米尔·伊里 奇非常高兴,他在1901年1月16日的信中写道:“多谢……给我 寄书,尤其多谢她托表兄从维也纳转寄来非常美丽而有趣的照片; 我希望能经常收到这样的礼物。”④ 顺便说说,《火星报》及其他秘密出版物寄往俄国的时候,信封 上写的是“清白的”、合法的通讯处。我们还利用这些通讯处作为自 己接收书刊的地方。有时就在合法的信件里通知某个包裹已经寄 出,以便我们能及时向收件人查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下面这 一段话(1900年12月14日的信)显然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记 得在9日给你寄去了一个你喜欢的小玩意儿。”⑤娜捷施达·康斯 坦丁诺夫娜在1916年2月8日的信中写道:“沃洛佳收到你那封 8 列 宁 全 集 第五十三卷 ① ② ③ ④ ⑤ 同上,第239页。——编者注 同上,第242—243页。——编者注 同上,第256页。——编者注 同上,第235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420页。——编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问候与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同时流放 在沃洛格达的瓦·瓦·沃罗夫斯基时写道:“向波兰朋友们问好, 并且希望他们能尽力给以帮助。”①“中国旅行家”②是指阿·巴· 斯克利亚连科,他当时在满洲的铁路上工作;“去年同我们一道划 船的那位先生”③,是指维·亚·列维茨基;等等。 在提到邮寄秘密出版物、秘密通讯稿和里面用化学方法写了 信的书籍时,也要用隐喻。 1900年12月底,本文作者曾托出国的格·波·克拉辛把《社 会革命党宣言》带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了不被发现起见,就 把宣言夹在一本照片簿里。捎去的这件东西使弗拉基米尔·伊里 奇非常高兴,他在1901年1月16日的信中写道:“多谢……给我 寄书,尤其多谢她托表兄从维也纳转寄来非常美丽而有趣的照片; 我希望能经常收到这样的礼物。”④ 顺便说说,《火星报》及其他秘密出版物寄往俄国的时候,信封 上写的是“清白的”、合法的通讯处。我们还利用这些通讯处作为自 己接收书刊的地方。有时就在合法的信件里通知某个包裹已经寄 出,以便我们能及时向收件人查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下面这 一段话(1900年12月14日的信)显然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记 得在9日给你寄去了一个你喜欢的小玩意儿。”⑤娜捷施达·康斯 坦丁诺夫娜在1916年2月8日的信中写道:“沃洛佳收到你那封 8 列 宁 全 集 第五十三卷 ① ② ③ ④ ⑤ 同上,第239页。——编者注 同上,第242—243页。——编者注 同上,第256页。——编者注 同上,第235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420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