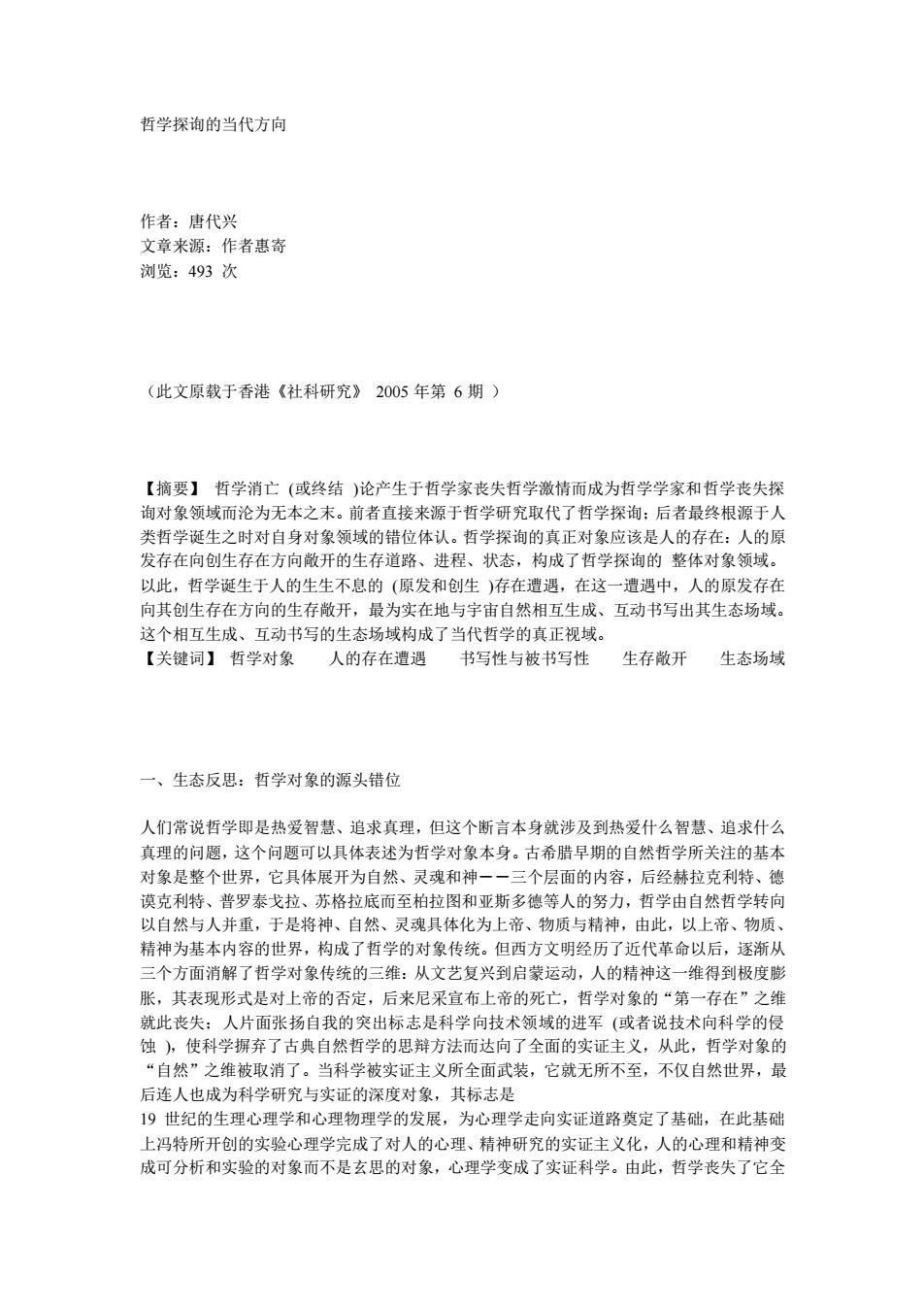
哲学探询的当代方向 作者:唐代兴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刘览:493次 (此文原载于香港《社科研究》2005年第6期) 【摘要】哲学消亡(或终结)论产生于哲学家丧失哲学激情而成为哲学学家和哲学丧失探 询对象领域而沦为无本之末。前者直接来源于哲学研究取代了哲学探询:后者最终根源于人 类哲学证生之时对自身对象苑域的错位体认。哲学探询的直正对象应该是人的存在:人的原 发存在向创生存在方向敞开的生存道路、进程、状态,构成了哲学探询的整体对象领域。 以此,哲学诞生于人的生生不总的(原发和创生)存在遭遇,在这一遭遇中,人的原发存 向其创生存在方向的生存敞开,最为实在地与字宙自然相互生成、互动书写出其生态场域。 这个相互生成、互动书写的生态场域构成了当代哲学的真正视域。 【关健词】哲学对象人的存在遭遇书写性与被书写性生存散开生态场域 一、生态反思:哲学对象的源头错位 人们常说哲学即是热爱智慧、追求真理,但这个断言本身就涉及到热爱什么智慧、追求什么 真理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具体表述为哲学对象本身。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所关注的基本 对象是整个世界,它具体展开为自然、灵魂和神一一三个层面的内容,后经赫拉克利特、德 漠克利特、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而至柏拉图和亚斯多德等人的努力,哲学由自然哲学转向 以自然与人并重,于是将神、自然、灵魂具体化为上帝、物质与精神,由此,以上帝、物质、 精神为基本内容的世界,构成了哲学的对象传统。但西方文明经历了近代革命以后,逐渐从 三个方面消解了哲学对象传统的三维: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人的精神这 一维得到极度脸 账,其表现形式是对上帝的否定,后来尼采宣布上帝的死亡,哲学对象的“第一存在”之维 就此丧失:人片面张扬自我的突出标志是科学向技术领域的进军(或者说技术向科学的侵 蚀),使科学握弃了古典自然哲学的思辩方法而达向了全面的实证主义,从此,哲学对象的 “自然”之维被取消了。当科学被实证主义所全面武装,它就无所不至,不仅自然世界,最 后连人也成为科学研究与实证的深度对象,其标志是 19世纪的生理心理学和心理物理学的发展,为心理学走向实证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 上冯特所开创的实验心理学完成了对人的心理、精神研究的实证主义化,人的心理和精神变 成可分析和实验的对象而不是玄思的对象,心理学变成了实证科学。由此,哲学丧失了它全
哲学探询的当代方向 作者:唐代兴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浏览:493 次 (此文原载于香港《社科研究》 2005 年第 6 期 ) 【摘要】 哲学消亡 (或终结 )论产生于哲学家丧失哲学激情而成为哲学学家和哲学丧失探 询对象领域而沦为无本之末。前者直接来源于哲学研究取代了哲学探询;后者最终根源于人 类哲学诞生之时对自身对象领域的错位体认。哲学探询的真正对象应该是人的存在:人的原 发存在向创生存在方向敞开的生存道路、进程、状态,构成了哲学探询的 整体对象领域。 以此,哲学诞生于人的生生不息的 (原发和创生 )存在遭遇,在这一遭遇中,人的原发存在 向其创生存在方向的生存敞开,最为实在地与宇宙自然相互生成、互动书写出其生态场域。 这个相互生成、互动书写的生态场域构成了当代哲学的真正视域。 【关键词】 哲学对象 人的存在遭遇 书写性与被书写性 生存敞开 生态场域 一、生态反思:哲学对象的源头错位 人们常说哲学即是热爱智慧、追求真理,但这个断言本身就涉及到热爱什么智慧、追求什么 真理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具体表述为哲学对象本身。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所关注的基本 对象是整个世界,它具体展开为自然、灵魂和神――三个层面的内容,后经赫拉克利特、德 谟克利特、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而至柏拉图和亚斯多德等人的努力,哲学由自然哲学转向 以自然与人并重,于是将神、自然、灵魂具体化为上帝、物质与精神,由此,以上帝、物质、 精神为基本内容的世界,构成了哲学的对象传统。但西方文明经历了近代革命以后,逐渐从 三个方面消解了哲学对象传统的三维: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人的精神这一维得到极度膨 胀,其表现形式是对上帝的否定,后来尼采宣布上帝的死亡,哲学对象的“第一存在”之维 就此丧失;人片面张扬自我的突出标志是科学向技术领域的进军 (或者说技术向科学的侵 蚀 ),使科学摒弃了古典自然哲学的思辩方法而达向了全面的实证主义,从此,哲学对象的 “自然”之维被取消了。当科学被实证主义所全面武装,它就无所不至,不仅自然世界,最 后连人也成为科学研究与实证的深度对象,其标志是 19 世纪的生理心理学和心理物理学的发展,为心理学走向实证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 上冯特所开创的实验心理学完成了对人的心理、精神研究的实证主义化,人的心理和精神变 成可分析和实验的对象而不是玄思的对象,心理学变成了实证科学。由此,哲学丧失了它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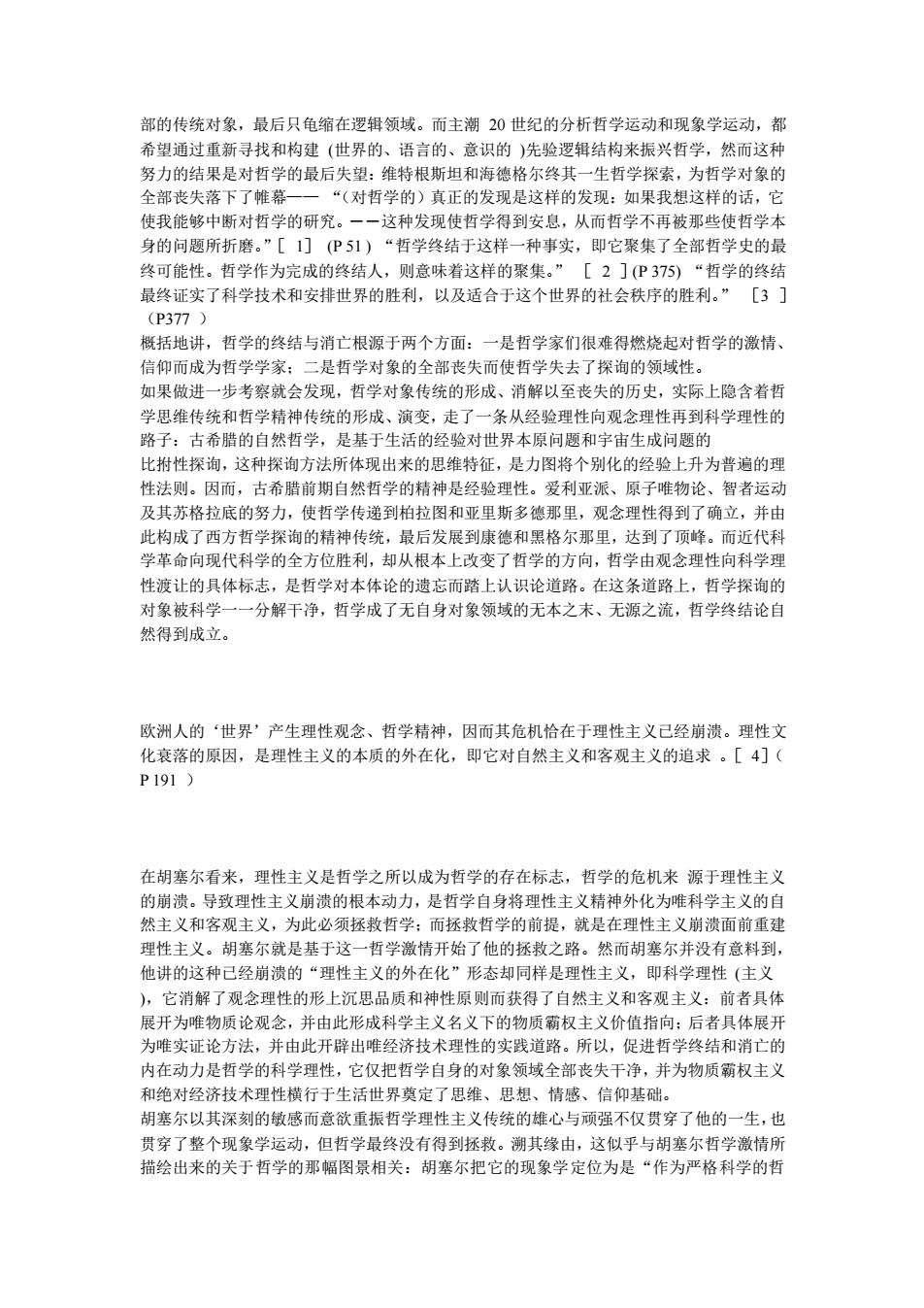
部的传统对象,最后只龟缩在逻辑领域。而主潮20世纪的分析哲学运动和现象学运动,都 希望通过重新寻找和构建 (世界的、语言的、意识的)先验逻辑结构来振兴哲学,然而这种 努力的结果是对哲学的最后失望: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终其 生哲学探索 为哲学对象的 全部丧失落下了帷幕 “(对哲学的)真正的发现是这样的发现:如果我想这样的话,它 使我能够中断对哲学的研究。一一这种发现使哲学得到安总,从而哲学不再被那些使哲学本 身的问题所折磨。”[1]P51)“哲学终结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它聚集了全部哲学史的最 终可能性。哲学作为完成的终结人,则意味着这样的聚集。”【2](P375)“哲学的终结 最终证实了科学技术和安排世界的胜利,以及适合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胜利。 [3] (P377 概括地讲,哲学的终结与消亡根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哲学家们很难得燃烧起对哲学的激情、 信仰而成为哲学学家:二是哲学对象的全部丧失而使哲学失去了探询的领域性。 如果做讲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哲学对象传统的形成、消解以至丧失的历史,实际上跨含着哲 学思维传统和哲学精神传统的形成、演变 走了 一条从经验理性向观念理性再到科学理性的 路子: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是基于生活的经验对世界本原问题和字宙生成问题的 比拊性探询,这种探询方法所体现出来的思维特征,是力图将个别化的经验上升为普遍的理 性法则。因而,古希腊前期自然哲学的精神是经验理性。爱利亚派、原子唯物论、智者运动 及其苏格拉底的努力,使哲学传递到柏拉图和亚里撕多德那里,观念理性得到了确立,并由 此构成了西方哲学探询的精神传统,最后发展到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而近代科 学革命向现代科 学的全方位胜利,却从根本上 了哲学的 方向, 哲学由观念理性向科学 性渡让的具体标志,是哲学对本体论的遗忘而踏上认识论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哲学探询的 对象被科学一一分解干净,哲学成了无自身对象领域的无本之末、无源之流,哲学终结论自 然得到成立。 欧洲人的‘世界'产生理性观念、哲学精神,因而其危机恰在于理性主义已经崩溃。理性文 化衰落的原因,是理性主义的本质的外在化,即它对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追求。[4]( P191) 在胡塞尔看来,理性主义是哲学之所以成为哲学的存在标志,哲学的危机来源于理性主义 的前溃。导致理性主义崩遗的根本动力,是哲学自身将理性主义精神外化为难科学主义的自 然主义和客观主义,为此必须拯教哲学:而拯救哲学的前提,就是在理性主义崩遗面前重建 理性主义。胡塞尔就是基于这 哲学激情开始了他的拯之路 然而胡塞尔并没有意料到 他讲的这种已经崩溃的“理性主义的外在化”形态却同样是理性主义,即科学理性(主义 ),它消解了观念理性的形上沉思品质和神性原则而获得了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前者具体 展开为难物质论观念,并由此形成科学主义名义下的物质霸权主义价值指向:后者具体展开 为唯实证论方法,并由此开辟出唯经济技术理性的实践道路。所以,促讲哲学终结和消亡的 内在动力是哲兰 的科学理性,它仅把哲学自身的对象领域全部丧失干净 并为物质霸权主义 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横行于生活世界奠定了思维、思想、情感、信仰基础 胡塞尔以其深刻的敏感而意欲重振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雄心与顽强不仅贯穿了他的一生,也 贯穿了整个现象学运动,但哲学最终没有得到拯救。溯其缘由,这似乎与胡塞尔哲学激情所 描绘出来的关于哲学的那幅图景相关:胡塞尔把它的现象学定位为是“作为严格科学的皙
部的传统对象,最后只龟缩在逻辑领域。而主潮 20 世纪的分析哲学运动和现象学运动,都 希望通过重新寻找和构建 (世界的、语言的、意识的 )先验逻辑结构来振兴哲学,然而这种 努力的结果是对哲学的最后失望: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终其一生哲学探索,为哲学对象的 全部丧失落下了帷幕—— “(对哲学的)真正的发现是这样的发现:如果我想这样的话,它 使我能够中断对哲学的研究。――这种发现使哲学得到安息,从而哲学不再被那些使哲学本 身的问题所折磨。”[ 1] (P 51 ) “哲学终结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它聚集了全部哲学史的最 终可能性。哲学作为完成的终结人,则意味着这样的聚集。” [ 2 ](P 375) “哲学的终结 最终证实了科学技术和安排世界的胜利,以及适合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胜利。” [3 ] (P377 ) 概括地讲,哲学的终结与消亡根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哲学家们很难得燃烧起对哲学的激情、 信仰而成为哲学学家;二是哲学对象的全部丧失而使哲学失去了探询的领域性。 如果做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哲学对象传统的形成、消解以至丧失的历史,实际上隐含着哲 学思维传统和哲学精神传统的形成、演变,走了一条从经验理性向观念理性再到科学理性的 路子: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是基于生活的经验对世界本原问题和宇宙生成问题的 比拊性探询,这种探询方法所体现出来的思维特征,是力图将个别化的经验上升为普遍的理 性法则。因而,古希腊前期自然哲学的精神是经验理性。爱利亚派、原子唯物论、智者运动 及其苏格拉底的努力,使哲学传递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那里,观念理性得到了确立,并由 此构成了西方哲学探询的精神传统,最后发展到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而近代科 学革命向现代科学的全方位胜利,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方向,哲学由观念理性向科学理 性渡让的具体标志,是哲学对本体论的遗忘而踏上认识论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哲学探询的 对象被科学一一分解干净,哲学成了无自身对象领域的无本之末、无源之流,哲学终结论自 然得到成立。 欧洲人的‘世界’产生理性观念、哲学精神,因而其危机恰在于理性主义已经崩溃。理性文 化衰落的原因,是理性主义的本质的外在化,即它对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追求 。[ 4]( P 191 ) 在胡塞尔看来,理性主义是哲学之所以成为哲学的存在标志,哲学的危机来 源于理性主义 的崩溃。导致理性主义崩溃的根本动力,是哲学自身将理性主义精神外化为唯科学主义的自 然主义和客观主义,为此必须拯救哲学;而拯救哲学的前提,就是在理性主义崩溃面前重建 理性主义。胡塞尔就是基于这一哲学激情开始了他的拯救之路。然而胡塞尔并没有意料到, 他讲的这种已经崩溃的“理性主义的外在化”形态却同样是理性主义,即科学理性 (主义 ),它消解了观念理性的形上沉思品质和神性原则而获得了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前者具体 展开为唯物质论观念,并由此形成科学主义名义下的物质霸权主义价值指向;后者具体展开 为唯实证论方法,并由此开辟出唯经济技术理性的实践道路。所以,促进哲学终结和消亡的 内在动力是哲学的科学理性,它仅把哲学自身的对象领域全部丧失干净,并为物质霸权主义 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横行于生活世界奠定了思维、思想、情感、信仰基础。 胡塞尔以其深刻的敏感而意欲重振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雄心与顽强不仅贯穿了他的一生,也 贯穿了整个现象学运动,但哲学最终没有得到拯救。溯其缘由,这似乎与胡塞尔哲学激情所 描绘出来的关于哲学的那幅图景相关:胡塞尔把它的现象学定位为是“作为严格科学的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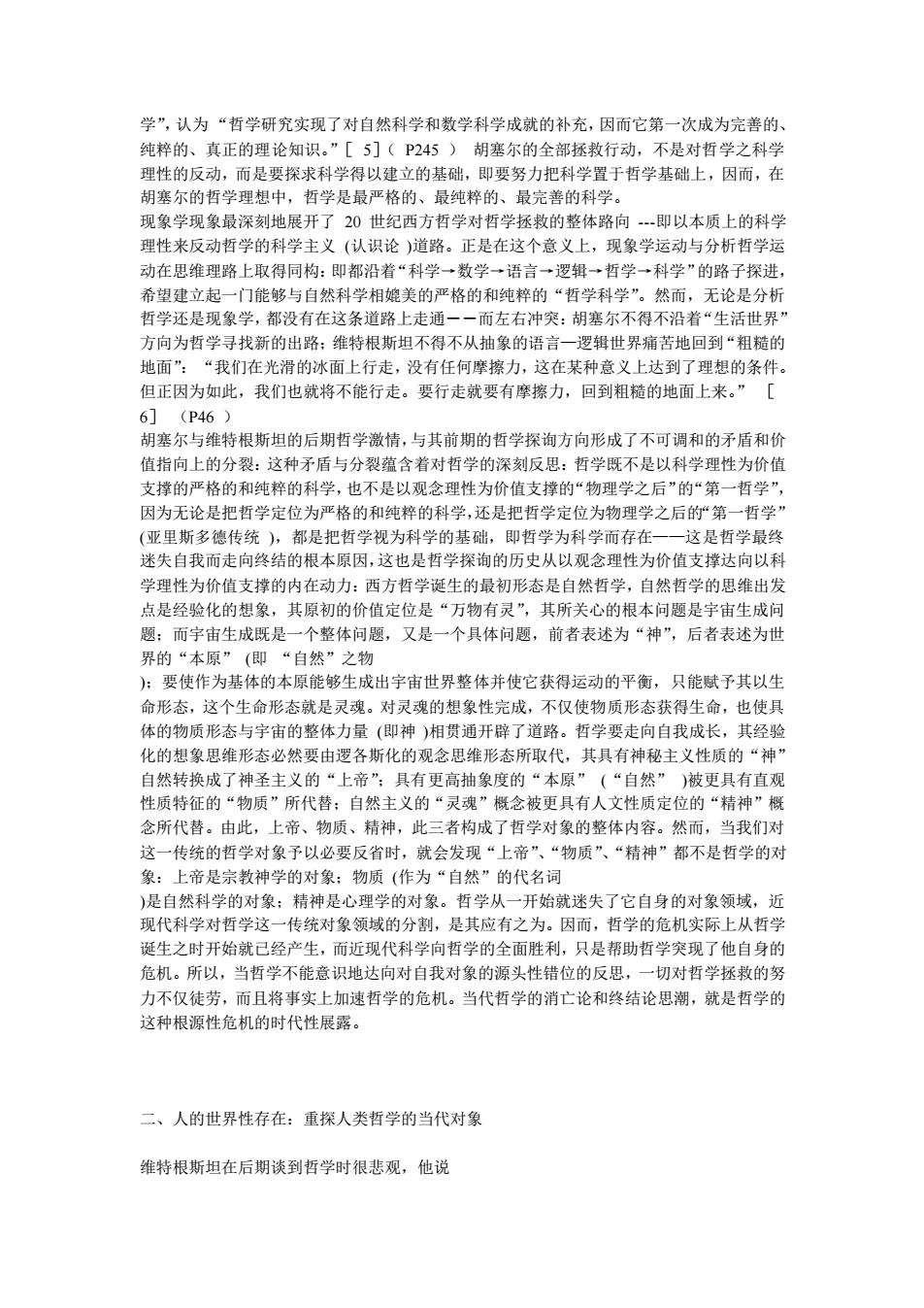
学”,认为“哲学研究实现了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科学成就的补充,因而它第一次成为完善的、 纯终的、直正的理论知识。”「51(245)胡塞尔的全部拯数行动,不是对哲学之到学 理性的反动,而是要探求科学得以建立的基础,即要努力把科学置于哲学基础上,因而,在 胡塞尔的哲学理想中,哲学是最严格的、最纯粹的、最完善的科学 现象学现象最深刻地展开了20世纪西方哲学对哲学拯救的整体路向一即以本质上的科 理性来反动哲学的科学主义(认识论)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坛动与分折哲学运 动在思维理路上取得同构:即都沿若“科学,数学·语言,罗辑,哲学科学”的路子探讲 希望建立起一门能够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严格的和纯粹的 “哲学科学”。然而,无论是分析 哲学还是现象等 都没有在这条道路上走通 而左右冲突:胡塞尔不得不沿者 活世 方向为哲学寻找新的出路:维特根斯坦不得不从抽象的语言一逻辑世界痛苦地回到“粗糙的 地面”:“我们在光滑的冰面上行走,没有任何摩擦力,这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理想的条件。 但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将不能行走。要行走就要有摩擦力,回到粗情的地面上来。”「 6 (P46 胡客尔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激情 与其前期的哲学探询方向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价 值指向上的分裂:这种矛盾与分裂蕴含着对哲学的深刻反思:哲学既不是以科学理性为价值 支撑的严格的和纯粹的科学,也不是以观念理性为价值支撑的“物理学之后”的“第一哲学”, 因为无论是把哲学定位为严格的和纯粹的科学,还是把哲学定位为物理学之后的第一哲学 亚里斯多德传统),都是把哲学视为科学的基础,即哲学为科学而存在 -这是哲学最终 迷失自我而走向终结的根 本原因,这也是哲学探询的历史从以观念理性为价值支撑达向以科 学理性为价值支撑的内在动力:西方哲学诞生的最初形态是自然哲学,自然哲学的思维出发 点是经验化的想象,其原初的价值定位是“万物有灵”,其所关心的根本问题是宇宙生成问 题:而宇宙生成既是一个整体问题,义是一个具体问题,前者表述为“神”,后者表述为世 界的“木原”(即“自然”之物 片要使作为基体的本原能够生成出字宙世界整体并使它获得运动的平衡,只能赋予其以生 命形态,这个生命形态就是灵魂。对灵魂的想象性完成,不仅使物质形态获得生命,也使具 体的物质形态与字宙的整体力量(即神)相贯通开群了道路。哲学要走向自我成长,其经验 化的想象思维形态必然要由罗各斯化的观念思维形态所取代,其具有神秘主义性质的“神 自然转换成了神圣主义的“上帝”:具有更高抽象度的“本原”(“自然”)被更具有直观 性质特征的“物质”所代替:自然主义的“灵魂”概今被更且有人文性质定位的“精神”概 念所代替。由此, 上帝、 物质、精神,此三者构成了哲学对象的整体内容。然而 当我们对 这一传统的哲学对象予以必要反省时,就会发现“上帝”、“物质”、“精神”都不是哲学的对 象:上帝是宗教神学的对象:物质(作为“自然”的代名词 是自然科学的对象:精神是心理学的对象。哲学从一开始就迷失了它自身的对象领域,近 现代科学对哲学这一传统对象领域的分割,是其应有之为。因而,哲学的危机实际上从哲学 生之时开始就己经产生,而近现代科学向哲学的全面胜利,只是帮助哲学突现了他自身的 危机。所以,当哲学不能意识地达向对自我对象的源头性错位的反思 切对哲学拯救的多 力不仅徒劳,而且将事实上加速哲学的危机。当代哲学的消亡论和终结论思潮,就是哲学的 这种根源性危机的时代性展露。 二、人的世界性存在:重探人类哲学的当代对象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谈到哲学时很悲观,他说
学”,认为 “哲学研究实现了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科学成就的补充,因而它第一次成为完善的、 纯粹的、真正的理论知识。”[ 5]( P245 ) 胡塞尔的全部拯救行动,不是对哲学之科学 理性的反动,而是要探求科学得以建立的基础,即要努力把科学置于哲学基础上,因而,在 胡塞尔的哲学理想中,哲学是最严格的、最纯粹的、最完善的科学。 现象学现象最深刻地展开了 20 世纪西方哲学对哲学拯救的整体路向 ---即以本质上的科学 理性来反动哲学的科学主义 (认识论 )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运动与分析哲学运 动在思维理路上取得同构:即都沿着“科学→数学→语言→逻辑→哲学→科学”的路子探进, 希望建立起一门能够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严格的和纯粹的“哲学科学”。然而,无论是分析 哲学还是现象学,都没有在这条道路上走通――而左右冲突:胡塞尔不得不沿着“生活世界” 方向为哲学寻找新的出路;维特根斯坦不得不从抽象的语言—逻辑世界痛苦地回到“粗糙的 地面”:“我们在光滑的冰面上行走,没有任何摩擦力,这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理想的条件。 但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将不能行走。要行走就要有摩擦力,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 [ 6] (P46 ) 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激情,与其前期的哲学探询方向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价 值指向上的分裂:这种矛盾与分裂蕴含着对哲学的深刻反思:哲学既不是以科学理性为价值 支撑的严格的和纯粹的科学,也不是以观念理性为价值支撑的“物理学之后”的“第一哲学”, 因为无论是把哲学定位为严格的和纯粹的科学,还是把哲学定位为物理学之后的“第一哲学” (亚里斯多德传统 ),都是把哲学视为科学的基础,即哲学为科学而存在——这是哲学最终 迷失自我而走向终结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哲学探询的历史从以观念理性为价值支撑达向以科 学理性为价值支撑的内在动力:西方哲学诞生的最初形态是自然哲学,自然哲学的思维出发 点是经验化的想象,其原初的价值定位是“万物有灵”,其所关心的根本问题是宇宙生成问 题;而宇宙生成既是一个整体问题,又是一个具体问题,前者表述为“神”,后者表述为世 界的“本原” (即 “自然”之物 );要使作为基体的本原能够生成出宇宙世界整体并使它获得运动的平衡,只能赋予其以生 命形态,这个生命形态就是灵魂。对灵魂的想象性完成,不仅使物质形态获得生命,也使具 体的物质形态与宇宙的整体力量 (即神 )相贯通开辟了道路。哲学要走向自我成长,其经验 化的想象思维形态必然要由逻各斯化的观念思维形态所取代,其具有神秘主义性质的“神” 自然转换成了神圣主义的“上帝”;具有更高抽象度的“本原” (“自然” )被更具有直观 性质特征的“物质”所代替;自然主义的“灵魂”概念被更具有人文性质定位的“精神”概 念所代替。由此,上帝、物质、精神,此三者构成了哲学对象的整体内容。然而,当我们对 这一传统的哲学对象予以必要反省时,就会发现“上帝”、“物质”、“精神”都不是哲学的对 象:上帝是宗教神学的对象;物质 (作为“自然”的代名词 )是自然科学的对象;精神是心理学的对象。哲学从一开始就迷失了它自身的对象领域,近 现代科学对哲学这一传统对象领域的分割,是其应有之为。因而,哲学的危机实际上从哲学 诞生之时开始就已经产生,而近现代科学向哲学的全面胜利,只是帮助哲学突现了他自身的 危机。所以,当哲学不能意识地达向对自我对象的源头性错位的反思,一切对哲学拯救的努 力不仅徒劳,而且将事实上加速哲学的危机。当代哲学的消亡论和终结论思潮,就是哲学的 这种根源性危机的时代性展露。 二、人的世界性存在:重探人类哲学的当代对象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谈到哲学时很悲观,他说

“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是:我不知道其出路何在。”「7](P49)维特根斯的悲观,由后 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所扩散而普遍化:后现代主义对哲学的挽歌,是一种不知哲学出路何在 的消极行为:解构主义既积极解构哲学又不放弃哲学,同样是不知哲学出路何在的盲动行为 因而,当代哲学要重椒自我,既不能跟着后现代主义唱挽歌,也不能附和解构主义左右摇摆 而应该着手探索其“出路”的正确途径。 探寻哲学出路的正确途径,是重新追问并确立哲学的自身对象领域。 哲学的自身对象领域是什么呢 关于这问题,其实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激情己经透露出了消息:胡塞尔提出“生 活世界”和“回到事物本身去”的口号,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最终应该从“光滑的冰面上行 走”回到有摩擦力的“粗糙的地面”的主张,都隐含了对哲学自身的本真对象的无意识直观 哲学的自身对象非它,即 人的存在 哲学因人的存在而诞生:人的存在既是哲学诞生的前提,又成为哲学的根本对象。因而, 只要有人的存在,哲学就有自身探询的对象领域,哲学一旦有其自身探询的对象领域,就不 可终结与消亡 其实“人的存在”问题,自普罗泰戈拉以来一直是哲学的关注对象,但以前的哲学对“人的 存在”的关注 ,只是停留在 产止抽象 “类”层 做文留 情况去 开专 非如此:人不 是孤立的存在者,他始终存在于他者之中,并与他者结成关系:人的存在是一种关系的存 在。首先,人是存在于宇宙时空和自然之中,他与字宙时空和自然之间形成一种时空关系、 自然关系,所以,人的存在既是一种自然存在,更是一种字宙时空存在。其次,人的生命诞 牛千他者某个女人的身体和其个男人的基因),因而, 人与他人(个人、家庭、种族)之 间构成了血缘关系:而这些个人、家庭、 中族又与其他的个 种族之间有着直接 间接的关联性,这样,人又获得了血缘的和群的存在关系。第三,人是具有自我进化潜力的 人,这种自我进化潜力表征为人对自我意识、自我关怀,由此形成了人的现象自我和本体自 我的双重性,人与自我生命本体之间又构成了一种实在的存在命运关系。 客观地看,对人与自我生命存在命运之关系的意识性关注, 集中展开为神话体系的解构 对人与宇宙时空 自然之存在关系的关怀 则产生了人对人自己之来龙 神学和人对自然之 柔花法的关注的学报对人写素,北会之存关的的染 产生出人对人伦关系的看待的政治与伦理,和人对自己的看待的人文精神。因而,哲学生发 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学宙时空 )、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之复杂多变的关系解构演变之中:哲学始终立足于人的存在整体 为其存在本身的复杂演变而敏感与惊奇、困惑和追问:整体地看,哲学的对象领域乃人的 世界性存在本身。 具体而言 ,哲学的对象领域展开为人与自然(包括宇宙时空)的存在 系、人与他人和群体即社会 )的存在关系、人与自我生命存在命运的存在关系。如果从人类精神探询的领域角度看,哲 学的对象不是自然科学的对象:自然利料学的对象是自然、宇宙,其重心在于探讨自然和字由 的存在法则和运行规律:而哲学却以人与自然、宇宙之存在关系为探询对象。所以哲学必 须担当起反思自然科 作 自然科学必须为哲学提供反思的材料。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式 系是:自然科学是对自然事实的研究,哲 是对原理的反思,即自然科学关心自然如何存有 的事实,而哲学却在此基础上关心自然与人之间如何存在的关系事实和怎样才能形成更好的 存在关系的可能性。所以,没有科学为哲学提供反思的材料,哲学却不能很好地探询人与自 然之存在关系:如果“没有哲学的开始,自然科学就不能走出多远,并且哲学通过启发科学
“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是:我不知道其出路何在。”[ 7]( P49) 维特根斯的悲观,由后 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所扩散而普遍化:后现代主义对哲学的挽歌,是一种不知哲学出路何在 的消极行为;解构主义既积极解构哲学又不放弃哲学,同样是不知哲学出路何在的盲动行为。 因而,当代哲学要重振自我,既不能跟着后现代主义唱挽歌,也不能附和解构主义左右摇摆, 而应该着手探索其“出路”的正确途径。 探寻哲学出路的正确途径,是重新追问并确立哲学的自身对象领域。 哲学的自身对象领域是什么呢? 关于这问题,其实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激情已经透露出了消息:胡塞尔提出“生 活世界”和“回到事物本身去”的口号,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最终应该从“光滑的冰面上行 走”回到有摩擦力的“粗糙的地面”的主张,都隐含了对哲学自身的本真对象的无意识直观: 哲学的自身对象非它,即 人的存在。 哲学因 人的存在而诞生:人的存在既是哲学诞生的前提,又成为哲学的根本对象。因而, 只要有人的存在,哲学就有自身探询的对象领域,哲学一旦有其自身探询的对象领域,就不 可终结与消亡。 其实“人的存在”问题,自普罗泰戈拉以来一直是哲学的关注对象,但以前的哲学对“人的 存在”的关注,只是停留在静止抽象的“类”层面做文章,而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人不 是孤立的存在者,他始终存在于他者之中,并与他者结成关系:人的存在是一种 关系的存 在。首先,人是存在于宇宙时空和自然之中,他与宇宙时空和自然之间形成一种时空关系、 自然关系,所以,人的存在既是一种自然存在,更是一种宇宙时空存在。其次,人的生命诞 生于他者 (某个女人的身体和某个男人的基因 ),因而,人与他人 (个人、家庭、种族 )之 间构成了血缘关系;而这些个人、家庭、种族又与其他的个人、家庭、种族之间有着直接或 间接的关联性,这样,人又获得了血缘的和群的存在关系。第三,人是具有自我进化潜力的 人,这种自我进化潜力表征为人对自我意识、自我关怀,由此形成了人的现象自我和本体自 我的双重性,人与自我生命本体之间又构成了一种实在的存在命运关系。 客观地看,对人与自我生命存在命运之关系的意识性关注, 集中展开为神话体系的解构; 对 人与宇宙时空和自然之存在关系的关怀,则产生了人对人自己之来龙去脉的关注的宗教 神学和人对自然之来龙去脉的关注的科学探索;对人与他者、社会之存在关系的意识性探询, 产生出人对人伦关系的看待的政治与伦理,和人对自己的看待的人文精神。因而,哲学生发 于人与人、人与自然 (宇宙时空 )、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之复杂多变的关系解构演变之中:哲学始终立足于人的存在整体, 为其存在本身的复杂演变而敏感与惊奇、困惑和追问: 整体地看,哲学的对象领域乃 人的 世界性存在 本身。具体而言,哲学的对象领域展开为人与自然( 包括宇宙时空) 的存在关 系、人与他人和群体( 即社会 ) 的存在关系、人与自我生命存在命运的存在关系。如果从人类精神探询的领域角度看,哲 学的对象不是自然科学的对象: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宇宙,其重心在于探讨自然和宇宙 的存在法则和运行规律;而哲学却以人与自然、宇宙之 存在关系为探询对象。所以哲学必 须担当起反思自然科学的工作,自然科学必须为哲学提供反思的材料。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 系是:自然科学是对自然事实的研究,哲学是对原理的反思,即自然科学关心自然如何存在 的事实,而哲学却在此基础上关心自然与人之间如何存在的关系事实和怎样才能形成更好的 存在关系的可能性。所以,没有科学为哲学提供反思的材料,哲学却不能很好地探询人与自 然之存在关系;如果“没有哲学的开始,自然科学就不能走出多远,并且哲学通过启发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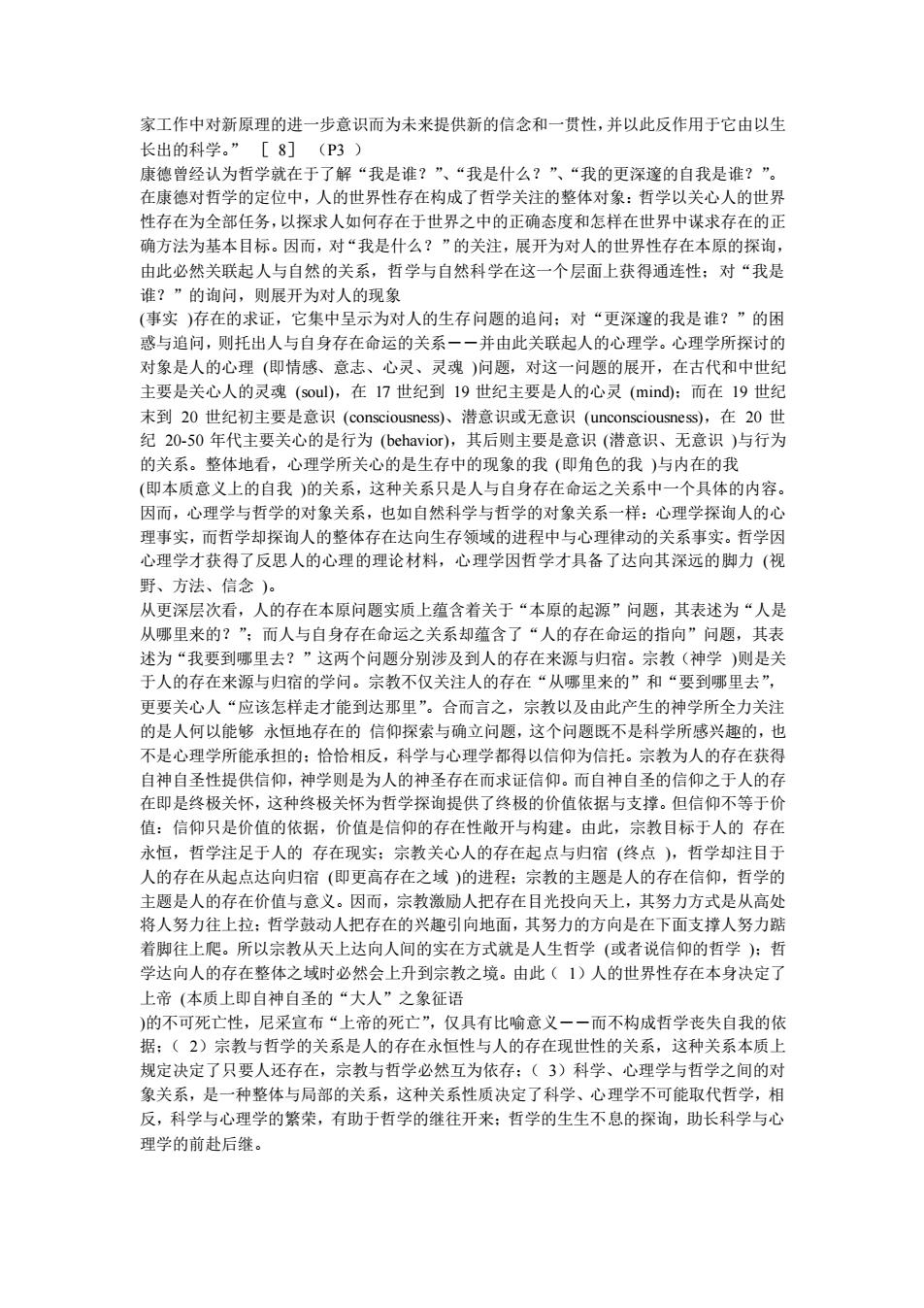
家工作中对新原理的进一步意识而为未来提供新的信念和一贯性,并以此反作用于它由以生 长出的学。”「81(p3】 康德曾经认为哲学就在于了解“我是谁?”、“我是什么?”、“我的更深邃的自我是谁?” 在康德对哲学的定位中,人的世界性存在构成了哲学关注的整体对象:哲学以关心人的世界 性存在为全部任务,以探求人如何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正确态度和怎样在世界中谋求存在的正 确方法为基本目标。因而,对“我是什么?”的关注,展开为对人的世界性存在本原的探询, 由此必然关联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哲学与自然科学在这一个层面上获得通连性:对“我是 谁?”的询问,则展开为对人的现象 (事实)存在的求证 它集中 示为对人的生存问题的追问: 对“更深邃的我是谁?”的困 惑与追问,则托出人与自身存在命运的关系 并由此关联起人的心理学。心理学所探讨的 对象是人的心理(即情感、意志、心灵、灵魂)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展开,在古代和中世纪 主要是关心人的灵魂(sou),在17世纪到19世纪主要是人的心灵(mid:而在19世纪 末到20世纪初主要是意识( sness 、潜意识或无意识 在20出 纪20-50年代主要关心 的是行为(beh: 其后则主要 意识(潜意识 意识)与行为 的关系。整体地看,心理学所关心的是生存中的现象的我(即角色的我)与内在的我 (即本质意义上的自我)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是人与自身存在命运之关系中一个具体的内容。 因而,心理学与哲学的对象关系,也如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对象关系一样:心理学探询人的心 理事实,而哲学却探询人的整体存在达向生存领域的进程中与心理律动的关系事实。哲学因 理学才得了后里人的心理的理论材。 心理学因哲学才具备了达向其深远的脚力(视 野、方法、信念)· 从更深层次看,人的存在本原问题实质上蕴含着关于“本原的起源”问题,其表述为“人是 从哪里来的?”:而人与自身存在命运之关系却蕴含了“人的存在命运的指向”问题,其表 球为“我要到哪甲去?”这两个问颗分别涉及到人的存在来源与归宿。宗教(神学)则是关 于人的存在来源与归宿的学问。宗教不仅关注人的存在“从哪里来的”和“要到哪里去” 更要关心人“应该怎样走才能到达那里 合而言之 宗教以及由此 生 的神学所全力关江 的是人何以能多永恒地存在的信仰探索与确立问题,这个问题既不是科学所感兴趣的,也 不是心理学所能承担的:恰恰相反,科学与心理学都得以信仰为信托。宗教为人的存在获得 自神自圣性提供信仰,神学则是为人的神圣存在而求证信仰。而自神自圣的信仰之于人的存 在即是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为哲学探询提供了终极的价值依据与支撑。但信仰不等于价 值:信仰只是价值的依据 价值 是信仰的存在性散开与构建 由此, 宗教目标于人的存在 水恒,西学注足于人的存在现实:示教关心人的存在起点与归宿(终点),哲学却注目 人的存在从起点达向归宿(即更高存在之域)的进程:宗教的主题是人的存在信仰,哲学的 主题是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因而,宗教微励人把存在目光投向天上,其努力方式是从高处 将人努力往上拉:哲学鼓动人把存在的兴趣引向地面,其努力的方向是在下面支撞人努力那 着脚往上爬。所以宗教从天上达向人间的实在方式就是人生哲学(或者说信仰的哲学): 学达向人的存在整体之域时必然会上升到宗教之境。由此(1)人的世界性存在本身决定了 上帝(本质上即自神自圣的“大人”之象征语 )的不可死亡性,尼采官布“上帝的死亡”,仅且有出比哈意义一一而不成哲学丧失自我的依 据:(2)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是人的存在永恒性与人的存在现世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 定决定了只要人坏存在, 宗教与哲学必然互为依存:(3)科学、 心理学与析学之间的对 象关系,是一种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这种关系性质决定 了科学 心理学不可能 代哲学, 反,科学与心理学的繁荣,有助于哲学的继往开米:哲学的生生不总的探询,助长科学与心 理学的前赴后继
家工作中对新原理的进一步意识而为未来提供新的信念和一贯性,并以此反作用于它由以生 长出的科学。” [ 8] (P3 ) 康德曾经认为哲学就在于了解“我是谁?”、“我是什么?”、“我的更深邃的自我是谁?”。 在康德对哲学的定位中,人的世界性存在构成了哲学关注的整体对象:哲学以关心人的世界 性存在为全部任务,以探求人如何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正确态度和怎样在世界中谋求存在的正 确方法为基本目标。因而,对“我是什么?”的关注,展开为对人的世界性存在本原的探询, 由此必然关联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哲学与自然科学在这一个层面上获得通连性;对“我是 谁?”的询问,则展开为对人的现象 (事实 )存在的求证,它集中呈示为对人的生存问题的追问;对“更深邃的我是谁?”的困 惑与追问,则托出人与自身存在命运的关系――并由此关联起人的心理学。心理学所探讨的 对象是人的心理 (即情感、意志、心灵、灵魂 )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展开,在古代和中世纪 主要是关心人的灵魂 (soul),在 17 世纪到 19 世纪主要是人的心灵 (mind);而在 19 世纪 末到 20 世纪初主要是意识 (consciousness)、潜意识或无意识 (unconsciousness),在 20 世 纪 20-50 年代主要关心的是行为 (behavior),其后则主要是意识 (潜意识、无意识 )与行为 的关系。整体地看,心理学所关心的是生存中的现象的我 (即角色的我 )与内在的我 (即本质意义上的自我 )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是人与自身存在命运之关系中一个具体的内容。 因而,心理学与哲学的对象关系,也如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对象关系一样:心理学探询人的心 理事实,而哲学却探询人的整体存在达向生存领域的进程中与心理律动的关系事实。哲学因 心理学才获得了反思人的心理的理论材料,心理学因哲学才具备了达向其深远的脚力 (视 野、方法、信念 )。 从更深层次看,人的存在本原问题实质上蕴含着关于“本原的起源”问题,其表述为“人是 从哪里来的?”;而人与自身存在命运之关系却蕴含了“人的存在命运的指向”问题,其表 述为“我要到哪里去?”这两个问题分别涉及到人的存在来源与归宿。宗教(神学 )则是关 于人的存在来源与归宿的学问。宗教不仅关注人的存在“从哪里来的”和“要到哪里去”, 更要关心人“应该怎样走才能到达那里”。合而言之,宗教以及由此产生的神学所全力关注 的是人何以能够 永恒地存在的 信仰探索与确立问题,这个问题既不是科学所感兴趣的,也 不是心理学所能承担的;恰恰相反,科学与心理学都得以信仰为信托。宗教为人的存在获得 自神自圣性提供信仰,神学则是为人的神圣存在而求证信仰。而自神自圣的信仰之于人的存 在即是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为哲学探询提供了终极的价值依据与支撑。但信仰不等于价 值:信仰只是价值的依据,价值是信仰的存在性敞开与构建。由此,宗教目标于人的 存在 永恒,哲学注足于人的 存在现实;宗教关心人的存在起点与归宿 (终点 ),哲学却注目于 人的存在从起点达向归宿 (即更高存在之域 )的进程;宗教的主题是人的存在信仰,哲学的 主题是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因而,宗教激励人把存在目光投向天上,其努力方式是从高处 将人努力往上拉;哲学鼓动人把存在的兴趣引向地面,其努力的方向是在下面支撑人努力踮 着脚往上爬。所以宗教从天上达向人间的实在方式就是人生哲学 (或者说信仰的哲学 );哲 学达向人的存在整体之域时必然会上升到宗教之境。由此( 1)人的世界性存在本身决定了 上帝 (本质上即自神自圣的“大人”之象征语 )的不可死亡性,尼采宣布“上帝的死亡”,仅具有比喻意义――而不构成哲学丧失自我的依 据;( 2)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是人的存在永恒性与人的存在现世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 规定决定了只要人还存在,宗教与哲学必然互为依存;( 3)科学、心理学与哲学之间的对 象关系,是一种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种关系性质决定了科学、心理学不可能取代哲学,相 反,科学与心理学的繁荣,有助于哲学的继往开来;哲学的生生不息的探询,助长科学与心 理学的前赴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