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论 导 论 如果有人细心规察各个现代国家借釉管理其司法的制度安排 的多样性,无穷无尽的、令人无从着手的课题就会呈现在他 她)面前。多样化的程度是如此之深)广,以至于用一套通用的词 汇很难对之加以表达,并使我们不敢肯定我们的参照点是否充 分。法律程序是否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要求有三个独立方面 原告、被告和裁决者一的互动,抑或它也可以采用“双边 事务”(affaire a deux)的形式,在个人与政府官员之间进行?为 了使程序保持它的合法性质,需要由个国家“法官”对之加以 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吗?他主要是一个纠纷解决者还是一个国家政 策执行者?是一个教育家还是一个矫治师?如果牵涉到诉讼程序 之中的个人成了国家推行其政策和计划所需要的证据源和信息提 供者,他(她)们仍然是“当事人”吗?在现代国家中,什么是 正当程序的最低要求?这些以及许多其它问题都迫切需要澄清, 因为在现代法律制度中,它们已经被赋子了多种不同的答案。 并非所有制度设置和司法形式上的差异都能被一眼看出。有 些差异潜伏在表面的相似性之后,只有通过仔细的考察才能识别 出来。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有时会宜称取 得了许多方面的共识,而这种共识主要是一种修辞上的或果。实 际土,所有的国家都同意这样一些观点:法官应该独立,被告应 该被推定无罪,直到证实了相反的情况。但是,一旦我们思考这 些观点的含义以及它们在不同国家司法活动中的操作意义时,这

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 种一致性就会破裂 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在一个国家中,也可以发现对此类事项 的不同安排以及对于既定安排的意见冲突。在美国,由各法域的 不同程序与制度模式拼凑成的司法图景以及对于司法管理玫革的 持久争论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不管一国内部存在多么广泛的 2差异,从外部来看,这种内部的不一致似乎往往只是一种更大的 同构性之中的一些变量,这种同构性表现为关于什么是“公正 和“有序”、应当如何来建构司法制度等方面的观念,而且,选 择可用方案的参数通常也是共享的。对争论焦点的类分模式得到 普遍地、不加反思地接受:讨论总是在同样的话语模式中进行。 要想感受一下实际上的差异是多么的繁复,面话语共同体的 限度又是多么的显著,我们不必越过“西方”的疆域。我们谆要 考虑一下英美法系(普通法法系)程序制度和大陆法系(民法法 系)程序制度之间的这种著名的(同时也是不甚明了的)区分就 可以了。在这两套制度中,举证和论辩的合法方式截然不同: 方面是律师的直接取证和交叉质证,另一方面是国家司法机构的 司法调查。对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面言,刑事被告通过自认其罪 而放弃接受审判的权利是一种常态,但是,对于大陆法系国家的 律师来说,这种做法无论在什么样的案件中都是极不恰当的。在 那里,所有的案件都必须经过审判,无论其中的被告是否自认其 罪,民事案件当事人有权拒绝作证,这在欧陆国家得到普遍的接 受,但却会令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职业者感到震惊。在大多数普 通法法系国家中,刑事案件中的取证比民事案件中的取证受到更 多的限制,这使民法法系国家的法律家们觉得难以理解。除了上 述这些显著的差异以外,还有一些观念分歧则不为人们所熟知。 这些分歧所针对的往往是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一审程序与预审程 序、上诉审程序之间的关系以及司法职务的确切属性等等。如果 不揭示出这些微妙的差异,它们很可能会引起英美法系法律家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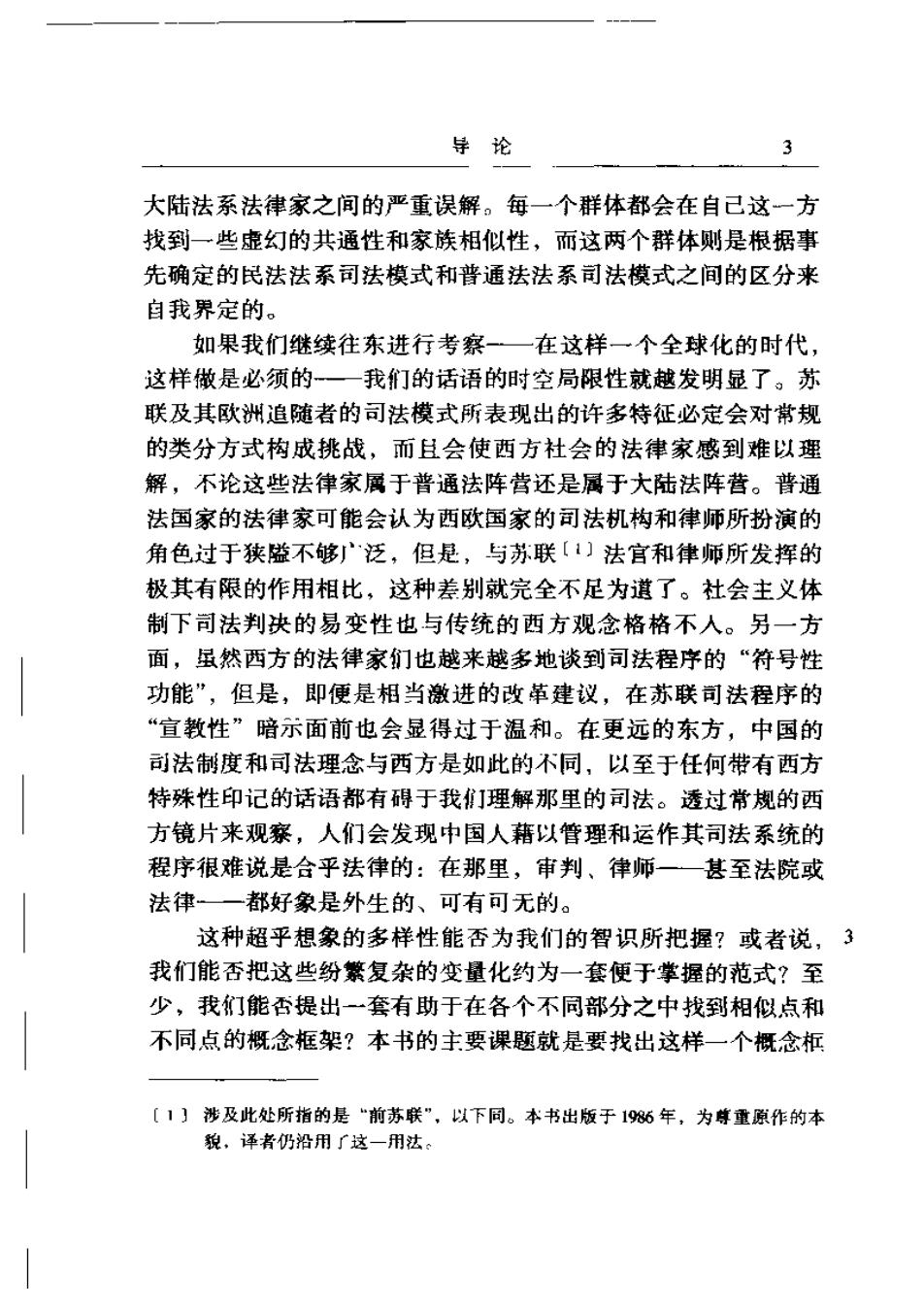
导论 大陆法系法律家之间的严重误解。每一个群体都会在自己这一方 找到一些虚幻的共通性和家族相似性,而这两个群体则是根据事 先确定的民法法系司法模式和普通法法系司法模式之间的区分来 自我界定的。 如果我们继续往东进行考察-一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这样橄是必须的-一一我们的话语的时空局限性就越发明显了。苏 联及其欧洲追随者的司法模式所表现出的许多特征必定会对常规 的类分方式构成挑战,而且会使西方社会的法律家感到难以理 解,不论这些法律家属于普通法阵营还是属于大陆法阵营。普通 法国家的法律家可能会认为西欧国家的司法机构和律师所粉演的 角色过于狭磁不够泛,但是,与苏联〔1)法宫和律师所发挥的 极其有限的作用相比,这种差别就完全不足为道了。社会主义体 制下司法判决的易变性也与传统的西方观念格格不人。另一方 面,虽然西方的法律家们也越来越多地谈到司法程序的“符号性 功能”,但是,即便是相当激进的改革建议,在苏联司法程序的 “宣教性”暗示面前也会显得过于温和。在更远的东方,中国的 司法制度和司法理念与西方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任何带有西方 特殊性印记的话语都有碍于我们理解那里的司法。透过常规的西 方镜片来观察,人们会发现中国人藉以管理和运作其司法系统的 程序很难说是合乎法律的:在那里,审判、律师一—甚至法院或 法律一一都好象是外生的、可有可无的。 这种超乎想象的多样性能否为我们的智识所把握?或者说,3 我们能否把这些纷繁复杂的变量化约为一套便于掌握的范式?至 少,我们能否提出一套有助于在各个不同部分之中找到相似点和 不同点的概念框架?本书的主要课题就是要找出这样一个概念板 〔1涉及此处所指的是“前苏联”,以下同。本书出版于196年,为尊重原作的本 说,率者仍沿用了这一用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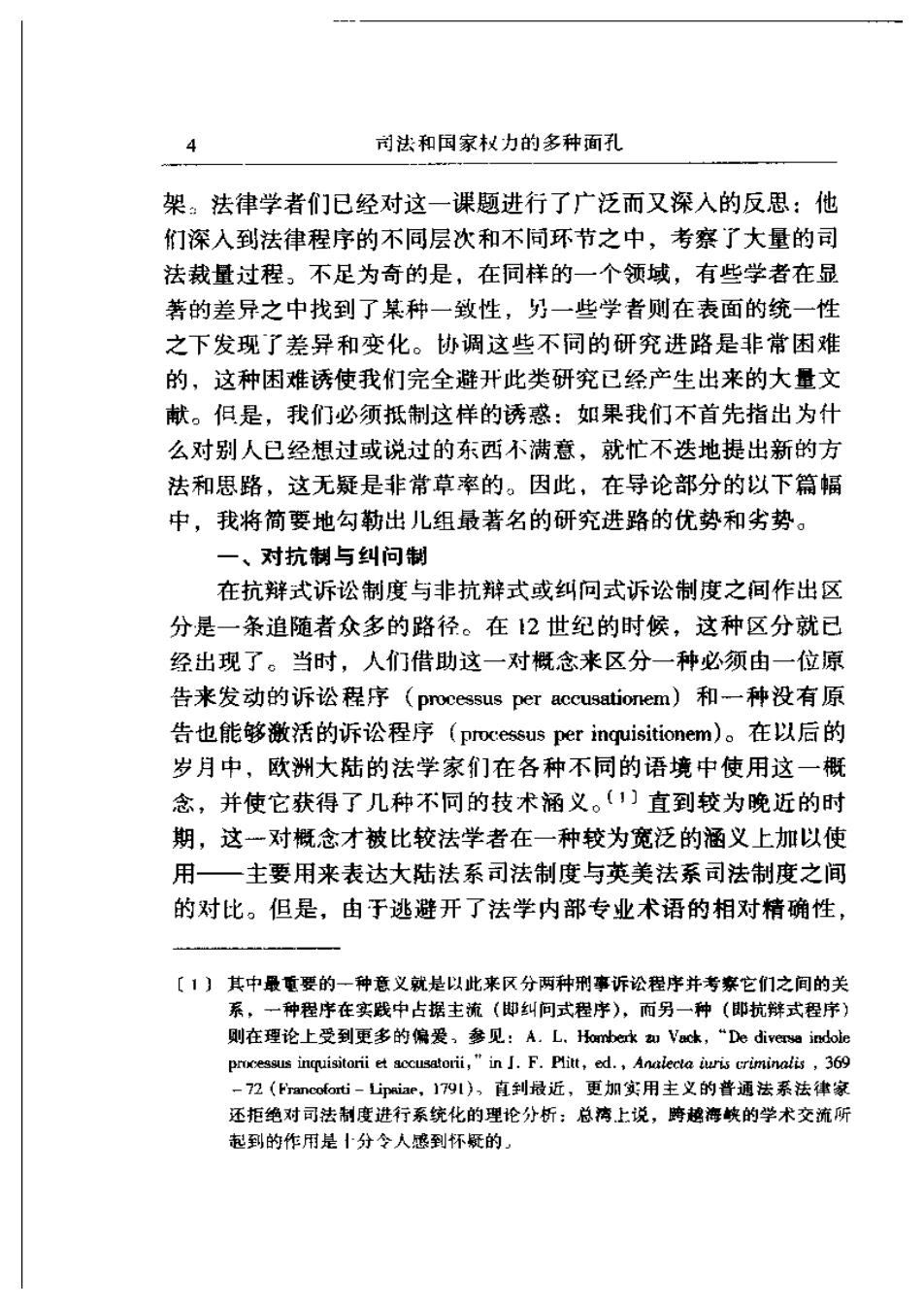
润法和同家权力的多种面孔 架。法律学者们已经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反思:他 们深入到法律程序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环节之中,考察了大量的司 法裁量过程。不足为奇的是,在同样的一个领域,有些学者在显 著的差异之中找到了某种一致性,另一些学者则在表面的统一性 之下发现了差异和变化。协调这些不同的研究进路是非常困难 的,这种困难诱使我们完全避开此类研究已经产生出来的大量文 献。但是,我们必须抵制这样的诱惑:如果我们不首先指出为什 么对别人已经想过或说过的东西不满意,就忙不迭地提出新的方 法和思路,这无疑是非常草率的。因此,在导论部分的以下篇辐 中,我将简要地勾勒出儿组最著名的研究进路的优势和劣势。 一、对抗制与纠问制 在抗辩式诉讼制度与非抗辩式或纠问式诉讼制度之间作出区 分是一条追随者众多的路径。在2世纪的时候,这种区分就已 经出现了。当时,人们借助这一对概念来区分一种必须由一位原 告来发动的诉讼程序(processus per accusationem)和一种没有原 告也能够激活的诉讼程序(per inquisitionem)。在以后的 岁月中,欧洲大陆的法学家]在各种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这一概 念,并使它获得了几种不同的技术涵义。(1〕直到较为晚近的时 期,这一对概念才被比较法学者在一种较为宽泛的涵义上加以使 用一主要用来表达大陆法系司法制度与英美法系司法制度之间 的对比。但是,由于逃避开了法学内部专业术语的相对精确性, 【1)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意义就是以此来区分两种刑事诉讼程序并考案它们之间的关 系,一种程序在实践中占据主流(即纠问式程序),而另一种(即抗辩式程序) 则在理论上受到更多的偏爱,参见:A.L.omberk知Vack,“De dives ndo processus inquisitorii et accusatorii,"in J.F.Plitt,ed.,Anaiecta iuris criminalis,369 -2(rancoforti-ipiae,」79I),直到最近,更加实用主义的普通法系法律家 还拒绝对司法制度进行系统化的理伦分析:总湾上说,跨鹅海峡的学术交流所 起到的作用是十分令人感到怀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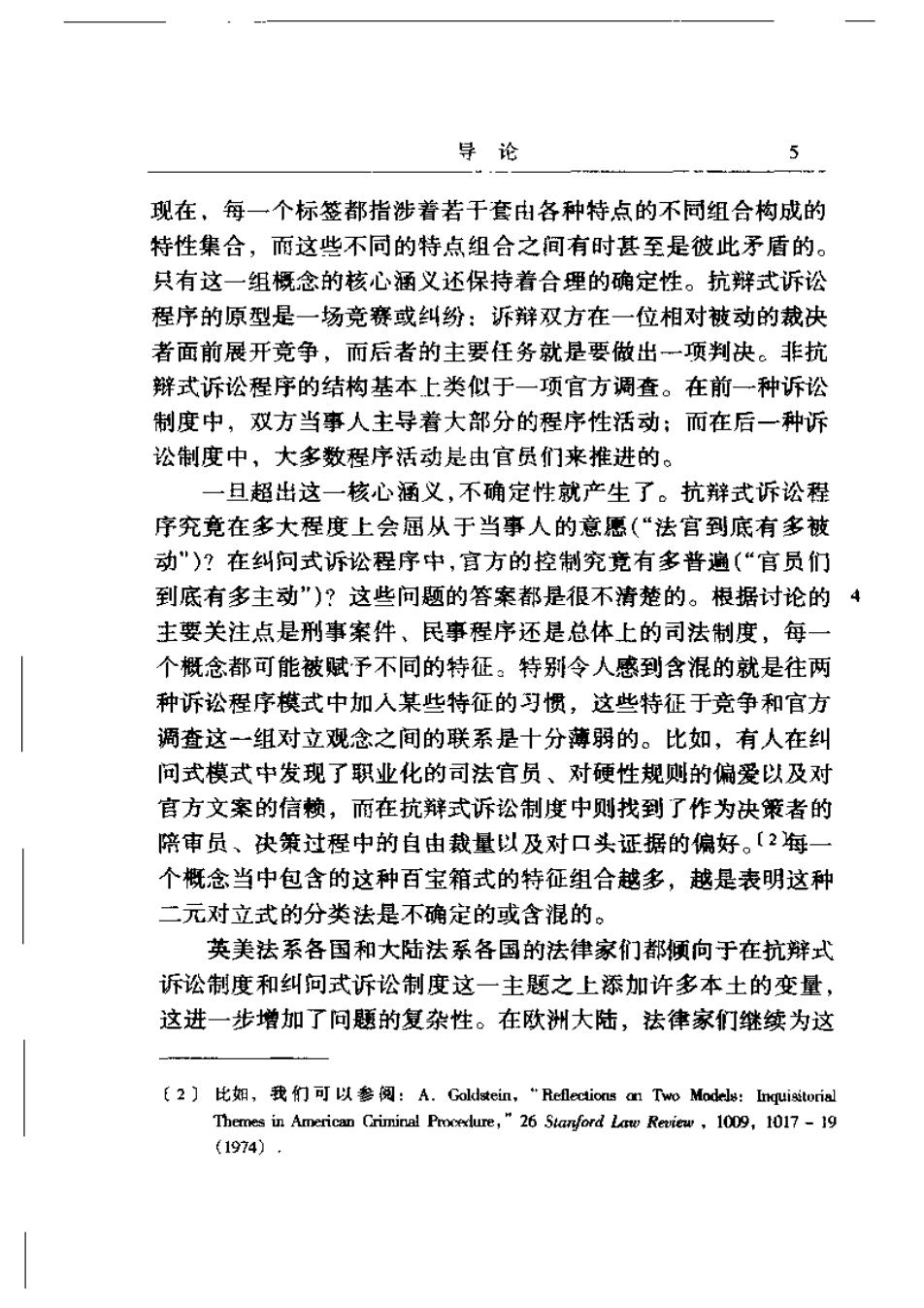
导论 5 现在,每一个标签都指涉着若干套由各种特点的不同组合构成的 特性集合,而这些不同的特点组合之间有时甚至是彼此矛盾的。 只有这一组概念的核心涵义还保持着合理的确定性。抗辩式诉讼 程序的原型是一场竞赛或纠纷:诉辩双方在一位相对被动的裁决 者面前展开竞争,而后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做出一项判决。非抗 辩式诉讼程序的结构基本上类似于一项官方调查。在前一种诉讼 制度中,双方当事人主导着大部分的程序性活动:而在后一种诉 讼制度中,大多数程序活动是由官员们来推进的。 一旦超出这一核心涵义,不确定性就产生了。抗辩式诉讼程 序究竞在多大程度上会屈从于当事人的意愿(“法宫到底有多被 动")?在纠问式诉讼程序中,官方的控制究竞有多普遍(“官员们 到底有多主动”)?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很不清楚的。根据讨论的 4 主要关注点是刑事案件、民事程序还是总体上的司法制度,每 个概念都可能被赋予不同的特征。特别令人感到含混的就是往两 种诉讼程序模式中加入某些特征的习惯,这些特征于竞争和官方 调查这一组对立观念之间的联系是十分薄羽的。比如,有人在纠 问式模式中发现了职业化的司法官员、对硬性规则的偏爱以及对 官方文案的信赖,而在抗辩式诉讼制度中则找到了作为决策者的 陪审员、决策过程中的自由裁量以及对口头证据的偏好。〔2每 个概念当中包含的这种百宝箱式的特征组合越多,越是表明这种 二元对立式的分类法是不确定的或含混的。 英美法系各国和大陆法系各国的法律家们都倾向于在抗辩式 诉讼制度和纠问式诉讼制度这一主题之上添加许多本土的变量, 这进一步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在欧洲大陆,法律家们继续为这 2比如,我们可以参阅:A.Goldstein,“Reflections on Two Mode: Themes in American Criminal Procedure,"26 Starford Law Review.1009,1017-19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