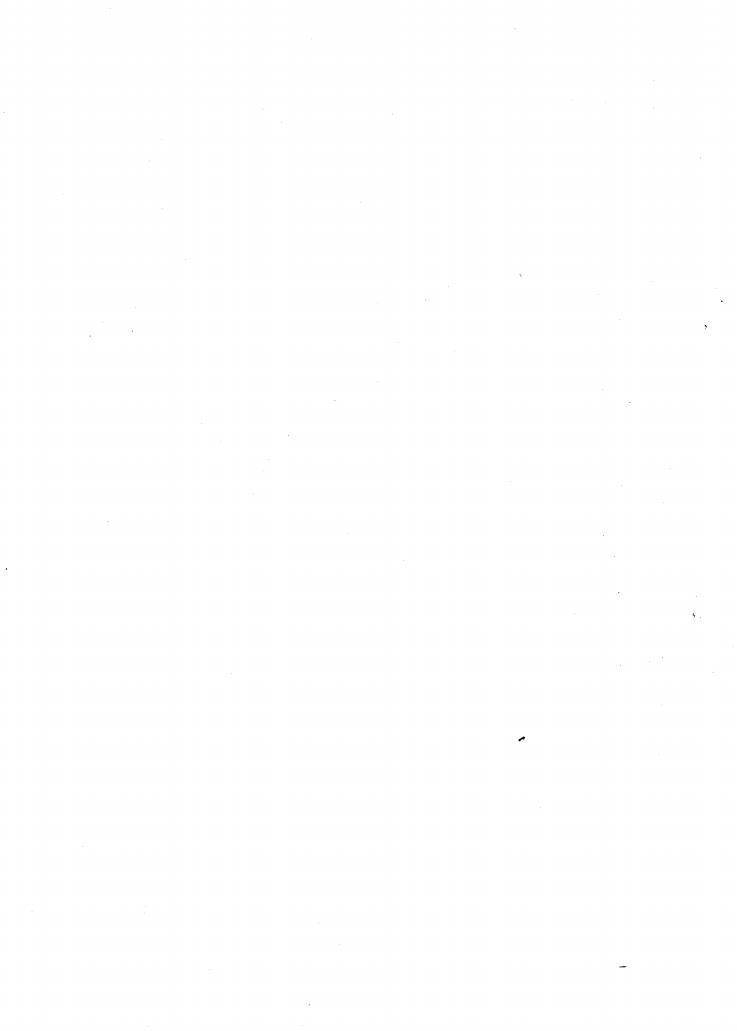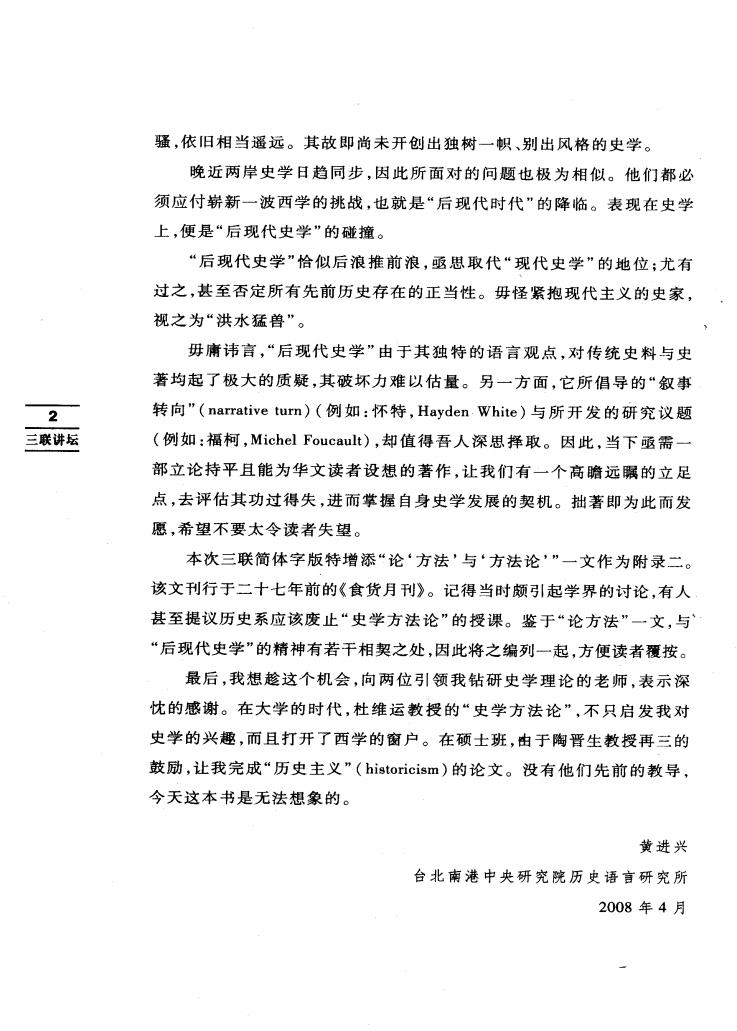
骚,依旧相当遥远。其故即尚未开创出独树一帜、别出风格的史学。 晚近两岸史学日趋同步,因此所面对的问题也极为相似。他们都必 须应付崭新一波西学的挑战,也就是“后现代时代”的降临。表现在史学 上,便是“后现代史学”的碰撞。 “后现代史学”恰似后浪推前浪,亟思取代“现代史学”的地位:尤有 过之,甚至否定所有先前历史存在的正当性。毋怪紧抱现代主义的史家, 视之为“洪水猛兽”。 毋庸讳言,“后现代史学”由于其独特的语言观点,对传统史料与史 著均起了极大的质疑,其破坏力难以估量。另一方面,它所倡导的“叙事 2 转向”(narrative turn)(例如:怀特,Hayden White)与所开发的研究议题 三联讲坛 (例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却值得吾人深思择取。因此,当下亟需一 部立论持平且能为华文读者设想的著作,让我们有一个高雕远瞩的立足 点,去评估其功过得失,进而掌握自身史学发展的契机。拙著即为此而发 愿,希望不要太令读者失望。 本次三联简体字版特增添“论‘方法'与‘方法论,”一文作为附录二。 该文刊行于二十七年前的《食货月刊》。记得当时领引起学界的讨论,有人 甚至提议历史系应该废止“史学方法论”的授课。鉴于“论方法”一文,与 “后现代史学”的精神有若干相契之处,因此将之编列一起,方便读者覆按。 最后,我想趁这个机会,向两位引领我钻研史学理论的老师,表示深 忱的感谢。在大学的时代,杜维运教授的“史学方法论”,不只启发我对 史学的兴趣,而且打开了西学的窗户。在硕士班,由于陶晋生教授再三的 鼓励,让我完成“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论文。没有他们先前的教导 今天这本书是无法想象的。 黄进兴 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08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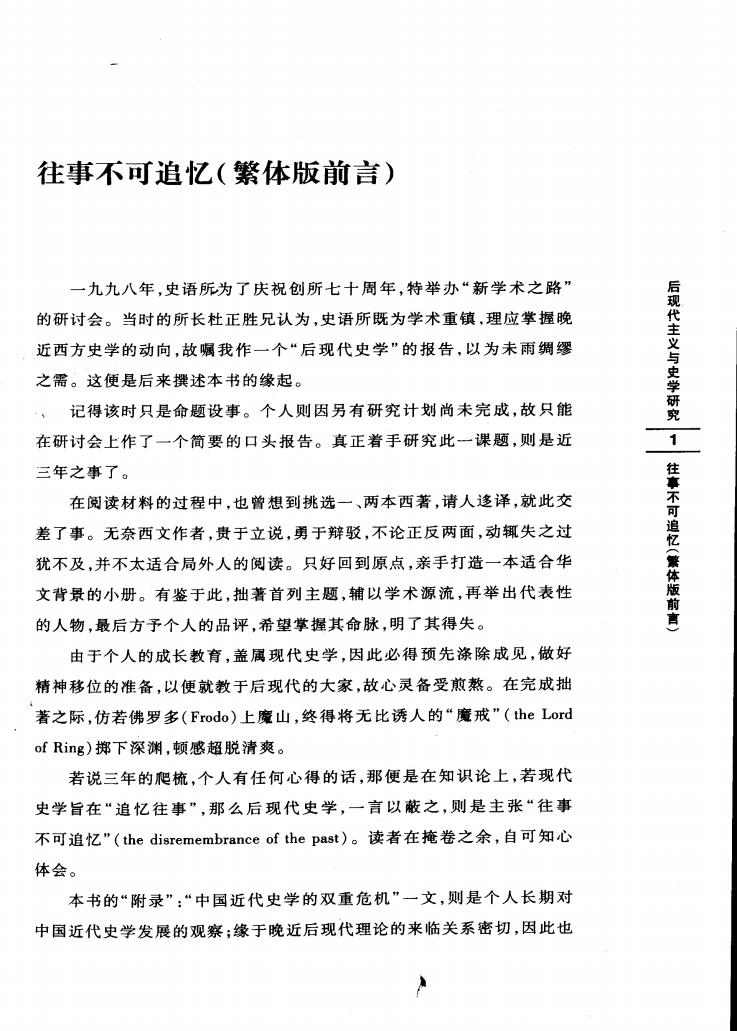
往事不可追忆(繁体版前言) 一九九八年,史语所为了庆视祝创所七十周年,特举办“新学术之路” 的研讨会。当时的所长杜正胜兄认为,史语所既为学术重镇,理应掌握晚 近西方史学的动向,故嘱我作一个“后现代史学”的报告,以为未雨绸缪 之需。这便是后来撰述本书的缘起。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 、记得该时只是命题设事。个人则因另有研究计划尚未完成,故只能 在研讨会上作了一个简要的口头报告。真正着手研究此一课题,则是近 1 三年之事了。 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也曾想到挑选一、两本西著,请人逐译,就此交 差了事。无奈西文作者,贵于立说,勇于辩驳,不论正反两面,动辄失之过 往拿不可追忆 犹不及,并不太适合局外人的阅读。只好回到原点,亲手打造一本适合华 文背景的小册。有鉴于此,拙著首列主题,辅以学术源流,再举出代表性 繁体版前言 的人物,最后方予个人的品评,希望掌握其命脉,明了其得失。 由于个人的成长教育,盖属现代史学,因此必得预先涤除成见,做好 精神移位的准备,以便就教于后现代的大家,故心灵备受煎熬。在完成拙 著之际,仿若佛罗多(Frodo)上魔山,终得将无比诱人的“魔戒”(the Lord of Ring)掷下深渊,顿感超脱清爽。 若说三年的爬梳,个人有任何心得的话,那便是在知识论上,若现代 史学旨在“追忆往事”,那么后现代史学,一言以蔽之,则是主张“往事 不可追忆”(the disremembrance of the past)。读者在掩卷之余,自可知心 体会。 本书的“附录”:“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一文,则是个人长期对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观察;缘于晚近后现代理论的来临关系密切,因此也

收人于后。 最后,在我踉踉跄跄的写作过程中,承蒙余英时老师与师母一路的扶 持,永远铭感于衷。另外,许倬云、李亦园老师的勉励亦不可或缺。余国 藩教授,之前虽未曾谋面,但一见如故,与其请益,如沐春风。我的朋友哈 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及加州大学的徐澄琪教 授,与楼一宁先生,均是本书许多篇章的试读者,他们的意见与支持,令人 感动。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的方万全兄经常解答我的哲学之惑,史语所西 洋史组的张谷铭、陈正国、戴丽娟、梁其姿以及以前的老同事卢建荣兄都 是我时相请益的对象,一并致谢。 2 三联讲坛 黄进兴 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06年1月

第一章 绪论:后现代主义与 “历史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