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将全书构成统一的整体。现存的宋元平话已经分卷分目,E国维 绪 认为这是“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唐三藏取经诗话跋》),但这时 的目录,字数参差不等,未作修饬。至明代,目录文字越来越讲究」 今见最早的嘉靖壬午(1522)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每回标题都 是单句七字。《水浒传》每回的标题已是双句,大致对偶。崇祯本 《金瓶梅》,回目已十分工整完美,所以有人说:“吾见小说中,其回 日之最佳者,莫如《金瓶梅》。”(曼殊《小说丛话》)除分回立目之 外,章回小说还保存了宋元话本中开头引开场诗,结尾用散场诗的 体制。正文常以“话说”两字起首,往往在情节开展的紧要关头煞 尾,用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中间又多引诗 词曲赋来作场景描写或人物评赞等。明代章回小说在体制上得以 定型的同时,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日趋成熟。以《三国志通俗演 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四大奇书”为主要标 志,清晰地展示了长篇小说艺术发展的历程。这主要表现在:成书 过程从历代集体编著过渡到个人独创;创作意识从借史演义,寓言 寄托,到面对现实,关注人生;表现题材从着眼于兴废争战等国家 大事,到注目于日常生活、家庭琐事;描写的人物从非凡的英雄怪 杰,到寻常的平民百姓;塑造的典型从突出特征性的性格到用多 色、动感的笔触去刻画人物的个性:情节结构从线性的流动,到网 状的交叉;小说的语言从半文半白,到口语化、方言化;如此等等 都足以说明明代的章回小说在我国的小说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与章回小说交相辉映的是,明代中后期的白话短篇小说在宋 元“小说”话本的基础上也出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发展得更为精 致:文言小说在话本化的道路上也有新的变化。因此,人们常把小 说作为明代最具时代特征的文学样式,这是有一定根据的。 明代中后期俗文学兴盛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戏曲在元代高 度繁荣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明代戏曲的主流是由宋 元南戏演变而来的传奇。明代前期的传奇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好的 作品,但总的色彩比较黯谈。嘉靖以后,《宝剑记》、《鸣凤记》,以 14

及第一次用昆腔曲调写作的《浣纱记》陆续问世,标志着以昆腔为 4 主导的传奇的繁荣时期到来。昆腔是元末明初流行于昆山一带的 第 地方声腔,嘉靖初年,经魏良辅改造后,声调纡徐宛转、悠扬细腻, 兼用笛、箫、笙、琵琶等乐器伴奏,加之舞蹈性强,表现风格优美,成 文学 为我国古代戏曲史上一种最为完整的表演艺术体系,因而在城市 舞台上长期居于霸主的地位。直到清代乾隆以前,一些著名的传 奇作家几乎都是用昆腔来写作的。但在农村,弋阳腔则具有广泛 的基础。弋阳腔的特点是:文人雅士少有创作,往往是改编昆山腔 的现成剧本而成:唱词通俗,“顺口可歌”,便于群众接受:其歌唱 方式是一人独唱,众人帮腔,只用喧闹的锣鼓等打击乐伴奏,适宜 特性认识的深 于通衢野外演出。因而它在民间广泛流行,以后发展为众多的支 派,长期与昆山腔争锋媲美。明代中期以后的传奇,以昆山腔、弋 阳腔为主,造就了汤显祖、沈璟、屠隆、王骥德、吕天成、高濂、周朝 俊、冯梦龙、祁彪佳、吴炳、袁于令、孟称舜等一大批剧作家和曲论 家。他们或主才情意趣、词采奇丽;或重格律严峻、语言本色;或求 文辞骈绮、堆垛典实,形成了不同流派争妍斗艳的局面,创造了明 代戏曲的一个黄金时期。南戏传奇的繁荣,促进了北曲杂剧的蜕 变。明代前期的杂剧作家在固守元剧体制的同时,个别人在形式 上已有所突破,如朱有墩的剧作打破了一本四折的惯例,采用了对 唱,合唱、接唱等形式,甚至出现了南北合套的体式;王九思的《中 山狼院本》以一折为一本,开启了短剧创作的先风。至明代中 期,以徐渭的《四声猿》为代表,用南曲写杂剧的风气大兴,形成了 明代后期杂剧普遍南曲化的独特风貌,将元杂剧中一本四折、一人 主唱等格局全部打破。剧作家或用南曲,或用北曲,或用南北合 套,不拘成法,随意灵活,这就有利于创作时开拓题材,抒写怀抱。 徐复祚、王衡、孟称舜等一些优秀的作家涌现出来,使得杂刷在传 奇的冲击下,行将退出演出舞台之前又别具了一番风光。 明代戏曲、小说及民歌等通俗文学的发展,明显地促进了人们 对于文学特性认识的深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5

一、高度重视文学的情感特征。明代文学家对于情感的论述 绪 特别丰富,往往把情感作为品评作品美学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准则。 这是宋元以来对于理学专制的反弹,是肯定自我、张扬个性的一种 表现。俗文学一般都“绝假纯真”,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影,所以 往往成为主情论者的“样板”,于此加深了他们对于文学情感特征 的思考和认识,并以此来作为批判“假文学”的武器。这从李梦阳 赞扬民歌“无非其情也”,说“真诗乃在民间”(《李空同全集》卷五 十《诗集自序》),到袁宏道称民歌“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 欲”,是“真人所作”之“真声”(《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 诗》):从徐渭强调“曲本取于感发人心”(《南词叙录》),反对在戏 曲创作中玩弄“时文气”,到汤显粗创造“理之所必无”而“情之所 必有”的“有情人”杜丽娘(《牡丹亭题辞》);从瞿佑称作文言小说 “哀穷悼屈”(《剪灯新话序》),李贽称《水浒传》是“发愤之所作 (《忠义水浒传叙》),到冯梦龙编短篇小说集名之日《情史》,提出 “情教”说(《情史序》),都表明明代情感论的发展与俗文学的繁荣 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晰认识文学的“虚”“实”关系。明代以前的文学理论, 主要建筑在诗论文评的基础上,重在诚、真、信、实,反对浮、夸、虚、 幻,往往不能正确地认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而戏曲、小 说与诗歌、散文不同,它们描绘的故事与人物大都是虚实相间、真 幻互出,多有艺术虚构。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戏曲、小 说艺术虚构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就文言小说而言,直到胡 应麟才对唐传奇的艺术虚构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少室山 房笔丛》中说“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作“幻设语”。 同时,他论戏曲说:“凡传奇以戏文为称也,亡往而非戏也,故其事 欲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颠倒而亡实也。”在他前后,熊大木、谢肇 湘、汤显祖、王骥德、李日华、叶昼、冯梦龙、袁于令等都对文学的虚 构性作了较好的论述。如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凡为小说及 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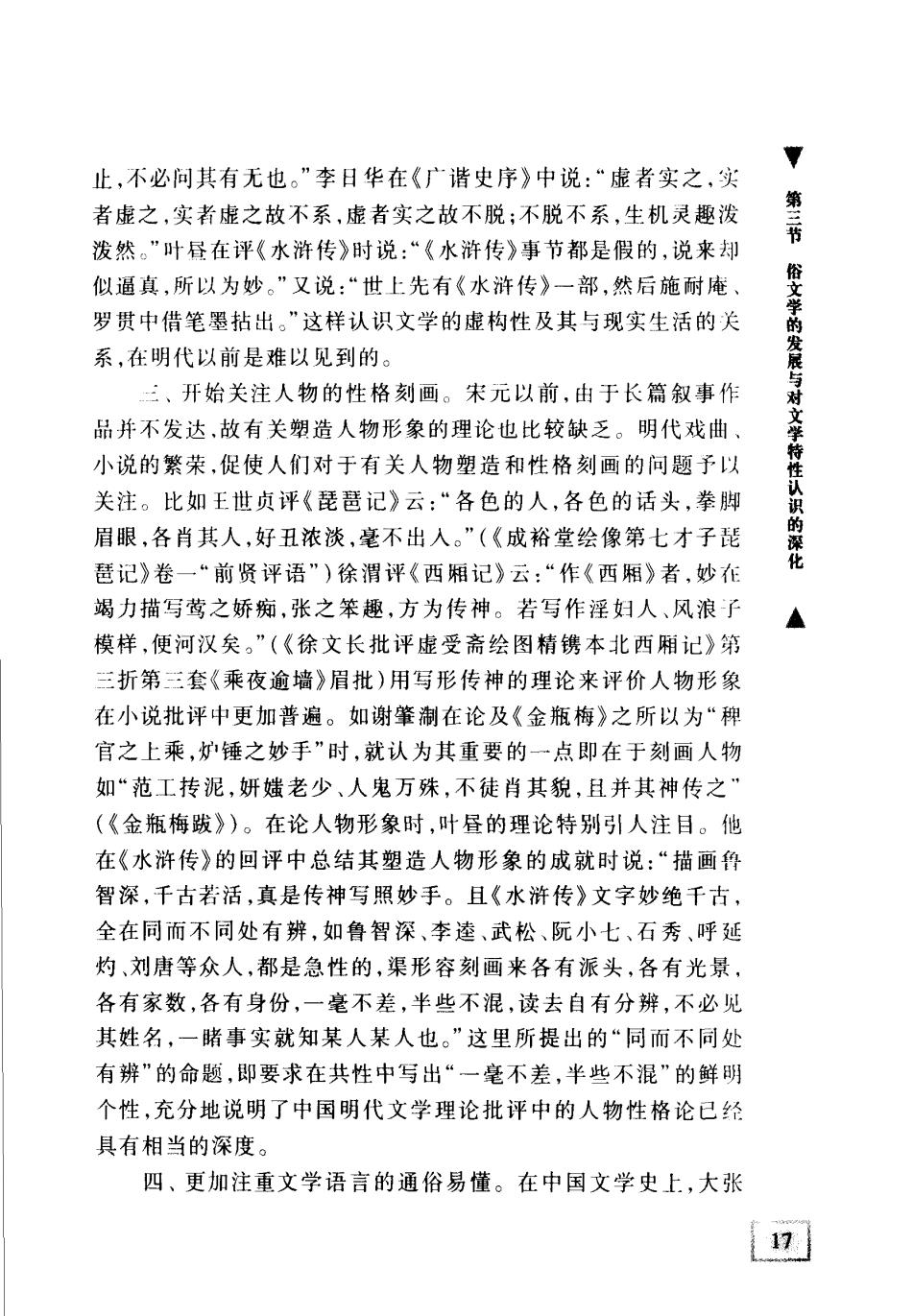
7 止,不必问其有无也。”李日华在《广谐史序》中说:“虚者实之,实 者虚之,实者虚之故不系,虚者实之故不脱:不脱不系,生机灵趣泼 泼然。”叶昼在评《水浒传》时说:“《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 似逼真,所以为妙。”又说:“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 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这样认识文学的虚构性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关 的 系,在明代以前是难以见到的。 三、开始关注人物的性格刻画。米元以前,由于长篇叙事作 对 品并不发达,故有关塑造人物形象的理论也比较缺乏。明代戏曲 小说的繁荣,促使人们对于有关人物塑造和性格刻画的问题予以 关注。比如王世贞评《琵琶记》云:“各色的人,各色的话头,拳脚 眉眼,各肖其人,好丑浓淡,毫不出入。”(《成裕堂绘像第七才子琵 琶记》卷一“前贤评语”)徐渭评《西厢记》云:“作《西厢》者,妙在 竭力描写莺之娇痴,张之笨趣,方为传神。若写作淫妇人、风浪子 模样,便河汉矣。”(《徐文长批评虚受斋绘图精镌本北西厢记》第 三折第三套《乘夜逾墙》眉批)用写形传神的理论来评价人物形象 在小说批评中更加普遍。如谢肇制在论及《金瓶梅》之所以为“稗 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时,就认为其重要的一点即在于刻画人物 如“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 (《金瓶梅跋》)。在论人物形象时,叶昼的理论特别引人注目。他 在《水浒传》的回评中总结其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就时说:“描画鲁 智深,千古若活,真是传神写照妙手。且《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 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 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 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 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这里所提出的“同而不同处 有辨”的命题,即要求在共性中写出“一毫不差,半些不混”的鲜明 个性,充分地说明了中国明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人物性格论已经 具有相当的深度。 四、更加注重文学语言的通俗易懂。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张 17

4 旗鼓地提倡语言的通俗化,是随着白话小说的繁荣而兴起的。嘉 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书名就突出了“通俗”两字。其书卷首蒋 大器序十分强调通俗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写得“读诵者人人得而知 之”,才能使“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以后的小说论者 曾从各个角度论证了使用“俗近语”的重要意义。至于戏曲,虽有 一定的特殊性,但不少论者在谈及宾白时,也都强调通俗性,如王 骥德在《曲律·论宾白》中说:“《琵琶》黄门白,只是寻常话头,略 加贯串,人人晓得,所以至今不废。对口白须明白简质,用不得太 文字;凡用‘之乎者也',俱非当家。《浣纱》纯是四六,宁不厌人! ”明代文学家对于语言通俗化的注重,不但对当时俗文学的发展起 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后来特别是晚清文学革命也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俗文学的发展,推动、刺激了雅文学向着俗化的方向演变,而 俗文学自身也在雅文学的规范、熏陶下趋向雅化。明代文学就在 较之前代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俗与雅的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相互转 化的过程中留下了独特的发展轨迹。比如正宗的雅文学诗歌、散 文,从李梦阳到徐渭,再到袁宏道、张岱,在民间文学的滋润下,陆 续创作了一些通俗如话、自由活泼,但又俗而有趣、浅而不薄的作 品。原为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所创作和欣赏的文言传奇小说,也在 时尚的驱动和说话艺术的影响下,逐渐变成下层文士和一般市民 的娱乐品,呈现了种种话本化的倾向。反过来,民歌、笑话等的收 集和刊刻,实际上都经过了文人的整理和加工。“鄙俚浅近”(王 骥德《曲律·杂论》)的戏文,在文人的参与下,演变为传奇“雅 部”。长、短篇通俗小说的编辑、创作,也大都从文言小说、三教经 典、历史文本和诗词散文中汲取养料,于是从创作意趣、题材取向、 表现手法,到语言运用,都越来越趋向雅化。雅、俗文学的交融,大 大地改变了作者队伍的面貌,造就了一批新型的雅俗兼顾的作者 群。在明代五百多名戏曲作者和一百多名通俗小说作者中”,尽 管绝大多数是下层文士或民间艺人,但也有相当部分是高雅的文 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