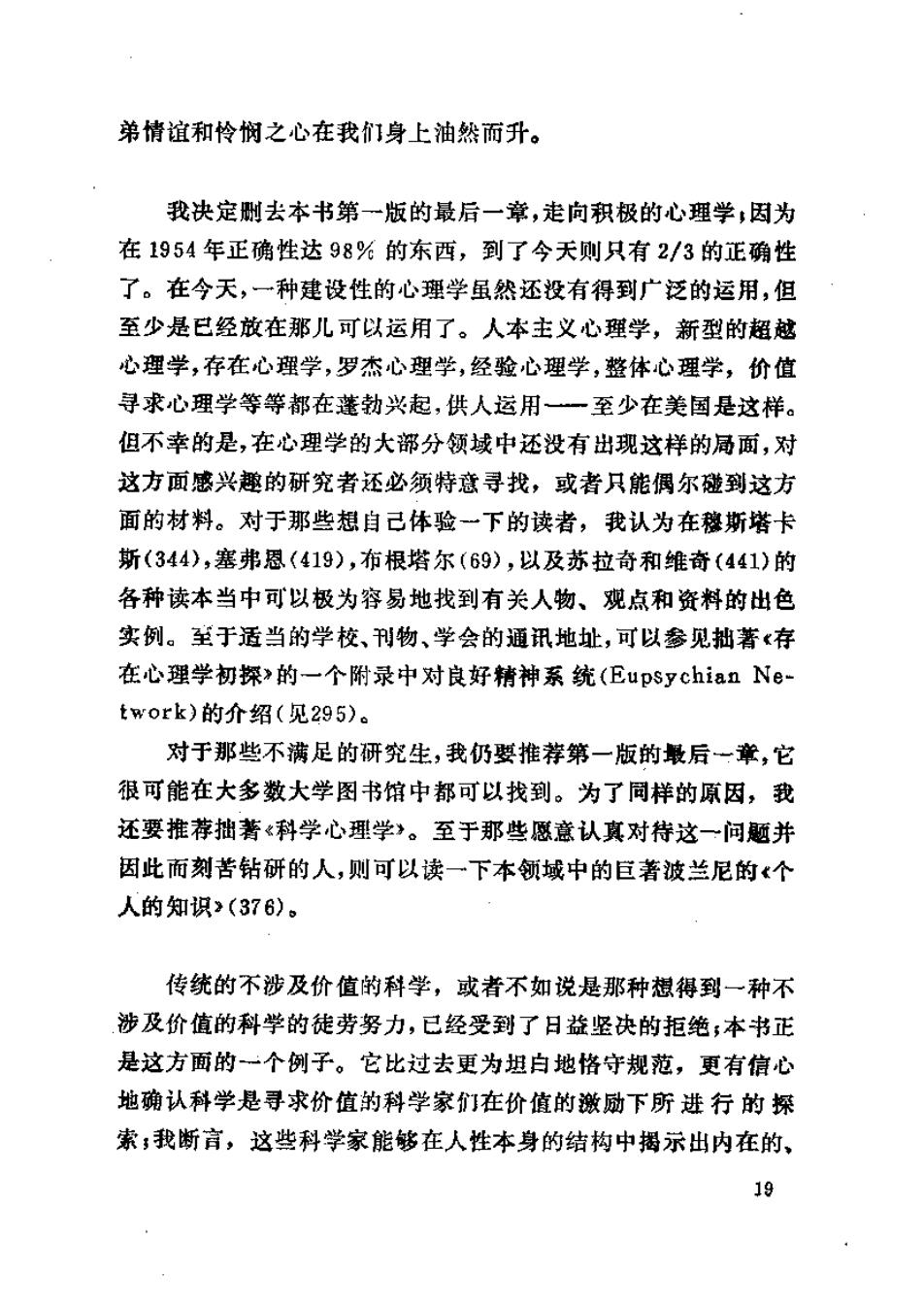
弟情谊和怜悯之心在我们身上油然而升。 我决定删去本书第一版的最后一章,走向积极的心理学,因为 在1954年正确性达98%的东西,到了今天则只有2/3的正确性 了。在今天,一种建设性的心理学虽然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但 至少是已经放在那儿可以运用了。人本主义心理学,新型的超越 心理学,存在心理学,罗杰心理学,经验心理学,整体心理学,价值 寻求心理学等等都在莲勃兴起,供人运用一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但不幸的是,在心理学的大部分领域中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局面,对 这方面感兴趣的研究者还必须特意寻找,或者只能偶尔碰到这方 面的材料。对于那些想自己体验一下的读者,我认为在穆斯塔卡 斯(344),塞弗恩(419),布根塔尔(69),以及苏拉奇和维奇(441)的 各种读本当中可以极为容易地找到有关人物、观点和资料的出色 实例。至于适当的学校、刊物、学会的通讯地址,可以参见拙著《存 在心理学初探》的一个附录中对良好精神系统(Eupsychian Ne- twork)的介绍(见295)。 对于那些不满足的研究生,我仍要推荐第一版的最后一章,它 很可能在大多数大学图书馆中都可以找到。为了同样的原因,我 还要推荐抽著科学心理学》。至于那些感意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并 因此而刻苦钻研的人,则可以读一下本领域中的巨著波兰尼的《个 人的知识》(376)。 传统的不涉及价值的科学,或者不如说是那种想得到一种不 涉及价值的科学的徒劳努力,已经受到了日益坚决的拒绝,本书正 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它比过去更为坦白地格守规范,更有信心 地确认科学是寻求价值的科学家们在价值的激励下所进行的探 索,我断言,这些科学家能够在人性本身的结构中羯示出内在的、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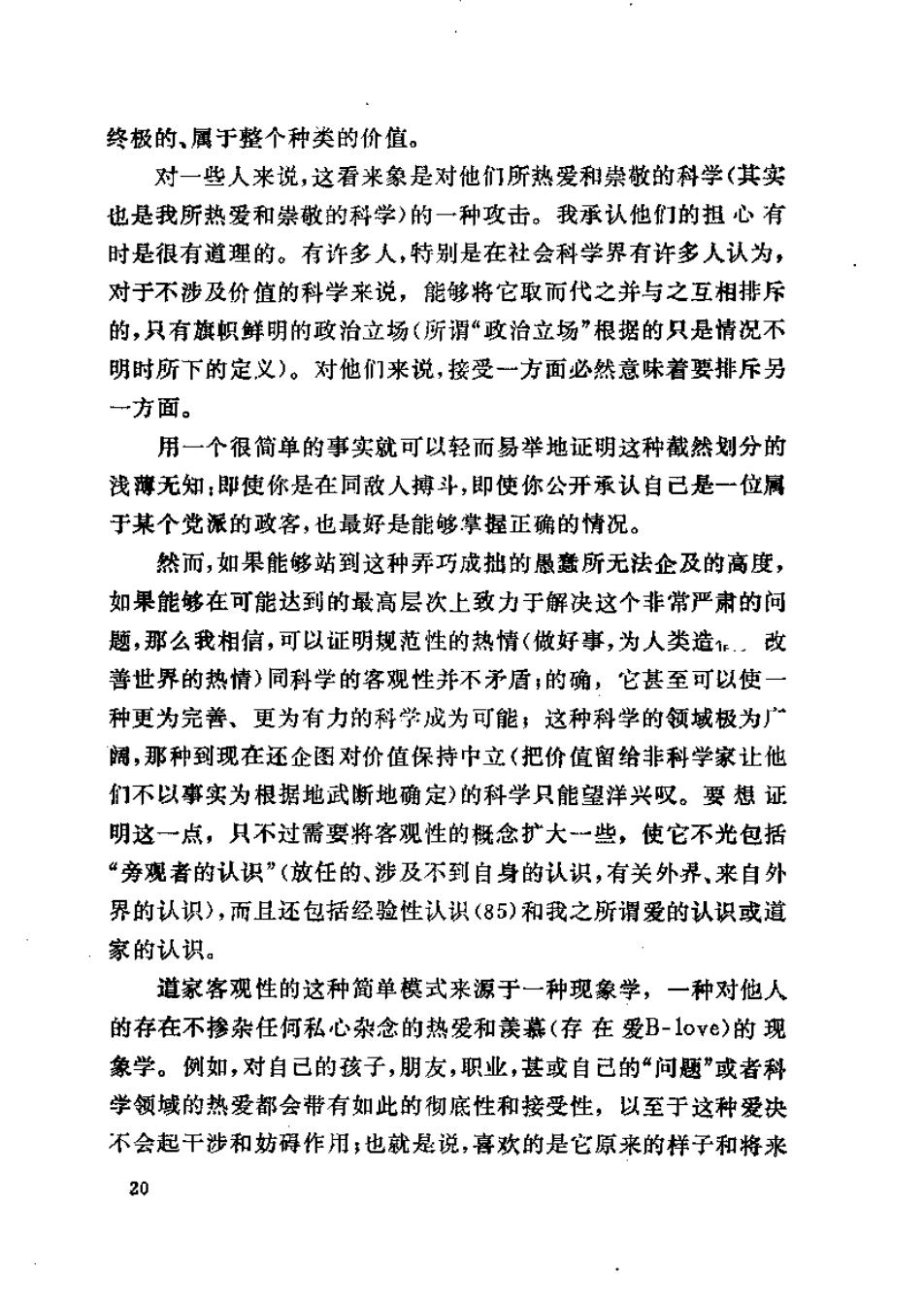
终极的、属于整个种类的价值。 对一些人来说,这看来象是对他们所热爱和崇敬的科学(其实 也是我所热爱和崇敬的科学)的一种攻击。我承认他们的担心有 时是很有道理的。有许多人,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界有许多人认为, 对于不涉及价值的科学来说,能够将它取而代之并与之互相排序 的,只有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所谓“政治立场”根据的只是情祝不 明时所下的定义)。对他们来说,接受一方面必然意味着要排斥另 一方面。 用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这种截然划分的 浅薄无知:即使你是在同敌人搏斗,即使你公开承认自已是一位属 于某个党派的政客,也最好是能够掌握正确的情况。 然而,如果能够站到这种弄巧成拙的愚意所无法企及的高度, 如果能够在可能达到的最高层次上致力于解决这个非常严肃的问 题,那么我相信,可以证明规范性的热情(做好事,为人类造:.,改 善世界的热情)同科学的客观性并不矛盾,的确,它甚至可以使一 种更为完善、更为有力的科学成为可能;这种科学的领域极为 阔,那种到现在还企图对价值保持中立(把价值留给非科学家让他 们不以事实为根据地武断地确定)的科学只能望洋兴叹。要想证 明这一点,只不过需要将客观性的概念扩大一些,使它不光包括 “旁观者的认识”(放任的、涉及不到自身的认识,有关外界、来自外 界的认识),而且还包括经验性认识(85)和我之所谓爱的认识或道 家的认识。 道家客观性的这种简单模式来源于一种现象学,一种对他人 的存在不摻杂任何私心杂念的热爱和羡幕(存在爱B-love)的现 象学。例如,对自己的孩子,朋友,职业,甚或自己的“问题”或者科 学领域的热爱都会带有如此的彻底性和接受性,以至于这种爱决 不会起干涉和妨得作用,也就是说,喜欢的是它原来的样子和将来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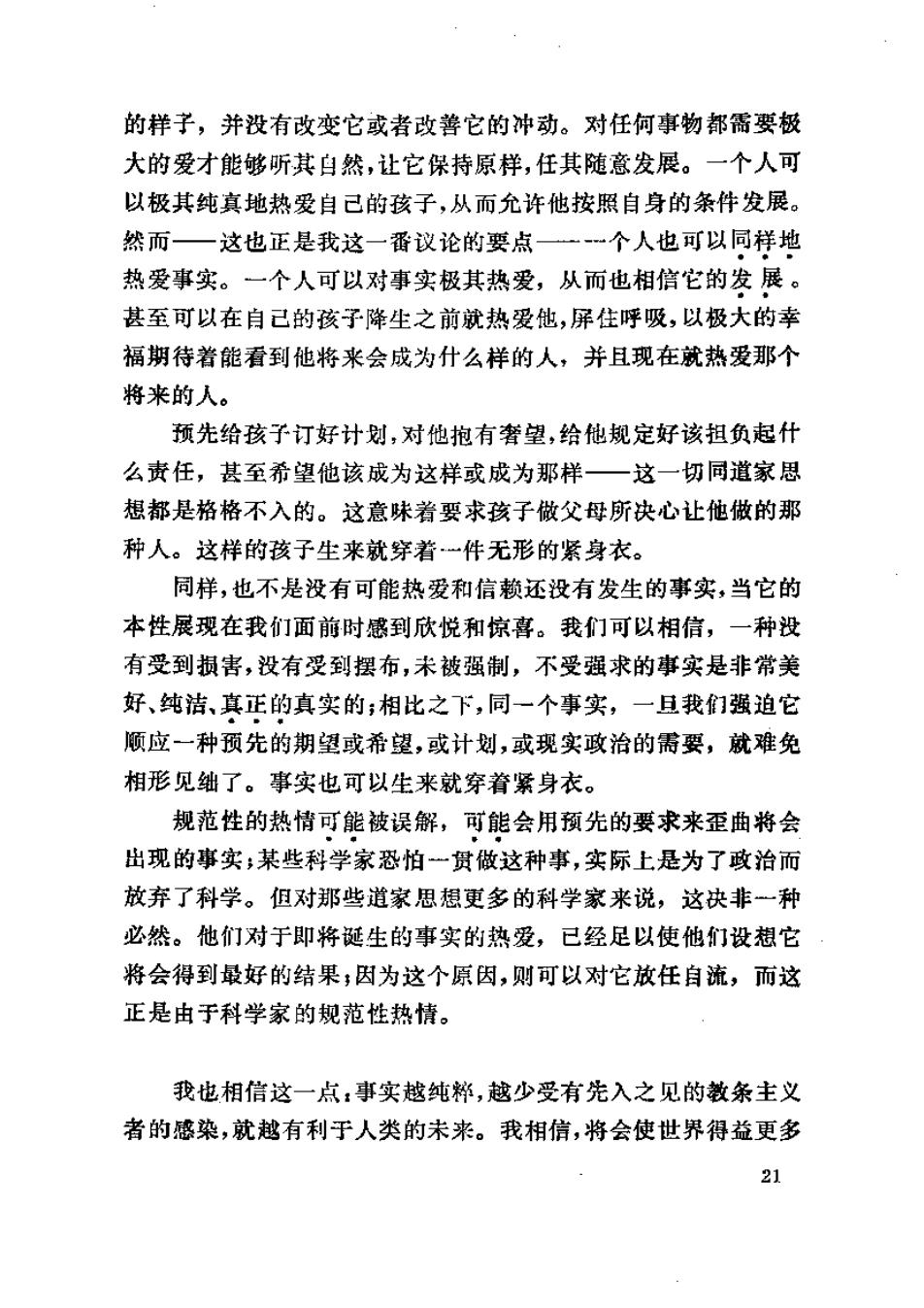
的样子,并没有改变它或者改善它的冲动。对任何事物都需要极 大的爱才能够所其自然,让它保持原样,任其随意发展。一个人可 以极其纯真地热爱自己的孩子,从而允许他按照自身的条件发展。 然而一这也正是我这一番议论的要点一一个人也可以同样地 热爱事实。一个人可以对事实极其热爱,从而也相倍它的发展。 甚至可以在自已的孩子降生之前就热爱他,屏住呼吸,以极大的幸 福期待着能看到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且现在就热爱那个 将来的人。 预先给孩子订好计划,对他抱有奢望,给他规定好该担负起什 么责任,甚至希望他该成为这样或成为那样一这一切同道家思 想都是格格不入的。这意味着要求孩子做父母所决心让他做的那 种人。这样的孩子生来就穿着一件无形的紧身衣。 同样,也不是没有可能热爱和信赖还没有发生的事实,当它的 本性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感到欣悦和惊喜。我们可以相信,一种没 有受到损害,没有受到摆布,未被强制,不受强求的事实是非常美 好、纯洁、真正的真实的;相比之下,同一个事实,一且我们强迫它 顺应一种预先的期望或希望,或计划,或现实政治的需要,就难免 相形见绌了。事实也可以生来就穿着紧身衣。 规范性的热情可能被误解,可能会用预先的要求来歪曲将会 出现的事实;某些科学家恐怕一贯做这种事,实际上是为了政治而 放弃了科学。但对那些道家思想更多的科学家来说,这决非一种 必然。他们对于即将诞生的事实的热爱,已经足以使他们设想它 将会得到最好的结果,因为这个原因,则可以对它放任自流,而这 正是由于科学家的规范性热情。 我也相信这一点:事实越纯郴,越少受有先入之见的教条主义 者的感染,就越有利于人类的未来。我相信,将会使世界得益更多 21

的不是我今关所奉行的政治信念,而是将来的事实。我对将来的 认识比对我本人今天的认识更为信赖。 这是“服从的是上帝的意感,而不是我的意感”的一种人本主 义科学的翻版。我对于人类的担心和希望,我对于行善的渴望,我 需求安宁和友情的愿望,我的规范性的热情一一我觉得这一切的 利益都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只要我对事实保持一种虚怀若谷的态 度,只要我在道家拒绝对事实先入为主、任意摆弄的意义上保持客 魂,不掺杂任何个人色彩,只要我一直坚信所知愈多裨益愈大。 ,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在本书之后所发表的许多论文、论著 中,我都假定一个人真实潜能的实现取决于是否有能够满足基本 需要的父母和其他人,取决于现在被称为“生态学”的因素,取决于 是否有“健康的”文化,取决于整个世界的情况,等等。一个“有利 于先决条件”的复杂分类系统使我们有可能向自我实现和完竺人 性方面进行发展。这些物理、化学、生物学、人际间、文化的条件对 个人至关紧要,最终竟达到了决定能否向个人提供人类的基本必 需品和基本“权利”的程度,一个人只有拥有这些必需品和基本“权 利”,才能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人性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旦对这些先决条件进行探讨,我们不免会感到悲伤,因为人 类的潜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被擢毁,被抑制,因此,一个具有完 整人性的人看起来就象一个奇迹,这样一个人的出现真是太希罕 了,所以只能让人肃然起敏。但同时,我也会感到振奋,因为自 我实现的人毕竞是存在的,因此也是可能存在的。严峻的考验并 非不能经受,终点线也并非不可逾越。 在这里,研究者几平会毫无疑问地受到种种贲难的夹击,这些 责难既是人与人之间的,也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不是责怪他过于 “乐观”,就是责怪他过于“悲观”,根据其实就是他当时着眼于哪 22

方面。同样,一方面会责怪他鼓吹遗传,另一方面则会攻击他鼓吹 环境。各种政治派别前无疑会根据当时的宣传要,强行给他贴 上各类不同的标签。 科学家当然会抗拒这些截然划分、乱贴标签的不全则无的倾 向,将会继续分层次、按等级地思考问题,整体地把握许许多多同 时起作用的决定因素。他将尽全力接受各种资料,并将它们尽可 能清楚地同自己的愿望、希望、担心区别开。现在已经非常清楚, 这些问题一一什么样的人是健全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是健全的社 会一完全属于经验科学的领城,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在这 些领域内促进认识的发展(316)。 同第二个问题相比,即什么样的社会能够造就具有完整人格 的人,本书更多地着眼于第一个问题,即具有完整人格的人本身。 自从本书于1954年初版以来,我就这一问题写了大量文章,但我 并不想把这些研究成果收进修订本。相反,我要请读者参考我就这 一问题写的一些文章(291,301,303,311a,311b,312,315);同时, 我想着重强调,有必要熟悉一下关于规范性社会心理学的大量研 究文献(有时它还被称为组织发展,組织理论,管理理论等等)。在 我看来,这些理论、病例报皆、研究等等极为深刻,提供了一种真正 切实可行的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民主和极权理论,以及其它 现有的各种杜会科学理论的种种翻版一样可供人们选择。我屡次 惊讶地发现,甚至连略知阿吉里斯(15,16),本尼斯(42,43,45),利 克特(275),麦格雷戈(332)等人的研究工作的心理半家也为数甚 少,而这只不过是刚刚提到这一领域中的儿位知名人物。无论如 何,要想认真对待自我实现的理论,则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新型的社 会心理学。如果有人想要了解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让我选择一 本刊物推荐给他们,哪我就会选择《应用行为科学学报》,尽管它的 名称肯定会使人产生误解。 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