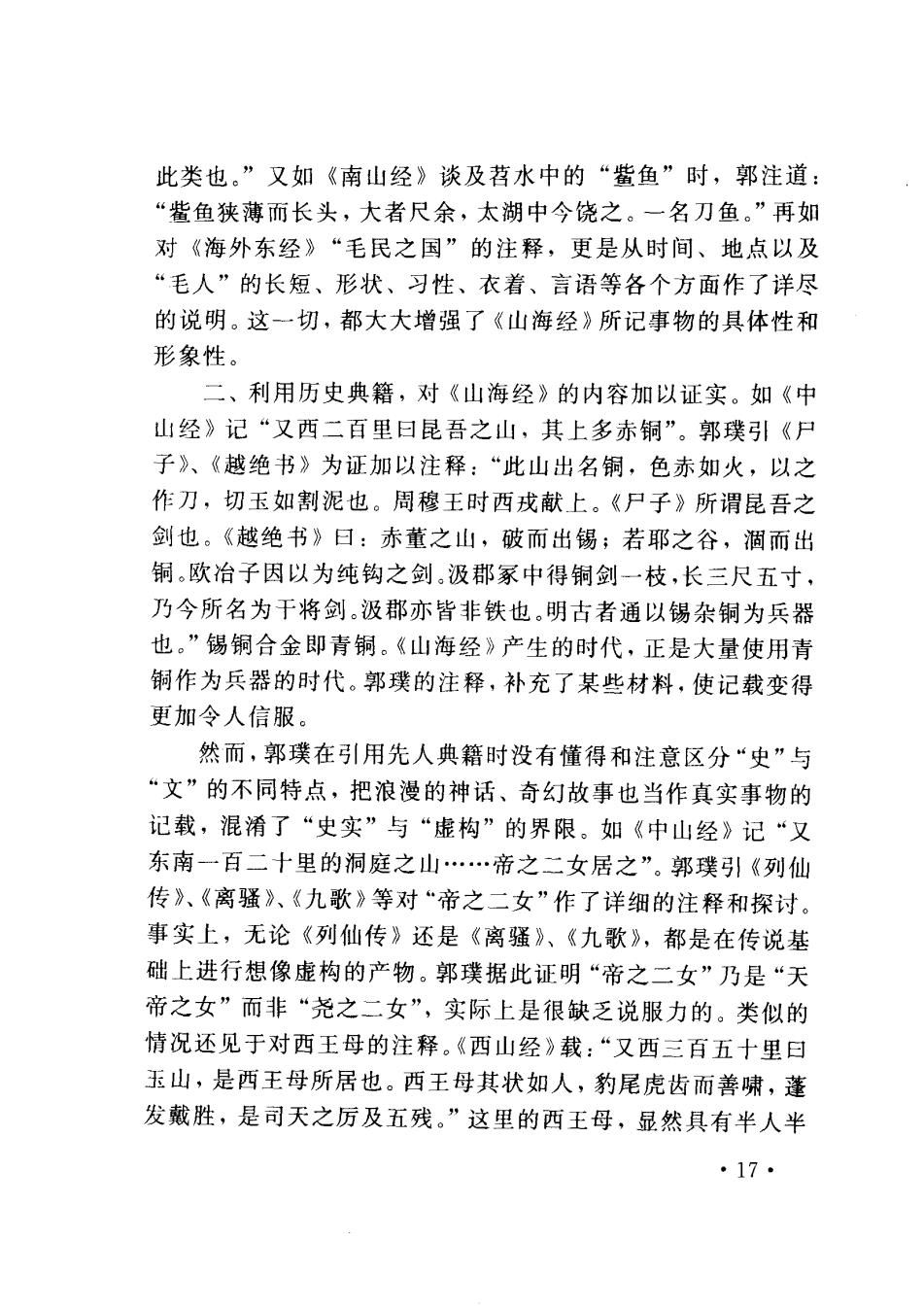
此类也。”又如《南山经》谈及苕水中的“酱鱼”时,郭注道: “指鱼狭薄而长头,大者尺余,太湖中今饶之。一名刀鱼。”再如 对《海外东经》“毛民之国”的注释,更是从时间、地点以及 “毛人”的长短、形状、习性、衣着、言语等各个方面作了详尽 的说明。这一切,都大大增强了《山海经》所记事物的具体性和 形象性。 二、利用历史典籍,对《山海经》的内容加以证实。如《中 山经》记“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郭璞引《尸 子》、《越绝书》为证加以注释:“此山出名铜,色赤如火,以之 作刀,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时西戎献上。《尸子》所谓昆吾之 剑也。《越绝书》日:赤董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谷,涸而出 铜。欧冶子因以为纯钩之剑.汲郡冢中得铜剑一枝,长三尺五寸, 乃今所名为干将剑。汲郡亦皆非铁也。明古者通以锡杂铜为兵器 也。”锡铜合金即青铜。《山海经》产生的时代,正是大量使用青 铜作为兵器的时代。郭璞的注释,补充了某些材料,使记载变得 更加令人信服。 然而,郭璞在引用先人典籍时没有懂得和注意区分“史”与 “文”的不同特点,把浪漫的神话、奇幻故事也当作真实事物的 记载,混淆了“史实”与“虚构”的界限。如《中山经》记“又 东南一百二十里的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引《列仙 传》、《离骚》、《九歌》等对“帝之二女”作了详细的注释和探讨 事实上,无论《列仙传》还是《离骚》、《九歌》,都是在传说基 础上进行想像虚构的产物。郭璞据此证明“帝之二女”乃是“天 帝之女”而非“尧之二女”,实际上是很缺乏说服力的。类似的 情况还见于对西王母的注释。《西山经》载:“又西三百五十里曰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 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这里的西王母,显然具有半人半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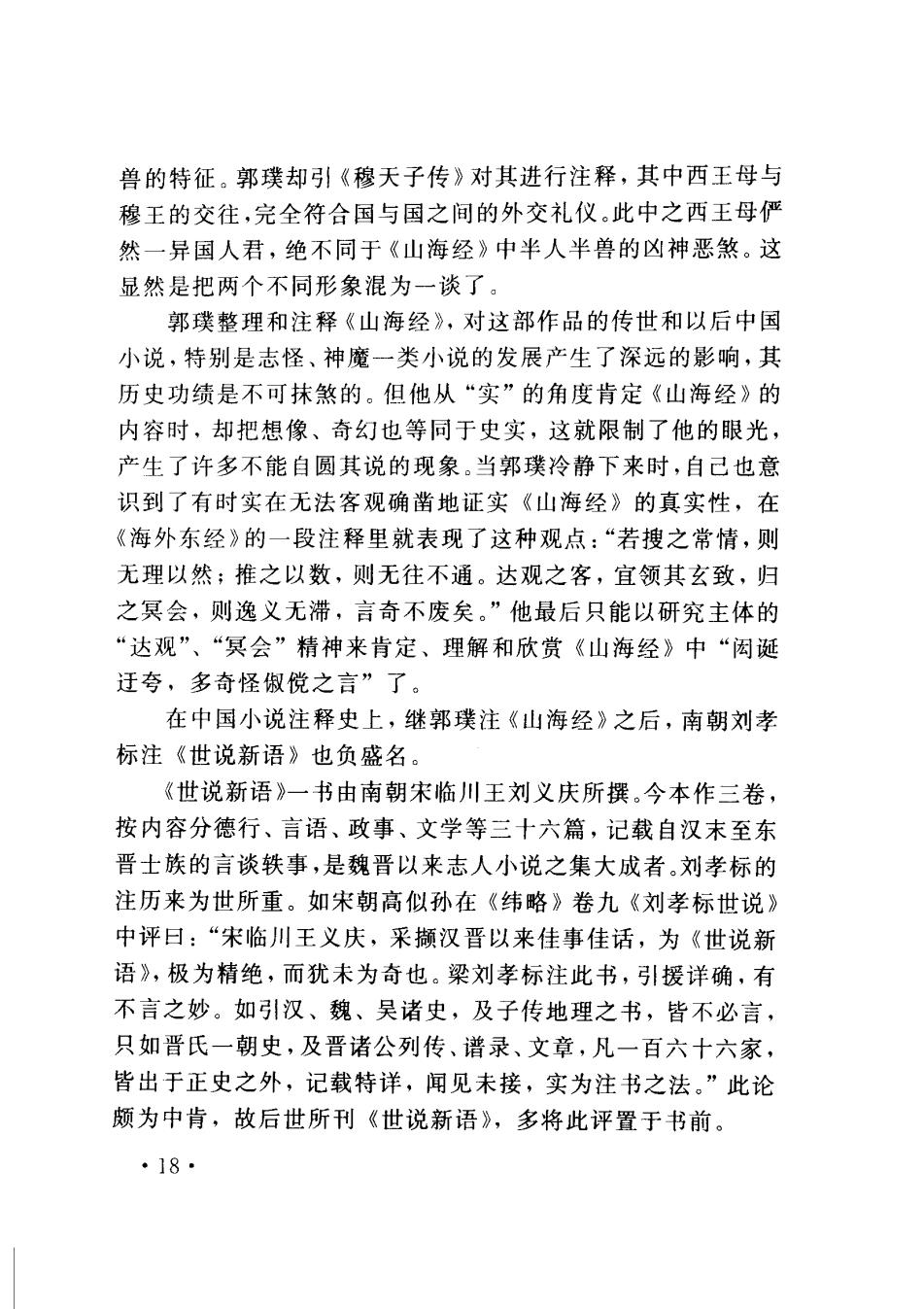
兽的特征。郭璞却引《穆天子传》对其进行注释,其中西王母与 穆王的交往,完全符合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礼仪。此中之西王母俨 然一异国人君,绝不同于《山海经》中半人半兽的凶神恶煞。这 显然是把两个不同形象混为一谈了。 郭璞整理和注释《山海经》,对这部作品的传世和以后中国 小说,特别是志怪、神魔一类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 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但他从“实”的角度肯定《山海经》的 内容时,却把想像、奇幻也等同于史实,这就限制了他的眼光, 产生了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现象。当郭璞冷静下来时,自己也意 识到了有时实在无法客观确凿地证实《山海经》的真实性,在 《海外东经》的一段注释里就表现了这种观点:“若搜之常情,则 无理以然;推之以数,则无往不通。达观之客,宜领其玄致,归 之冥会,则逸义无滞,言奇不废矣。”他最后只能以研究主体的 “达观”、“冥会”精神来肯定、理解和欣赏《山海经》中“闳诞 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了。 在中国小说注释史上,继郭璞注《山海经》之后,南朝刘孝 标注《世说新语》也负盛名。 《世说新语》一书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撰。今本作三卷, 按内容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记载自汉末至东 晋士族的言谈轶事,是魏晋以来志人小说之集大成者。刘孝标的 注历来为世所重。如宋朝高似孙在《纬略》卷九《刘孝标世说 中评日:“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 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 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 只如晋氏一朝史,及晋诸公列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 皆出于正史之外,记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此论 颇为中肯,故后世所刊《世说新语》,多将此评置于书前。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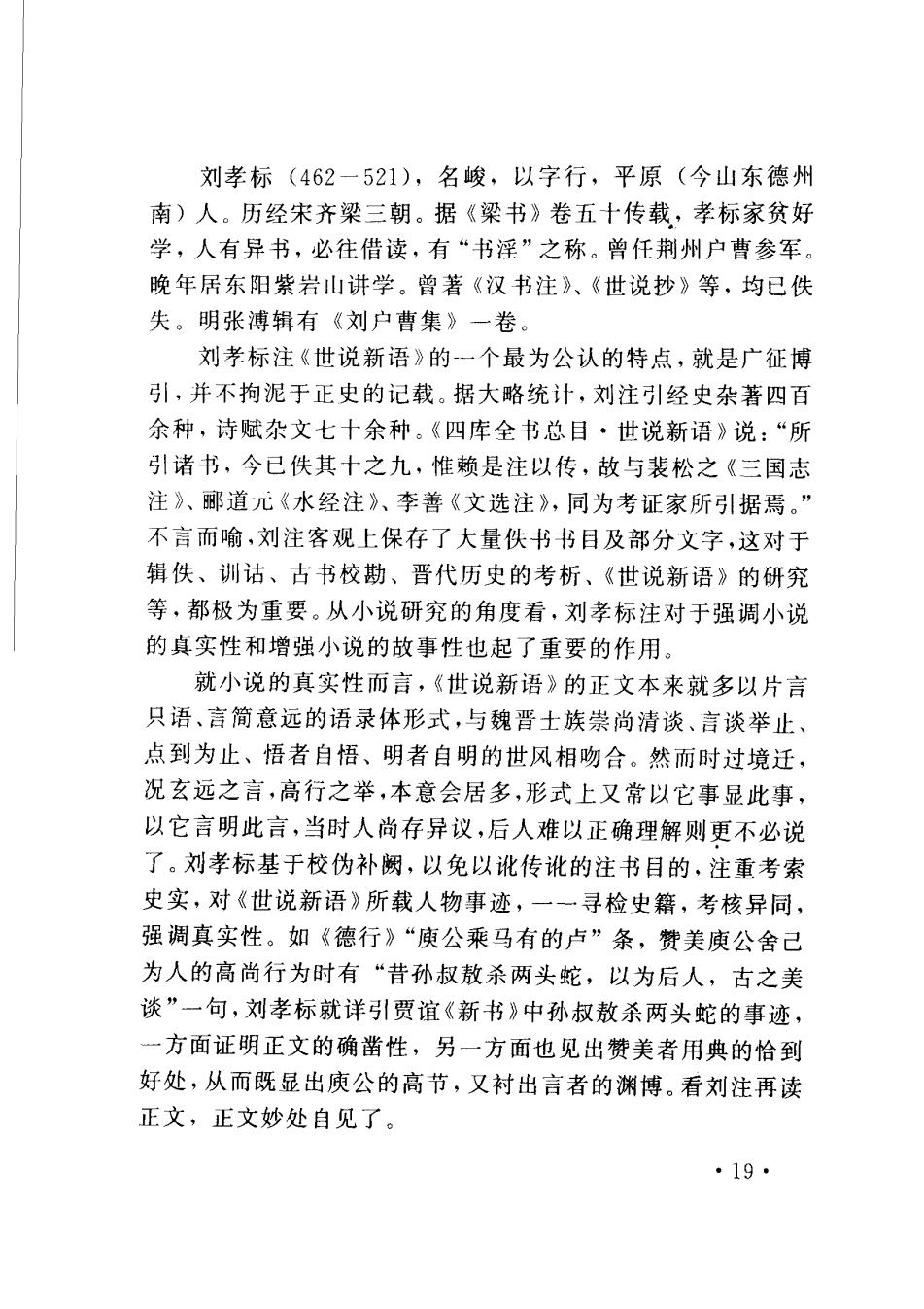
刘孝标(462一521),名峻,以字行,平原(今山东德州 南)人。历经宋齐梁三朝。据《梁书》卷五十传载,孝标家贫好 学,人有异书,必往借读,有“书淫”之称。曾任荆州户曹参军。 晚年居东阳紫岩山讲学。曾著《汉书注》、《世说抄》等,均已佚 失。明张溥辑有《刘户曹集》一卷。 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的一个最为公认的特点,就是广征博 引,并不拘泥于正史的记载。据大略统计,刘注引经史杂著四百 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四库全书总目·世说新语》说:“所 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 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 不言而喻,刘注客观上保存了大量佚书书目及部分文字,这对于 辑佚、训诂、古书校勘、晋代历史的考析、《世说新语》的研究 等,都极为重要。从小说研究的角度看,刘孝标注对于强调小说 的真实性和增强小说的故事性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就小说的真实性而言,《世说新语》的正文本来就多以片言 只语、言简意远的语录体形式,与魏晋士族崇尚清淡、言谈举止、 点到为止、悟者自悟、明者自明的世风相吻合。然而时过境迁, 况玄远之言,高行之举,本意会居多,形式上又常以它事显此事, 以它言明此言,当时人尚存异议,后人难以正确理解则更不必说 了。刘孝标基于校伪补阙,以免以讹传讹的注书目的,注重考索 史实,对《世说新语》所载人物事迹,一一寻检史籍,考核异同, 强调真实性。如《德行》“庾公乘马有的卢”条,赞美庾公舍己 为人的高尚行为时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 谈”一句,刘孝标就详引贾谊《新书》中孙叔敖杀两头蛇的事迹 一方面证明正文的确凿性,另一方面也见出赞美者用典的恰到 好处,从而既显出庾公的高节,又衬出言者的渊博。看刘注再读 正文,正文妙处自见了。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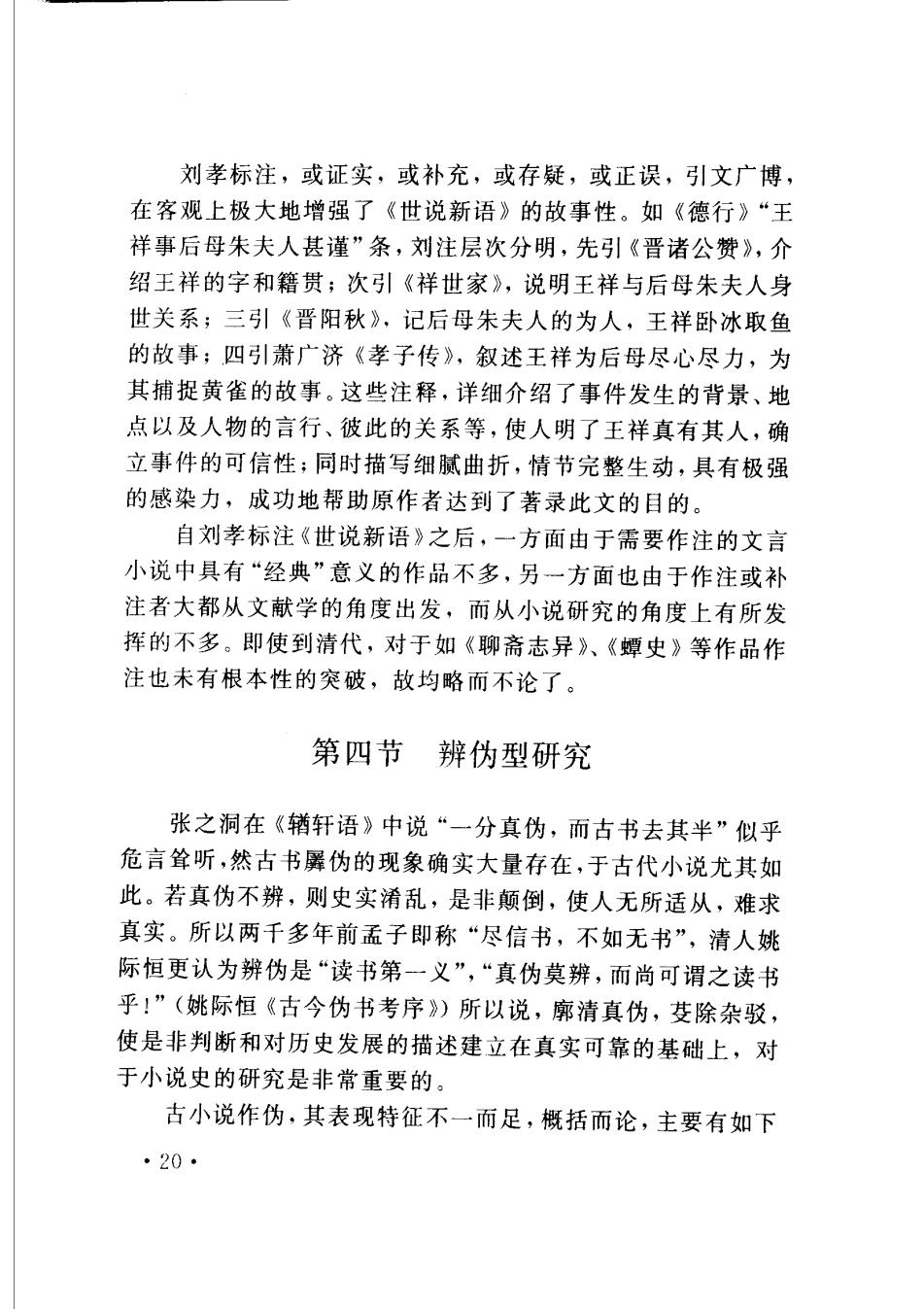
刘孝标注,或证实,或补充,或存疑,或正误,引文广博, 在客观上极大地增强了《世说新语》的故事性。如《德行》“王 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条,刘注层次分明,先引《晋诸公赞》,介 绍王祥的字和籍贯;次引《祥世家》,说明王祥与后母朱夫人身 世关系;三引《晋阳秋》,记后母朱夫人的为人,王祥卧冰取鱼 的故事;四引萧广济《孝子传》,叙述王祥为后母尽心尽力,为 其捕捉黄雀的故事。这些注释,详细介绍了事件发生的背景、地 点以及人物的言行、彼此的关系等,使人明了王祥真有其人,确 立事件的可信性:同时描写细腻曲折,情节完整生动,具有极强 的感染力,成功地帮助原作者达到了著录此文的目的。 自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之后,一方面由于需要作注的文言 小说中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不多,另一方面也由于作注或补 注者大都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而从小说研究的角度上有所发 挥的不多。即使到清代,对于如《聊斋志异》、《蟬史》等作品作 注也未有根本性的突破,故均略而不论了。 第四节辨伪型研究 张之洞在《销轩语》中说“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似乎 危言耸听,然古书羼伪的现象确实大量存在,于古代小说尤其如 此。若真伪不辨,则史实淆乱,是非颠倒,使人无所适从,难求 真实。所以两千多年前孟子即称“尽信书,不如无书”,清人姚 际恒更认为辨伪是“读书第一义”,“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 乎!”(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序》)所以说,廓清真伪,芟除杂驳, 使是非判断和对历史发展的描述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基础上,对 于小说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古小说作伪,其表现特征不一而足,概括而论,主要有如下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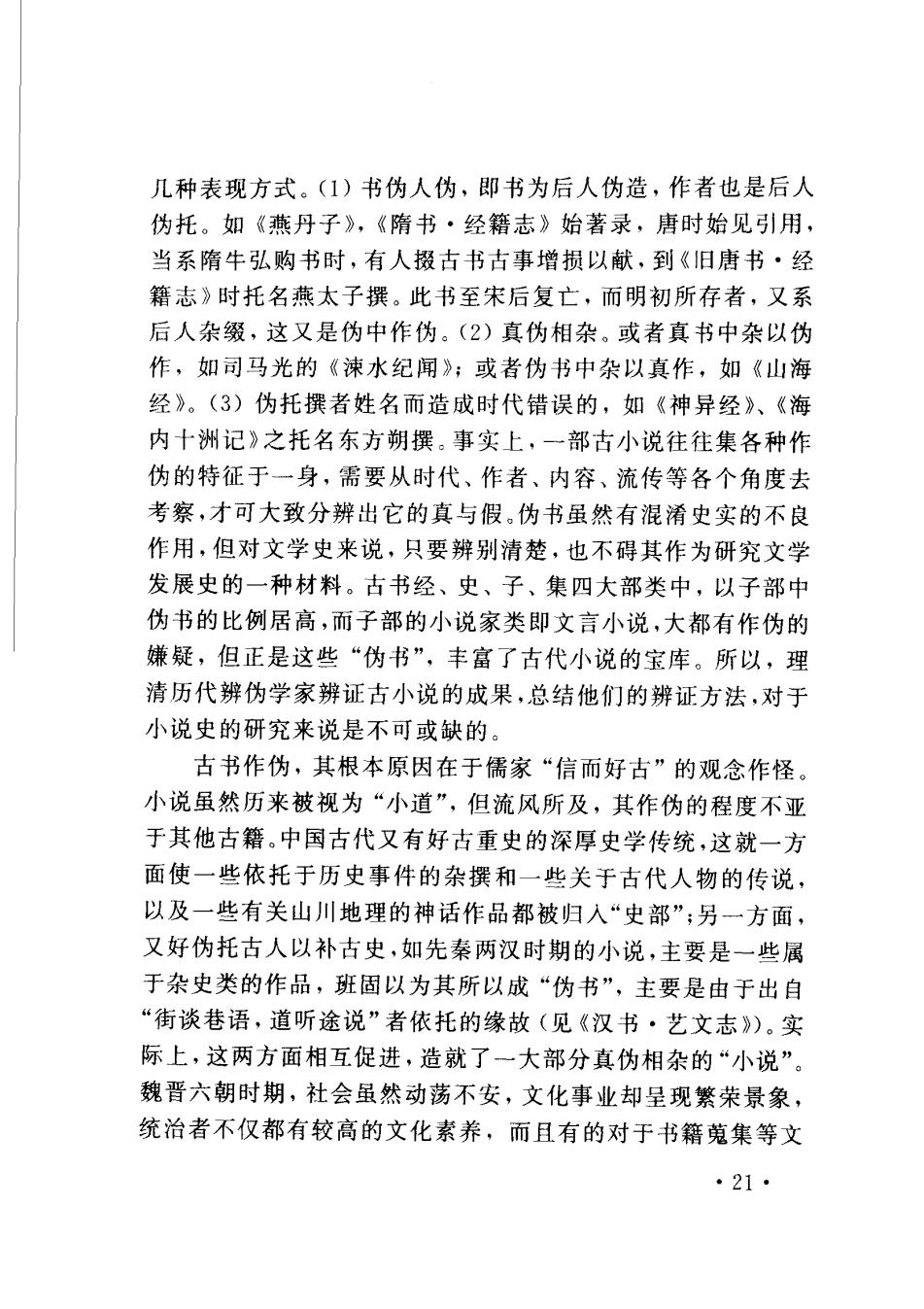
几种表现方式。(1)书伪人伪,即书为后人伪造,作者也是后人 伪托。如《燕丹子》,《隋书·经籍志》始著录,唐时始见引用, 当系隋牛弘购书时,有人掇古书古事增损以献,到《旧唐书·经 籍志》时托名燕太子撰。此书至宋后复亡,而明初所存者,又系 后人杂缀,这又是伪中作伪。(2)真伪相杂。或者真书中杂以伪 作,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或者伪书中杂以真作,如《山海 经》。(3)伪托撰者姓名而造成时代错误的,如《神异经》、《海 内十洲记》之托名东方朔撰。事实上,一部古小说往往集各种作 伪的特征于一身,需要从时代、作者、内容、流传等各个角度去 考察,才可大致分辨出它的真与假,伪书虽然有混淆史实的不良 作用,但对文学史来说,只要辨别清楚,也不碍其作为研究文学 发展史的一种材料。古书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中,以子部中 伪书的比例居高,而子部的小说家类即文言小说,大都有作伪的 嫌疑,但正是这些“伪书”,丰富了古代小说的宝库。所以,理 清历代辨伪学家辨证古小说的成果,总结他们的辨证方法,对于 小说史的研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古书作伪,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信而好古”的观念作怪 小说虽然历来被视为“小道”,但流风所及,其作伪的程度不亚 于其他古籍。中国古代又有好古重史的深厚史学传统,这就一方 面使一些依托于历史事件的杂撰和一些关于古代人物的传说, 以及一些有关山川地理的神话作品都被归入“史部”;另一方面, 又好伪托古人以补古史,如先秦两汉时期的小说,主要是一些属 于杂史类的作品,班固以为其所以成“伪书”,主要是由于出自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依托的缘故(见《汉书·艺文志》)。实 际上,这两方面相互促进,造就了一大部分真伪相杂的“小说” 魏晋六朝时期,社会虽然动荡不安,文化事业却呈现繁荣景象, 统治者不仅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有的对于书籍蒐集等文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