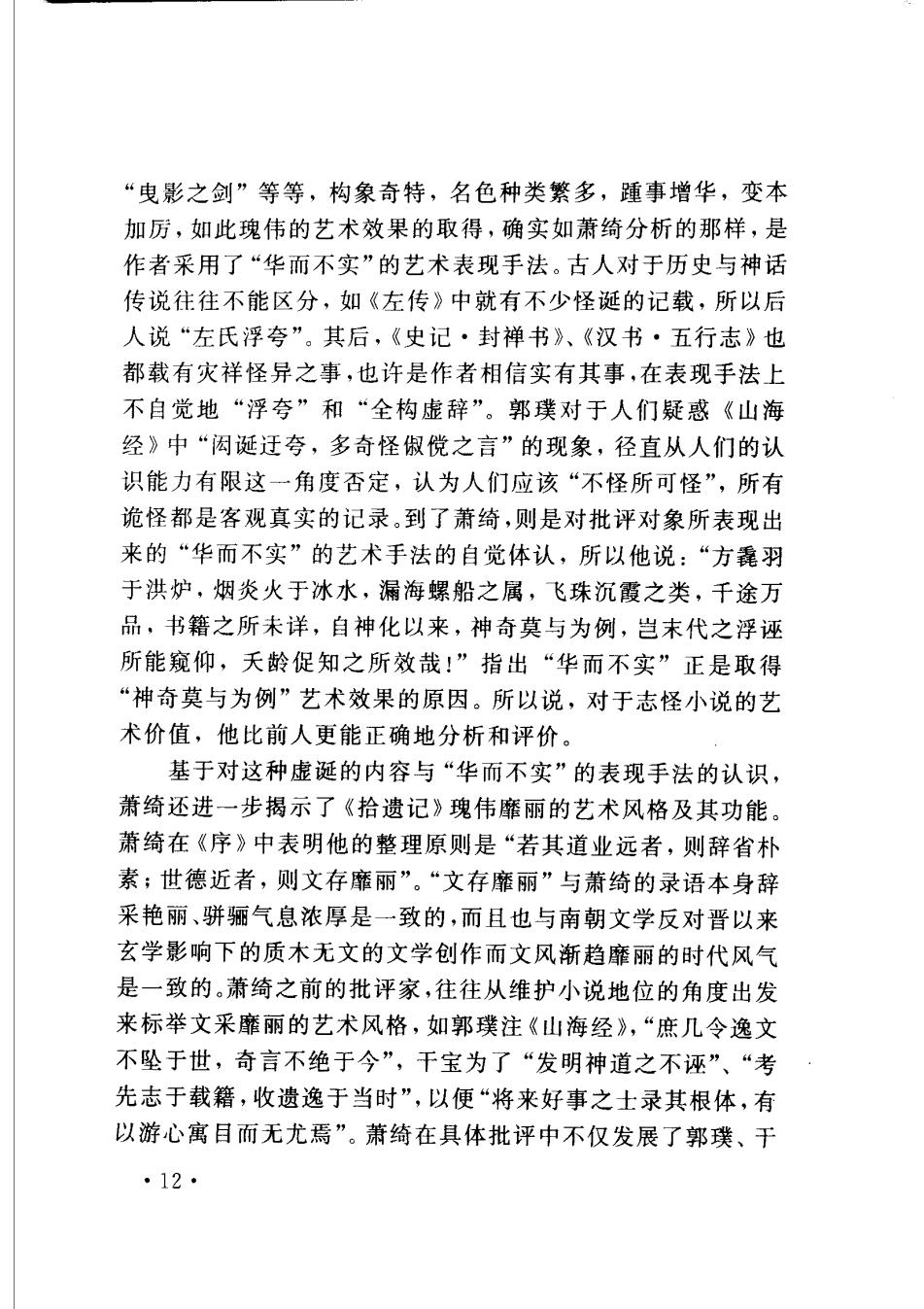
“曳影之剑”等等,构象奇特,名色种类繁多,踵事增华,变本 加厉,如此瑰伟的艺术效果的取得,确实如萧绮分析的那样,是 作者采用了“华而不实”的艺术表现手法。古人对于历史与神话 传说往往不能区分,如《左传》中就有不少怪诞的记载,所以后 人说“左氏浮夸”。其后,《史记·封禅书》、《汉书·五行志》也 都载有灾祥怪异之事,也许是作者相信实有其事,在表现手法上 不自觉地“浮夸”和“全构虚辞”。郭璞对于人们疑惑《山海 经》中“闳诞迂夸,多奇怪佩傥之言”的现象,径直从人们的认 识能力有限这一角度否定,认为人们应该“不怪所可怪”,所有 诡怪都是客观真实的记录。到了萧绮,则是对批评对象所表现出 来的“华而不实”的艺术手法的自觉体认,所以他说:“方毳羽 于洪炉,烟炎火于冰水,漏海螺船之属,飞珠沉霞之类,千途万 品,书籍之所未详,自神化以来,神奇莫与为例,岂末代之浮诬 所能窥仰,天龄促知之所效哉!”指出“华而不实”正是取得 “神奇莫与为例”艺术效果的原因。所以说,对于志怪小说的艺 术价值,他比前人更能正确地分析和评价。 基于对这种虚诞的内容与“华而不实”的表现手法的认识, 萧绮还进一步揭示了《拾遗记》瑰伟靡丽的艺术风格及其功能。 萧绮在《序》中表明他的整理原则是“若其道业远者,则辞省朴 素;世德近者,则文存靡丽”。“文存靡丽”与萧绮的录语本身辞 采艳丽、骈骊气息浓厚是一致的,而且也与南朝文学反对晋以来 玄学影响下的质木无文的文学创作而文风渐趋靡丽的时代风气 是一致的。萧绮之前的批评家,往往从维护小说地位的角度出发 来标举文采靡丽的艺术风格,如郭璞注《山海经》,“庶几令逸文 不坠于世,奇言不绝于今”,干宝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考 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以便“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 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萧绮在具体批评中不仅发展了郭璞、干 ·12·

宝的这一理论,而且对靡丽的文采有了进一步的自觉体认。例如 卷六《前汉下》:“(汉)灵帝初平三年,游于西园,起裸游馆千 间,采绿苔而被阶,引渠水以绕砌,周流澄澈。乘船以游漾,使 宫人乘之,选玉色轻体者,以执篙楫,摇漾于渠中.又秦《招 商》之歌,以来凉气也。歌曰:‘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 夜舒,惟日不足乐有余,清丝流管歌玉凫,千年万岁喜难逾。’渠 中植莲,大如盖,长一丈,南国所献;其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 莲丛生、名日夜舒荷’:亦云月出则舒也,故日‘望舒荷’。”王 嘉往往借“十不一真”的一点点历史线索铺彩错金,敷衍成文, 这正是志怪小说的艺术风格。萧绮在录语中赞赏道:“历览群经, 披求方册,未若斯之宏丽矣。”认为群经方册也没有这样宏丽的 描写,“宏丽”成为取舍的首要标准,无须步趋史家其文直、不 虚美的文风。又如卷一《少吴》载“少吴.母日皇娥,处璇宫 而夜织,或称桴木而昼游,经历穷桑沧茫之浦。时有神童,容貌 绝俗,称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际,与皇娥燕戏,奏 女更娟之乐,游漾忘归。.帝子与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为表, 结薰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帝子与皇娥并坐,抚桐 峰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日:‘天清地旷浩茫茫,万象回薄化无 方。浛天荡荡望沧沧,乘枰轻漾著日傍。当其何所至穷桑,心知 和乐悦未央。’.白帝子答歌:‘四维八埏眇难极,驱光逐影穷 水域。璇宫夜静当轩织。桐峰文梓千寻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 歌流畅乐难极,沧湄海浦来栖息。’”王嘉从历史传说出发,铺陈 成情节婉曲、辞采斐然的故事;在环境的铺叙和气氛的烘托等方 面,极尽铺排描写之能事,将青年男女的热恋场景描绘成了秀丽 飘渺的仙境。因为远离了经典的记载,被后来的封建学者斥为 “上诬古圣”,萧绮却认识到了“其广异宏丽之靡”的风格而加以 弘扬。而且他还指出,“广异宏丽”的志怪小说以其诡奇的内容 ·13

和靡丽的风格,可以使读者博闻其事,在“见奇”骇怪中得到审 美享受。如卷三“越谋灭吴”条录日:“观越之灭吴,屈柔之礼 尽焉,荐非世之绝姬,收历代之神宝,斯皆迹殊而事同矣。博识 君子,验斯言焉。”另外如“神奇莫与为例”(卷四录语),“见奇 而悦,万世之瑰伟也”(卷六录语)等评论,都在力图提示作品 的这种艺术风格及其给读者的审美享受。 基于对经史观念影响下的小说理论的突破和具体的分析批 评,萧绮对志怪小说的地位也有比较进步的认识。他力图为志怪 小说的存在争一席地位,不仅认为小说所载尽管与经史有异,但 作为“记其殊别”也可存在,而且他能从靡丽的艺术风格和“华 而不实”的艺术手法的分析批评中揭示小说的价值。正如卷一末 录语指出:“考传闻于前古,求佥言于中世,而教道参差,祥德 递起,指明群说,能无仿佛!精灵冥昧,至圣所不语,安以浅末, 贬其有无者哉!.茫茫遐迩,渺渺流文,百家迂阔,各尚斯异, 非守文于一说者矣。”不固守圣道,不强求有无,不守文于一说 这种为志怪小说伸张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这也使他成为同时 代较有眼光的小说批评家和研究家。 从批评方式而言,萧绮的“录”是在小说研究中继承、发展 了汉代以来的目录学和以序(流行于史学领域内的诸如《史记》 每篇纪传后的“太史公日”、《汉书》每传后的“传赞”等,大都 以轩轾历史人物、阐发作者的感慨为旨,与经学研究中的“序' 大致相同)、注为主要批评方式的基础上创建的。但它比“序”更 为细致而没有“注”那样琐碎,使小说得到了进一步深人研究。 也给批评家们研讨作品、建立理论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和方便。从 此,“录”这种批评方式在古代小说批评史上不绝如缕地发展着。 唐五代时期的孙光宪在笔记小说集《北梦琐言》中每篇后的“葆 光子日”,赵宋刘斧在文言小说集《青琐高议》每篇后的“议 ·14·

日”(即“高议”),赵宋逶心子编辑的志怪小说集《分门古今类 事》每篇后的简短议论,都是与萧绮的“录”这种批评方式一脉 相承的。到了明清时期,“录”这种批评方式发展演变成章回小 说的“回评”,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批评 形式领域蔚成大国,使中国小说研究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所以 说,萧绮的“录”作为“回评”的滥觞,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 评点这一研究形态的建立中,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节注释型研究 古人将研究对象中的字词障碍、难解句法、名物史实、写作 背景等予以点明和解释,一般称作“注”。“注者,著也。言为之 解说,使其著也。”(孔颖达《毛诗正义》)顾炎武在《日知录· 十三经注疏》中说,古人或称“注”为“传”、“笺”、“解” “学”等。后来人们相沿用的“故”、“训”、“训故”、“解故”、 “训纂”、“说义”、“章句”等名目,意义也相近。另有一种旨在 疏通注文的文字称作“疏”、“疏义”、“义疏”、“正义”等等。其 “注释”之名,始于隋代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书证》篇。颜氏 所说的“注释”,即指后魏刘芳所撰的《毛诗笺义证》对《毛 诗》的解释。今一般即用此通俗易懂的“注释”或“注解”来统 称这类特殊的工作;而假如将“注释”或“注解”作名词用的话, 则就是指这类解释性的文字。 注释并不是一种纯技术性的工作,它也是一种建筑在研究 基础上的富有创造性的劳动。然中国古代的一部注释史,主要是 经学史。千百年来使多少学者皓首所穷的主要是一些“经典”和 史、子、集部中的经典性著作,而对大量属于“小道”之类的小 说是并不重视的。历史上有注的小说只是有数的几部。在唐宋以 ·15

前,较有代表性的小说注本要数郭璞注《山海经》和刘孝标注 《世说新语》了。 《山海经》本是一部“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的作品, 被称为“古今语怪之祖”,大约成书于先秦时代。晋郭璞将其整 理为十八卷本加以注释,使之得以较为完整地流传后世。郭璞 (276一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东晋初为著作 郎,后任王敦记室参军,为王敦所杀。他学识渊博,善诗赋,曾 注有《尔雅》、《楚辞》、《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其《山海 经》注、在小说研究中颇有代表性。他整理研究《山海经》的主 要观点见于《注山海经叙》中。在这篇序文里,他从研究主体的 认识着手,根据史家实录的精神,充分肯定了《山海经》的幻奇 特点。他认为《山海经》所描写的内容,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本 身并无“异”与“不异”之分。所谓“怪”、“异”,在根本上是 决定于研究主体的认识。所谓“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 所不可怪,则未始有可怪也”。这种观点,指导着他对《山海 经》的整个注释工作。如其对《海内西经》所载“贰负之臣日 危”一节言及汉宣帝于上郡石室中得一人时注道:“论者多以为 是其尸象,非真体也。意者以灵怪变化,论难以理测。物禀异气, 出于自然,不可以常运推,不可以近数揆”一语,正是对研究和 审美主体认识的要求,同《叙》中所讲的道理是一致的。 为了强调《山海经》中的“怪异”的真实性,郭璞的注释就 不仅仅是疏通字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记载内容的补充、说 明和论证,具有以下两种特色: 一、利用客观的事实,对《山海经》的内容进行补充说明。 如《中山经》中所载共水中多“鸣石”一条,郭注又作增补云: “晋永康元年,襄阳郡上鸣石。似玉,色青。撞之声闻七八里。今 零陵泉陵县永正乡有鸣石二所,其一状如鼓,俗因名为石鼓,即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