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静志居诗话》中记述梁辰鱼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传奇家曲 别本,弋阳子弟可以改调歌之,惟《浣纱》不能。”在这段话里,可 以看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除《浣纱》外,大量的昆山等腔的传奇剧 本,弋阳腔都可以采集来上演,所用的办法就是“改调歌之”。后来 的事实,是《浣纱记》也被改调而歌了。从事这种改调歌之的人是 “弋阳子弟”,即艺人自己。“改调歌之”,从声腔来说是把原系昆 山腔或其他声腔剧种的剧本改用自己的弋阳腔来上演。在有了“加 滚”的办法以后,更可以加入曲文丰富原作的内容并加以通俗化。从 个曲调来说,则是指同样一支曲牌,弋阳腔艺人在演唱时,却根据 自己的语言特点及演唱风格把它加以变化了,这就使得一首同名的曲 牌到了弋阳腔里就变了样子,别有一番风格面貌。这后一种情况,在 当时海盐、余姚、昆山诸腔中也是存在的,如果没有这种区别,也就 不会有各种不同声腔的存在。只是由于这三腔都用吴浙音,语言音调 相近,所以曲调的变化、风格的差异就不如此显著,相比之下,弋阳 腔善于改调而歌的特点就更加突出了。弋阳腔的这种特点,正是南戏 “随口令” “顺口可歌”的民间戏曲艺术特征的维续和发展。二、 “错用乡语”。《客座赘语》曾把弋阳腔与海盐腔加以对照,说: 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土客喜闻之;海盐多用官话,两京人用 之。”明确指出弋阳腔“错用乡语”这样一种在演唱方面的特点。七 阳腔在演出活动中随着流传地区的不同,常杂用各地的方言土语,这 种情况尽管在上层社会的观众看来不免失之鄙俚,却为一般中下层观 众所普遍欢迎。反之,正因为观众喜闻乐见,也就会继续促进这种特 点的保持和发扬。艺人在演唱中“错用乡语”,有利于它每到一地, 很快就能与当地语言结合起来,而语言上的变化也就会促使音乐上的 变化。因此,当弋阳腔在民间广为流传以后,更使它易于在某些地区 生根,演变为当地的声腔剧种。三、弋阳腔还具有“向无曲谱,只沿 土俗”(清·李调元《剧话》)的特点,这说明它在流传中并无固定 的曲谱规范,更不像昆山腔那样格律谨严,纯粹是民间口头创作出来 的土腔土调,弋阳腔艺人在演唱中有很大的创作上的灵活性,并可以 加以即兴的自由发挥。这一特点,不仅有助于与各地语言的结合,而 且对吸收、融合各地的民间音乐,如民歌等,促成声腔的地方化,形 421

成新的地方声腔剧种,同样起很大的作用。以上三个方面,在弋阳腔 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并不是各自孤立地存在着,而是彼此相通互为 影响的。它们反映了弋阳腔具有强烈的适应性,而这种适应性却正好 说明它是植根于农民、手工业工人以及广大中下层观众中的声腔剧 种,是依据他们的要求、欣赏习惯而变迁的。由弋阳腔发展变化而来 的青阳、徽州、四平等腔,一直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在民间保持着旺 盛的生命力,对清中叶“花部”的勃兴有着直接的影响。 与此相反,另一个支派京腔,却走上了衰落的道路。它的情况, 我们在下编结合地方戏的兴起再来叙述。 DG 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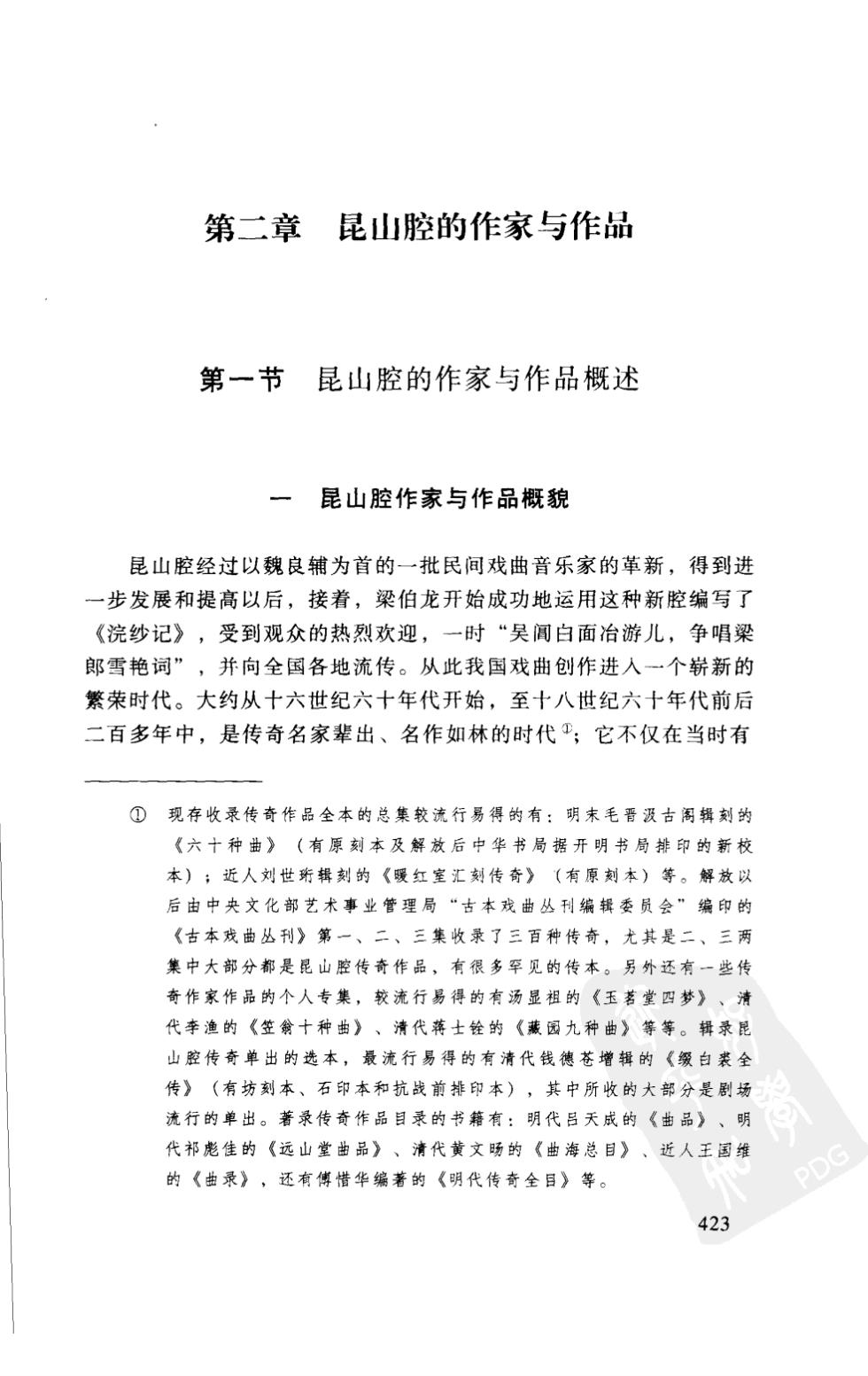
第二章昆山腔的作家与作品 第一节昆山腔的作家与作品概述 一昆山腔作家与作品概貌 昆山腔经过以魏良辅为首的一批民间戏曲音乐家的革新,得到进 步发展和提高以后,接着,梁伯龙开始成功地运用这种新腔编写了 《浣纱记》,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一时“吴间白面冶游儿,争唱梁 郎雪艳词”,并向全国各地流传。从此我国戏曲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 繁荣时代。大约从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至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前后 二百多年中,是传奇名家辈出、名作如林的时代;它不仅在当时有 ①现存收录传奇作品全本的总集较流行易得的有:明未毛香没古阁辑刻的 《六十种曲》(有原刻本及解放后中华书局据开明书局排印的新校 本);近人刘世珩辑刻的《暖红室汇刻传奇》(有原刺本)等。解救以 后由中央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古本我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印的 《古本戏曲丛刊》第一、二、三集收录了三百种传奇,尤其是二、三两 集中大部分都是昆山腔传奇作品,有很多罕见的传本。另外还有一些传 奇作家作品的个人专集,较流行易得的有汤显祖的《玉若堂四梦》、清 代李渔的《笠翁十种曲》、清代蒋士能的《装园九种曲》等等。辑录昆 山腔传奇单出的选本,最流行易得的有清代钱德苍增辑的《领白表全 传》(有坊刻本、石印本和抗战前排印本),共中所收的大部分是副场 流行的单出。著录传奇作品目柔的书箱有:明代吕天成的《曲品》、明 代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清代黄文肠的《曲海总目》、近人王国维 的《曲录》,还有傅惜华编著的《明代传奇全目》等。 423

广泛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今天的戏曲都有直接的、深厚的巨大影响。 新的昆山腔传奇的创作,是和宋元以来南戏传奇一脉相承的。 方面,新兴的昆山腔传奇创作不可能不给予其他南戏以重大影响,而 其他南戏传奇和昆山腔传奇可以互相改调而歌;另一方面,在昆山腔 改革前后,正统的北杂剧已经日益衰微,而许多传奇作家往往又兼作 日益“南曲化”的、甚至是完全用昆山腔写作的杂剧,因此,关于其 他非弋阳腔系统的南戏传奇和明清杂剧④,都将在这一节中环绕昆山 腔的创作情况一并加以叙述。 昆山腔革新以前的明初传奇创作情况,由于资料很少,现在很难 全面了解。根据成书于嘉靖后期的《金瓶梅词话》记述,当时作为南 戏“正宗”的海盐腔演出剧目有《刘智远红袍记》、《玉环记》、 《四节记》等。从题材来看,前两个当是改编的民间传统剧目;写文 人学士杜甫等人风流故事的《四节记》则该是士大夫(或沈采)之 作。当时民间作家(包括下层文人)和土大夫之作是并行于歌台舞 榭的。在这一时期中,有姓名和作品可考的传奇作家主要有以下两 类人: 一类是仅知其姓氏籍贯和作品,但其年代和生平事迹都难以稽考 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多取材于古来的传统剧目或民间故事,民间风格 较浓,语言较为通俗、质朴,适宜于场上搬演,作品中的某些折子, 一直保留到今天的昆曲等剧种中。他们当是属于正德、嘉靖以前的文 人或民间艺术家,其中如: 李日华,吴县人,生平不详(和万历时著《紫桃轩杂缀》的嘉兴 ①据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一书和《清代杂剧全目》藕的初步统计:明 代杂剧约有五百二十种,有剧本流传的有一百八十余种(创作于元、明 之际,由明代内廷教坊演出的大批无名氏杂剧,时代难于考核,还没有 统计在内);清代杂剧的数字更是鹿大,约达一千三百种,现在能看到 剧本的有四百五十余种(属于杂制体栽,在清代官廷演出的开场、团场 承应戏和庆典、月令承应戏,还没有计算进去)。其中明代的重要作 品,多见干《盛明杂剧》初、二集;明末清初的重要作品见《杂剧三 集》(以上均有中国戏副出版社影印本)。清人杂剧的重要作品,多见 于郑叛锋编印的《清人杂剧》初集及二集。 424

李日华不是一个人),著有《南西厢记》。这部传奇虽然因多割裂王 实甫《北西厢》的原词,以致在明代多招物议,但是,明代以来南戏 场上搬演的《西厢记》,实际上也只有这部作品。清人戏曲选本如 《纳书楹曲谱》、《缀白裘》、《审音鉴古录》,以及近人编选的 《集成曲谱》、《六也曲谱》、《昆曲大全》中所收的《西厢记》零 折,全从此本出。其中《跳墙》、《寄柬》、《佳期》、《拷红》等 一直是昆曲的保留剧目,由六(贴)旦应工的这几出戏在唱腔上有高 度的成就。 王济(?一1540),字伯禹,号雨舟,浙江乌程(湖州)人,作 有以吕布与貂婵为题材的《连环记》。其中《起布》、《议剑》、 《问探》、《拜月》、《小宴》、《大宴》、《梳妆》、《掷戟》等 折,至今昆曲仍能演出;京戏和一些地方戏也都有改编本。 沈采,字练川,江苏嘉定人,编有写韩信故事的《千金记》。其 中《起霸》、《鸿门》、《追信》、《别姬》、《埋伏》也都是昆曲 的保留剧目,并且是京戏等剧种据以改编、传唱不衰的折子。 苏复之,里居生平不详,著有《金印记》。内容写苏秦刻苦读 书,终于六国封相的故事。因为它对士不得志时的世态炎凉有一定程 度的揭露,最后又以旧时代一般人所艳羡的衣锦还乡结束,很能迎合 观众,在昆曲及弋阳腔系统的地方戏中(或改名为《黄金印》、《六 国封相》等等)是个极为流行的剧目。 陈罴斋,字里生平不详,著有《跃鲤记》。故事原本《后汉书· 烈女传》,写姜诗之妻庞三娘奉姑至孝的故事。其中对封建家庭中的 婆媳矛盾有一定程度的揭露,因此流传很广,几乎成为各种古老声腔 剧种都有改编本的一个戏。其中《芦林相会》(即《芦林辩非》)至 今仍是昆曲(以及弋阳腔系统)的保留剧目。 沈鲸,字涅川,浙江平湖人,作有《双珠记》、《鲛绡记》。前 者写唐王楫与妻郭氏、子九龄、妹慧姬一家悲欢离合的故事;后者写 魏从道为子必简结姻于沈必贵之女琼英的故事,因其中有赠鲛绡帕的 关目,故名。《缀白裘》、《醉怡情》、《六也曲谱》等书中分别收 有两剧的一些单折。 姚茂良,字静山,浙江武康人,作有《张巡许远双忠记》,写唐 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