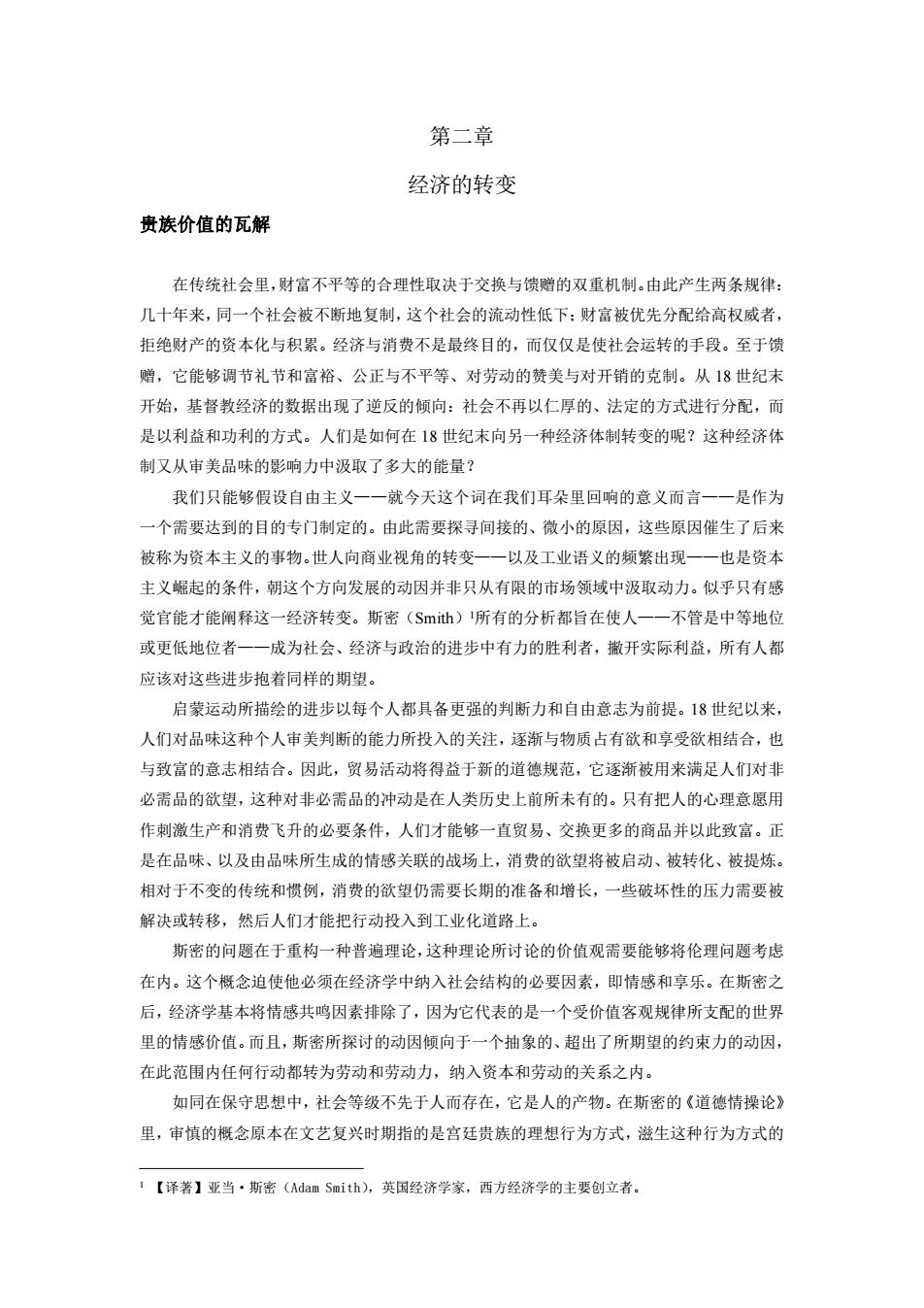
第二章 经济的转变 贵族价值的瓦解 在传统社会里,财富不平等的合理性取决于交换与馈赠的双重机制。由此产生两条规律: 几十年来,同一个社会被不断地复制,这个社会的流动性低下:财富被优先分配给高权威者, 拒绝财产的资本化与积累。经济与消费不是最终目的,而仅仅是使社会运转的手段。至于馈 赠,它能够调节礼节和富裕、公正与不平等、对劳动的赞美与对开销的克制。从18世纪末 开始,基督教经济的数据出现了逆反的倾向:社会不再以仁厚的、法定的方式进行分配,而 是以利益和功利的方式。人们是如何在18世纪末向另一种经济体制转变的呢?这种经济体 制又从审美品味的影响力中汲取了多大的能量? 我们只能够假设自由主义一一就今天这个词在我们耳朵里回响的意义而言一一是作为 一个需要达到的目的专门制定的。由此需要探寻间接的、微小的原因,这些原因催生了后来 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事物。世人向商业视角的转变一一以及工业语义的频繁出现一一也是资本 主义崛起的条件,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动因并非只从有限的市场领域中汲取动力。似乎只有感 觉官能才能阐释这一经济转变。斯密(Smith)1所有的分析都旨在使人一一不管是中等地位 或更低地位者一一成为社会、经济与政治的进步中有力的胜利者,撇开实际利益,所有人都 应该对这些进步抱着同样的期望。 启蒙运动所描绘的进步以每个人都具备更强的判断力和自由意志为前提。18世纪以来, 人们对品味这种个人审美判断的能力所投入的关注,逐渐与物质占有欲和享受欲相结合,也 与致富的意志相结合。因此,贸易活动将得益于新的道德规范,它逐渐被用来满足人们对非 必需品的欲望,这种对非必需品的冲动是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只有把人的心理意愿用 作刺激生产和消费飞升的必要条件,人们才能够一直贸易、交换更多的商品并以此致富。正 是在品味、以及由品味所生成的情感关联的战场上,消费的欲望将被启动、被转化、被提炼。 相对于不变的传统和惯例,消费的欲望仍需要长期的准备和增长,一些破坏性的压力需要被 解决或转移,然后人们才能把行动投入到工业化道路上。 斯密的问题在于重构一种普遍理论,这种理论所讨论的价值观需要能够将伦理问题考虑 在内。这个概念迫使他必须在经济学中纳入社会结构的必要因素,即情感和享乐。在斯密之 后,经济学基本将情感共鸣因素排除了,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受价值客观规律所支配的世界 里的情感价值。而且,斯密所探讨的动因倾向于一个抽象的、超出了所期望的约束力的动因, 在此范围内任何行动都转为劳动和劳动力,纳入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之内。 如同在保守思想中,社会等级不先于人而存在,它是人的产物。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里,审慎的概念原本在文艺复兴时期指的是宫廷贵族的理想行为方式,滋生这种行为方式的 !【译著】亚当·斯密(Adam Smith),英国经济学家,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
第二章 经济的转变 贵族价值的瓦解 在传统社会里,财富不平等的合理性取决于交换与馈赠的双重机制。由此产生两条规律: 几十年来,同一个社会被不断地复制,这个社会的流动性低下;财富被优先分配给高权威者, 拒绝财产的资本化与积累。经济与消费不是最终目的,而仅仅是使社会运转的手段。至于馈 赠,它能够调节礼节和富裕、公正与不平等、对劳动的赞美与对开销的克制。从 18 世纪末 开始,基督教经济的数据出现了逆反的倾向:社会不再以仁厚的、法定的方式进行分配,而 是以利益和功利的方式。人们是如何在 18 世纪末向另一种经济体制转变的呢?这种经济体 制又从审美品味的影响力中汲取了多大的能量? 我们只能够假设自由主义——就今天这个词在我们耳朵里回响的意义而言——是作为 一个需要达到的目的专门制定的。由此需要探寻间接的、微小的原因,这些原因催生了后来 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事物。世人向商业视角的转变——以及工业语义的频繁出现——也是资本 主义崛起的条件,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动因并非只从有限的市场领域中汲取动力。似乎只有感 觉官能才能阐释这一经济转变。斯密(Smith)1所有的分析都旨在使人——不管是中等地位 或更低地位者——成为社会、经济与政治的进步中有力的胜利者,撇开实际利益,所有人都 应该对这些进步抱着同样的期望。 启蒙运动所描绘的进步以每个人都具备更强的判断力和自由意志为前提。18 世纪以来, 人们对品味这种个人审美判断的能力所投入的关注,逐渐与物质占有欲和享受欲相结合,也 与致富的意志相结合。因此,贸易活动将得益于新的道德规范,它逐渐被用来满足人们对非 必需品的欲望,这种对非必需品的冲动是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只有把人的心理意愿用 作刺激生产和消费飞升的必要条件,人们才能够一直贸易、交换更多的商品并以此致富。正 是在品味、以及由品味所生成的情感关联的战场上,消费的欲望将被启动、被转化、被提炼。 相对于不变的传统和惯例,消费的欲望仍需要长期的准备和增长,一些破坏性的压力需要被 解决或转移,然后人们才能把行动投入到工业化道路上。 斯密的问题在于重构一种普遍理论,这种理论所讨论的价值观需要能够将伦理问题考虑 在内。这个概念迫使他必须在经济学中纳入社会结构的必要因素,即情感和享乐。在斯密之 后,经济学基本将情感共鸣因素排除了,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受价值客观规律所支配的世界 里的情感价值。而且,斯密所探讨的动因倾向于一个抽象的、超出了所期望的约束力的动因, 在此范围内任何行动都转为劳动和劳动力,纳入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之内。 如同在保守思想中,社会等级不先于人而存在,它是人的产物。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里,审慎的概念原本在文艺复兴时期指的是宫廷贵族的理想行为方式,滋生这种行为方式的 1 【译著】亚当·斯密(Adam Smith),英国经济学家,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

是前浪漫主义者根据内部权威的愿望强加在个人身上的改变,而现在审慎的能力已经扩展到 了大多数人身上。只有预先修改所有目前造成障碍的那些继承自贵族制度的价值观,才能够 改革道德风俗并使人们适应新的生活习惯。18世纪将废除贵族制度中对“审慎”的定义, 即在宫廷中通过才华来展现自我的艺术,取而代之的是适用于任何人的观点,无论他属于哪 个社会阶层。斯密斯让人们重新思考君主制中审美品味的原则。这实际上是一个决定性的举 动,因为它相当于从构成经济建筑心理基础的欣赏能力开始,由下至上彻底颠覆了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人与物质财富的关系以及欲望与物品之间的联系。1 在宫廷社会里,具备审慎的艺术,要求高贵的阶级出身(这个阶级拒绝一切职业和商业 的活动)、对取悦和引诱的艺术的热爱、以及适应各种场合的高超意识。斯密所描述的“审 慎人士”与格拉西昂的“宫廷人士”和伏尔泰的“上流人士”己经不太相似。他突出了另一 类人,对于这一类人而言,审慎的艺术有利于工业和物质利益。为了建立工作模式和发展工 业活动,宫廷贵族的技艺被有条不紊的逐渐废除。如果说审慎在过去所指的是“对自我的控 制”,即宫廷贵族己经熟悉的技能,那它从此有了新的含义。从此这门技能的目标在于排除 风险,使一个商业企业的成功机会最优化。人类命运的发展建立在谋算和对情绪与情感的掌 控的基础上。2 在斯密看来,真正的审慎位于幸福的水平线上,关乎私利,而私利本身则在一定程度上 与经济繁荣相互关联。与必须拒绝一切职业以维持其作为自由人的地位的宫廷人士不同,审 慎人士必须拥有一个职业,“他们的活动需要技术和勤勉,他们的一切开销需要节制、甚至 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节省。”3他们的任何动机都不符合宫廷人士的精神自由,宫廷贵族认为劳 动职业是卑贱的,因此完全拒绝职业。与其承受算账的精神折磨、抑制其开销,贵族们即使 破产,也必须要自我表现。对于贵族身份最重要的荣耀,产生于一个以拒绝为了商业规则放 弃精神的高贵价值为特征的社会群体。而劳动与享有权之间紧密的价值联系,不承认这种荣 耀。 希望致富的人通常与高贵的出身相去甚远,相反的,他们往往具备较低阶级者的所有特 点:生活的朴素促使他们改善自己的条件。地位卑微的人最能够回应工业社会发展的期待, 因为他们的野心使他们必然能够摆脱高阶级者闲散的习惯。而那些怀有经济野心的贵族则更 应该早早摆脱根深蒂固的旧习俗,与他原本的社会阶级分道扬镳。 斯密如此表述他所捍卫的生活方式,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坚决放弃现有的安逸和愉 悦,是为了期盼虽然遥远、但会更持久的更大的安逸和愉悦。”4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这最 后一种品质与贵族阶级必须隐藏自己情感的态度仍然相似,这使他们能够为了纯粹社会化的 目的而谋算行动。从此,重要的是在某些场合下、在平衡与压力的潮起潮落之间,能够自我 I在《宫廷社会》一书中,埃里亚斯(Norbert Elias)全面评估了这一举动:“自我表现的义务的放宽,即 使对于工业文明社会中最富最强的精英,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体现在家居装潢、衣着、以及更普遍的对 艺术品的品味的发展上。” 2 Adam SMITH,《道德情操论》(Theorie des sentiments moraux),卷四,章2,页263. 3同上,页296 4同上,页298
是前浪漫主义者根据内部权威的愿望强加在个人身上的改变,而现在审慎的能力已经扩展到 了大多数人身上。只有预先修改所有目前造成障碍的那些继承自贵族制度的价值观,才能够 改革道德风俗并使人们适应新的生活习惯。18 世纪将废除贵族制度中对“审慎”的定义, 即在宫廷中通过才华来展现自我的艺术,取而代之的是适用于任何人的观点,无论他属于哪 个社会阶层。斯密斯让人们重新思考君主制中审美品味的原则。这实际上是一个决定性的举 动,因为它相当于从构成经济建筑心理基础的欣赏能力开始,由下至上彻底颠覆了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人与物质财富的关系以及欲望与物品之间的联系。1 在宫廷社会里,具备审慎的艺术,要求高贵的阶级出身(这个阶级拒绝一切职业和商业 的活动)、对取悦和引诱的艺术的热爱、以及适应各种场合的高超意识。斯密所描述的“审 慎人士”与格拉西昂的“宫廷人士”和伏尔泰的“上流人士”已经不太相似。他突出了另一 类人,对于这一类人而言,审慎的艺术有利于工业和物质利益。为了建立工作模式和发展工 业活动,宫廷贵族的技艺被有条不紊的逐渐废除。如果说审慎在过去所指的是“对自我的控 制”,即宫廷贵族已经熟悉的技能,那它从此有了新的含义。从此这门技能的目标在于排除 风险,使一个商业企业的成功机会最优化。人类命运的发展建立在谋算和对情绪与情感的掌 控的基础上。2 在斯密看来,真正的审慎位于幸福的水平线上,关乎私利,而私利本身则在一定程度上 与经济繁荣相互关联。与必须拒绝一切职业以维持其作为自由人的地位的宫廷人士不同,审 慎人士必须拥有一个职业,“他们的活动需要技术和勤勉,他们的一切开销需要节制、甚至 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节省。”3他们的任何动机都不符合宫廷人士的精神自由,宫廷贵族认为劳 动职业是卑贱的,因此完全拒绝职业。与其承受算账的精神折磨、抑制其开销,贵族们即使 破产,也必须要自我表现。对于贵族身份最重要的荣耀,产生于一个以拒绝为了商业规则放 弃精神的高贵价值为特征的社会群体。而劳动与享有权之间紧密的价值联系,不承认这种荣 耀。 希望致富的人通常与高贵的出身相去甚远,相反的,他们往往具备较低阶级者的所有特 点:生活的朴素促使他们改善自己的条件。地位卑微的人最能够回应工业社会发展的期待, 因为他们的野心使他们必然能够摆脱高阶级者闲散的习惯。而那些怀有经济野心的贵族则更 应该早早摆脱根深蒂固的旧习俗,与他原本的社会阶级分道扬镳。 斯密如此表述他所捍卫的生活方式,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坚决放弃现有的安逸和愉 悦,是为了期盼虽然遥远、但会更持久的更大的安逸和愉悦。”4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这最 后一种品质与贵族阶级必须隐藏自己情感的态度仍然相似,这使他们能够为了纯粹社会化的 目的而谋算行动。从此,重要的是在某些场合下、在平衡与压力的潮起潮落之间,能够自我 1 在《宫廷社会》一书中,埃里亚斯(Norbert Elias)全面评估了这一举动:“自我表现的义务的放宽,即 使对于工业文明社会中最富最强的精英,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体现在家居装潢、衣着、以及更普遍的对 艺术品的品味的发展上。” 2 Adam SMITH, 《道德情操论》(Théorie des sentiments moraux),卷四,章 2,页 263. 3 同上,页 296. 4 同上,页 298

控制。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有一个共同点,相比起即时的情感反应,他们都更重视长期计划。 然而,为了获取收益所运用的谋算原本就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对于资产阶级而言,需要考 虑计算金钱的得失。对于贵族阶级而言,则是一个通过声誉和地位获得社会影响力的机遇问 题。在改革者看来,资产阶级依靠自己的能力,过与之相衬的生活,从不做力不能及的事情: 而贵族阶级,他们通过名誉和好品味消费,这种消费注定是超出其经济能力的。缩减开销至 适应一般生活需求即可,反而能够提高致富的机会。1审慎,要求任何人都必须为了利己目 的投入到节约的计划中,这是必须预想的、无法逃避的纪律,它要求人们“花足够的时间慎 重冷静地思考可能的后果。”2 斯密从不探讨宫廷贵族,但是当他贬低宫廷里那种没有内涵的矫揉造作作风时,贵族就 成了他攻击的对象。因此,所谓“审慎人士”指的是那些真正明白自己声称明白的事物的人, 而不是仅仅劝服别人自己明白的人。必须把真诚放在比社交生活的斑斓色彩更重要的位置 上。从这方面来看,勤勉的资产阶级的特征完全符合“审慎人士”的优点: 并且,尽管他们的才华可能不总是非常出众,却总是完全真实的。他们绝不会试图用伪君子的狡猾计 谋来欺骗你,也不会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老学究作态,更不会像一个既肤浅又冒失的假装者那样妄下断言。 他从不浮夸、即使是自己真正具备的能力也不对人炫耀。他的谈吐是简洁谦逊的,而且他们反感所有虚伪 的事物,即那些其他人常常用以获取荣耀与名声的虚假手段。3 一个人的名声应该与他的成就有关,应该因其真正的价值被衡量和欣赏。与阴谋诡计、 狡猾骗术、浮夸作风、出格言行和口是心非相反,对真实性的要求将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新的 交往方式,从此优雅意味着真诚。剥夺宫廷贵族的信誉,是为了使社交关系变得更清晰更透 明、不再是仅仅于某个小圈子内曖味不清,因为过去宫廷贵族由于各种条条框框和行为规矩, 不得不屈服于各种引诱的计谋,而创造出虚伪的社交关系。真实性是一种需求,其结果将是 增强交流的流动性一一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物品、思想、贸易的交换,它排除了 贵族社交关系中复杂的等级分层,也摒弃了让人摸不清方向的关于外表的游戏。将对方遭遇 欺诈的风险最小化、或者减少因贵族的虚假作风所造成的理解错误,这无疑是在交易中一种 担保自己的承诺、使人安心、并增加信誉的手段。 对于贵族而言,以其身份,奢侈品与其说是享乐的源泉,毋宁说是社会等级的指标。然 而对于资产阶级而言,自我整理,例如对自己内在的调整意味着财富积累与幸福感、工作与 认可、劳动与奖赏之间的平衡,期待着在私人领域里能够享受到他值得享受的满足感。于是, 从对于贵族身份而言必不可少的象征性补偿,过渡到了资产阶级对满足感的要求,这种满足 感表现为所有吸金者对物质享受的喜好。没有什么比对真实性的要求更能描述这一特征的 !“一个在其收入范围内生活的人,必然对其状况感到满足:他的结余不断积少成多,他每天都在进步。” 同上 2同上 3同上,页27
控制。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有一个共同点,相比起即时的情感反应,他们都更重视长期计划。 然而,为了获取收益所运用的谋算原本就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对于资产阶级而言,需要考 虑计算金钱的得失。对于贵族阶级而言,则是一个通过声誉和地位获得社会影响力的机遇问 题。在改革者看来,资产阶级依靠自己的能力,过与之相衬的生活,从不做力不能及的事情; 而贵族阶级,他们通过名誉和好品味消费,这种消费注定是超出其经济能力的。缩减开销至 适应一般生活需求即可,反而能够提高致富的机会。1审慎,要求任何人都必须为了利己目 的投入到节约的计划中,这是必须预想的、无法逃避的纪律,它要求人们“花足够的时间慎 重冷静地思考可能的后果。”2 斯密从不探讨宫廷贵族,但是当他贬低宫廷里那种没有内涵的矫揉造作作风时,贵族就 成了他攻击的对象。因此,所谓“审慎人士”指的是那些真正明白自己声称明白的事物的人, 而不是仅仅劝服别人自己明白的人。必须把真诚放在比社交生活的斑斓色彩更重要的位置 上。从这方面来看,勤勉的资产阶级的特征完全符合“审慎人士”的优点: 并且,尽管他们的才华可能不总是非常出众,却总是完全真实的。他们绝不会试图用伪君子的狡猾计 谋来欺骗你,也不会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老学究作态,更不会像一个既肤浅又冒失的假装者那样妄下断言。 他从不浮夸、即使是自己真正具备的能力也不对人炫耀。他的谈吐是简洁谦逊的,而且他们反感所有虚伪 的事物,即那些其他人常常用以获取荣耀与名声的虚假手段。3 一个人的名声应该与他的成就有关,应该因其真正的价值被衡量和欣赏。与阴谋诡计、 狡猾骗术、浮夸作风、出格言行和口是心非相反,对真实性的要求将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新的 交往方式,从此优雅意味着真诚。剥夺宫廷贵族的信誉,是为了使社交关系变得更清晰更透 明、不再是仅仅于某个小圈子内暧昧不清,因为过去宫廷贵族由于各种条条框框和行为规矩, 不得不屈服于各种引诱的计谋,而创造出虚伪的社交关系。真实性是一种需求,其结果将是 增强交流的流动性——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物品、思想、贸易的交换,它排除了 贵族社交关系中复杂的等级分层,也摒弃了让人摸不清方向的关于外表的游戏。将对方遭遇 欺诈的风险最小化、或者减少因贵族的虚假作风所造成的理解错误,这无疑是在交易中一种 担保自己的承诺、使人安心、并增加信誉的手段。 对于贵族而言,以其身份,奢侈品与其说是享乐的源泉,毋宁说是社会等级的指标。然 而对于资产阶级而言,自我整理,例如对自己内在的调整意味着财富积累与幸福感、工作与 认可、劳动与奖赏之间的平衡,期待着在私人领域里能够享受到他值得享受的满足感。于是, 从对于贵族身份而言必不可少的象征性补偿,过渡到了资产阶级对满足感的要求,这种满足 感表现为所有吸金者对物质享受的喜好。没有什么比对真实性的要求更能描述这一特征的 1 “一个在其收入范围内生活的人,必然对其状况感到满足:他的结余不断积少成多,他每天都在进步。” 同上. 2 同上. 3 同上,页 2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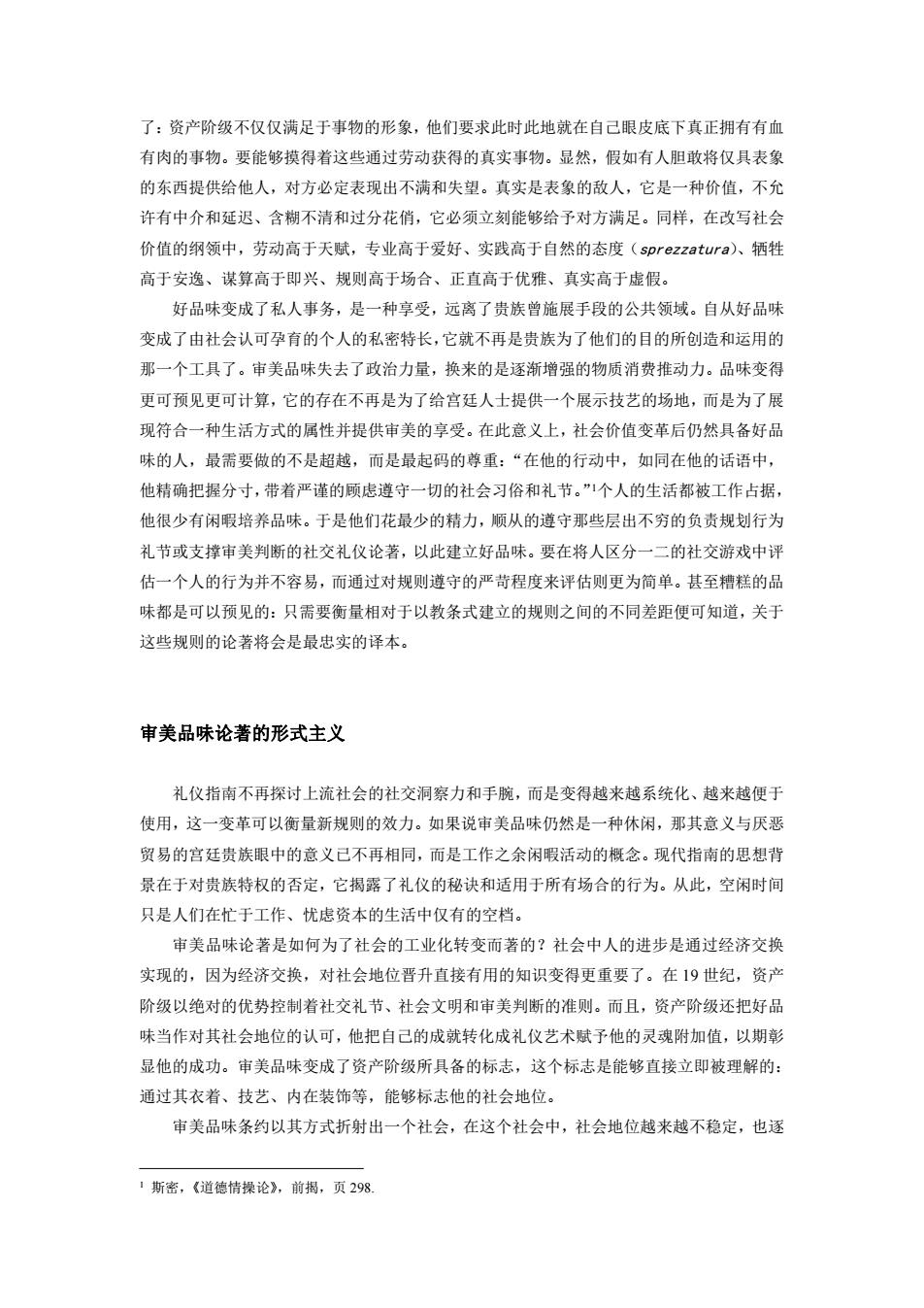
了:资产阶级不仅仅满足于事物的形象,他们要求此时此地就在自己眼皮底下真正拥有有血 有肉的事物。要能够摸得着这些通过劳动获得的真实事物。显然,假如有人胆敢将仅具表象 的东西提供给他人,对方必定表现出不满和失望。真实是表象的敌人,它是一种价值,不允 许有中介和延迟、含糊不清和过分花俏,它必须立刻能够给予对方满足。同样,在改写社会 价值的纲领中,劳动高于天赋,专业高于爱好、实践高于自然的态度(sprezzatura)、牺牲 高于安逸、谋算高于即兴、规则高于场合、正直高于优雅、真实高于虚假。 好品味变成了私人事务,是一种享受,远离了贵族曾施展手段的公共领域。自从好品味 变成了由社会认可孕育的个人的私密特长,它就不再是贵族为了他们的目的所创造和运用的 那一个工具了。审美品味失去了政治力量,换来的是逐渐增强的物质消费推动力。品味变得 更可预见更可计算,它的存在不再是为了给宫廷人士提供一个展示技艺的场地,而是为了展 现符合一种生活方式的属性并提供审美的享受。在此意义上,社会价值变革后仍然具备好品 味的人,最需要做的不是超越,而是最起码的尊重:“在他的行动中,如同在他的话语中, 他精确把握分寸,带着严谨的顾虑遵守一切的社会习俗和礼节。”1个人的生活都被工作占据, 他很少有闲暇培养品味。于是他们花最少的精力,顺从的遵守那些层出不穷的负责规划行为 礼节或支撑审美判断的社交礼仪论著,以此建立好品味。要在将人区分一二的社交游戏中评 估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容易,而通过对规则遵守的严苛程度来评估则更为简单。甚至糟糕的品 味都是可以预见的:只需要衡量相对于以教条式建立的规则之间的不同差距便可知道,关于 这些规则的论著将会是最忠实的译本。 审美品味论著的形式主义 礼仪指南不再探讨上流社会的社交洞察力和手腕,而是变得越来越系统化、越来越便于 使用,这一变革可以衡量新规则的效力。如果说审美品味仍然是一种休闲,那其意义与厌恶 贸易的宫廷贵族眼中的意义己不再相同,而是工作之余闲暇活动的概念。现代指南的思想背 景在于对贵族特权的否定,它揭露了礼仪的秘诀和适用于所有场合的行为。从此,空闲时间 只是人们在忙于工作、忧虑资本的生活中仅有的空档。 审美品味论著是如何为了社会的工业化转变而著的?社会中人的进步是通过经济交换 实现的,因为经济交换,对社会地位晋升直接有用的知识变得更重要了。在19世纪,资产 阶级以绝对的优势控制着社交礼节、社会文明和审美判断的准则。而且,资产阶级还把好品 味当作对其社会地位的认可,他把自己的成就转化成礼仪艺术赋予他的灵魂附加值,以期彰 显他的成功。审美品味变成了资产阶级所具备的标志,这个标志是能够直接立即被理解的: 通过其衣着、技艺、内在装饰等,能够标志他的社会地位。 审美品味条约以其方式折射出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社会地位越来越不稳定,也逐 1斯密,《道德情操论》,前揭,页298
了:资产阶级不仅仅满足于事物的形象,他们要求此时此地就在自己眼皮底下真正拥有有血 有肉的事物。要能够摸得着这些通过劳动获得的真实事物。显然,假如有人胆敢将仅具表象 的东西提供给他人,对方必定表现出不满和失望。真实是表象的敌人,它是一种价值,不允 许有中介和延迟、含糊不清和过分花俏,它必须立刻能够给予对方满足。同样,在改写社会 价值的纲领中,劳动高于天赋,专业高于爱好、实践高于自然的态度(sprezzatura)、牺牲 高于安逸、谋算高于即兴、规则高于场合、正直高于优雅、真实高于虚假。 好品味变成了私人事务,是一种享受,远离了贵族曾施展手段的公共领域。自从好品味 变成了由社会认可孕育的个人的私密特长,它就不再是贵族为了他们的目的所创造和运用的 那一个工具了。审美品味失去了政治力量,换来的是逐渐增强的物质消费推动力。品味变得 更可预见更可计算,它的存在不再是为了给宫廷人士提供一个展示技艺的场地,而是为了展 现符合一种生活方式的属性并提供审美的享受。在此意义上,社会价值变革后仍然具备好品 味的人,最需要做的不是超越,而是最起码的尊重:“在他的行动中,如同在他的话语中, 他精确把握分寸,带着严谨的顾虑遵守一切的社会习俗和礼节。”1个人的生活都被工作占据, 他很少有闲暇培养品味。于是他们花最少的精力,顺从的遵守那些层出不穷的负责规划行为 礼节或支撑审美判断的社交礼仪论著,以此建立好品味。要在将人区分一二的社交游戏中评 估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容易,而通过对规则遵守的严苛程度来评估则更为简单。甚至糟糕的品 味都是可以预见的:只需要衡量相对于以教条式建立的规则之间的不同差距便可知道,关于 这些规则的论著将会是最忠实的译本。 审美品味论著的形式主义 礼仪指南不再探讨上流社会的社交洞察力和手腕,而是变得越来越系统化、越来越便于 使用,这一变革可以衡量新规则的效力。如果说审美品味仍然是一种休闲,那其意义与厌恶 贸易的宫廷贵族眼中的意义已不再相同,而是工作之余闲暇活动的概念。现代指南的思想背 景在于对贵族特权的否定,它揭露了礼仪的秘诀和适用于所有场合的行为。从此,空闲时间 只是人们在忙于工作、忧虑资本的生活中仅有的空档。 审美品味论著是如何为了社会的工业化转变而著的?社会中人的进步是通过经济交换 实现的,因为经济交换,对社会地位晋升直接有用的知识变得更重要了。在 19 世纪,资产 阶级以绝对的优势控制着社交礼节、社会文明和审美判断的准则。而且,资产阶级还把好品 味当作对其社会地位的认可,他把自己的成就转化成礼仪艺术赋予他的灵魂附加值,以期彰 显他的成功。审美品味变成了资产阶级所具备的标志,这个标志是能够直接立即被理解的: 通过其衣着、技艺、内在装饰等,能够标志他的社会地位。 审美品味条约以其方式折射出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社会地位越来越不稳定,也逐 1 斯密,《道德情操论》,前揭,页 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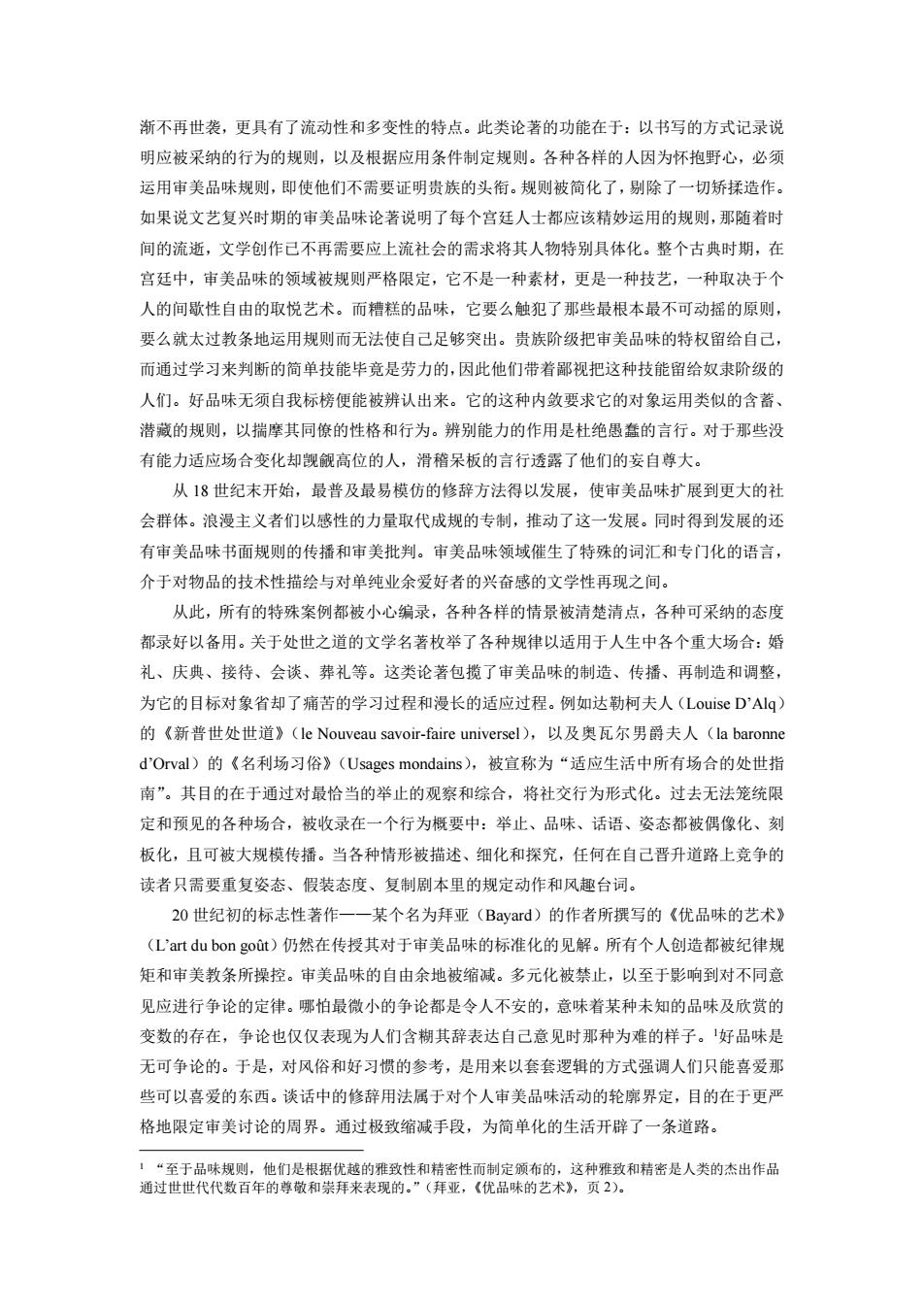
渐不再世袭,更具有了流动性和多变性的特点。此类论著的功能在于:以书写的方式记录说 明应被采纳的行为的规则,以及根据应用条件制定规则。各种各样的人因为怀抱野心,必须 运用审美品味规则,即使他们不需要证明贵族的头衔。规则被简化了,剔除了一切矫揉造作。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品味论著说明了每个宫廷人士都应该精妙运用的规则,那随着时 间的流逝,文学创作己不再需要应上流社会的需求将其人物特别具体化。整个古典时期,在 宫廷中,审美品味的领域被规则严格限定,它不是一种素材,更是一种技艺,一种取决于个 人的间歇性自由的取悦艺术。而糟糕的品味,它要么触犯了那些最根本最不可动摇的原则, 要么就太过教条地运用规则而无法使自己足够突出。贵族阶级把审美品味的特权留给自己, 而通过学习来判断的简单技能毕竟是劳力的,因此他们带着鄙视把这种技能留给奴隶阶级的 人们。好品味无须自我标榜便能被辨认出来。它的这种内敛要求它的对象运用类似的含蓄、 潜藏的规则,以揣摩其同僚的性格和行为。辨别能力的作用是杜绝愚蠢的言行。对于那些没 有能力适应场合变化却觊觎高位的人,滑稽呆板的言行透露了他们的妄自尊大。 从18世纪末开始,最普及最易模仿的修辞方法得以发展,使审美品味扩展到更大的社 会群体。浪漫主义者们以感性的力量取代成规的专制,推动了这一发展。同时得到发展的还 有审美品味书面规则的传播和审美批判。审美品味领域催生了特殊的词汇和专门化的语言, 介于对物品的技术性描绘与对单纯业余爱好者的兴奋感的文学性再现之间。 从此,所有的特殊案例都被小心编录,各种各样的情景被清楚清点,各种可采纳的态度 都录好以备用。关于处世之道的文学名著枚举了各种规律以适用于人生中各个重大场合:婚 礼、庆典、接待、会谈、葬礼等。这类论著包揽了审美品味的制造、传播、再制造和调整, 为它的目标对象省却了痛苦的学习过程和漫长的适应过程。例如达勒柯夫人(Louise D'Alq) 的《新普世处世道》(le Nouveau savoir-faire universel),以及奥瓦尔男爵夫人(la baronne d'Orval)的《名利场习俗》(Usages mondains),被宣称为“适应生活中所有场合的处世指 南”。其目的在于通过对最恰当的举止的观察和综合,将社交行为形式化。过去无法笼统限 定和预见的各种场合,被收录在一个行为概要中:举止、品味、话语、姿态都被偶像化、刻 板化,且可被大规模传播。当各种情形被描述、细化和探究,任何在自己晋升道路上竞争的 读者只需要重复姿态、假装态度、复制剧本里的规定动作和风趣台词。 20世纪初的标志性著作一一某个名为拜亚(Bayard)的作者所撰写的《优品味的艺术》 (L'art du bon gout)仍然在传授其对于审美品味的标准化的见解。所有个人创造都被纪律规 矩和审美教条所操控。审美品味的自由余地被缩减。多元化被禁止,以至于影响到对不同意 见应进行争论的定律。哪怕最微小的争论都是令人不安的,意味着某种未知的品味及欣赏的 变数的存在,争论也仅仅表现为人们含糊其辞表达自己意见时那种为难的样子。好品味是 无可争论的。于是,对风俗和好习惯的参考,是用来以套套逻辑的方式强调人们只能喜爱那 些可以喜爱的东西。谈话中的修辞用法属于对个人审美品味活动的轮廓界定,目的在于更严 格地限定审美讨论的周界。通过极致缩减手段,为简单化的生活开辟了一条道路。 !“至于品味规则,他们是根据优越的雅致性和精密性而制定颁布的,这种雅致和精密是人类的杰出作品 通过世世代代数百年的尊敬和崇拜来表现的。”(拜亚,《优品味的艺术》,页2)
渐不再世袭,更具有了流动性和多变性的特点。此类论著的功能在于:以书写的方式记录说 明应被采纳的行为的规则,以及根据应用条件制定规则。各种各样的人因为怀抱野心,必须 运用审美品味规则,即使他们不需要证明贵族的头衔。规则被简化了,剔除了一切矫揉造作。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品味论著说明了每个宫廷人士都应该精妙运用的规则,那随着时 间的流逝,文学创作已不再需要应上流社会的需求将其人物特别具体化。整个古典时期,在 宫廷中,审美品味的领域被规则严格限定,它不是一种素材,更是一种技艺,一种取决于个 人的间歇性自由的取悦艺术。而糟糕的品味,它要么触犯了那些最根本最不可动摇的原则, 要么就太过教条地运用规则而无法使自己足够突出。贵族阶级把审美品味的特权留给自己, 而通过学习来判断的简单技能毕竟是劳力的,因此他们带着鄙视把这种技能留给奴隶阶级的 人们。好品味无须自我标榜便能被辨认出来。它的这种内敛要求它的对象运用类似的含蓄、 潜藏的规则,以揣摩其同僚的性格和行为。辨别能力的作用是杜绝愚蠢的言行。对于那些没 有能力适应场合变化却觊觎高位的人,滑稽呆板的言行透露了他们的妄自尊大。 从 18 世纪末开始,最普及最易模仿的修辞方法得以发展,使审美品味扩展到更大的社 会群体。浪漫主义者们以感性的力量取代成规的专制,推动了这一发展。同时得到发展的还 有审美品味书面规则的传播和审美批判。审美品味领域催生了特殊的词汇和专门化的语言, 介于对物品的技术性描绘与对单纯业余爱好者的兴奋感的文学性再现之间。 从此,所有的特殊案例都被小心编录,各种各样的情景被清楚清点,各种可采纳的态度 都录好以备用。关于处世之道的文学名著枚举了各种规律以适用于人生中各个重大场合:婚 礼、庆典、接待、会谈、葬礼等。这类论著包揽了审美品味的制造、传播、再制造和调整, 为它的目标对象省却了痛苦的学习过程和漫长的适应过程。例如达勒柯夫人(Louise D’Alq) 的《新普世处世道》(le Nouveau savoir-faire universel),以及奥瓦尔男爵夫人(la baronne d’Orval)的《名利场习俗》(Usages mondains),被宣称为“适应生活中所有场合的处世指 南”。其目的在于通过对最恰当的举止的观察和综合,将社交行为形式化。过去无法笼统限 定和预见的各种场合,被收录在一个行为概要中:举止、品味、话语、姿态都被偶像化、刻 板化,且可被大规模传播。当各种情形被描述、细化和探究,任何在自己晋升道路上竞争的 读者只需要重复姿态、假装态度、复制剧本里的规定动作和风趣台词。 20 世纪初的标志性著作——某个名为拜亚(Bayard)的作者所撰写的《优品味的艺术》 (L’art du bon goût)仍然在传授其对于审美品味的标准化的见解。所有个人创造都被纪律规 矩和审美教条所操控。审美品味的自由余地被缩减。多元化被禁止,以至于影响到对不同意 见应进行争论的定律。哪怕最微小的争论都是令人不安的,意味着某种未知的品味及欣赏的 变数的存在,争论也仅仅表现为人们含糊其辞表达自己意见时那种为难的样子。1好品味是 无可争论的。于是,对风俗和好习惯的参考,是用来以套套逻辑的方式强调人们只能喜爱那 些可以喜爱的东西。谈话中的修辞用法属于对个人审美品味活动的轮廓界定,目的在于更严 格地限定审美讨论的周界。通过极致缩减手段,为简单化的生活开辟了一条道路。 1 “至于品味规则,他们是根据优越的雅致性和精密性而制定颁布的,这种雅致和精密是人类的杰出作品 通过世世代代数百年的尊敬和崇拜来表现的。”(拜亚,《优品味的艺术》,页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