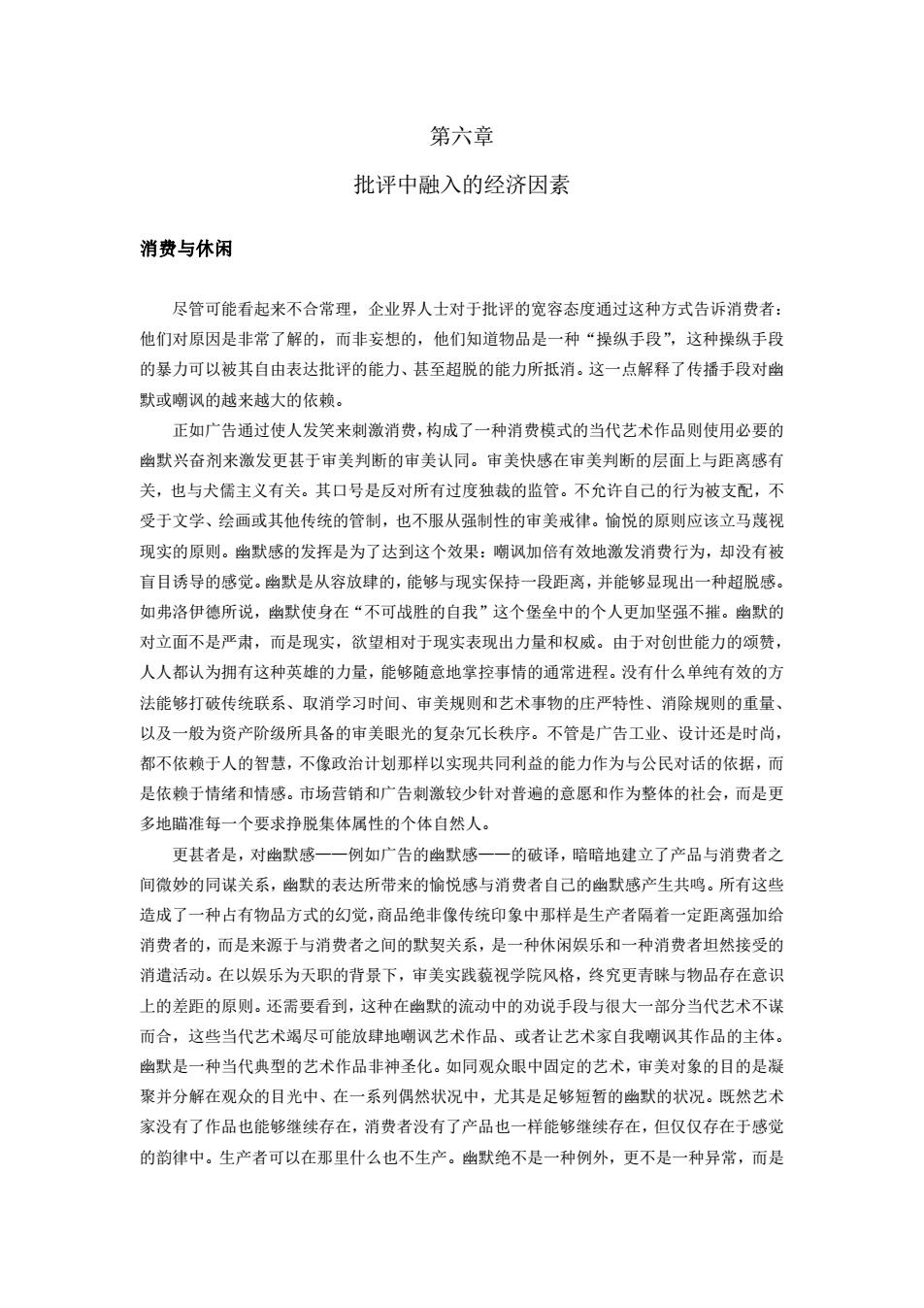
第六章 批评中融入的经济因素 消费与休闲 尽管可能看起来不合常理,企业界人士对于批评的宽容态度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消费者: 他们对原因是非常了解的,而非妄想的,他们知道物品是一种“操纵手段”,这种操纵手段 的暴力可以被其自由表达批评的能力、甚至超脱的能力所抵消。这一点解释了传播手段对幽 默或嘲讽的越来越大的依赖。 正如广告通过使人发笑来刺激消费,构成了一种消费模式的当代艺术作品则使用必要的 幽默兴奋剂来激发更甚于审美判断的审美认同。审美快感在审美判断的层面上与距离感有 关,也与犬儒主义有关。其口号是反对所有过度独裁的监管。不允许自己的行为被支配,不 受于文学、绘画或其他传统的管制,也不服从强制性的审美戒律。愉悦的原则应该立马蔑视 现实的原则。幽默感的发挥是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嘲讽加倍有效地激发消费行为,却没有被 盲目诱导的感觉。幽默是从容放肆的,能够与现实保持一段距离,并能够显现出一种超脱感。 如弗洛伊德所说,幽默使身在“不可战胜的自我”这个堡垒中的个人更加坚强不摧。幽默的 对立面不是严肃,而是现实,欲望相对于现实表现出力量和权威。由于对创世能力的颂赞, 人人都认为拥有这种英雄的力量,能够随意地掌控事情的通常进程。没有什么单纯有效的方 法能够打破传统联系、取消学习时间、审美规则和艺术事物的庄严特性、消除规则的重量、 以及一般为资产阶级所具备的审美眼光的复杂冗长秩序。不管是广告工业、设计还是时尚, 都不依赖于人的智慧,不像政治计划那样以实现共同利益的能力作为与公民对话的依据,而 是依赖于情绪和情感。市场营销和广告刺激较少针对普遍的意愿和作为整体的社会,而是更 多地瞄准每一个要求挣脱集体属性的个体自然人。 更甚者是,对幽默感一一例如广告的幽默感一一的破译,暗暗地建立了产品与消费者之 间微妙的同谋关系,幽默的表达所带来的愉悦感与消费者自己的幽默感产生共鸣。所有这些 造成了一种占有物品方式的幻觉,商品绝非像传统印象中那样是生产者隔着一定距离强加给 消费者的,而是来源于与消费者之间的默契关系,是一种休闲娱乐和一种消费者坦然接受的 消遣活动。在以娱乐为天职的背景下,审美实践藐视学院风格,终究更青睐与物品存在意识 上的差距的原则。还需要看到,这种在幽默的流动中的劝说手段与很大一部分当代艺术不谋 而合,这些当代艺术竭尽可能放肆地嘲讽艺术作品、或者让艺术家自我嘲讽其作品的主体。 幽默是一种当代典型的艺术作品非神圣化。如同观众眼中固定的艺术,审美对象的目的是凝 聚并分解在观众的目光中、在一系列偶然状况中,尤其是足够短暂的幽默的状况。既然艺术 家没有了作品也能够继续存在,消费者没有了产品也一样能够继续存在,但仅仅存在于感觉 的韵律中。生产者可以在那里什么也不生产。幽默绝不是一种例外,更不是一种异常,而是
第六章 批评中融入的经济因素 消费与休闲 尽管可能看起来不合常理,企业界人士对于批评的宽容态度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消费者: 他们对原因是非常了解的,而非妄想的,他们知道物品是一种“操纵手段”,这种操纵手段 的暴力可以被其自由表达批评的能力、甚至超脱的能力所抵消。这一点解释了传播手段对幽 默或嘲讽的越来越大的依赖。 正如广告通过使人发笑来刺激消费,构成了一种消费模式的当代艺术作品则使用必要的 幽默兴奋剂来激发更甚于审美判断的审美认同。审美快感在审美判断的层面上与距离感有 关,也与犬儒主义有关。其口号是反对所有过度独裁的监管。不允许自己的行为被支配,不 受于文学、绘画或其他传统的管制,也不服从强制性的审美戒律。愉悦的原则应该立马蔑视 现实的原则。幽默感的发挥是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嘲讽加倍有效地激发消费行为,却没有被 盲目诱导的感觉。幽默是从容放肆的,能够与现实保持一段距离,并能够显现出一种超脱感。 如弗洛伊德所说,幽默使身在“不可战胜的自我”这个堡垒中的个人更加坚强不摧。幽默的 对立面不是严肃,而是现实,欲望相对于现实表现出力量和权威。由于对创世能力的颂赞, 人人都认为拥有这种英雄的力量,能够随意地掌控事情的通常进程。没有什么单纯有效的方 法能够打破传统联系、取消学习时间、审美规则和艺术事物的庄严特性、消除规则的重量、 以及一般为资产阶级所具备的审美眼光的复杂冗长秩序。不管是广告工业、设计还是时尚, 都不依赖于人的智慧,不像政治计划那样以实现共同利益的能力作为与公民对话的依据,而 是依赖于情绪和情感。市场营销和广告刺激较少针对普遍的意愿和作为整体的社会,而是更 多地瞄准每一个要求挣脱集体属性的个体自然人。 更甚者是,对幽默感——例如广告的幽默感——的破译,暗暗地建立了产品与消费者之 间微妙的同谋关系,幽默的表达所带来的愉悦感与消费者自己的幽默感产生共鸣。所有这些 造成了一种占有物品方式的幻觉,商品绝非像传统印象中那样是生产者隔着一定距离强加给 消费者的,而是来源于与消费者之间的默契关系,是一种休闲娱乐和一种消费者坦然接受的 消遣活动。在以娱乐为天职的背景下,审美实践藐视学院风格,终究更青睐与物品存在意识 上的差距的原则。还需要看到,这种在幽默的流动中的劝说手段与很大一部分当代艺术不谋 而合,这些当代艺术竭尽可能放肆地嘲讽艺术作品、或者让艺术家自我嘲讽其作品的主体。 幽默是一种当代典型的艺术作品非神圣化。如同观众眼中固定的艺术,审美对象的目的是凝 聚并分解在观众的目光中、在一系列偶然状况中,尤其是足够短暂的幽默的状况。既然艺术 家没有了作品也能够继续存在,消费者没有了产品也一样能够继续存在,但仅仅存在于感觉 的韵律中。生产者可以在那里什么也不生产。幽默绝不是一种例外,更不是一种异常,而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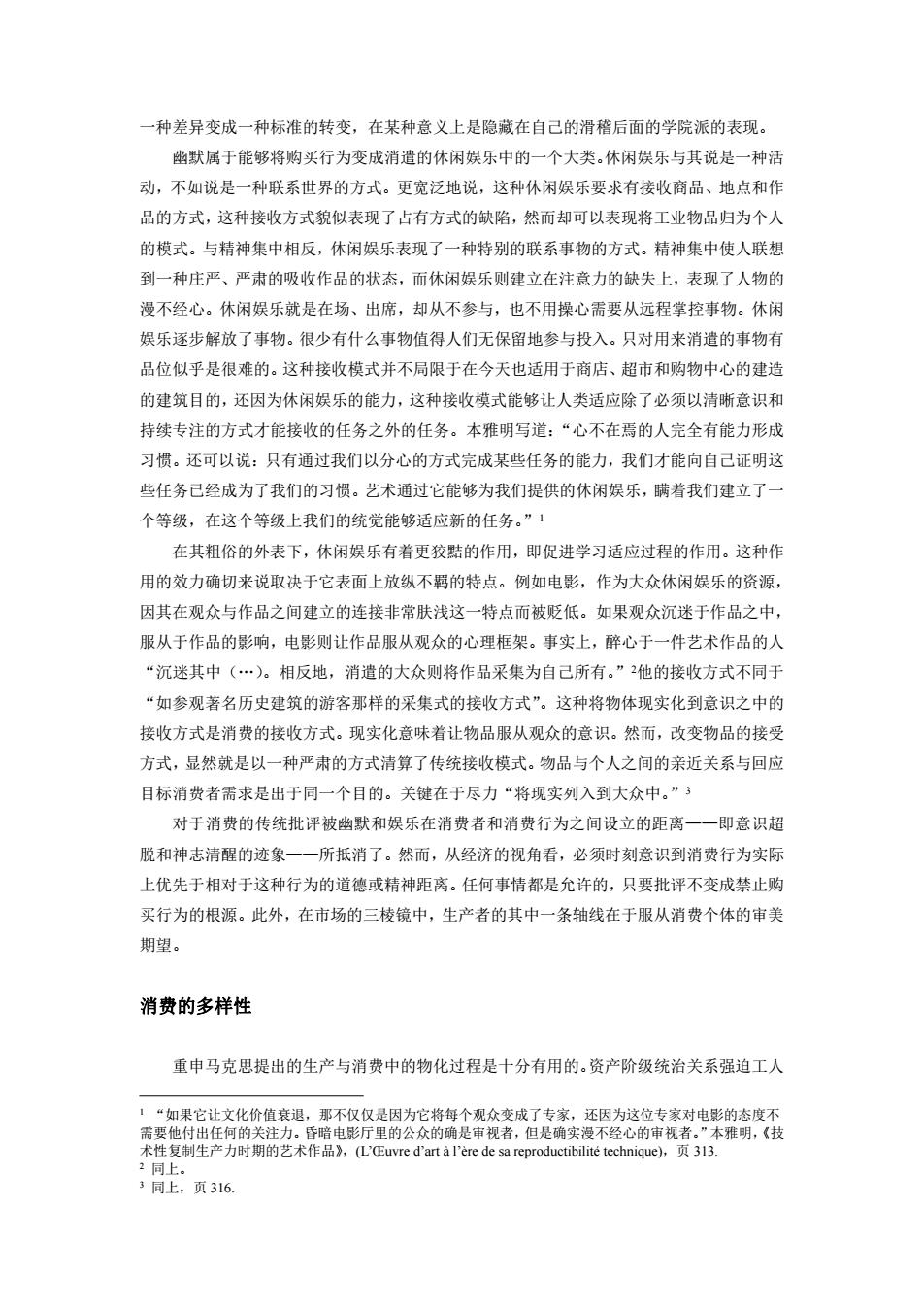
一种差异变成一种标准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是隐藏在自己的滑稽后面的学院派的表现。 幽默属于能够将购买行为变成消遣的休闲娱乐中的一个大类。休闲娱乐与其说是一种活 动,不如说是一种联系世界的方式。更宽泛地说,这种休闲娱乐要求有接收商品、地点和作 品的方式,这种接收方式貌似表现了占有方式的缺陷,然而却可以表现将工业物品归为个人 的模式。与精神集中相反,休闲娱乐表现了一种特别的联系事物的方式。精神集中使人联想 到一种庄严、严肃的吸收作品的状态,而休闲娱乐则建立在注意力的缺失上,表现了人物的 漫不经心。休闲娱乐就是在场、出席,却从不参与,也不用操心需要从远程掌控事物。休闲 娱乐逐步解放了事物。很少有什么事物值得人们无保留地参与投入。只对用来消遣的事物有 品位似乎是很难的。这种接收模式并不局限于在今天也适用于商店、超市和购物中心的建造 的建筑目的,还因为休闲娱乐的能力,这种接收模式能够让人类适应除了必须以清晰意识和 持续专注的方式才能接收的任务之外的任务。本雅明写道:“心不在焉的人完全有能力形成 习惯。还可以说:只有通过我们以分心的方式完成某些任务的能力,我们才能向自己证明这 些任务己经成为了我们的习惯。艺术通过它能够为我们提供的休闲娱乐,瞒着我们建立了一 个等级,在这个等级上我们的统觉能够适应新的任务。”1 在其粗俗的外表下,休闲娱乐有着更狡黠的作用,即促进学习适应过程的作用。这种作 用的效力确切来说取决于它表面上放纵不羁的特点。例如电影,作为大众休闲娱乐的资源, 因其在观众与作品之间建立的连接非常肤浅这一特点而被贬低。如果观众沉迷于作品之中, 服从于作品的影响,电影则让作品服从观众的心理框架。事实上,醉心于一件艺术作品的人 “沉迷其中(…)。相反地,消遣的大众则将作品采集为自己所有。”2他的接收方式不同于 “如参观著名历史建筑的游客那样的采集式的接收方式”。这种将物体现实化到意识之中的 接收方式是消费的接收方式。现实化意味着让物品服从观众的意识。然而,改变物品的接受 方式,显然就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清算了传统接收模式。物品与个人之间的亲近关系与回应 目标消费者需求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关键在于尽力“将现实列入到大众中。”3 对于消费的传统批评被幽默和娱乐在消费者和消费行为之间设立的距离一一即意识超 脱和神志清醒的迹象一一所抵消了。然而,从经济的视角看,必须时刻意识到消费行为实际 上优先于相对于这种行为的道德或精神距离。任何事情都是允许的,只要批评不变成禁止购 买行为的根源。此外,在市场的三棱镜中,生产者的其中一条轴线在于服从消费个体的审美 期望。 消费的多样性 重申马克思提出的生产与消费中的物化过程是十分有用的。资产阶级统治关系强迫工人 !“如果它让文化价值衰退,那不仅仅是因为它将每个观众变成了专家,还因为这位专家对电影的态度不 需要他付出任何的关注力。昏暗电影厅里的公众的确是审视者,但是确实漫不经心的审视者。”本雅明,《技 术性复制生产力时期的艺术作品》,(L'正uvre d'art al'ere de sa reproductibilite technique),页3l3. 2同上。 3同上,页316
一种差异变成一种标准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是隐藏在自己的滑稽后面的学院派的表现。 幽默属于能够将购买行为变成消遣的休闲娱乐中的一个大类。休闲娱乐与其说是一种活 动,不如说是一种联系世界的方式。更宽泛地说,这种休闲娱乐要求有接收商品、地点和作 品的方式,这种接收方式貌似表现了占有方式的缺陷,然而却可以表现将工业物品归为个人 的模式。与精神集中相反,休闲娱乐表现了一种特别的联系事物的方式。精神集中使人联想 到一种庄严、严肃的吸收作品的状态,而休闲娱乐则建立在注意力的缺失上,表现了人物的 漫不经心。休闲娱乐就是在场、出席,却从不参与,也不用操心需要从远程掌控事物。休闲 娱乐逐步解放了事物。很少有什么事物值得人们无保留地参与投入。只对用来消遣的事物有 品位似乎是很难的。这种接收模式并不局限于在今天也适用于商店、超市和购物中心的建造 的建筑目的,还因为休闲娱乐的能力,这种接收模式能够让人类适应除了必须以清晰意识和 持续专注的方式才能接收的任务之外的任务。本雅明写道:“心不在焉的人完全有能力形成 习惯。还可以说:只有通过我们以分心的方式完成某些任务的能力,我们才能向自己证明这 些任务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习惯。艺术通过它能够为我们提供的休闲娱乐,瞒着我们建立了一 个等级,在这个等级上我们的统觉能够适应新的任务。”1 在其粗俗的外表下,休闲娱乐有着更狡黠的作用,即促进学习适应过程的作用。这种作 用的效力确切来说取决于它表面上放纵不羁的特点。例如电影,作为大众休闲娱乐的资源, 因其在观众与作品之间建立的连接非常肤浅这一特点而被贬低。如果观众沉迷于作品之中, 服从于作品的影响,电影则让作品服从观众的心理框架。事实上,醉心于一件艺术作品的人 “沉迷其中(…)。相反地,消遣的大众则将作品采集为自己所有。”2他的接收方式不同于 “如参观著名历史建筑的游客那样的采集式的接收方式”。这种将物体现实化到意识之中的 接收方式是消费的接收方式。现实化意味着让物品服从观众的意识。然而,改变物品的接受 方式,显然就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清算了传统接收模式。物品与个人之间的亲近关系与回应 目标消费者需求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关键在于尽力“将现实列入到大众中。”3 对于消费的传统批评被幽默和娱乐在消费者和消费行为之间设立的距离——即意识超 脱和神志清醒的迹象——所抵消了。然而,从经济的视角看,必须时刻意识到消费行为实际 上优先于相对于这种行为的道德或精神距离。任何事情都是允许的,只要批评不变成禁止购 买行为的根源。此外,在市场的三棱镜中,生产者的其中一条轴线在于服从消费个体的审美 期望。 消费的多样性 重申马克思提出的生产与消费中的物化过程是十分有用的。资产阶级统治关系强迫工人 1 “如果它让文化价值衰退,那不仅仅是因为它将每个观众变成了专家,还因为这位专家对电影的态度不 需要他付出任何的关注力。昏暗电影厅里的公众的确是审视者,但是确实漫不经心的审视者。”本雅明,《技 术性复制生产力时期的艺术作品》,(L’Œuvre d’art à l’ère de sa reproductibilité technique),页 313. 2 同上。 3 同上,页 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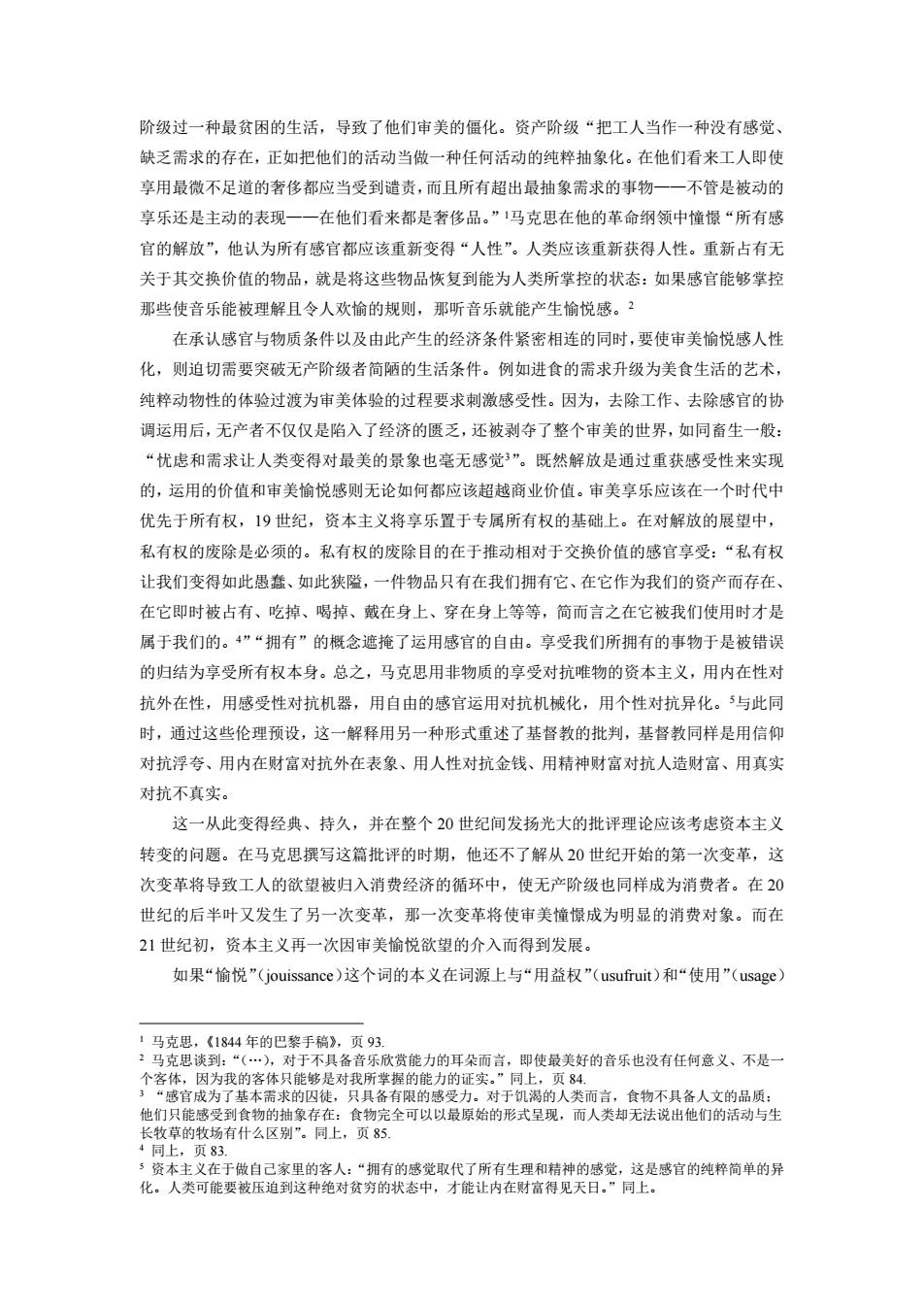
阶级过一种最贫困的生活,导致了他们审美的僵化。资产阶级“把工人当作一种没有感觉、 缺乏需求的存在,正如把他们的活动当做一种任何活动的纯粹抽象化。在他们看来工人即使 享用最微不足道的奢侈都应当受到谴责,而且所有超出最抽象需求的事物一一不管是被动的 享乐还是主动的表现一一在他们看来都是奢侈品。”1马克思在他的革命纲领中憧憬“所有感 官的解放”,他认为所有感官都应该重新变得“人性”。人类应该重新获得人性。重新占有无 关于其交换价值的物品,就是将这些物品恢复到能为人类所掌控的状态:如果感官能够掌控 那些使音乐能被理解且令人欢愉的规则,那听音乐就能产生愉悦感。2 在承认感官与物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条件紧密相连的同时,要使审美愉悦感人性 化,则迫切需要突破无产阶级者简陋的生活条件。例如进食的需求升级为美食生活的艺术, 纯粹动物性的体验过渡为审美体验的过程要求刺激感受性。因为,去除工作、去除感官的协 调运用后,无产者不仅仅是陷入了经济的匮乏,还被剥夺了整个审美的世界,如同畜生一般: “忧虑和需求让人类变得对最美的景象也毫无感觉3”。既然解放是通过重获感受性来实现 的,运用的价值和审美愉悦感则无论如何都应该超越商业价值。审美享乐应该在一个时代中 优先于所有权,19世纪,资本主义将享乐置于专属所有权的基础上。在对解放的展望中, 私有权的废除是必须的。私有权的废除目的在于推动相对于交换价值的感官享受:“私有权 让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如此狭隘,一件物品只有在我们拥有它、在它作为我们的资产而存在、 在它即时被占有、吃掉、喝掉、戴在身上、穿在身上等等,简而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时才是 属于我们的。4”“拥有”的概念遮掩了运用感官的自由。享受我们所拥有的事物于是被错误 的归结为享受所有权本身。总之,马克思用非物质的享受对抗唯物的资本主义,用内在性对 抗外在性,用感受性对抗机器,用自由的感官运用对抗机械化,用个性对抗异化。5与此同 时,通过这些伦理预设,这一解释用另一种形式重述了基督教的批判,基督教同样是用信仰 对抗浮夸、用内在财富对抗外在表象、用人性对抗金钱、用精神财富对抗人造财富、用真实 对抗不真实。 这一从此变得经典、持久,并在整个20世纪间发扬光大的批评理论应该考虑资本主义 转变的问题。在马克思撰写这篇批评的时期,他还不了解从20世纪开始的第一次变革,这 次变革将导致工人的欲望被归入消费经济的循环中,使无产阶级也同样成为消费者。在20 世纪的后半叶又发生了另一次变革,那一次变革将使审美憧憬成为明显的消费对象。而在 21世纪初,资本主义再一次因审美愉悦欲望的介入而得到发展。 如果“愉悦”(jouissance)这个词的本义在词源上与“用益权”(usufruit).和“使用”(usage) 1马克思,《1844年的巴黎手稿》,页93. ?马克思谈到:“(),对于不具备音乐欣赏能力的耳朵而言,即使最美好的音乐也没有任何意义、不是一 个客体,因为我的客体只能够是对我所掌握的能力的证实。”同上,页84. 3“感官成为了基本需求的囚徒,只具备有限的感受力。对于饥渴的人类而言,食物不具备人文的品质: 他们只能感受到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完全可以以最原始的形式呈现,而人类却无法说出他们的活动与生 长牧草的牧场有什么区别”。同上,页85 4同上,页83. 5资本主义在于做自己家里的客人:“拥有的感觉取代了所有生理和精神的感觉,这是感官的纯粹简单的异 化。人类可能要被压迫到这种绝对贫穷的状态中,才能让内在财富得见天日。”同上
阶级过一种最贫困的生活,导致了他们审美的僵化。资产阶级“把工人当作一种没有感觉、 缺乏需求的存在,正如把他们的活动当做一种任何活动的纯粹抽象化。在他们看来工人即使 享用最微不足道的奢侈都应当受到谴责,而且所有超出最抽象需求的事物——不管是被动的 享乐还是主动的表现——在他们看来都是奢侈品。”1马克思在他的革命纲领中憧憬“所有感 官的解放”,他认为所有感官都应该重新变得“人性”。人类应该重新获得人性。重新占有无 关于其交换价值的物品,就是将这些物品恢复到能为人类所掌控的状态:如果感官能够掌控 那些使音乐能被理解且令人欢愉的规则,那听音乐就能产生愉悦感。2 在承认感官与物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条件紧密相连的同时,要使审美愉悦感人性 化,则迫切需要突破无产阶级者简陋的生活条件。例如进食的需求升级为美食生活的艺术, 纯粹动物性的体验过渡为审美体验的过程要求刺激感受性。因为,去除工作、去除感官的协 调运用后,无产者不仅仅是陷入了经济的匮乏,还被剥夺了整个审美的世界,如同畜生一般: “忧虑和需求让人类变得对最美的景象也毫无感觉3”。既然解放是通过重获感受性来实现 的,运用的价值和审美愉悦感则无论如何都应该超越商业价值。审美享乐应该在一个时代中 优先于所有权,19 世纪,资本主义将享乐置于专属所有权的基础上。在对解放的展望中, 私有权的废除是必须的。私有权的废除目的在于推动相对于交换价值的感官享受:“私有权 让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如此狭隘,一件物品只有在我们拥有它、在它作为我们的资产而存在、 在它即时被占有、吃掉、喝掉、戴在身上、穿在身上等等,简而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时才是 属于我们的。4”“拥有”的概念遮掩了运用感官的自由。享受我们所拥有的事物于是被错误 的归结为享受所有权本身。总之,马克思用非物质的享受对抗唯物的资本主义,用内在性对 抗外在性,用感受性对抗机器,用自由的感官运用对抗机械化,用个性对抗异化。5与此同 时,通过这些伦理预设,这一解释用另一种形式重述了基督教的批判,基督教同样是用信仰 对抗浮夸、用内在财富对抗外在表象、用人性对抗金钱、用精神财富对抗人造财富、用真实 对抗不真实。 这一从此变得经典、持久,并在整个 20 世纪间发扬光大的批评理论应该考虑资本主义 转变的问题。在马克思撰写这篇批评的时期,他还不了解从 20 世纪开始的第一次变革,这 次变革将导致工人的欲望被归入消费经济的循环中,使无产阶级也同样成为消费者。在 20 世纪的后半叶又发生了另一次变革,那一次变革将使审美憧憬成为明显的消费对象。而在 21 世纪初,资本主义再一次因审美愉悦欲望的介入而得到发展。 如果“愉悦”(jouissance)这个词的本义在词源上与“用益权”(usufruit)和“使用”(usage) 1 马克思,《1844 年的巴黎手稿》,页 93. 2 马克思谈到:“(…),对于不具备音乐欣赏能力的耳朵而言,即使最美好的音乐也没有任何意义、不是一 个客体,因为我的客体只能够是对我所掌握的能力的证实。”同上,页 84. 3 “感官成为了基本需求的囚徒,只具备有限的感受力。对于饥渴的人类而言,食物不具备人文的品质; 他们只能感受到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完全可以以最原始的形式呈现,而人类却无法说出他们的活动与生 长牧草的牧场有什么区别”。同上,页 85. 4 同上,页 83. 5 资本主义在于做自己家里的客人:“拥有的感觉取代了所有生理和精神的感觉,这是感官的纯粹简单的异 化。人类可能要被压迫到这种绝对贫穷的状态中,才能让内在财富得见天日。”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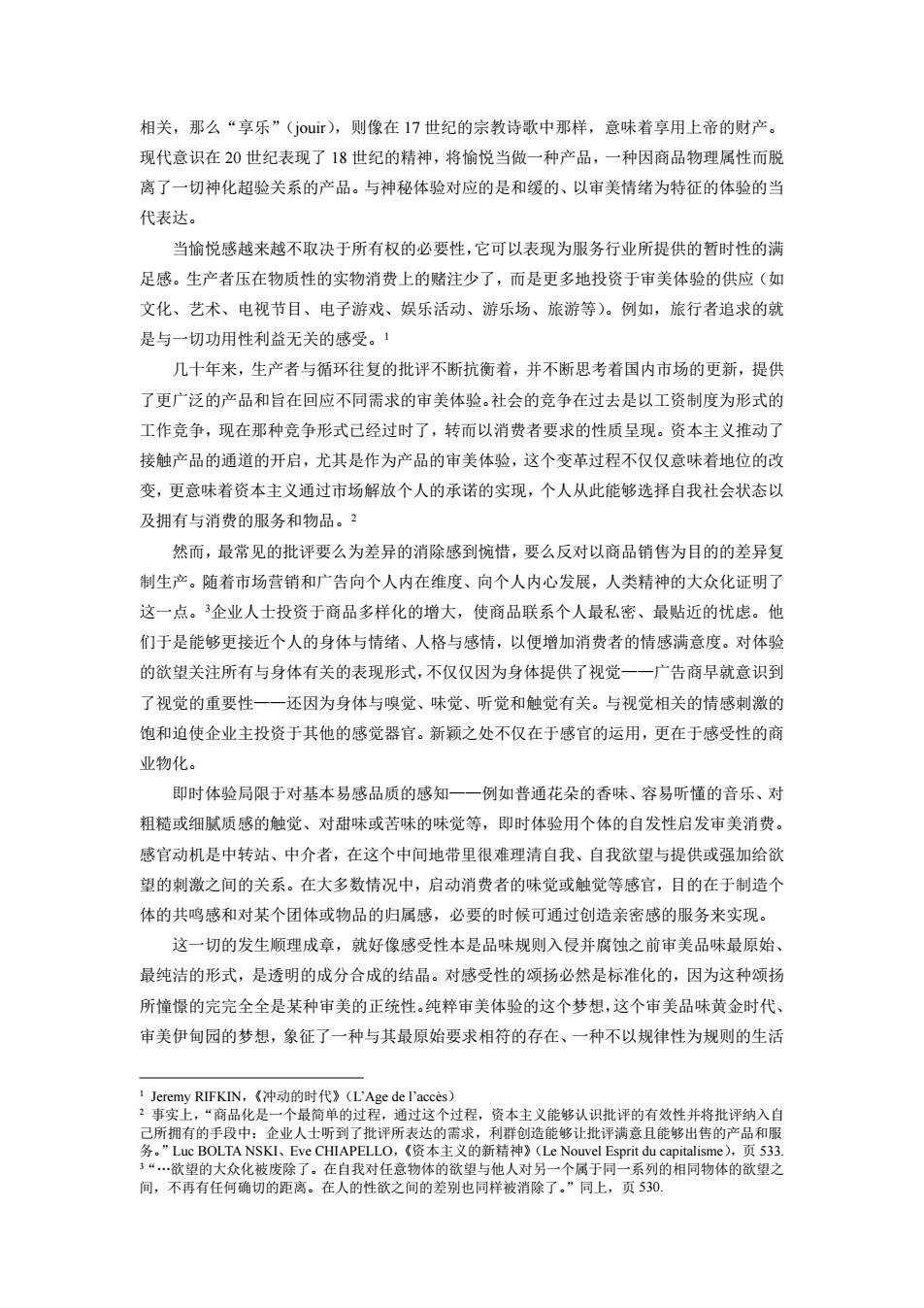
相关,那么“享乐”(joui),则像在17世纪的宗教诗歌中那样,意味着享用上帝的财产。 现代意识在20世纪表现了18世纪的精神,将愉悦当做一种产品,一种因商品物理属性而脱 离了一切神化超验关系的产品。与神秘体验对应的是和缓的、以审美情绪为特征的体验的当 代表达。 当愉悦感越来越不取决于所有权的必要性,它可以表现为服务行业所提供的暂时性的满 足感。生产者压在物质性的实物消费上的赌注少了,而是更多地投资于审美体验的供应(如 文化、艺术、电视节目、电子游戏、娱乐活动、游乐场、旅游等)。例如,旅行者追求的就 是与一切功用性利益无关的感受。1 几十年来,生产者与循环往复的批评不断抗衡着,并不断思考着国内市场的更新,提供 了更广泛的产品和旨在回应不同需求的审美体验。社会的竞争在过去是以工资制度为形式的 工作竞争,现在那种竞争形式己经过时了,转而以消费者要求的性质呈现。资本主义推动了 接触产品的通道的开启,尤其是作为产品的审美体验,这个变革过程不仅仅意味着地位的改 变,更意味着资本主义通过市场解放个人的承诺的实现,个人从此能够选择自我社会状态以 及拥有与消费的服务和物品。2 然而,最常见的批评要么为差异的消除感到惋惜,要么反对以商品销售为目的的差异复 制生产。随着市场营销和广告向个人内在维度、向个人内心发展,人类精神的大众化证明了 这一点。3企业人士投资于商品多样化的增大,使商品联系个人最私密、最贴近的忧虑。他 们于是能够更接近个人的身体与情绪、人格与感情,以便增加消费者的情感满意度。对体验 的欲望关注所有与身体有关的表现形式,不仅仅因为身体提供了视觉一一广告商早就意识到 了视觉的重要性一一还因为身体与嗅觉、味觉、听觉和触觉有关。与视觉相关的情感刺激的 饱和迫使企业主投资于其他的感觉器官。新颖之处不仅在于感官的运用,更在于感受性的商 业物化。 即时体验局限于对基本易感品质的感知一一例如普通花朵的香味、容易听懂的音乐、对 粗糙或细腻质感的触觉、对甜味或苦味的味觉等,即时体验用个体的自发性启发审美消费。 感官动机是中转站、中介者,在这个中间地带里很难理清自我、自我欲望与提供或强加给欲 望的刺激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中,启动消费者的味觉或触觉等感官,目的在于制造个 体的共鸣感和对某个团体或物品的归属感,必要的时候可通过创造亲密感的服务来实现。 这一切的发生顺理成章,就好像感受性本是品味规则入侵并腐蚀之前审美品味最原始、 最纯洁的形式,是透明的成分合成的结晶。对感受性的颂扬必然是标准化的,因为这种颂扬 所憧憬的完完全全是某种审美的正统性。纯粹审美体验的这个梦想,这个审美品味黄金时代、 审美伊甸园的梦想,象征了一种与其最原始要求相符的存在、一种不以规律性为规则的生活 1 Jeremy RIFKIN,《冲动的时代》(L'Age de'I acces) 2事实上,“商品化是一个最简单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资本主义能够认识批评的有效性并将批评纳入自 己所拥有的手段中:企业人士听到了批评所表达的需求,利群创造能够让批评满意且能够出售的产品和服 务。”Luc BOLTA NSKI、Eve CHIAPELLO,《资本主义的新精神》(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页533. 3“…欲望的大众化被废除了。在自我对任意物体的欲望与他人对另一个属于同一系列的相同物体的欲望之 间,不再有任何确切的距离。在人的性欲之间的差别也同样被消除了。”同上,页530
相关,那么“享乐”(jouir),则像在 17 世纪的宗教诗歌中那样,意味着享用上帝的财产。 现代意识在 20 世纪表现了 18 世纪的精神,将愉悦当做一种产品,一种因商品物理属性而脱 离了一切神化超验关系的产品。与神秘体验对应的是和缓的、以审美情绪为特征的体验的当 代表达。 当愉悦感越来越不取决于所有权的必要性,它可以表现为服务行业所提供的暂时性的满 足感。生产者压在物质性的实物消费上的赌注少了,而是更多地投资于审美体验的供应(如 文化、艺术、电视节目、电子游戏、娱乐活动、游乐场、旅游等)。例如,旅行者追求的就 是与一切功用性利益无关的感受。1 几十年来,生产者与循环往复的批评不断抗衡着,并不断思考着国内市场的更新,提供 了更广泛的产品和旨在回应不同需求的审美体验。社会的竞争在过去是以工资制度为形式的 工作竞争,现在那种竞争形式已经过时了,转而以消费者要求的性质呈现。资本主义推动了 接触产品的通道的开启,尤其是作为产品的审美体验,这个变革过程不仅仅意味着地位的改 变,更意味着资本主义通过市场解放个人的承诺的实现,个人从此能够选择自我社会状态以 及拥有与消费的服务和物品。2 然而,最常见的批评要么为差异的消除感到惋惜,要么反对以商品销售为目的的差异复 制生产。随着市场营销和广告向个人内在维度、向个人内心发展,人类精神的大众化证明了 这一点。3企业人士投资于商品多样化的增大,使商品联系个人最私密、最贴近的忧虑。他 们于是能够更接近个人的身体与情绪、人格与感情,以便增加消费者的情感满意度。对体验 的欲望关注所有与身体有关的表现形式,不仅仅因为身体提供了视觉——广告商早就意识到 了视觉的重要性——还因为身体与嗅觉、味觉、听觉和触觉有关。与视觉相关的情感刺激的 饱和迫使企业主投资于其他的感觉器官。新颖之处不仅在于感官的运用,更在于感受性的商 业物化。 即时体验局限于对基本易感品质的感知——例如普通花朵的香味、容易听懂的音乐、对 粗糙或细腻质感的触觉、对甜味或苦味的味觉等,即时体验用个体的自发性启发审美消费。 感官动机是中转站、中介者,在这个中间地带里很难理清自我、自我欲望与提供或强加给欲 望的刺激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中,启动消费者的味觉或触觉等感官,目的在于制造个 体的共鸣感和对某个团体或物品的归属感,必要的时候可通过创造亲密感的服务来实现。 这一切的发生顺理成章,就好像感受性本是品味规则入侵并腐蚀之前审美品味最原始、 最纯洁的形式,是透明的成分合成的结晶。对感受性的颂扬必然是标准化的,因为这种颂扬 所憧憬的完完全全是某种审美的正统性。纯粹审美体验的这个梦想,这个审美品味黄金时代、 审美伊甸园的梦想,象征了一种与其最原始要求相符的存在、一种不以规律性为规则的生活 1 Jeremy RIFKIN,《冲动的时代》(L’Age de l’accès) 2 事实上,“商品化是一个最简单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资本主义能够认识批评的有效性并将批评纳入自 己所拥有的手段中:企业人士听到了批评所表达的需求,利群创造能够让批评满意且能够出售的产品和服 务。”Luc BOLTA NSKI、Eve CHIAPELLO,《资本主义的新精神》(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页 533. 3“…欲望的大众化被废除了。在自我对任意物体的欲望与他人对另一个属于同一系列的相同物体的欲望之 间,不再有任何确切的距离。在人的性欲之间的差别也同样被消除了。”同上,页 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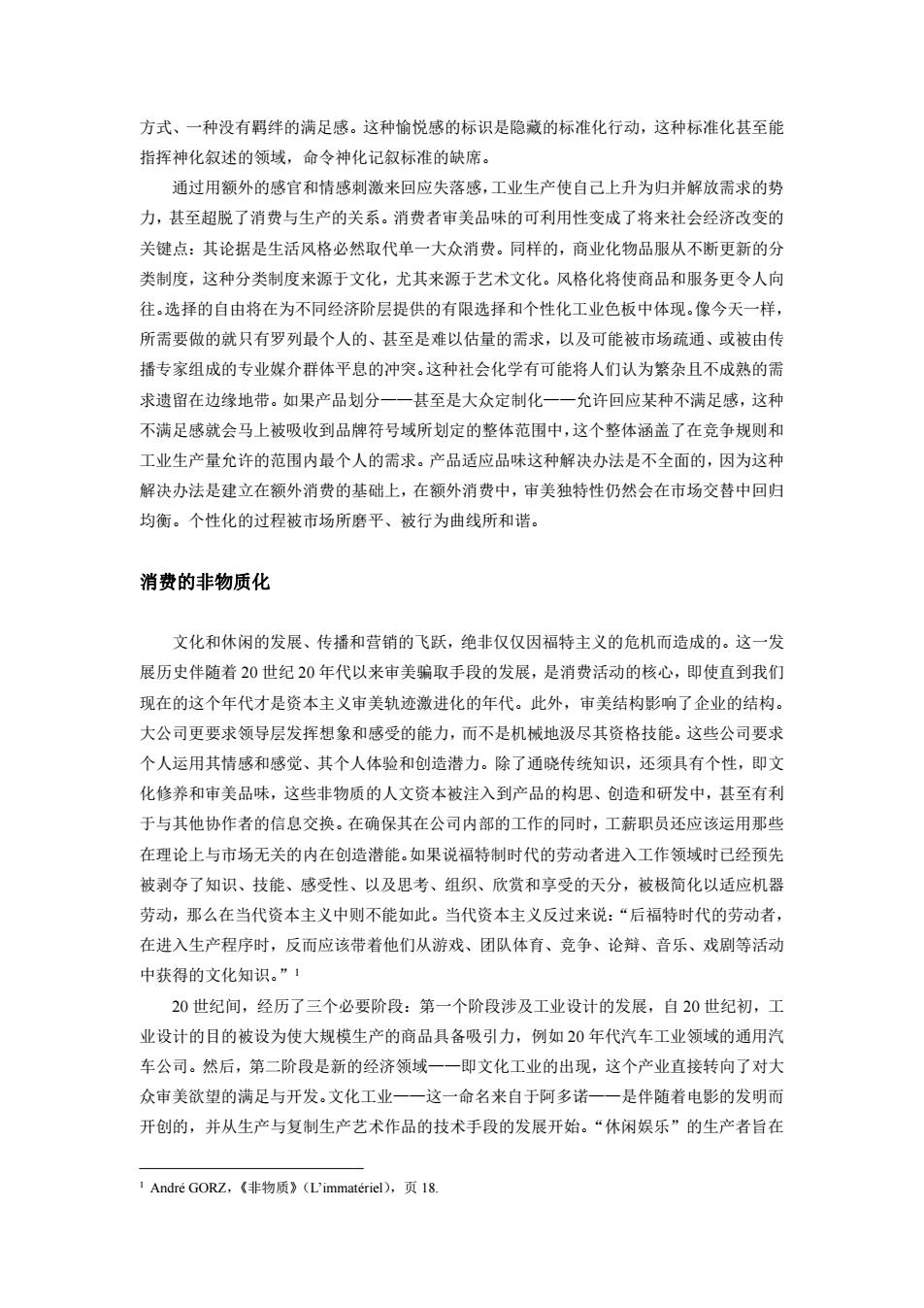
方式、一种没有羁绊的满足感。这种愉悦感的标识是隐藏的标准化行动,这种标准化甚至能 指挥神化叙述的领域,命令神化记叙标准的缺席。 通过用额外的感官和情感刺激来回应失落感,工业生产使自己上升为归并解放需求的势 力,甚至超脱了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消费者审美品味的可利用性变成了将来社会经济改变的 关键点:其论据是生活风格必然取代单一大众消费。同样的,商业化物品服从不断更新的分 类制度,这种分类制度来源于文化,尤其来源于艺术文化。风格化将使商品和服务更令人向 往。选择的自由将在为不同经济阶层提供的有限选择和个性化工业色板中体现。像今天一样, 所需要做的就只有罗列最个人的、甚至是难以估量的需求,以及可能被市场疏通、或被由传 播专家组成的专业媒介群体平息的冲突。这种社会化学有可能将人们认为繁杂且不成熟的需 求遗留在边缘地带。如果产品划分一一甚至是大众定制化一一允许回应某种不满足感,这种 不满足感就会马上被吸收到品牌符号域所划定的整体范围中,这个整体涵盖了在竞争规则和 工业生产量允许的范围内最个人的需求。产品适应品味这种解决办法是不全面的,因为这种 解决办法是建立在额外消费的基础上,在额外消费中,审美独特性仍然会在市场交替中回归 均衡。个性化的过程被市场所磨平、被行为曲线所和谐。 消费的非物质化 文化和休闲的发展、传播和营销的飞跃,绝非仅仅因福特主义的危机而造成的。这一发 展历史伴随着20世纪20年代以来审美骗取手段的发展,是消费活动的核心,即使直到我们 现在的这个年代才是资本主义审美轨迹激进化的年代。此外,审美结构影响了企业的结构。 大公司更要求领导层发挥想象和感受的能力,而不是机械地汲尽其资格技能。这些公司要求 个人运用其情感和感觉、其个人体验和创造潜力。除了通晓传统知识,还须具有个性,即文 化修养和审美品味,这些非物质的人文资本被注入到产品的构思、创造和研发中,甚至有利 于与其他协作者的信息交换。在确保其在公司内部的工作的同时,工薪职员还应该运用那些 在理论上与市场无关的内在创造潜能。如果说福特制时代的劳动者进入工作领域时已经预先 被剥夺了知识、技能、感受性、以及思考、组织、欣赏和享受的天分,被极简化以适应机器 劳动,那么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则不能如此。当代资本主义反过来说:“后福特时代的劳动者, 在进入生产程序时,反而应该带着他们从游戏、团队体育、竞争、论辩、音乐、戏剧等活动 中获得的文化知识。”1 20世纪间,经历了三个必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涉及工业设计的发展,自20世纪初,工 业设计的目的被设为使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具备吸引力,例如20年代汽车工业领域的通用汽 车公司。然后,第二阶段是新的经济领域一一即文化工业的出现,这个产业直接转向了对大 众审美欲望的满足与开发。文化工业一一这一命名来自于阿多诺一一是伴随着电影的发明而 开创的,并从生产与复制生产艺术作品的技术手段的发展开始。“休闲娱乐”的生产者旨在 Andre GORZ,《非物质》(L'immateriel),页I8
方式、一种没有羁绊的满足感。这种愉悦感的标识是隐藏的标准化行动,这种标准化甚至能 指挥神化叙述的领域,命令神化记叙标准的缺席。 通过用额外的感官和情感刺激来回应失落感,工业生产使自己上升为归并解放需求的势 力,甚至超脱了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消费者审美品味的可利用性变成了将来社会经济改变的 关键点:其论据是生活风格必然取代单一大众消费。同样的,商业化物品服从不断更新的分 类制度,这种分类制度来源于文化,尤其来源于艺术文化。风格化将使商品和服务更令人向 往。选择的自由将在为不同经济阶层提供的有限选择和个性化工业色板中体现。像今天一样, 所需要做的就只有罗列最个人的、甚至是难以估量的需求,以及可能被市场疏通、或被由传 播专家组成的专业媒介群体平息的冲突。这种社会化学有可能将人们认为繁杂且不成熟的需 求遗留在边缘地带。如果产品划分——甚至是大众定制化——允许回应某种不满足感,这种 不满足感就会马上被吸收到品牌符号域所划定的整体范围中,这个整体涵盖了在竞争规则和 工业生产量允许的范围内最个人的需求。产品适应品味这种解决办法是不全面的,因为这种 解决办法是建立在额外消费的基础上,在额外消费中,审美独特性仍然会在市场交替中回归 均衡。个性化的过程被市场所磨平、被行为曲线所和谐。 消费的非物质化 文化和休闲的发展、传播和营销的飞跃,绝非仅仅因福特主义的危机而造成的。这一发 展历史伴随着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审美骗取手段的发展,是消费活动的核心,即使直到我们 现在的这个年代才是资本主义审美轨迹激进化的年代。此外,审美结构影响了企业的结构。 大公司更要求领导层发挥想象和感受的能力,而不是机械地汲尽其资格技能。这些公司要求 个人运用其情感和感觉、其个人体验和创造潜力。除了通晓传统知识,还须具有个性,即文 化修养和审美品味,这些非物质的人文资本被注入到产品的构思、创造和研发中,甚至有利 于与其他协作者的信息交换。在确保其在公司内部的工作的同时,工薪职员还应该运用那些 在理论上与市场无关的内在创造潜能。如果说福特制时代的劳动者进入工作领域时已经预先 被剥夺了知识、技能、感受性、以及思考、组织、欣赏和享受的天分,被极简化以适应机器 劳动,那么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则不能如此。当代资本主义反过来说:“后福特时代的劳动者, 在进入生产程序时,反而应该带着他们从游戏、团队体育、竞争、论辩、音乐、戏剧等活动 中获得的文化知识。”1 20 世纪间,经历了三个必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涉及工业设计的发展,自 20 世纪初,工 业设计的目的被设为使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具备吸引力,例如 20 年代汽车工业领域的通用汽 车公司。然后,第二阶段是新的经济领域——即文化工业的出现,这个产业直接转向了对大 众审美欲望的满足与开发。文化工业——这一命名来自于阿多诺——是伴随着电影的发明而 开创的,并从生产与复制生产艺术作品的技术手段的发展开始。“休闲娱乐”的生产者旨在 1 André GORZ,《非物质》(L’immatériel),页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