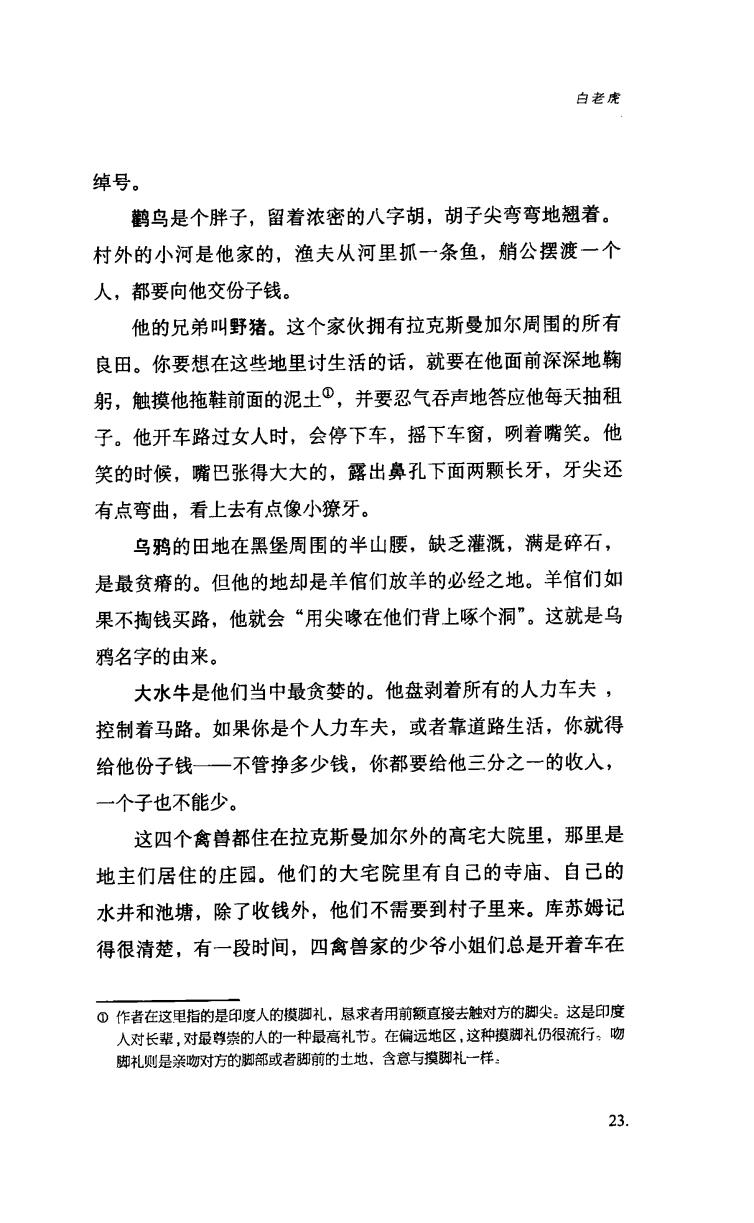
白老虎 绰号。 鹊鸟是个胖子,留着浓密的八字胡,胡子尖弯弯地翘着。 村外的小河是他家的,渔夫从河里抓一条鱼,艄公摆渡一个 人,都要向他交份子钱。 他的兄弟叫野猪。这个家伙拥有拉克斯曼加尔周围的所有 良田。你要想在这些地里讨生活的话,就要在他面前深深地鞠 躬,触摸他拖鞋前面的泥土①,并要忍气吞声地答应他每天抽租 子。他开车路过女人时,会停下车,摇下车窗,咧着嘴笑。他 笑的时候,嘴巴张得大大的,露出鼻孔下面两颗长牙,牙尖还 有点弯曲,看上去有点像小獠牙。 乌鸦的田地在黑堡周围的半山腰,缺乏灌溉,满是碎石, 是最贫瘠的。但他的地却是羊倌们放羊的必经之地。羊倌们如 果不掏钱买路,他就会“用尖喙在他们背上啄个洞”。这就是乌 鸦名字的由来。 大水牛是他们当中最贪婪的。他盘剥着所有的人力车夫, 控制着马路。如果你是个人力车夫,或者靠道路生活,你就得 给他份子钱一不管挣多少钱,你都要给他三分之一的收入, 一个子也不能少。 这四个禽兽都住在拉克斯曼加尔外的高宅大院里,那里是 地主们居住的庄园。他们的大宅院里有自己的寺庙、自己的 水井和池塘,除了收钱外,他们不需要到村子里来。库苏姆记 得很清楚,有一段时间,四禽兽家的少爷小姐们总是开着车在 ①作者在这里指的是印度人的摸脚礼,恳求者用前额直接去触对方的脚尖。这是印度 人对长辈,对最尊崇的人的一种最高礼节。在偏远地区,这种摸脚礼仍很流行。吻 脚礼则是亲吻对方的脚部或者脚前的士地、含意与摸脚礼一样: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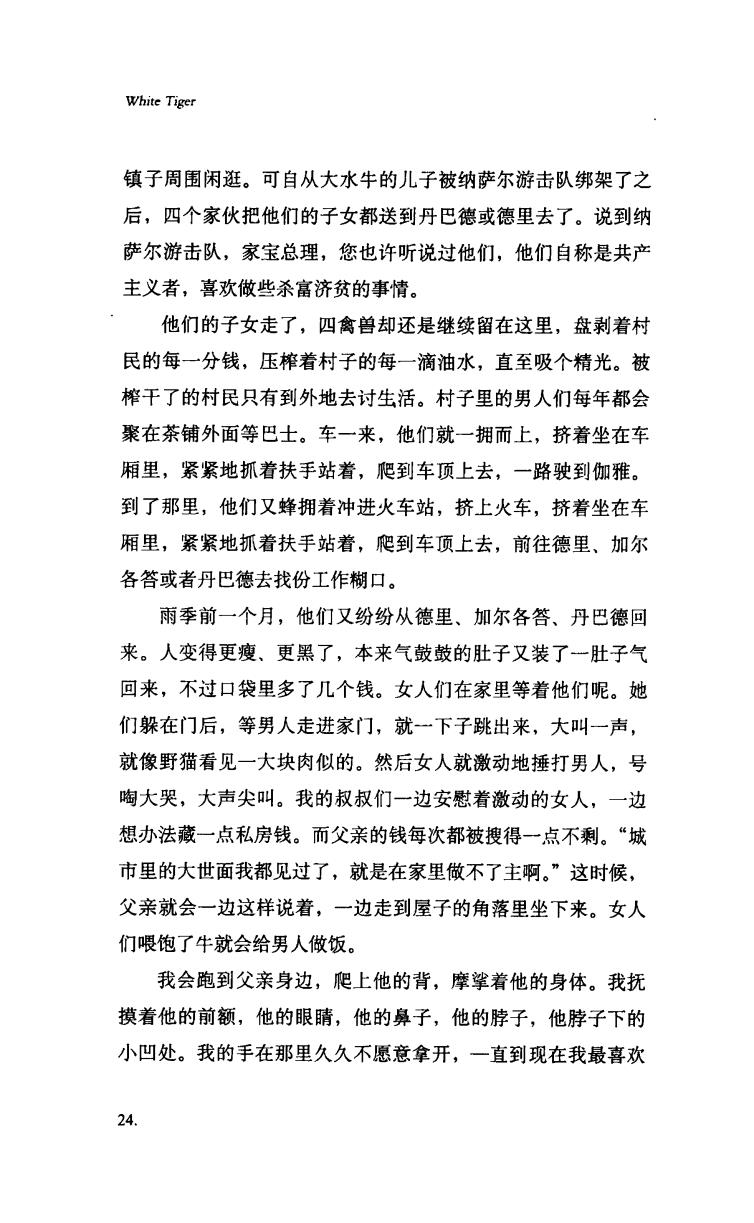
White Tiger 镇子周围闲逛。可自从大水牛的儿子被纳萨尔游击队绑架了之 后,四个家伙把他们的子女都送到丹巴德或德里去了。说到纳 萨尔游击队,家宝总理,您也许听说过他们,他们自称是共产 主义者,喜欢做些杀富济贫的事情。 他们的子女走了,四禽兽却还是继续留在这里,盘剥着村 民的每一分钱,压榨着村子的每一滴油水,直至吸个精光。被 榨干了的村民只有到外地去讨生活。村子里的男人们每年都会 聚在茶铺外面等巴士。车一来,他们就一拥而上,挤着坐在车 厢里,紧紧地抓着扶手站着,爬到车顶上去,一路驶到伽雅。 到了那里,他们又蜂拥着冲进火车站,挤上火车,挤着坐在车 厢里,紧紧地抓着扶手站着,爬到车顶上去,前往德里、加尔 各答或者丹巴德去找份工作糊口。 雨季前一个月,他们又纷纷从德里、加尔各答、丹巴德回 来。人变得更瘦、更黑了,本来气鼓鼓的肚子又装了一肚子气 回来,不过口袋里多了几个钱。女人们在家里等着他们呢。她 们躲在门后,等男人走进家门,就一下子跳出来,大叫一声, 就像野猫看见一大块肉似的。然后女人就激动地捶打男人,号 陶大哭,大声尖叫。我的叔叔们一边安慰着激动的女人,一边 想办法藏一点私房钱。而父亲的钱每次都被搜得一点不剩。“城 市里的大世面我都见过了,就是在家里做不了主啊。”这时候, 父亲就会一边这样说着,一边走到屋子的角落里坐下来。女人 们喂饱了牛就会给男人做饭。 我会跑到父亲身边,爬上他的背,摩挲着他的身体。我抚 摸着他的前额,他的眼睛,他的鼻子,他的脖子,他脖子下的 小凹处。我的手在那里久久不愿意拿开,一直到现在我最喜欢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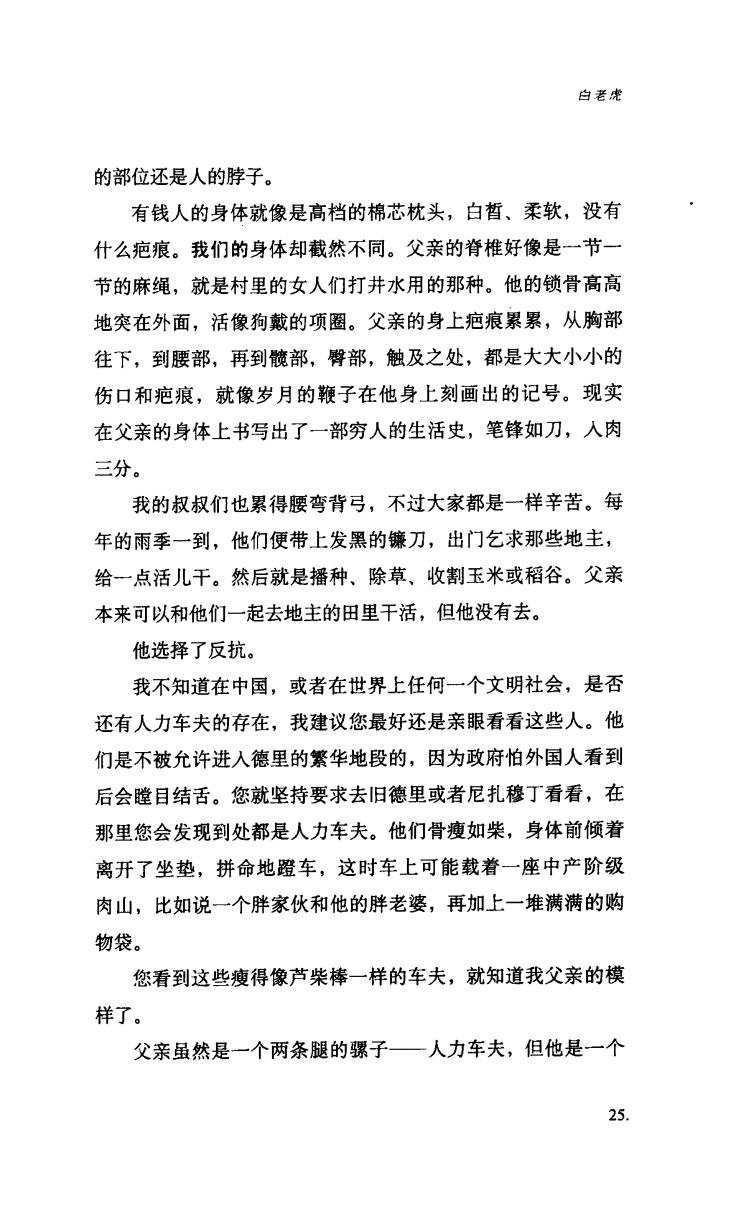
白老虎 的部位还是人的脖子。 有钱人的身体就像是高档的棉芯枕头,白皙、柔软,没有 什么疤痕。我们的身体却截然不同。父亲的脊椎好像是一节一 节的麻绳,就是村里的女人们打井水用的那种。他的锁骨高高 地突在外面,活像狗戴的项圈。父亲的身上疤痕累累,从胸部 往下,到腰部,再到髋部,臀部,触及之处,都是大大小小的 伤口和疤痕,就像岁月的鞭子在他身上刻画出的记号。现实 在父亲的身体上书写出了一部穷人的生活史,笔锋如刀,入肉 三分。 我的叔叔们也累得腰弯背弓,不过大家都是一样辛苦。每 年的雨季一到,他们便带上发黑的镰刀,出门乞求那些地主, 给一点活儿干。然后就是播种、除草、收割玉米或稻谷。父亲 本来可以和他们一起去地主的田里干活,但他没有去。 他选择了反抗。 我不知道在中国,或者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社会,是否 还有人力车夫的存在,我建议您最好还是亲眼看看这些人。他 们是不被允许进入德里的繁华地段的,因为政府怕外国人看到 后会瞠目结舌。您就坚持要求去旧德里或者尼扎穆丁看看,在 那里您会发现到处都是人力车夫。他们骨瘦如柴,身体前倾着 离开了坐垫,拼命地蹬车,这时车上可能载着一座中产阶级 肉山,比如说一个胖家伙和他的胖老婆,再加上一堆满满的购 物袋。 您看到这些瘦得像芦柴棒一样的车夫,就知道我父亲的模 样了。 父亲虽然是一个两条腿的骡子一人力车夫,但他是一个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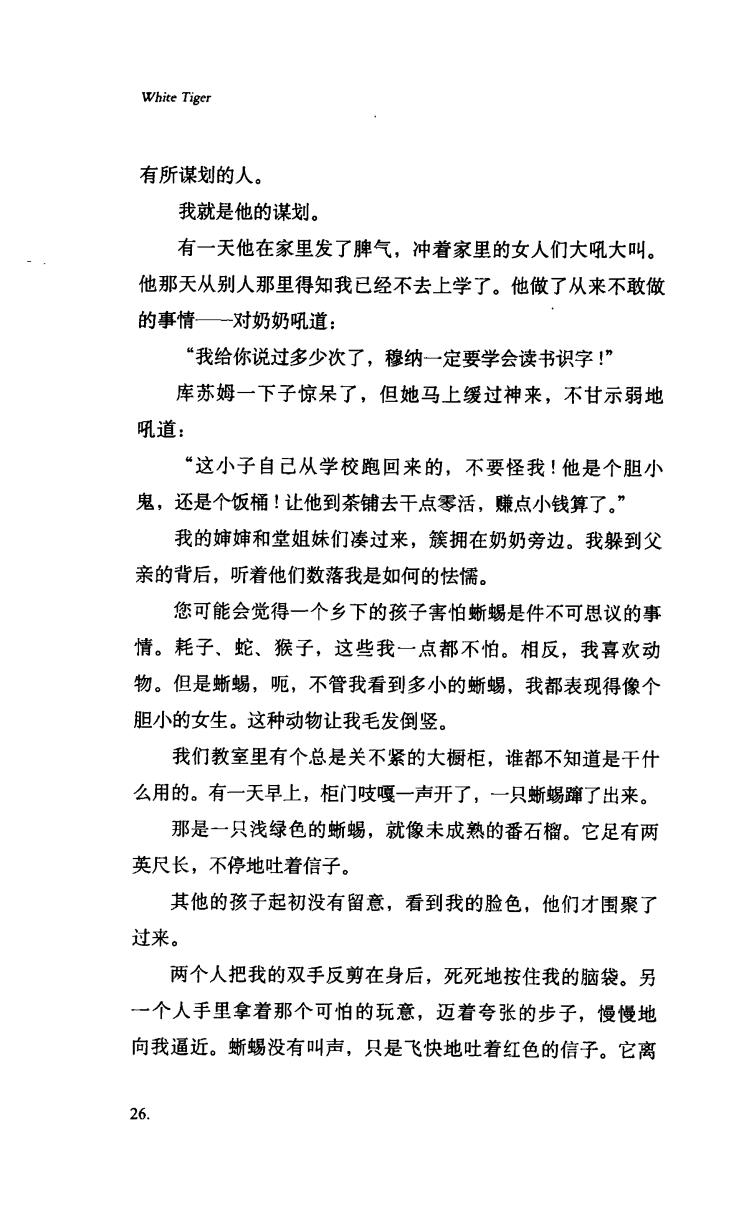
White Tiger 有所谋划的人。 我就是他的谋划。 有一天他在家里发了脾气,冲着家里的女人们大吼大叫。 他那天从别人那里得知我已经不去上学了。他做了从来不敢做 的事情一对奶奶吼道: “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穆纳一定要学会读书识字!” 库苏姆一下子惊呆了,但她马上缓过神来,不甘示弱地 吼道: “这小子自己从学校跑回来的,不要怪我!他是个胆小 鬼,还是个饭桶!让他到茶铺去干点零活,赚点小钱算了。” 我的婶婶和堂姐妹们凑过来,簇拥在奶奶旁边。我躲到父 亲的背后,听着他们数落我是如何的怯懦。 您可能会觉得一个乡下的孩子害怕蜥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情。耗子、蛇、猴子,这些我一点都不怕。相反,我喜欢动 物。但是蜥蜴,呃,不管我看到多小的蜥蜴,我都表现得像个 胆小的女生。这种动物让我毛发倒竖。 我们教室里有个总是关不紧的大橱柜,谁都不知道是千什 么用的。有一天早上,柜门吱嘎一声开了,一只蜥蜴蹿了出来。 那是一只浅绿色的蜥蜴,就像未成熟的番石榴。它足有两 英尺长,不停地吐着信子。 其他的孩子起初没有留意,看到我的脸色,他们才围聚了 过来。 两个人把我的双手反剪在身后,死死地按住我的脑袋。另 一个人手里拿着那个可怕的玩意,迈着夸张的步子,慢慢地 向我逼近。蜥蜴没有叫声,只是飞快地吐着红色的信子。它离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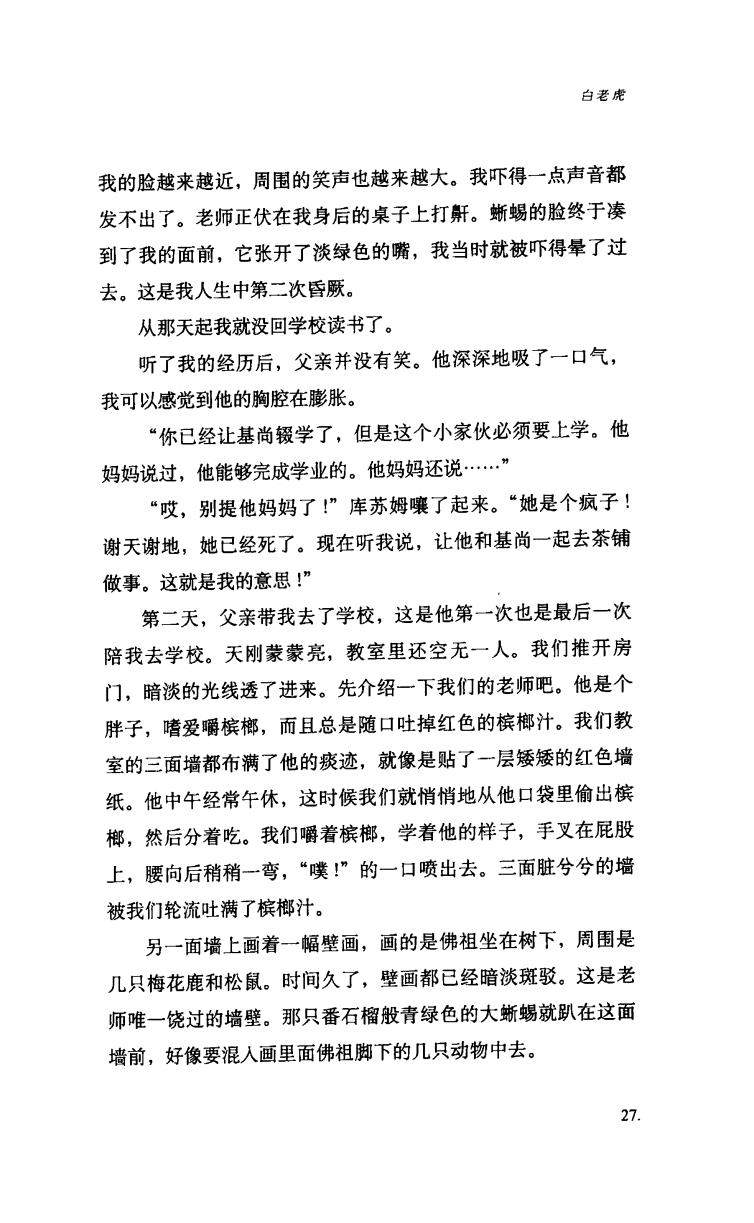
白老虎 我的脸越来越近,周围的笑声也越来越大。我吓得一点声音都 发不出了。老师正伏在我身后的桌子上打鼾。蜥蜴的脸终于凑 到了我的面前,它张开了淡绿色的嘴,我当时就被吓得晕了过 去。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昏厥。 从那天起我就没回学校读书了。 听了我的经历后,父亲并没有笑。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胸腔在膨胀。 “你已经让基尚辍学了,但是这个小家伙必须要上学。他 妈妈说过,他能够完成学业的。他妈妈还说…” “哎,别提他妈妈了!”库苏姆嚷了起来。“她是个疯子! 谢天谢地,她已经死了。现在听我说,让他和基尚一起去茶铺 做事。这就是我的意思!” 第二天,父亲带我去了学校,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陪我去学校。天刚蒙蒙亮,教室里还空无一人。我们推开房 门,暗淡的光线透了进来。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老师吧。他是个 胖子,嗜爱嚼槟榔,而且总是随口吐掉红色的槟榔汁。我们教 室的三面墙都布满了他的痰迹,就像是贴了一层矮矮的红色墙 纸。他中午经常午休,这时候我们就悄悄地从他口袋里偷出槟 榔,然后分着吃。我们嚼着槟榔,学着他的样子,手叉在屁股 上,腰向后稍稍一弯,“噗!”的一口喷出去。三面脏兮兮的墙 被我们轮流吐满了槟榔汁。 另一面墙上画着一幅壁画,画的是佛祖坐在树下,周围是 几只梅花鹿和松鼠。时间久了,壁画都已经暗淡斑驳。这是老 师唯一绕过的墙壁。那只番石榴般青绿色的大蜥蜴就趴在这面 墙前,好像要混入画里面佛祖脚下的几只动物中去。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