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釋作“宗”。1此後學術界多從此說。2後來,黄盛璋先生把這個字改釋爲“主(宝)”。他 認爲,首先,“以事其宗”在盟書中講不通,故“A”不能是宗廟,而愿該是“主”字。其 次,據中山器以及傳抄古文中的“主(宝)”字的寫法,“A”字確是“主(宝)”。另外, 侯馬盟書明確的“宗”字从“示”,而“主(宝)”字下从“市、“T”,雨字区别明顯。 3現在看來,把此字釋作“主(宝)”正確可從。 (6)、明亟硯(視)之 侯馬盟書常見“明亟硯(視)之”一語,或作“永亟硯(視)之”,在溫縣盟書中則 作“童(諦)亟硯(視)之”、“帝(諦)惑(極)硯(視)女(汝)”等。下面以侯馬 盟書中的“明亟硯(視)之”爲例進行闡述。 學術界通常把“明亟硯(視)之”中的“亟”讀作“殛”,“硯”讀作“視”,均可 信。但是對其解釋則存在分歧。陶正刚、王克林先生把“殛”訓作“誅”,認爲“明亟硯(視) 之”是“誅减和监視”的意思。4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侯馬工作站人員認爲“明亟硯(視) 之”就是“神明鑒察之意”。5《侯馬盟書》從之。6這些解釋均有未安之處。唐鈺明先生曾 作過詳細的分析。他認爲,第一種解釋,“誅减”和“監視”既不是遞進關係,也不是互補 關係,無法放到同一語境之中。因爲“誅减”之後是無需再“監視”的。而第二種解釋,則 抛開了“亟”字,顯然也不妥當。要解釋這句話的關鍵是正確理解“殛”字。典籍中“殛” 字既有“誅”的意思,也有“懲罚”之義。而侯馬盟書中的“殛”字當理解成“懲罚”的意 思。故“明亟硯(視)之”或“永亟硯(視)之”,說的是先君神靈對背盟者的“懲罰”。 最近,董珊先生重新梳理了這個問题。他認爲,這句話的直接賓語是“明殛”,謂語動 詞是“視”,在此訓作“示”,兩批盟書中的“視(示)”的詞義是“降示”或“加示”, 有比較強的自上(“大冢”或“吾君”)降加于下(“之”或“汝”)的意味。侯馬盟書中 的“明殛”意思是“大的、明顯的懲罰”;“永殛”是長久懲罰之意;溫縣盟書中的“童” 即“謫”字,訓爲“責”,與“殛”義近連用,“謫殛”就是責罰。盟書這句話翻譯成現代 漢語就是:“大冢(或吾君)以大罰示他(你)。”8 唐鈺明和董珊先生的意見,有助於對文意的理解。至於董珊先生把“童”釋作“謫” 字,訓爲“責”的説法,我們將在“歸字説明”部分略作分析。 (7)、麻夷非是 侯馬和溫縣盟書屡見“麻夷非是”一語有時又作“麻夷非氏”,其中的“麻”、“夷” 等字異體甚多,此處只用通式文字釋寫。 【郭沫若:《侯馬盟書試探》,《文物》1965年第2期。 2可参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合:《侯馬盟書》,文物出版社,1976年,76真。陳萝家:《東周盟誓與出 土戴書》,《考古》1966年第5期。唐蘭:《侯馬出土晉國趙嘉之盟胶書新釋》,《文物》1972年第8期。高 明:《侯馬戟書盟主考》,《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79年,103-115頁。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 跟頷,陶正刚,張守中:《侯馬盟書》(增訂本),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331頁。 3黄盛璋:《關於侯馬盟書的主要周题》,《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黄盛璋:《中山國銘刻在古文字、語 言上若干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中華書局,1982年,83-84頁。 4陶正刚、王克林:《侯馬束周盟誓遺址》,《文物》1972年第4期。 5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侯馬工作站:《“侯馬盟者”注釋四種》,《文物》1975年第5期。 6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侯馬盟書》,文物出版社,1976年,36頁。 7唐钰明:《重論“麻夷非是“》,《廣州師院學報》,1989年第2期。又載《著名中年譜言學家自選集·唐 鈺明卷》,安微教育出版社,2002年。本文引用後者。 8董珊:《侯馬、溫縣盟書中的“明殛视之”的句法分析》,《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中華替局,2008 年,356-362頁。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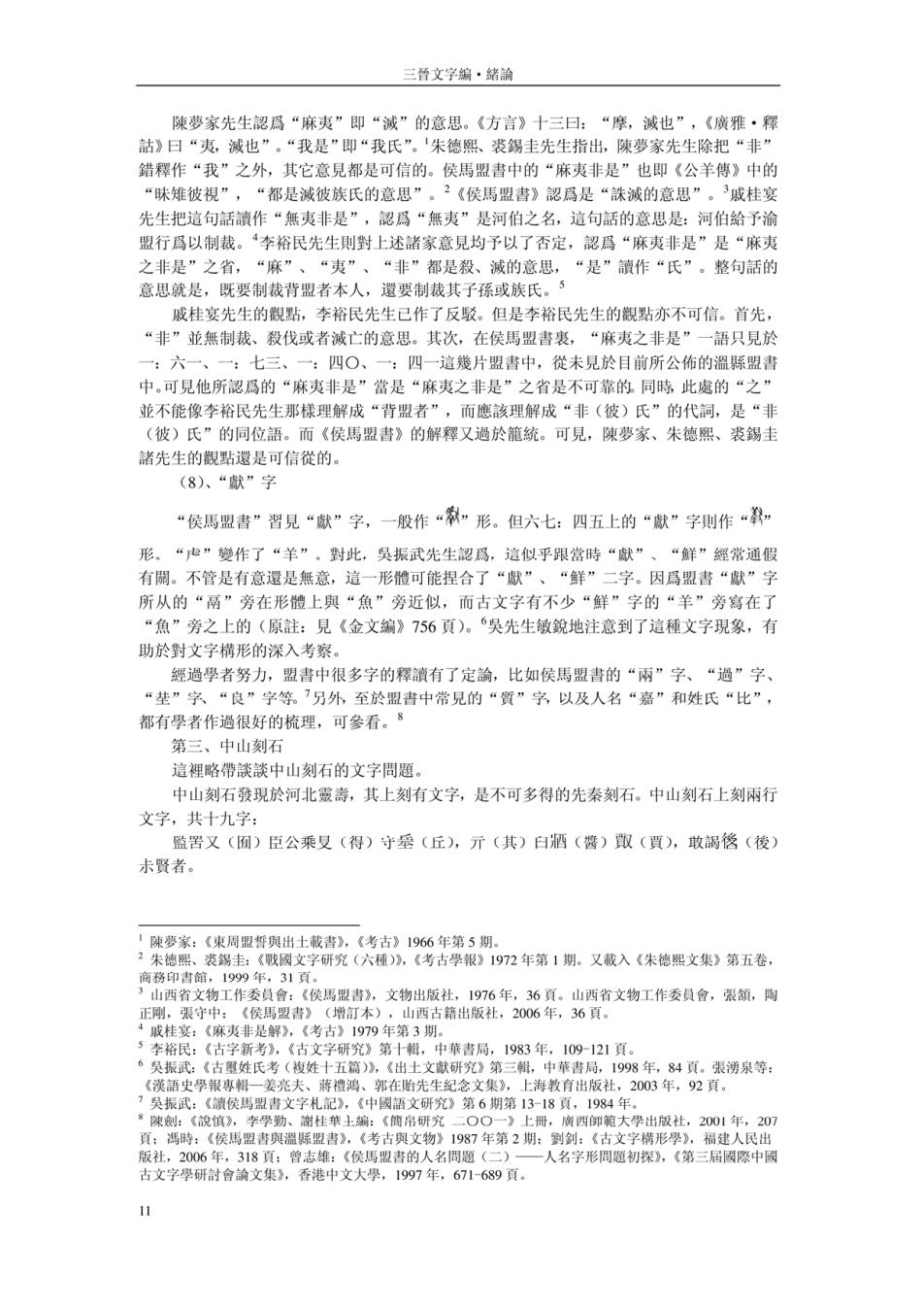
三晉文字編·绪論 陳萝家先生認爲“麻夷”即“减”的意思。《方言》十三曰:“摩,减也”,《廣雅·釋 詁》曰“夷,减也”。“我是”即“我氏”。'朱德熙、裘錫圭先生指出,陳夢家先生除把“非” 錯釋作“我”之外,其它意見都是可信的。侯馬盟書中的“麻夷非是”也即《公羊傳》中的 “昧雉彼視”,“都是减彼族氏的意思”。2《侯馬盟書》認爲是“誅减的意思”。3戚桂宴 先生把這句話讀作“無夷非是”,認爲“無夷”是河伯之名,這句話的意思是:河伯給予渝 盟行爲以制裁。4李裕民先生則對上述諸家意見均予以了否定,認爲“麻夷非是”是“麻夷 之非是”之省,“麻”、“夷”、“非”都是殺、减的意思,“是”讀作“氏”。整句話的 意思就是,既要制裁背盟者本人,還要制裁其子孫或族氏。5 戚桂宴先生的觀點,李裕民先生已作了反駁。但是李裕民先生的觀點亦不可信。首先, “非”並無制裁、殺伐或者减亡的意思。其次,在侯馬盟書裹,“麻夷之非是”一語只見於 一:六一、一:七三、一:四O、一:四一這幾片盟書中,從未見於目前所公佈的溫縣盟書 中。可見他所認爲的“麻夷非是”當是“麻夷之非是”之省是不可靠的。同陈此處的“之” 並不能像李裕民先生那樣理解成“背盟者”,而應該理解成“非(彼)氏”的代詞,是“非 (彼)氏”的同位語。而《侯馬盟書》的解釋又過於籠統。可見,陳夢家、朱德熙、裘錫圭 諸先生的觀點還是可信從的。 (8)、“献”字 “侯馬盟書”習見“献”字,一般作“”形。但六七:四五上的“献”字則作“载 形。“虍”變作了“羊”。對此,吳振武先生認爲,這似乎跟當時“獻”、“鲜”經常通假 有關。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這一形體可能捏合了“獻”、“鲜”二字。因爲盟書“獻”字 所从的“鬲”旁在形體上與“魚”旁近似,而古文字有不少“鲜”字的“羊”旁寫在了 “魚”旁之上的(原註:見《金文编》756頁)。6吳先生敏銳地注意到了這種文字現象,有 助於對文字構形的深入考察。 經過學者努力,盟書中很多字的釋讀有了定論,比如侯馬盟書的“兩”字、“過”字、 “基”字“良”字等。7另外至於盟書中常見的“質”字以及人名“嘉”和姓氏“比”, 都有學者作過很好的梳理,可參看。8 第三、中山刻石 這裡略帶談談中山刻石的文字問题。 中山刻石發現於河北靈壽,其上刻有文字,是不可多得的先秦刻石。中山刻石上刻雨行 文字,共十九字: 監罟又(囿)臣公乘夏(得)守星(丘),亓(其)白酒(醬)取(賈),敢謁修(後) 未贤者。 1陳夢家:《束周盟誓與出土載書》,《考古》1966年第5期。 ?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六種)》,《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又截入《朱德熙文集》第五卷, 商務印書館,1999年,31頁。 3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合:《侯馬盟書》,文物出版社,1976年,36真。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張额,陶 正刚,跟守中:《侯馬盟書》(增盯本),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36頁。 4戚桂宴:《麻夷非是解》,《考古》1979年第3期。 5李裕民:《古字新考》,《古文字研究》第十朝,中華者局,1983年,109121夏。 6吳振武:《古凰姓氏考(複姓十五篇)》,《出土文献研究》第三輯,中華書局,1998年,84頁。張湧泉等: 《漢語史學報專粗一姜亮夫、蔣禮鸿、郭在胎先生紀念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92頁。 7吳振武:《讀侯馬盟書文字札記》,《中國語文研究》第6期第13-18页,1984年。 8陳劍:《說慎》,李學勤、謝桂華土编:《簡帛研究二O○一》上冊,廣西邻舱大學出版社,2001年,207 頁:馮時:《侯馬盟書與温縣盟書》,《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2期:到剑:《古文字構形學》,福建人民出 版社,2006年,318頁:曾志雄:《侯馬盟潜的人名問题(二)一人名字形周题初探》,《第三届國際中國 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1997年,671-689真

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監署”兩字,發掘簡報據李學勤先生的意見首釋,'已成定論。但對“監罟”的解釋 則有爭議。發掘簡報、《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2、黃盛璋’、李學勤先生均表示是職官名, 陳邦懷先生讀作“監寂”,未作解釋。5董珊先生認爲是人名6。 “又”,發掘簡報釋作“尤”讀作“囿”;《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釋作“有”;黄盛 璋先生釋作“有”讀作“囿”,與發掘簡報一樣,根據當地的地理環境認爲“囿臣”跟古代 的苑囿管理有關,相當於《周禮》的“獸人”及“囿人”。李學勤先生釋作“尤”,認爲“尤 臣”即“罪臣”。陳邦懷先生讀作“右”。董珊先生認爲“又”讀作“有”,“有臣”在此 表示隸屬關係,是說“監罟”“是‘公乘得'的主君。” “公乘”,一般均認爲是姓氏。董珊先生則認爲是爵稱。 “守丘”,各家均認爲是守護墳塋之意。 “元(其)白酒(醬)取(賈)”,發掘筒報、《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李學勤、陳 邦懷先生均讀“白”作“舊”,讀“酒”作“將”,認爲“白酒”即“舊將”之意。黄盛 璋先生讀作“柩”。董珊先生釋作“白”括注爲“齒”,並打了個問號,顯然還有懷疑。 “取”字,有多種意見,我們贊同何琳儀先生釋作“賈”的觀點,並在“歸字説明” 部分略作解釋。然而“亓(其)白晒取(賈)”一句頗難索解,只能存以待考。 “未”,發掘簡報、《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讀作“俶”,黄盛璋先生釋作“先”,認 爲“後先”即“先後”的倒文。李學勤先生讀作“淑”訓作“善”。何琳儀先生釋作“叔” 讀作“淑”。7董珊先生釋作“赤”讀作“造”,訓作“至”、“到”。“敢謁後赤賢者” 就是“敬告於後來的贤者”的意思。 按,“監罟”一詞應理解爲職官名更爲妥當。“又”讀作“有”沒有問题,在此可理解 成苑囿之“囿”。至於“有臣”之說尚需更多證據。董珊先生也承認,在文默出現“有臣” 詞的例子中,“臣名上也常加姓氏,並且沒見有加爵稱的例子。”跟文獻中的例子比較起 來,守丘刻石的例子“是顯得特殊了一點。”8因此,把“監罟”看作官職,把“公乘”理 解爲姓氏,把“又”讀作“囿”,當可信。 “敢謁德(後)赤(淑)賢者”當如董珊先生所言,是“敬告於後來的贤者”之義。 文字考釋固然重要,但誠如黄盛璋先生所言:“石刻的最大價值還在於戰國文字的研究 上,它不僅提供新的資料,更主要的是給戰國文字的分國與時代的研究提供了依據。”9譬 如,根據石刻及《少俯盉》中的“有”字,可判斷出數十方帶有“有”字的璽印爲三晉璽印: 又如據複姓“公乘”可以把類似寫法的霞印歸入三晉系列:還有“丘”、“赤”、“者”等 字,均可作爲判斷國別和時代的標準。0 (一)、铜器 中國古代,一般稱青铜禮器爲彝器。《左傳·襄公十九年》:“且夫大伐小,取其所 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杜預注:“彝,常也。謂鐘 鼎爲宗廟之常器。”到了戰國時代,除了個別器物(如中山三器)外,青銅器原有的“宗 廟之常器”的作用趨于削弱,而實用性則日漸增強。如趙國的“十一年庫嗇夫鼎”、魏國 1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國墓葬發掘筒報》,《文物》1979年第1期。 2河北省博物館、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202真。 3黄盛璋:《平山戰國中山刻石初步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八輯,中華書局,1983年,43-44頁。 4李學勤:《中山石刻釋文》,《戰國中山因靈壽城》,文物出版社,又截入李學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 務印書館,2008年,338-339頁。本文引用後者。 5陳邦懷:《中山王墓守丘刻石文字跋》,陳邦懷:《一得集》,齊魯書社,1989年,212-213頁。 6董珊:《戰國题銘與工官制度》,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尊師:李零),2002年,139页。 7何琳儀:《戰因文字通論》(訂補),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137頁。 8董珊:《戰國题銘與工官制度》,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李零),2002年,141頁。 9黄盛璋:《平山戰國中山刻石初步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八輯,中華替局,1983年,52頁。 0黄盛璋:《平山戰國中山刻石初步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八輯,中華書局,1983年,52-55頁。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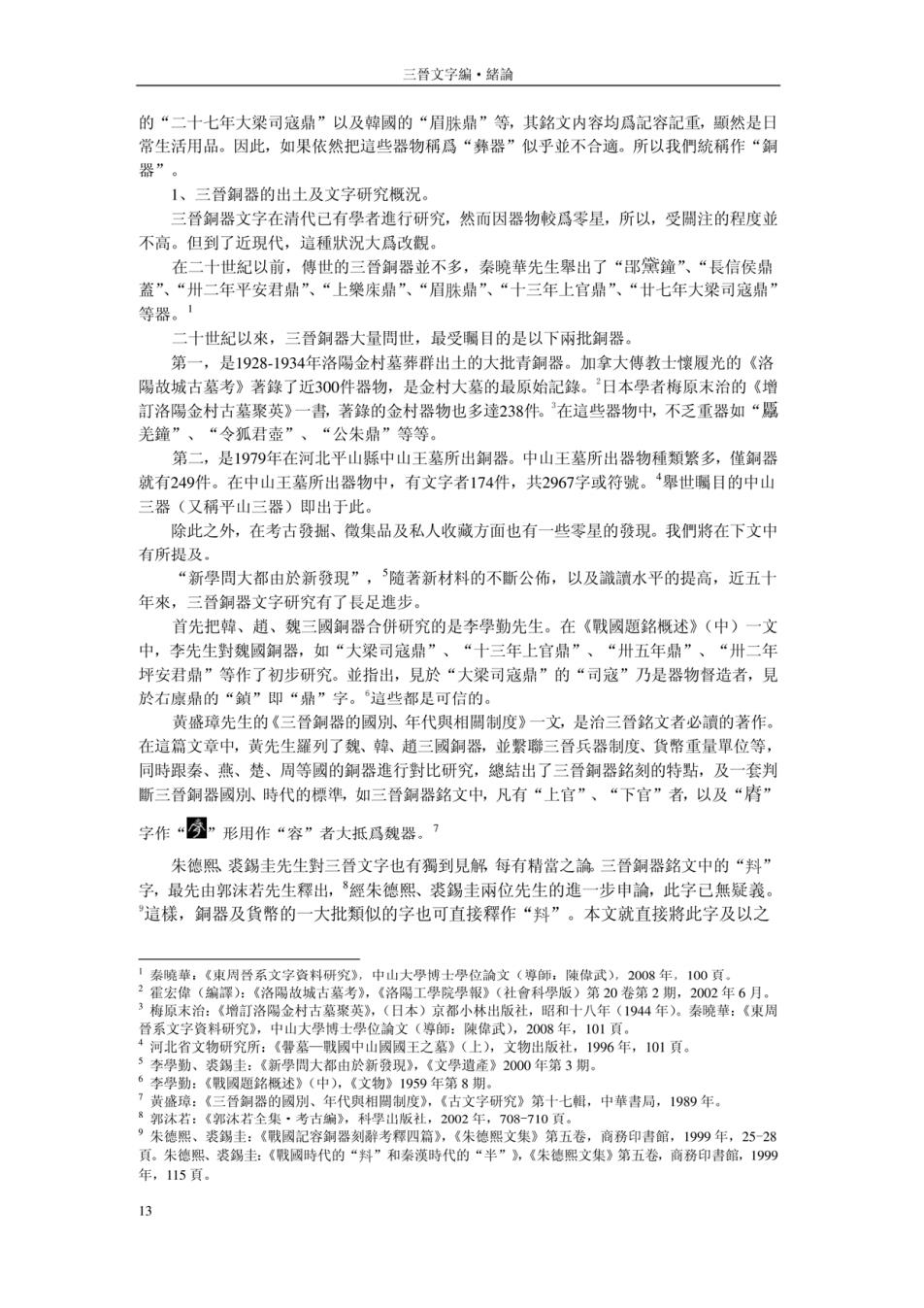
三晉文字编·緒論 的“二十七年大梁司寇鼎”以及韓國的“眉胨鼎”等,其銘文内容均爲記容記重,顯然是日 常生活用品。因此,如果依然把這些器物稱爲“彝器”似乎並不合適。所以我們統稱作“铜 器”。 1、三晉铜器的出土及文字研究概况。 三晉铜器文字在清代己有學者進行研究,然而因器物較爲零星,所以,受關注的程度並 不高。但到了近現代,這種状况大爲改觀。 在二十世紀以前,傳世的三晉銅器並不多,秦曉華先生舉出了“邵黛鐘”、“長信侯鼎 蓋”、“州二年平安君鼎”、“上樂床鼎”、“眉肤鼎”、“十三年上官鼎”、“廿七年大梁司寇鼎” 等器。1 二十世紀以來,三晉铜器大量問世,最受矚目的是以下兩批铜器。 第一,是1928-1934年洛陽金村墓葬群出土的大批青銅器。加拿大傳教士懷履光的《洛 陽故城古墓考》著錄了近300件器物,是金村大墓的最原始記錄。日本學者梅原末治的《增 訂洛陽金村古墓聚英》一書,著錄的金村器物也多達238件。在這些器物中,不乏重器如“團 羌鐘”、“令狐君壶”、“公朱鼎”等等。 第二,是1979年在河北平山縣中山王墓所出铜器。中山王墓所出器物種類繁多,僅銅器 就有249件。在中山王墓所出器物中,有文字者174件,共2967字或符號。4舉世矚目的中山 三器(又稱平山三器)即出于此。 除此之外,在考古發掘、徵集品及私人收藏方面也有一些零星的發現。我們將在下文中 有所提及。 “新學問大都由於新發現”,5隨著新材料的不断公布,以及識讀水平的提高,近五十 年來,三晉銅器文字研究有了長足進步。 首先把韓、趙、魏三國銅器合併研究的是李學勤先生。在《戰國题銘概述》(中)一文 中,李先生對魏國铜器,如“大梁司寇鼎”、“十三年上官鼎”、“州五年鼎”、“州二年 坪安君鼎”等作了初步研究。並指出,見於“大梁司寇鼎”的“司寇”乃是器物督造者,見 於右廪鼎的“鎖”即“鼎”字。這些都是可信的。 黄盛璋先生的《三晉铜器的國別、年代與相關制度》一文,是治三晉銘文者必讀的著作。 在這篇文章中,黄先生羅列了魏、韓、趙三國铜器,並繫聯三晉兵器制度、货幣重量單位等, 同時跟秦、燕、楚、周等國的铜器進行對比研究,總結出了三晉銅器銘刻的特點,及一套判 斷三晉銅器國別、時代的標準,如三晉銅器銘文中,凡有“上官”、“下官”者,以及“瘠” 字作“形用作“容”者大抵爲魏器。7 朱德熙裘錫圭先生對三晉文字也有獨到見解每有精當之論三晉銅器銘文中的“料” 字,最先由郭沫若先生釋出,8經朱德熙、裘錫圭兩位先生的進一步申論,此字已無疑義。 "這樣,銅器及貨幣的一大批類似的字也可直接釋作“料”。本文就直接將此字及以之 「秦曉華:《東周骨系文字資料研究》,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陳做武),2008年,100真。 2霍宏偉(编譯):《洛陽故城古墓考》,《洛陽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0卷第2期,2002年6月。 3梅原末治:《增訂洛陽金村古墓聚英》,(日本)京都小林出版社,昭和十八年(1944年)。秦晓華:《東周 晉系文字資料研究》,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陕偉武),2008年,101頁。 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婴墓一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6年,101真。 5李學勤、裘錫圭:《新孕問大都由於新發現》,《文學遭產》2000年第3期。 6李學勤:《戰國题銘概述》(中),《文物》1959年第8期。 7黄盛璋:《三晉铜器的國別、年代與相闋制度》,《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中華書局,1989年。 8郭沐若:《郭沐若全集·考古编》,科學山版社,2002年,708-710真。 9朱德熙、裘錫圭:《戰國記容铜器刻辭考四篇》,《朱德熙文集》第五卷,商務印書館,1999年,25-28 頁。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時代的“料”和秦漢時代的“半”》,《朱德熙文集》第五卷,商務印書館,1999 年,115頁。 13

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爲偏旁的字徑釋作“料”或从“料”。 唐蘭先生對金村墓葬的國別、“愿羌鐘”年代等的考證,最終解决了此墓葬國別及“屬 羌鐘”年代問题。李家浩先生對“向”字的分析,使得三晉文字中的“向”字有了着落。2 吳振武先生對中山器“崩(也)”字的考證有助於對此字的理解。3 此外,有學者嘗試從文字書體及寫法的地域特點入手,考證器物的國別。近年來在 這方面做得比較出色的是吳良寶先生。他的《戰國金文考釋兩篇》一文的第一部分,利 用新出的“湏脒鼎”“襄”字及其他國家“襄”字的不同寫法指出,金文中“襄”字作 “圄”形者一般爲魏器:作“”形,内部寫法改造成“羊”字的一般是趙器:从“支” 作“置”形的則是韓國特有的寫法。拔此可知,《罩彙》0004、0077、0125、3134,《陶彙》 9·50均是趙國之物。而《集成》2303、11565等則是韓國器物。這給我們判断器物國別提 供了新的方法和依據。此外,根據器物所記載的度量衡數值,亦可作爲判断銅器國別的標尺。 有些學者則對古文字中的“府”及“春”字作了專門考察。6 目前,三晉文字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下面我們分國進行概述。 三晉銅器銘文以記容記重爲主,同時,也有不少職官名。對此,我們不作深入探討,一 則,已有學者作過很好的概述及研究。其次,鑒于本文研究的篦疇,我們將把側重點放在 文字研究上。 1、趙國銅器銘文研究舉要 趙國銅器極罕見,目前所知,僅有“十一年庫嗇夫鼎”、“土勻绅”、“智君子鑑”(兩 件)、“趙孟介壺”、“四年昌國鼎”、“上尔床鼎”及“六年相室趙婴鼎”等。 (1)、“十一年庫嗇夫鼎”(《集成》2608)中的“翊”和“所爲”、“空”字 “翊”字異說頗多,迄今有釋作“命”讀作“令”的、有隸作“途”的、有釋作“命” 的、有釋作“等”讀作“令”的、有釋作“令”的、也有作不識字處理的。8董珊先生在其 博士論文裹把這個字隸作“翊”,無說。9 “第原作。 形 三晋文字“命”字一般作“ ”形,奥 字區別明顯。 而三晉文字“吊”字一般作“ (《集成》4663“哀成叔豆”)形,也有作“伤” (《型彙》 ·唐蘭:《甌羌鍾考釋》,故宫博物院编:《唐蘭先生金文論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1頁。 2李家浩:《戰國货幣考(七篇)》“邮布考”,李家浩:《著名中青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安徽 教有出版社,2002年。 3吳振武:《試說平山戰國中山王墓铜器銘文中的“前”字》,《中國文字學報》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6 年,73頁。 4吳良寶:《戰因金文考釋雨篇》,《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2期。 5參看黄盛璋:《就論三晉兵器的國别和年代及其相调周题》,《考古學報》1974年第1期。唐友波:《春成 侯盃與長子盃综合研究》,《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八朝,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李家浩:《談春成侯盃 與少府盉的铭文及其容量》,《華學》第五朝,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唐友波:《新見洹蛛鼎小識》,《上 海博物館集刊》第九解,上海書责出版社,2002年。秦曉華:《束周晉系文字資料研究》,中山大學2008 年博士學位論文(導師:陳偉武),114頁。 6王輝:《戰國“府”之考察》,《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一紀念夏頭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87 年。王人聪:《戰國記容銅器刻銘“将”字試釋》,《江漠考古》,1991年第1期。 7秦晚華:《束周晉系文字資料研究》,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御:陳你武),2008年,16-31、102-106 页。 8李刚:《三晉系記容配重銅器銘文集釋》,吉林大學硕士學位論文(導師:吳振武),2005年,87頁。 9董珊:《戰國题銘奥工官制度》,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尊師:李零),2002年,51頁。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