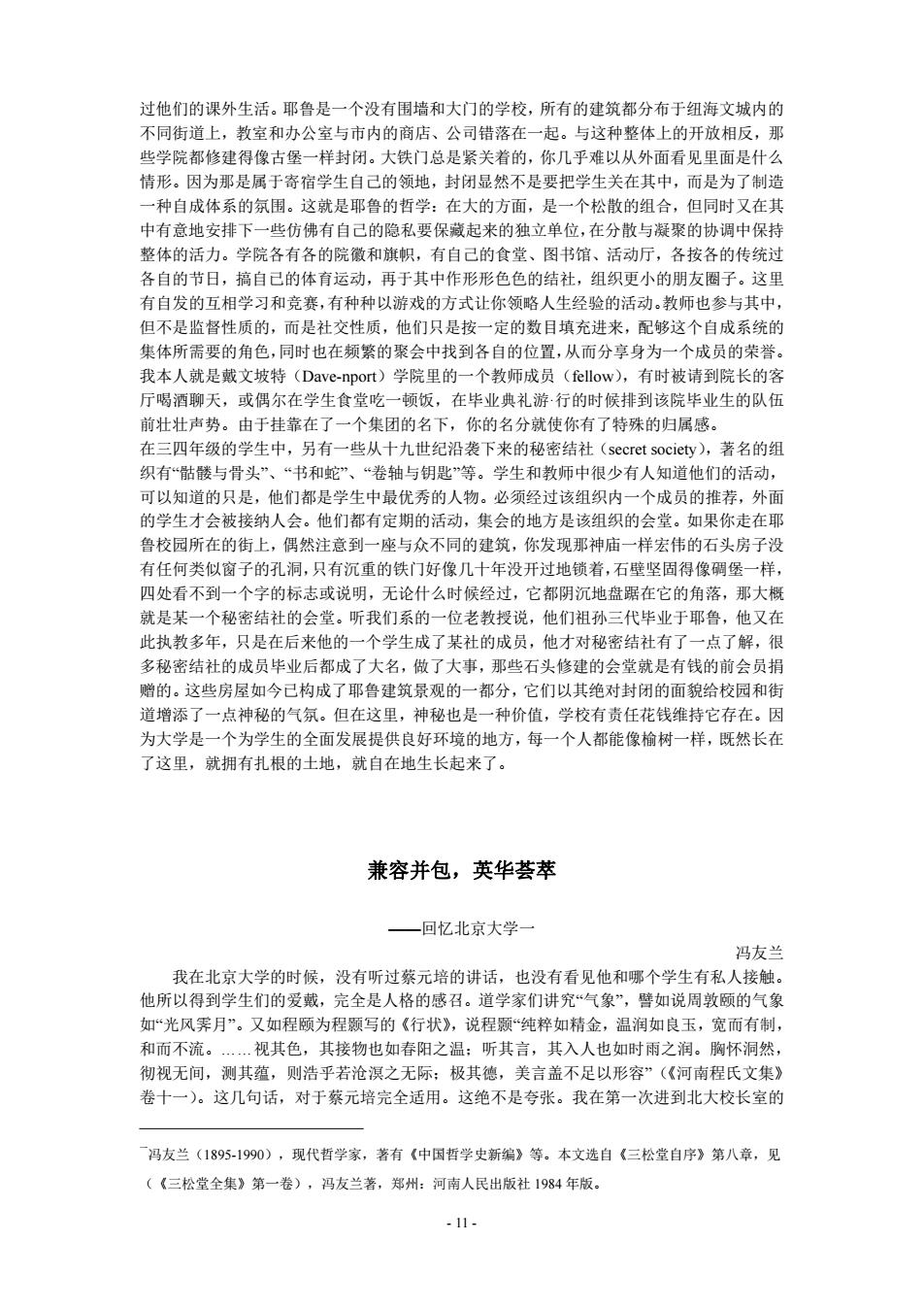
过他们的课外生活。耶鲁是一个没有围墙和大门的学校,所有的建筑都分布于纽海文城内的 不同街道上,教室和办公室与市内的商店、公司错落在一起。与这种整体上的开放相反,那 些学院都修建得像古堡一样封闭。大铁门总是紧关着的,你几乎难以从外面看见里面是什么 情形。因为那是属于寄宿学生自己的领地,封闭显然不是要把学生关在其中,而是为了制造 一种自成体系的氛围。这就是耶鲁的哲学:在大的方面,是一个松散的组合,但同时又在其 中有意地安排下一些仿佛有自己的隐私要保藏起来的独立单位,在分散与凝聚的协调中保持 整体的活力。学院各有各的院徽和旗帜,有自己的食堂、图书馆、活动厅,各按各的传统过 各自的节日,搞自己的体育运动,再于其中作形形色色的结社,组织更小的朋友圈子。这里 有自发的互相学习和竞赛,有种种以游戏的方式让你领略人生经验的活动。教师也参与其中, 但不是监督性质的,而是社交性质,他们只是按一定的数目填充进来,配够这个自成系统的 集体所需要的角色,同时也在频繁的聚会中找到各自的位置,从而分享身为一个成员的荣誉。 我本人就是戴文坡特(Dave-nport)学院里的一个教师成员(fellow),有时被请到院长的客 厅喝酒聊天,或偶尔在学生食堂吃一顿饭,在毕业典礼游行的时候排到该院毕业生的队伍 前壮壮声势。由于挂靠在了一个集团的名下,你的名分就使你有了特殊的归属感。 在三四年级的学生中,另有一些从十九世纪沿袭下来的秘密结社(secret society),著名的组 织有“骷髅与骨头”、“书和蛇”、“卷轴与钥匙等。学生和教师中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活动, 可以知道的只是,他们都是学生中最优秀的人物。必须经过该组织内一个成员的推荐,外面 的学生才会被接纳人会。他们都有定期的活动,集会的地方是该组织的会堂。如果你走在耶 鲁校园所在的街上,偶然注意到一座与众不同的建筑,你发现那神庙一样宏伟的石头房子没 有任何类似窗子的孔洞,只有沉重的铁门好像几十年没开过地锁着,石壁坚固得像碉堡一样, 四处看不到一个字的标志或说明,无论什么时候经过,它都阴沉地盘踞在它的角落,那大概 就是某一个秘密结社的会堂。听我们系的一位老教授说,他们祖孙三代毕业于耶鲁,他又在 此执教多年,只是在后来他的一个学生成了某社的成员,他才对秘密结社有了一点了解,很 多秘密结社的成员毕业后都成了大名,做了大事,那些石头修建的会堂就是有钱的前会员捐 赠的。这些房屋如今已构成了耶鲁建筑景观的一都分,它们以其绝对封闭的面貌给校园和街 道增添了一点神秘的气氛。但在这里,神秘也是一种价值,学校有贵任花钱维持它存在。因 为大学是一个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环境的地方,每一个人都能像榆树一样,既然长在 了这里,就拥有扎根的土地,就自在地生长起来了。 兼容并包,英华荟萃 一回忆北京大学一 冯友兰 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 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顾的气象 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 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 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 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 「冯友兰(1895-1990),现代哲学家,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等。本文选自《三松堂自序》第八章,见 (《三松堂全集》第一卷),冯友兰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
- 11 - 过他们的课外生活。耶鲁是一个没有围墙和大门的学校,所有的建筑都分布于纽海文城内的 不同街道上,教室和办公室与市内的商店、公司错落在一起。与这种整体上的开放相反,那 些学院都修建得像古堡一样封闭。大铁门总是紧关着的,你几乎难以从外面看见里面是什么 情形。因为那是属于寄宿学生自己的领地,封闭显然不是要把学生关在其中,而是为了制造 一种自成体系的氛围。这就是耶鲁的哲学:在大的方面,是一个松散的组合,但同时又在其 中有意地安排下一些仿佛有自己的隐私要保藏起来的独立单位,在分散与凝聚的协调中保持 整体的活力。学院各有各的院徽和旗帜,有自己的食堂、图书馆、活动厅,各按各的传统过 各自的节日,搞自已的体育运动,再于其中作形形色色的结社,组织更小的朋友圈子。这里 有自发的互相学习和竞赛,有种种以游戏的方式让你领略人生经验的活动。教师也参与其中, 但不是监督性质的,而是社交性质,他们只是按一定的数目填充进来,配够这个自成系统的 集体所需要的角色,同时也在频繁的聚会中找到各自的位置,从而分享身为一个成员的荣誉。 我本人就是戴文坡特(Dave-nport)学院里的一个教师成员(fellow),有时被请到院长的客 厅喝酒聊天,或偶尔在学生食堂吃一顿饭,在毕业典礼游·行的时候排到该院毕业生的队伍 前壮壮声势。由于挂靠在了一个集团的名下,你的名分就使你有了特殊的归属感。 在三四年级的学生中,另有一些从十九世纪沿袭下来的秘密结社(secret society),著名的组 织有“骷髅与骨头”、“书和蛇”、“卷轴与钥匙”等。学生和教师中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活动, 可以知道的只是,他们都是学生中最优秀的人物。必须经过该组织内一个成员的推荐,外面 的学生才会被接纳人会。他们都有定期的活动,集会的地方是该组织的会堂。如果你走在耶 鲁校园所在的街上,偶然注意到一座与众不同的建筑,你发现那神庙一样宏伟的石头房子没 有任何类似窗子的孔洞,只有沉重的铁门好像几十年没开过地锁着,石壁坚固得像碉堡一样, 四处看不到一个字的标志或说明,无论什么时候经过,它都阴沉地盘踞在它的角落,那大概 就是某一个秘密结社的会堂。听我们系的一位老教授说,他们祖孙三代毕业于耶鲁,他又在 此执教多年,只是在后来他的一个学生成了某社的成员,他才对秘密结社有了一点了解,很 多秘密结社的成员毕业后都成了大名,做了大事,那些石头修建的会堂就是有钱的前会员捐 赠的。这些房屋如今已构成了耶鲁建筑景观的一都分,它们以其绝对封闭的面貌给校园和街 道增添了一点神秘的气氛。但在这里,神秘也是一种价值,学校有责任花钱维持它存在。因 为大学是一个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环境的地方,每一个人都能像榆树一样,既然长在 了这里,就拥有扎根的土地,就自在地生长起来了。 兼容并包,英华荟萃 ——回忆北京大学一 冯友兰 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 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 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 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 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 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 一冯友兰(1895-1990),现代哲学家,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等。本文选自《三松堂自序》第八章,见 (《三松堂全集》第一卷),冯友兰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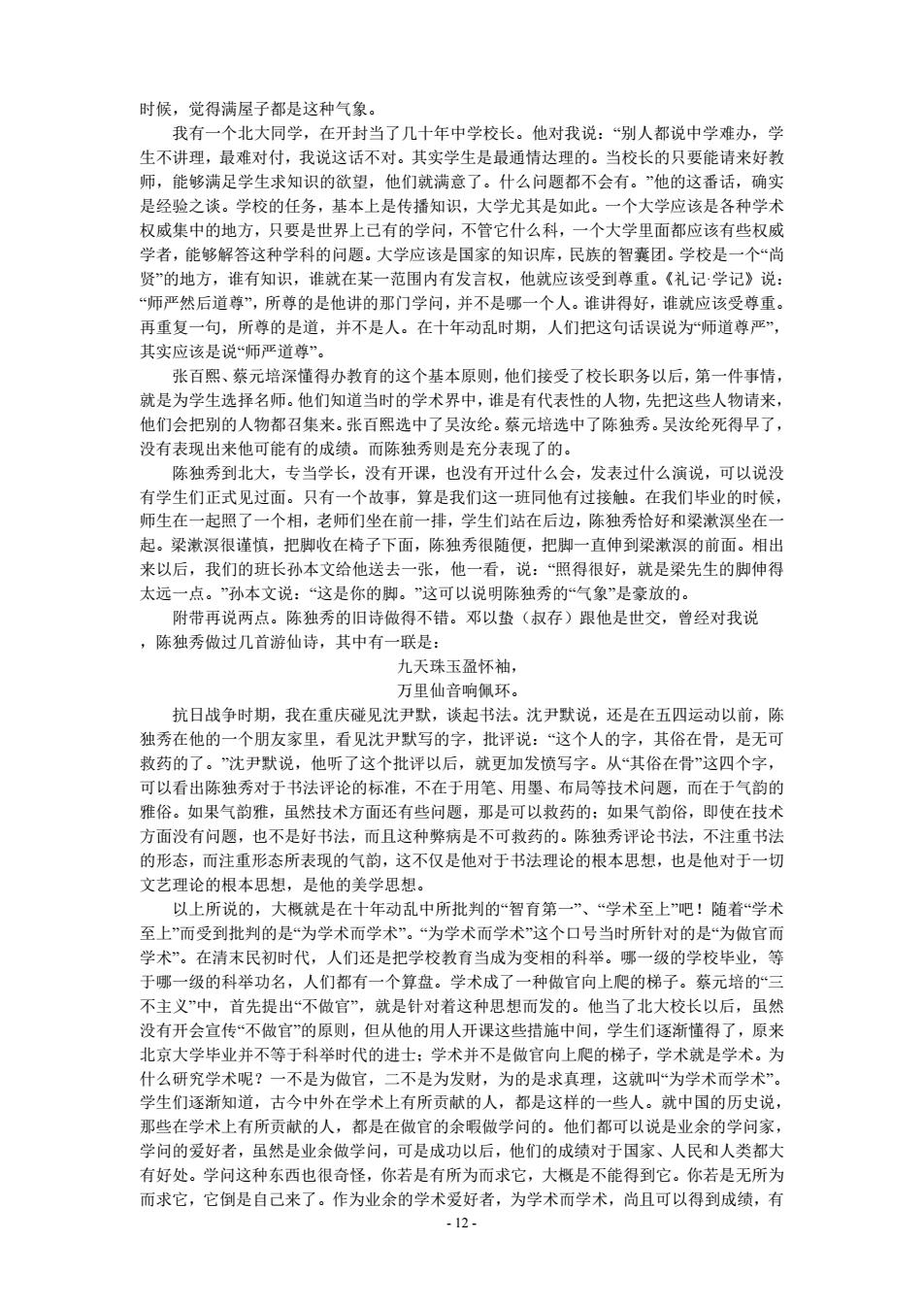
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我有一个北大同学,在开封当了几十年中学校长。他对我说:“别人都说中学难办,学 生不讲理,最难对付,我说这话不对。其实学生是最通情达理的。当校长的只要能请来好教 师,能够满足学生求知识的欲望,他们就满意了。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的这番话,确实 是经验之谈。学校的任务,基本上是传播知识,大学尤其是如此。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学术 权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己有的学问,不管它什么科,一个大学里面都应该有些权威 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的问题。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 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礼记·学记》说: “师严然后道尊”,所尊的是他讲的那门学问,并不是哪一个人。谁讲得好,谁就应该受尊重。 再重复一句,所尊的是道,并不是人。在十年动乱时期,人们把这句话误说为师道尊严”, 其实应该是说“师严道尊”。 张百熙、蔡元培深懂得办教育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接受了校长职务以后,第一件事情, 就是为学生选择名师。他们知道当时的学术界中,谁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这些人物请来, 他们会把别的人物都召集来。张百熙选中了吴汝纶。蔡元培选中了陈独秀。吴汝纶死得早了, 没有表现出来他可能有的成绩。而陈独秀则是充分表现了的。 陈独秀到北大,专当学长,没有开课,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发表过什么演说,可以说没 有学生们正式见过面。只有一个故事,算是我们这一班同他有过接触。在我们毕业的时候, 师生在一起照了一个相,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 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随便,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出 来以后,我们的班长孙本文给他送去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 太远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这可以说明陈独秀的气象”是豪放的。 附带再说两点。陈独秀的旧诗做得不错。邓以蛰(叔存)跟他是世交,曾经对我说 ,陈独秀做过几首游仙诗,其中有一联是: 九天珠玉盈怀袖, 万里仙音响佩环。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碰见沈尹默,谈起书法。沈尹默说,还是在五四运动以前,陈 独秀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看见沈尹默写的字,批评说:“这个人的字,其俗在骨,是无可 救药的了。”沈尹默说,他听了这个批评以后,就更加发愤写字。从“其俗在骨”这四个字, 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于书法评论的标准,不在于用笔、用墨、布局等技术问题,而在于气韵的 雅俗。如果气韵雅,虽然技术方面还有些问题,那是可以救药的:如果气韵俗,即使在技术 方面没有问题,也不是好书法,而且这种弊病是不可救药的。陈独秀评论书法,不注重书法 的形态,而注重形态所表现的气韵,这不仅是他对于书法理论的根本思想,也是他对于一切 文艺理论的根本思想,是他的美学思想。 以上所说的,大概就是在十年动乱中所批判的“智育第一”、“学术至上”吧!随着“学术 至上”而受到批判的是“为学术而学术”。“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口号当时所针对的是“为做官而 学术”。在清末民初时代,人们还是把学校教育当成为变相的科举。哪一级的学校毕业,等 于哪一级的科举功名,人们都有一个算盘。学术成了一种做官向上爬的梯子。蔡元培的“三 不主义”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针对着这种思想而发的。他当了北大校长以后,虽然 没有开会宣传“不做官”的原则,但从他的用人开课这些措施中间,学生们逐渐懂得了,原来 北京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时代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 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 学生们逐渐知道,古今中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这样的一些人。就中国的历史说, 那些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在做官的余暇做学问的。他们都可以说是业余的学问家, 学问的爱好者,虽然是业余做学问,可是成功以后,他们的成绩对于国家、人民和人类都大 有好处。学问这种东西也很奇怪,你若是有所为而求它,大概是不能得到它。你若是无所为 而求它,它倒是自己来了。作为业余的学术爱好者,为学术而学术,尚且可以得到成绩,有 -12-
- 12 - 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我有一个北大同学,在开封当了几十年中学校长。他对我说:“别人都说中学难办,学 生不讲理,最难对付,我说这话不对。其实学生是最通情达理的。当校长的只要能请来好教 师,能够满足学生求知识的欲望,他们就满意了。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的这番话,确实 是经验之谈。学校的任务,基本上是传播知识,大学尤其是如此。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学术 权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学问,不管它什么科,一个大学里面都应该有些权威 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的问题。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 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礼记·学记》说: “师严然后道尊”,所尊的是他讲的那门学问,并不是哪一个人。谁讲得好,谁就应该受尊重。 再重复一句,所尊的是道,并不是人。在十年动乱时期,人们把这句话误说为“师道尊严”, 其实应该是说“师严道尊”。 张百熙、蔡元培深懂得办教育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接受了校长职务以后,第一件事情, 就是为学生选择名师。他们知道当时的学术界中,谁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这些人物请来, 他们会把别的人物都召集来。张百熙选中了吴汝纶。蔡元培选中了陈独秀。吴汝纶死得早了, 没有表现出来他可能有的成绩。而陈独秀则是充分表现了的。 陈独秀到北大,专当学长,没有开课,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发表过什么演说,可以说没 有学生们正式见过面。只有一个故事,算是我们这一班同他有过接触。在我们毕业的时候, 师生在一起照了一个相,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 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随便,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出 来以后,我们的班长孙本文给他送去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 太远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这可以说明陈独秀的“气象”是豪放的。 附带再说两点。陈独秀的旧诗做得不错。邓以蛰(叔存)跟他是世交,曾经对我说 ,陈独秀做过几首游仙诗,其中有一联是: 九天珠玉盈怀袖, 万里仙音响佩环。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碰见沈尹默,谈起书法。沈尹默说,还是在五四运动以前,陈 独秀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看见沈尹默写的字,批评说:“这个人的字,其俗在骨,是无可 救药的了。”沈尹默说,他听了这个批评以后,就更加发愤写字。从“其俗在骨”这四个字, 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于书法评论的标准,不在于用笔、用墨、布局等技术问题,而在于气韵的 雅俗。如果气韵雅,虽然技术方面还有些问题,那是可以救药的;如果气韵俗,即使在技术 方面没有问题,也不是好书法,而且这种弊病是不可救药的。陈独秀评论书法,不注重书法 的形态,而注重形态所表现的气韵,这不仅是他对于书法理论的根本思想,也是他对于一切 文艺理论的根本思想,是他的美学思想。 以上所说的,大概就是在十年动乱中所批判的“智育第一”、“学术至上”吧!随着“学术 至上”而受到批判的是“为学术而学术”。“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口号当时所针对的是“为做官而 学术”。在清末民初时代,人们还是把学校教育当成为变相的科举。哪一级的学校毕业,等 于哪一级的科举功名,人们都有一个算盘。学术成了一种做官向上爬的梯子。蔡元培的“三 不主义”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针对着这种思想而发的。他当了北大校长以后,虽然 没有开会宣传“不做官”的原则,但从他的用人开课这些措施中间,学生们逐渐懂得了,原来 北京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时代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 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 学生们逐渐知道,古今中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这样的一些人。就中国的历史说, 那些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在做官的余暇做学问的。他们都可以说是业余的学问家, 学问的爱好者,虽然是业余做学问,可是成功以后,他们的成绩对于国家、人民和人类都大 有好处。学问这种东西也很奇怪,你若是有所为而求它,大概是不能得到它。你若是无所为 而求它,它倒是自己来了。作为业余的学术爱好者,为学术而学术,尚且可以得到成绩,有

所贡献。如果有人能够把为学术而学术作为本业,那他的成绩必定更好,贡献必定更大。 在十年动乱时期,还批判了所谓“教授治校”。这也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 其目的也是调动教授们的积极性,叫他们在大学中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之感。当时的具体办 法之一,是民主选举教务长。照当时的制度,校长之下,有两个长:一个是总务长,管理学 校的一般行政事务:一个是教务长,管理教学科研方面的事务。蔡元培规定,教务长由教授 选举,每两年改选一次。我在北大的时候,以学生的地位,还不很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究竞 是怎么个治法。后来到了清华,以教授的地位,才进一步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的精神。 教授之所以为教授,在于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在他本行中是个权威,并不在于他在政 治上有什么主张。譬如辜鸿铭,在民国己经成立了几年之后,还是带着辫子,穿着清朝衣冠, 公开主张帝制。但是他的英文水平很高,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请他教英文。这在蔡元培到 校以前就是事实。蔡元培到校后不但没有改变这个事实,还又加聘了一个反动人物,就是刘 师培(申叔)。刘师培出身于一个讲汉学的旧家,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学,说是留学,实际 上是在东京讲中国学问。那时候,在东京这样的人不少,章太炎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在东 京,这样的人中,比较年轻的都以章太炎为师,刘师培却是独立讲学的。这样的人也都受孙 中山的影响,大多数赞成同盟会。刘师培也是如此。袁世凯计划篡国称帝的时候,为了制造 舆论,办了一个“筹安会”,宣传只有实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国转危为安。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 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其中学术界有两个名人,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在袁世 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 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 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 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他没有上几课,就病逝了。这就是所谓“兼容 并包”。 金岳霖先生一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 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关 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 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去,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 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晴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 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 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 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一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 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 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 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 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一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 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 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 汪曾祺(1920-1997),当代作家,著有小说《受戒》等。本文选自《中国当代散文检阅》(名家卷),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
- 13 - 所贡献。如果有人能够把为学术而学术作为本业,那他的成绩必定更好,贡献必定更大。 在十年动乱时期,还批判了所谓“教授治校”。这也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 其目的也是调动教授们的积极性,叫他们在大学中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之感。当时的具体办 法之一,是民主选举教务长。照当时的制度,校长之下,有两个长:一个是总务长,管理学 校的一般行政事务;一个是教务长,管理教学科研方面的事务。蔡元培规定,教务长由教授 选举,每两年改选一次。我在北大的时候,以学生的地位,还不很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究竟 是怎么个治法。后来到了清华,以教授的地位,才进一步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的精神。 教授之所以为教授,在于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在他本行中是个权威,并不在于他在政 治上有什么主张。譬如辜鸿铭,在民国已经成立了几年之后,还是带着辫子,穿着清朝衣冠, 公开主张帝制。但是他的英文水平很高,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请他教英文。这在蔡元培到 校以前就是事实。蔡元培到校后不但没有改变这个事实,还又加聘了一个反动人物,就是刘 师培(申叔)。刘师培出身于一个讲汉学的旧家,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学,说是留学,实际 上是在东京讲中国学问。那时候,在东京这样的人不少,章太炎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在东 京,这样的人中,比较年轻的都以章太炎为师,刘师培却是独立讲学的。这样的人也都受孙 中山的影响,大多数赞成同盟会。刘师培也是如此。袁世凯计划篡国称帝的时候,为了制造 舆论,办了一个“筹安会”,宣传只有实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国转危为安。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 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其中学术界有两个名人,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在袁世 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 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 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 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他没有上几课,就病逝了。这就是所谓“兼容 并包”。 金岳霖先生一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 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关 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 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去,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 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 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 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 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 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 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 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 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 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 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 一汪曾祺(1920-1997),当代作家,著有小说《受戒》等。本文选自《中国当代散文检阅》(名家卷),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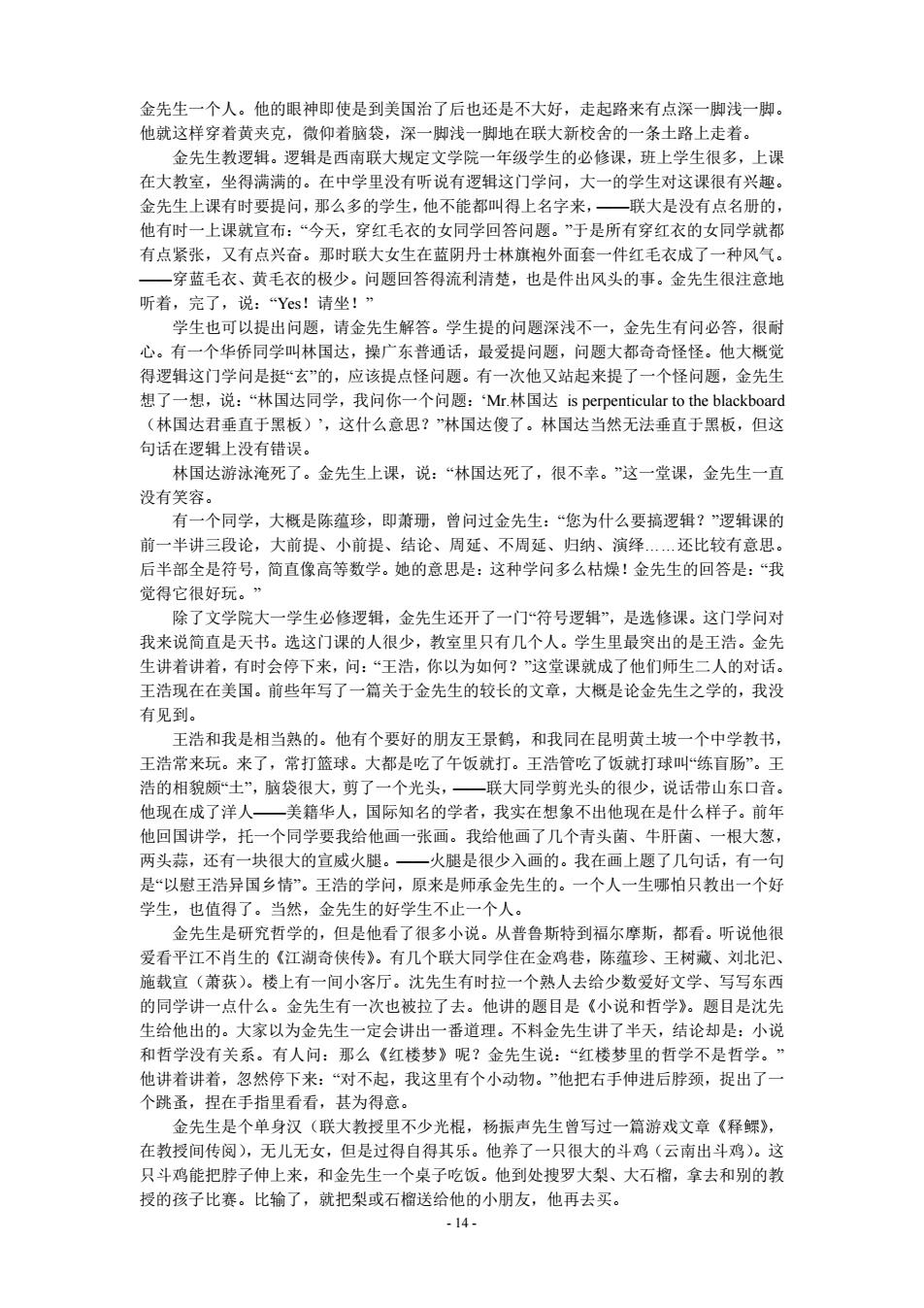
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 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 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 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一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 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 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 一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 听着,完了,说:“Y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 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 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 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 (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 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 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 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 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 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逻辑,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 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 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大概是论金先生之学的,我没 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书, 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 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一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 他现在成了洋人一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 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 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一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 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 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 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 施载宣(萧荻)。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 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 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 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 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鳏》, 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 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 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14-
- 14 - 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 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 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 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 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 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 ——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 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 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 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 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 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 (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 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 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 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 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 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逻辑,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 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 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大概是论金先生之学的,我没 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书, 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 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 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 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 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 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 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 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 施载宣(萧荻)。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 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 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 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 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鳏》, 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 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 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家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 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 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 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 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 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己经八十岁了, 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我 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 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金先生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 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须问王浩。 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 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 本章词语 1.大学: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学校,却又不时被人类视作文化高地上的精神堡垒。北 京大学的校史,最早可追溯到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欧洲大学则始于12世纪,最早的 有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 2.狷介:洁身自好,有气节,必有所不为,更不屑同流合污。《论语·子路》中的“狂 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便是此意。当你无力挽浊世于横流,就把手插在口袋,不去浑水 摸鱼,而为坊间留一份清白,也近“狷介”。 3.气象:这不是对暑寒阴晴、风云雾霜等大气物理现象的统称,而是对蔡元培、金岳霖等 大师的精神襟怀的一种命名,它似介于无形与有形之间,它内敛,无意张扬,却更诱人从这 静穆中读出“大音希声”。 圆桌议题 1.金耀基明知“雾里的剑桥,也许不真”,却又写得如此传神且传奇,当源自剑桥的“美 的神秘”。请试述文中的剑桥为何竞“美”得“神秘”? 2.望细深体悟你所就读的大学校园,是否也有值得你珍视的剑桥式的传奇、耶鲁式的 狷介或北大式的遗韵呢? 链接 1.刘琅、桂岑主编:《大学的精神》,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一年版。 2.甘阳、李猛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大学之道丛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夏中义、丁东主编:《大学人文》丛刊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版。 5.《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1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1996年版。 6.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7.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胡适:《中国公学18年级毕业赠言》,见《不朽的 声音一一世界经典演讲》,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 -15-
- 15 -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家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 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 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 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 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 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 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我 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 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金先生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 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须问王浩。 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 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 本章词语 1.大学: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学校,却又不时被人类视作文化高地上的精神堡垒。北 京大学的校史,最早可追溯到 1898 年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欧洲大学则始于 12 世纪,最早的 有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 2.狷介:洁身自好,有气节,必有所不为,更不屑同流合污。《论语·子路》中的“狂 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便是此意。当你无力挽浊世于横流,就把手插在口袋,不去浑水 摸鱼,而为坊间留一份清白,也近“狷介”。 3.气象:这不是对暑寒阴晴、风云雾霜等大气物理现象的统称,而是对蔡元培、金岳霖等 大师的精神襟怀的一种命名,它似介于无形与有形之间,它内敛,无意张扬,却更诱人从这 静穆中读出“大音希声”。 圆桌议题 1.金耀基明知“雾里的剑桥,也许不真”,却又写得如此传神且传奇,当源自剑桥的“美 的神秘”。请试述文中的剑桥为何竟“美”得“神秘”? 2.望细深体悟你所就读的大学校园,是否也有值得你珍视的剑桥式的传奇、耶鲁式的 狷介或北大式的遗韵呢? 链接 1.刘琅、桂岑主编:《大学的精神》,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一年版。 2.甘阳、李猛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3.《大学之道丛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4.夏中义、丁东主编:《大学人文》丛刊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版。 5.《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 1 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1996 年版。 6.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7.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胡适:《中国公学 18 年级毕业赠言》,见《不朽的 声音——世界经典演讲》,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0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