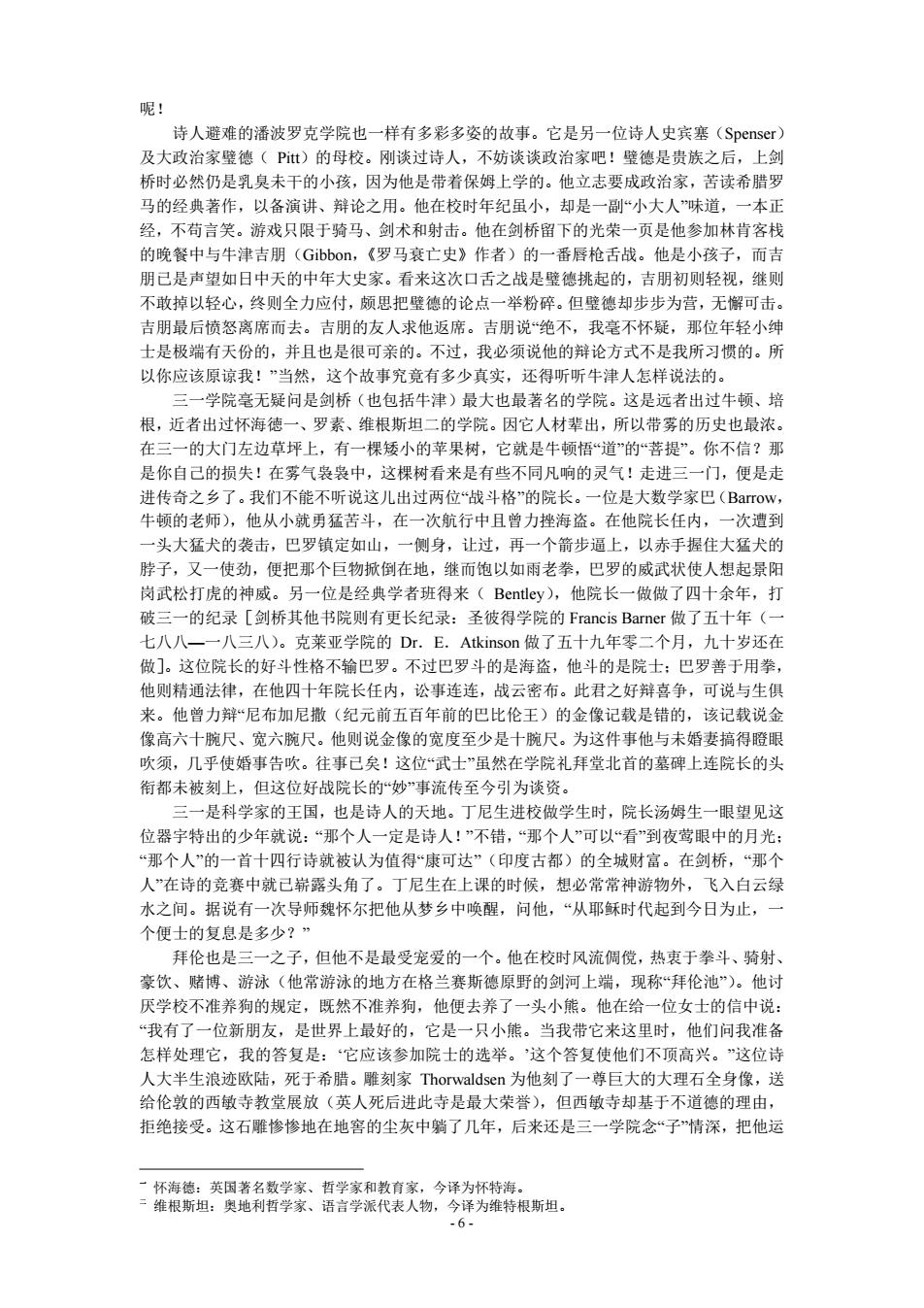
呢! 诗人避难的潘波罗克学院也一样有多彩多姿的故事。它是另一位诗人史宾塞(Spenser) 及大政治家璧德(Pt)的母校。刚谈过诗人,不妨谈谈政治家吧!璧德是贵族之后,上剑 桥时必然仍是乳臭未干的小孩,因为他是带着保姆上学的。他立志要成政治家,苦读希腊罗 马的经典著作,以备演讲、辩论之用。他在校时年纪虽小,却是一副“小大人味道,一本正 经,不苟言笑。游戏只限于骑马、剑术和射击。他在剑桥留下的光荣一页是他参加林肯客栈 的晚餐中与牛津吉朋(Gibbor,《罗马衰亡史》作者)的一番唇枪舌战。他是小孩子,而吉 朋己是声望如日中天的中年大史家。看来这次口舌之战是璧德挑起的,吉朋初则轻视,继则 不敢掉以轻心,终则全力应付,颇思把璧德的论点一举粉碎。但璧德却步步为营,无懈可击。 吉朋最后愤怒离席而去。吉朋的友人求他返席。吉朋说“绝不,我毫不怀疑,那位年轻小绅 士是极端有天份的,并且也是很可亲的。不过,我必须说他的辩论方式不是我所习惯的。所 以你应该原谅我!”当然,这个故事究竞有多少真实,还得听听牛津人怎样说法的。 三一学院毫无疑问是剑桥(也包括牛津)最大也最著名的学院。这是远者出过牛顿、培 根,近者出过怀海德一、罗素、维根斯坦二的学院。因它人材辈出,所以带雾的历史也最浓。 在三一的大门左边草坪上,有一棵矮小的苹果树,它就是牛顿悟“道”的“菩提”。你不信?那 是你自己的损失!在雾气袅袅中,这棵树看来是有些不同凡响的灵气!走进三一门,便是走 进传奇之乡了。我们不能不听说这儿出过两位“战斗格”的院长。一位是大数学家巴(Barrow, 牛顿的老师),他从小就勇猛苦斗,在一次航行中且曾力挫海盗。在他院长任内,一次遭到 一头大猛犬的袭击,巴罗镇定如山,一侧身,让过,再一个箭步逼上,以赤手握住大猛犬的 脖子,又一使劲,便把那个巨物掀倒在地,继而饱以如雨老拳,巴罗的威武状使人想起景阳 岗武松打虎的神威。另一位是经典学者班得来(Bentley),他院长一做做了四十余年,打 破三一的纪录[剑桥其他书院则有更长纪录:圣彼得学院的Francis Barner做了五十年(一 七八八一一八三八)。克莱亚学院的Dr.E.Atkinson做了五十九年零二个月,九十岁还在 做]。这位院长的好斗性格不输巴罗。不过巴罗斗的是海盗,他斗的是院士:巴罗善于用拳, 他则精通法律,在他四十年院长任内,讼事连连,战云密布。此君之好辩喜争,可说与生俱 来。他曾力辩“尼布加尼撒(纪元前五百年前的巴比伦王)的金像记载是错的,该记载说金 像高六十腕尺、宽六腕尺。他则说金像的宽度至少是十腕尺。为这件事他与未婚妻搞得瞪眼 吹须,几乎使婚事告吹。往事已矣!这位“武士”虽然在学院礼拜堂北首的墓碑上连院长的头 衔都未被刻上,但这位好战院长的“妙”事流传至今引为谈资。 三一是科学家的王国,也是诗人的天地。丁尼生进校做学生时,院长汤姆生一眼望见这 位器宇特出的少年就说:“那个人一定是诗人!”不错,“那个人”可以“看”到夜莺眼中的月光: “那个人”的一首十四行诗就被认为值得“康可达”(印度古都)的全城财富。在剑桥,“那个 人”在诗的竞赛中就已崭露头角了。丁尼生在上课的时候,想必常常神游物外,飞入白云绿 水之间。据说有一次导师魏怀尔把他从梦乡中唤醒,问他,“从耶稣时代起到今日为止,一 个便士的复息是多少?” 拜伦也是三一之子,但他不是最受宠爱的一个。他在校时风流倜傥,热衷于拳斗、骑射、 豪饮、赌博、游泳(他常游泳的地方在格兰赛斯德原野的剑河上端,现称“拜伦池”)。他讨 厌学校不准养狗的规定,既然不准养狗,他便去养了一头小熊。他在给一位女士的信中说: “我有了一位新朋友,是世界上最好的,它是一只小熊。当我带它来这里时,他们问我准备 怎样处理它,我的答复是:它应该参加院士的选举。这个答复使他们不顶高兴。”这位诗 人大半生浪迹欧陆,死于希腊。雕刻家Thorwaldsen为他刻了一尊巨大的大理石全身像,送 给伦敦的西敏寺教堂展放(英人死后进此寺是最大荣誉),但西敏寺却基于不道德的理由, 拒绝接受。这石雕惨惨地在地窖的尘灰中躺了几年,后来还是三一学院念“子情深,把他运 一怀海德: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今译为怀特海。 二维根斯坦:奥地利哲学家、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今译为维特根斯坦。 -6-
- 6 - 呢! 诗人避难的潘波罗克学院也一样有多彩多姿的故事。它是另一位诗人史宾塞(Spenser) 及大政治家璧德( Pitt)的母校。刚谈过诗人,不妨谈谈政治家吧!璧德是贵族之后,上剑 桥时必然仍是乳臭未干的小孩,因为他是带着保姆上学的。他立志要成政治家,苦读希腊罗 马的经典著作,以备演讲、辩论之用。他在校时年纪虽小,却是一副“小大人”味道,一本正 经,不苟言笑。游戏只限于骑马、剑术和射击。他在剑桥留下的光荣一页是他参加林肯客栈 的晚餐中与牛津吉朋(Gibbon,《罗马衰亡史》作者)的一番唇枪舌战。他是小孩子,而吉 朋已是声望如日中天的中年大史家。看来这次口舌之战是璧德挑起的,吉朋初则轻视,继则 不敢掉以轻心,终则全力应付,颇思把璧德的论点一举粉碎。但璧德却步步为营,无懈可击。 吉朋最后愤怒离席而去。吉朋的友人求他返席。吉朋说“绝不,我毫不怀疑,那位年轻小绅 士是极端有天份的,并且也是很可亲的。不过,我必须说他的辩论方式不是我所习惯的。所 以你应该原谅我!”当然,这个故事究竟有多少真实,还得听听牛津人怎样说法的。 三一学院毫无疑问是剑桥(也包括牛津)最大也最著名的学院。这是远者出过牛顿、培 根,近者出过怀海徳一、罗素、维根斯坦二的学院。因它人材辈出,所以带雾的历史也最浓。 在三一的大门左边草坪上,有一棵矮小的苹果树,它就是牛顿悟“道”的“菩提”。你不信?那 是你自己的损失!在雾气袅袅中,这棵树看来是有些不同凡响的灵气!走进三一门,便是走 进传奇之乡了。我们不能不听说这儿出过两位“战斗格”的院长。一位是大数学家巴(Barrow, 牛顿的老师),他从小就勇猛苦斗,在一次航行中且曾力挫海盗。在他院长任内,一次遭到 一头大猛犬的袭击,巴罗镇定如山,一侧身,让过,再一个箭步逼上,以赤手握住大猛犬的 脖子,又一使劲,便把那个巨物掀倒在地,继而饱以如雨老拳,巴罗的威武状使人想起景阳 岗武松打虎的神威。另一位是经典学者班得来( Bentley),他院长一做做了四十余年,打 破三一的纪录[剑桥其他书院则有更长纪录:圣彼得学院的 Francis Barner 做了五十年(一 七八八—一八三八)。克莱亚学院的 Dr.E.Atkinson 做了五十九年零二个月,九十岁还在 做]。这位院长的好斗性格不输巴罗。不过巴罗斗的是海盗,他斗的是院士;巴罗善于用拳, 他则精通法律,在他四十年院长任内,讼事连连,战云密布。此君之好辩喜争,可说与生俱 来。他曾力辩“尼布加尼撒(纪元前五百年前的巴比伦王)的金像记载是错的,该记载说金 像高六十腕尺、宽六腕尺。他则说金像的宽度至少是十腕尺。为这件事他与未婚妻搞得瞪眼 吹须,几乎使婚事告吹。往事已矣!这位“武士”虽然在学院礼拜堂北首的墓碑上连院长的头 衔都未被刻上,但这位好战院长的“妙”事流传至今引为谈资。 三一是科学家的王国,也是诗人的天地。丁尼生进校做学生时,院长汤姆生一眼望见这 位器宇特出的少年就说:“那个人一定是诗人!”不错,“那个人”可以“看”到夜莺眼中的月光; “那个人”的一首十四行诗就被认为值得“康可达”(印度古都)的全城财富。在剑桥,“那个 人”在诗的竞赛中就已崭露头角了。丁尼生在上课的时候,想必常常神游物外,飞入白云绿 水之间。据说有一次导师魏怀尔把他从梦乡中唤醒,问他,“从耶稣时代起到今日为止,一 个便士的复息是多少?” 拜伦也是三一之子,但他不是最受宠爱的一个。他在校时风流倜傥,热衷于拳斗、骑射、 豪饮、赌博、游泳(他常游泳的地方在格兰赛斯德原野的剑河上端,现称“拜伦池”)。他讨 厌学校不准养狗的规定,既然不准养狗,他便去养了一头小熊。他在给一位女士的信中说: “我有了一位新朋友,是世界上最好的,它是一只小熊。当我带它来这里时,他们问我准备 怎样处理它,我的答复是:‘它应该参加院士的选举。’这个答复使他们不顶高兴。”这位诗 人大半生浪迹欧陆,死于希腊。雕刻家 Thorwaldsen 为他刻了一尊巨大的大理石全身像,送 给伦敦的西敏寺教堂展放(英人死后进此寺是最大荣誉),但西敏寺却基于不道德的理由, 拒绝接受。这石雕惨惨地在地窖的尘灰中躺了几年,后来还是三一学院念“子”情深,把他运 一 怀海德: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今译为怀特海。 二 维根斯坦:奥地利哲学家、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今译为维特根斯坦

回,摆在雷恩图书馆最醒目的位置。当你凝视拜伦丰神俊貌之余,联想到他生前养熊的故事, 就不会觉得他冷冰冰地不发一语了。 讲剑桥的传奇不能不讲基督学院。这是《物种始原》一的作者达尔文的学院,也是《失 乐园》的作者弥尔顿的母校。达尔文在基督学院时就狂热于收集昆虫了。他抓甲虫是又专注, 又在行。有一次他一眼看见好几只精彩的,双手一扑,就抓到了一只。说时迟,那时快,他 把抓到的放在口里,再去抓一只,不想口里的一只发了威,刺了他舌头,他一痛只好张口让 它眼巴巴飞去,而手边的一只又因分神而被溜掉。我们可以想见这位小博物学者的懊丧。达 尔文在剑桥并不出名,不过,由于他常跟植物学教授汉斯劳一起散步,为此人家都称他为: “那个跟汉斯劳一起散步的人”。而今,说起汉斯劳时,恐怕要说是“那个跟达尔文一起散步 的教授了。” 科学家的传奇在剑桥总是没有诗人的多,也没有诗人的有浪漫情调。我觉得最富传奇性 的该是弥尔顿的故事了。最引起好奇与争论的不是基督学院庭园中那棵亭亭桑树是不是弥尔 顿所手植,而是究竞弥尔顿在校时有否遭过导师查沛尔的体罚。牛津文豪约翰笙(Samuel Johnson)在他的The Lives of English Poets书中,则一口咬定确有其事。剑桥人则说约翰笙 无中生有,并指出弥尔顿终其身都对母校保有深挚的感情。这些争论对研究弥尔顿的人或许 是重要的,但在我们看,真正有意思的是下面的传奇:话说一位风姿绰约的外国少女,在一 个晚春初夏的日子访游剑桥,她被一位睡在树下的少男的美色所震惊,在频频凝视之余,情 不自禁地用意大利文写下了几行爱慕的诗句,轻柔地放在睡者的手中。当弥尔顿醒来时,读 了留下的诗句,问了附近目睹的同学,认为是“天赐良缘”,从此在脑海中浮现了一位才貌双 绝的仙子,对这位未谋一面的佳人朝思暮想,产生了狂热的爱情。后来,他买棹远去意大利 寻芳,真是“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无奈音容茫茫,仙子无踪。米尔顿想她、 思她,直到临终一刻,长恨以殁,这真正成为了他的“失乐园”! 雾里的剑桥也许不真,却是美的神秘! 耶鲁的狷介二 康正果 (上) 与美国各地的大学大致相同,耶鲁的暑假每年也放得很早,大约到了五月的中旬,在考 完最后一门课之后的当天或次日,住在十二个寄宿学院内的学生便群鸟般四散而去,三两天 之间,纽海文大草地周围的街道就显得空空荡荡了。今年暑期,我没什么地方可去,一天到 晚,大都泡在自己的办公室内读书消夏。看到同事们出游的出游,去暑期学校授课的授课, 我自满足这孤云独在的悠闲。有时候在室内坐闷了,我就出了门沿庙街(Temple St.)向校 园的中心走去,穿过圣玛丽教堂石壁外的夹道,转到纪念堂(Me-morial Hall)的大圆顶下, 然后在威廉大楼(WLH)前那块鲜嫩的草地上坐下来,靠着大榆树消受浓阴下的清凉。我 觉得,闲暇和宁静的确是生活的补药,闲暇滋长了人寻觅的幽趣,宁静则拓宽了我思考的空 间,享着这样难得的清福,再加上终日独处,平时让忙碌弄得麻木了的感觉遂慢慢地恢复过 来,心里忽然有了一点省思和回顾的冲动。 比如拿刚才提到的这段路线来说,它其实就是我每天来威廉大楼上课所走的捷径。只我 《物种始原》:今译作《物种起源》 康正果(1944-),旅美学者。本文选自中国台北《世界日报》1997年8月5一6日,题目为编者所拟。 -7-
- 7 - 回,摆在雷恩图书馆最醒目的位置。当你凝视拜伦丰神俊貌之余,联想到他生前养熊的故事, 就不会觉得他冷冰冰地不发一语了。 讲剑桥的传奇不能不讲基督学院。这是《物种始原》一的作者达尔文的学院,也是《失 乐园》的作者弥尔顿的母校。达尔文在基督学院时就狂热于收集昆虫了。他抓甲虫是又专注, 又在行。有一次他一眼看见好几只精彩的,双手一扑,就抓到了一只。说时迟,那时快,他 把抓到的放在口里,再去抓一只,不想口里的一只发了威,刺了他舌头,他一痛只好张口让 它眼巴巴飞去,而手边的一只又因分神而被溜掉。我们可以想见这位小博物学者的懊丧。达 尔文在剑桥并不出名,不过,由于他常跟植物学教授汉斯劳一起散步,为此人家都称他为: “那个跟汉斯劳一起散步的人”。而今,说起汉斯劳时,恐怕要说是“那个跟达尔文一起散步 的教授了。” 科学家的传奇在剑桥总是没有诗人的多,也没有诗人的有浪漫情调。我觉得最富传奇性 的该是弥尔顿的故事了。最引起好奇与争论的不是基督学院庭园中那棵亭亭桑树是不是弥尔 顿所手植,而是究竟弥尔顿在校时有否遭过导师查沛尔的体罚。牛津文豪约翰笙(Samuel Johnson)在他的 The Lives of English Poets 书中,则一口咬定确有其事。剑桥人则说约翰笙 无中生有,并指出弥尔顿终其身都对母校保有深挚的感情。这些争论对研究弥尔顿的人或许 是重要的,但在我们看,真正有意思的是下面的传奇:话说一位风姿绰约的外国少女,在一 个晚春初夏的日子访游剑桥,她被一位睡在树下的少男的美色所震惊,在频频凝视之余,情 不自禁地用意大利文写下了几行爱慕的诗句,轻柔地放在睡者的手中。当弥尔顿醒来时,读 了留下的诗句,问了附近目睹的同学,认为是“天赐良缘”,从此在脑海中浮现了一位才貌双 绝的仙子,对这位未谋一面的佳人朝思暮想,产生了狂热的爱情。后来,他买棹远去意大利 寻芳,真是“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无奈音容茫茫,仙子无踪。米尔顿想她、 思她,直到临终一刻,长恨以殁,这真正成为了他的“失乐园”! 雾里的剑桥也许不真,却是美的神秘! 耶鲁的狷介二 康正果 (上) 与美国各地的大学大致相同,耶鲁的暑假每年也放得很早,大约到了五月的中旬,在考 完最后一门课之后的当天或次日,住在十二个寄宿学院内的学生便群鸟般四散而去,三两天 之间,纽海文大草地周围的街道就显得空空荡荡了。今年暑期,我没什么地方可去,一天到 晚,大都泡在自己的办公室内读书消夏。看到同事们出游的出游,去暑期学校授课的授课, 我自满足这孤云独在的悠闲。有时候在室内坐闷了,我就出了门沿庙街(Temple St.)向校 园的中心走去,穿过圣玛丽教堂石壁外的夹道,转到纪念堂(Me-morial Hall)的大圆顶下, 然后在威廉大楼(WLH)前那块鲜嫩的草地上坐下来,靠着大榆树消受浓阴下的清凉。我 觉得,闲暇和宁静的确是生活的补药,闲暇滋长了人寻觅的幽趣,宁静则拓宽了我思考的空 间,享着这样难得的清福,再加上终日独处,平时让忙碌弄得麻木了的感觉遂慢慢地恢复过 来,心里忽然有了一点省思和回顾的冲动。 比如拿刚才提到的这段路线来说,它其实就是我每天来威廉大楼上课所走的捷径。只我 一 《物种始原》:今译作《物种起源》。 二康正果(1944-),旅美学者。本文选自中国台北《世界日报》1997 年 8 月 5—6 日,题目为编者所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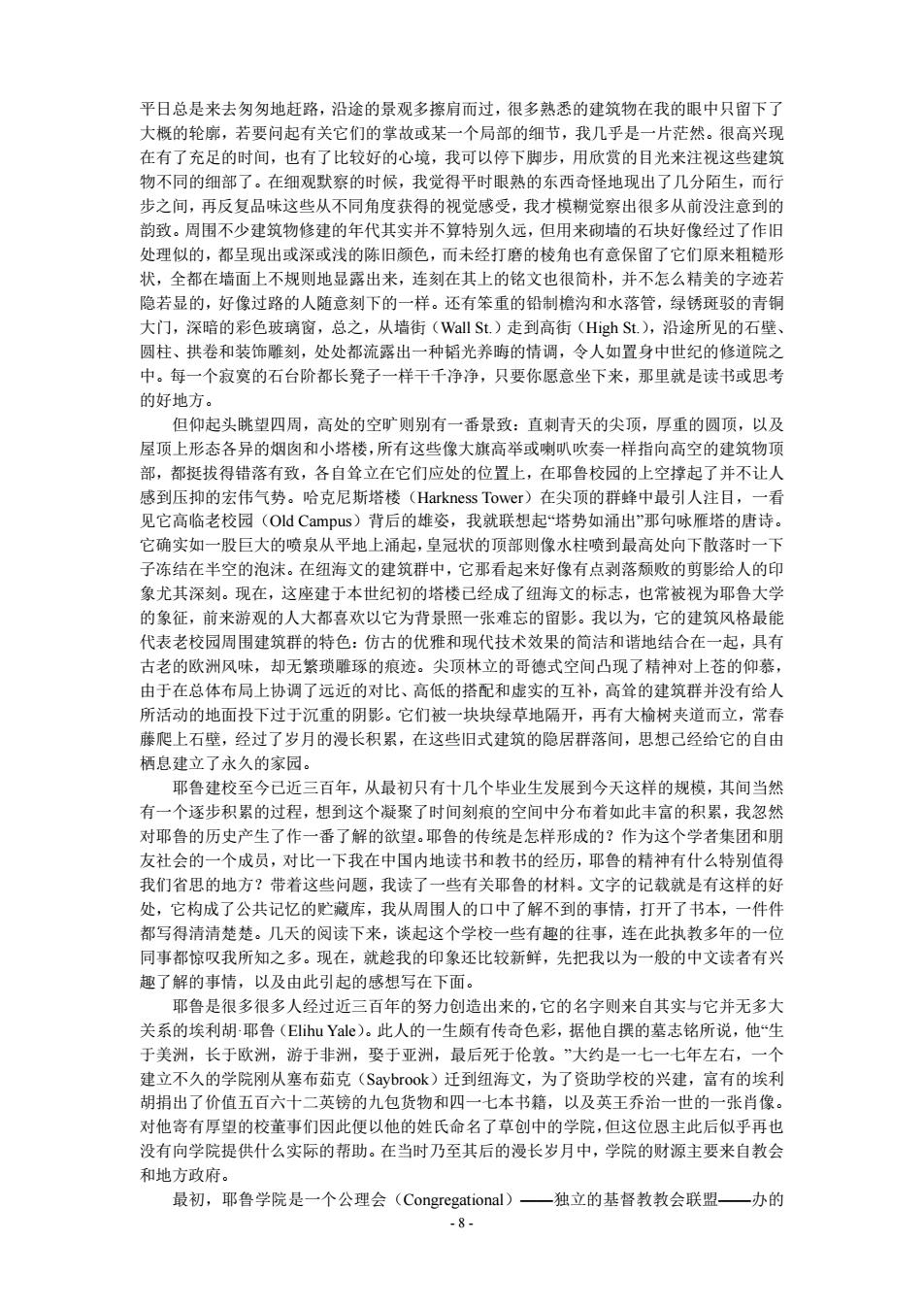
平日总是来去匆匆地赶路,沿途的景观多擦肩而过,很多熟悉的建筑物在我的眼中只留下了 大概的轮廓,若要问起有关它们的掌故或某一个局部的细节,我几乎是一片茫然。很高兴现 在有了充足的时间,也有了比较好的心境,我可以停下脚步,用欣赏的目光来注视这些建筑 物不同的细部了。在细观默察的时候,我觉得平时眼熟的东西奇怪地现出了几分陌生,而行 步之间,再反复品味这些从不同角度获得的视觉感受,我才模糊觉察出很多从前没注意到的 韵致。周围不少建筑物修建的年代其实并不算特别久远,但用来砌墙的石块好像经过了作旧 处理似的,都呈现出或深或浅的陈旧颜色,而未经打磨的棱角也有意保留了它们原来粗糙形 状,全都在墙面上不规则地显露出来,连刻在其上的铭文也很简朴,并不怎么精美的字迹若 隐若显的,好像过路的人随意刻下的一样。还有笨重的铅制檐沟和水落管,绿锈斑驳的青铜 大门,深暗的彩色玻璃窗,总之,从墙街(Wall St..)走到高街(High St..),沿途所见的石壁、 圆柱、拱卷和装饰雕刻,处处都流露出一种韬光养晦的情调,令人如置身中世纪的修道院之 中。每一个寂宽的石台阶都长凳子一样干千净净,只要你愿意坐下来,那里就是读书或思考 的好地方。 但仰起头跳望四周,高处的空旷则别有一番景致:直刺青天的尖顶,厚重的圆顶,以及 屋顶上形态各异的烟囱和小塔楼,所有这些像大旗高举或喇叭吹奏一样指向高空的建筑物顶 部,都挺拔得错落有致,各自耸立在它们应处的位置上,在耶鲁校园的上空撑起了并不让人 感到压抑的宏伟气势。哈克尼斯塔楼(Harkness Tower)在尖顶的群蜂中最引人注目,一看 见它高临老校园(Old Campus)背后的雄姿,我就联想起塔势如涌出”那句咏雁塔的唐诗。 它确实如一股巨大的喷泉从平地上涌起,皇冠状的顶部则像水柱喷到最高处向下散落时一下 子冻结在半空的泡沫。在纽海文的建筑群中,它那看起来好像有点剥落颓败的剪影给人的印 象尤其深刻。现在,这座建于本世纪初的塔楼己经成了纽海文的标志,也常被视为耶鲁大学 的象征,前来游观的人大都喜欢以它为背景照一张难忘的留影。我以为,它的建筑风格最能 代表老校园周围建筑群的特色:仿古的优雅和现代技术效果的简洁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具有 古老的欧洲风味,却无繁琐雕琢的痕迹。尖顶林立的哥德式空间凸现了精神对上苍的仰慕, 由于在总体布局上协调了远近的对比、高低的搭配和虚实的互补,高耸的建筑群并没有给人 所活动的地面投下过于沉重的阴影。它们被一块块绿草地隔开,再有大榆树夹道而立,常春 藤爬上石壁,经过了岁月的漫长积累,在这些旧式建筑的隐居群落间,思想己经给它的自由 栖息建立了永久的家园。 耶鲁建校至今己近三百年,从最初只有十几个毕业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其间当然 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想到这个凝聚了时间刻痕的空间中分布着如此丰富的积累,我忽然 对耶鲁的历史产生了作一番了解的欲望。耶鲁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作为这个学者集团和朋 友社会的一个成员,对比一下我在中国内地读书和教书的经历,耶鲁的精神有什么特别值得 我们省思的地方?带着这些问题,我读了一些有关耶鲁的材料。文字的记载就是有这样的好 处,它构成了公共记忆的贮藏库,我从周围人的口中了解不到的事情,打开了书本,一件件 都写得清清楚楚。几天的阅读下来,谈起这个学校一些有趣的往事,连在此执教多年的一位 同事都惊叹我所知之多。现在,就趁我的印象还比较新鲜,先把我以为一般的中文读者有兴 趣了解的事情,以及由此引起的感想写在下面。 耶鲁是很多很多人经过近三百年的努力创造出来的,它的名字则来自其实与它并无多大 关系的埃利胡-耶鲁(Elihu Yale)。此人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据他自撰的墓志铭所说,他“生 于美洲,长于欧洲,游于非洲,娶于亚洲,最后死于伦敦。”大约是一七一七年左右,一个 建立不久的学院刚从塞布茹克(Saybrook)迁到纽海文,为了资助学校的兴建,富有的埃利 胡捐出了价值五百六十二英镑的九包货物和四一七本书籍,以及英王乔治一世的一张肖像。 对他寄有厚望的校董事们因此便以他的姓氏命名了草创中的学院,但这位恩主此后似乎再也 没有向学院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在当时乃至其后的漫长岁月中,学院的财源主要来自教会 和地方政府。 最初,耶鲁学院是一个公理会(Congregational)一独立的基督教教会联盟一办的 -8-
- 8 - 平日总是来去匆匆地赶路,沿途的景观多擦肩而过,很多熟悉的建筑物在我的眼中只留下了 大概的轮廓,若要问起有关它们的掌故或某一个局部的细节,我几乎是一片茫然。很高兴现 在有了充足的时间,也有了比较好的心境,我可以停下脚步,用欣赏的目光来注视这些建筑 物不同的细部了。在细观默察的时候,我觉得平时眼熟的东西奇怪地现出了几分陌生,而行 步之间,再反复品味这些从不同角度获得的视觉感受,我才模糊觉察出很多从前没注意到的 韵致。周围不少建筑物修建的年代其实并不算特别久远,但用来砌墙的石块好像经过了作旧 处理似的,都呈现出或深或浅的陈旧颜色,而未经打磨的棱角也有意保留了它们原来粗糙形 状,全都在墙面上不规则地显露出来,连刻在其上的铭文也很简朴,并不怎么精美的字迹若 隐若显的,好像过路的人随意刻下的一样。还有笨重的铅制檐沟和水落管,绿锈斑驳的青铜 大门,深暗的彩色玻璃窗,总之,从墙街(Wall St.)走到高街(High St.),沿途所见的石壁、 圆柱、拱卷和装饰雕刻,处处都流露出一种韬光养晦的情调,令人如置身中世纪的修道院之 中。每一个寂寞的石台阶都长凳子一样干千净净,只要你愿意坐下来,那里就是读书或思考 的好地方。 但仰起头眺望四周,高处的空旷则别有一番景致:直刺青天的尖顶,厚重的圆顶,以及 屋顶上形态各异的烟囱和小塔楼,所有这些像大旗高举或喇叭吹奏一样指向高空的建筑物顶 部,都挺拔得错落有致,各自耸立在它们应处的位置上,在耶鲁校园的上空撑起了并不让人 感到压抑的宏伟气势。哈克尼斯塔楼(Harkness Tower)在尖顶的群蜂中最引人注目,一看 见它高临老校园(Old Campus)背后的雄姿,我就联想起“塔势如涌出”那句咏雁塔的唐诗。 它确实如一股巨大的喷泉从平地上涌起,皇冠状的顶部则像水柱喷到最高处向下散落时一下 子冻结在半空的泡沫。在纽海文的建筑群中,它那看起来好像有点剥落颓败的剪影给人的印 象尤其深刻。现在,这座建于本世纪初的塔楼已经成了纽海文的标志,也常被视为耶鲁大学 的象征,前来游观的人大都喜欢以它为背景照一张难忘的留影。我以为,它的建筑风格最能 代表老校园周围建筑群的特色:仿古的优雅和现代技术效果的简洁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具有 古老的欧洲风味,却无繁琐雕琢的痕迹。尖顶林立的哥德式空间凸现了精神对上苍的仰慕, 由于在总体布局上协调了远近的对比、高低的搭配和虚实的互补,高耸的建筑群并没有给人 所活动的地面投下过于沉重的阴影。它们被一块块绿草地隔开,再有大榆树夹道而立,常春 藤爬上石壁,经过了岁月的漫长积累,在这些旧式建筑的隐居群落间,思想己经给它的自由 栖息建立了永久的家园。 耶鲁建校至今已近三百年,从最初只有十几个毕业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其间当然 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想到这个凝聚了时间刻痕的空间中分布着如此丰富的积累,我忽然 对耶鲁的历史产生了作一番了解的欲望。耶鲁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作为这个学者集团和朋 友社会的一个成员,对比一下我在中国内地读书和教书的经历,耶鲁的精神有什么特别值得 我们省思的地方?带着这些问题,我读了一些有关耶鲁的材料。文字的记载就是有这样的好 处,它构成了公共记忆的贮藏库,我从周围人的口中了解不到的事情,打开了书本,一件件 都写得清清楚楚。几天的阅读下来,谈起这个学校一些有趣的往事,连在此执教多年的一位 同事都惊叹我所知之多。现在,就趁我的印象还比较新鲜,先把我以为一般的中文读者有兴 趣了解的事情,以及由此引起的感想写在下面。 耶鲁是很多很多人经过近三百年的努力创造出来的,它的名字则来自其实与它并无多大 关系的埃利胡·耶鲁(Elihu Yale)。此人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据他自撰的墓志铭所说,他“生 于美洲,长于欧洲,游于非洲,娶于亚洲,最后死于伦敦。”大约是一七一七年左右,一个 建立不久的学院刚从塞布茹克(Saybrook)迁到纽海文,为了资助学校的兴建,富有的埃利 胡捐出了价值五百六十二英镑的九包货物和四一七本书籍,以及英王乔治一世的一张肖像。 对他寄有厚望的校董事们因此便以他的姓氏命名了草创中的学院,但这位恩主此后似乎再也 没有向学院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在当时乃至其后的漫长岁月中,学院的财源主要来自教会 和地方政府。 最初,耶鲁学院是一个公理会(Congregational)——独立的基督教教会联盟——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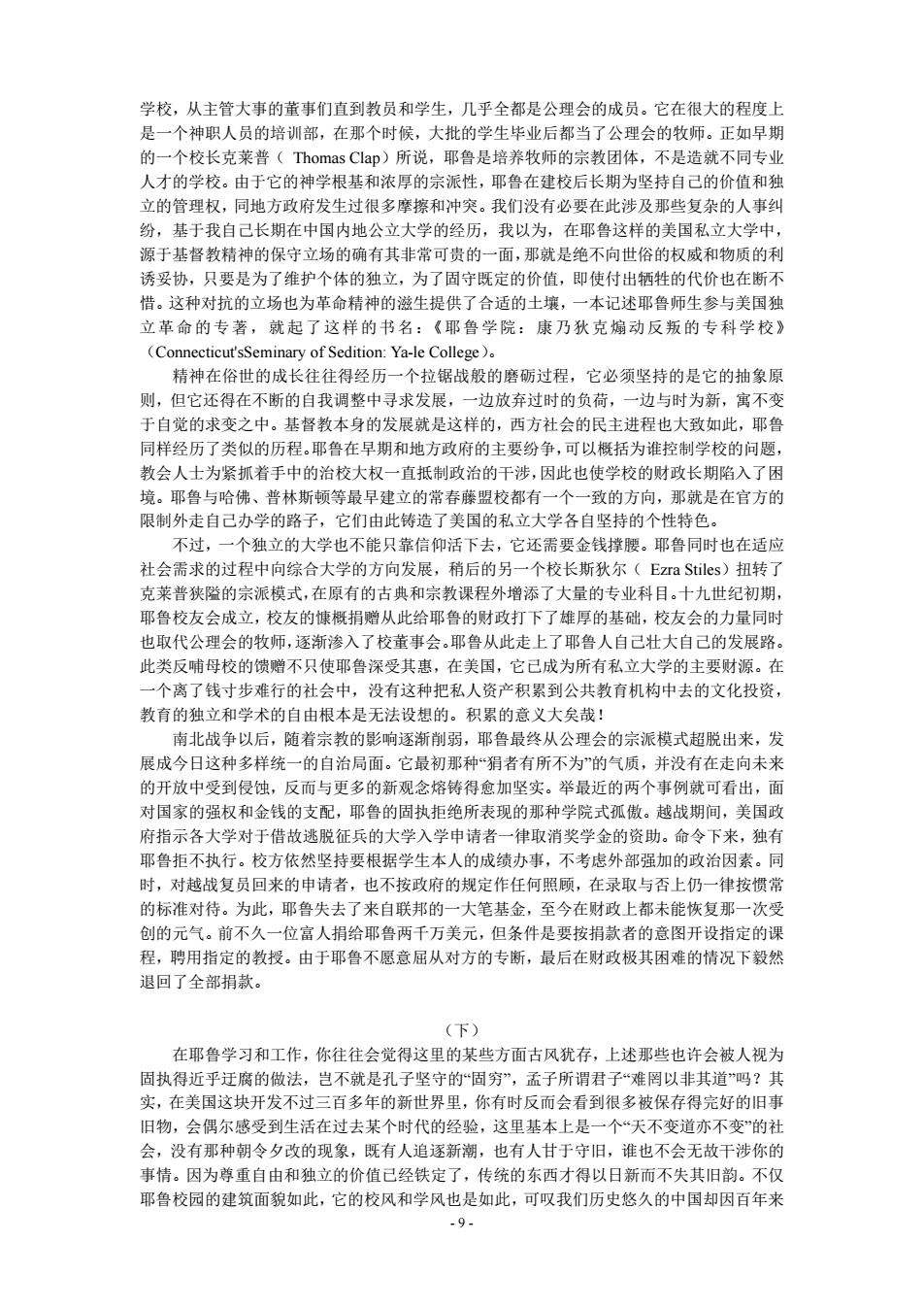
学校,从主管大事的董事们直到教员和学生,几乎全都是公理会的成员。它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一个神职人员的培训部,在那个时候,大批的学生毕业后都当了公理会的牧师。正如早期 的一个校长克莱普(Thomas Clap)所说,耶鲁是培养牧师的宗教团体,不是造就不同专业 人才的学校。由于它的神学根基和浓厚的宗派性,耶鲁在建校后长期为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独 立的管理权,同地方政府发生过很多摩擦和冲突。我们没有必要在此涉及那些复杂的人事纠 纷,基于我自己长期在中国内地公立大学的经历,我以为,在耶鲁这样的美国私立大学中, 源于基督教精神的保守立场的确有其非常可贵的一面,那就是绝不向世俗的权威和物质的利 诱妥协,只要是为了维护个体的独立,为了固守既定的价值,即使付出牺牲的代价也在断不 惜。这种对抗的立场也为革命精神的滋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一本记述耶鲁师生参与美国独 立革命的专著,就起了这样的书名:《耶鲁学院:康乃狄克煽动反叛的专科学校》 Connecticut'sSeminary of Sedition:Ya-le College ) 精神在俗世的成长往往得经历一个拉锯战般的磨砺过程,它必须坚持的是它的抽象原 则,但它还得在不断的自我调整中寻求发展,一边放弃过时的负荷,一边与时为新,寓不变 于自觉的求变之中。基督教本身的发展就是这样的,西方社会的民主进程也大致如此,耶鲁 同样经历了类似的历程。耶鲁在早期和地方政府的主要纷争,可以概括为谁控制学校的问题, 教会人士为紧抓着手中的治校大权一直抵制政治的干涉,因此也使学校的财政长期陷入了困 境。耶鲁与哈佛、普林斯顿等最早建立的常春藤盟校都有一个一致的方向,那就是在官方的 限制外走自己办学的路子,它们由此铸造了美国的私立大学各自坚持的个性特色。 不过,一个独立的大学也不能只靠信仰活下去,它还需要金钱撑腰。耶鲁同时也在适应 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向综合大学的方向发展,稍后的另一个校长斯狄尔(Ezra Stiles)扭转了 克莱普狭隘的宗派模式,在原有的古典和宗教课程外增添了大量的专业科目。十九世纪初期, 耶鲁校友会成立,校友的慷概捐赠从此给耶鲁的财政打下了雄厚的基础,校友会的力量同时 也取代公理会的牧师,逐渐渗入了校董事会。耶鲁从此走上了耶鲁人自己壮大自己的发展路。 此类反哺母校的馈赠不只使耶鲁深受其惠,在美国,它已成为所有私立大学的主要财源。在 一个离了钱寸步难行的社会中,没有这种把私人资产积累到公共教育机构中去的文化投资, 教育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根本是无法设想的。积累的意义大矣哉! 南北战争以后,随着宗教的影响逐渐削弱,耶鲁最终从公理会的宗派模式超脱出来,发 展成今日这种多样统一的自治局面。它最初那种“狷者有所不为”的气质,并没有在走向未来 的开放中受到侵蚀,反而与更多的新观念熔铸得愈加坚实。举最近的两个事例就可看出,面 对国家的强权和金钱的支配,耶鲁的固执拒绝所表现的那种学院式孤傲。越战期间,美国政 府指示各大学对于借故逃脱征兵的大学入学申请者一律取消奖学金的资助。命令下来,独有 耶鲁拒不执行。校方依然坚持要根据学生本人的成绩办事,不考虑外部强加的政治因素。同 时,对越战复员回来的申请者,也不按政府的规定作任何照顾,在录取与否上仍一律按惯常 的标准对待。为此,耶鲁失去了来自联邦的一大笔基金,至今在财政上都未能恢复那一次受 创的元气。前不久一位富人捐给耶鲁两千万美元,但条件是要按捐款者的意图开设指定的课 程,聘用指定的教授。由于耶鲁不愿意屈从对方的专断,最后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毅然 退回了全部捐款。 (下) 在耶鲁学习和工作,你往往会觉得这里的某些方面古风犹存,上述那些也许会被人视为 固执得近乎迂腐的做法,岂不就是孔子坚守的“固穷”,孟子所谓君子“难罔以非其道”吗?其 实,在美国这块开发不过三百多年的新世界里,你有时反而会看到很多被保存得完好的旧事 旧物,会偶尔感受到生活在过去某个时代的经验,这里基本上是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社 会,没有那种朝令夕改的现象,既有人追逐新潮,也有人甘于守旧,谁也不会无故干涉你的 事情。因为尊重自由和独立的价值己经铁定了,传统的东西才得以日新而不失其旧韵。不仅 耶鲁校园的建筑面貌如此,它的校风和学风也是如此,可叹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国却因百年来 -9-
- 9 - 学校,从主管大事的董事们直到教员和学生,几乎全都是公理会的成员。它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一个神职人员的培训部,在那个时候,大批的学生毕业后都当了公理会的牧师。正如早期 的一个校长克莱普( Thomas Clap)所说,耶鲁是培养牧师的宗教团体,不是造就不同专业 人才的学校。由于它的神学根基和浓厚的宗派性,耶鲁在建校后长期为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独 立的管理权,同地方政府发生过很多摩擦和冲突。我们没有必要在此涉及那些复杂的人事纠 纷,基于我自己长期在中国内地公立大学的经历,我以为,在耶鲁这样的美国私立大学中, 源于基督教精神的保守立场的确有其非常可贵的一面,那就是绝不向世俗的权威和物质的利 诱妥协,只要是为了维护个体的独立,为了固守既定的价值,即使付出牺牲的代价也在断不 惜。这种对抗的立场也为革命精神的滋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一本记述耶鲁师生参与美国独 立革命的专著,就起了这样的书名:《耶鲁学院:康乃狄克煽动反叛的专科学校》 (Connecticut'sSeminary of Sedition: Ya-le College)。 精神在俗世的成长往往得经历一个拉锯战般的磨砺过程,它必须坚持的是它的抽象原 则,但它还得在不断的自我调整中寻求发展,一边放弃过时的负荷,一边与时为新,寓不变 于自觉的求变之中。基督教本身的发展就是这样的,西方社会的民主进程也大致如此,耶鲁 同样经历了类似的历程。耶鲁在早期和地方政府的主要纷争,可以概括为谁控制学校的问题, 教会人士为紧抓着手中的治校大权一直抵制政治的干涉,因此也使学校的财政长期陷入了困 境。耶鲁与哈佛、普林斯顿等最早建立的常春藤盟校都有一个一致的方向,那就是在官方的 限制外走自己办学的路子,它们由此铸造了美国的私立大学各自坚持的个性特色。 不过,一个独立的大学也不能只靠信仰活下去,它还需要金钱撑腰。耶鲁同时也在适应 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向综合大学的方向发展,稍后的另一个校长斯狄尔( Ezra Stiles)扭转了 克莱普狭隘的宗派模式,在原有的古典和宗教课程外增添了大量的专业科目。十九世纪初期, 耶鲁校友会成立,校友的慷概捐赠从此给耶鲁的财政打下了雄厚的基础,校友会的力量同时 也取代公理会的牧师,逐渐渗入了校董事会。耶鲁从此走上了耶鲁人自己壮大自己的发展路。 此类反哺母校的馈赠不只使耶鲁深受其惠,在美国,它已成为所有私立大学的主要财源。在 一个离了钱寸步难行的社会中,没有这种把私人资产积累到公共教育机构中去的文化投资, 教育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根本是无法设想的。积累的意义大矣哉! 南北战争以后,随着宗教的影响逐渐削弱,耶鲁最终从公理会的宗派模式超脱出来,发 展成今日这种多样统一的自治局面。它最初那种“狷者有所不为”的气质,并没有在走向未来 的开放中受到侵蚀,反而与更多的新观念熔铸得愈加坚实。举最近的两个事例就可看出,面 对国家的强权和金钱的支配,耶鲁的固执拒绝所表现的那种学院式孤傲。越战期间,美国政 府指示各大学对于借故逃脱征兵的大学入学申请者一律取消奖学金的资助。命令下来,独有 耶鲁拒不执行。校方依然坚持要根据学生本人的成绩办事,不考虑外部强加的政治因素。同 时,对越战复员回来的申请者,也不按政府的规定作任何照顾,在录取与否上仍一律按惯常 的标准对待。为此,耶鲁失去了来自联邦的一大笔基金,至今在财政上都未能恢复那一次受 创的元气。前不久一位富人捐给耶鲁两千万美元,但条件是要按捐款者的意图开设指定的课 程,聘用指定的教授。由于耶鲁不愿意屈从对方的专断,最后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毅然 退回了全部捐款。 (下) 在耶鲁学习和工作,你往往会觉得这里的某些方面古风犹存,上述那些也许会被人视为 固执得近乎迂腐的做法,岂不就是孔子坚守的“固穷”,孟子所谓君子“难罔以非其道”吗?其 实,在美国这块开发不过三百多年的新世界里,你有时反而会看到很多被保存得完好的旧事 旧物,会偶尔感受到生活在过去某个时代的经验,这里基本上是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社 会,没有那种朝令夕改的现象,既有人追逐新潮,也有人甘于守旧,谁也不会无故干涉你的 事情。因为尊重自由和独立的价值已经铁定了,传统的东西才得以日新而不失其旧韵。不仅 耶鲁校园的建筑面貌如此,它的校风和学风也是如此,可叹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国却因百年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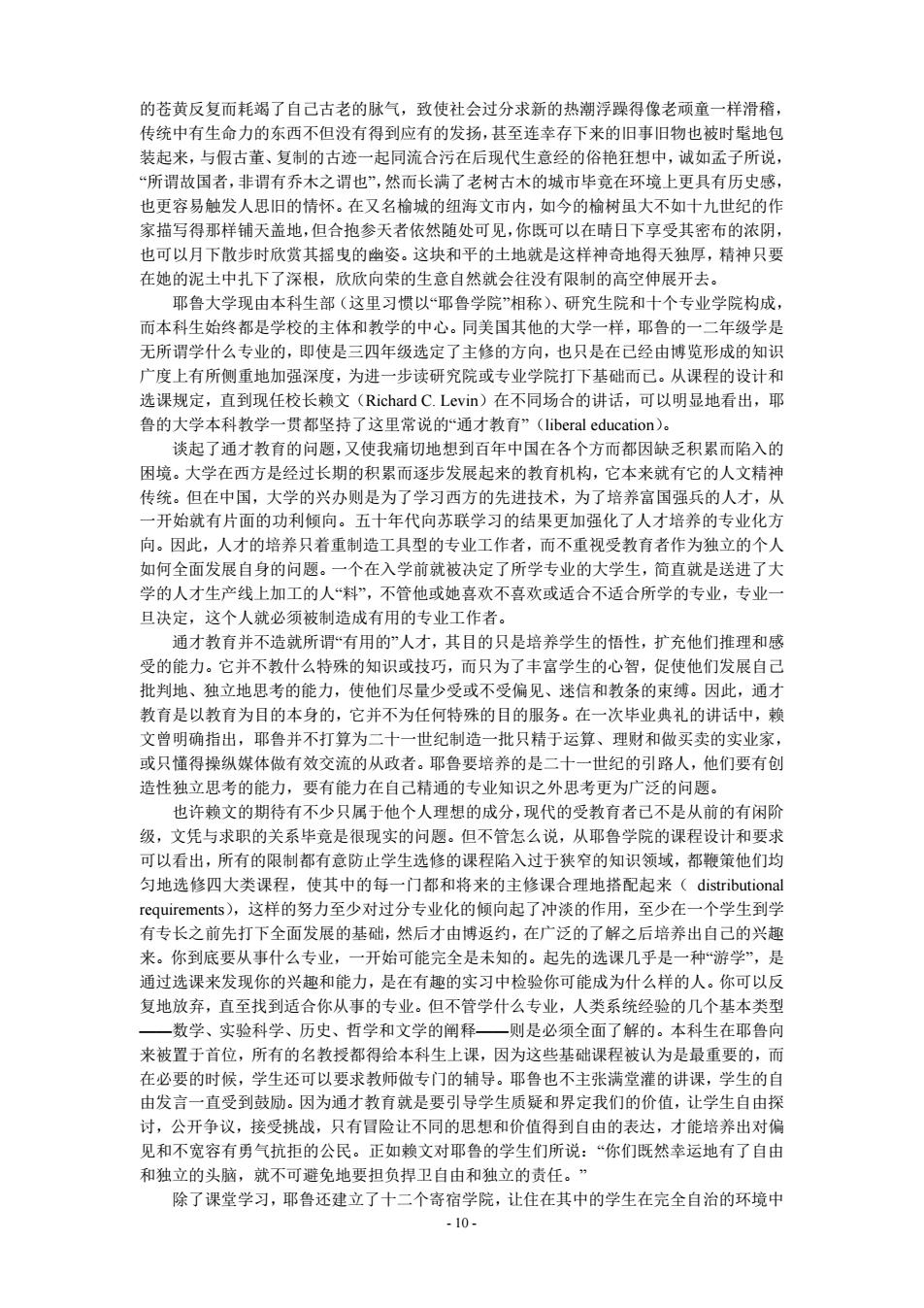
的苍黄反复而耗竭了自己古老的脉气,致使社会过分求新的热潮浮躁得像老顽童一样滑稽, 传统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扬,甚至连幸存下来的旧事旧物也被时髦地包 装起来,与假古董、复制的古迹一起同流合污在后现代生意经的俗艳狂想中,诚如孟子所说,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然而长满了老树古木的城市毕竞在环境上更具有历史感, 也更容易触发人思旧的情怀。在又名榆城的纽海文市内,如今的榆树虽大不如十九世纪的作 家描写得那样铺天盖地,但合抱参天者依然随处可见,你既可以在晴日下享受其密布的浓阴, 也可以月下散步时欣赏其摇曳的幽姿。这块和平的土地就是这样神奇地得天独厚,精神只要 在她的泥土中扎下了深根,欣欣向荣的生意自然就会往没有限制的高空伸展开去。 耶鲁大学现由本科生部(这里习惯以“耶鲁学院”相称)、研究生院和十个专业学院构成, 而本科生始终都是学校的主体和教学的中心。同美国其他的大学一样,耶鲁的一二年级学是 无所谓学什么专业的,即使是三四年级选定了主修的方向,也只是在己经由博览形成的知识 广度上有所侧重地加强深度,为进一步读研究院或专业学院打下基础而已。从课程的设计和 选课规定,直到现任校长赖文(Richard C.Levin)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可以明显地看出,耶 鲁的大学本科教学一贯都坚持了这里常说的“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 谈起了通才教育的问题,又使我痛切地想到百年中国在各个方而都因缺乏积累而陷入的 困境。大学在西方是经过长期的积累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教育机构,它本来就有它的人文精神 传统。但在中国,大学的兴办则是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为了培养富国强兵的人才,从 一开始就有片面的功利倾向。五十年代向苏联学习的结果更加强化了人才培养的专业化方 向。因此,人才的培养只着重制造工具型的专业工作者,而不重视受教育者作为独立的个人 如何全面发展自身的问题。一个在入学前就被决定了所学专业的大学生,简直就是送进了大 学的人才生产线上加工的人“料”,不管他或她喜欢不喜欢或适合不适合所学的专业,专业一 旦决定,这个人就必须被制造成有用的专业工作者。 通才教育并不造就所谓“有用的”人才,其目的只是培养学生的悟性,扩充他们推理和感 受的能力。它并不教什么特殊的知识或技巧,而只为了丰富学生的心智,促使他们发展自己 批判地、独立地思考的能力,使他们尽量少受或不受偏见、迷信和教条的束缚。因此,通才 教育是以教育为目的本身的,它并不为任何特殊的目的服务。在一次毕业典礼的讲话中,赖 文曾明确指出,耶鲁并不打算为二十一世纪制造一批只精于运算、理财和做买卖的实业家, 或只懂得操纵媒体做有效交流的从政者。耶鲁要培养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引路人,他们要有创 造性独立思考的能力,要有能力在自己精通的专业知识之外思考更为广泛的问题。 也许赖文的期待有不少只属于他个人理想的成分,现代的受教育者已不是从前的有闲阶 级,文凭与求职的关系毕竞是很现实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从耶鲁学院的课程设计和要求 可以看出,所有的限制都有意防止学生选修的课程陷入过于狭窄的知识领域,都鞭策他们均 匀地选修四大类课程,使其中的每一门都和将来的主修课合理地搭配起来(distributional requirements),这样的努力至少对过分专业化的倾向起了冲淡的作用,至少在一个学生到学 有专长之前先打下全面发展的基础,然后才由博返约,在广泛的了解之后培养出自己的兴趣 来。你到底要从事什么专业,一开始可能完全是未知的。起先的选课几乎是一种“游学”,是 通过选课来发现你的兴趣和能力,是在有趣的实习中检验你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反 复地放弃,直至找到适合你从事的专业。但不管学什么专业,人类系统经验的几个基本类型 一数学、实验科学、历史、哲学和文学的阐释一则是必须全面了解的。本科生在耶鲁向 来被置于首位,所有的名教授都得给本科生上课,因为这些基础课程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而 在必要的时候,学生还可以要求教师做专门的辅导。耶鲁也不主张满堂灌的讲课,学生的自 由发言一直受到鼓励。因为通才教育就是要引导学生质疑和界定我们的价值,让学生自由探 讨,公开争议,接受挑战,只有冒险让不同的思想和价值得到自由的表达,才能培养出对偏 见和不宽容有勇气抗拒的公民。正如赖文对耶鲁的学生们所说:“你们既然幸运地有了自由 和独立的头脑,就不可避免地要担负捍卫自由和独立的责任。” 除了课堂学习,耶鲁还建立了十二个寄宿学院,让住在其中的学生在完全自治的环境中 -10-
- 10 - 的苍黄反复而耗竭了自己古老的脉气,致使社会过分求新的热潮浮躁得像老顽童一样滑稽, 传统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扬,甚至连幸存下来的旧事旧物也被时髦地包 装起来,与假古董、复制的古迹一起同流合污在后现代生意经的俗艳狂想中,诚如孟子所说,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然而长满了老树古木的城市毕竟在环境上更具有历史感, 也更容易触发人思旧的情怀。在又名榆城的纽海文市内,如今的榆树虽大不如十九世纪的作 家描写得那样铺天盖地,但合抱参天者依然随处可见,你既可以在晴日下享受其密布的浓阴, 也可以月下散步时欣赏其摇曳的幽姿。这块和平的土地就是这样神奇地得天独厚,精神只要 在她的泥土中扎下了深根,欣欣向荣的生意自然就会往没有限制的高空伸展开去。 耶鲁大学现由本科生部(这里习惯以“耶鲁学院”相称)、研究生院和十个专业学院构成, 而本科生始终都是学校的主体和教学的中心。同美国其他的大学一样,耶鲁的一二年级学是 无所谓学什么专业的,即使是三四年级选定了主修的方向,也只是在已经由博览形成的知识 广度上有所侧重地加强深度,为进一步读研究院或专业学院打下基础而已。从课程的设计和 选课规定,直到现任校长赖文(Richard C. Levin)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可以明显地看出,耶 鲁的大学本科教学一贯都坚持了这里常说的“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 谈起了通才教育的问题,又使我痛切地想到百年中国在各个方而都因缺乏积累而陷入的 困境。大学在西方是经过长期的积累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教育机构,它本来就有它的人文精神 传统。但在中国,大学的兴办则是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为了培养富国强兵的人才,从 一开始就有片面的功利倾向。五十年代向苏联学习的结果更加强化了人才培养的专业化方 向。因此,人才的培养只着重制造工具型的专业工作者,而不重视受教育者作为独立的个人 如何全面发展自身的问题。一个在入学前就被决定了所学专业的大学生,简直就是送进了大 学的人才生产线上加工的人“料”,不管他或她喜欢不喜欢或适合不适合所学的专业,专业一 旦决定,这个人就必须被制造成有用的专业工作者。 通才教育并不造就所谓“有用的”人才,其目的只是培养学生的悟性,扩充他们推理和感 受的能力。它并不教什么特殊的知识或技巧,而只为了丰富学生的心智,促使他们发展自己 批判地、独立地思考的能力,使他们尽量少受或不受偏见、迷信和教条的束缚。因此,通才 教育是以教育为目的本身的,它并不为任何特殊的目的服务。在一次毕业典礼的讲话中,赖 文曾明确指出,耶鲁并不打算为二十一世纪制造一批只精于运算、理财和做买卖的实业家, 或只懂得操纵媒体做有效交流的从政者。耶鲁要培养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引路人,他们要有创 造性独立思考的能力,要有能力在自己精通的专业知识之外思考更为广泛的问题。 也许赖文的期待有不少只属于他个人理想的成分,现代的受教育者已不是从前的有闲阶 级,文凭与求职的关系毕竟是很现实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从耶鲁学院的课程设计和要求 可以看出,所有的限制都有意防止学生选修的课程陷入过于狭窄的知识领域,都鞭策他们均 匀地选修四大类课程,使其中的每一门都和将来的主修课合理地搭配起来( distributional requirements),这样的努力至少对过分专业化的倾向起了冲淡的作用,至少在一个学生到学 有专长之前先打下全面发展的基础,然后才由博返约,在广泛的了解之后培养出自己的兴趣 来。你到底要从事什么专业,一开始可能完全是未知的。起先的选课几乎是一种“游学”,是 通过选课来发现你的兴趣和能力,是在有趣的实习中检验你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反 复地放弃,直至找到适合你从事的专业。但不管学什么专业,人类系统经验的几个基本类型 ——数学、实验科学、历史、哲学和文学的阐释——则是必须全面了解的。本科生在耶鲁向 来被置于首位,所有的名教授都得给本科生上课,因为这些基础课程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而 在必要的时候,学生还可以要求教师做专门的辅导。耶鲁也不主张满堂灌的讲课,学生的自 由发言一直受到鼓励。因为通才教育就是要引导学生质疑和界定我们的价值,让学生自由探 讨,公开争议,接受挑战,只有冒险让不同的思想和价值得到自由的表达,才能培养出对偏 见和不宽容有勇气抗拒的公民。正如赖文对耶鲁的学生们所说:“你们既然幸运地有了自由 和独立的头脑,就不可避免地要担负捍卫自由和独立的责任。” 除了课堂学习,耶鲁还建立了十二个寄宿学院,让住在其中的学生在完全自治的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