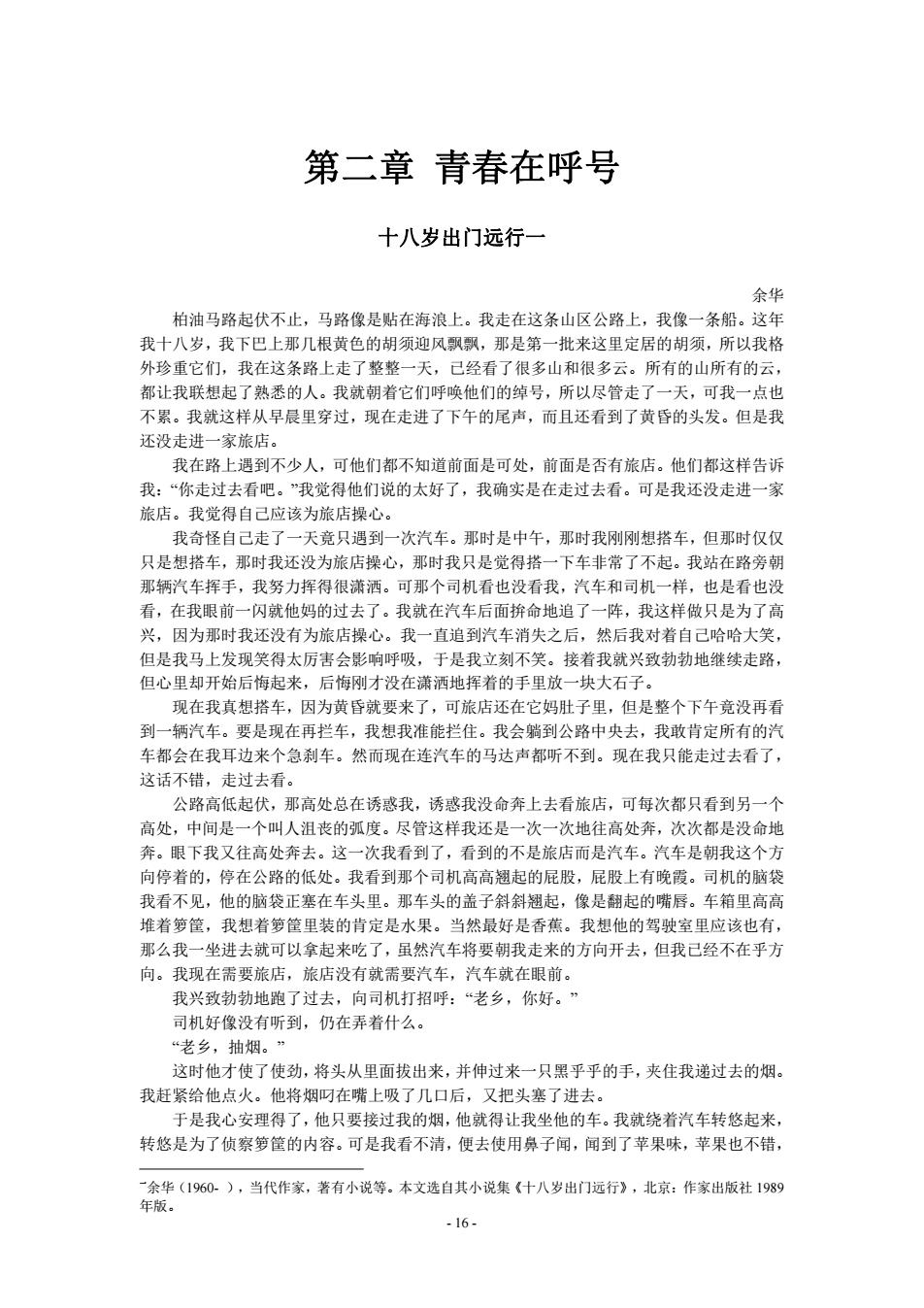
第二章青春在呼号 十八岁出门远行一 余华 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这年 我十八岁,我下巴上那几根黄色的胡须迎风飘飘,那是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胡须,所以我格 外珍重它们,我在这条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己经看了很多山和很多云。所有的山所有的云, 都让我联想起了熟悉的人。我就朝着它们呼唤他们的绰号,所以尽管走了一天,可我一点也 不累。我就这样从早晨里穿过,现在走进了下午的尾声,而且还看到了黄昏的头发。但是我 还没走进一家旅店。 我在路上遇到不少人,可他们都不知道前面是可处,前面是否有旅店。他们都这样告诉 我:“你走过去看吧。”我觉得他们说的太好了,我确实是在走过去看。可是我还没走进一家 旅店。我觉得自己应该为旅店操心。 我奇怪自己走了一天竞只遇到一次汽车。那时是中午,那时我刚刚想搭车,但那时仅仅 只是想搭车,那时我还没为旅店操心,那时我只是觉得搭一下车非常了不起。我站在路旁朝 那辆汽车挥手,我努力挥得很潇洒。可那个司机看也没看我,汽车和司机一样,也是看也没 看,在我眼前一闪就他妈的过去了。我就在汽车后面拚命地追了一阵,我这样做只是为了高 兴,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为旅店操心。我一直追到汽车消失之后,然后我对着自己哈哈大笑, 但是我马上发现笑得太厉害会影响呼吸,于是我立刻不笑。接着我就兴致勃勃地继续走路, 但心里却开始后悔起来,后悔刚才没在潇洒地挥着的手里放一块大石子。 现在我真想搭车,因为黄昏就要来了,可旅店还在它妈肚子里,但是整个下午竞没再看 到一辆汽车。要是现在再拦车,我想我准能拦住。我会躺到公路中央去,我敢肯定所有的汽 车都会在我耳边来个急刹车。然而现在连汽车的马达声都听不到。现在我只能走过去看了, 这话不错,走过去看。 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没命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 高处,中间是一个叫人沮丧的弧度。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次次都是没命地 奔。眼下我又往高处奔去。这一次我看到了,看到的不是旅店而是汽车。汽车是朝我这个方 向停着的,停在公路的低处。我看到那个司机高高翘起的屁股,屁股上有晚霞。司机的脑袋 我看不见,他的脑袋正塞在车头里。那车头的盖子斜斜翘起,像是翻起的嘴唇。车箱里高高 堆着箩筐,我想着箩筐里装的肯定是水果。当然最好是香蕉。我想他的驾驶室里应该也有, 那么我一坐进去就可以拿起来吃了,虽然汽车将要朝我走来的方向开去,但我己经不在乎方 向。我现在需要旅店,旅店没有就需要汽车,汽车就在眼前。 我兴致勃勃地跑了过去,向司机打招呼:“老乡,你好。” 司机好像没有听到,仍在弄着什么。 “老乡,抽烟。” 这时他才使了使劲,将头从里面拔出来,并伸过来一只黑乎乎的手,夹住我递过去的烟。 我赶紧给他点火。他将烟叼在嘴上吸了几口后,又把头塞了进去。 于是我心安理得了,他只要接过我的烟,他就得让我坐他的车。我就绕着汽车转悠起来, 转悠是为了侦察箩筐的内容。可是我看不清,便去使用鼻子闻,闻到了苹果味,苹果也不错, 一余华(1960-),当代作家,著有小说等。本文选自其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 年版。 -16-
- 16 - 第二章 青春在呼号 十八岁出门远行一 余华 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这年 我十八岁,我下巴上那几根黄色的胡须迎风飘飘,那是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胡须,所以我格 外珍重它们,我在这条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已经看了很多山和很多云。所有的山所有的云, 都让我联想起了熟悉的人。我就朝着它们呼唤他们的绰号,所以尽管走了一天,可我一点也 不累。我就这样从早晨里穿过,现在走进了下午的尾声,而且还看到了黄昏的头发。但是我 还没走进一家旅店。 我在路上遇到不少人,可他们都不知道前面是可处,前面是否有旅店。他们都这样告诉 我:“你走过去看吧。”我觉得他们说的太好了,我确实是在走过去看。可是我还没走进一家 旅店。我觉得自己应该为旅店操心。 我奇怪自己走了一天竟只遇到一次汽车。那时是中午,那时我刚刚想搭车,但那时仅仅 只是想搭车,那时我还没为旅店操心,那时我只是觉得搭一下车非常了不起。我站在路旁朝 那辆汽车挥手,我努力挥得很潇洒。可那个司机看也没看我,汽车和司机一样,也是看也没 看,在我眼前一闪就他妈的过去了。我就在汽车后面拚命地追了一阵,我这样做只是为了高 兴,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为旅店操心。我一直追到汽车消失之后,然后我对着自己哈哈大笑, 但是我马上发现笑得太厉害会影响呼吸,于是我立刻不笑。接着我就兴致勃勃地继续走路, 但心里却开始后悔起来,后悔刚才没在潇洒地挥着的手里放一块大石子。 现在我真想搭车,因为黄昏就要来了,可旅店还在它妈肚子里,但是整个下午竟没再看 到一辆汽车。要是现在再拦车,我想我准能拦住。我会躺到公路中央去,我敢肯定所有的汽 车都会在我耳边来个急刹车。然而现在连汽车的马达声都听不到。现在我只能走过去看了, 这话不错,走过去看。 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没命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 高处,中间是一个叫人沮丧的弧度。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次次都是没命地 奔。眼下我又往高处奔去。这一次我看到了,看到的不是旅店而是汽车。汽车是朝我这个方 向停着的,停在公路的低处。我看到那个司机高高翘起的屁股,屁股上有晚霞。司机的脑袋 我看不见,他的脑袋正塞在车头里。那车头的盖子斜斜翘起,像是翻起的嘴唇。车箱里高高 堆着箩筐,我想着箩筐里装的肯定是水果。当然最好是香蕉。我想他的驾驶室里应该也有, 那么我一坐进去就可以拿起来吃了,虽然汽车将要朝我走来的方向开去,但我已经不在乎方 向。我现在需要旅店,旅店没有就需要汽车,汽车就在眼前。 我兴致勃勃地跑了过去,向司机打招呼:“老乡,你好。” 司机好像没有听到,仍在弄着什么。 “老乡,抽烟。” 这时他才使了使劲,将头从里面拔出来,并伸过来一只黑乎乎的手,夹住我递过去的烟。 我赶紧给他点火。他将烟叼在嘴上吸了几口后,又把头塞了进去。 于是我心安理得了,他只要接过我的烟,他就得让我坐他的车。我就绕着汽车转悠起来, 转悠是为了侦察箩筐的内容。可是我看不清,便去使用鼻子闻,闻到了苹果味,苹果也不错, 一余华(1960- ),当代作家,著有小说等。本文选自其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北京:作家出版社 1989 年版

我这样想。 不一会他修好了车,就盖上车盖跳了下来。我赶紧走上去说:“老乡,我想搭车。”不料 他用黑乎乎的手推了我一把,粗暴地说:“滚开。” 我气得无话可说,他却慢悠悠地打开车门钻了进去,然后发动机响了起来。我知道要是 错过这次机会,将不再有机会。我知道现在应该豁出去了。于是我跑到另一侧,也拉开车门 钻了进去。我准备与他在驾驶室里大打一场。我进去时首先是冲着他吼了一声:“你嘴里还 叼着我的烟。”这时汽车已经活动了。 然而他却笑嘻嘻地十分友好地看起我来,这让我大惑不解。他问:“你上哪?” 我说:“随便上哪。” 他又亲切地问:“想吃苹果吗?”他仍然看着我。 “那还用问。” “到后面去拿吧。” 他把汽车开得那么快,我敢爬出驾驶室爬到后面去吗?于是我就说:“算了吧。” 他说:“去拿吧。”他的眼睛还在看着我。 我说:“别看了,我脸上没公路。” 他这才扭过头去看公路了。 汽车朝我来时的方向驰着,我舒服地坐在座椅上,看着窗外,和司机聊着天。现在我和 他已经成为朋友了。我已经知道他是在个体贩运。这汽车是他自己的,苹果也是他的。我还 听到了他口袋里面钱儿叮当响。我问他:“你到什么地方去?” 他说:“开过去看吧。” 这话简直像是我兄弟说的,这话可多亲切。我觉得自己与他更亲近了。车窗外的一切应 该是我熟悉的,那些山那些云都让我联想起来了另一帮熟悉人来了,于是我又叫唤起另一批 绰号来了。 现在我根本不在乎什么旅店,这汽车这司机这座椅让我心安而理得。我不知道汽车要到 什么地方去,他也不知道。反正前面是什么地方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只要汽车在驰着, 那就驰过去看吧。 可是这汽车抛锚了,那个时候我们己经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了。我把手搭在他肩上, 他把手搭在我肩上。他正在把他的恋爱说给我听,正要说第一次拥抱女性的感觉时,这汽车 抛锚了。汽车是在上坡时抛锚的,那个时候汽车突然不叫唤了,像死猪那样突然不动了。于 是他又爬到车头上去了,又把那上嘴唇翻了起来,脑袋又塞了进去。我坐在驾驶室里,我知 道他的屁股此刻肯定又高高翘起,但上嘴唇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到他的屁股,可我听得 到他修车的声音。 过了一会他把脑袋拔了出来,把车盖盖上。他那时的手更黑了,他把脏手在衣服上擦了 又擦,然后跳到地上走了过来。 “修好了?”我问。 “完了,没法修了。”他说。 我想完了,“那怎么办呢”我问。 “等着瞧吧。”他漫不经心地说。 我仍在汽车里坐着,不知该怎么办。眼下我又想起什么旅店来了。那个时候太阳要落山 了,晚霞则像蒸气似地在升腾。旅店就这样重又来到了我脑中,并且逐渐膨胀,不一会便把 我的脑袋塞满了。那时铁脑袋没有了,脑袋的地方长出了一个旅店。 司机这时在公路中央做起了广播操,他从第一节做到最后一节,做得很认真。做完又绕 着汽车小跑起来。司机也许是在驾驶室里呆得太久,现在他需要锻炼身体了。看着他在外面 活动,我在里面也坐不住,于是,打开车门也跳了下去。但我没做放手操也没小跑。我在想 着旅店和旅店。 这个时候我看到坡上有五个骑着自行车下来,每辆自行车后座上都用一根扁担绑着两只 -17-
- 17 - 我这样想。 不一会他修好了车,就盖上车盖跳了下来。我赶紧走上去说:“老乡,我想搭车。”不料 他用黑乎乎的手推了我一把,粗暴地说:“滚开。” 我气得无话可说,他却慢悠悠地打开车门钻了进去,然后发动机响了起来。我知道要是 错过这次机会,将不再有机会。我知道现在应该豁出去了。于是我跑到另一侧,也拉开车门 钻了进去。我准备与他在驾驶室里大打一场。我进去时首先是冲着他吼了一声:“你嘴里还 叼着我的烟。”这时汽车已经活动了。 然而他却笑嘻嘻地十分友好地看起我来,这让我大惑不解。他问:“你上哪?” 我说:“随便上哪。” 他又亲切地问:“想吃苹果吗?”他仍然看着我。 “那还用问。” “到后面去拿吧。” 他把汽车开得那么快,我敢爬出驾驶室爬到后面去吗?于是我就说:“算了吧。” 他说:“去拿吧。”他的眼睛还在看着我。 我说:“别看了,我脸上没公路。” 他这才扭过头去看公路了。 汽车朝我来时的方向驰着,我舒服地坐在座椅上,看着窗外,和司机聊着天。现在我和 他已经成为朋友了。我已经知道他是在个体贩运。这汽车是他自己的,苹果也是他的。我还 听到了他口袋里面钱儿叮当响。我问他:“你到什么地方去?” 他说:“开过去看吧。” 这话简直像是我兄弟说的,这话可多亲切。我觉得自己与他更亲近了。车窗外的一切应 该是我熟悉的,那些山那些云都让我联想起来了另一帮熟悉人来了,于是我又叫唤起另一批 绰号来了。 现在我根本不在乎什么旅店,这汽车这司机这座椅让我心安而理得。我不知道汽车要到 什么地方去,他也不知道。反正前面是什么地方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只要汽车在驰着, 那就驰过去看吧。 可是这汽车抛锚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了。我把手搭在他肩上, 他把手搭在我肩上。他正在把他的恋爱说给我听,正要说第一次拥抱女性的感觉时,这汽车 抛锚了。汽车是在上坡时抛锚的,那个时候汽车突然不叫唤了,像死猪那样突然不动了。于 是他又爬到车头上去了,又把那上嘴唇翻了起来,脑袋又塞了进去。我坐在驾驶室里,我知 道他的屁股此刻肯定又高高翘起,但上嘴唇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到他的屁股,可我听得 到他修车的声音。 过了一会他把脑袋拔了出来,把车盖盖上。他那时的手更黑了,他把脏手在衣服上擦了 又擦,然后跳到地上走了过来。 “修好了?”我问。 “完了,没法修了。”他说。 我想完了,“那怎么办呢”我问。 “等着瞧吧。”他漫不经心地说。 我仍在汽车里坐着,不知该怎么办。眼下我又想起什么旅店来了。那个时候太阳要落山 了,晚霞则像蒸气似地在升腾。旅店就这样重又来到了我脑中,并且逐渐膨胀,不一会便把 我的脑袋塞满了。那时铁脑袋没有了,脑袋的地方长出了一个旅店。 司机这时在公路中央做起了广播操,他从第一节做到最后一节,做得很认真。做完又绕 着汽车小跑起来。司机也许是在驾驶室里呆得太久,现在他需要锻炼身体了。看着他在外面 活动,我在里面也坐不住,于是,打开车门也跳了下去。但我没做放手操也没小跑。我在想 着旅店和旅店。 这个时候我看到坡上有五个骑着自行车下来,每辆自行车后座上都用一根扁担绑着两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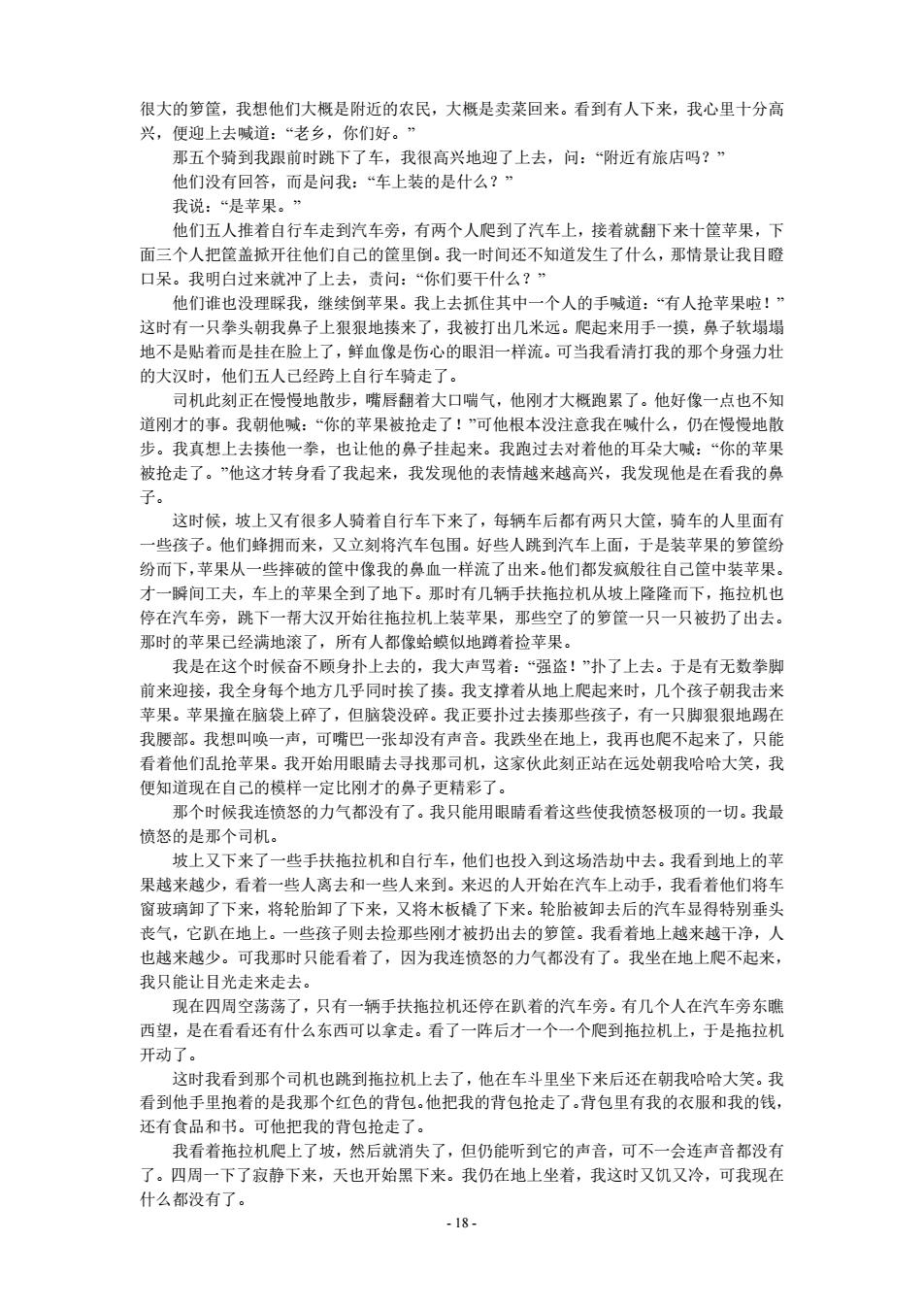
很大的箩筐,我想他们大概是附近的农民,大概是卖菜回来。看到有人下来,我心里十分高 兴,便迎上去喊道:“老乡,你们好。” 那五个骑到我跟前时跳下了车,我很高兴地迎了上去,问:“附近有旅店吗?” 他们没有回答,而是问我:“车上装的是什么?” 我说:“是苹果。” 他们五人推着自行车走到汽车旁,有两个人爬到了汽车上,接着就翻下来十筐苹果,下 面三个人把筐盖掀开往他们自己的筐里倒。我一时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情景让我目瞪 口呆。我明白过来就冲了上去,责问:“你们要干什么?” 他们谁也没理睬我,继续倒苹果。我上去抓住其中一个人的手喊道:“有人抢苹果啦!” 这时有一只拳头朝我鼻子上狠狠地揍来了,我被打出几米远。爬起来用手一摸,鼻子软塌塌 地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了,鲜血像是伤心的眼泪一样流。可当我看清打我的那个身强力壮 的大汉时,他们五人已经跨上自行车骑走了。 司机此刻正在慢慢地散步,嘴唇翻着大口喘气,他刚才大概跑累了。他好像一点也不知 道刚才的事。我朝他喊:“你的苹果被抢走了!”可他根本没注意我在喊什么,仍在慢慢地散 步。我真想上去揍他一拳,也让他的鼻子挂起来。我跑过去对着他的耳朵大喊:“你的苹果 被抢走了。”他这才转身看了我起来,我发现他的表情越来越高兴,我发现他是在看我的鼻 子。 这时候,坡上又有很多人骑着自行车下来了,每辆车后都有两只大筐,骑车的人里面有 一些孩子。他们蜂拥而来,又立刻将汽车包围。好些人跳到汽车上面,于是装苹果的箩筐纷 纷而下,苹果从一些摔破的筐中像我的鼻血一样流了出来。他们都发疯般往自己筐中装苹果。 才一瞬间工夫,车上的苹果全到了地下。那时有几辆手扶拖拉机从坡上隆隆而下,拖拉机也 停在汽车旁,跳下一帮大汉开始往拖拉机上装苹果,那些空了的箩筐一只一只被扔了出去。 那时的苹果己经满地滚了,所有人都像蛤蟆似地蹲着捡苹果。 我是在这个时候奋不顾身扑上去的,我大声骂着:“强盗!”扑了上去。于是有无数拳脚 前来迎接,我全身每个地方几乎同时挨了揍。我支撑着从地上爬起来时,几个孩子朝我击来 苹果。苹果撞在脑袋上碎了,但脑袋没碎。我正要扑过去揍那些孩子,有一只脚狠狠地踢在 我腰部。我想叫唤一声,可嘴巴一张却没有声音。我跌坐在地上,我再也爬不起来了,只能 看着他们乱抢苹果。我开始用眼晴去寻找那司机,这家伙此刻正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我 便知道现在自己的模样一定比刚才的鼻子更精彩了。 那个时候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只能用眼睛看着这些使我愤怒极顶的一切。我最 愤怒的是那个司机。 坡上又下来了一些手扶拖拉机和自行车,他们也投入到这场浩劫中去。我看到地上的苹 果越来越少,看着一些人离去和一些人来到。来迟的人开始在汽车上动手,我看着他们将车 窗玻璃卸了下来,将轮胎卸了下来,又将木板橇了下来。轮胎被卸去后的汽车显得特别垂头 丧气,它趴在地上。一些孩子则去捡那些刚才被扔出去的箩筐。我看着地上越来越干净,人 也越来越少。可我那时只能看着了,因为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 我只能让目光走来走去。 现在四周空荡荡了,只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还停在趴着的汽车旁。有几个人在汽车旁东瞧 西望,是在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走。看了一阵后才一个一个爬到拖拉机上,于是拖拉机 开动了。 这时我看到那个司机也跳到拖拉机上去了,他在车斗里坐下来后还在朝我哈哈大笑。我 看到他手里抱着的是我那个红色的背包。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背包里有我的衣服和我的钱, 还有食品和书。可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 我看着拖拉机爬上了坡,然后就消失了,但仍能听到它的声音,可不一会连声音都没有 了。四周一下了寂静下来,天也开始黑下来。我仍在地上坐着,我这时又饥又冷,可我现在 什么都没有了。 -18-
- 18 - 很大的箩筐,我想他们大概是附近的农民,大概是卖菜回来。看到有人下来,我心里十分高 兴,便迎上去喊道:“老乡,你们好。” 那五个骑到我跟前时跳下了车,我很高兴地迎了上去,问:“附近有旅店吗?” 他们没有回答,而是问我:“车上装的是什么?” 我说:“是苹果。” 他们五人推着自行车走到汽车旁,有两个人爬到了汽车上,接着就翻下来十筐苹果,下 面三个人把筐盖掀开往他们自己的筐里倒。我一时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情景让我目瞪 口呆。我明白过来就冲了上去,责问:“你们要干什么?” 他们谁也没理睬我,继续倒苹果。我上去抓住其中一个人的手喊道:“有人抢苹果啦!” 这时有一只拳头朝我鼻子上狠狠地揍来了,我被打出几米远。爬起来用手一摸,鼻子软塌塌 地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了,鲜血像是伤心的眼泪一样流。可当我看清打我的那个身强力壮 的大汉时,他们五人已经跨上自行车骑走了。 司机此刻正在慢慢地散步,嘴唇翻着大口喘气,他刚才大概跑累了。他好像一点也不知 道刚才的事。我朝他喊:“你的苹果被抢走了!”可他根本没注意我在喊什么,仍在慢慢地散 步。我真想上去揍他一拳,也让他的鼻子挂起来。我跑过去对着他的耳朵大喊:“你的苹果 被抢走了。”他这才转身看了我起来,我发现他的表情越来越高兴,我发现他是在看我的鼻 子。 这时候,坡上又有很多人骑着自行车下来了,每辆车后都有两只大筐,骑车的人里面有 一些孩子。他们蜂拥而来,又立刻将汽车包围。好些人跳到汽车上面,于是装苹果的箩筐纷 纷而下,苹果从一些摔破的筐中像我的鼻血一样流了出来。他们都发疯般往自己筐中装苹果。 才一瞬间工夫,车上的苹果全到了地下。那时有几辆手扶拖拉机从坡上隆隆而下,拖拉机也 停在汽车旁,跳下一帮大汉开始往拖拉机上装苹果,那些空了的箩筐一只一只被扔了出去。 那时的苹果已经满地滚了,所有人都像蛤蟆似地蹲着捡苹果。 我是在这个时候奋不顾身扑上去的,我大声骂着:“强盗!”扑了上去。于是有无数拳脚 前来迎接,我全身每个地方几乎同时挨了揍。我支撑着从地上爬起来时,几个孩子朝我击来 苹果。苹果撞在脑袋上碎了,但脑袋没碎。我正要扑过去揍那些孩子,有一只脚狠狠地踢在 我腰部。我想叫唤一声,可嘴巴一张却没有声音。我跌坐在地上,我再也爬不起来了,只能 看着他们乱抢苹果。我开始用眼睛去寻找那司机,这家伙此刻正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我 便知道现在自己的模样一定比刚才的鼻子更精彩了。 那个时候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只能用眼睛看着这些使我愤怒极顶的一切。我最 愤怒的是那个司机。 坡上又下来了一些手扶拖拉机和自行车,他们也投入到这场浩劫中去。我看到地上的苹 果越来越少,看着一些人离去和一些人来到。来迟的人开始在汽车上动手,我看着他们将车 窗玻璃卸了下来,将轮胎卸了下来,又将木板橇了下来。轮胎被卸去后的汽车显得特别垂头 丧气,它趴在地上。一些孩子则去捡那些刚才被扔出去的箩筐。我看着地上越来越干净,人 也越来越少。可我那时只能看着了,因为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 我只能让目光走来走去。 现在四周空荡荡了,只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还停在趴着的汽车旁。有几个人在汽车旁东瞧 西望,是在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走。看了一阵后才一个一个爬到拖拉机上,于是拖拉机 开动了。 这时我看到那个司机也跳到拖拉机上去了,他在车斗里坐下来后还在朝我哈哈大笑。我 看到他手里抱着的是我那个红色的背包。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背包里有我的衣服和我的钱, 还有食品和书。可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 我看着拖拉机爬上了坡,然后就消失了,但仍能听到它的声音,可不一会连声音都没有 了。四周一下了寂静下来,天也开始黑下来。我仍在地上坐着,我这时又饥又冷,可我现在 什么都没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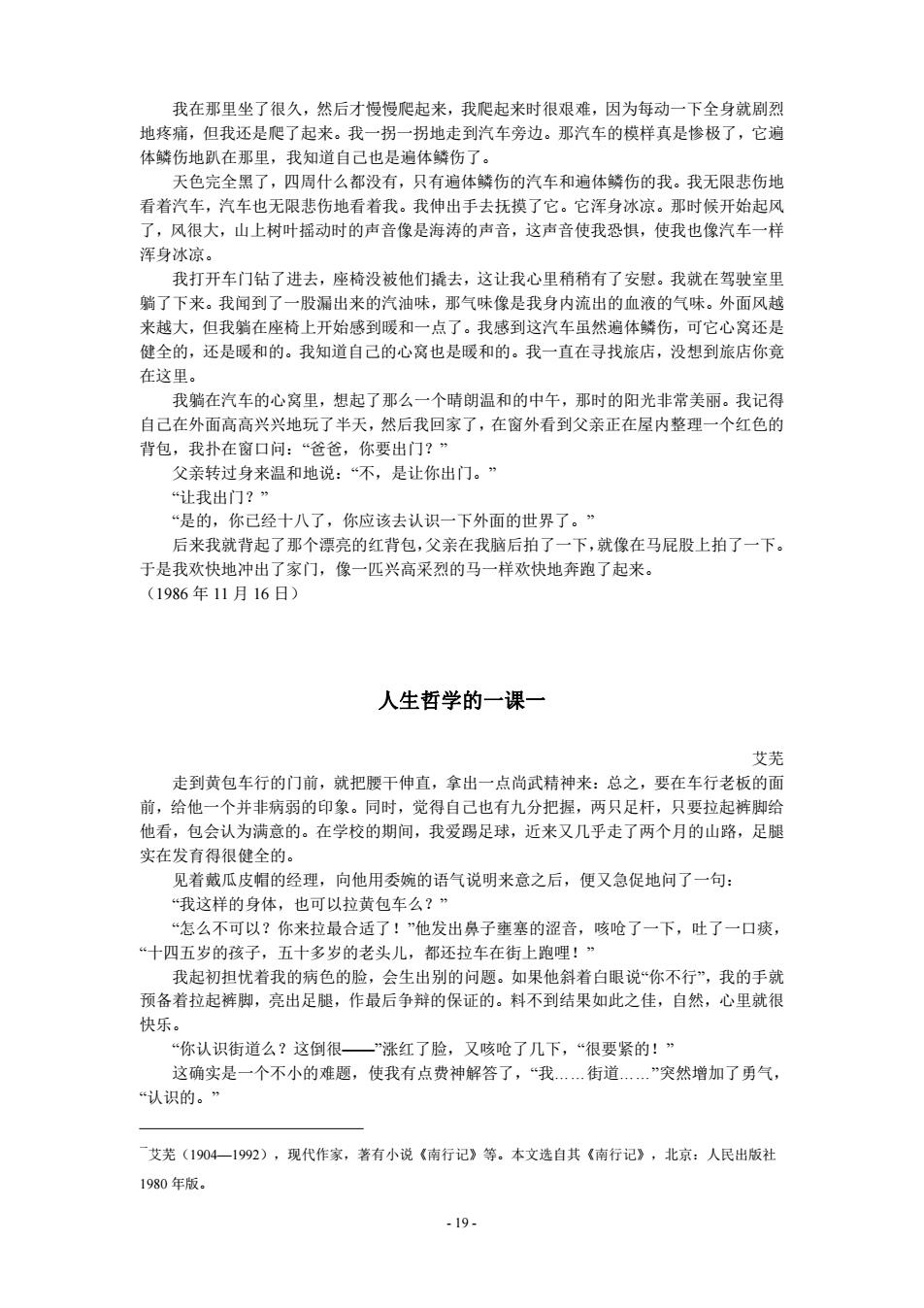
我在那里坐了很久,然后才慢慢爬起来,我爬起来时很艰难,因为每动一下全身就刷烈 地疼痛,但我还是爬了起来。我一拐一拐地走到汽车旁边。那汽车的模样真是惨极了,它遍 体鳞伤地趴在那里,我知道自己也是遍体鳞伤了。 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 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了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开始起风 了,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也像汽车一样 浑身冰凉。 我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座椅没被他们撬去,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了安慰。我就在驾驶室里 躺了下来。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那气味像是我身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外面风越 来越大,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一点了。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 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竞 在这里。 我躺在汽车的心窝里,想起了那么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那时的阳光非常美丽。我记得 自己在外面高高兴兴地玩了半天,然后我回家了,在窗外看到父亲正在屋内整理一个红色的 背包,我扑在窗口问:“爸爸,你要出门?” 父亲转过身来温和地说:“不,是让你出门。” “让我出门?” “是的,你己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 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1986年11月16日) 人生哲学的一课一 艾芜 走到黄包车行的门前,就把腰干伸直,拿出一点尚武精神来:总之,要在车行老板的面 前,给他一个并非病弱的印象。同时,觉得自己也有九分把握,两只足杆,只要拉起裤脚给 他看,包会认为满意的。在学校的期间,我爱踢足球,近来又几乎走了两个月的山路,足腿 实在发育得很健全的。 见着戴瓜皮帽的经理,向他用委婉的语气说明来意之后,便又急促地问了一句: “我这样的身体,也可以拉黄包车么?” “怎么不可以?你来拉最合适了!”他发出鼻子壅塞的涩音,咳呛了一下,吐了一口痰, “十四五岁的孩子,五十多岁的老头儿,都还拉车在街上跑哩!” 我起初担忧着我的病色的脸,会生出别的问题。如果他斜着白眼说“你不行”,我的手就 预备着拉起裤脚,亮出足腿,作最后争辩的保证的。料不到结果如此之佳,自然,心里就很 快乐。 “你认识街道么?这倒很一”涨红了脸,又咳呛了几下,“很要紧的!” 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使我有点费神解答了,“我..街道…”突然增加了勇气, “认识的。” 一艾芜(1904一1992),现代作家,著有小说《南行记》等。本文选自其《南行记》,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19-
- 19 - 我在那里坐了很久,然后才慢慢爬起来,我爬起来时很艰难,因为每动一下全身就剧烈 地疼痛,但我还是爬了起来。我一拐一拐地走到汽车旁边。那汽车的模样真是惨极了,它遍 体鳞伤地趴在那里,我知道自己也是遍体鳞伤了。 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 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了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开始起风 了,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也像汽车一样 浑身冰凉。 我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座椅没被他们撬去,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了安慰。我就在驾驶室里 躺了下来。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那气味像是我身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外面风越 来越大,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一点了。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 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 在这里。 我躺在汽车的心窝里,想起了那么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那时的阳光非常美丽。我记得 自己在外面高高兴兴地玩了半天,然后我回家了,在窗外看到父亲正在屋内整理一个红色的 背包,我扑在窗口问:“爸爸,你要出门?” 父亲转过身来温和地说:“不,是让你出门。” “让我出门?” “是的,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 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1986 年 11 月 16 日) 人生哲学的一课一 艾芜 走到黄包车行的门前,就把腰干伸直,拿出一点尚武精神来:总之,要在车行老板的面 前,给他一个并非病弱的印象。同时,觉得自己也有九分把握,两只足杆,只要拉起裤脚给 他看,包会认为满意的。在学校的期间,我爱踢足球,近来又几乎走了两个月的山路,足腿 实在发育得很健全的。 见着戴瓜皮帽的经理,向他用委婉的语气说明来意之后,便又急促地问了一句: “我这样的身体,也可以拉黄包车么?” “怎么不可以?你来拉最合适了!”他发出鼻子壅塞的涩音,咳呛了一下,吐了一口痰, “十四五岁的孩子,五十多岁的老头儿,都还拉车在街上跑哩!” 我起初担忧着我的病色的脸,会生出别的问题。如果他斜着白眼说“你不行”,我的手就 预备着拉起裤脚,亮出足腿,作最后争辩的保证的。料不到结果如此之佳,自然,心里就很 快乐。 “你认识街道么?这倒很——”涨红了脸,又咳呛了几下,“很要紧的!” 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使我有点费神解答了,“我……街道……”突然增加了勇气, “认识的。” 一艾芜(1904—1992),现代作家,著有小说《南行记》等。本文选自其《南行记》,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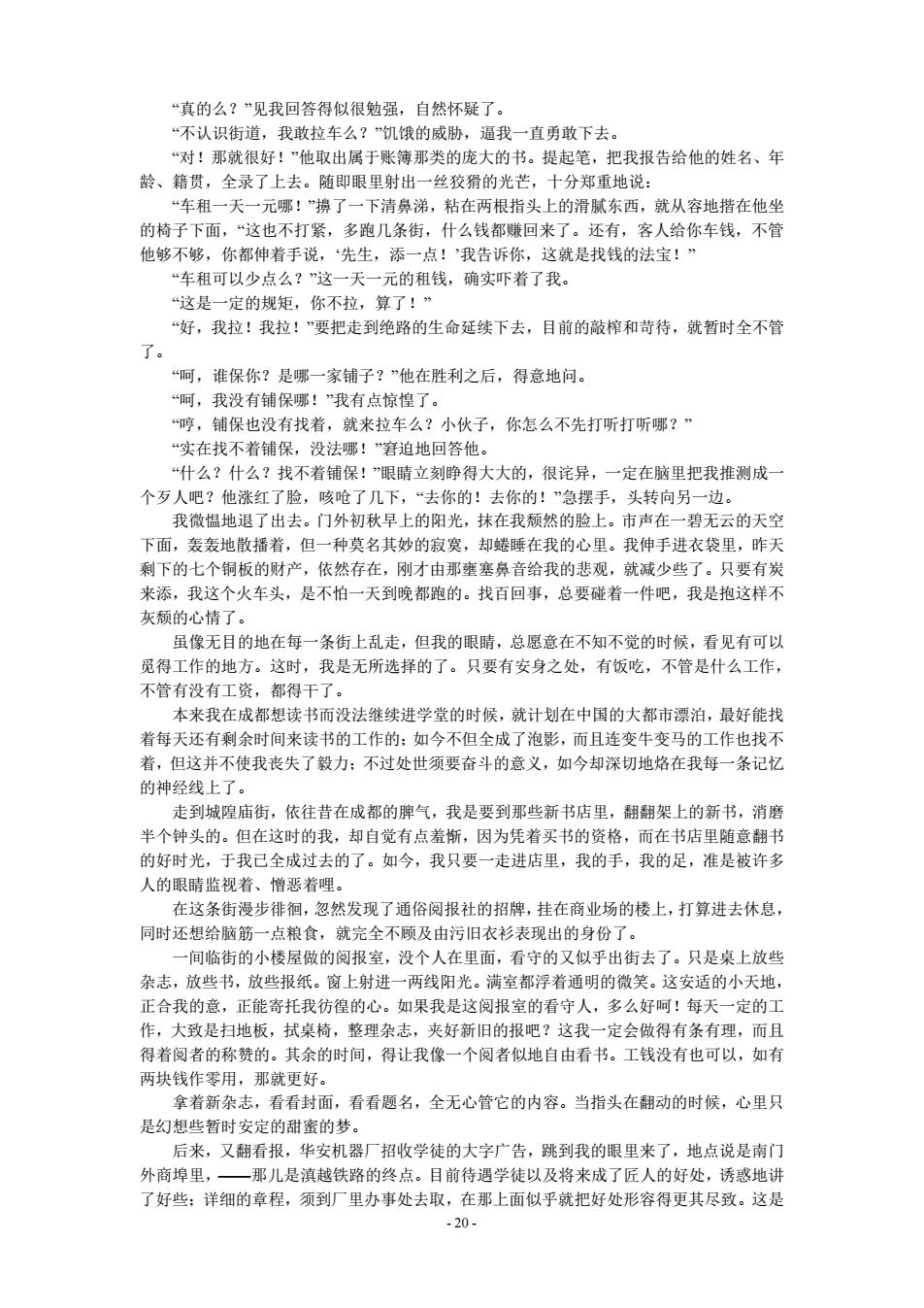
“真的么?”见我回答得似很勉强,自然怀疑了。 “不认识街道,我敢拉车么?饥饿的威胁,逼我一直勇敢下去。 “对!那就很好!”他取出属于账簿那类的庞大的书。提起笔,把我报告给他的姓名、年 龄、籍贯,全录了上去。随即眼里射出一丝狡猾的光芒,十分郑重地说: “车租一天一元哪!”擤了一下清鼻涕,粘在两根指头上的滑腻东西,就从容地揩在他坐 的椅子下面,“这也不打紧,多跑几条街,什么钱都赚回来了。还有,客人给你车钱,不管 他够不够,你都伸着手说,先生,添一点!我告诉你,这就是找钱的法宝!” “车租可以少点么?”这一天一元的租钱,确实吓着了我。 “这是一定的规矩,你不拉,算了!” “好,我拉!我拉!”要把走到绝路的生命延续下去,目前的敲榨和苛待,就暂时全不管 了。 “呵,谁保你?是哪一家铺子?”他在胜利之后,得意地问。 “呵,我没有铺保哪!”我有点惊惶了。 “哼,铺保也没有找着,就来拉车么?小伙子,你怎么不先打听打听哪?” “实在找不着铺保,没法哪!”窘迫地回答他。 “什么?什么?找不着铺保!”眼晴立刻睁得大大的,很诧异,一定在脑里把我推测成一 个歹人吧?他涨红了脸,咳呛了几下,“去你的!去你的!”急摆手,头转向另一边。 我微愠地退了出去。门外初秋早上的阳光,抹在我颓然的脸上。市声在一碧无云的天空 下面,轰轰地散播着,但一种莫名其妙的寂寞,却蜷睡在我的心里。我伸手进衣袋里,昨天 剩下的七个铜板的财产,依然存在,刚才由那壅塞鼻音给我的悲观,就减少些了。只要有炭 来添,我这个火车头,是不怕一天到晚都跑的。找百回事,总要碰着一件吧,我是抱这样不 灰颓的心情了。 虽像无目的地在每一条街上乱走,但我的眼睛,总愿意在不知不觉的时候,看见有可以 觅得工作的地方。这时,我是无所选择的了。只要有安身之处,有饭吃,不管是什么工作, 不管有没有工资,都得干了。 本来我在成都想读书而没法继续进学堂的时候,就计划在中国的大都市漂泊,最好能找 着每天还有剩余时间来读书的工作的:如今不但全成了泡影,而且连变牛变马的工作也找不 着,但这并不使我丧失了毅力:不过处世须要奋斗的意义,如今却深切地烙在我每一条记忆 的神经线上了。 走到城隍庙街,依往昔在成都的脾气,我是要到那些新书店里,翻翻架上的新书,消磨 半个钟头的。但在这时的我,却自觉有点羞惭,因为凭着买书的资格,而在书店里随意翻书 的好时光,于我己全成过去的了。如今,我只要一走进店里,我的手,我的足,准是被许多 人的眼睛监视着、憎恶着哩。 在这条街漫步徘徊,忽然发现了通俗阅报社的招牌,挂在商业场的楼上,打算进去休息, 同时还想给脑筋一点粮食,就完全不顾及由污旧衣衫表现出的身份了。 一间临街的小楼屋做的阅报室,没个人在里面,看守的又似乎出街去了。只是桌上放些 杂志,放些书,放些报纸。窗上射进一两线阳光。满室都浮着通明的微笑。这安适的小天地, 正合我的意,正能寄托我彷徨的心。如果我是这阅报室的看守人,多么好呵!每天一定的工 作,大致是扫地板,拭桌椅,整理杂志,夹好新旧的报吧?这我一定会做得有条有理,而且 得着阅者的称赞的。其余的时间,得让我像一个阅者似地自由看书。工钱没有也可以,如有 两块钱作零用,那就更好。 拿着新杂志,看看封面,看看题名,全无心管它的内容。当指头在翻动的时候,心里只 是幻想些暂时安定的甜蜜的梦。 后来,又翻看报,华安机器厂招收学徒的大字广告,跳到我的眼里来了,地点说是南门 外商埠里,一那儿是滇越铁路的终点。目前待遇学徒以及将来成了匠人的好处,诱惑地讲 了好些:详细的章程,须到厂里办事处去取,在那上面似乎就把好处形容得更其尽致。这是 -20-
- 20 - “真的么?”见我回答得似很勉强,自然怀疑了。 “不认识街道,我敢拉车么?”饥饿的威胁,逼我一直勇敢下去。 “对!那就很好!”他取出属于账簿那类的庞大的书。提起笔,把我报告给他的姓名、年 龄、籍贯,全录了上去。随即眼里射出一丝狡猾的光芒,十分郑重地说: “车租一天一元哪!”擤了一下清鼻涕,粘在两根指头上的滑腻东西,就从容地揩在他坐 的椅子下面,“这也不打紧,多跑几条街,什么钱都赚回来了。还有,客人给你车钱,不管 他够不够,你都伸着手说,‘先生,添一点!’我告诉你,这就是找钱的法宝!” “车租可以少点么?”这一天一元的租钱,确实吓着了我。 “这是一定的规矩,你不拉,算了!” “好,我拉!我拉!”要把走到绝路的生命延续下去,目前的敲榨和苛待,就暂时全不管 了。 “呵,谁保你?是哪一家铺子?”他在胜利之后,得意地问。 “呵,我没有铺保哪!”我有点惊惶了。 “哼,铺保也没有找着,就来拉车么?小伙子,你怎么不先打听打听哪?” “实在找不着铺保,没法哪!”窘迫地回答他。 “什么?什么?找不着铺保!”眼睛立刻睁得大大的,很诧异,一定在脑里把我推测成一 个歹人吧?他涨红了脸,咳呛了几下,“去你的!去你的!”急摆手,头转向另一边。 我微愠地退了出去。门外初秋早上的阳光,抹在我颓然的脸上。市声在一碧无云的天空 下面,轰轰地散播着,但一种莫名其妙的寂寞,却蜷睡在我的心里。我伸手进衣袋里,昨天 剩下的七个铜板的财产,依然存在,刚才由那壅塞鼻音给我的悲观,就减少些了。只要有炭 来添,我这个火车头,是不怕一天到晚都跑的。找百回事,总要碰着一件吧,我是抱这样不 灰颓的心情了。 虽像无目的地在每一条街上乱走,但我的眼睛,总愿意在不知不觉的时候,看见有可以 觅得工作的地方。这时,我是无所选择的了。只要有安身之处,有饭吃,不管是什么工作, 不管有没有工资,都得干了。 本来我在成都想读书而没法继续进学堂的时候,就计划在中国的大都市漂泊,最好能找 着每天还有剩余时间来读书的工作的;如今不但全成了泡影,而且连变牛变马的工作也找不 着,但这并不使我丧失了毅力;不过处世须要奋斗的意义,如今却深切地烙在我每一条记忆 的神经线上了。 走到城隍庙街,依往昔在成都的脾气,我是要到那些新书店里,翻翻架上的新书,消磨 半个钟头的。但在这时的我,却自觉有点羞惭,因为凭着买书的资格,而在书店里随意翻书 的好时光,于我已全成过去的了。如今,我只要一走进店里,我的手,我的足,准是被许多 人的眼睛监视着、憎恶着哩。 在这条街漫步徘徊,忽然发现了通俗阅报社的招牌,挂在商业场的楼上,打算进去休息, 同时还想给脑筋一点粮食,就完全不顾及由污旧衣衫表现出的身份了。 一间临街的小楼屋做的阅报室,没个人在里面,看守的又似乎出街去了。只是桌上放些 杂志,放些书,放些报纸。窗上射进一两线阳光。满室都浮着通明的微笑。这安适的小天地, 正合我的意,正能寄托我彷徨的心。如果我是这阅报室的看守人,多么好呵!每天一定的工 作,大致是扫地板,拭桌椅,整理杂志,夹好新旧的报吧?这我一定会做得有条有理,而且 得着阅者的称赞的。其余的时间,得让我像一个阅者似地自由看书。工钱没有也可以,如有 两块钱作零用,那就更好。 拿着新杂志,看看封面,看看题名,全无心管它的内容。当指头在翻动的时候,心里只 是幻想些暂时安定的甜蜜的梦。 后来,又翻看报,华安机器厂招收学徒的大字广告,跳到我的眼里来了,地点说是南门 外商埠里,——那儿是滇越铁路的终点。目前待遇学徒以及将来成了匠人的好处,诱惑地讲 了好些;详细的章程,须到厂里办事处去取,在那上面似乎就把好处形容得更其尽致。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