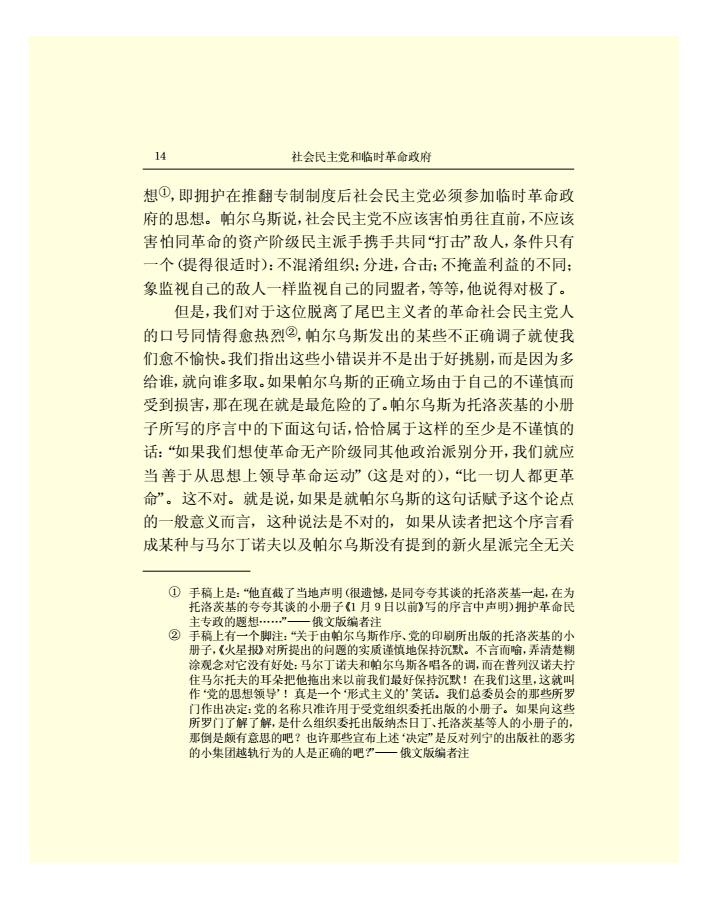
想①,即拥护在推翻专制制度后社会民主党必须参加临时革命政 府的思想。帕尔乌斯说,社会民主党不应该害怕勇往直前,不应该 害怕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手携手共同“打击”敌人,条件只有 一个(提得很适时):不混淆组织;分进,合击;不掩盖利益的不同; 象监视自己的敌人一样监视自己的同盟者,等等,他说得对极了。 但是,我们对于这位脱离了尾巴主义者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 的口号同情得愈热烈②,帕尔乌斯发出的某些不正确调子就使我 们愈不愉快。我们指出这些小错误并不是出于好挑剔,而是因为多 给谁,就向谁多取。如果帕尔乌斯的正确立场由于自己的不谨慎而 受到损害,那在现在就是最危险的了。帕尔乌斯为托洛茨基的小册 子所写的序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恰恰属于这样的至少是不谨慎的 话:“如果我们想使革命无产阶级同其他政治派别分开,我们就应 当 善于从思想上领导革命运动”(这是对的),“比一切人都更革 命”。这不对。就是说,如果是就帕尔乌斯的这句话赋予这个论点 的一般意义而言,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从读者把这个序言看 成某种与马尔丁诺夫以及帕尔乌斯没有提到的新火星派完全无关 14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 ① ② 手稿上有一个脚注:“关于由帕尔乌斯作序、党的印刷所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小 册子,《火星报》对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谨慎地保持沉默。不言而喻,弄清楚糊 涂观念对它没有好处:马尔丁诺夫和帕尔乌斯各唱各的调,而在普列汉诺夫拧 住马尔托夫的耳朵把他拖出来以前我们最好保持沉默!在我们这里,这就叫 作‘党的思想领导’!真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笑话。我们总委员会的那些所罗 门作出决定:党的名称只准许用于受党组织委托出版的小册子。如果向这些 所罗门了解了解,是什么组织委托出版纳杰日丁、托洛茨基等人的小册子的, 那倒是颇有意思的吧?也许那些宣布上述‘决定”是反对列宁的出版社的恶劣 的小集团越轨行为的人是正确的吧?”—— 俄文版编者注 手稿上是:“他直截了当地声明(很遗憾,是同夸夸其谈的托洛茨基一起,在为 托洛茨基的夸夸其谈的小册子《1月9日以前》写的序言中声明)拥护革命民 主专政的题想……”——俄文版编者注
想①,即拥护在推翻专制制度后社会民主党必须参加临时革命政 府的思想。帕尔乌斯说,社会民主党不应该害怕勇往直前,不应该 害怕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手携手共同“打击”敌人,条件只有 一个(提得很适时):不混淆组织;分进,合击;不掩盖利益的不同; 象监视自己的敌人一样监视自己的同盟者,等等,他说得对极了。 但是,我们对于这位脱离了尾巴主义者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 的口号同情得愈热烈②,帕尔乌斯发出的某些不正确调子就使我 们愈不愉快。我们指出这些小错误并不是出于好挑剔,而是因为多 给谁,就向谁多取。如果帕尔乌斯的正确立场由于自己的不谨慎而 受到损害,那在现在就是最危险的了。帕尔乌斯为托洛茨基的小册 子所写的序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恰恰属于这样的至少是不谨慎的 话:“如果我们想使革命无产阶级同其他政治派别分开,我们就应 当 善于从思想上领导革命运动”(这是对的),“比一切人都更革 命”。这不对。就是说,如果是就帕尔乌斯的这句话赋予这个论点 的一般意义而言,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从读者把这个序言看 成某种与马尔丁诺夫以及帕尔乌斯没有提到的新火星派完全无关 14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 ① ② 手稿上有一个脚注:“关于由帕尔乌斯作序、党的印刷所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小 册子,《火星报》对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谨慎地保持沉默。不言而喻,弄清楚糊 涂观念对它没有好处:马尔丁诺夫和帕尔乌斯各唱各的调,而在普列汉诺夫拧 住马尔托夫的耳朵把他拖出来以前我们最好保持沉默!在我们这里,这就叫 作‘党的思想领导’!真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笑话。我们总委员会的那些所罗 门作出决定:党的名称只准许用于受党组织委托出版的小册子。如果向这些 所罗门了解了解,是什么组织委托出版纳杰日丁、托洛茨基等人的小册子的, 那倒是颇有意思的吧?也许那些宣布上述‘决定”是反对列宁的出版社的恶劣 的小集团越轨行为的人是正确的吧?”—— 俄文版编者注 手稿上是:“他直截了当地声明(很遗憾,是同夸夸其谈的托洛茨基一起,在为 托洛茨基的夸夸其谈的小册子《1月9日以前》写的序言中声明)拥护革命民 主专政的题想……”——俄文版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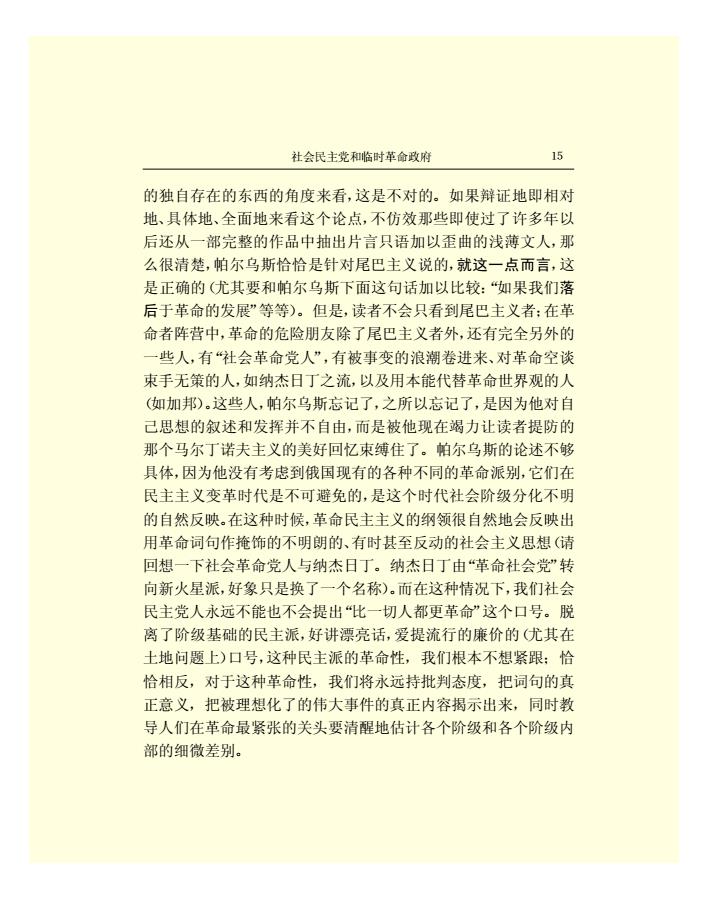
的独自存在的东西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对的。如果辩证地即相对 地、具体地、全面地来看这个论点,不仿效那些即使过了许多年以 后还从一部完整的作品中抽出片言只语加以歪曲的浅薄文人,那 么很清楚,帕尔乌斯恰恰是针对尾巴主义说的,就这一点而言,这 是正确的(尤其要和帕尔乌斯下面这句话加以比较:“如果我们落 后于革命的发展”等等)。但是,读者不会只看到尾巴主义者;在革 命者阵营中,革命的危险朋友除了尾巴主义者外,还有完全另外的 一些人,有“社会革命党人”,有被事变的浪潮卷进来、对革命空谈 束手无策的人,如纳杰日丁之流,以及用本能代替革命世界观的人 (如加邦)。这些人,帕尔乌斯忘记了,之所以忘记了,是因为他对自 己思想的叙述和发挥并不自由,而是被他现在竭力让读者提防的 那个马尔丁诺夫主义的美好回忆束缚住了。帕尔乌斯的论述不够 具体,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俄国现有的各种不同的革命派别,它们在 民主主义变革时代是不可避免的,是这个时代社会阶级分化不明 的自然反映。在这种时候,革命民主主义的纲领很自然地会反映出 用革命词句作掩饰的不明朗的、有时甚至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想(请 回想一下社会革命党人与纳杰日丁。纳杰日丁由“革命社会党”转 向新火星派,好象只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社会 民主党人永远不能也不会提出“比一切人都更革命”这个口号。脱 离了阶级基础的民主派,好讲漂亮话,爱提流行的廉价的(尤其在 土地问题上)口号,这种民主派的革命性,我们根本不想紧跟;恰 恰相反,对于这种革命性,我们将永远持批判态度,把词句的真 正意义,把被理想化了的伟大事件的真正内容揭示出来,同时教 导人们在革命最紧张的关头要清醒地估计各个阶级和各个阶级内 部的细微差别。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 15
的独自存在的东西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对的。如果辩证地即相对 地、具体地、全面地来看这个论点,不仿效那些即使过了许多年以 后还从一部完整的作品中抽出片言只语加以歪曲的浅薄文人,那 么很清楚,帕尔乌斯恰恰是针对尾巴主义说的,就这一点而言,这 是正确的(尤其要和帕尔乌斯下面这句话加以比较:“如果我们落 后于革命的发展”等等)。但是,读者不会只看到尾巴主义者;在革 命者阵营中,革命的危险朋友除了尾巴主义者外,还有完全另外的 一些人,有“社会革命党人”,有被事变的浪潮卷进来、对革命空谈 束手无策的人,如纳杰日丁之流,以及用本能代替革命世界观的人 (如加邦)。这些人,帕尔乌斯忘记了,之所以忘记了,是因为他对自 己思想的叙述和发挥并不自由,而是被他现在竭力让读者提防的 那个马尔丁诺夫主义的美好回忆束缚住了。帕尔乌斯的论述不够 具体,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俄国现有的各种不同的革命派别,它们在 民主主义变革时代是不可避免的,是这个时代社会阶级分化不明 的自然反映。在这种时候,革命民主主义的纲领很自然地会反映出 用革命词句作掩饰的不明朗的、有时甚至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想(请 回想一下社会革命党人与纳杰日丁。纳杰日丁由“革命社会党”转 向新火星派,好象只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社会 民主党人永远不能也不会提出“比一切人都更革命”这个口号。脱 离了阶级基础的民主派,好讲漂亮话,爱提流行的廉价的(尤其在 土地问题上)口号,这种民主派的革命性,我们根本不想紧跟;恰 恰相反,对于这种革命性,我们将永远持批判态度,把词句的真 正意义,把被理想化了的伟大事件的真正内容揭示出来,同时教 导人们在革命最紧张的关头要清醒地估计各个阶级和各个阶级内 部的细微差别。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 15

根据同样的理由,帕尔乌斯的下述论点也是不对的:“俄国临 时革命政府将是工人民主派的政府”,“如果社会民主党领导俄国 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那么这个政府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 社会民主主义的临时政府“将是社会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完整的政 府”。如果讲的不是瞬息即逝的偶然事件,而是在历史上多少能留 下点痕迹的时间比较长的革命专政,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 的。这种情况之所以不可能有,是因为只有依靠绝大多数人民的革 命专政才可能是比较巩固(当然不是绝对巩固,而是相对巩固)的 专政。而俄国无产阶级目前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它只有和半无 产者、半有产者群众,即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联合起来,才 能成为绝大多数。可能的和所希望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的 这种构成,当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的构成上,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 色的代表必然要参加这个政府,或者甚至在这个政府中占优势。在 这个问题上抱任何幻想都是十分有害的。空谈家托洛茨基现在说 (可惜是和帕尔乌斯一道),“加邦神父只能出现一次”,“第二个加 邦没有立足之地”,这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空谈家。如果俄国没有第 二个加邦的立足之地,那么,在我们这里,真正“伟大的”、彻底的民 主主义革命的立足之地也就不会有了。革命要成为伟大的革命,要 象1789—1793年,而不是象1848—1850年,并且要超过它们,就 必须唤起广大群众投入积极的生活,英勇奋斗,进行“扎扎实实的 历史性创造”,从可怕的无知状态,从空前的闭塞状态,从难以想象 的野蛮状态和暗无天日的愚昧状态觉醒起来。革命已经开始唤起 群众,它一定会唤起群众,—— 政府本身正在以自己痉挛性的反抗 促进这项工作,但是,不言而喻,要说这些群众和他们的为数众 多的 “土生土长的” 民众首领、甚至农民首领已经有成熟的政治 16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
根据同样的理由,帕尔乌斯的下述论点也是不对的:“俄国临 时革命政府将是工人民主派的政府”,“如果社会民主党领导俄国 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那么这个政府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 社会民主主义的临时政府“将是社会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完整的政 府”。如果讲的不是瞬息即逝的偶然事件,而是在历史上多少能留 下点痕迹的时间比较长的革命专政,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 的。这种情况之所以不可能有,是因为只有依靠绝大多数人民的革 命专政才可能是比较巩固(当然不是绝对巩固,而是相对巩固)的 专政。而俄国无产阶级目前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它只有和半无 产者、半有产者群众,即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联合起来,才 能成为绝大多数。可能的和所希望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的 这种构成,当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的构成上,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 色的代表必然要参加这个政府,或者甚至在这个政府中占优势。在 这个问题上抱任何幻想都是十分有害的。空谈家托洛茨基现在说 (可惜是和帕尔乌斯一道),“加邦神父只能出现一次”,“第二个加 邦没有立足之地”,这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空谈家。如果俄国没有第 二个加邦的立足之地,那么,在我们这里,真正“伟大的”、彻底的民 主主义革命的立足之地也就不会有了。革命要成为伟大的革命,要 象1789—1793年,而不是象1848—1850年,并且要超过它们,就 必须唤起广大群众投入积极的生活,英勇奋斗,进行“扎扎实实的 历史性创造”,从可怕的无知状态,从空前的闭塞状态,从难以想象 的野蛮状态和暗无天日的愚昧状态觉醒起来。革命已经开始唤起 群众,它一定会唤起群众,—— 政府本身正在以自己痉挛性的反抗 促进这项工作,但是,不言而喻,要说这些群众和他们的为数众 多的 “土生土长的” 民众首领、甚至农民首领已经有成熟的政治 16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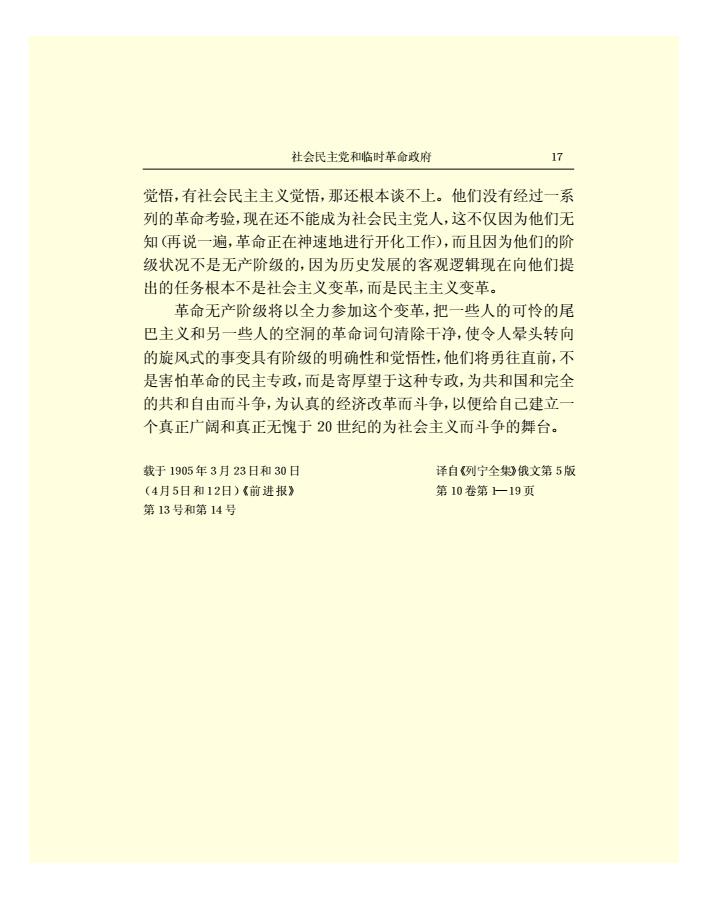
觉悟,有社会民主主义觉悟,那还根本谈不上。他们没有经过一系 列的革命考验,现在还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不仅因为他们无 知(再说一遍,革命正在神速地进行开化工作),而且因为他们的阶 级状况不是无产阶级的,因为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现在向他们提 出的任务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变革,而是民主主义变革。 革命无产阶级将以全力参加这个变革,把一些人的可怜的尾 巴主义和另一些人的空洞的革命词句清除干净,使令人晕头转向 的旋风式的事变具有阶级的明确性和觉悟性,他们将勇往直前,不 是害怕革命的民主专政,而是寄厚望于这种专政,为共和国和完全 的共和自由而斗争,为认真的经济改革而斗争,以便给自己建立一 个真正广阔和真正无愧于20世纪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舞台。 载于1905年3月23日和30日 (4月5日和12日)《前进报》 第13号和第1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第10卷第1—19页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 17
觉悟,有社会民主主义觉悟,那还根本谈不上。他们没有经过一系 列的革命考验,现在还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不仅因为他们无 知(再说一遍,革命正在神速地进行开化工作),而且因为他们的阶 级状况不是无产阶级的,因为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现在向他们提 出的任务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变革,而是民主主义变革。 革命无产阶级将以全力参加这个变革,把一些人的可怜的尾 巴主义和另一些人的空洞的革命词句清除干净,使令人晕头转向 的旋风式的事变具有阶级的明确性和觉悟性,他们将勇往直前,不 是害怕革命的民主专政,而是寄厚望于这种专政,为共和国和完全 的共和自由而斗争,为认真的经济改革而斗争,以便给自己建立一 个真正广阔和真正无愧于20世纪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舞台。 载于1905年3月23日和30日 (4月5日和12日)《前进报》 第13号和第1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第10卷第1—19页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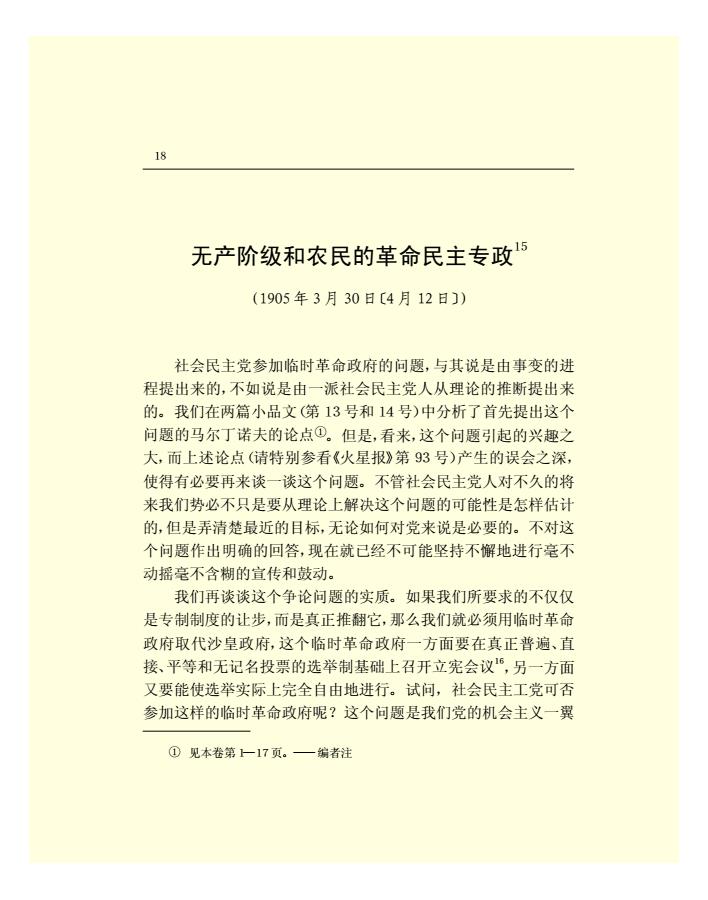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15 (1905年3月30日〔4月12日〕) 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与其说是由事变的进 程提出来的,不如说是由一派社会民主党人从理论的推断提出来 的。我们在两篇小品文(第13号和14号)中分析了首先提出这个 问题的马尔丁诺夫的论点①。但是,看来,这个问题引起的兴趣之 大,而上述论点(请特别参看《火星报》第93号)产生的误会之深, 使得有必要再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不管社会民主党人对不久的将 来我们势必不只是要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是怎样估计 的,但是弄清楚最近的目标,无论如何对党来说是必要的。不对这 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现在就已经不可能坚持不懈地进行毫不 动摇毫不含糊的宣传和鼓动。 我们再谈谈这个争论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所要求的不仅仅 是专制制度的让步,而是真正推翻它,那么我们就必须用临时革命 政府取代沙皇政府,这个临时革命政府一方面要在真正普遍、直 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16,另一方面 又要能使选举实际上完全自由地进行。试问,社会民主工党可否 参加这样的临时革命政府呢?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一翼 18 ① 见本卷第1—17页。—— 编者注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15 (1905年3月30日〔4月12日〕) 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与其说是由事变的进 程提出来的,不如说是由一派社会民主党人从理论的推断提出来 的。我们在两篇小品文(第13号和14号)中分析了首先提出这个 问题的马尔丁诺夫的论点①。但是,看来,这个问题引起的兴趣之 大,而上述论点(请特别参看《火星报》第93号)产生的误会之深, 使得有必要再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不管社会民主党人对不久的将 来我们势必不只是要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是怎样估计 的,但是弄清楚最近的目标,无论如何对党来说是必要的。不对这 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现在就已经不可能坚持不懈地进行毫不 动摇毫不含糊的宣传和鼓动。 我们再谈谈这个争论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所要求的不仅仅 是专制制度的让步,而是真正推翻它,那么我们就必须用临时革命 政府取代沙皇政府,这个临时革命政府一方面要在真正普遍、直 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16,另一方面 又要能使选举实际上完全自由地进行。试问,社会民主工党可否 参加这样的临时革命政府呢?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一翼 18 ① 见本卷第1—17页。—— 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