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该书除间收不见于旧钱谱的珍品之外,还采用了近人的考释,颇有参考价值。 玺印文字历代都有发现,明代已出现印谱,但是比较系统地搜辑和整理玺印文字则 是从清代开始的。与战国货币相反,战国玺印的时代曾一度被误认为秦汉。乾嘉著名学 者程瑶田首先释出“。尔”为“私玺”,并指出“玺但用尔者,古文省也”【11】。程氏 把战国玺印文字归属于“古文”,见解十分犀利。后来徐同柏索性把古玺称为“古文印” 【12】,吴式芬又进一步分出“古玺官印”和“古朱文印”【13】。同治年间,陈介祺荟萃 各家印谱编辑《十钟山房印举》,其中古玺的材料十分丰富。该书虽兼收汉以下材料,但 是首列“古玺”,又进而先列官玺,后列私玺,这一体例至今仍在沿用。陈氏“朱文铜玺 似以六国文字,玉印似六国书法近两周者”【14】的推测也颇有见地。光绪年间,吴大徵编 纂《说文古籀补》。该书虽以收录金文为主,但兼收古玺570余字,其释读间有可采。民 国期间,丁佛言的《说文古籀补补》又对吴氏之书有所补充。嗣后出现许多古玺印谱, 较重要者有黄濬《尊古斋古玺集林》、方清霖《周秦古玺菁华》等。1930年,罗福颐《古 玺文字徵》出版,收录可识玺文629字,这是我国第一部古玺字书。吴幼潜《封泥汇编》 收录十几方战国封泥,也是研究玺文的罕见对比材料。 清同治年间,陈介祺开始鉴定和搜辑山东潍县出土的陶文。嗣后山东、河南、陕西 等地又发现了齐、燕、韩、秦诸国陶文,其中以齐、燕旧地出土量最多。早期研究陶文 的学者以陈介祺和吴大微的贡献最大,但二人的著作多未刊行。吴大微对陶文研究的部 分成果散见于《吴愙斋尺牍》,而《说文古籀补》对陶文的考释不过反映他的部分研究成 果而己。民国期间,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强运开《说文古籀三补》均收录陶文。后 来顾廷龙《古陶文看录》不但收录陶文单字,而且附有辞例,体例更为完备,是当时最 权威的陶文工具书。这一时期几篇有关陶文研究的论文颇具水平,例如:唐兰考证陶文 “陈向”即典籍之“田常”【15】,张政烺考证陶文“陈得”与陈璋壶、子禾子釜铭文的 “陈得”实为一人【16】。凡此种种无疑提高了陶文的史料价值。著录陶文的著作主要有: 陈介祺《簠斋藏陶》、刘愕鹗《铁云藏陶》、周进《季木藏陶》(参李零《新编全本季木藏陶》 分类考释)等。 1942年,在湖南长沙古墓出土的楚帛书,是战国文字罕见的缣帛文字材料。楚帛书 发现不久即流失国外,国内只有不精确的摹本,研究著作有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 1883年,吴大瀓草创按《说文》顺序收录古文字的体例,编纂《说文古籀补》。这类 古文字字典虽以收录金文为主,但也收录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战国铜器、兵器、货币、玺 印、陶器等文字,这为战国文字字形的系统整理奠定了基础。这类字书对战国文字的释 读多有可取之处,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上吴大徵、丁佛言、强运开所著三书,就战国文字的考释水平而论,丁佛言《说 文古籀补补》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例如莓”(P2)、“登”(P6)、“屎”(P7)、“訬”(P11)、 “腏”(P19)、“陷”(P19)、“虡”(P22)、“来”(P25)、“夏”(P25)、“韩”(P25)、“柏” (P26)、“瘳”(P36)、“罟”(P37)、“聘”(P51)、“永”(P63)、“垔”(P63)、“瘳”(P65)、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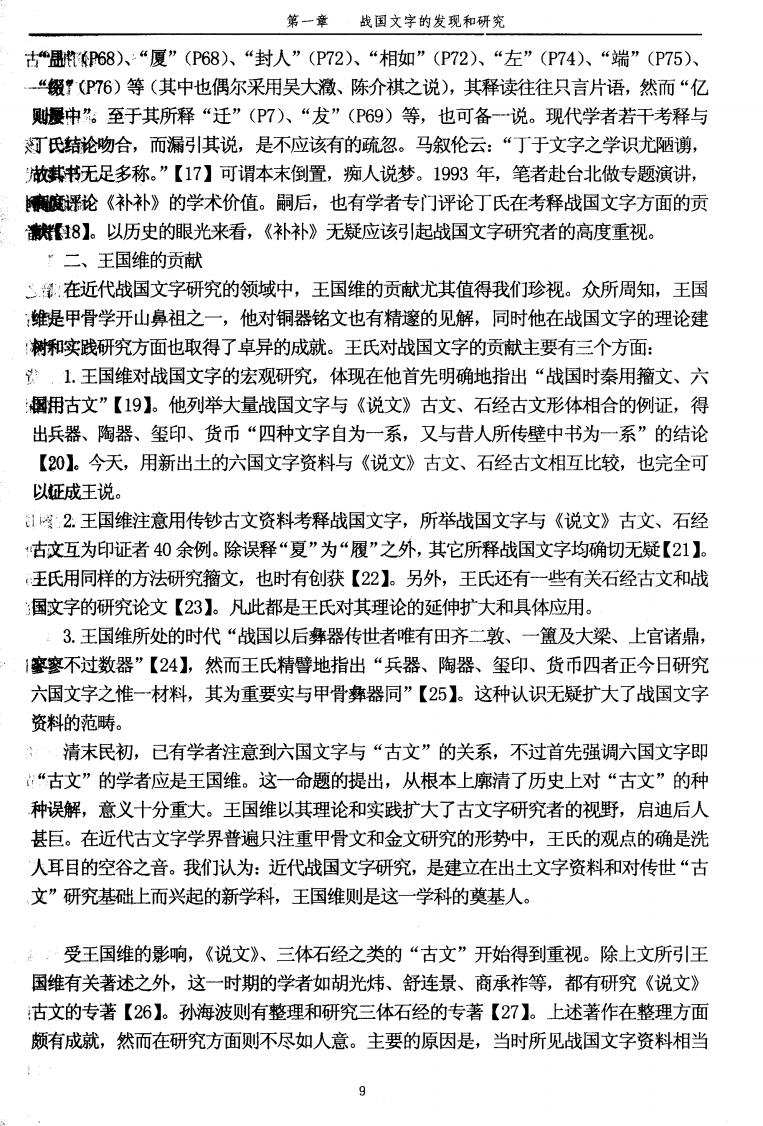
第一童 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古68)、“厦”(P68)、“封人”(P72)、“相如”(P72)、“左”(P74)、“端”(P75)、 “缀譬76)等(其中也偶尔采用吴大澄、陈介祺之说),其释读往往只言片语,然而“亿 则爆中”。至于其所释“迁”(P7)、“发”(P69)等,也可备一说。现代学者若干考释与 灯氏结论吻合,而漏引其说,是不应该有的疏忽。马叙伦云:“丁于文字之学识尤陋谫, 放其书无足多称。”【17】可谓本末倒置,痴人说梦。1993年,笔者赴台北做专题演讲, 南簸评论《补补》的学术价值。嗣后,也有学者专门评论丁氏在考释战国文字方面的贡 8】。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补补》无疑应该引起战国文字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二、王国维的贡献 ∴:在近代战国文字研究的领域中,王国维的贡献尤其值得我们珍视。众所周知,王国 维是甲骨学开山鼻祖之一,他对铜器铭文也有精邃的见解,同时他在战国文字的理论建 :树和实践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卓异的成就。王氏对战国文字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1.王国维对战国文字的宏观研究,体现在他首先明确地指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 国用古文”【19】。他列举大量战国文字与《说文》古文、石经古文形体相合的例证,得 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四种文字自为一系,又与昔人所传壁中书为一系”的结论 【0】。今天,用新出土的六国文字资料与《说文》古文、石经古文相互比较,也完全可 以证成王说。 12.王国维注意用传钞古文资料考释战国文字,所举战国文字与《说文》古文、石经 古文互为印证者40余例。除误释“夏”为“履”之外,其它所释战国文字均确切无疑【21】。 王氏用同样的方法研究籀文,也时有创获【22】。另外,王氏还有一些有关石经古文和战 国文字的研究论文【23】。凡此都是王氏对其理论的延伸扩大和具体应用。 3.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战国以后彝器传世者唯有田齐二敦、一簠及大梁、上官诸鼎, 1蜜寥不过数器”【24】,然而王氏精譬地指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四者正今日研究 六国文字之惟一材料,其为重要实与甲骨彝器同”【25】。这种认识无疑扩大了战国文字 资料的范畴。 清末民初,已有学者注意到六国文字与“古文”的关系,不过首先强调六国文字即 #“古文”的学者应是王国维。这一命题的提出,从根本上廓清了历史上对“古文”的种 种误解,意义十分重大。王国维以其理论和实践扩大了古文字研究者的视野,启迪后人 甚巨。在近代古文字学界普遍只注重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形势中,王氏的观点的确是洗 人耳目的空谷之音。我们认为:近代战国文字研究,是建立在出土文字资料和对传世“古 文”研究基础上而兴起的新学科,王国维则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人。 受王国维的影响,《说文》、三体石经之类的“古文”开始得到重视。除上文所引王 国维有关著述之外,这一时期的学者如胡光炜、舒连景、商承祚等,都有研究《说文》 :古文的专著【26】。孙海波则有整理和研究三体石经的专著【27】。上述著作在整理方面 颇有成就,然而在研究方面则不尽如人意。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所见战国文字资料相当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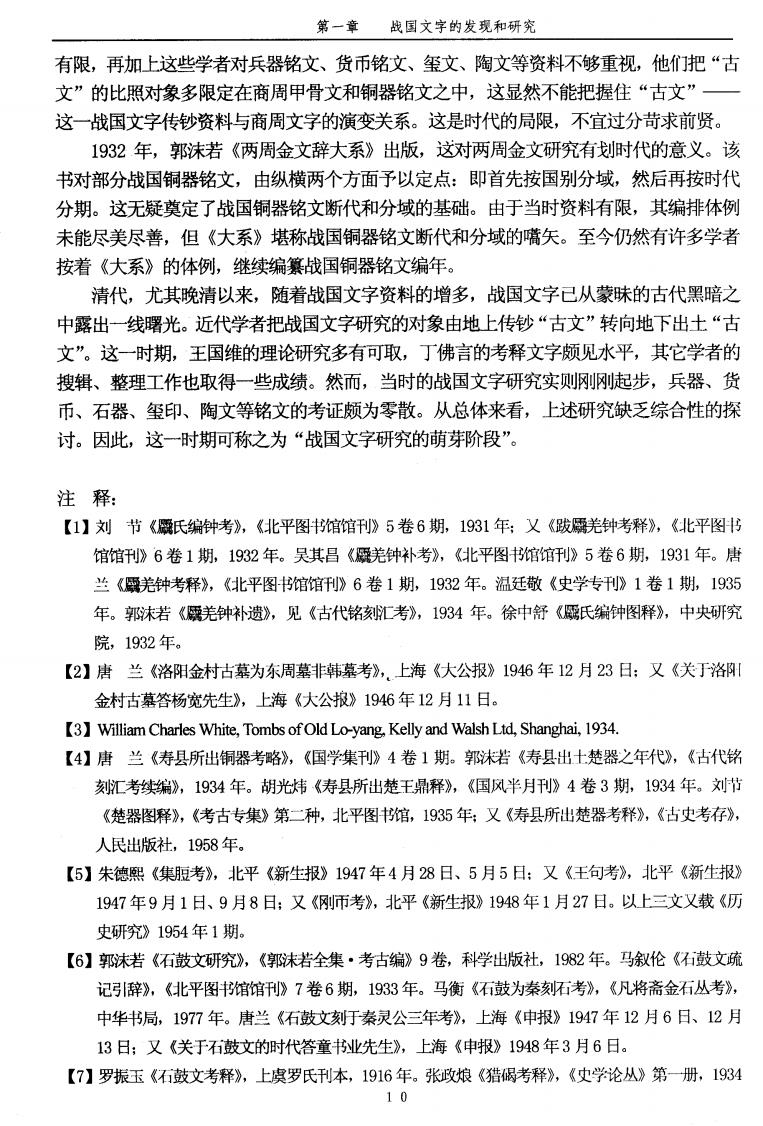
第一章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有限,再加上这些学者对兵器铭文、货币铭文、玺文、陶文等资料不够重视,他们把“古 文”的比照对象多限定在商周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之中,这显然不能把握住“古文”一 这一战国文字传钞资料与商周文字的演变关系。这是时代的局限,不宜过分苛求前贤。 1932年,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出版,这对两周金文研究有划时代的意义。该 书对部分战国铜器铭文,由纵横两个方面予以定点:即首先按国别分域,然后再按时代 分期。这无疑奠定了战国铜器铭文断代和分域的基础。由于当时资料有限,其编排体例 未能尽美尽善,但《大系》堪称战国铜器铭文断代和分域的嚆矢。至今仍然有许多学者 按着《大系》的体例,继续编纂战国铜器铭文编年。 清代,尤其晚清以来,随着战国文字资料的增多,战国文字已从蒙昧的古代黑暗之 中露出一线曙光。近代学者把战国文字研究的对象由地上传钞“古文”转向地下出土“古 文”。这一时期,王国维的理论研究多有可取,丁佛言的考释文字颇见水平,其它学者的 搜辑、整理工作也取得一些成绩。然而,当时的战国文字研究实则刚刚起步,兵器、货 币、石器、玺印、陶文等铭文的考证颇为零散。从总体来看,上述研究缺乏综合性的探 讨。因此,这一时期可称之为“战国文字研究的萌芽阶段”。 注释: 【1】刘节《瞬氏编钟考》,《北平图书馆馆刊》5卷6期,1931年:又《跋厮羌钟考释》,《北平图书 馆馆刊》6卷1期,1932年。吴其昌《魘羌钟补考》,《北平图馆馆刊》5卷6期,1931年。唐 兰《嚼羌钟考释》,《北平图书馆馆刊》6卷1期,1932年。温廷敬《史学专刊》1卷1期,1935 年。郭沫若《露羌钟补遗》,见《古代铭刻汇考》,1934年。徐中舒《厮氏编钟图释》,中央研究 院,1932年。 【2】唐兰《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墓考》,上海《大公报》1946年12月23日:又《关于洛 金村古墓答杨宽先生》,上海《大公报》1946年12月11日。 [3)William Charles White,Tombs of Old Lo-yang,Kelly and Walsh Ltd,Shanghai,1934 【4】唐兰《寿县所出铜器考略》,《国学集刊》4卷1期。郭沫若《寿县出土楚器之年代》,《古代铭 刻汇考续编》,1934年。胡光炜《寿县所出楚王鼎释》,《国风半月刊》4卷3期,1934年。刘节 《楚器图释》,《考古专集》第二种,北平图馆,1935年:又《寿县所出楚器考释》,《古史考存》, 人民出版社,1958年。 【5】朱德熙《集脰考》,北平《新生报》1947年4月28日、5月5日:又《王句考》,北平《新生报》 1947年9月1日、9月8日:又《刚币考》,北平《新生报》1948年1月27日。以上三文又载《历 史研究》1954年1期。 【6】郭沫若《石鼓文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编》9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马叙伦《石鼓文疏 记引辞》,《北平图馆馆刊》7卷6期,1933年。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凡将斋金石丛考》, 中华书局,1977年。唐兰《石鼓文刻于素灵公三年考》,上海《申报》1947年12月6日、12月 13日;又《关于石鼓文的时代答童书业先生》,上海《申报》1948年3月6日。 【7】罗振玉《石鼓文考释》,上虞罗氏刊本,1916年。张政娘《猎碣考释》,《史学论丛》第一册,1934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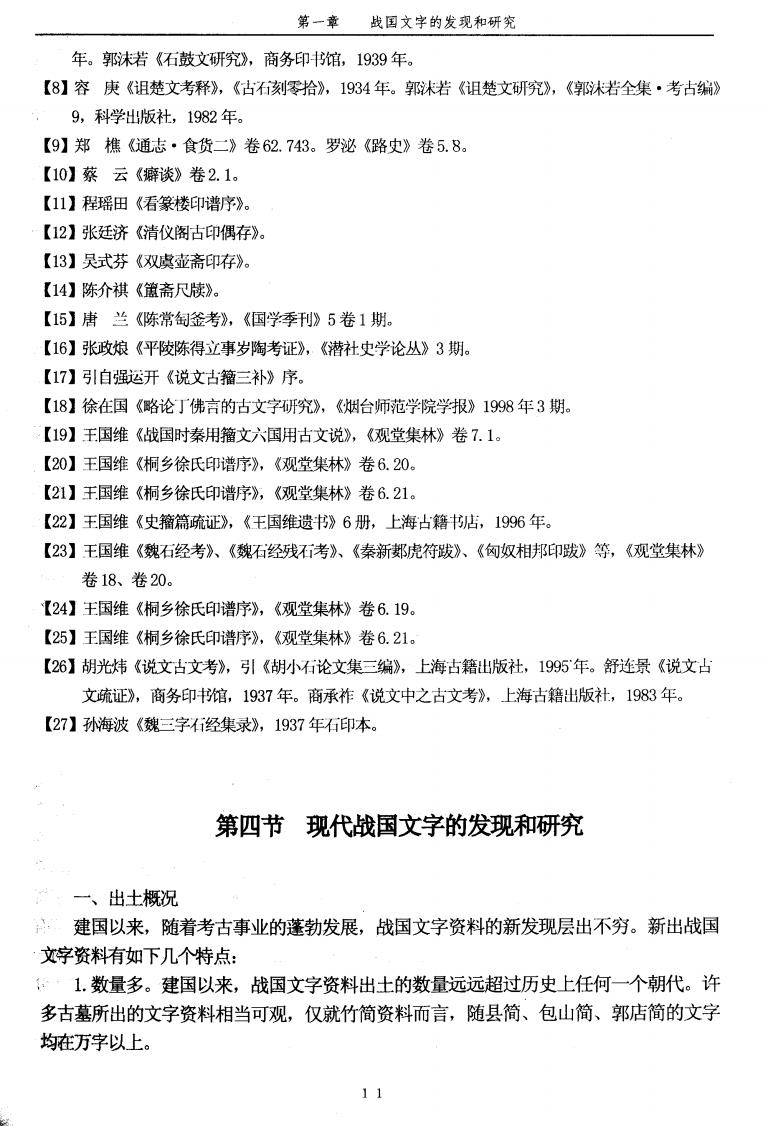
第一章 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年。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商务印书馆,1939年。 【8】容庚《诅楚文考释》,《古石刻零拾》,1934年。郭若《诅楚文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编》 9,科学出版社,1982年。 【9】郑樵《通志·食货二》卷62.743。罗泌《路史》卷5.8。 【10】蔡云《癖谈》卷2.1。 【11】程瑶田《看篆楼印谱序》。 【12】张廷济《清仪阁古印偶存》。 【13】吴式芬《双虞壶斋印存》。 【14】陈介祺《簠斋尺牍》。 【15】唐兰《陈常匋釜考》,《国学季刊》5卷1期。 【16】张政烺《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潜社史学论丛》3期。 【17】引自强运开《说文古籀三补》序。 【18】徐在国《略论丁佛言的古文字研究》,《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3期。 【19】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观堂集林》卷7.1。 【20】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观堂集林》卷6.20。 【21】于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观堂集林》卷6.21。 【22】王国维《史籀篇疏证》,《王国维遗书》6册,上海占籍书店,1996年。 【23】王国维《魏石经考》、《魏石经残石考》、《秦新鄴虎符跋》、《匈奴相邦印跋》等,《观堂集林》 卷18、卷20。 【24】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观堂集林》卷6.19。 【25】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观堂集林》卷6.21。 【26】胡光炜《说文古文考》,引《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舒连景《说文占 文疏证》,商务印书馆,1937年。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7】孙海波《魏三字石经集录》,1937年石印本。 第四节 现代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一、出士概况 建国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战国文字资料的新发现层出不穷。新出战国 文字资料有如下几个特点: 0 1.数量多。建国以来,战国文字资料出土的数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许 多古墓所出的文字资料相当可观,仅就竹简资料而言,随县简、包山简、郭店简的文字 均在万字以上。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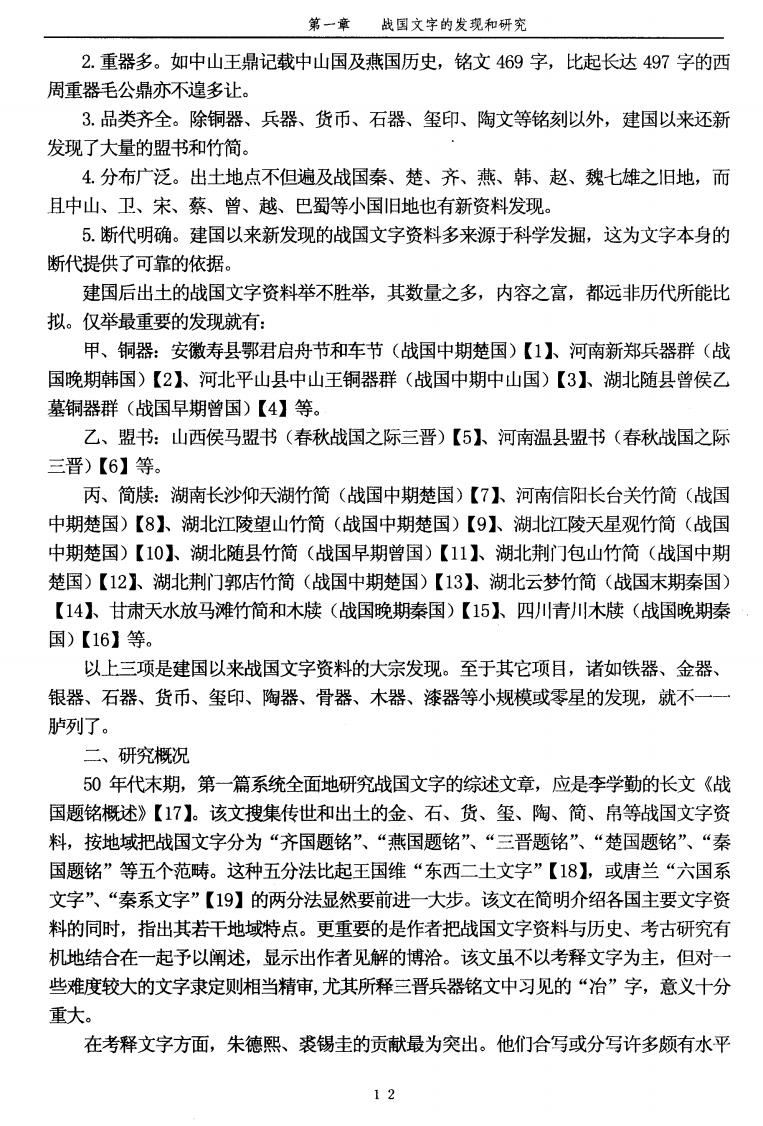
第一章 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2.重器多。如中山王鼎记载中山国及燕国历史,铭文469字,比起长达497字的西 周重器毛公鼎亦不遑多让。 3.品类齐全。除铜器、兵器、货币、石器、玺印、陶文等铭刻以外,建国以来还新 发现了大量的盟书和竹简。 4.分布广泛。出土地点不但遍及战国秦、楚、齐、燕、韩、赵、魏七雄之旧地,而 且中山、卫、宋、蔡、曾、越、巴蜀等小国旧地也有新资料发现。 5.断代明确。建国以来新发现的战国文字资料多来源于科学发掘,这为文字本身的 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建国后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举不胜举,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富,都远非历代所能比 拟。仅举最重要的发现就有: 甲、铜器:安徽寿县鄂君启舟节和车节(战国中期楚国)【1】、河南新郑兵器群(战 国晚期韩国)【2】、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铜器群(战国中期中山国)【3】、湖北随县曾侯乙 墓铜器群(战国早期曾国)【4】等。 乙、盟书:山西侯马盟书(春秋战国之际三晋)【5、河南温县盟书(春秋战国之际 三晋)【6】等。 丙、简牍:湖南长沙仰天湖竹简(战国中期楚国)【7、河南信阳长台关竹简(战国 中期楚国)【8】、湖北江陵望山竹简(战国中期楚国)【9、湖北江陵天星观竹简(战国 中期楚国)【10】、湖北随县竹简(战国早期曾国)【11】、湖北荆门包山竹简(战国中期 楚国)【12】、湖北荆门郭店竹简(战国中期楚国)【13】、湖北云梦竹简(战国末期秦国) 【14】、甘肃天水放马滩竹简和木牍(战国晚期秦国)【15八、四川青川木牍(战国晚期秦 国)【16】等。 以上三项是建国以来战国文字资料的大宗发现。至于其它项目,诸如铁器、金器、 银器、石器、货币、玺印、陶器、骨器、木器、漆器等小规模或零星的发现,就不一一 胪列了。 二、研究概况 50年代末期,第一篇系统全面地研究战国文字的综述文章,应是李学勤的长文《战 国题铭概述》【17】。该文搜集传世和出土的金、石、货、玺、陶、简、帛等战国文字资 料,按地域把战国文字分为“齐国题铭”、“燕国题铭”、“三晋题铭”、“楚国题铭”、“秦 国题铭”等五个范畴。这种五分法比起王国维“东西二土文字”【18】,或唐兰“六国系 文字”、“秦系文字”【19】的两分法显然要前进一大步。该文在简明介绍各国主要文字资 料的同时,指出其若干地域特点。更重要的是作者把战国文字资料与历史、考古研究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予以阐述,显示出作者见解的博洽。该文虽不以考释文字为主,但对一 些难度较大的文字隶定则相当精审,尤其所释三晋兵器铭文中习见的“冶”字,意义十分 重大。 在考释文字方面,朱德熙、裘锡圭的贡献最为突出。他们合写或分写许多颇有水平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