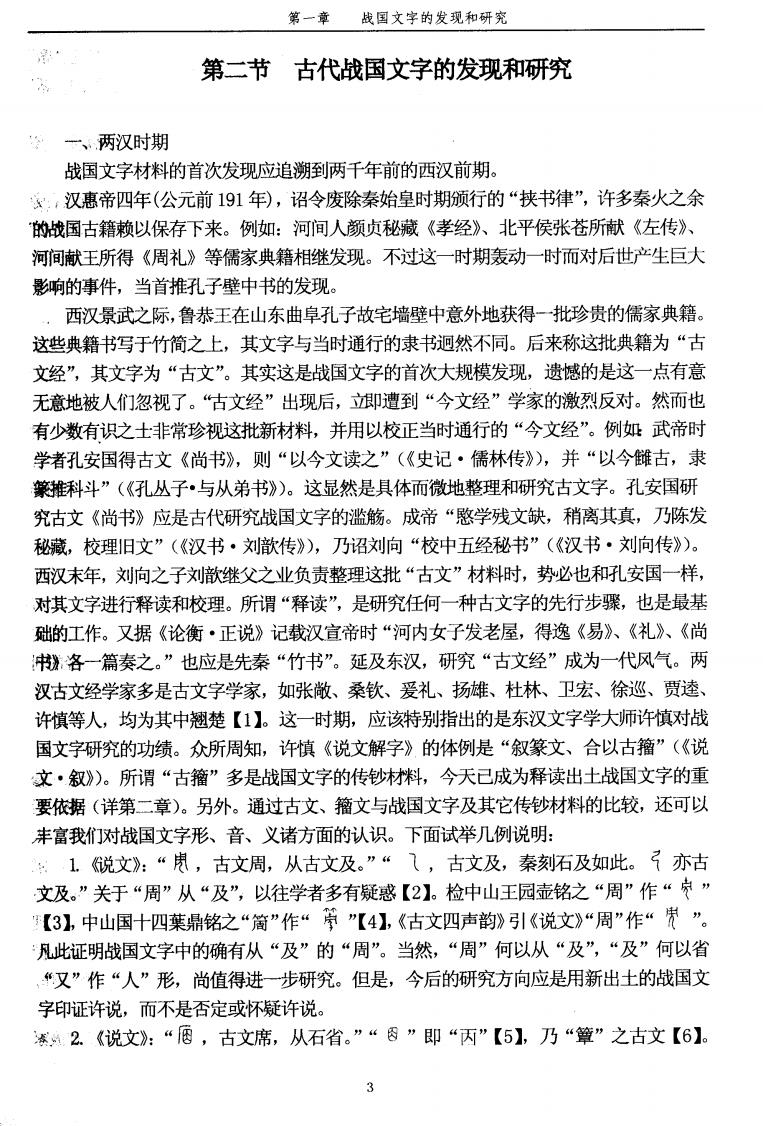
第一章 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第二节 古代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一、两汉时期 战国文字材料的首次发现应追溯到两千年前的西汉前期。 x: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诏令废除秦始皇时期颁行的“挟书律”,许多秦火之余 的战国古籍赖以保存下来。例如:河间人颜贞秘藏《孝经》、北平侯张苍所献《左传》、 河间献王所得《周礼》等儒家典籍相继发现。不过这一时期轰动一时而对后世产生巨大 影响的事件,当首推孔子壁中书的发现。 西汉景武之际,鲁恭王在山东曲阜孔子故宅墙壁中意外地获得一批珍贵的儒家典籍。 这些典籍书写于竹简之上,其文字与当时通行的隶书迥然不同。后来称这批典籍为“古 文经”,其文字为“古文”。其实这是战国文字的首次大规模发现,遗憾的是这一点有意 无意地被人们忽视了。“古文经”出现后,即遭到“今文经”学家的激烈反对。然而也 有少数有识之士非常珍视这批新材料,并用以校正当时通行的“今文经”。例如武帝时 学者孔安国得古文《尚书》,则“以今文读之”(《史记·儒林传》),并“以今雠古,隶 篆推科斗”(《孔丛子·与从弟书》)。这显然是具体而微地整理和研究古文字。孔安国研 究古文《尚书》应是古代研究战国文字的滥觞。成帝“愍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 秘藏,校理旧文”(《汉书·刘歆传》),乃诏刘向“校中五经秘书”(《汉书·刘向传》)。 西汉末年,刘向之子刘歆继父之业负责整理这批“古文”材料时,势必也和孔安国一样, 对其文字进行释读和校理。所谓“释读”,是研究任何一种古文字的先行步骤,也是最基 础的工作。又据《论衡·正说》记载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 书》洛一篇奏之。”也应是先秦“竹书”。延及东汉,研究“古文经”成为一代风气。两 汉古文经学家多是古文字学家,如张敞、桑钦、爰礼、扬雄、杜林、卫宏、徐巡、贾逵、 许慎等人,均为其中翘楚【1】。这一时期,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东汉文字学大师许慎对战 国文字研究的功绩。众所周知,许慎《说文解字》的体例是“叙篆文、合以古籀”(《说 文·叙》)。所谓“古籀”多是战国文字的传钞材料,今天已成为释读出土战国文字的重 要依据(详第二章)。另外。通过古文、籀文与战国文字及其它传钞材料的比较,还可以 丰富我们对战国文字形、音、义诸方面的认识。下面试举几例说明: 1说文》:“闲,古文周,从古文及。”“飞,古文及,秦刻石及如此。亦古 文及。”关于“周”从“及”,以往学者多有疑惑【2】。检中山王园壶铭之“周”作“京” 【3】,中山国十四莱鼎铭之“商”作“宁”【4】,《古文四声韵》引《说文》“周”作“界”。 凡此证明战国文字中的确有从“及”的“周”。当然,“周”何以从“及”,“及”何以省 “又”作“人”形,尚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今后的研究方向应是用新出土的战国文 字印证许说,而不是否定或怀疑许说。 添2.《说文》:“图,古文席,从石省。”“图”即“丙”【5】,乃“簟”之古文【6】。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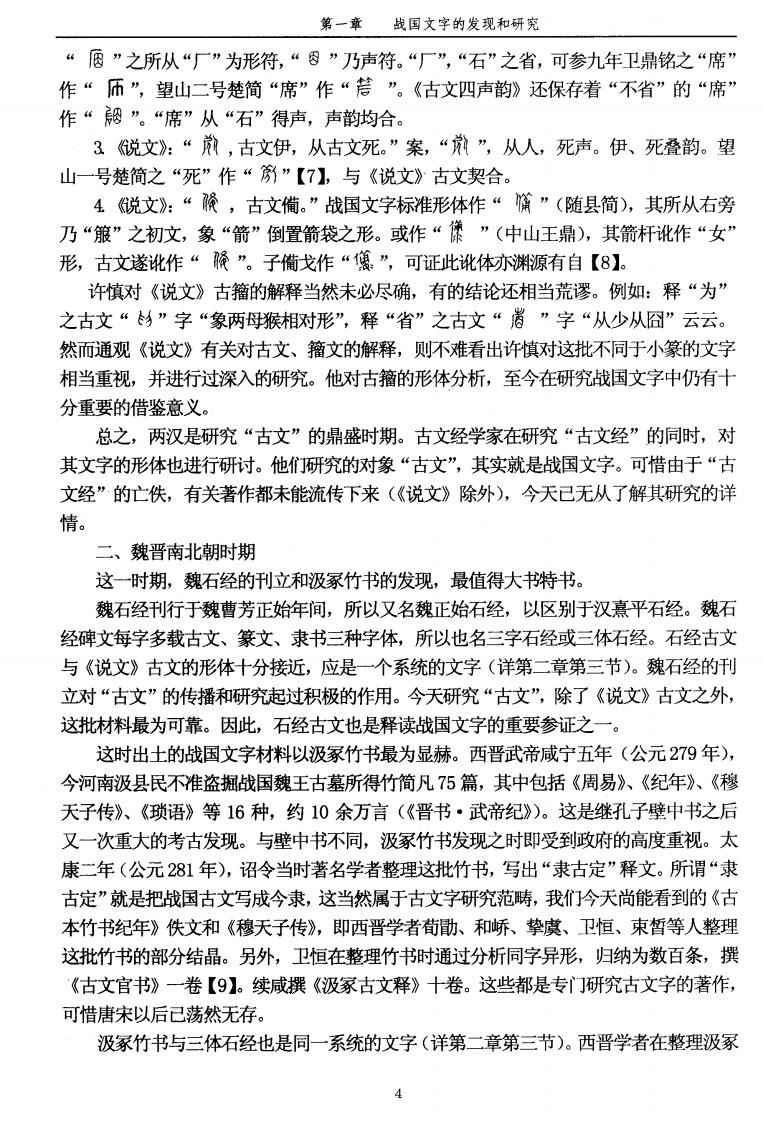
第一章 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之所从“厂”为形符,“图”乃声符。“厂”,“石”之省,可参九年卫鼎铭之“席” 作“历”,望山二号楚简“席”作“篇”。《古文四声韵》还保存着“不省”的“席” 作“恐”。“席”从“石”得声,声韵均合。 3说文》:“前,古文伊,从古文死。”案,“”,从人,死声。伊、死叠韵。望 山一号楚简之“死”作“”【7】,与《说文》古文契合。 4说文》:“晚,古文简。”战国文字标准形体作“嘴”(随县简),其所从右旁 乃“箙”之初文,象“箭”倒置箭袋之形。或作“镖”(中山王鼎),其箭杆讹作“女” 形,古文遂讹作“晚”。子備戈作“篱。”,可证此讹体亦渊源有自【8】。 许慎对《说文》古籀的解释当然未必尽确,有的结论还相当荒谬。例如:释“为” 之古文“”字“象两母猴相对形”,释“省”之古文“茵”字“从少从囧”云云。 然而通观《说文》有关对古文、籀文的解释,则不难看出许慎对这批不同于小篆的文字 相当重视,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对古籀的形体分析,至今在研究战国文字中仍有十 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之,两汉是研究“古文”的鼎盛时期。古文经学家在研究“古文经”的同时,对 其文字的形体也进行研讨。他们研究的对象“古文”,其实就是战国文字。可借由于“古 文经”的亡佚,有关著作都未能流传下来(《说文》除外),今天已无从了解其研究的详 情。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魏石经的刊立和汲冢竹书的发现,最值得大书特书。 魏石经刊行于魏曹芳正始年间,所以又名魏正始石经,以区别于汉熹平石经。魏石 经碑文每字多载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所以也名三字石经或三体石经。石经古文 与《说文》古文的形体十分接近,应是一个系统的文字(详第二章第三节)。魏石经的刊 立对“古文”的传播和研究起过积极的作用。今天研究“古文”,除了《说文》古文之外, 这批材料最为可靠。因此,石经古文也是释读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证之一。 这时出土的战国文字材料以汲冢竹书最为显赫。西晋武帝减宁五年(公元279年), 今河南汲县民不准盗掘战国魏王古墓所得竹简凡75篇,其中包括《周易》、《纪年》、《穆 天子传》、《琐语》等16种,约10余万言(《晋书·武帝纪》)。这是继孔子壁中书之后 又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与壁中书不同,汲冢竹书发现之时即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太 康二年(公元281年),诏令当时著名学者整理这批竹书,写出“隶古定”释文。所谓“隶 古定”就是把战国古文写成今隶,这当然属于古文字研究范畴,我们今天尚能看到的《古 本竹书纪年》佚文和《穆天子传》,即西晋学者荀勖、和峤、挚虞、卫恒、束皙等人整理 这批竹书的部分结晶。另外,卫恒在整理竹书时通过分析同字异形,归纳为数百条,撰 《古文官书》一卷【9】。续咸撰《汲冢古文释》十卷。这些都是专门研究古文字的著作, 可惜唐宋以后已荡然无存。 汲冢竹书与三体石经也是同一系统的文字(洋第二章第三节)。西晋学者在整理汲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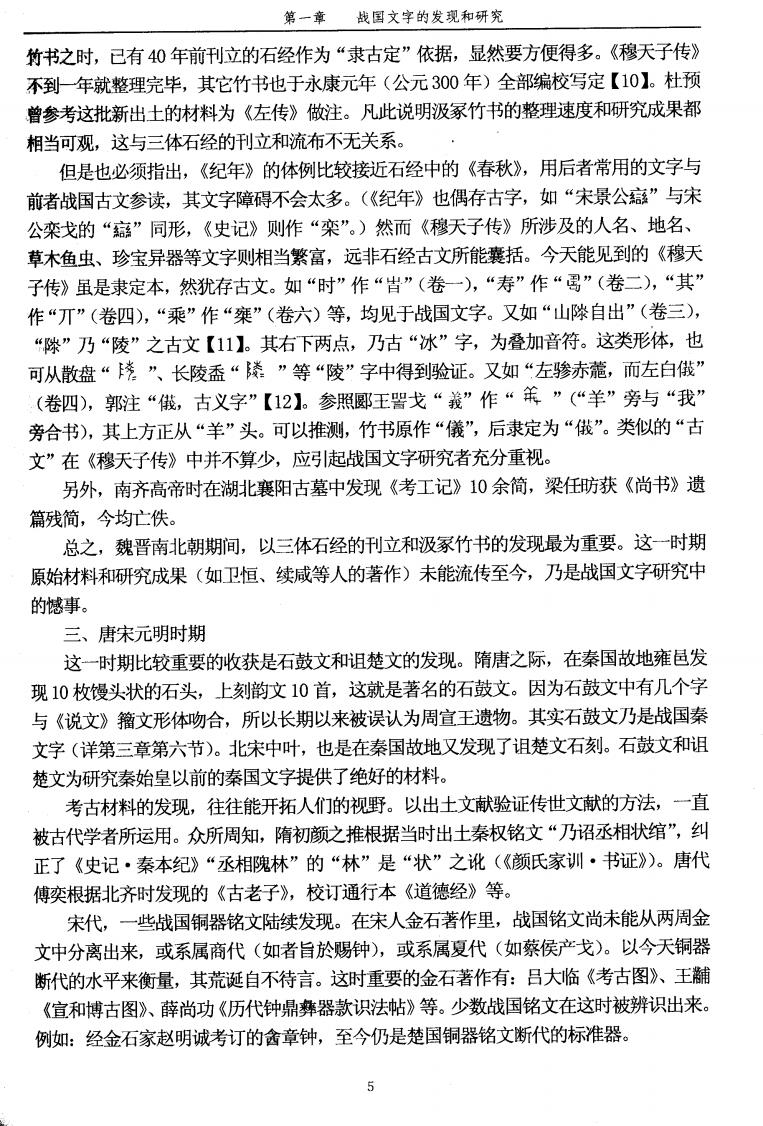
第一章 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竹书之时,已有40年前刊立的石经作为“隶古定”依据,显然要方便得多。《穆天子传》 不到一年就整理完毕,其它竹书也于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全部编校写定【10】。杜预 曾参考这批新出土的材料为《左传》做注。凡此说明汲冢竹书的整理速度和研究成果都 相当可观,这与三体石经的刊立和流布不无关系。 但是也必须指出,《纪年》的体例比较接近石经中的《春秋》,用后者常用的文字与 前者战国古文参读,其文字障碍不会太多。(《纪年》也偶存古字,如“宋景公”与宋 公栾戈的“癌”同形,《史记》则作“栾”。)然而《穆天子传》所涉及的人名、地名、 草木鱼虫、珍宝异器等文字则相当繁富,远非石经古文所能囊括。今天能见到的《穆天 子传》虽是隶定本,然犹存古文。如“时”作“皆”(卷一),“寿”作“写”(卷二),“其” 作“丌”(卷四),“乘”作“椉”(卷六)等,均见于战国文字。又如“山暰自出”(卷三), “滕”乃“陵”之古文【11】。其右下两点,乃古“冰”字,为叠加音符。这类形体,也 可从散盘“浇”、长陵盉“谈”等“陵”字中得到验证。又如“左骖赤巃,而左白俄” (卷四),郭注“俄,古义字”【12】。参照郾王罂戈“義”作“羊”(“羊”旁与“我” 旁合书),其上方正从“羊”头。可以推测,竹书原作“儀”,后隶定为“俄”。类似的“古 文”在《穆天子传》中并不算少,应引起战国文字研究者充分重视。 另外,南齐高帝时在湖北襄阳古墓中发现《考工记》10余简,梁任防获《尚书》遗 篇残简,今均亡佚。 总之,魏晋南北朝期间,以三体石经的刊立和汲冢竹书的发现最为重要。这一时期 原始材料和研究成果(如卫恒、续减等人的著作)未能流传至今,乃是战国文字研究中 的憾事。 三、唐宋元明时期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收获是石鼓文和诅楚文的发现。隋唐之际,在秦国故地雍邑发 现10枚馒头状的石头,上刻韵文10首,这就是著名的石鼓文。因为石鼓文中有几个字 与《说文》籀文形体吻合,所以长期以来被误认为周宣王遗物。其实石鼓文乃是战国秦 文字(详第三章第六节)。北宋中叶,也是在秦国故地又发现了诅楚文石刻。石鼓文和诅 楚文为研究秦始皇以前的秦国文字提供了绝好的材料。 考古材料的发现,往往能开拓人们的视野。以出土文献验证传世文献的方法,一直 被古代学者所运用。众所周知,隋初颜之推根据当时出土秦权铭文“乃诏丞相状绾”,纠 正了《史记·秦本纪》“丞相隗林”的“林”是“状”之讹(《颜氏家训·书证》)。唐代 傅奕根据北齐时发现的《古老子》,校订通行本《道德经》等。 宋代,一些战国铜器铭文陆续发现。在宋人金石著作里,战国铭文尚未能从两周金 文中分离出来,或系属商代(如者旨於赐钟),或系属夏代(如蔡侯产戈)。以今天铜器 断代的水平来衡量,其荒诞自不待言。这时重要的金石著作有:吕大临《考古图》、王黼 《宣和博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少数战国铭文在这时被辨识出来。 例如:经金石家赵明诚考订的金章钟,至今仍是楚国铜器铭文断代的标准器。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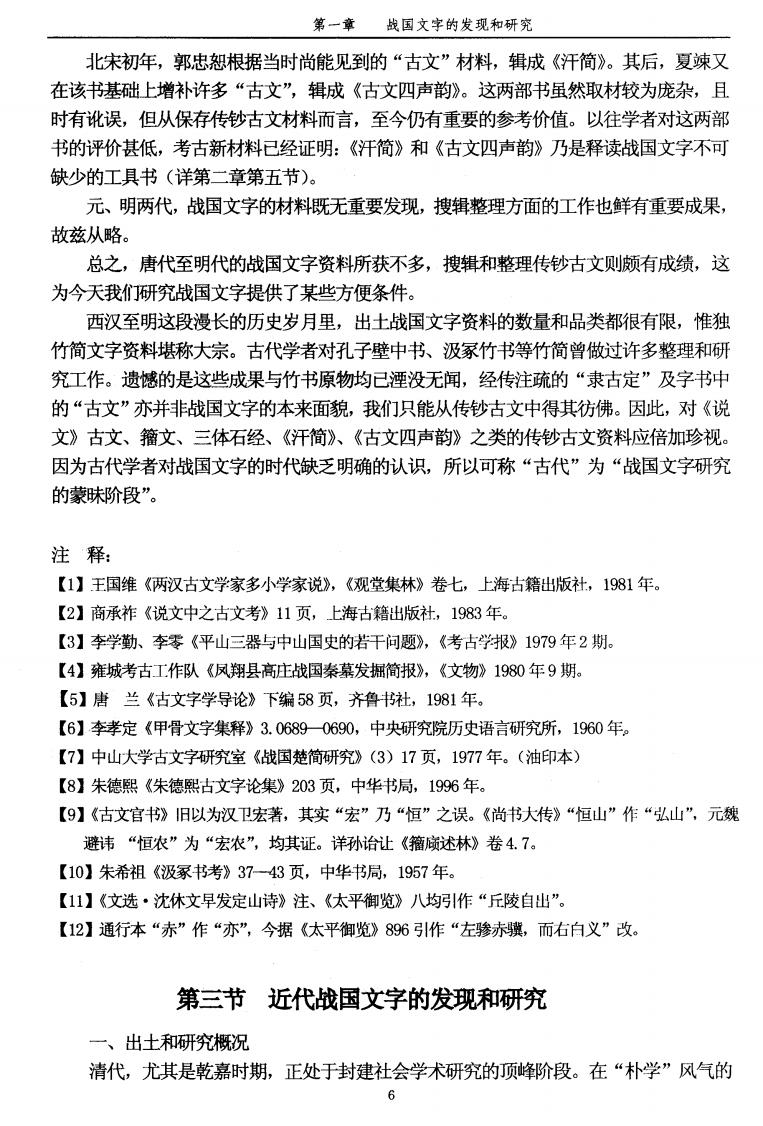
第一章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北宋初年,郭忠恕根据当时尚能见到的“古文”材料,辑成《汗简》。其后,夏竦又 在该书基础上增补许多“古文”,辑城《古文四声韵》。这两部书虽然取材较为庞杂,且 时有讹误,但从保存传钞古文材料而言,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往学者对这两部 书的评价甚低,考古新材料已经证明:《汗简》和《古文四声韵》乃是释读战国文字不可 缺少的工具书(详第二章第五节)。 元、明两代,战国文字的材料既无重要发现,搜辑整理方面的工作也鲜有重要成果, 故兹从略。 总之,唐代至明代的战国文字资料所获不多,搜辑和整理传钞古文则颇有成绩,这 为今天我们研究战国文字提供了某些方便条件。 西汉至明这段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出土战国文字资料的数量和品类都很有限,惟独 竹简文字资料堪称大宗。古代学者对孔子壁中书、汲冢竹书等竹简曾做过许多整理和研 究工作。遗憾的是这些成果与竹书原物均已湮没无闻,经传注疏的“隶古定”及字书中 的“古文”亦并非战国文字的本来面貌,我们只能从传钞古文中得其仿佛。因此,对《说 文》古文、籀文、三体石经、《汗简》、《古文四声韵》之类的传钞古文资料应倍加珍视。 因为古代学者对战国文字的时代缺乏明确的认识,所以可称“古代”为“战国文字研究 的蒙味阶段”。 注释: 【1】王国维《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观堂集林》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3】李学勤、李零《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2期。 【4】雍城考古工作队《凤翔县高庄战国秦幕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9期。 【5】唐兰《古文字学导论》下编58页,齐鲁书社,1981年。 【6】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3.0689069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0年。 【7】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战国楚简研究》(3)17页,1977年。(油印本) 【8】朱德熙《朱德熙古文字论集》203页,中华书局,1996年。 【9】《古文宫官书》旧以为汉卫宏著,其实“宏”乃“恒”之误。《尚书大传》“恒山”作“以山”,元魏 避讳“恒农”为“宏农”,均其证。详孙诒让《籀庼述林》卷4.7。 【10】朱希祖《汲冢书考》37-43页,中华书局,1957年。 【11】《文选·沈休文早发定山诗》注、《太平御览》八均引作“丘陵自出”。 【12】通行本“赤”作“亦”,今据《太平御览》896引作“左骖赤骥,而右白义”改。 第三节近代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一、出土和研究概况 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正处于封建社会学术研究的顶峰阶段。在“朴学”风气的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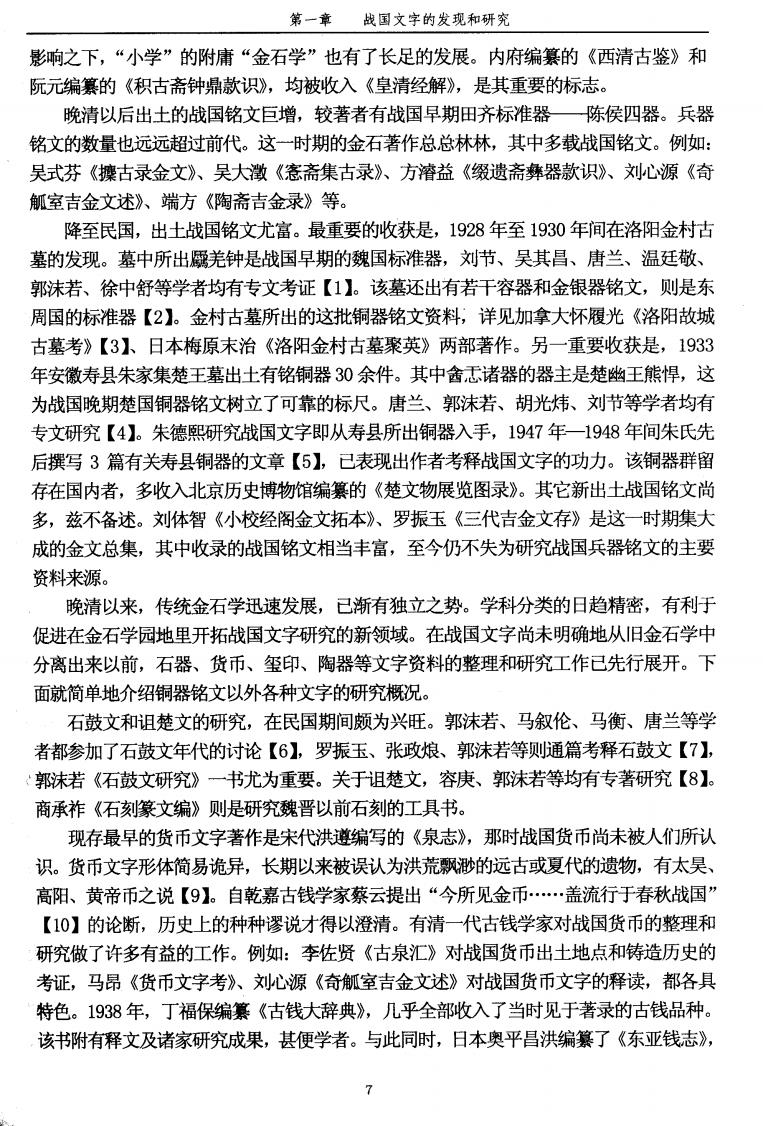
第一章 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影响之下,“小学”的附庸“金石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内府编纂的《西清古鉴》和 阮元编纂的《积古斋钟鼎款识》,均被收入《皇清经解》,是其重要的标志。 晚清以后出土的战国铭文巨增,较著者有战国早期田齐标准器一陈侯四器。兵器 铭文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前代。这一时期的金石著作总总林林,其中多载战国铭文。例如: 吴式芬《攈古录金文》、吴大澂《愙斋集古录》、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刘心源《奇 觚室吉金文述》、端方《陶斋吉金录》等。 降至民国,出土战国铭文尤富。最重要的收获是,1928年至1930年间在洛阳金村古 墓的发现。墓中所出嚼羌钟是战国早期的魏国标准器,刘节、吴其昌、唐兰、温廷敬、 郭沫若、徐中舒等学者均有专文考证【1】。该墓还出有若干容器和金银器铭文,则是东 周国的标准器【2】。金村古墓所出的这批铜器铭文资料,详见加拿大怀履光《洛阳故城 古墓考》【3】、日本梅原末治《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两部著作。另一重要收获是,1933 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出土有铭铜器30余件。其中舍忑诸器的器主是楚幽王熊悍,这 为战国晚期楚国铜器铭文树立了可靠的标尺。唐兰、郭沫若、胡光炜、刘节等学者均有 专文研究【4】。朱德熙研究战国文字即从寿县所出铜器入手,1947年一1948年间朱氏先 后撰写3篇有关寿县铜器的文章【5】,已表现出作者考释战国文字的功力。该铜器群留 存在国内者,多收入北京历史博物馆编纂的《楚文物展览图录》。其它新出土战国铭文尚 多,兹不备述。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是这一时期集大 成的金文总集,其中收录的战国铭文相当丰富,至今仍不失为研究战国兵器铭文的主要 资料来源。 晚清以来,传统金石学迅速发展,已渐有独立之势。学科分类的日趋精密,有利于 促进在金石学园地里开拓战国文字研究的新领域。在战国文字尚未明确地从旧金石学中 分离出来以前,石器、货币、玺印、陶器等文字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已先行展开。下 面就简单地介绍铜器铭文以外各种文字的研究概况。 石鼓文和诅楚文的研究,在民国期间颇为兴旺。郭沫若、马叙伦、马衡、唐兰等学 者都参加了石鼓文年代的讨论【6】,罗振玉、张政烺、郭沫若等则通篇考释石鼓文【7】,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一书尤为重要。关于诅楚文,容庚、郭沫若等均有专著研究【8】。 商承祚《石刻篆文编》则是研究魏晋以前石刻的工具书。 现存最早的货币文字著作是宋代洪遵编写的《泉志》,那时战国货币尚未被人们所认 识。货币文字形体简易诡异,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洪荒飘渺的远古或夏代的遗物,有太昊、 高阳、黄帝币之说【9】。自乾嘉古钱学家蔡云提出“今所见金币…盖流行于春秋战国” 【10】的论断,历史上的种种谬说才得以澄清。有清一代古钱学家对战国货币的整理和 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例如:李佐贤《古泉汇》对战国货币出土地点和铸造历史的 考证,马昂《货币文字考》、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对战国货币文字的释读,都各具 特色。1938年,丁福保编纂《古钱大辞典》,几乎全部收入了当时见于著录的古钱品种。 该书附有释文及诸家研究成果,甚便学者。与此同时,日本奥平昌洪编纂了《东亚钱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