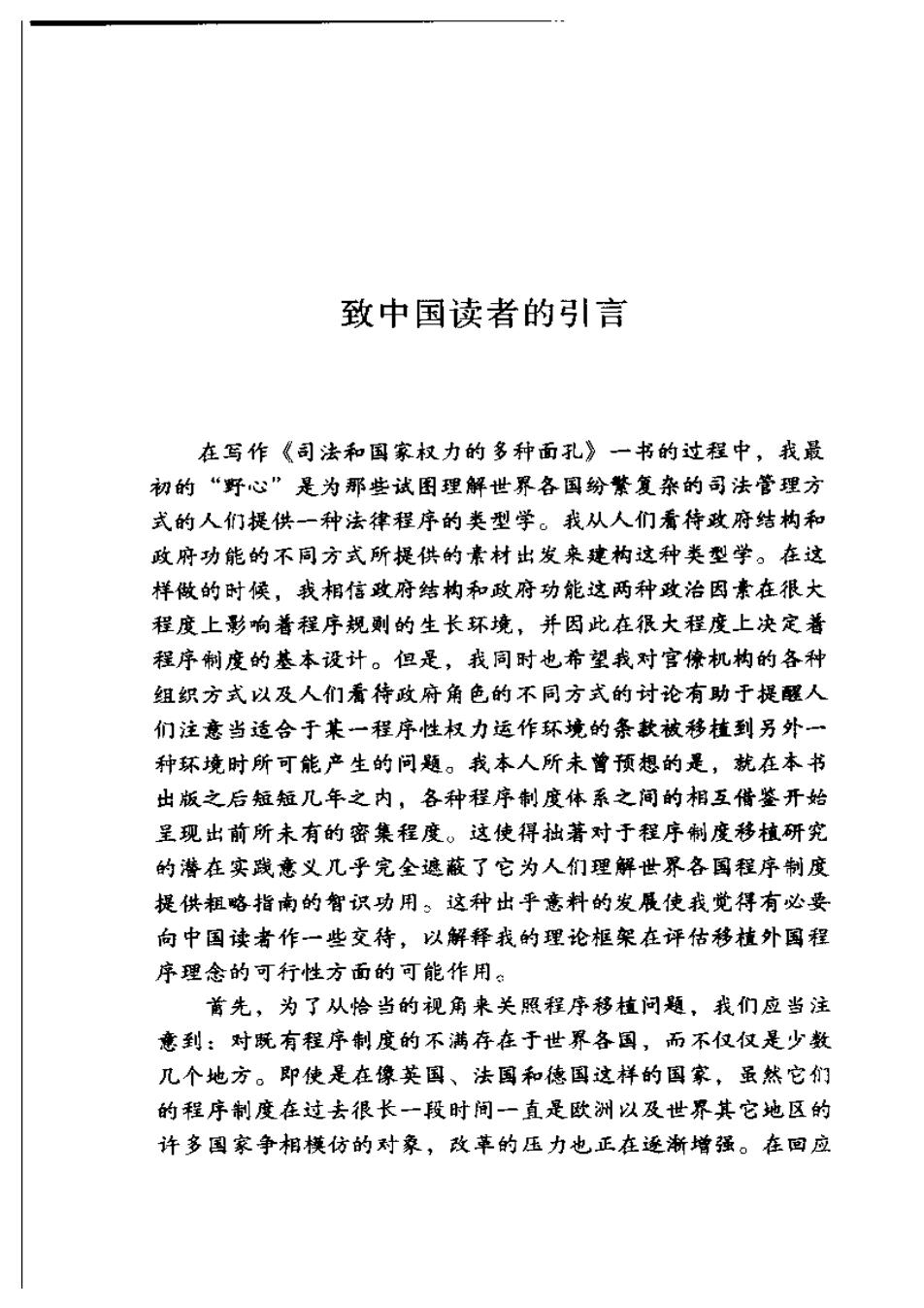
致中国读者的引言 在写作《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一书的过程中,我最 初的“野心”是为那些试图理解世界各国纷繁复杂的司法常理方 式的人们提供一种法律程序的类型学。我从人们看待政府结构和 政府功能的不同方式所提供的素材出发来建构这种类型学。在这 样做的时候,我相信政府结构和政府功能这两种政治图素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程序规测的生长环境,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程序制度的基本设计。但是,我同时也希望我对宫僚机构的各种 组织方式以及人们看待政府角色的不同方式的讨论有助于提醒人 们注意当适合于莱一程序性权力运作环境的条款被移植到另外一 种环境时所可能产生的问题。我本人所未曾预想的是,就在本书 出版之后短短几年之内,各种程序制度体系之间的相互借鉴开始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密集程度。这使得拙著对于程序制度移植研究 的潜在实践意义兀乎完全遮蔽了它为人们理解世界各国程序制度 提供粗略指南的智识功用。这种出乎患料的发展使我觉得有必要 向中国读者作一些交待,以解释我的理论框架在评估移植外国程 序理念的可行性方面的可能作用。 首先,为了从恰当的视角来关照程序移植问题,我们应当注 意到:对既有程序制度的不满存在于世界各国,而不仅仅是少数 几个地方。即使是在像英国、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虽然它们 的程序制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欧洲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 许多国家争相模仿的对豪,改苹的压力也正在逐渐增强。在回应

致中国读者的引言 这种压力以及到本土经验之外去寻找创新的启迪的过程中,承担 着改革重任的各国法律家们总是很容易为一些他国的制度设计所 吸孔,因为这些制度可能体现着较为健全的原则或者表现出良好 的意图。但是,匆忙将这些制度纳入到本国法律体系之中的做法 可能很容易导致不尽人意的结果。 导致这种危险的一个明显原因就是:规范司法管理的各项规 则往往是相互关联的,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相互支持的关 系。因此,用一项进口条款来取代一项本国条款的尝试不可避免 地会影响到那些改革者并不想加以改变的制度。因此,在折服于 一项外国规范的魅力之前,改革者们首先应当认真思考这项规范 与本国的整个规刚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可能性。但是, 这一类的法律分析只能算是一场精心构思的改革的第一步。这是 因为,程序创新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那些喜欢欣赏规 则之完备性的法律人。改革的成欣主要取决于新规则与某一特定 国家的司法管理模式所植根于其中的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兼容性。 因此,策划一场程序改革就像是策划一场音乐会。法律规则就好 像是一个个育符,尽管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可能具有内在的艺术 价值,但这并不能保证一场音乐会的成功。完备的乐器、娴热的 演奏者以及音乐类型对听众的吸引力也是同等重要的必备条件。 本书的重点在于讨论改治意识形态和政府组织形式的程序意 义,而很少涉及到一种引进的程序安排与司法制度的文化背景之 间所可能产生的紧张关系。但是,本书的重点讨论的骑已级提醒 人们注意:如果激发国内改草的源泉是一种外来的理念,而且这 种理念所来自的国家具有一套不同的程序制度,这种程序制度根 植于人们对待国家权力结构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改府职能观 念,那么,改革者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道慎。将英美程序理念 移植到中国的尝试就属于这种类型。因为,根据我的分析框架, 中国的程序苏境所展现出来的特征比较亲合于一种能动型的改府

致中国读者的引言 和一套科层式的权力组织机制,而英美的程序环境则呈现出恰恰 相反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其亲合于一种回应性的政府和一套协作 性的、更加注重平等的权力组织结构。为了说明由此而导致的不 同的结构安排,我们可以举出这样一个实例:包括辩诉交易和交 叉质证在内的许多英美程序安排都需要依靠一个人数众多并充满 活力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来推动其正常运作。相反,在中国,律师 的人数相对较少,并且不习惯于在诉讼过程中粉演积极的角色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这些英美程序安排移植到中国土壤中,它 们很可能会在实施的过程中道到扭曲或阁割。 为了避免一种可能的误解,我必须马上作出补充性的说明 我的研究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一个具有不同攻治传统的国 家移植程序性条款是绝对不可能的。采取这种立场就等于是对有 益的变化视而不见并且强迫人们满足于现状。我的研究旨在提醒 人们在进行此类移植的时候保持高度的审慎。在考惑移核莱一外 国规则的时候,当务之急是首先仔细考察在本国的制度背景中是 否存在使此项外国规则有可能发挥实际效用的先决条件。本国制 度能否接纳拟议中的创新?或者,本国制度在经过适当调整后能 否接纳拟议中的创新?这是任何改革者都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不过,即使实际的制度移植并没有发生,一种源自外国政治环境 的程序理念仍然可能澈发本国学者或政革者的灵感,帮助他们在 对外国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造的情况下设计出一种可行的本国制度 创新。 只要本书能够在帮助中国读者理解中国程序传统如何能够与 西方理念进行有意义的整合方面起到一点微的作用,郑戈博士 投入到这一翻译工作中的巨大努力便被证明是值得的。 米尔伊安·达玛什卡 2000年3月于康涅狄格州新港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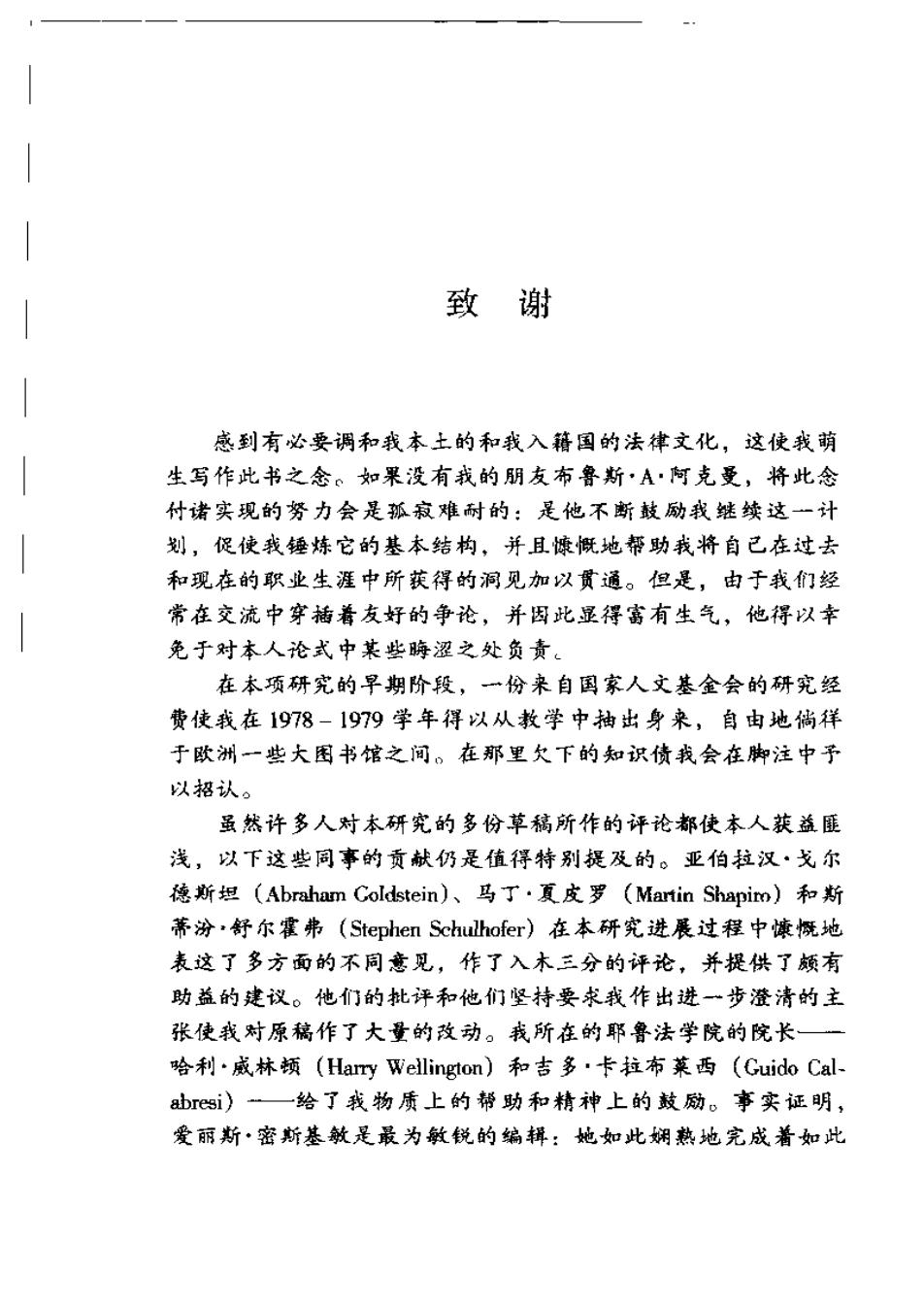
致谢 感到有必要调和我本土的和我入籍国的法律文化,这使我萌 生写作此书之念。如果没有我的朋友布鲁斯·A·阿克曼,将此念 付诸实现的努力会是孤寂难耐的:是他不断鼓励我继续这一计 划,促使我锤炼它的基本结构,并且慷慨地蒂助我将自己在过去 和现在的职业生涯中所获得的洞见加以贯通。但是,由于我们经 常在交流中穿插着友好的争论,并因此显得富有生气,他得以幸 免于对本人沦式中某些晦涩之处负责, 在木项研究的早期阶段,一份来自国家人文基金会的研究经 费使我在1978一1979学年得以从救学中抽出身来,自由地倘样 于欧洲一些大困书馆之间。在那里欠下的知识债我会在脚注中予 以招认。 虽然许多人对本研究的多份草稿所作的评论都使本人获益匪 浅,以下这些同事的贡献仍是值得特别提及的。亚伯拉汉·戈尔 德斯坦(Abraham Coldstein)、马了·夏皮罗(Martin Shapiro)和斯 蒂汾,舒尔襄弗(Stephen Schulhofer)在本研究进展过程中慷慨地 表这了多方面的不同意见,作了入木三分的评论,并提供了颇有 助益的建议。他们的批评和他们坚持要求我作出进一步澄清的主 张使我对原稿作了大量的改动。我所在的耶鲁法学院的院长 哈利·威林顿(Harry Weillington)和吉多·卡拉布莱西(Guido Cal- abresi)一给了我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鼓勋。事实证明 爱丽断·密斯基敏是最为敏锐的编辑:她如此娴熟地完成着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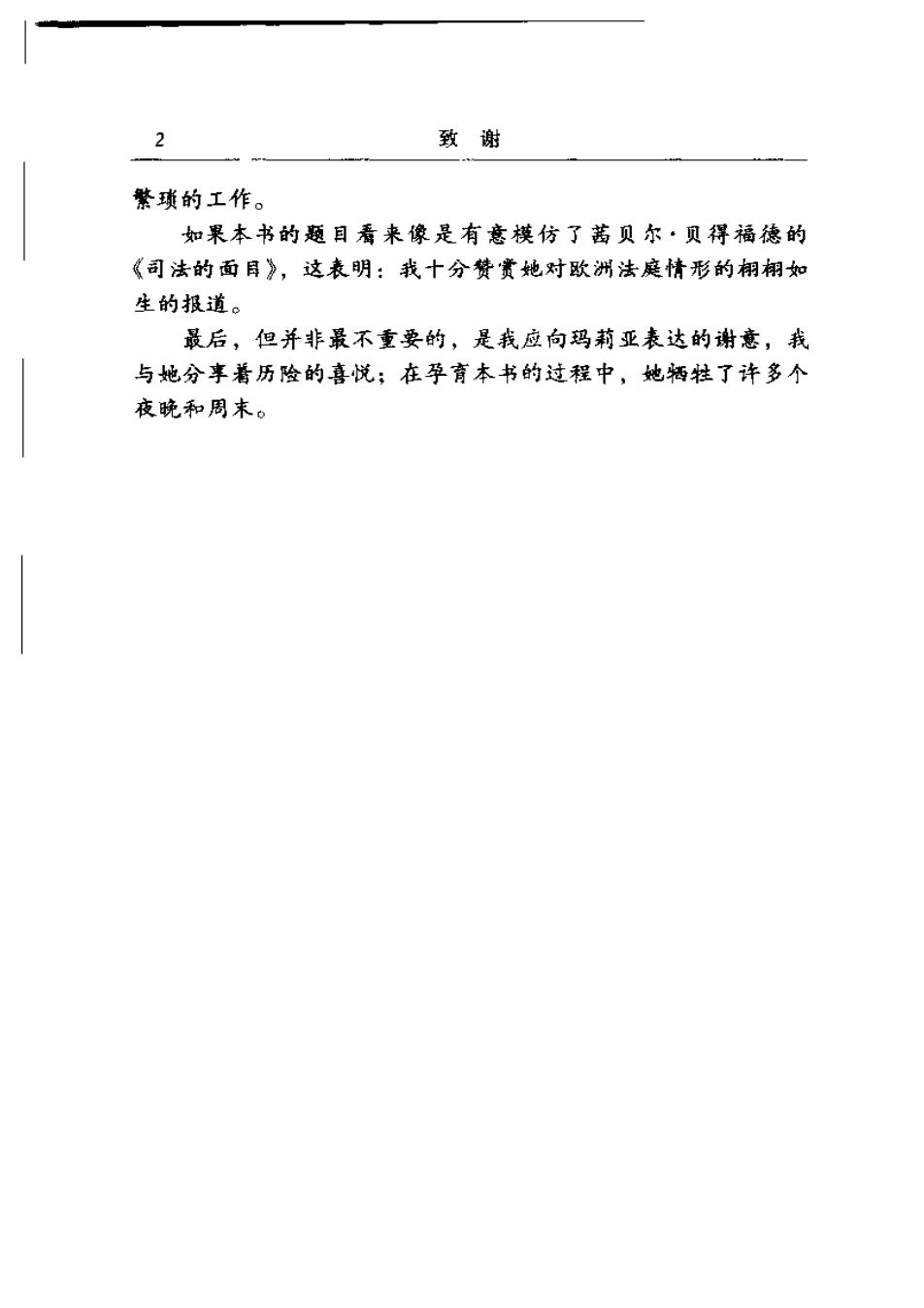
2 致谢 繁琐的工作。 如果本书的题目看来像是有意模仿了茜贝尔·贝得福德的 《司法的面目》,这表明:我十分赞赏地对欧洲法庭情形的翔栩如 生的报道。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应向玛莉亚表达的谢意,我 与她分享着历险的喜悦;在孕育本书的过程中,她牺牲了许多个 夜晚和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