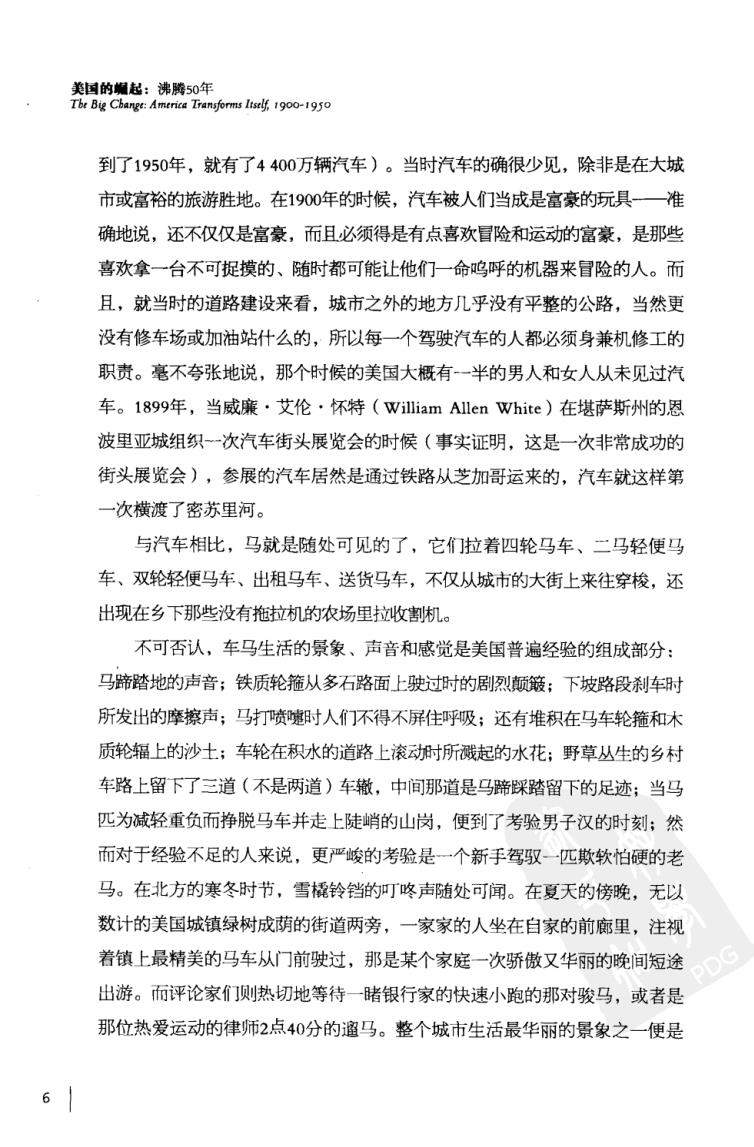
美国的崛起:沸腾50年 The Big Change:America Transforms Itself 1900-1950 到了1950年,就有了4400万辆汽车)。当时汽车的确很少见,除非是在大城 市或富裕的旅游胜地。在1900年的时候,汽车被人们当成是富豪的玩具一准 确地说,还不仅仅是富豪,而且必须得是有点喜欢冒险和运动的富豪,是那些 喜欢拿一台不可捉摸的、随时都可能让他们一命鸣呼的机器来冒险的人。而 且,就当时的道路建设来看,城市之外的地方几乎没有平整的公路,当然更 没有修车场或加油站什么的,所以每一个驾驶汽车的人都必须身兼机修工的 职责。毫不夸张地说,那个时候的美国大概有一半的男人和女人从未见过汽 车。1899年,当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在堪萨斯州的恩 波里亚城组织一次汽车街头展览会的时候(事实证明,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 街头展览会),参展的汽车居然是通过铁路从芝加哥运来的,汽车就这样第 一次横渡了密苏里河。 与汽车相比,马就是随处可见的了,它们拉着四轮马车、二马轻便马 车、双轮轻便马车、出租马车、送货马车,不仅从城市的大街上来往穿梭,还 出现在乡下那些没有拖拉机的农场里拉收割机。 不可否认,车马生活的景象、声音和感觉是美国普遍经验的组成部分: 马蹄踏地的声音;铁质轮箍从多石路面上驶过时的剧烈颠簸;下坡路段杀刹车时 所发出的摩擦声;马打喷嚏时人们不得不屏住呼吸;还有堆积在马车轮箍和木 质轮辐上的沙土;车轮在积水的道路上滚动时所溅起的水花:野草丛生的乡村 车路上留下了三道(不是两道)车辙,中间那道是马蹄踩踏留下的足迹;当马 匹为减轻重负而挣脱马车并走上陡峭的山岗,便到了考验男子汉的时刻;然 而对于经验不足的人来说,更严峻的考验是一个新手驾驭一匹欺软怕硬的老 马。在北方的寒冬时节,雪橘铃铛的叮咚声随处可闻。在夏天的傍晚,无以 数计的美国城镇绿树成荫的街道两旁,一家家的人坐在自家的前廊里,注视 着镇上最精美的马车从门前驶过,那是某个家庭一次骄傲又华丽的晚间短途 出游。而评论家们则热切地等待一睹银行家的快速小跑的那对骏马,或者是 那位热爱运动的律师2点40分的遛马。整个城市生活最华丽的景象之一便是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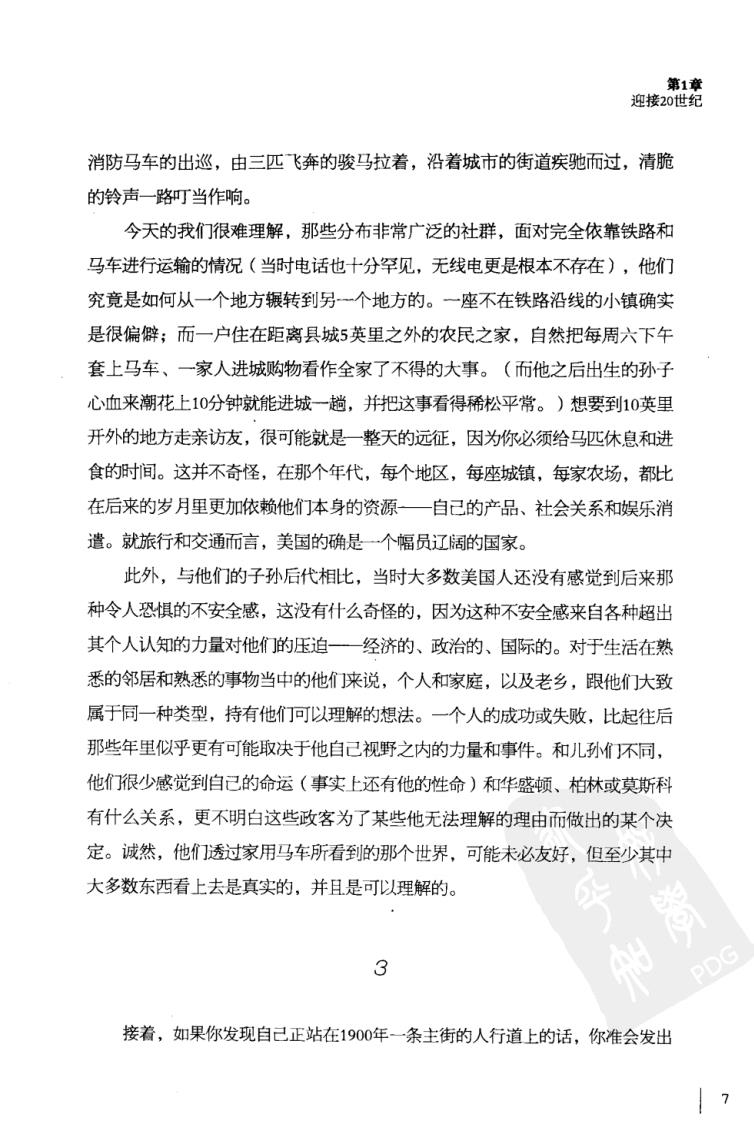
第1章 迎接20世纪 消防马车的出巡,由三匹飞奔的骏马拉着,沿着城市的街道疾驰而过,清脆 的铃声一路叮当作响。 今天的我们很难理解,那些分布非常广泛的社群,面对完全依靠铁路和 马车进行运输的情况(当时电话也十分罕见,无线电更是根本不存在),他们 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一个地方的。一座不在铁路沿线的小镇确实 是很偏僻:而一户住在距离县城5英里之外的农民之家,自然把每周六下午 套上马车、一家人进城购物看作全家了不得的大事。(而他之后出生的孙子 心血来潮花上10分钟就能进城一趟,并把这事看得稀松平常。)想要到10英里 开外的地方走亲访友,很可能就是一整天的远征,因为你必须给马匹休息和进 食的时间。这并不奇怪,在那个年代,每个地区,每座城镇,每家农场,都比 在后来的岁月里更加依赖他们本身的资源一自己的产品、社会关系和娱乐消 遣。就旅行和交通而言,美国的确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此外,与他们的子孙后代相比,当时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感觉到后来那 种令人恐惧的不安全感,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种不安全感来自各种超出 其个人认知的力量对他们的压迫一一经济的、政治的、国际的。对于生活在熟 悉的邻居和熟悉的事物当中的他们来说,个人和家庭,以及老乡,跟他们大致 属于同一种类型,持有他们可以理解的想法。一个人的成功成失败,比起往后 那些年里似乎更有可能取决于他自己视野之内的力量和事件。和儿孙不同, 他们很少感觉到自己的命运(事实上还有他的性命)和华盛顿、柏林或莫斯科 有什么关系,更不明白这些政客为了某些他无法理解的理由而做出的某个决 定。诚然,他们透过家用马车所看到的那个世界,可能未必友好,但至少其中 大多数东西看上去是真实的,并且是可以理解的。 3 PDG 接着,如果你发现自己正站在1900年一条主街的人行道上的话,你准会发出 7

美国的帽起:沸腾50年 The Big Cbange:America Transforms ltself 1900-1950 第二声惊呼:“瞧,看看这些裙子!” 在当时,小镇上每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女人都会穿一件实际上是在“扫大街” 的衣服,事实上,这些女人们几乎是时不时地在扫着大街,磨损并弄脏裙子的褶 边一如果裙子的主人没学会保持它干净的话。从衬衫的高领直到地面,1900年 的女人完全被包裹在一堆布料中。(当然,对这个外套还是有一些不恰当的限 制。那些时尚女性的晚礼服还是可以像1950年代的电视明星一样低颈露肩。但它 还是有拖在身后的裙裾,在跳舞的时候她必须尽最大限度地提起裙裾。)而对于 乡村的穿着,即便是打高尔夫或网球的衣着,女士们的裙子也必须有两到三英寸 拖到地面上,而那顶帽子(通常是一顶硬水手帽)几乎是必须要戴的。今天,随 意从1900年的相册里抽出一张照片,你的第一印象必定是:即便是在海边或在山 里,所有女人也都必须穿城里的衣服。 无论任何季节,一个女人都必须被从里到外一层层地包裹起来一衬衣、衬 裤、胸衣、胸衣外面的背心、一条或多条衬裙。那年头的胸衣简直就是一间可怕 的人身监狱,真是托了鲸须的福,恨不能竭尽全力把女性的形体扭曲成一个沙漏 形状。这身行头总是由两部分组成,由胸衣开始的惩罚并没有就此结束,还有紧 身马甲,马甲被绷得紧紧的,以完成沙漏的效果。女人的胸部被尽可能压成单一 结构,正确的姿势要求从这片隆起的高地向下,造成一种“后斜前直”的效果。 所以,画时装样片的艺术家们总是把穿着入时的女人描绘成几乎是在向前倾倒 的,完全不管实际上的平衡,只是为了努力实现一种完美的姿态。 至于男人的穿着,依照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的衣服中规中矩、僵硬刻板。 衣领又高又硬。对于那些场面上的人,即使是日常的西服套装也必须包括三颗 扣子的外套、必不可少的马甲,以及有些狭窄的裤子,在里面,还很可能穿着一 件袖口僵硬、胸襟多半也很僵硬的衬衫。如果他是个银行家,或者是个有经理身 份的商人,则多半会穿一件双排扣长礼服去上班,还得戴一顶缎面大礼帽(而不 是一顶不那么正式的圆顶礼帽),只有在5月15日至9月15日这段时间除外,按习 PDG 惯规定,这段时间要戴一顶硬草帽(对有钱人来说,多半是一顶巴拿马草帽)。 不戴帽子出门(除非是在开阔的露天场所)对穿台考究的男人来说简直就是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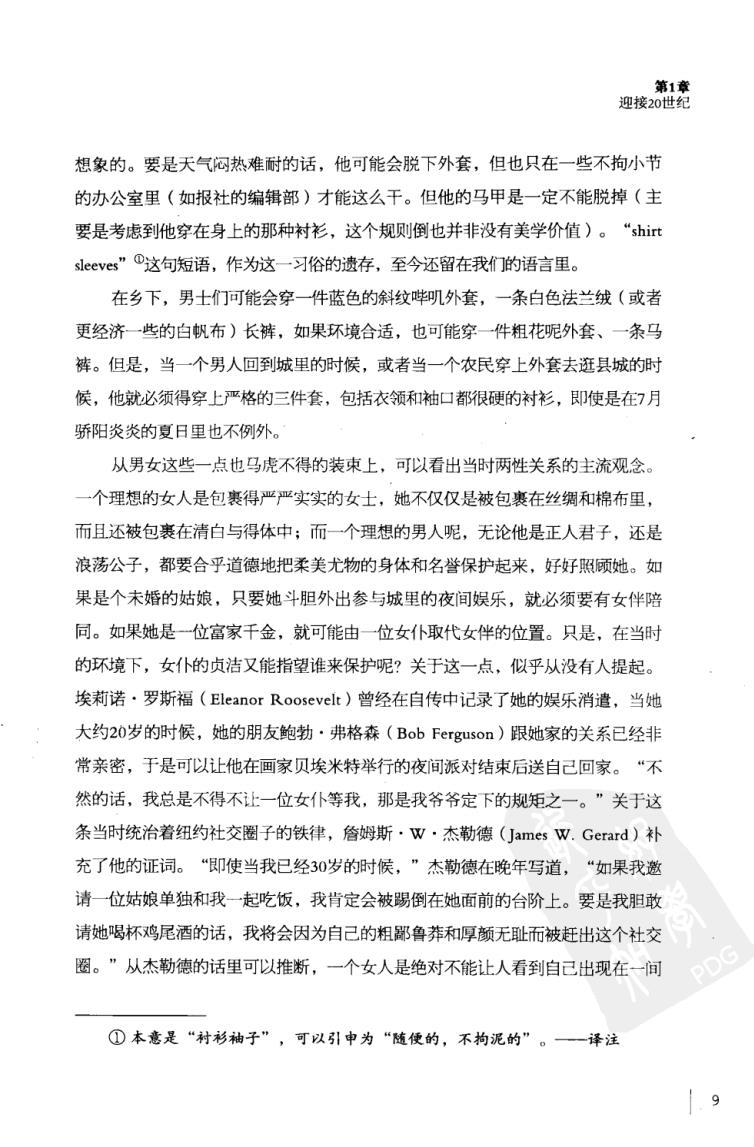
第1章 迎接20世纪 想象的。要是天气闷热难耐的话,他可能会脱下外套,但也只在一些不拘小节 的办公室里(如报社的编辑部)才能这么干。但他的马甲是一定不能脱掉(主 要是考虑到他穿在身上的那种衬衫,这个规则倒也并非没有美学价值)。“shit sleeves'”①这句短语,作为这一习俗的遗存,至今还留在我们的语言里。 在乡下,男士们可能会穿一件蓝色的斜纹哔叽外套,一条白色法兰绒(或者 更经济一些的白帆布)长裤,如果环境合适,也可能穿一件粗花呢外套、一条马 裤。但是,当一个男人回到城里的时候,或者当一个农民穿上外套去逛县城的时 候,他就必须得穿上严格的三件套,包括衣领和袖口都很硬的衬衫,即使是在7月 骄阳炎炎的夏日里也不例外。 从男女这些一点也马虎不得的装束上,可以看出当时两性关系的主流观念。 一个理想的女人是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士,她不仅仅是被包裹在丝绸和棉布里, 而且还被包裹在清白与得体中:而一个理想的男人呢,无论他是正人君子,还是 浪荡公子,都要合乎道德地把柔美尤物的身体和名誉保护起来,好好照顾她。如 果是个未婚的姑娘,只要她斗胆外出参与城里的夜间娱乐,就必须要有女伴陪 同。如果她是位富家千金,就可能由一位女仆取代女伴的位置。只是,在当时 的环境下,女仆的贞洁又能指望谁来保护呢?关于这一点,似乎从没有人提起。 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曾经在自传中记录了她的娱乐消遣,当她 大约20岁的时候,她的朋友鲍勃·弗格森(Bob Ferguson)跟她家的关系已经非 常亲密,于是可以让他在画家贝埃米特举行的夜间派对结束后送自己回家。“不 然的话,我总是不得不让一位女仆等我,那是我爷爷定下的规矩之一。”关于这 条当时统治着纽约社交圈子的铁律,詹姆斯·W·杰勒德(James W.Gerard)补 充了他的证词。“即使当我已经30岁的时候,”杰勒德在晚年写道,“如果我邀 请一位姑娘单独和我一起吃饭,我肯定会被踢倒在她面前的台阶上。要是我胆敢 请她喝杯鸡尾酒的话,我将会因为自己的粗鄙鲁莽和厚颜无耻而被赶出这个社交 圈。”从杰勒德的话里可以推断,一个女人是绝对不能让人看到自己出现在一间 PDG ①本意是“衬衫袖子”,可以引中为“随便的,不拘泥的”。一译注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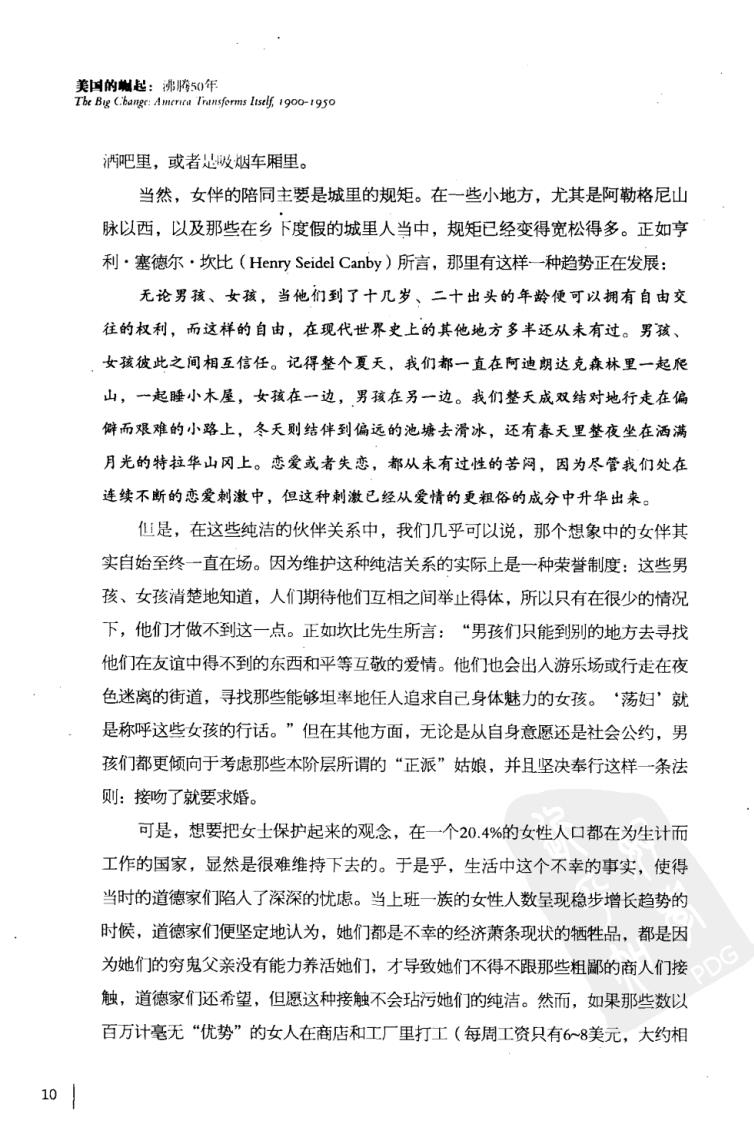
美国的州起:沸腾5)年 The Big (.bangr:Ameriru Transforms Itself 1900-195o 吧里,或者是吸烟车厢里。 当然,女伴的陪同主要是城里的规矩。在一些小地方,尤其是阿勒格尼山 脉以西,以及那些在乡下度假的城里人当中,规矩已经变得宽松得多。正如亨 利·塞德尔·坎比(Henry Seidel Canby)所言,那里有这样一种趋势正在发展: 无论男孩、女孩,当他们到了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年龄便可以拥有自由交 往的权利,而这样的自由,在现代世界史上的其他地方多半还从未有过。男孩、 女孩彼此之间相互信任。记得整个夏天,我们都一直在阿迪朗达克森林里一起爬 山,一起睡小木屋,女孩在一边,男孩在另一边。我们整天成双结对地行走在偏 僻而艰难的小路上,冬天则结伴到偏远的池塘去滑冰,还有春天里整夜坐在洒满 月光的特拉华山冈上。恋爱或者失恋,都从未有过性的苦闷,因为尽管我们处在 连续不断的恋爱刺激中,但这种刺激已经从爱情的更粗俗的成分中升华出来。 是,在这些纯洁的伙伴关系中,我们几乎可以说,那个想象中的女伴其 实自始至终一直在场。因为维护这种纯洁关系的实际上是一种荣誉制度:这些男 孩、女孩清楚地知道,人们期待他们互相之间举止得体,所以只有在很少的情况 下,他们才做不到这一点。正如坎比先生所言:“男孩们只能到别的地方去寻找 他们在友谊中得不到的东西和平等互敬的爱情。他们也会出入游乐场或行走在夜 色迷离的街道,寻找那些能够坦率地任人追求自己身体魅力的女孩。·荡妇'就 是称呼这些女孩的行话。”但在其他方面,无论是从自身意愿还是社会公约,男 孩们都更倾向于考虑那些本阶层所谓的“正派”姑娘,并且坚决奉行这样一条法 则:接吻了就要求婚。 可是,想要把女士保护起来的观念,在一个20.4%的女性人口都在为生计而 工作的国家,显然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于是乎,生活中这个不幸的事实,使得 当时的道德家们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当上班一族的女性人数呈现稳步增长趋势的 时候,道德家们便坚定地认为,她们都是不幸的经济萧条现状的栖牲品,都是因 为她们的穷鬼父亲没有能力养活她们,才导致她们]不得不跟那些粗鄙的商人们接 触,道德家们还希望,但愿这种接触不会玷污她们的纯洁。然而,如果那些数以 百万计毫无“优势”的女人在商店和工厂里打工(每周工资只有6一8美元,大约相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