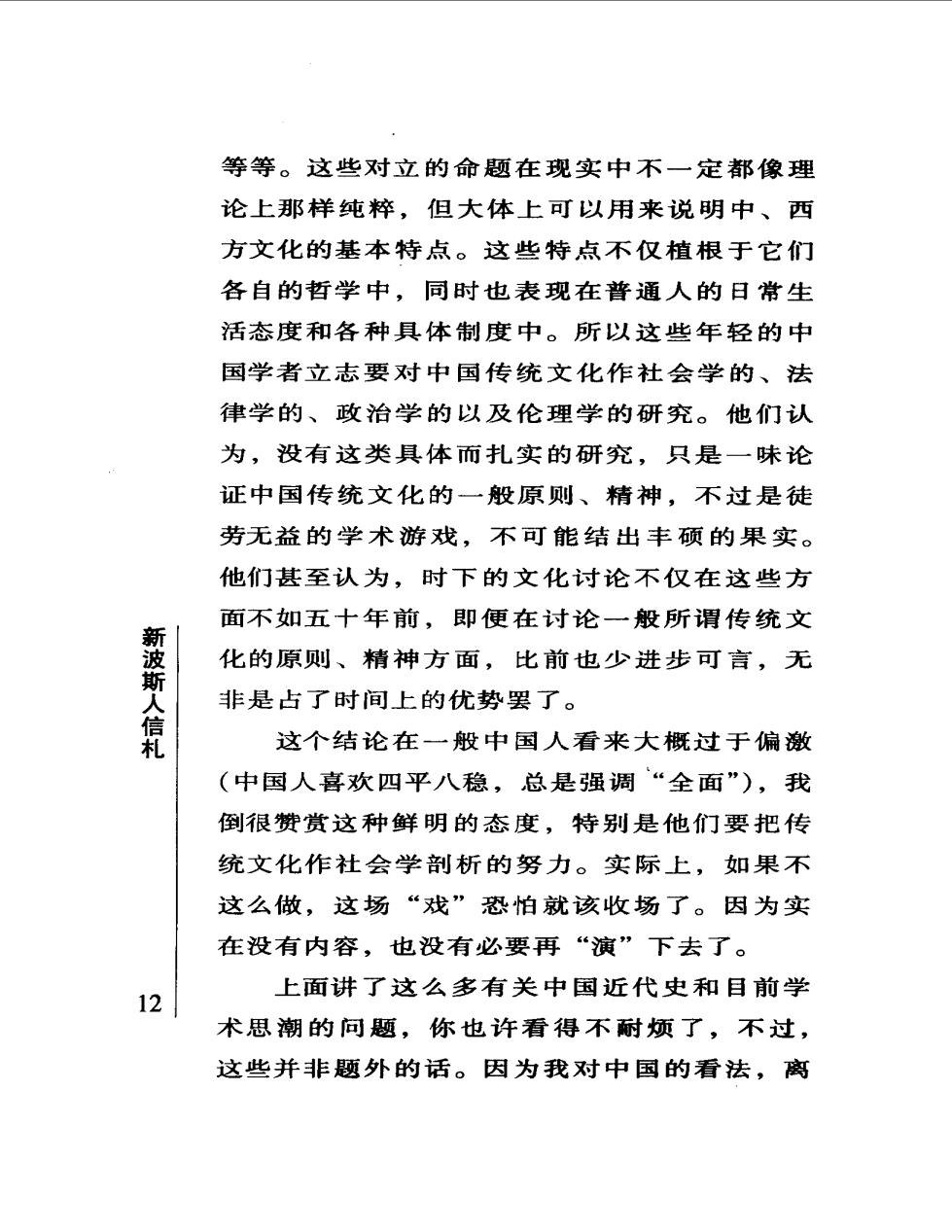
等等。这些对立的命题在现实中不一定都像理 论上那样纯粹,但大体上可以用来说明中、西 方文化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不仅植根于它们 各自的哲学中,同时也表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 活态度和各种具体制度中。所以这些年轻的中 国学者立志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作社会学的、法 律学的、政治学的以及伦理学的研究。他们认 为,没有这类具体而扎实的研究,只是一味论 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般原则、精神,不过是徒 劳无益的学术游戏,不可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他们甚至认为,时下的文化讨论不仅在这些方 面不如五十年前,即便在讨论一般所谓传统文 波斯, 化的原则、精神方面,比前也少进步可言,无 非是占了时间上的优势罢了。 这个结论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大概过于偏激 (中国人喜欢四平八稳,总是强调“全面”),我 倒很赞赏这种鲜明的态度,特别是他们要把传 统文化作社会学剖析的努力。实际上,如果不 这么做,这场“戏”恐怕就该收场了。因为实 在没有内容,也没有必要再“演”下去了。 上面讲了这么多有关中国近代史和目前学 术思潮的问题,你也许看得不耐烦了,不过, 这些并非题外的话。因为我对中国的看法,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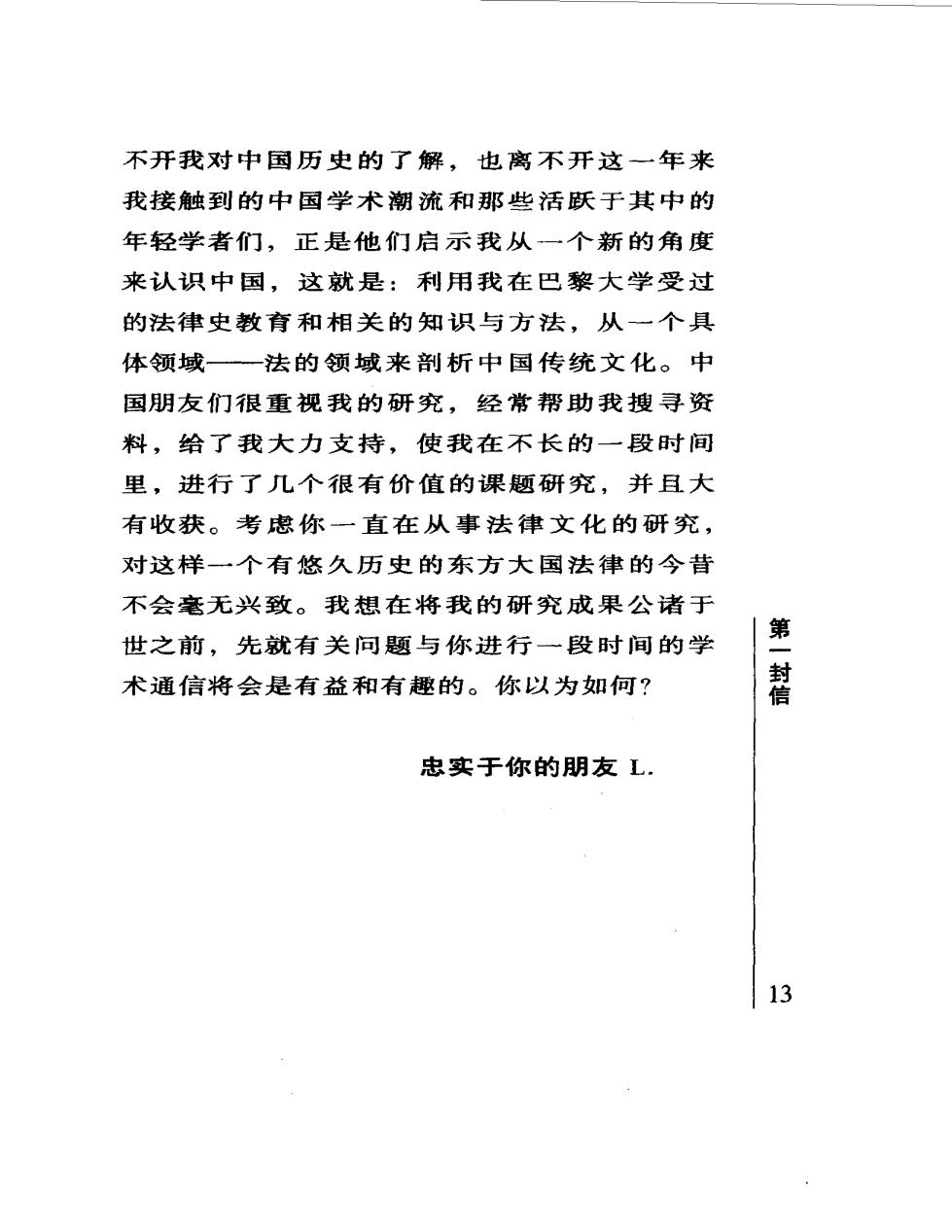
不开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也离不开这一年来 我接触到的中国学术潮流和那些活跃于其中的 年轻学者们,正是他们启示我从一个新的角度 来认识中国,这就是:利用我在巴黎大学受过 的法律史教育和相关的知识与方法,从一个具 体领域—法的领域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中 国朋友们很重视我的研究,经常帮助我搜寻资 料,给了我大力支持,使我在不长的一段时间 里,进行了几个很有价值的课题研究,并且大 有收获。考虑你一直在从事法律文化的研究, 对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法律的今昔 不会毫无兴致。我想在将我的研究成果公诸于 世之前,先就有关问题与你进行一段时间的学 第 术通信将会是有益和有趣的。你以为如何? 辖 忠实于你的朋友L. 13

第二封信 法即是刑,是令人生畏的暴力, 其社会功能,特别表现在“令行禁止” 新波斯人信札 四个字上面。这种法,很容易变成帝 王权力的延伸,执行统治者意志的强 暴手段,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因 此也很难为人们所信仰。如果不改变 这种传统,我不知道中国人如何去实 现法治。 亲爱的比尔: 14 想不到这么快就接到你的回信,你对我上 封信中的提议表现出如此的热情和兴趣,使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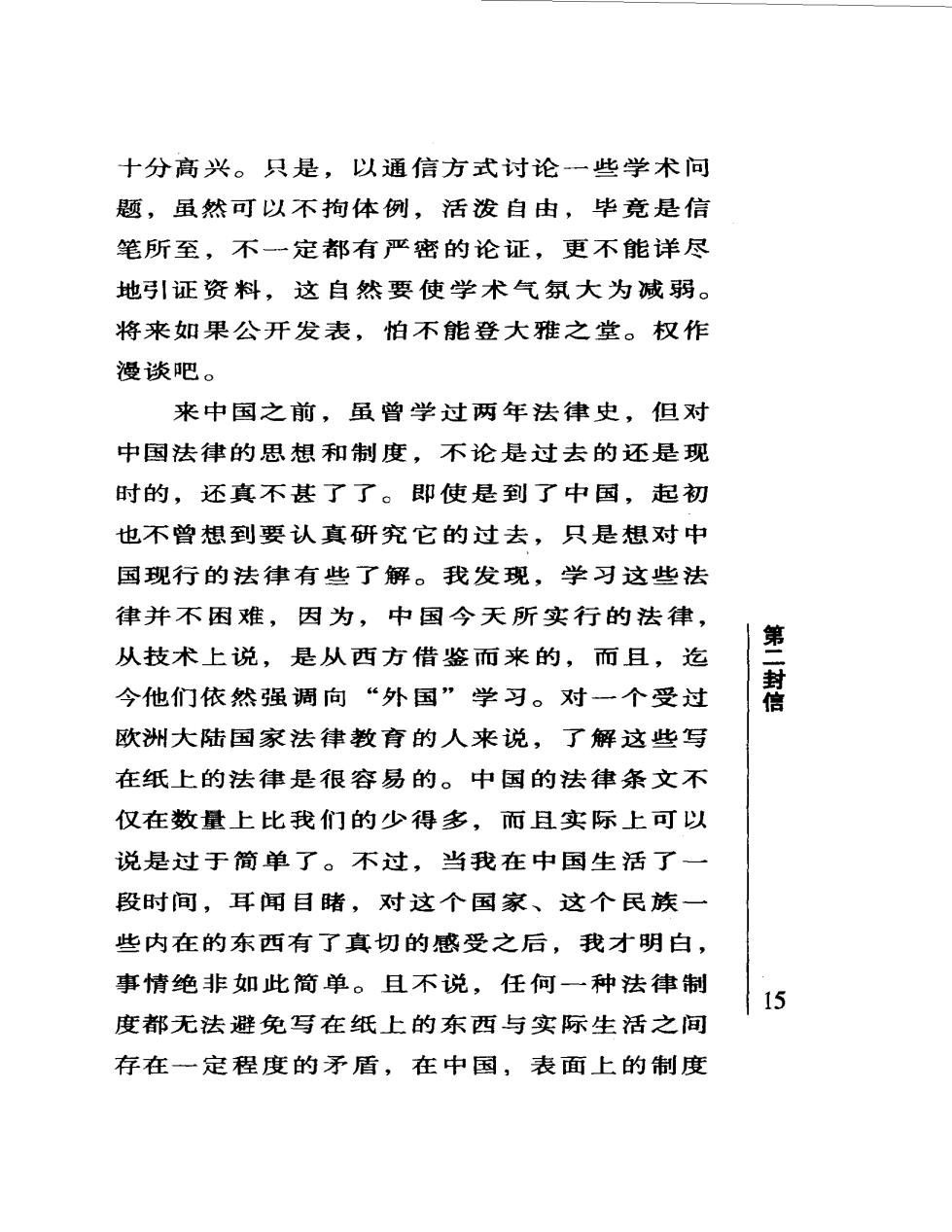
十分高兴。只是,以通信方式讨论一些学术问 题,虽然可以不拘体例,活泼自由,毕竞是信 笔所至,不一定都有严密的论证,更不能详尽 地引证资料,这自然要使学术气氛大为减弱。 将来如果公开发表,怕不能登大雅之堂。权作 漫谈吧。 来中国之前,虽曾学过两年法律史,但对 中国法律的思想和制度,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 时的,还真不甚了了。即使是到了中国,起初 也不曾想到要认真研究它的过去,只是想对中 国现行的法律有些了解。我发现,学习这些法 律并不困难,因为,中国今天所实行的法律, 第 从技术上说,是从西方借鉴而来的,而且,迄 今他们依然强调向“外国”学习。对一个受过 君 欧州大陆国家法律教育的人来说,了解这些写 在纸上的法律是很容易的。中国的法律条文不 仅在数量上比我们的少得多,而且实际上可以 说是过于简单了。不过,当我在中国生活了一 段时间,耳闻目睹,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 些内在的东西有了真切的感受之后,我才明白, 事情绝非如此简单。且不说,任何一种法律制 15 度都无法避免写在纸上的东西与实际生活之间 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在中国,表面上的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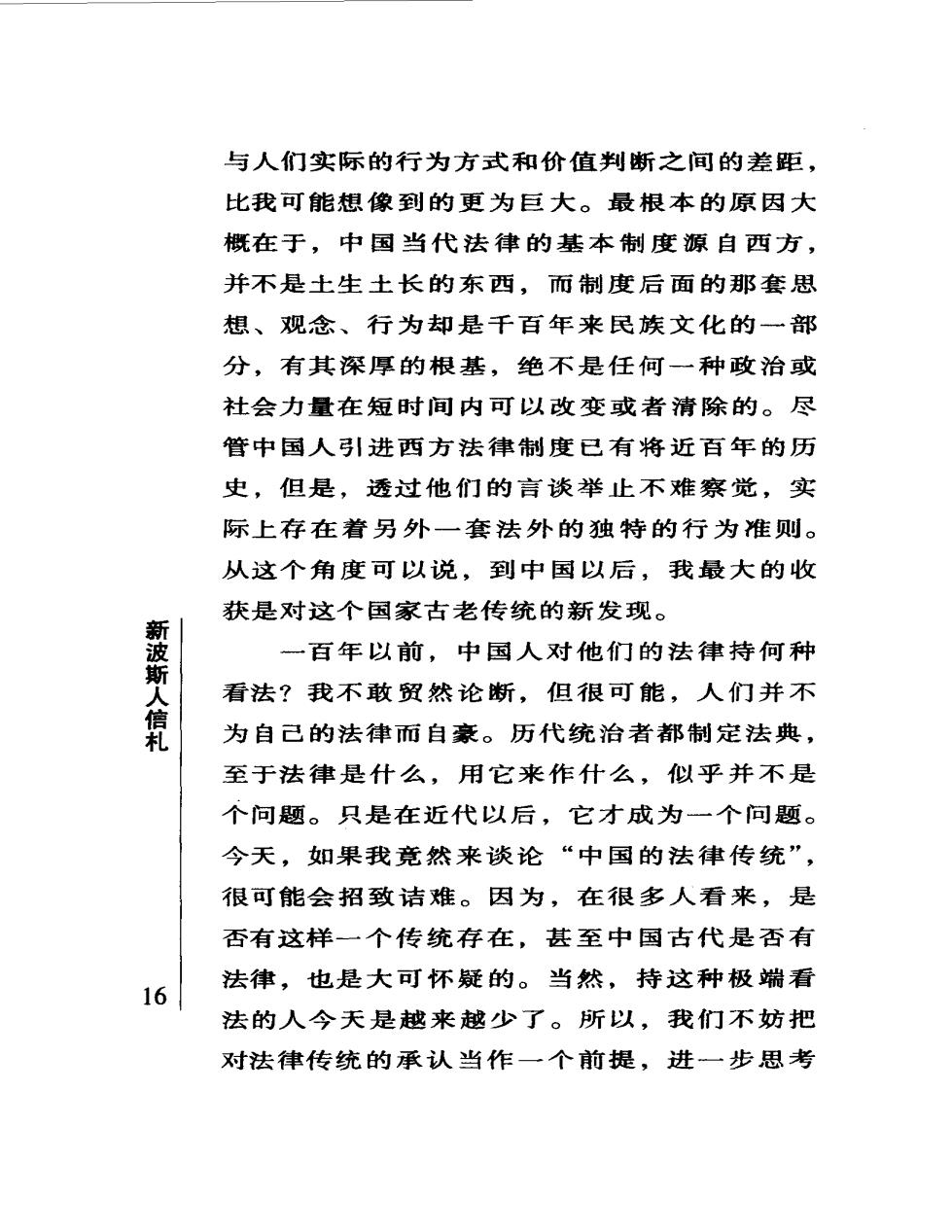
与人们实际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判断之间的差距, 比我可能想像到的更为巨大。最根本的原因大 概在于,中国当代法律的基本制度源自西方, 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东西,而制度后面的那套思 想、观念、行为却是千百年来民族文化的一部 分,有其深厚的根基,绝不是任何一种政治或 社会力量在短时间内可以改变或者清除的。尽 管中国人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已有将近百年的历 史,但是,透过他们的言谈举止不难察觉,实 际上存在着另外一套法外的独特的行为准则。 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到中国以后,我最大的收 获是对这个国家古老传统的新发现。 一百年以前,中国人对他们的法律持何种 看法?我不敢贸然论断,但很可能,人们并不 札 为自己的法律而自豪。历代统治者都制定法典, 至于法律是什么,用它来作什么,似乎并不是 个问题。只是在近代以后,它才成为一个问题。 今天,如果我竞然来谈论“中国的法律传统”, 很可能会招致诘雄。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是 否有这样一个传统存在,甚至中国古代是否有 法律,也是大可怀疑的。当然,持这种极端看 16 法的人今天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不妨把 对法律传统的承认当作一个前提,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