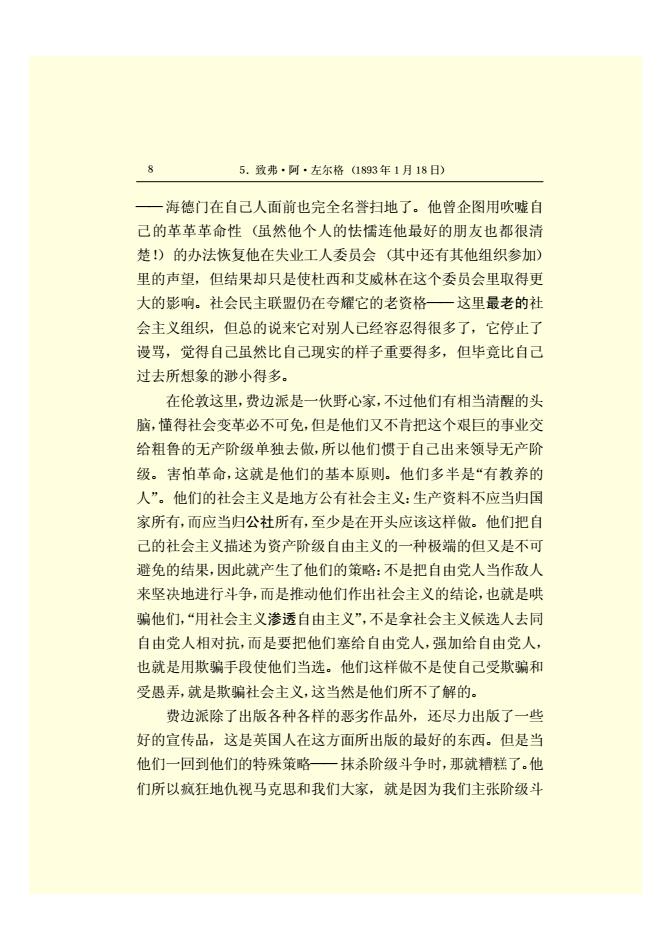
—— 海德门在自己人面前也完全名誉扫地了。他曾企图用吹嘘自 己的革革革命性 (虽然他个人的怯懦连他最好的朋友也都很清 楚!)的办法恢复他在失业工人委员会 (其中还有其他组织参加) 里的声望,但结果却只是使杜西和艾威林在这个委员会里取得更 大的影响。社会民主联盟仍在夸耀它的老资格—— 这里最老的社 会主义组织,但总的说来它对别人已经容忍得很多了,它停止了 谩骂,觉得自己虽然比自己现实的样子重要得多,但毕竟比自己 过去所想象的渺小得多。 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 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 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 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 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不应当归国 家所有,而应当归公社所有,至少是在开头应该这样做。他们把自 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但又是不可 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当作敌人 来坚决地进行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 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拿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 自由党人相对抗,而是要把他们塞给自由党人,强加给自由党人, 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他们当选。他们这样做不是使自己受欺骗和 受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他们所不了解的。 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 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当 他们一回到他们的特殊策略—— 抹杀阶级斗争时,那就糟糕了。他 们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主张阶级斗 8 5.致弗·阿·左尔格 (1893年1月18日)
—— 海德门在自己人面前也完全名誉扫地了。他曾企图用吹嘘自 己的革革革命性 (虽然他个人的怯懦连他最好的朋友也都很清 楚!)的办法恢复他在失业工人委员会 (其中还有其他组织参加) 里的声望,但结果却只是使杜西和艾威林在这个委员会里取得更 大的影响。社会民主联盟仍在夸耀它的老资格—— 这里最老的社 会主义组织,但总的说来它对别人已经容忍得很多了,它停止了 谩骂,觉得自己虽然比自己现实的样子重要得多,但毕竟比自己 过去所想象的渺小得多。 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 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 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 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 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不应当归国 家所有,而应当归公社所有,至少是在开头应该这样做。他们把自 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但又是不可 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当作敌人 来坚决地进行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 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拿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 自由党人相对抗,而是要把他们塞给自由党人,强加给自由党人, 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他们当选。他们这样做不是使自己受欺骗和 受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他们所不了解的。 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 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当 他们一回到他们的特殊策略—— 抹杀阶级斗争时,那就糟糕了。他 们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主张阶级斗 8 5.致弗·阿·左尔格 (1893年1月18日)

争。 费边派当然有许多资产阶级信徒,所以也有钱。在外省,他们 拥有很多干练的工人,这些工人根本不愿同社会民主联盟沾边。这 个组织在外省的成员,却有六分之五在不同程度上同意我们的观 点,并且在转折关头会坚决离开费边派。在布莱得弗德(他们的代 表也出席了),他们一再坚决表示反对费边派的伦敦执行委员会。 你可以看到,这是这里的运动的一个转折点,新的组织是可 能有所成就的。有一个时期,它差一点为秦平—— 他在自觉地或 不自觉地为托利党工作,正象费边派在为自由党工作一样—— 及 其同盟者马耳特曼·巴里(你在海牙8见过)所控制(巴里自己承 认,他是托利党永久的雇佣代理人和“保守党人社会主义派”9的头 目!—— 请看11月和12月的《工人时报》)。但是秦平最后还是 重新出版了他的《工人选民》报,从而使自己同《工人时报》和 新党处于对立地位。 凯尔·哈第担任起这个新党的领导人,这是明智的,而约翰 ·白恩士由于完全不在他的选区以外进行活动,本来已使他自己 受到很大损害,这一次仍然置身局外,是又干了一件蠢事。我担 心他要陷入一种完全难以支持的境地。 至于在这里,象凯·哈第、肖·马克斯韦尔这样一些人,也 在追求各种各样怀有个人野心的目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由 此产生的危险,正随着党本身变得更具有群众性和更强大而逐渐 减少;由于在互相竞争的党派面前必须自重,这种危险确实已经 减少了。最近几年,社会主义已深入到工业地区的群众中去,而 且我指望这些群众能管住自己的领导人。当然,还会干不少蠢事, 也还会有种种倾轧,只要能控制在适当范围内就行了。 5.致弗·阿·左尔格 (1893年1月18日) 9
争。 费边派当然有许多资产阶级信徒,所以也有钱。在外省,他们 拥有很多干练的工人,这些工人根本不愿同社会民主联盟沾边。这 个组织在外省的成员,却有六分之五在不同程度上同意我们的观 点,并且在转折关头会坚决离开费边派。在布莱得弗德(他们的代 表也出席了),他们一再坚决表示反对费边派的伦敦执行委员会。 你可以看到,这是这里的运动的一个转折点,新的组织是可 能有所成就的。有一个时期,它差一点为秦平—— 他在自觉地或 不自觉地为托利党工作,正象费边派在为自由党工作一样—— 及 其同盟者马耳特曼·巴里(你在海牙8见过)所控制(巴里自己承 认,他是托利党永久的雇佣代理人和“保守党人社会主义派”9的头 目!—— 请看11月和12月的《工人时报》)。但是秦平最后还是 重新出版了他的《工人选民》报,从而使自己同《工人时报》和 新党处于对立地位。 凯尔·哈第担任起这个新党的领导人,这是明智的,而约翰 ·白恩士由于完全不在他的选区以外进行活动,本来已使他自己 受到很大损害,这一次仍然置身局外,是又干了一件蠢事。我担 心他要陷入一种完全难以支持的境地。 至于在这里,象凯·哈第、肖·马克斯韦尔这样一些人,也 在追求各种各样怀有个人野心的目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由 此产生的危险,正随着党本身变得更具有群众性和更强大而逐渐 减少;由于在互相竞争的党派面前必须自重,这种危险确实已经 减少了。最近几年,社会主义已深入到工业地区的群众中去,而 且我指望这些群众能管住自己的领导人。当然,还会干不少蠢事, 也还会有种种倾轧,只要能控制在适当范围内就行了。 5.致弗·阿·左尔格 (1893年1月18日)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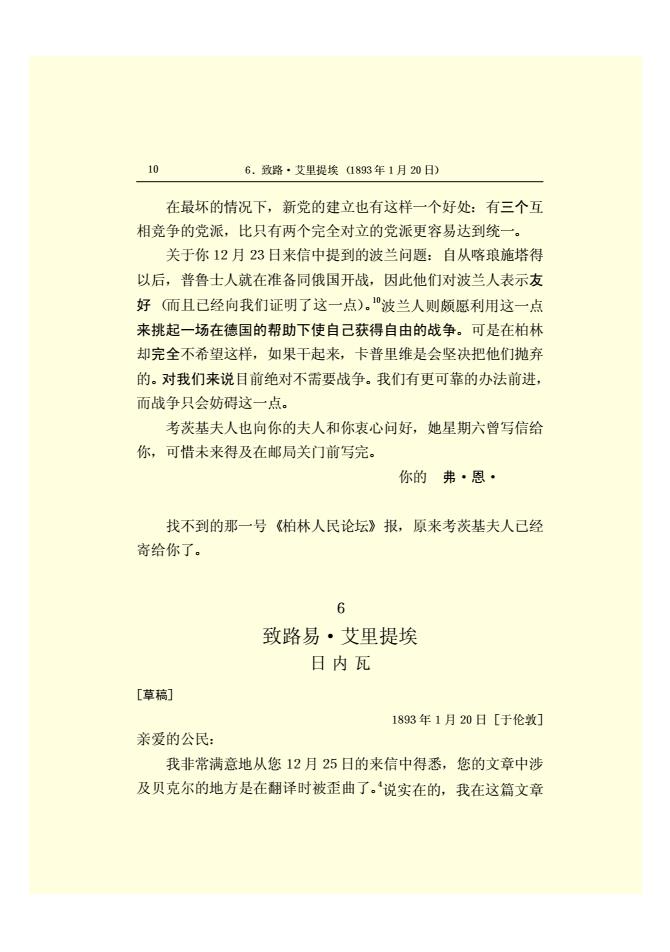
在最坏的情况下,新党的建立也有这样一个好处:有三个互 相竞争的党派,比只有两个完全对立的党派更容易达到统一。 关于你12月23日来信中提到的波兰问题:自从喀琅施塔得 以后,普鲁士人就在准备同俄国开战,因此他们对波兰人表示友 好 (而且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10波兰人则颇愿利用这一点 来挑起一场在德国的帮助下使自己获得自由的战争。可是在柏林 却完全不希望这样,如果干起来,卡普里维是会坚决把他们抛弃 的。对我们来说目前绝对不需要战争。我们有更可靠的办法前进, 而战争只会妨碍这一点。 考茨基夫人也向你的夫人和你衷心问好,她星期六曾写信给 你,可惜未来得及在邮局关门前写完。 你的 弗·恩· 找不到的那一号《柏林人民论坛》报,原来考茨基夫人已经 寄给你了。 6 致路易·艾里提埃 日 内 瓦 [草稿] 1893年1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非常满意地从您12月25日的来信中得悉,您的文章中涉 及贝克尔的地方是在翻译时被歪曲了。4说实在的,我在这篇文章 10 6.致路·艾里提埃 (1893年1月20日)
在最坏的情况下,新党的建立也有这样一个好处:有三个互 相竞争的党派,比只有两个完全对立的党派更容易达到统一。 关于你12月23日来信中提到的波兰问题:自从喀琅施塔得 以后,普鲁士人就在准备同俄国开战,因此他们对波兰人表示友 好 (而且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10波兰人则颇愿利用这一点 来挑起一场在德国的帮助下使自己获得自由的战争。可是在柏林 却完全不希望这样,如果干起来,卡普里维是会坚决把他们抛弃 的。对我们来说目前绝对不需要战争。我们有更可靠的办法前进, 而战争只会妨碍这一点。 考茨基夫人也向你的夫人和你衷心问好,她星期六曾写信给 你,可惜未来得及在邮局关门前写完。 你的 弗·恩· 找不到的那一号《柏林人民论坛》报,原来考茨基夫人已经 寄给你了。 6 致路易·艾里提埃 日 内 瓦 [草稿] 1893年1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非常满意地从您12月25日的来信中得悉,您的文章中涉 及贝克尔的地方是在翻译时被歪曲了。4说实在的,我在这篇文章 10 6.致路·艾里提埃 (1893年1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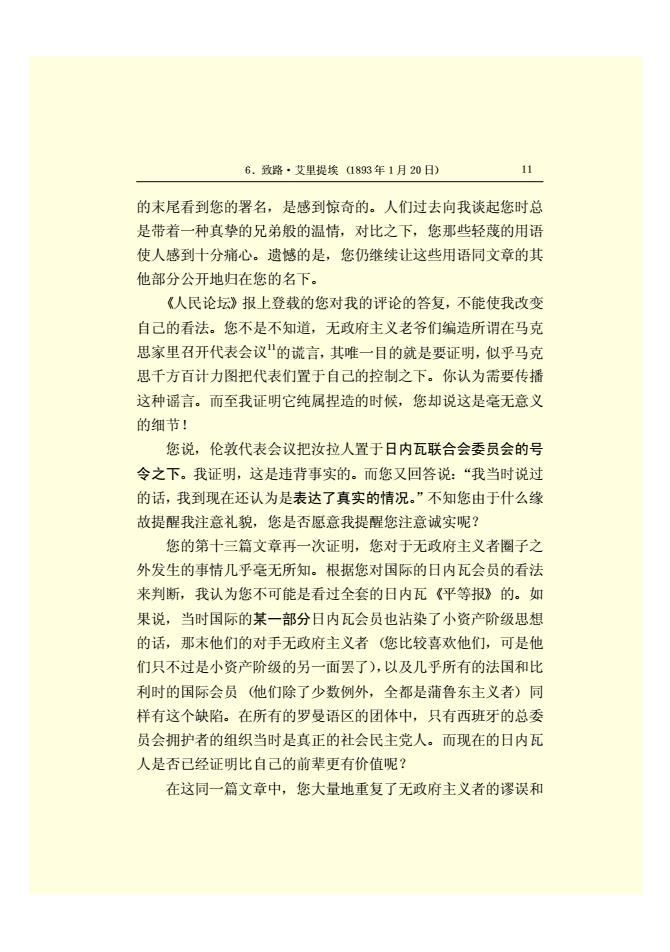
的末尾看到您的署名,是感到惊奇的。人们过去向我谈起您时总 是带着一种真挚的兄弟般的温情,对比之下,您那些轻蔑的用语 使人感到十分痛心。遗憾的是,您仍继续让这些用语同文章的其 他部分公开地归在您的名下。 《人民论坛》报上登载的您对我的评论的答复,不能使我改变 自己的看法。您不是不知道,无政府主义老爷们编造所谓在马克 思家里召开代表会议11的谎言,其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似乎马克 思千方百计力图把代表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你认为需要传播 这种谣言。而至我证明它纯属捏造的时候,您却说这是毫无意义 的细节! 您说,伦敦代表会议把汝拉人置于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号 令之下。我证明,这是违背事实的。而您又回答说:“我当时说过 的话,我到现在还认为是表达了真实的情况。”不知您由于什么缘 故提醒我注意礼貌,您是否愿意我提醒您注意诚实呢? 您的第十三篇文章再一次证明,您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圈子之 外发生的事情几乎毫无所知。根据您对国际的日内瓦会员的看法 来判断,我认为您不可能是看过全套的日内瓦《平等报》的。如 果说,当时国际的某一部分日内瓦会员也沾染了小资产阶级思想 的话,那末他们的对手无政府主义者 (您比较喜欢他们,可是他 们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另一面罢了),以及几乎所有的法国和比 利时的国际会员 (他们除了少数例外,全都是蒲鲁东主义者)同 样有这个缺陷。在所有的罗曼语区的团体中,只有西班牙的总委 员会拥护者的组织当时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而现在的日内瓦 人是否已经证明比自己的前辈更有价值呢? 在这同一篇文章中,您大量地重复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误和 6.致路·艾里提埃 (1893年1月20日) 11
的末尾看到您的署名,是感到惊奇的。人们过去向我谈起您时总 是带着一种真挚的兄弟般的温情,对比之下,您那些轻蔑的用语 使人感到十分痛心。遗憾的是,您仍继续让这些用语同文章的其 他部分公开地归在您的名下。 《人民论坛》报上登载的您对我的评论的答复,不能使我改变 自己的看法。您不是不知道,无政府主义老爷们编造所谓在马克 思家里召开代表会议11的谎言,其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似乎马克 思千方百计力图把代表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你认为需要传播 这种谣言。而至我证明它纯属捏造的时候,您却说这是毫无意义 的细节! 您说,伦敦代表会议把汝拉人置于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号 令之下。我证明,这是违背事实的。而您又回答说:“我当时说过 的话,我到现在还认为是表达了真实的情况。”不知您由于什么缘 故提醒我注意礼貌,您是否愿意我提醒您注意诚实呢? 您的第十三篇文章再一次证明,您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圈子之 外发生的事情几乎毫无所知。根据您对国际的日内瓦会员的看法 来判断,我认为您不可能是看过全套的日内瓦《平等报》的。如 果说,当时国际的某一部分日内瓦会员也沾染了小资产阶级思想 的话,那末他们的对手无政府主义者 (您比较喜欢他们,可是他 们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另一面罢了),以及几乎所有的法国和比 利时的国际会员 (他们除了少数例外,全都是蒲鲁东主义者)同 样有这个缺陷。在所有的罗曼语区的团体中,只有西班牙的总委 员会拥护者的组织当时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而现在的日内瓦 人是否已经证明比自己的前辈更有价值呢? 在这同一篇文章中,您大量地重复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误和 6.致路·艾里提埃 (1893年1月20日)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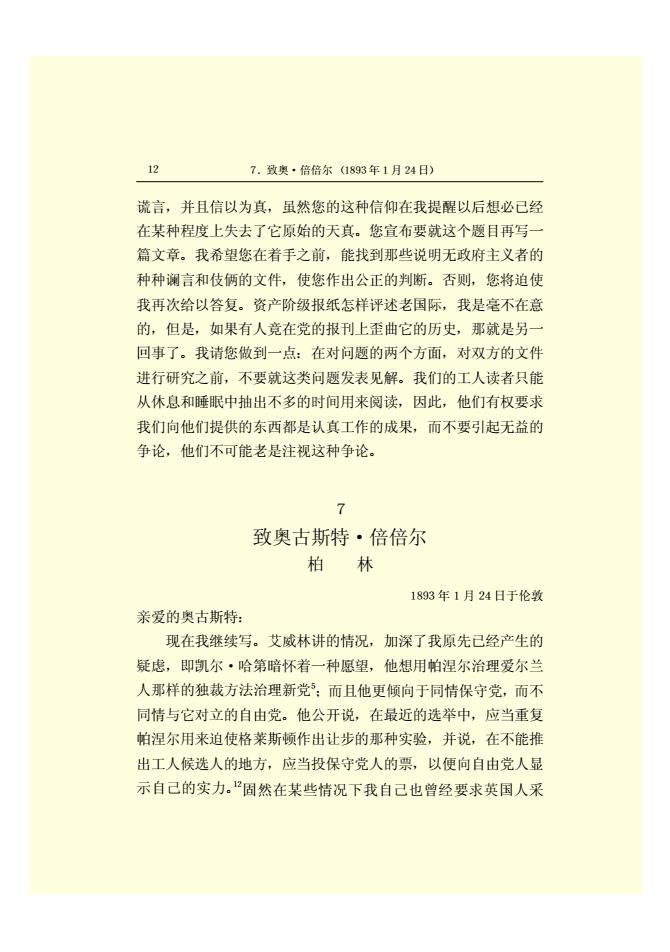
谎言,并且信以为真,虽然您的这种信仰在我提醒以后想必已经 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它原始的天真。您宣布要就这个题目再写一 篇文章。我希望您在着手之前,能找到那些说明无政府主义者的 种种谰言和伎俩的文件,使您作出公正的判断。否则,您将迫使 我再次给以答复。资产阶级报纸怎样评述老国际,我是毫不在意 的,但是,如果有人竟在党的报刊上歪曲它的历史,那就是另一 回事了。我请您做到一点:在对问题的两个方面,对双方的文件 进行研究之前,不要就这类问题发表见解。我们的工人读者只能 从休息和睡眠中抽出不多的时间用来阅读,因此,他们有权要求 我们向他们提供的东西都是认真工作的成果,而不要引起无益的 争论,他们不可能老是注视这种争论。 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 林 1893年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现在我继续写。艾威林讲的情况,加深了我原先已经产生的 疑虑,即凯尔·哈第暗怀着一种愿望,他想用帕涅尔治理爱尔兰 人那样的独裁方法治理新党5;而且他更倾向于同情保守党,而不 同情与它对立的自由党。他公开说,在最近的选举中,应当重复 帕涅尔用来迫使格莱斯顿作出让步的那种实验,并说,在不能推 出工人候选人的地方,应当投保守党人的票,以便向自由党人显 示自己的实力。12固然在某些情况下我自己也曾经要求英国人采 12 7.致奥·倍倍尔 (1893年1月24日)
谎言,并且信以为真,虽然您的这种信仰在我提醒以后想必已经 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它原始的天真。您宣布要就这个题目再写一 篇文章。我希望您在着手之前,能找到那些说明无政府主义者的 种种谰言和伎俩的文件,使您作出公正的判断。否则,您将迫使 我再次给以答复。资产阶级报纸怎样评述老国际,我是毫不在意 的,但是,如果有人竟在党的报刊上歪曲它的历史,那就是另一 回事了。我请您做到一点:在对问题的两个方面,对双方的文件 进行研究之前,不要就这类问题发表见解。我们的工人读者只能 从休息和睡眠中抽出不多的时间用来阅读,因此,他们有权要求 我们向他们提供的东西都是认真工作的成果,而不要引起无益的 争论,他们不可能老是注视这种争论。 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 林 1893年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现在我继续写。艾威林讲的情况,加深了我原先已经产生的 疑虑,即凯尔·哈第暗怀着一种愿望,他想用帕涅尔治理爱尔兰 人那样的独裁方法治理新党5;而且他更倾向于同情保守党,而不 同情与它对立的自由党。他公开说,在最近的选举中,应当重复 帕涅尔用来迫使格莱斯顿作出让步的那种实验,并说,在不能推 出工人候选人的地方,应当投保守党人的票,以便向自由党人显 示自己的实力。12固然在某些情况下我自己也曾经要求英国人采 12 7.致奥·倍倍尔 (1893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