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小声地矫正:“到了1946年,人家小陆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了。” “那是跟她结婚以后的事。”父亲接着说:“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里明白。有 时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从语气里,看得出父亲对她 的怜惜与叹惋。 我认识小陆是在全家去青岛避暑的途中。在火车的软卧车厢里,他对妻子照料之周,体贴 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实在是福。 小陆出出进进,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话下。午饭后,史良说要小憩片刻。 小陆听了,立刻打开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镶有法式花边的白色织物;继而 取出一个纸口袋,口袋里装的是一把小钉锤,两粒小铁钉,一节软铁丝。我们面面相觑,不 知要搞什么名堂。接着,他请来列车长,比比划划,低语几句后,只见小陆携工具爬到上铺, 在左右两壁各打进一小钉,然后把那卷织物抖落开一一原来是两尺见宽的帏帘。帏帘上端缀 着一个个小铜环,小陆将它们套入铁丝,再把铁丝的两端系于两边的铁钉。这样,一副床帏 在几分钟之内便做成了。它质地轻薄,尺寸合适,既把上铺遮得严严实实,又开合自如。史 良在帘内换上睡衣,戴好睡帽后,小陆从行李箱拿出一个木质衣架,把史良换下的衣服抚平 撑好,挂于下铺的衣帽钩。 车在行驶,车内寂静。帏帘将夏日的阳光挡在了外边,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陆端着 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赏着窗外的风景。我只要从他身边经过,叫声“陆叔叔”, 他都要点点头,圆圆的脸上泛起浅浅的笑… 后来母亲告诉我,尽管小陆对史大姐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比保姆还保姆,但人们都认 为史大姐应该享有更好的婚烟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机会。 “什么机会?”我追问着。 母亲说:“就是和你的罗伯伯(即罗隆基)呗。抗战时在重庆,他俩的关系已基本被大家 默认。史大姐对这件事是认真的,表现得从容大度。可谁也没料到会冒出个浦熙修来,老罗 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献殷勤。史大姐察觉后,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不想地位那么高、每 逢“三·八”妇女节便要向全中国妇女大谈或大写女性解放问题的人,在内心深处同样掩埋 着一个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伤痛。 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开什么会议,参加会议的既有中共的高官,也有民主 党派的领导。会议规定:与会者可携带一名家属,那时母亲在北京市卫生局当副局长,干 得十分起劲。她说自己没有时间休假,叫我去陪父亲。会议似乎开得轻松、顺利,父亲的 脸上总挂着笑容。趁着开会的空隙,他和交通部的人并邀请了苏联专家去视察秦皇岛港 (注一一父亲时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大概父亲觉得到海上一游的机会难得,便请史良同 行。 那天的风浪特别大,我们乘坐的船,是艘类乎快艇的玩意儿,颠簸得厉害。好多男人都受 不了。他们一个个在大海的魔力下,像显了原形一样:或东倒西歪,或愁眉苦脸,或钩腰 驼背。我干脆就趴下放平,如一只壁虎,紧贴于地。这时,发现整条船上唯有史良在正襟
母亲小声地矫正:“到了 1946 年,人家小陆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了。” “那是跟她结婚以后的事。”父亲接着说:“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里明白。有 时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从语气里,看得出父亲对她 的怜惜与叹惋。 我认识小陆是在全家去青岛避暑的途中。在火车的软卧车厢里,他对妻子照料之周,体贴 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实在是福。 小陆出出进进,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话下。午饭后,史良说要小憩片刻。 小陆听了,立刻打开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镶有法式花边的白色织物;继而 取出一个纸口袋,口袋里装的是一把小钉锤,两粒小铁钉,一节软铁丝。我们面面相觑,不 知要搞什么名堂。接着,他请来列车长,比比划划,低语几句后,只见小陆携工具爬到上铺, 在左右两壁各打进一小钉,然后把那卷织物抖落开——原来是两尺见宽的帏帘。帏帘上端缀 着一个个小铜环,小陆将它们套入铁丝,再把铁丝的两端系于两边的铁钉。这样,一副床帏 在几分钟之内便做成了。它质地轻薄,尺寸合适,既把上铺遮得严严实实,又开合自如。史 良在帘内换上睡衣,戴好睡帽后,小陆从行李箱拿出一个木质衣架,把史良换下的衣服抚平 撑好,挂于下铺的衣帽钩。 车在行驶,车内寂静。帏帘将夏日的阳光挡在了外边,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陆端着 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赏着窗外的风景。我只要从他身边经过,叫声“陆叔叔”, 他都要点点头,圆圆的脸上泛起浅浅的笑…… 后来母亲告诉我,尽管小陆对史大姐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比保姆还保姆,但人们都认 为史大姐应该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机会。 “什么机会?”我追问着。 母亲说:“就是和你的罗伯伯(即罗隆基)呗。抗战时在重庆,他俩的关系已基本被大家 默认。史大姐对这件事是认真的,表现得从容大度。可谁也没料到会冒出个浦熙修来,老罗 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献殷勤。史大姐察觉后,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不想地位那么高、每 逢“三·八”妇女节便要向全中国妇女大谈或大写女性解放问题的人,在内心深处同样掩埋 着一个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伤痛。 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开什么会议,参加会议的既有中共的高官,也 有民主 党派的领导。会议规定:与会者可携带一名家属,那时母亲在北京市卫生局 当副局长,干 得十分起劲。她说自己没有时间休假,叫我去陪父亲。会议似乎开得 轻松、顺利,父亲的 脸上总挂着笑容。趁着开会的空隙,他和交通部的人并邀请了 苏联专家去视察秦皇岛港 (注——父亲时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大概父亲觉得到海 上一游的机会难得,便请史良同 行。 那天的风浪特别大,我们乘坐的船,是艘类乎快艇的玩意儿,颠簸得厉害。好多男 人都受 不了。他们一个个在大海的魔力下,像显了原形一样:或东倒西歪,或愁眉 苦脸,或钩腰 驼背。我干脆就趴下放平,如一只壁虎,紧贴于地。这时,发现整条 船上唯有史良在正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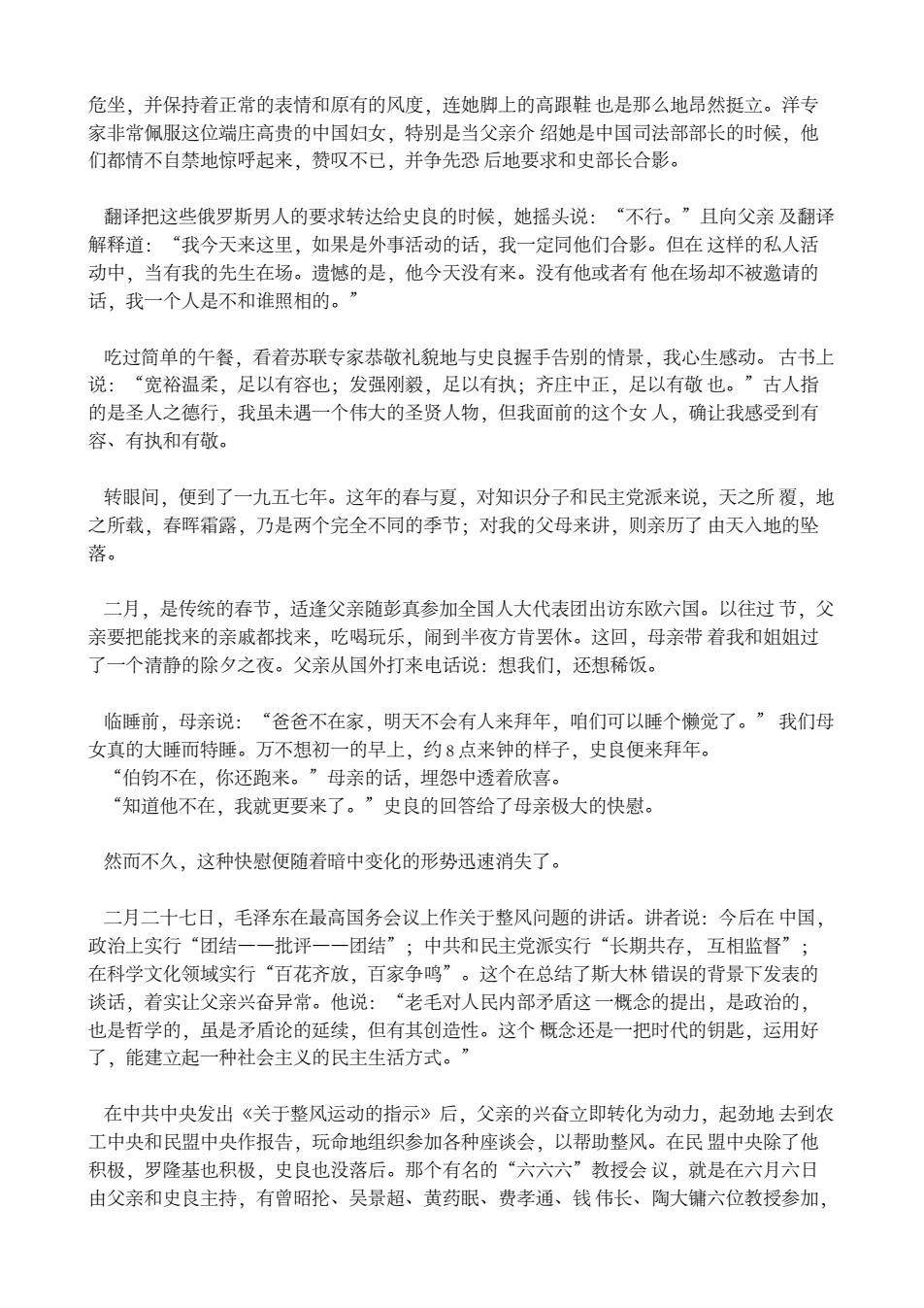
危坐,并保持着正常的表情和原有的风度,连她脚上的高跟鞋也是那么地昂然挺立。洋专 家非常佩服这位端庄高贵的中国妇女,特别是当父亲介绍她是中国司法部部长的时候,他 们都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赞叹不已,并争先恐后地要求和史部长合影。 翻译把这些俄罗斯男人的要求转达给史良的时候,她摇头说:“不行。”且向父亲及翻译 解释道:“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他们合影。但在这样的私人活 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遗憾的是,他今天没有来。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 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吃过简单的午餐,看着苏联专家恭敬礼貌地与史良握手告别的情景,我心生感动。古书上 说:“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古人指 的是圣人之德行,我虽未遇一个伟大的圣贤人物,但我面前的这个女人,确让我感受到有 容、有执和有敬。 转眼间,便到了一九五七年。这年的春与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说,天之所覆,地 之所载,春晖霜露,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季节;对我的父母来讲,则亲历了由天入地的坠 落。 二月,是传统的春节,适逢父亲随彭真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东欧六国。以往过节,父 亲要把能找来的亲戚都找来,吃喝玩乐,闹到半夜方肯罢休。这回,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过 了一个清静的除夕之夜。父亲从国外打来电话说:想我们,还想稀饭。 临睡前,母亲说:“爸爸不在家,明天不会有人来拜年,咱们可以睡个懒觉了。”我们母 女真的大睡而特睡。万不想初一的早上,约8点来钟的样子,史良便来拜年。 “伯钧不在,你还跑来。”母亲的话,埋怨中透着欣喜。 “知道他不在,我就更要来了。”史良的回答给了母亲极大的快慰。 然而不久,这种快慰便随着暗中变化的形势迅速消失了。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问题的讲话。讲者说:今后在中国, 政治上实行“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中共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在总结了斯大林错误的背景下发表的 谈话,着实让父亲兴奋异常。他说:“老毛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 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这个概念还是一把时代的钥匙,运用好 了,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 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父亲的兴奋立即转化为动力,起劲地去到农 工中央和民盟中央作报告,玩命地组织参加各种座谈会,以帮助整风。在民盟中央除了他 积极,罗隆基也积极,史良也没落后。那个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会议,就是在六月六日 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有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六位教授参加
危坐,并保持着正常的表情和原有的风度,连她脚上的高跟鞋 也是那么地昂然挺立。洋专 家非常佩服这位端庄高贵的中国妇女,特别是当父亲介 绍她是中国司法部部长的时候,他 们都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赞叹不已,并争先恐 后地要求和史部长合影。 翻译把这些俄罗斯男人的要求转达给史良的时候,她摇头说:“不行。”且向父亲 及翻译 解释道:“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他们合影。但在 这样的私人活 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遗憾的是,他今天没有来。没有他或者有 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 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吃过简单的午餐,看着苏联专家恭敬礼貌地与史良握手告别的情景,我心生感动。 古书上 说:“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庄中正,足以有敬 也。”古人指 的是圣人之德行,我虽未遇一个伟大的圣贤人物,但我面前的这个女 人,确让我感受到有 容、有执和有敬。 转眼间,便到了一九五七年。这年的春与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说,天之所 覆,地 之所载,春晖霜露,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季节;对我的父母来讲,则亲历了 由天入地的坠 落。 二月,是传统的春节,适逢父亲随彭真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东欧六国。以往过 节,父 亲要把能找来的亲戚都找来,吃喝玩乐,闹到半夜方肯罢休。这回,母亲带 着我和姐姐过 了一个清静的除夕之夜。父亲从国外打来电话说:想我们,还想稀饭。 临睡前,母亲说:“爸爸不在家,明天不会有人来拜年,咱们可以睡个懒觉了。” 我们母 女真的大睡而特睡。万不想初一的早上,约 8 点来钟的样子,史良便来拜年。 “伯钧不在,你还跑来。”母亲的话,埋怨中透着欣喜。 “知道他不在,我就更要来了。”史良的回答给了母亲极大的快慰。 然而不久,这种快慰便随着暗中变化的形势迅速消失了。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问题的讲话。讲者说:今后在 中国, 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中共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在总结了斯大林 错误的背景下发表的 谈话,着实让父亲兴奋异常。他说:“老毛对人民内部矛盾这 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 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这个 概念还是一把时代的钥匙,运用好 了,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 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父亲的兴奋立即转化为动力,起劲地 去到农 工中央和民盟中央作报告,玩命地组织参加各种座谈会,以帮助整风。在民 盟中央除了他 积极,罗隆基也积极,史良也没落后。那个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会 议,就是在六月六日 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有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 伟长、陶大镛六位教授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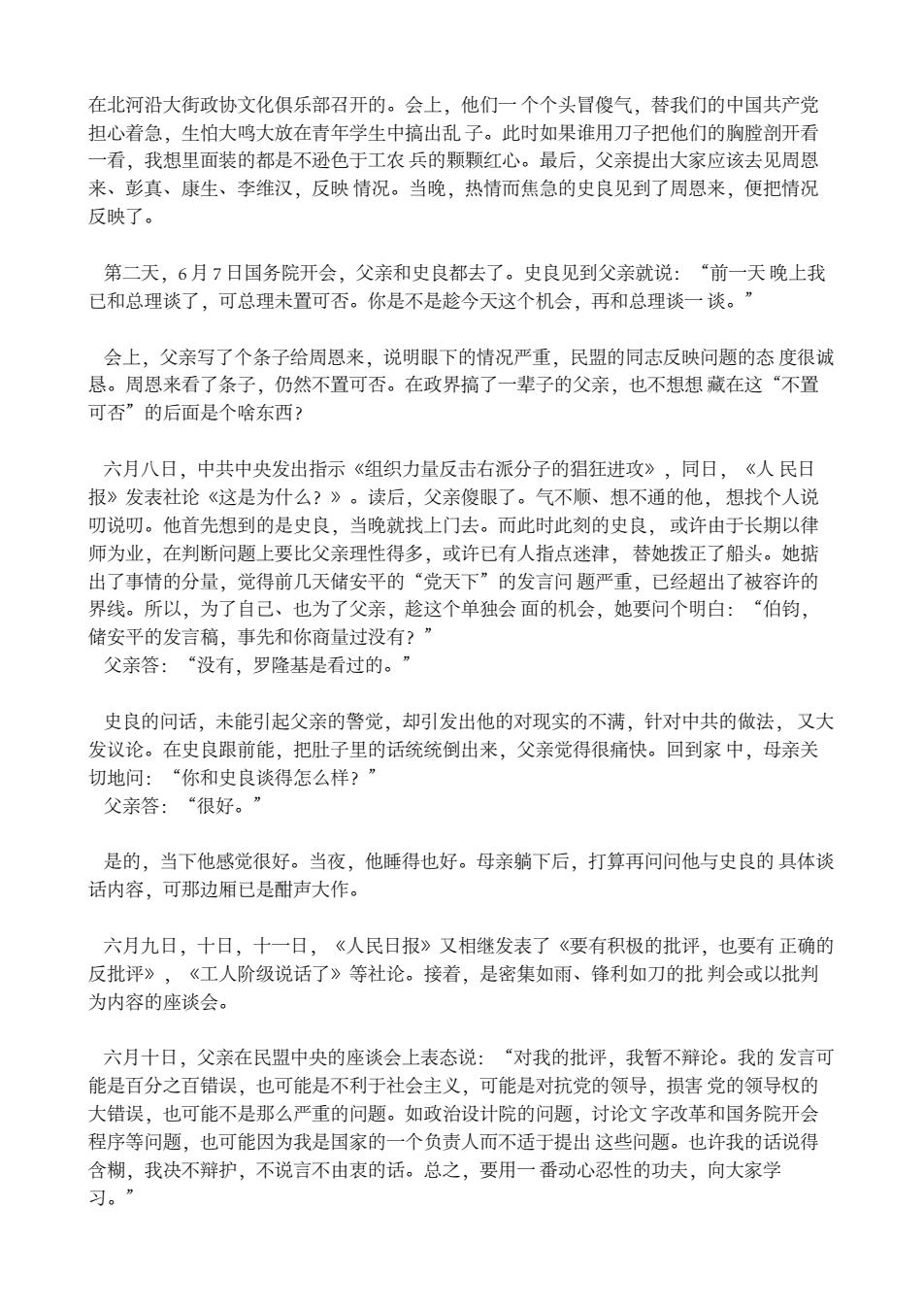
在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会上,他们一个个头冒傻气,替我们的中国共产党 担心着急,生怕大鸣大放在青年学生中搞出乱子。此时如果谁用刀子把他们的胸膛剖开看 一看,我想里面装的都是不逊色于工农兵的颗颗红心。最后,父亲提出大家应该去见周恩 来、彭真、康生、李维汉,反映情况。当晚,热情而焦急的史良见到了周恩来,便把情况 反映了。 第二天,6月7日国务院开会,父亲和史良都去了。史良见到父亲就说:“前一天晚上我 已和总理谈了,可总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这个机会,再和总理谈一谈。” 会上,父亲写了个条子给周恩来,说明眼下的情况严重,民盟的同志反映问题的态度很诚 恳。周恩来看了条子,仍然不置可否。在政界搞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想想藏在这“不置 可否”的后面是个啥东西?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 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读后,父亲傻眼了。气不顺、想不通的他,想找个人说 叨说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当晚就找上门去。而此时此刻的史良,或许由于长期以律 师为业,在判断问题上要比父亲理性得多,或许已有人指点迷津,替她拨正了船头。她掂 出了事情的分量,觉得前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问题严重,已经超出了被容许的 界线。所以,为了自己、也为了父亲,趁这个单独会面的机会,她要问个明白:“伯钧, 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 父亲答:“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史良的问话,未能引起父亲的警觉,却引发出他的对现实的不满,针对中共的做法,又大 发议论。在史良跟前能,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出来,父亲觉得很痛快。回到家中,母亲关 切地问:“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 父亲答:“很好。” 是的,当下他感觉很好。当夜,他睡得也好。母亲躺下后,打算再问问他与史良的具体谈 话内容,可那边厢已是酣声大作。 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人民日报》又相继发表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 反批评》,《工人阶级说话了》等社论。接着,是密集如雨、锋利如刀的批判会或以批判 为内容的座谈会。 六月十日,父亲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 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 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如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讨论文字改革和国务院开会 程序等问题,也可能因为我是国家的一个负责人而不适于提出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 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 习
在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会上,他们一 个个头冒傻气,替我们的中国共产党 担心着急,生怕大鸣大放在青年学生中搞出乱 子。此时如果谁用刀子把他们的胸膛剖开看 一看,我想里面装的都是不逊色于工农 兵的颗颗红心。最后,父亲提出大家应该去见周恩 来、彭真、康生、李维汉,反映 情况。当晚,热情而焦急的史良见到了周恩来,便把情况 反映了。 第二天,6 月 7 日国务院开会,父亲和史良都去了。史良见到父亲就说:“前一天 晚上我 已和总理谈了,可总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这个机会,再和总理谈一 谈。” 会上,父亲写了个条子给周恩来,说明眼下的情况严重,民盟的同志反映问题的态 度很诚 恳。周恩来看了条子,仍然不置可否。在政界搞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想想 藏在这“不置 可否”的后面是个啥东西?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 民日 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读后,父亲傻眼了。气不顺、想不通的他, 想找个人说 叨说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当晚就找上门去。而此时此刻的史良, 或许由于长期以律 师为业,在判断问题上要比父亲理性得多,或许已有人指点迷津, 替她拨正了船头。她掂 出了事情的分量,觉得前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问 题严重,已经超出了被容许的 界线。所以,为了自己、也为了父亲,趁这个单独会 面的机会,她要问个明白:“伯钧, 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 父亲答:“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史良的问话,未能引起父亲的警觉,却引发出他的对现实的不满,针对中共的做法, 又大 发议论。在史良跟前能,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出来,父亲觉得很痛快。回到家 中,母亲关 切地问:“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 父亲答:“很好。” 是的,当下他感觉很好。当夜,他睡得也好。母亲躺下后,打算再问问他与史良的 具体谈 话内容,可那边厢已是酣声大作。 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人民日报》又相继发表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 正确的 反批评》,《工人阶级说话了》等社论。接着,是密集如雨、锋利如刀的批 判会或以批判 为内容的座谈会。 六月十日,父亲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 发言可 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 党的领导权的 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如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讨论文 字改革和国务院开会 程序等问题,也可能因为我是国家的一个负责人而不适于提出 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 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 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 习

六月十二日,父亲在农工中央扩大座谈会上说:“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曾经谈到政治设计 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各办各委应当改变, 权放在各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 时的高兴,但语焉不详。可能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错误。” 六月十三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并写道:“这说明我 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国家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不良的影 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 父亲早被钦定为右派之首,自己却说“为右派分子所利用”。人家要求的和自己理解的, 相距岂止十万八千里。上边看到父亲竟是那么地不长进,不识相,不知趣,决定对其加温, 加压,加码。对一个民主人士而言,这个“温”“压”“码”暂时不能直接来自中共,而 必须弯曲地通过民主党派内部去实施。实施的步骤从六月十四日的晚上开始一一 六月十四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这个发言可以分作三段。 第一段是她继续帮助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史良说:“关于司法,我认为的确这几 年来成绩是巨大的,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点和错误是不容忽视的。审判机关历年来 在‘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中,是错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听见一些司法干部、 甚至是一些较负责的党员干部说:‘我们的错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几。’这是一种非常有害 的自满情绪。诚然,错判案件在整个判案数中是只有百分之几,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对被 错判的人则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拥护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 纠'的指示的,我看见很多地方是这样做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机关在执行这一原则 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件判错了经过当事人申请,甚至有关方面和上级司法机关指出, 审判人员也明知错了,但不肯承认错误,宣告无罪释放,还要硬找人家一点小辫子,宣判 为‘教育释放',其实应教育的不是无辜被告而正是主观主义的审判人员自己。更坏的是 本来错了,还迟迟不愿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时的平反。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 在对待我国原有的法学家上也是有缺点的。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在思想改造中,对待 有些老教授们是很不尊重的。当然,必须肯定,一切法律都是为阶级服务的,所有旧司法 人员是必须经过改造的。但是对一切愿意改造和批判自己旧法观点,并愿意为我国社会主 义服务的法学工作者也应给于机会,使其发挥作用。可是,在院系调整中,不少地方曾对 某些教授在一个相当长期内,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组织学习,闲置一旁,无人理会,形同 坐冷板凳。有的即使安排工作,也有安排不当的,或者无法发挥其潜力。我认为这是由于 某些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和宗派情绪,因而对本来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我国法学事业贡献 力量而又不能发挥潜力的教授们的苦楚心情,是领会不够的。因此,我们认为对原有教授 和法学家们愿为社会主义法制服务的热诚及其潜力,应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并进一步发挥 他们应有的作用。”这段话,表现出一个著名法学家的水准,一个司法部长的责任心
六月十二日,父亲在农工中央扩大座谈会上说:“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曾经谈到政 治设计 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各办 各委应当改变, 权放在各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 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 时的高兴,但语焉不详。可能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 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错误。” 六月十三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 认自己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并写道: “这说明我 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国家政策,以致造 成政治上不良的影 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 父亲早被钦定为右派之首,自己却说“为右派分子所利用”。人家要求的和自己理 解的, 相距岂止十万八千里。上边看到父亲竟是那么地不长进,不识相,不知趣, 决定对其加温, 加压,加码。对一个民主人士而言,这个“温”“压”“码”暂时 不能直接来自中共,而 必须弯曲地通过民主党派内部去实施。实施的步骤从六月十 四日的晚上开始—— 六月十四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这个发言可以分 作三段。 第一段是她继续帮助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史良说:“关于司法, 我认为的确这几 年来成绩是巨大的,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点和错误是不容忽 视的。审判机关历年来 在‘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中,是错判了一些案件, 可是,我常听见一些司法干部、 甚至是一些较负责的党员干部说:‘我们的错判案 件只有百分之几。’这是一种非常有害 的自满情绪。诚然,错判案件在整个判案数 中是只有百分之几,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对被 错判的人则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 不幸了。我是拥护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 纠’的指示的,我看见很多地方 是这样做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机关在执行这一原则 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 件判错了经过当事人申请,甚至有关方面和上级司法机关指出, 审判人员也明知错 了,但不肯承认错误,宣告无罪释放,还要硬找人家一点小辫子,宣判 为‘教育释 放’,其实应教育的不是无辜被告而正是主观主义的审判人员自己。更坏的是 本来 错了,还迟迟不愿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时的平反。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 在对待我国原有的法学家上也是有缺点的。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在思想改造中, 对待 有些老教授们是很不尊重的。当然,必须肯定,一切法律都是为阶级服务的, 所有旧司法 人员是必须经过改造的。但是对一切愿意改造和批判自己旧法观点,并 愿意为我国社会主 义服务的法学工作者也应给于机会,使其发挥作用。可是,在院 系调整中,不少地方曾对 某些教授在一个相当长期内,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组织学 习,闲置一旁,无人理会,形同 坐冷板凳。有的即使安排工作,也有安排不当的, 或者无法发挥其潜力。我认为这是由于 某些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和宗派情绪,因而 对本来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我国法学事业贡献 力量而又不能发挥潜力的教授们的苦 楚心情,是领会不够的。因此,我们认为对原有教授 和法学家们愿为社会主义法制 服务的热诚及其潜力,应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并进一步发挥 他们应有的作用。”这 段话,表现出一个著名法学家的水准,一个司法部长的责任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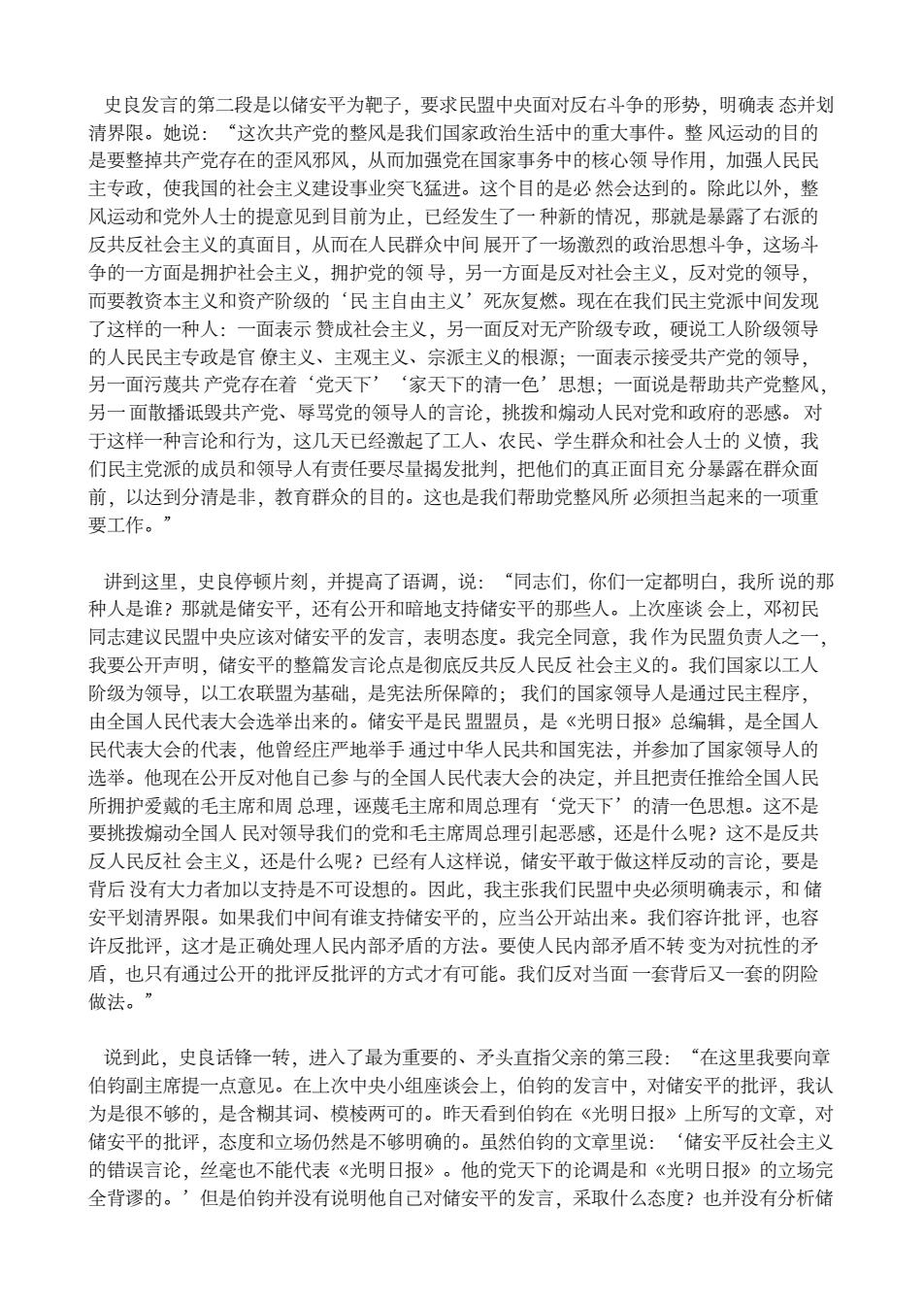
史良发言的第二段是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对反右斗争的形势,明确表态并划 清界限。她说:“这次共产党的整风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整风运动的目的 是要整掉共产党存在的歪风邪风,从而加强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加强人民民 主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这个目的是必然会达到的。除此以外,整 风运动和党外人士的提意见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一种新的情况,那就是暴露了右派的 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从而在人民群众中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这场斗 争的一方面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 而要教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主义’死灰复燃。现在在我们民主党派中间发现 了这样的一种人:一面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另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硬说工人阶级领导 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另一面污蔑共产党存在着‘党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一面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 另一面散播诋毁共产党、辱骂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挑拨和煽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恶感。对 于这样一种言论和行为,这几天已经激起了工人、农民、学生群众和社会人士的义愤,我 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和领导人有责任要尽量揭发批判,把他们的真正面目充分暴露在群众面 前,以达到分清是非,教育群众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帮助党整风所必须担当起来的一项重 要工作。” 讲到这里,史良停顿片刻,并提高了语调,说:“同志们,你们一定都明白,我所说的那 种人是谁?那就是储安平,还有公开和暗地支持储安平的那些人。上次座谈会上,邓初民 同志建议民盟中央应该对储安平的发言,表明态度。我完全同意,我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 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我们国家以工人 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宪法所保障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通过民主程序,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 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 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 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 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已经有人这样说,储安平敢于做这样反动的言论,要是 背后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我主张我们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 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我们容许批评,也容 许反批评,这才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使人民内部矛盾不转变为对抗性的矛 盾,也只有通过公开的批评反批评的方式才有可能。我们反对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的阴险 做法。” 说到此,史良话锋一转,进入了最为重要的、矛头直指父亲的第三段:“在这里我要向章 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 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昨天看到伯钧在《光明日报》上所写的文章,对 储安平的批评,态度和立场仍然是不够明确的。虽然伯钧的文章里说:‘储安平反社会主义 的错误言论,丝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报》。他的党天下的论调是和《光明日报》的立场完 全背谬的。’但是伯钧并没有说明他自己对储安平的发言,采取什么态度?也并没有分析储
史良发言的第二段是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对反右斗争的形势,明确表 态并划 清界限。她说:“这次共产党的整风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整 风运动的目的 是要整掉共产党存在的歪风邪风,从而加强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领 导作用,加强人民民 主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这个目的是必 然会达到的。除此以外,整 风运动和党外人士的提意见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一 种新的情况,那就是暴露了右派的 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从而在人民群众中间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这场斗 争的一方面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 导,另一方面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 而要教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 主自由主义’死灰复燃。现在在我们民主党派中间发现 了这样的一种人:一面表示 赞成社会主义,另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硬说工人阶级领导 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官 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另一面污蔑共 产党存在着‘党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一面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 另一 面散播诋毁共产党、辱骂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挑拨和煽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恶感。 对 于这样一种言论和行为,这几天已经激起了工人、农民、学生群众和社会人士的 义愤,我 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和领导人有责任要尽量揭发批判,把他们的真正面目充 分暴露在群众面 前,以达到分清是非,教育群众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帮助党整风所 必须担当起来的一项重 要工作。” 讲到这里,史良停顿片刻,并提高了语调,说:“同志们,你们一定都明白,我所 说的那 种人是谁?那就是储安平,还有公开和暗地支持储安平的那些人。上次座谈 会上,邓初民 同志建议民盟中央应该对储安平的发言,表明态度。我完全同意,我 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 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 社会主义的。我们国家以工人 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宪法所保障的;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通过民主程序,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储安平是民 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 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 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 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 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 要挑拨煽动全国人 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 反人民反社 会主义,还是什么呢?已经有人这样说,储安平敢于做这样反动的言论,要是 背后 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我主张我们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 储 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我们容许批 评,也容 许反批评,这才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使人民内部矛盾不转 变为对抗性的矛 盾,也只有通过公开的批评反批评的方式才有可能。我们反对当面 一套背后又一套的阴险 做法。” 说到此,史良话锋一转,进入了最为重要的、矛头直指父亲的第三段:“在这里我要向章 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 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昨天看到伯钧在《光明日报》上所写的文章,对 储安平的批评,态度和立场仍然是不够明确的。虽然伯钧的文章里说:‘储安平反社会主义 的错误言论,丝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报》。他的党天下的论调是和《光明日报》的立场完 全背谬的。’但是伯钧并没有说明他自己对储安平的发言,采取什么态度?也并没有分析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