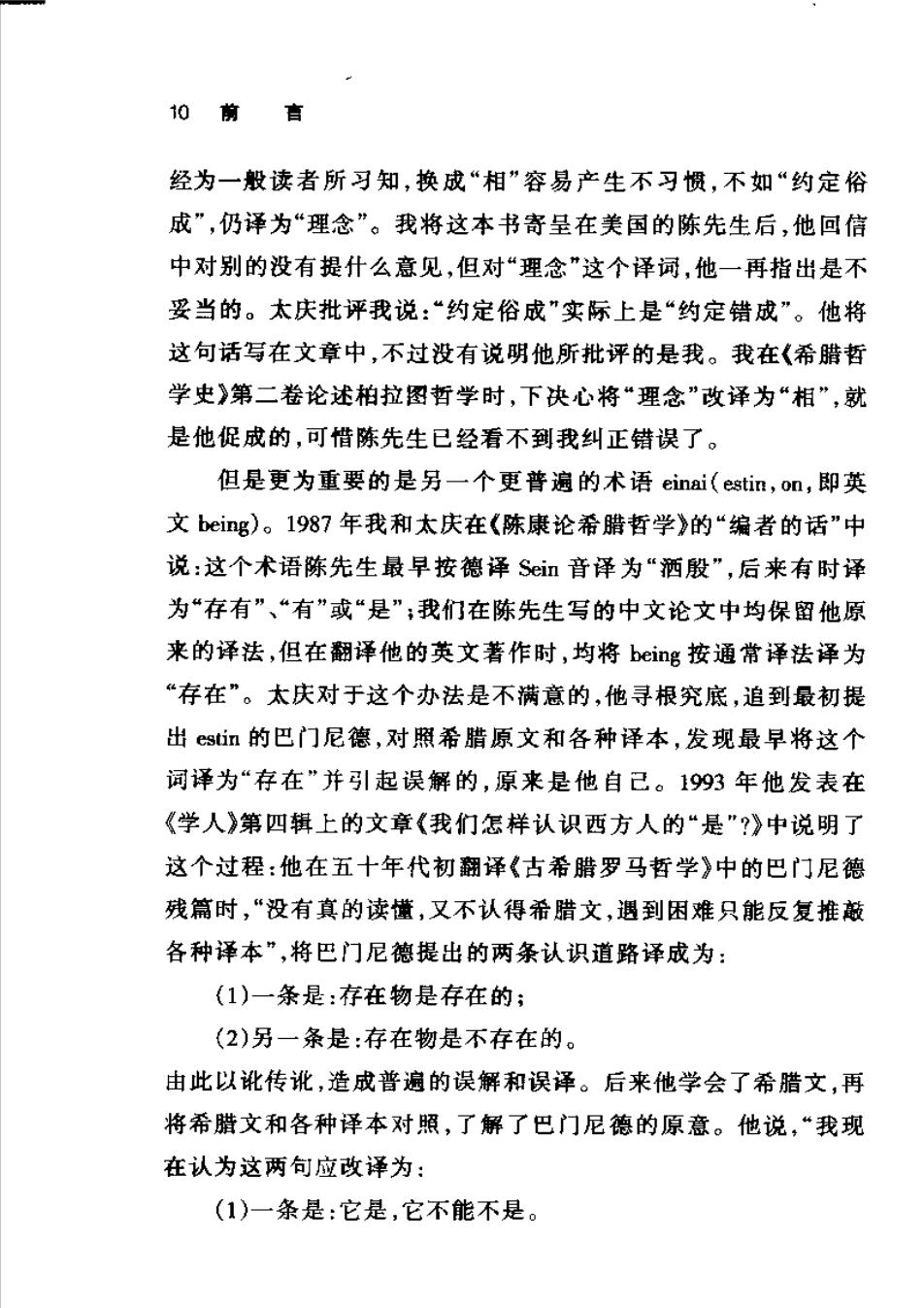
10 音 经为一般读者所习知,换成“相”容易产生不习惯,不如“约定俗 成”,仍译为“理念”。我将这本书寄呈在美国的陈先生后,他回信 中对别的没有提什么意见,但对“理念”这个译词,他一再指出是不 妥当的。太庆批评我说:“约定俗成”实际上是“约定错成”。他将 这句话写在文章中,不过没有说明他所批评的是我。我在《希腊哲 学史》第二卷论述柏拉图哲学时,下决心将“理念”改译为“相”,就 是他促成的,可惜陈先生已经看不到我纠正错误了。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另一个更普遍的术语einai(estin,on,即英 文being)。1987年我和太庆在《陈康论希腊哲学》的“编者的话”中 说:这个术语陈先生最早按德译Sin音译为“洒殷”,后来有时译 为“存有”、“有”或“是”:我们在陈先生写的中文论文中均保留他原 来的译法,但在翻译他的英文著作时,均将being按通常译法译为 “存在”。太庆对于这个办法是不满意的,他寻根究底,追到最初提 出esi的巴门尼德,对照希腊原文和各种译本,发现最早将这个 词译为“存在”并引起误解的,原来是他自己。993年他发表在 《学人》第四辑上的文章《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中说明了 这个过程:他在五十年代初翻译《古希腊罗马哲学》中的巴门尼德 残篇时,“没有真的读懂,又不认得希腊文,遇到困难只能反复推蔽 各种译本”,将巴门尼德提出的两条认识道路译成为: (1)一条是:存在物是存在的; (2)另一条是:存在物是不存在的。 由此以讹传讹,造成普遍的误解和误译。后来他学会了希腊文,再 将希腊文和各种译本对照,了解了巴门尼德的原意。他说,“我现 在认为这两句应改译为: (1)一条是:它是,它不能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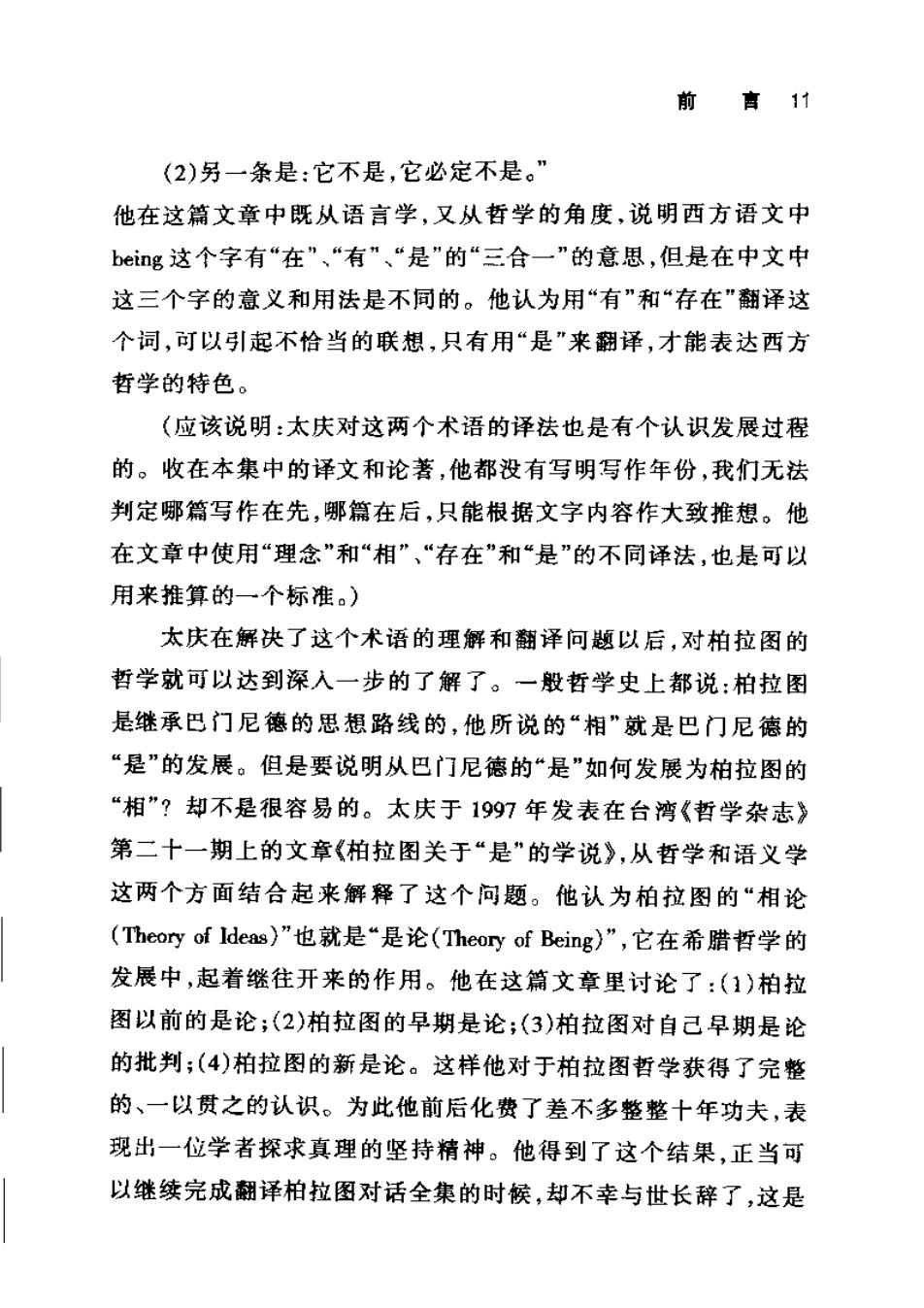
前 宫11 (2)另一条是:它不是,它必定不是。” 他在这篇文章中既从语言学,又从哲学的角度,说明西方语文中 being这个字有“在”、“有”、“是”的“三合一”的意思,但是在中文中 这三个字的意义和用法是不同的。他认为用“有”和“存在”翻译这 个词,可以引起不恰当的联想,只有用“是”来翻译,才能表达西方 哲学的特色。 (应该说明:太庆对这两个术语的译法也是有个认识发展过程 的。收在本集中的译文和论著,他都没有写明写作年份,我们无法 判定哪篇写作在先,哪篇在后,只能根据文字内容作大致推想。他 在文章中使用“理念”和“相”、“存在”和“是”的不同译法,也是可以 用来推算的一个标准。) 太庆在解决了这个术语的理解和翻译问题以后,对柏拉图的 哲学就可以达到深入一步的了解了。一般哲学史上都说:柏拉图 是继承巴门尼德的思想路线的,他所说的“相”就是巴门尼德的 “是”的发展。但是要说明从巴门尼德的“是”如何发展为柏拉图的 “相”?却不是很容易的。太庆于1997年发表在台湾《哲学杂志》 第二十一期上的文章《柏拉图关于“是”的学说》,从哲学和语义学 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柏拉图的“相论 (Theory of Ideas)”也就是“是论(Theory of Being)”,它在希腊哲学的 发展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他在这篇文章里讨论了:(1)柏拉 图以前的是论;(2)柏拉图的早期是论;(3)柏拉图对自己早期是论 的批判;(4)柏拉图的新是论。这样他对于柏拉图哲学获得了完整 的、一以贯之的认识。为此他前后化费了差不多整整十年功夫,表 现出一位学者探求真理的坚持精神。他得到了这个结果,正当可 以继续完成翻译柏拉图对话全集的时候,却不幸与世长辞了,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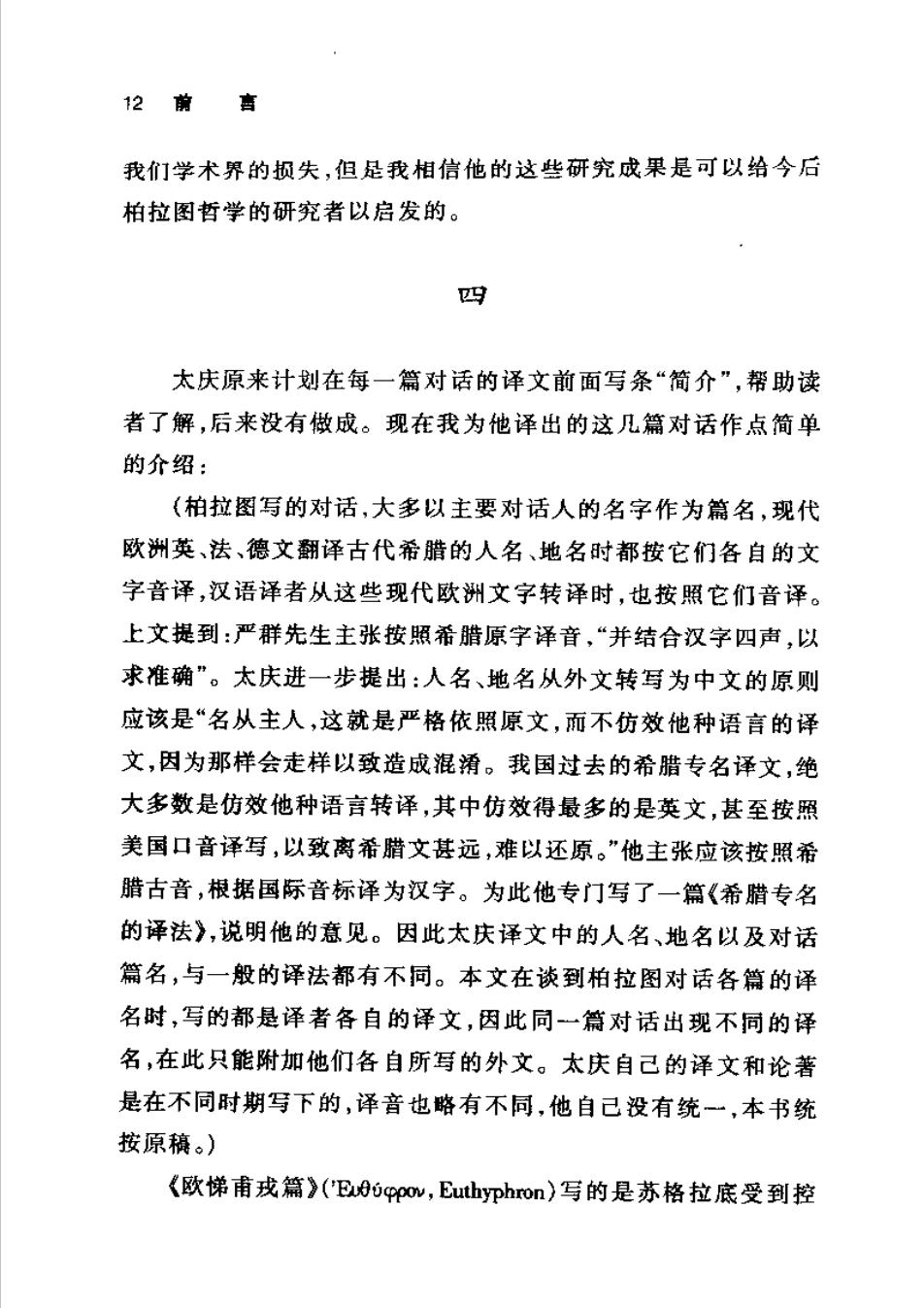
12前 喜 我们学术界的损失,但是我相信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是可以给今后 柏拉图哲学的研究者以启发的。 9 太庆原来计划在每一篇对话的译文前面写条“简介”,帮助读 者了解,后来没有做成。现在我为他译出的这几篇对话作点简单 的介绍: (柏拉图写的对话,大多以主要对话人的名字作为篇名,现代 欧洲英、法、德文翻译古代希腊的人名、地名时都按它们各自的文 字音译,汉语译者从这些现代欧洲文字转泽时,也按照它们音译。 上文提到:严群先生主张按照希腊原字译音,“并结合汉字四声,以 求准确”。太庆进一步提出:人名、地名从外文转写为中文的原则 应该是“名从主人,这就是严格依照原文,而不仿效他种语言的译 文,因为那样会走样以致造成混滑。我国过去的希腊专名译文,绝 大多数是仿效他种语言转译,其中仿效得最多的是英文,甚至按照 美国口音译写,以致离希腊文甚远,难以还原。”他主张应该按照希 腊古音,根据国际音标译为汉字。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希腊专名 的译法》,说明他的意见。因此太庆译文中的人名、地名以及对话 篇名,与一般的译法都有不同。本文在谈到柏拉图对话各篇的译 名时,写的都是译者各自的译文,因此同一篇对话出现不同的译 名,在此只能附加他们各自所写的外文。太庆自己的译文和论著 是在不同时期写下的,译音也略有不同,他自己没有统一,本书统 按原稿。) 《欧悌甫戎篇》(Eu0oopov,Euthyphron)写的是苏格拉底受到控

前 13 告,说他不信神;在他出庭受审之前,和热心宗教的欧悌甫戎讨论 什么是“虔诚(hosiotes,英译piety或holiness)”的问题。欧悌甫戎提 出几种县体的虔诚的例子,都被苏格拉底驳倒,最后以没有得出结 论告终。这是一篇“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苏格拉底的申辩篇》 (Aro以oYia,Apologia)写的是苏格拉底在审判庭.上侃侃而谈,为自己 辩护。这是一篇著名的文辞并茂、为世人传诵的文字。《格黎东 篇》(Kpirwv,Criton)写的是苏格拉底被投入监狱后,他的挚友、雅典 巨富格黎东去狱中,再三说服苏格拉底越狱逃生,苏格拉底认为任 何公民都不能违背法律,坚决拒绝。这三篇对话描述的都是苏格 拉底最后一段生活的情况,大体符合历史实际,可能是在苏格拉底 死后不久,柏拉图为了纪念他这位老师而写的。学者们认为是柏 拉图最早写成的对话,它们被列人柏拉图对话的最前列。上列许 多中文译本都译了这三篇对话,读者如果对照阅读,便可以看到译 文的不同和它们的发展变化。 柏拉图早期写的对话被称为“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苏格拉底 和青年人讨论伦理问题,问“什么是某某品德?”他要得到的回答是 这种品德的普遍定义,但是对话者都以这种品德的特殊事例来回 答他;虽经苏格拉底一再诱导,仍以不能得到普遍定义而告终。这 种情况大体符合苏格拉底当时与入论辩的实际情况,所以学者们 认为这些对话可以代表苏格拉底本人的思想。《卡尔弥德篇》 (Xcpu6s,Charmides)、《拉刻篇》(Aaxns,Laches)和《吕锡篇》(A)- s,Lyi8)是同一组的三篇对话,就是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的典 范。这些对话可以说是为柏拉图的相论作准备的,因为对于“什么 是某某?”的问题,能够并应该作出的回答也就是这个品德的普遍 定义,即这个品德的“相”,也就是它的“是”。《卡尔弥德篇》讨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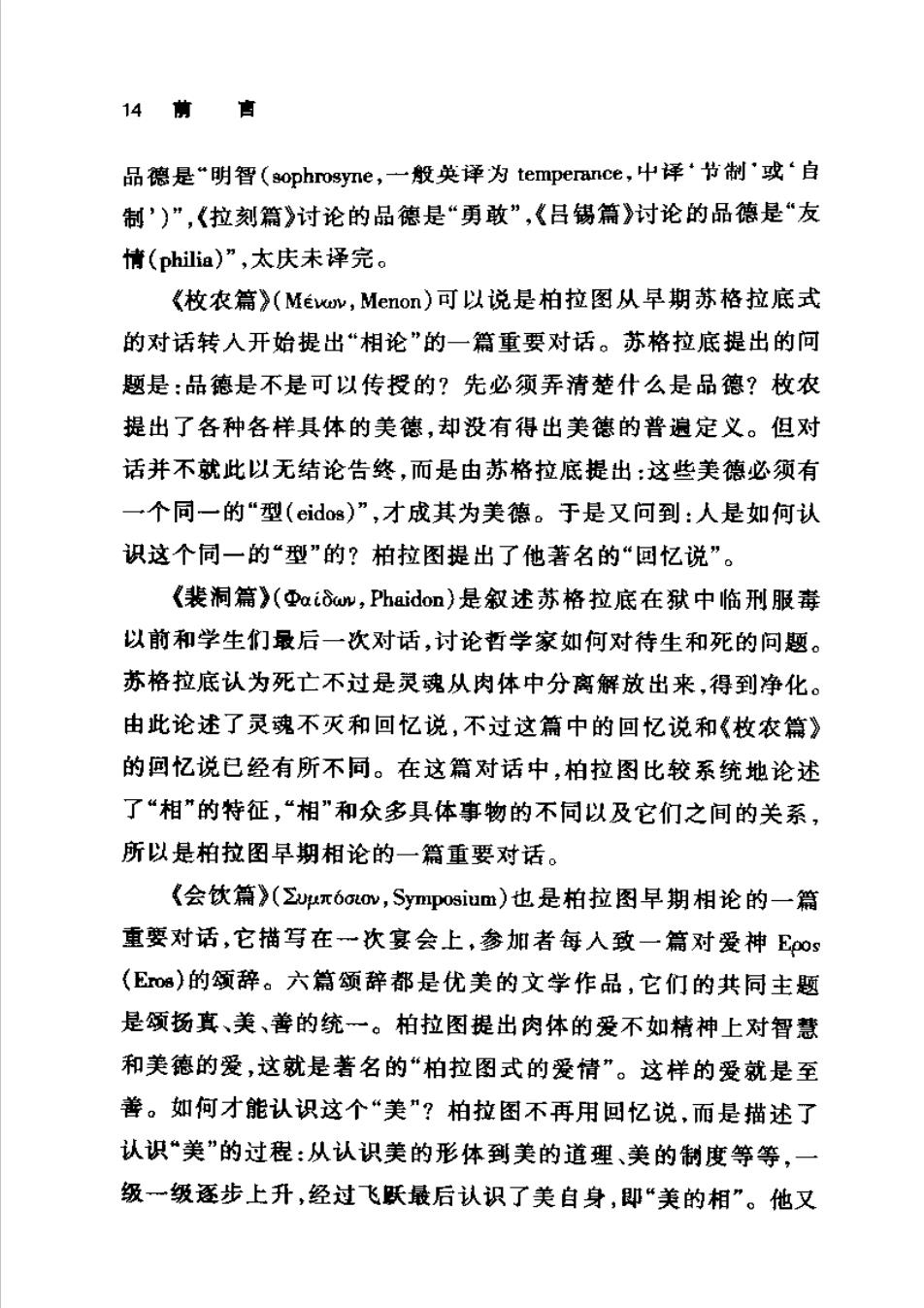
14 前 曹 品德是“明智(sophrosyne,一般英译为temperance,屮译+节制'或‘自 制’)”,《拉刻篇》讨论的品德是“勇敢”,《吕锡篇》讨论的品德是“友 情(philia)”,太庆未译完。 《枚农篇》(Mewv,Menon)可以说是柏拉图从早期苏格拉底式 的对话转入开始提出“相论”的一篇重要对话。苏格拉底提出的问 题是:品德是不是可以传授的?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品德?枚农 提出了各种各样具体的美德,却没有得出美德的普遍定义。但对 话并不就此以无结论告终,而是由苏格拉底提出:这些美德必须有 一个同一的“型(idos)”,才成其为美德。于是又问到:人是如何认 识这个同一的“型”的?柏拉图提出了他著名的“回忆说”。 《裴祠篇》(pai8ww,Phaidon)是叙述苏格拉底在狱中临刑服毒 以前和学生们最后一次对话,讨论哲学家如何对待生和死的问题。 苏格拉底认为死亡不过是灵魂从肉体中分离解放出来,得到净化。 由此论述了灵魂不灭和回忆说,不过这篇中的回忆说和《枚农篇》 的回忆说已经有所不同。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比较系统地论述 了“相”的特征,“相”和众多具体事物的不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是柏拉图早期相论的一篇重要对话。 《会饮篇》(2牡π6oov,Symposium)也是柏拉图早期相论的一篇 重要对话,它描写在一次宴会上,参加者每人致一篇对爱神Eos (E)的颂辞。六篇颂辞都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它们的共同主题 是颂扬真、美、善的统一。柏拉图提出肉体的爱不如精神上对智慧 和美德的爱,这就是著名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这样的爱就是至 善。如何才能认识这个“美”?柏拉图不再用回忆说,而是描述了 认识“美”的过程:从认识美的形体到美的道理、美的制度等等,一 级一级逐步上升,经过飞跃最后认识了美自身,即“美的相”。他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