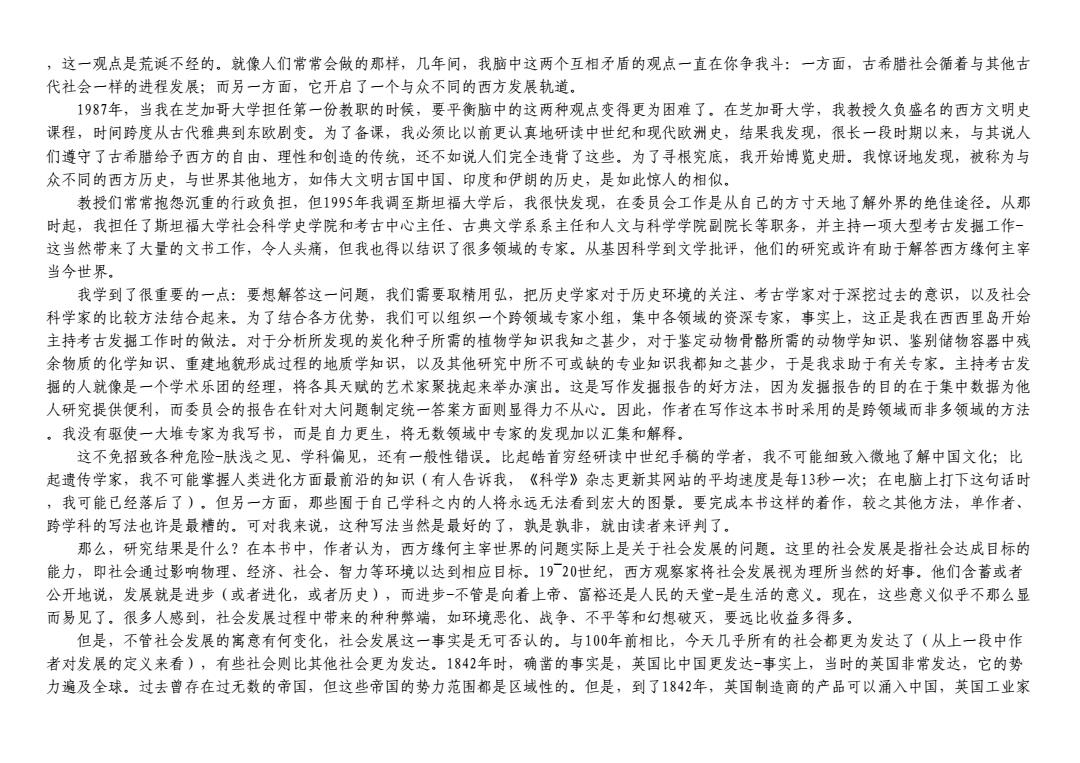
,这一观点是荒诞不经的。就像人们常常会做的那样,几年间,我脑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观点一直在你争我斗:一方面,古希腊社会循着与其他古 代社会一样的进程发展;而另一方面,它开启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西方发展轨道。 1987年,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第一份教职的时侯,要平衡脑中的这两种观点变得更为困难了。在芝加哥大学,我教授久负盛名的西方文明史 课程,时间跨度从古代雅典到东欧剧变。为了备课,我必须比以前更认真地研读中世纪和现代欧洲史,结果我发现,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与其说人 们遵守了古希腊给予西方的自由、理性和创造的传统,还不如说人们完全违背了这些。为了寻根究底,我开始博览史册。我惊讶地发现,被称为与 众不同的西方历史,与世界其他地方,如伟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和伊朗的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教授们常常抱怨沉重的行政负担,但1995年我调至斯坦福大学后,我很快发现,在委员会工作是从自己的方寸天地了解外界的绝佳途径。从那 时起,我担任了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史学院和考古中心主任、古典文学系系主任和人文与科学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并主持一项大型考古发掘工作- 这当然带来了大量的文书工作,令人头痛,但我也得以结识了很多领域的专家。从基因科学到文学批评,他们的研究或许有助于解答西方缘何主宰 当今世界。 我学到了很重要的一点:要想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取精用弘,把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环境的关注、考古学家对于深挖过去的意识,以及社会 科学家的比较方法结合起来。为了结合各方优势,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跨领域专家小组,集中各领域的资深专家,事实上,这正是我在西西里岛开始 主持考古发掘工作时的做法。对于分析所发现的炭化种子所需的植物学知识我知之甚少,对于鉴定动物骨骼所需的动物学知识、鉴别储物容器中残 余物质的化学知识、重建地貌形成过程的地质学知识,以及其他研究中所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我都知之甚少,于是我求助于有关专家。主持考古发 掘的人就像是一个学术乐团的经理,将各具天赋的艺术家聚拢起来举办演出。这是写作发掘报告的好方法,因为发掘报告的目的在于集中数据为他 人研究提供便利,而委员会的报告在针对大问题制定统一答案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作者在写作这本书时采用的是跨领域而非多领域的方法 。我没有驱使一大堆专家为我写书,而是自力更生,将无数领域中专家的发现加以汇集和解释。 这不免招致各种危险-肤浅之见、学科偏见,还有一般性错误。比起皓首穷经研读中世纪手稿的学者,我不可能细致入微地了解中国文化;比 起遗传学家,我不可能掌握人类进化方面最前沿的知识(有人告诉我,《科学》杂志更新其网站的平均速度是每13秒一次;在电脑上打下这句话时 ,我可能已经落后了)。但另一方面,那些囿于自己学科之内的人将永远无法看到宏大的图景。要完成本书这样的着作,较之其他方法,单作者、 跨学科的写法也许是最槽的。可对我来说,这种写法当然是最好的了,孰是孰非,就由读者来评判了。 那么,研究结果是什么?在本书中,作者认为,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社会发展的问题。这里的社会发展是指社会达成目标的 能力,即社会通过影响物理、经济、社会、智力等环境以达到相应目标。19ˉ20世纪,西方观察家将社会发展视为理所当然的好事。他们含蓄或者 公开地说,发展就是进步(或者进化,或者历史),而进步-不管是向着上帝、富裕还是人民的天堂-是生活的意义。现在,这些意义似乎不那么显 而易见了。很多人感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种种弊端,如环境恶化、战争、不平等和幻想破灭,要远比收益多得多。 但是,不管社会发展的寓意有何变化,社会发展这一事实是无可否认的。与100年前相比,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更为发达了(从上一段中作 者对发展的定义来看),有些社会则比其他社会更为发达。1842年时,确凿的事实是,英国比中国更发达-事实上,当时的英国非常发达,它的势 力遍及全球。过去曾存在过无数的帝国,但这些帝国的势力范围都是区域性的。但是,到了1842年,英国制造商的产品可以涌入中国,英国工业家
,这一观点是荒诞不经的。就像人们常常会做的那样,几年间,我脑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观点一直在你争我斗:一方面,古希腊社会循着与其他古 代社会一样的进程发展;而另一方面,它开启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西方发展轨道。 1987年,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第一份教职的时候,要平衡脑中的这两种观点变得更为困难了。在芝加哥大学,我教授久负盛名的西方文明史 课程,时间跨度从古代雅典到东欧剧变。为了备课,我必须比以前更认真地研读中世纪和现代欧洲史,结果我发现,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与其说人 们遵守了古希腊给予西方的自由、理性和创造的传统,还不如说人们完全违背了这些。为了寻根究底,我开始博览史册。我惊讶地发现,被称为与 众不同的西方历史,与世界其他地方,如伟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和伊朗的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教授们常常抱怨沉重的行政负担,但1995年我调至斯坦福大学后,我很快发现,在委员会工作是从自己的方寸天地了解外界的绝佳途径。从那 时起,我担任了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史学院和考古中心主任、古典文学系系主任和人文与科学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并主持一项大型考古发掘工作- 这当然带来了大量的文书工作,令人头痛,但我也得以结识了很多领域的专家。从基因科学到文学批评,他们的研究或许有助于解答西方缘何主宰 当今世界。 我学到了很重要的一点:要想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取精用弘,把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环境的关注、考古学家对于深挖过去的意识,以及社会 科学家的比较方法结合起来。为了结合各方优势,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跨领域专家小组,集中各领域的资深专家,事实上,这正是我在西西里岛开始 主持考古发掘工作时的做法。对于分析所发现的炭化种子所需的植物学知识我知之甚少,对于鉴定动物骨骼所需的动物学知识、鉴别储物容器中残 余物质的化学知识、重建地貌形成过程的地质学知识,以及其他研究中所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我都知之甚少,于是我求助于有关专家。主持考古发 掘的人就像是一个学术乐团的经理,将各具天赋的艺术家聚拢起来举办演出。这是写作发掘报告的好方法,因为发掘报告的目的在于集中数据为他 人研究提供便利,而委员会的报告在针对大问题制定统一答案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作者在写作这本书时采用的是跨领域而非多领域的方法 。我没有驱使一大堆专家为我写书,而是自力更生,将无数领域中专家的发现加以汇集和解释。 这不免招致各种危险-肤浅之见、学科偏见,还有一般性错误。比起皓首穷经研读中世纪手稿的学者,我不可能细致入微地了解中国文化;比 起遗传学家,我不可能掌握人类进化方面最前沿的知识(有人告诉我,《科学》杂志更新其网站的平均速度是每13秒一次;在电脑上打下这句话时 ,我可能已经落后了)。但另一方面,那些囿于自己学科之内的人将永远无法看到宏大的图景。要完成本书这样的着作,较之其他方法,单作者、 跨学科的写法也许是最糟的。可对我来说,这种写法当然是最好的了,孰是孰非,就由读者来评判了。 那么,研究结果是什么?在本书中,作者认为,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社会发展的问题。这里的社会发展是指社会达成目标的 能力,即社会通过影响物理、经济、社会、智力等环境以达到相应目标。19~20世纪,西方观察家将社会发展视为理所当然的好事。他们含蓄或者 公开地说,发展就是进步(或者进化,或者历史),而进步-不管是向着上帝、富裕还是人民的天堂-是生活的意义。现在,这些意义似乎不那么显 而易见了。很多人感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种种弊端,如环境恶化、战争、不平等和幻想破灭,要远比收益多得多。 但是,不管社会发展的寓意有何变化,社会发展这一事实是无可否认的。与100年前相比,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更为发达了(从上一段中作 者对发展的定义来看),有些社会则比其他社会更为发达。1842年时,确凿的事实是,英国比中国更发达-事实上,当时的英国非常发达,它的势 力遍及全球。过去曾存在过无数的帝国,但这些帝国的势力范围都是区域性的。但是,到了1842年,英国制造商的产品可以涌入中国,英国工业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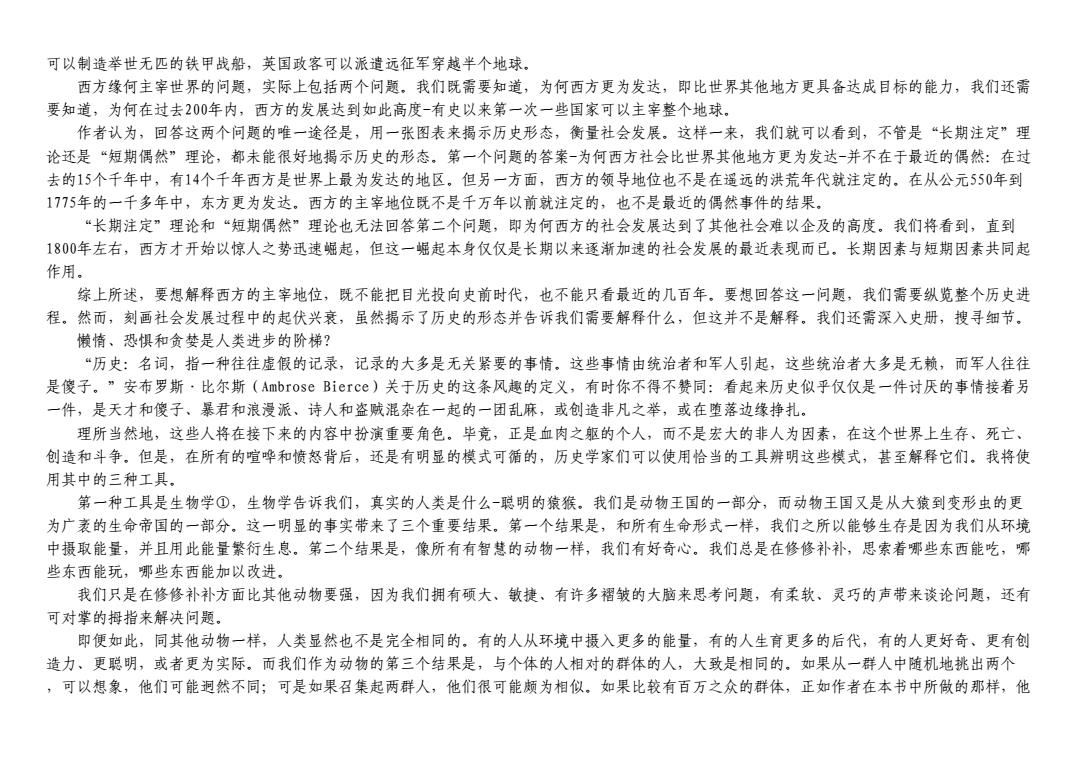
可以制造举世无匹的铁甲战船,英国政客可以派遣远征军穿越半个地球。 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我们既需要知道,为何西方更为发达,即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具备达成目标的能力,我们还需 要知道,为何在过去200年内,西方的发展达到如此高度-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些国家可以主宰整个地球。 作者认为,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用一张图表来揭示历史形态,衡量社会发展。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是“长期注定”理 论还是“短期偶然”理论,都未能很好地揭示历史的形态。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何西方社会比世界其他地方更为发达-并不在于最近的偶然:在过 去的15个千年中,有14个千年西方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地区。但另一方面,西方的领导地位也不是在遥远的洪荒年代就注定的。在从公元550年到 1775年的一千多年中,东方更为发达。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是千万年以前就注定的,也不是最近的偶然事件的结果。 “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也无法回答第二个问题,即为何西方的社会发展达到了其他社会难以企及的高度。我们将看到,直到 1800年左右,西方才开始以惊人之势迅速崛起,但这一崛起本身仅仅是长期以来逐渐加速的社会发展的最近表现而已。长期因素与短期因素共同起 作用。 综上所述,要想解释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能把目光投向史前时代,也不能只看最近的几百年。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纵览整个历史进 程。然而,刻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起伏兴衰,虽然揭示了历史的形态并告诉我们需要解释什么,但这并不是解释。我们还需深入史册,搜寻细节。 懒惰、恐惧和贪婪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历史:名词,指一种往往虚假的记录,记录的大多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些事情由统治者和军人引起,这些统治者大多是无赖,而军人往往 是傻子。”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关于历史的这条风趣的定义,有时你不得不赞同:看起来历史似乎仅仅是一件讨厌的事情接着另 一件,是天才和傻子、暴君和浪漫派、诗人和盗贼混杂在一起的一团乱麻,或创造非凡之举,或在堕落边缘挣扎。 理所当然地,这些人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扮演重要角色。毕竟,正是血肉之躯的个人,而不是宏大的非人为因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死亡、 创造和斗争。但是,在所有的喧哗和愤怒背后,还是有明显的模式可循的,历史学家们可以使用恰当的工具辨明这些模式,甚至解释它们。我将使 用其中的三种工具。 第一种工具是生物学①,生物学告诉我们,真实的人类是什么-聪明的猿猴。我们是动物王国的一部分,而动物王国又是从大猿到变形虫的更 为广袤的生命帝国的一部分。这一明显的事实带来了三个重要结果。第一个结果是,和所有生命形式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我们从环境 中摄取能量,并且用此能量繁衍生息。第二个结果是,像所有有智慧的动物一样,我们有好奇心。我们总是在修修补补,思索着哪些东西能吃,哪 些东西能玩,哪些东西能加以改进。 我们只是在修修补补方面比其他动物要强,因为我们拥有硕大、敏捷、有许多褶皱的大脑来思考问题,有柔软、灵巧的声带来谈论问题,还有 可对掌的拇指来解决问题。 即便如此,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显然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有的人从环境中摄入更多的能量,有的人生育更多的后代,有的人更好奇、更有创 造力、更聪明,或者更为实际。而我们作为动物的第三个结果是,与个体的人相对的群体的人,大致是相同的。如果从一群人中随机地挑出两个 ,可以想象,他们可能迥然不同;可是如果召集起两群人,他们很可能颇为相似。如果比较有百万之众的群体,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他
可以制造举世无匹的铁甲战船,英国政客可以派遣远征军穿越半个地球。 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我们既需要知道,为何西方更为发达,即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具备达成目标的能力,我们还需 要知道,为何在过去200年内,西方的发展达到如此高度-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些国家可以主宰整个地球。 作者认为,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用一张图表来揭示历史形态,衡量社会发展。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是“长期注定”理 论还是“短期偶然”理论,都未能很好地揭示历史的形态。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何西方社会比世界其他地方更为发达-并不在于最近的偶然:在过 去的15个千年中,有14个千年西方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地区。但另一方面,西方的领导地位也不是在遥远的洪荒年代就注定的。在从公元550年到 1775年的一千多年中,东方更为发达。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是千万年以前就注定的,也不是最近的偶然事件的结果。 “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也无法回答第二个问题,即为何西方的社会发展达到了其他社会难以企及的高度。我们将看到,直到 1800年左右,西方才开始以惊人之势迅速崛起,但这一崛起本身仅仅是长期以来逐渐加速的社会发展的最近表现而已。长期因素与短期因素共同起 作用。 综上所述,要想解释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能把目光投向史前时代,也不能只看最近的几百年。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纵览整个历史进 程。然而,刻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起伏兴衰,虽然揭示了历史的形态并告诉我们需要解释什么,但这并不是解释。我们还需深入史册,搜寻细节。 懒惰、恐惧和贪婪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历史:名词,指一种往往虚假的记录,记录的大多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些事情由统治者和军人引起,这些统治者大多是无赖,而军人往往 是傻子。”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关于历史的这条风趣的定义,有时你不得不赞同:看起来历史似乎仅仅是一件讨厌的事情接着另 一件,是天才和傻子、暴君和浪漫派、诗人和盗贼混杂在一起的一团乱麻,或创造非凡之举,或在堕落边缘挣扎。 理所当然地,这些人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扮演重要角色。毕竟,正是血肉之躯的个人,而不是宏大的非人为因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死亡、 创造和斗争。但是,在所有的喧哗和愤怒背后,还是有明显的模式可循的,历史学家们可以使用恰当的工具辨明这些模式,甚至解释它们。我将使 用其中的三种工具。 第一种工具是生物学①,生物学告诉我们,真实的人类是什么-聪明的猿猴。我们是动物王国的一部分,而动物王国又是从大猿到变形虫的更 为广袤的生命帝国的一部分。这一明显的事实带来了三个重要结果。第一个结果是,和所有生命形式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我们从环境 中摄取能量,并且用此能量繁衍生息。第二个结果是,像所有有智慧的动物一样,我们有好奇心。我们总是在修修补补,思索着哪些东西能吃,哪 些东西能玩,哪些东西能加以改进。 我们只是在修修补补方面比其他动物要强,因为我们拥有硕大、敏捷、有许多褶皱的大脑来思考问题,有柔软、灵巧的声带来谈论问题,还有 可对掌的拇指来解决问题。 即便如此,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显然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有的人从环境中摄入更多的能量,有的人生育更多的后代,有的人更好奇、更有创 造力、更聪明,或者更为实际。而我们作为动物的第三个结果是,与个体的人相对的群体的人,大致是相同的。如果从一群人中随机地挑出两个 ,可以想象,他们可能迥然不同;可是如果召集起两群人,他们很可能颇为相似。如果比较有百万之众的群体,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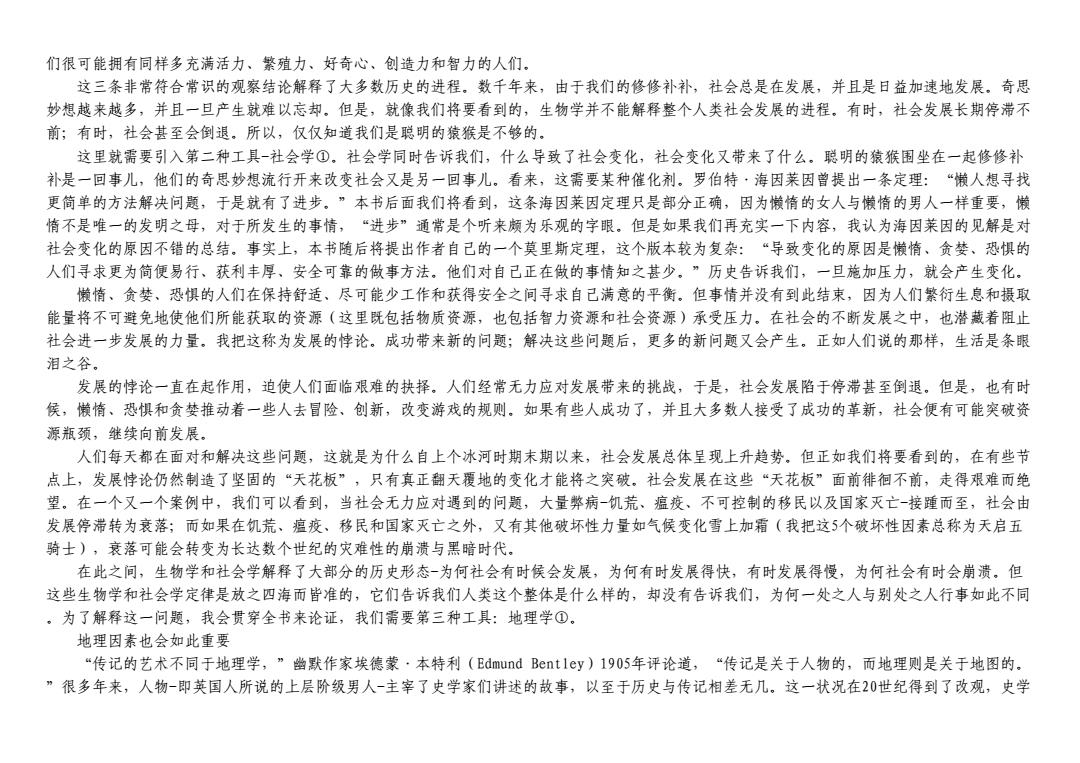
们很可能拥有同样多充满活力、繁殖力、好奇心、创造力和智力的人们。 这三条非常符合常识的观察结论解释了大多数历史的进程。数千年来,由于我们的修修补补,社会总是在发展,并且是日益加速地发展。奇思 妙想越来越多,并且一旦产生就难以忘却。但是,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生物学并不能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有时,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 前;有时,社会甚至会倒退。所以,仅仅知道我们是聪明的猿猴是不够的。 这里就需要引入第二种工具-社会学①。社会学同时告诉我们,什么导致了社会变化,社会变化又带来了什么。聪明的猿猴围坐在一起修修补 补是一回事儿,他们的奇思妙想流行开来改变社会又是另一回事儿。看来,这需要某种催化剂。罗伯特·海因菜因曾提出一条定理:“懒人想寻找 更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于是就有了进步。”本书后面我们将看到,这条海因莱因定理只是部分正确,因为懒惰的女人与懒惰的男人一样重要,懒 惰不是唯一的发明之母,对于所发生的事情,“进步”通常是个听来颇为乐观的字眼。但是如果我们再充实一下内容,我认为海因莱因的见解是对 社会变化的原因不错的总结。事实上,本书随后将提出作者自己的一个莫里斯定理,这个版本较为复杂:“导致变化的原因是懒惰、贪婪、恐惧的 人们寻求更为简便易行、获利丰厚、安全可靠的做事方法。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知之甚少。”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施加压力,就会产生变化。 懒情、贪婪、恐惧的人们在保持舒适、尽可能少工作和获得安全之间寻求自己满意的平衡。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人们繁衍生息和摄取 能量将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所能获取的资源(这里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承受压力。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之中,也潜藏着阻止 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力量。我把这称为发展的悖论。成功带来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后,更多的新问题又会产生。正如人们说的那样,生活是条眼 泪之谷。 发展的悖论一直在起作用,迫使人们面临艰难的抉择。人们经常无力应对发展带来的挑战,于是,社会发展陷于停带甚至倒退。但是,也有时 候,懒惰、恐惧和贪婪推动着一些人去冒险、创新,改变游戏的规则。如果有些人成功了,并且大多数人接受了成功的革新,社会便有可能突破资 源瓶颈,继续向前发展。 人们每天都在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自上个冰河时期未期以来,社会发展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有些节 点上,发展悖论仍然制造了坚固的“天花板”,只有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才能将之突破。社会发展在这些“天花板”面前徘徊不前,走得艰难而绝 望。在一个又一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社会无力应对遇到的问题,大量弊病-饥荒、瘟疫、不可控制的移民以及国家灭亡-接踵而至,社会由 发展停带转为衰落;而如果在饥荒、瘟疫、移民和国家灭亡之外,又有其他破坏性力量如气候变化雪上加霜(我把这5个破坏性因素总称为天启五 骑士),衰落可能会转变为长达数个世纪的灾难性的崩溃与黑暗时代。 在此之间,生物学和社会学解释了大部分的历史形态-为何社会有时候会发展,为何有时发展得快,有时发展得慢,为何社会有时会崩溃。但 这些生物学和社会学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们告诉我们人类这个整体是什么样的,却没有告诉我们,为何一处之人与别处之人行事如此不同 。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我会贯穿全书来论证,我们需要第三种工具:地理学①。 地理因素也会如此重要 “传记的艺术不同于地理学,”幽默作家埃德蒙·本特利(Edmund Bentley)1905年评论道,“传记是关于人物的,而地理则是关于地图的。 ”很多年来,人物-即英国人所说的上层阶级男人-主宰了史学家们讲述的故事,以至于历史与传记相差无几。这一状况在20世纪得到了改观,史学
们很可能拥有同样多充满活力、繁殖力、好奇心、创造力和智力的人们。 这三条非常符合常识的观察结论解释了大多数历史的进程。数千年来,由于我们的修修补补,社会总是在发展,并且是日益加速地发展。奇思 妙想越来越多,并且一旦产生就难以忘却。但是,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生物学并不能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有时,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 前;有时,社会甚至会倒退。所以,仅仅知道我们是聪明的猿猴是不够的。 这里就需要引入第二种工具-社会学①。社会学同时告诉我们,什么导致了社会变化,社会变化又带来了什么。聪明的猿猴围坐在一起修修补 补是一回事儿,他们的奇思妙想流行开来改变社会又是另一回事儿。看来,这需要某种催化剂。罗伯特·海因莱因曾提出一条定理:“懒人想寻找 更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于是就有了进步。”本书后面我们将看到,这条海因莱因定理只是部分正确,因为懒惰的女人与懒惰的男人一样重要,懒 惰不是唯一的发明之母,对于所发生的事情,“进步”通常是个听来颇为乐观的字眼。但是如果我们再充实一下内容,我认为海因莱因的见解是对 社会变化的原因不错的总结。事实上,本书随后将提出作者自己的一个莫里斯定理,这个版本较为复杂:“导致变化的原因是懒惰、贪婪、恐惧的 人们寻求更为简便易行、获利丰厚、安全可靠的做事方法。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知之甚少。”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施加压力,就会产生变化。 懒惰、贪婪、恐惧的人们在保持舒适、尽可能少工作和获得安全之间寻求自己满意的平衡。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人们繁衍生息和摄取 能量将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所能获取的资源(这里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承受压力。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之中,也潜藏着阻止 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力量。我把这称为发展的悖论。成功带来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后,更多的新问题又会产生。正如人们说的那样,生活是条眼 泪之谷。 发展的悖论一直在起作用,迫使人们面临艰难的抉择。人们经常无力应对发展带来的挑战,于是,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但是,也有时 候,懒惰、恐惧和贪婪推动着一些人去冒险、创新,改变游戏的规则。如果有些人成功了,并且大多数人接受了成功的革新,社会便有可能突破资 源瓶颈,继续向前发展。 人们每天都在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自上个冰河时期末期以来,社会发展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有些节 点上,发展悖论仍然制造了坚固的“天花板”,只有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才能将之突破。社会发展在这些“天花板”面前徘徊不前,走得艰难而绝 望。在一个又一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社会无力应对遇到的问题,大量弊病-饥荒、瘟疫、不可控制的移民以及国家灭亡-接踵而至,社会由 发展停滞转为衰落;而如果在饥荒、瘟疫、移民和国家灭亡之外,又有其他破坏性力量如气候变化雪上加霜(我把这5个破坏性因素总称为天启五 骑士),衰落可能会转变为长达数个世纪的灾难性的崩溃与黑暗时代。 在此之间,生物学和社会学解释了大部分的历史形态-为何社会有时候会发展,为何有时发展得快,有时发展得慢,为何社会有时会崩溃。但 这些生物学和社会学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们告诉我们人类这个整体是什么样的,却没有告诉我们,为何一处之人与别处之人行事如此不同 。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我会贯穿全书来论证,我们需要第三种工具:地理学①。 地理因素也会如此重要 “传记的艺术不同于地理学,”幽默作家埃德蒙·本特利(Edmund Bentley)1905年评论道,“传记是关于人物的,而地理则是关于地图的。 ”很多年来,人物-即英国人所说的上层阶级男人-主宰了史学家们讲述的故事,以至于历史与传记相差无几。这一状况在20世纪得到了改观,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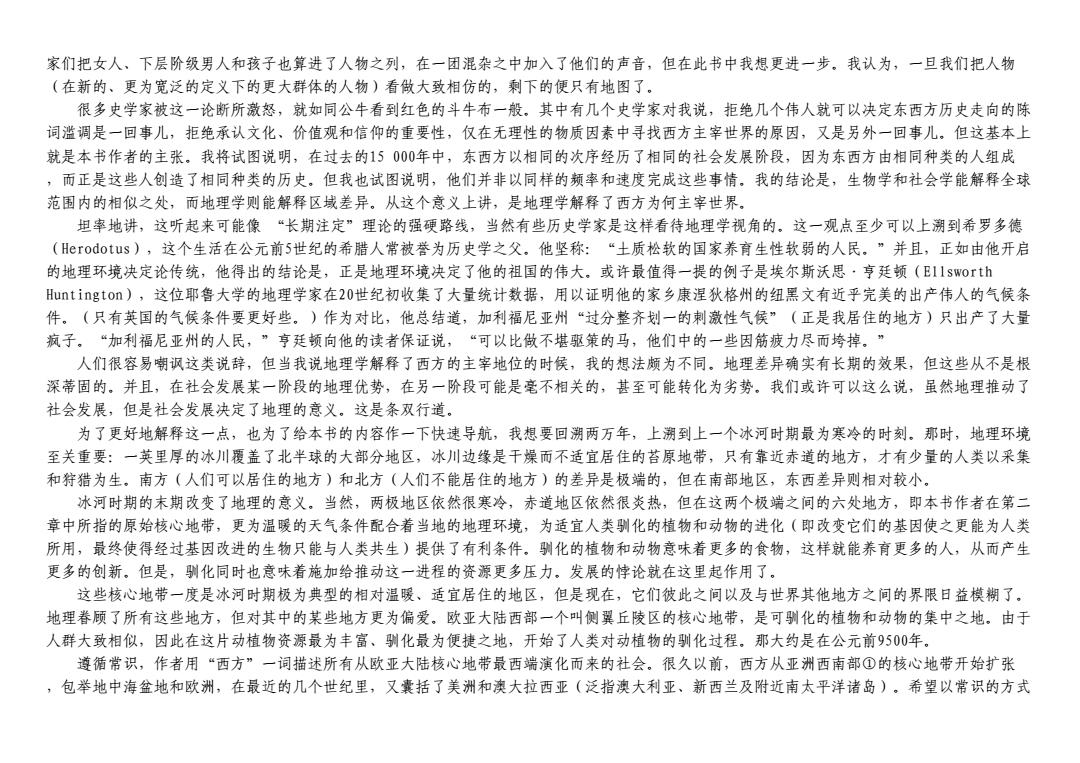
家们把女人、下层阶级男人和孩子也算进了人物之列,在一团混杂之中加入了他们的声音,但在此书中我想更进一步。我认为,一旦我们把人物 (在新的、更为宽泛的定义下的更大群体的人物)看做大致相仿的,剩下的便只有地图了。 很多史学家被这一论断所激怒,就如同公牛看到红色的斗牛布一般。其中有几个史学家对我说,拒绝几个伟人就可以决定东西方历史走向的陈 词滥调是一回事儿,拒绝承认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的重要性,仅在无理性的物质因素中寻找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但这基本上 就是本书作者的主张。我将试图说明,在过去的15000年中,东西方以相同的次序经历了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因为东西方由相同种类的人组成 ,而正是这些人创造了相同种类的历史。但我也试图说明,他们并非以同样的频率和速度完成这些事情。我的结论是,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 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地理学解释了西方为何主宰世界。 坦率地讲,这听起来可能像“长期注定”理论的强硬路线,当然有些历史学家是这样看待地理学视角的。这一观点至少可以上溯到希罗多德 (Herodotus),这个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常被誉为历史学之父。他坚称:“土质松软的国家养育生性软弱的人民。”并且,正如由他开启 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传统,他得出的结论是,正是地理环境决定了他的祖国的伟大。或许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11 sworth Huntington),这位耶鲁大学的地理学家在20世纪初收集了大量统计数据,用以证明他的家乡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有近乎完美的出产伟人的气候条 件。(只有英国的气候条件要更好些。)作为对比,他总结道,加利福尼亚州“过分整齐划一的刺激性气侯”(正是我居住的地方)只出产了大量 疯子。“加利福尼亚州的人民,”亨廷顿向他的读者保证说,“可以比做不堪驱策的马,他们中的一些因筋疲力尽而垮掉。” 人们很容易嘲讽这类说辞,但当我说地理学解释了西方的主宰地位的时侯,我的想法颇为不同。地理差异确实有长期的效果,但这些从不是根 深蒂固的。并且,在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的地理优势,在另一阶段可能是毫不相关的,甚至可能转化为劣势。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虽然地理推动了 社会发展,但是社会发展决定了地理的意义。这是条双行道。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点,也为了给本书的内容作一下快速导航,我想要回溯两万年,上溯到上一个冰河时期最为寒冷的时刻。那时,地理环境 至关重要:一英里厚的冰川覆盖了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冰川边缘是干燥而不适宜居住的苔原地带,只有靠近赤道的地方,才有少量的人类以采集 和狩猎为生。南方(人们可以居住的地方)和北方(人们不能居住的地方)的差异是极端的,但在南部地区,东西差异则相对较小。 冰河时期的末期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当然,两极地区依然很寒冷,赤道地区依然很炎热,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六处地方,即本书作者在第二 章中所指的原始核心地带,更为温暖的天气条件配合着当地的地理环境,为适宜人类驯化的植物和动物的进化(即改变它们的基因使之更能为人类 所用,最终使得经过基因改进的生物只能与人类共生)提供了有利条件。驯化的植物和动物意味着更多的食物,这样就能养育更多的人,从而产生 更多的创新。但是,驯化同时也意味着施加给推动这一进程的资源更多压力。发展的悖论就在这里起作用了。 这些核心地带一度是冰河时期极为典型的相对温暖、适宜居住的地区,但是现在,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了。 地理眷顾了所有这些地方,但对其中的某些地方更为偏爱。欧亚大陆西部一个叫侧翼丘陵区的核心地带,是可驯化的植物和动物的集中之地。由于 人群大致相似,因此在这片动植物资源最为丰富、别化最为便捷之地,开始了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过程。那大约是在公元前9500年。 遵循常识,作者用“西方”一词描述所有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很久以前,西方从亚洲西南部①的核心地带开始扩张 ,包举地中海盆地和欧洲,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又囊括了美洲和澳大拉西亚(泛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希望以常识的方式
家们把女人、下层阶级男人和孩子也算进了人物之列,在一团混杂之中加入了他们的声音,但在此书中我想更进一步。我认为,一旦我们把人物 (在新的、更为宽泛的定义下的更大群体的人物)看做大致相仿的,剩下的便只有地图了。 很多史学家被这一论断所激怒,就如同公牛看到红色的斗牛布一般。其中有几个史学家对我说,拒绝几个伟人就可以决定东西方历史走向的陈 词滥调是一回事儿,拒绝承认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的重要性,仅在无理性的物质因素中寻找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但这基本上 就是本书作者的主张。我将试图说明,在过去的15 000年中,东西方以相同的次序经历了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因为东西方由相同种类的人组成 ,而正是这些人创造了相同种类的历史。但我也试图说明,他们并非以同样的频率和速度完成这些事情。我的结论是,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 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地理学解释了西方为何主宰世界。 坦率地讲,这听起来可能像 “长期注定”理论的强硬路线,当然有些历史学家是这样看待地理学视角的。这一观点至少可以上溯到希罗多德 (Herodotus),这个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常被誉为历史学之父。他坚称:“土质松软的国家养育生性软弱的人民。”并且,正如由他开启 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传统,他得出的结论是,正是地理环境决定了他的祖国的伟大。或许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这位耶鲁大学的地理学家在20世纪初收集了大量统计数据,用以证明他的家乡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有近乎完美的出产伟人的气候条 件。(只有英国的气候条件要更好些。)作为对比,他总结道,加利福尼亚州“过分整齐划一的刺激性气候”(正是我居住的地方)只出产了大量 疯子。“加利福尼亚州的人民,”亨廷顿向他的读者保证说,“可以比做不堪驱策的马,他们中的一些因筋疲力尽而垮掉。” 人们很容易嘲讽这类说辞,但当我说地理学解释了西方的主宰地位的时候,我的想法颇为不同。地理差异确实有长期的效果,但这些从不是根 深蒂固的。并且,在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的地理优势,在另一阶段可能是毫不相关的,甚至可能转化为劣势。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虽然地理推动了 社会发展,但是社会发展决定了地理的意义。这是条双行道。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点,也为了给本书的内容作一下快速导航,我想要回溯两万年,上溯到上一个冰河时期最为寒冷的时刻。那时,地理环境 至关重要:一英里厚的冰川覆盖了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冰川边缘是干燥而不适宜居住的苔原地带,只有靠近赤道的地方,才有少量的人类以采集 和狩猎为生。南方(人们可以居住的地方)和北方(人们不能居住的地方)的差异是极端的,但在南部地区,东西差异则相对较小。 冰河时期的末期改变了地理的意义。当然,两极地区依然很寒冷,赤道地区依然很炎热,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六处地方,即本书作者在第二 章中所指的原始核心地带,更为温暖的天气条件配合着当地的地理环境,为适宜人类驯化的植物和动物的进化(即改变它们的基因使之更能为人类 所用,最终使得经过基因改进的生物只能与人类共生)提供了有利条件。驯化的植物和动物意味着更多的食物,这样就能养育更多的人,从而产生 更多的创新。但是,驯化同时也意味着施加给推动这一进程的资源更多压力。发展的悖论就在这里起作用了。 这些核心地带一度是冰河时期极为典型的相对温暖、适宜居住的地区,但是现在,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了。 地理眷顾了所有这些地方,但对其中的某些地方更为偏爱。欧亚大陆西部一个叫侧翼丘陵区的核心地带,是可驯化的植物和动物的集中之地。由于 人群大致相似,因此在这片动植物资源最为丰富、驯化最为便捷之地,开始了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过程。那大约是在公元前9500年。 遵循常识,作者用“西方”一词描述所有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很久以前,西方从亚洲西南部①的核心地带开始扩张 ,包举地中海盆地和欧洲,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又囊括了美洲和澳大拉西亚(泛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希望以常识的方式

来界定“西方”能更清晰明了(而不是挑出一些所谓独特的“西方”价值观念,诸如自由、理性、宽容,然后论证这些观念来自何方,以及世界的 哪些地方有这些观念),这对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重大影响。作者的目标是解释为何从原始的西方核心地带沿袭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首先是北 美-如今主宰地球,而不是西方其他地方的社会,即沿袭自其他原始核心地带的社会为何没有主宰全球。 遵循相同的逻辑,作者使用“东方”一词指代自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东端(古老程度仅次于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也是在很久以前,东方从 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原始核心地带开始扩展,那里对于植物的驯化大约始于公元前7500年,今天的东方包括了北至日本,南至中南半岛的广大 地区。 发源自其他核心地带的社会-位于今天的新几内亚的东南核心地带、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北印度的南亚核心地带、位于东撒哈拉沙漠的非洲 核心地带,以及分别位于墨西哥和秘鲁的两个新世界核心地带-都有它们各自令人神往的历史。在下文中,作者将反复提到这些地区,但着眼点还 将落在东西方对比上。我的主要根据是,自从冰河时期末期以来,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社会要么发源自原来的西方核心地带,要么发源自原来的东方 核心地带。艾伯特亲王在北京,与京巴狗洛蒂在巴尔莫勒尔堡相比,是个貌似可能的选择,而艾伯特亲王在库斯科、德里或者新几内亚则不然。因 此,要想解释西方缘何主宰世界,最有效的方式是聚焦东西方对比,这正是我所做的。 这样撰写本书是要付出代价的。通过更为全面的全球性论述,审视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这种处理方式在内容上将会比本书更为丰富并注意到 细微差别,也将为南亚文化、美洲文化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对整个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这种以全球视野论述的书也会存在 不足,尤其是将会导致失去焦点,篇幅较之本书也将会更为冗长。18世纪英国最机智的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1 Johnson)曾经评论道,虽然 人人都喜爱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但没人希望它更长”。这一评论适用于弥尔顿,更适用于作者将要着手论述的一切。 如果在解释历史方面,地理真的提供了一个希罗多德式的“长期注定”论解释,那么,在指出对动植物的驯化在西方核心地带始于公元前 9500年,在东方核心地带始于公元前7500年之后,我便可将本书匆匆结束。如此说来,西方社会的发展便会简简单单地领先于东方2000年,在西 方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东方还在发明书写。当然,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看到,地理并不能决定历史,因为地理优势最终 往往适得其反。它们推动了社会发展,但在此过程中社会发展又改变了地理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核心地带的范围扩大了,有时是通过移民,有时是通过邻近地区的效仿或者独立创新。在老的核心地带非常有效的技术-不 管是农业技术,还是关于村庄生活、城市和城邦、大帝国或者重工业的技术-扩散到新的社会和新的环境。有时候,这些技术在新的背景下兴旺发 达;有时候,它们无功无过;还有的时候,它们需要作出重大调整才能发挥作用。 尽管这看起来有些奇怪,但社会发展中的最大进步往往发生在这些无法很好地应用从更发达的核心地带引进或效仿的技术的地方。有时,这是 因为使旧方法适应新环境的努力迫使人们取得突破;有时,则是因为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无关紧要的地理因素,在另一个发展阶段变得举足轻重 例如,5000年前,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从欧洲大陆延伸至大西洋中,是地理上的一大劣势,意味着这些地区远离美索不达米亚(亦 称“两河流域”)①和埃及的文明。但是,500年前,社会的发展改变了地理条件的意义。有了新型的舰船可以横渡原先无法通行的海洋,于是突 然间扭转了形势,把延伸到大西洋的地理条件变成了一大优势。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舰船,而不是埃及或者伊拉克的舰船,开始驶向美
来界定“西方”能更清晰明了(而不是挑出一些所谓独特的“西方”价值观念,诸如自由、理性、宽容,然后论证这些观念来自何方,以及世界的 哪些地方有这些观念),这对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重大影响。作者的目标是解释为何从原始的西方核心地带沿袭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首先是北 美-如今主宰地球,而不是西方其他地方的社会,即沿袭自其他原始核心地带的社会为何没有主宰全球。 遵循相同的逻辑,作者使用“东方”一词指代自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东端(古老程度仅次于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也是在很久以前,东方从 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原始核心地带开始扩展,那里对于植物的驯化大约始于公元前7500年,今天的东方包括了北至日本,南至中南半岛的广大 地区。 发源自其他核心地带的社会-位于今天的新几内亚的东南核心地带、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北印度的南亚核心地带、位于东撒哈拉沙漠的非洲 核心地带,以及分别位于墨西哥和秘鲁的两个新世界核心地带-都有它们各自令人神往的历史。在下文中,作者将反复提到这些地区,但着眼点还 将落在东西方对比上。我的主要根据是,自从冰河时期末期以来,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社会要么发源自原来的西方核心地带,要么发源自原来的东方 核心地带。艾伯特亲王在北京,与京巴狗洛蒂在巴尔莫勒尔堡相比,是个貌似可能的选择,而艾伯特亲王在库斯科、德里或者新几内亚则不然。因 此,要想解释西方缘何主宰世界,最有效的方式是聚焦东西方对比,这正是我所做的。 这样撰写本书是要付出代价的。通过更为全面的全球性论述,审视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这种处理方式在内容上将会比本书更为丰富并注意到 细微差别,也将为南亚文化、美洲文化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对整个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这种以全球视野论述的书也会存在 不足,尤其是将会导致失去焦点,篇幅较之本书也将会更为冗长。18世纪英国最机智的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经评论道,虽然 人人都喜爱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但没人希望它更长”。这一评论适用于弥尔顿,更适用于作者将要着手论述的一切。 如果在解释历史方面,地理真的提供了一个希罗多德式的“长期注定”论解释,那么,在指出对动植物的驯化在西方核心地带始于公元前 9500年,在东方核心地带始于公元前7500年之后,我便可将本书匆匆结束。如此说来,西方社会的发展便会简简单单地领先于东方2 000年,在西 方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东方还在发明书写。当然,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看到,地理并不能决定历史,因为地理优势最终 往往适得其反。它们推动了社会发展,但在此过程中社会发展又改变了地理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核心地带的范围扩大了,有时是通过移民,有时是通过邻近地区的效仿或者独立创新。在老的核心地带非常有效的技术-不 管是农业技术,还是关于村庄生活、城市和城邦、大帝国或者重工业的技术-扩散到新的社会和新的环境。有时候,这些技术在新的背景下兴旺发 达;有时候,它们无功无过;还有的时候,它们需要作出重大调整才能发挥作用。 尽管这看起来有些奇怪,但社会发展中的最大进步往往发生在这些无法很好地应用从更发达的核心地带引进或效仿的技术的地方。有时,这是 因为使旧方法适应新环境的努力迫使人们取得突破;有时,则是因为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无关紧要的地理因素,在另一个发展阶段变得举足轻重 。 例如,5 000年前,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从欧洲大陆延伸至大西洋中,是地理上的一大劣势,意味着这些地区远离美索不达米亚(亦 称“两河流域”)①和埃及的文明。但是,500年前,社会的发展改变了地理条件的意义。有了新型的舰船可以横渡原先无法通行的海洋,于是突 然间扭转了形势,把延伸到大西洋的地理条件变成了一大优势。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舰船,而不是埃及或者伊拉克的舰船,开始驶向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