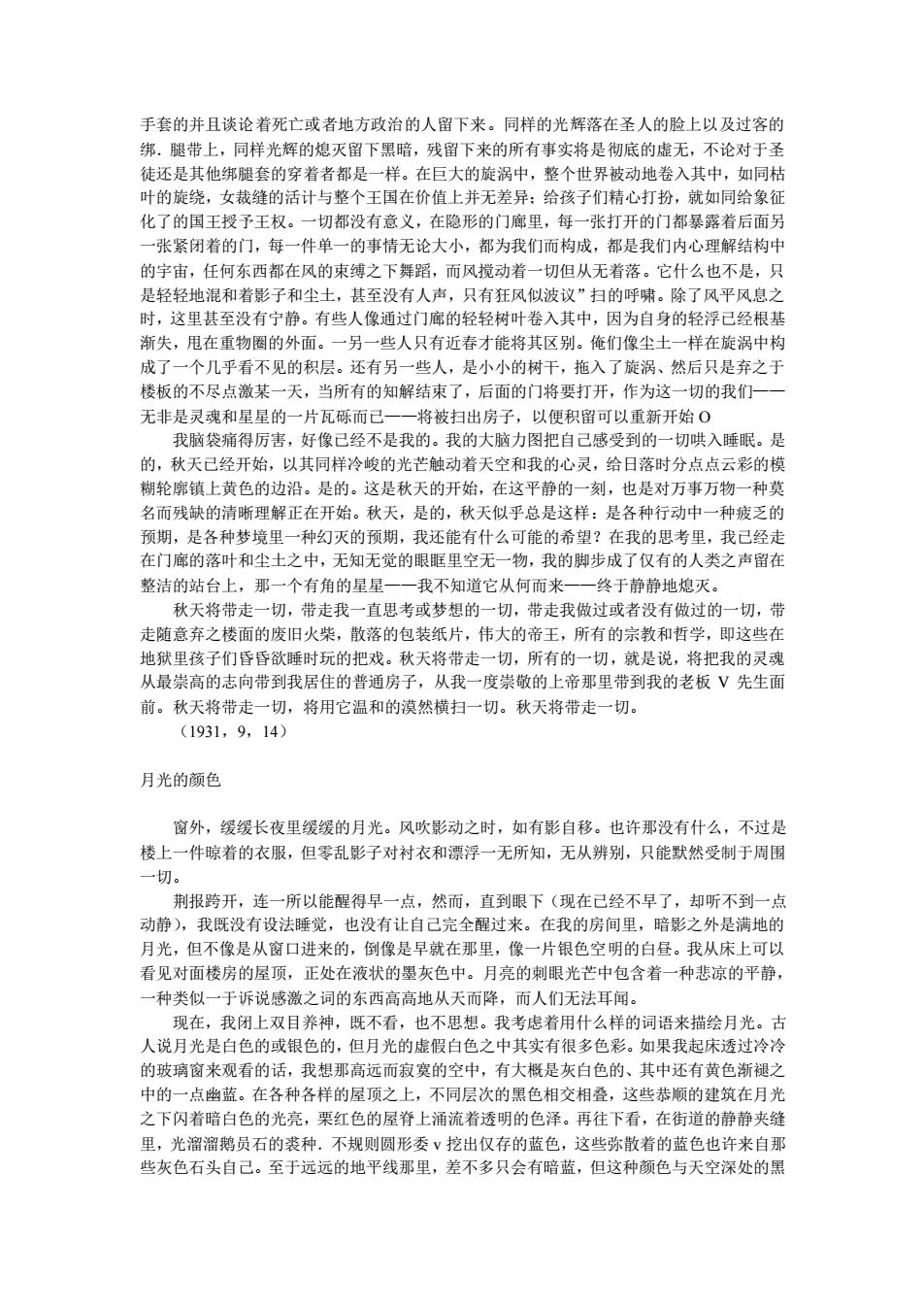
手套的并且谈论若死亡或者地方政治的人留下来。同样的光辉落在圣人的险上以及过客的 绑。腿带上,同样光辉的熄灭留下黑暗,残留下来的所有事实将是彻底的虚无,不论对于圣 徒还是其他绑腿套的穿着者都是 一样。在 大的旋涡中,整个世界被动地卷入其中,如同 叶的旋绕,女裁缝的活计与整个王国在价值上并无差异:给孩子们精心打扮,就如同给象征 化了的国王授予王权。一切都没有意义,在隐形的门廊里,每一张打开的门都暴露着后面另 一张紧闭着的门,每一件单一的事情无论大小,都为我们而构成,都是我们内心理解结构中 的字宙,任何东西都在风的束缚之下舞蹈,而风搅动着一切但从无若落。它什么也不是,只 是轻轻地 和者影子和尘士 ,甚至没有人声 有狂风似 扫的呼 了风平风息之 时,这里甚至没有宁静。有些人像通过门廊的轻轻树叶卷入其中,因为自身的轻浮已经根基 渐失,甩在重物圈的外面。一另一些人只有近春才能将其区别。俺们像尘士一样在旋涡中构 成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积层。还有另一些人,是小小的树干,拖入了旋涡、然后只是弃之于 楼板的不尽点激某一天,当所有的知解结束了,后面的门将要打开,作为这一切的我们- 无非是灵魂和星星的 片瓦砾而 将被扫出房子,以便积留可以重新开始 我脑袋痛得厉苦,好像已经不是我的。我的大脑力图把自己感受到的一切哄入睡眠。是 的,秋天已经开始,以其同样冷峻的光芒触动着天空和我的心灵,给日落时分点点云彩的模 糊轮廓镇上黄色的边沿。是的。这是秋天的开始,在这平静的一刻,也是对万事万物一种莫 名而残缺的清晰理解正在开始。秋天,是的,秋天似乎总是这样:是各种行动中一种疲乏的 预期,是各种梦境里 种幻灭的预期,我还能有什么可能的希望?在我的思考里,我己经走 在门廊的落 和尘土之中 无觉的 空无一物,我的脚 成 汉有的人类之声留有 整洁的站台上,那一个有角的星星 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 终于静静地熄灭 秋天将带走一切,带走我一直思考或梦想的一切,带走我做过或者没有做过的一切,带 走随意弃之楼面的废旧火柴,散落的包装纸片,伟大的帝王,所有的宗教和哲学,即这些在 地狱里孩子们昏昏欲睡时玩的把戏。秋天将带走一切,所有的一切,就是说,将把我的灵魂 从最崇高的志向带到我居住的普通房子 人我 一度当的上 帝那里带到我的老板V先生面 前。秋天将带走一切,将用它温和的漠然横扫一切。秋天将带走一切。 (1931,9,14) 月光的颜色 窗外,缓缓长夜里缓缓的月光。风吹影动之时,如有影自移。也许那没有什么,不过是 楼上一件晾着的衣服,但零乱影子对衬衣和漂浮一无所知,无从辨别,只能默然受制于周围 .切。 荆报跨开,连一所以能醒得早一点,然而,直到眼下(现在己经不早了,知听不到一点 动静),我既没有设法睡觉,也没有让自己完全醒过来。在我的房间里,暗影之外是满地的 月光,但不像是从窗口进来的,倒像是早就在那里, 一片银色空明的白昼。我从床上可以 看见对面楼房的屋顶,正处在液状的墨灰色中。月亮的刺眼光芒中包含着一种悲凉的平静, 一种类似一于诉说感激之词的东西高高地从天而降,而人们无法耳闻。 现在,我闭上双目养神,既不看,也不思想。我考虑着用什么样的词语米描绘月光。古 人说月光是白色的或银色的,但月光的虚假白色之中其实有很多色彩。如果我起床透过冷冷 的玻璃窗来观看的话,我想那高 的空中,有大概是灰白色的、其中还有黄色渐褪 中的一点幽蓝。在各种各样的屋顶之上,不同层次的黑色相交相叠,这些恭顺的建筑在月 之下闪着暗白色的光亮,栗红色的屋脊上涌流着透明的色泽。再往下看,在街道的静静夹 里,光溜溜鹅员石的裘种.不规则圆形委ν挖出仅存的蓝色,这些弥散着的蓝色也许来自那 些灰色石头自己。至于远远的地平线那里,差不多只会有暗蓝,但这种颜色与天空深处的里
手套的并且谈论着死亡或者地方政治的人留下来。同样的光辉落在圣人的脸上以及过客的 绑.腿带上,同样光辉的熄灭留下黑暗,残留下来的所有事实将是彻底的虚无,不论对于圣 徒还是其他绑腿套的穿着者都是一样。在巨大的旋涡中,整个世界被动地卷入其中,如同枯 叶的旋绕,女裁缝的活计与整个王国在价值上并无差异;给孩子们精心打扮,就如同给象征 化了的国王授予王权。一切都没有意义,在隐形的门廊里,每一张打开的门都暴露着后面另 一张紧闭着的门,每一件单一的事情无论大小,都为我们而构成,都是我们内心理解结构中 的宇宙,任何东西都在风的束缚之下舞蹈,而风搅动着一切但从无着落。它什么也不是,只 是轻轻地混和着影子和尘土,甚至没有人声,只有狂风似波议”扫的呼啸。除了风平风息之 时,这里甚至没有宁静。有些人像通过门廊的轻轻树叶卷入其中,因为自身的轻浮已经根基 渐失,甩在重物圈的外面。一另一些人只有近春才能将其区别。俺们像尘土一样在旋涡中构 成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积层。还有另一些人,是小小的树干,拖入了旋涡、然后只是弃之于 楼板的不尽点激某一天,当所有的知解结束了,后面的门将要打开,作为这一切的我们—— 无非是灵魂和星星的一片瓦砾而已——将被扫出房子,以便积留可以重新开始 O 我脑袋痛得厉害,好像已经不是我的。我的大脑力图把自己感受到的一切哄入睡眠。是 的,秋天已经开始,以其同样冷峻的光芒触动着天空和我的心灵,给日落时分点点云彩的模 糊轮廓镇上黄色的边沿。是的。这是秋天的开始,在这平静的一刻,也是对万事万物一种莫 名而残缺的清晰理解正在开始。秋天,是的,秋天似乎总是这样:是各种行动中一种疲乏的 预期,是各种梦境里一种幻灭的预期,我还能有什么可能的希望?在我的思考里,我已经走 在门廊的落叶和尘土之中,无知无觉的眼眶里空无一物,我的脚步成了仅有的人类之声留在 整洁的站台上,那一个有角的星星——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终于静静地熄灭。 秋天将带走一切,带走我一直思考或梦想的一切,带走我做过或者没有做过的一切,带 走随意弃之楼面的废旧火柴,散落的包装纸片,伟大的帝王,所有的宗教和哲学,即这些在 地狱里孩子们昏昏欲睡时玩的把戏。秋天将带走一切,所有的一切,就是说,将把我的灵魂 从最崇高的志向带到我居住的普通房子,从我一度崇敬的上帝那里带到我的老板 V 先生面 前。秋天将带走一切,将用它温和的漠然横扫一切。秋天将带走一切。 (1931,9,14) 月光的颜色 窗外,缓缓长夜里缓缓的月光。风吹影动之时,如有影自移。也许那没有什么,不过是 楼上一件晾着的衣服,但零乱影子对衬衣和漂浮一无所知,无从辨别,只能默然受制于周围 一切。 荆报跨开,连一所以能醒得早一点,然而,直到眼下(现在已经不早了,却听不到一点 动静),我既没有设法睡觉,也没有让自己完全醒过来。在我的房间里,暗影之外是满地的 月光,但不像是从窗口进来的,倒像是早就在那里,像一片银色空明的白昼。我从床上可以 看见对面楼房的屋顶,正处在液状的墨灰色中。月亮的刺眼光芒中包含着一种悲凉的平静, 一种类似一于诉说感激之词的东西高高地从天而降,而人们无法耳闻。 现在,我闭上双目养神,既不看,也不思想。我考虑着用什么样的词语来描绘月光。古 人说月光是白色的或银色的,但月光的虚假白色之中其实有很多色彩。如果我起床透过冷冷 的玻璃窗来观看的话,我想那高远而寂寞的空中,有大概是灰白色的、其中还有黄色渐褪之 中的一点幽蓝。在各种各样的屋顶之上,不同层次的黑色相交相叠,这些恭顺的建筑在月光 之下闪着暗白色的光亮,栗红色的屋脊上涌流着透明的色泽。再往下看,在街道的静静夹缝 里,光溜溜鹅员石的裘种.不规则圆形委 v 挖出仅存的蓝色,这些弥散着的蓝色也许来自那 些灰色石头自己。至于远远的地平线那里,差不多只会有暗蓝,但这种颜色与天空深处的黑

蓝大不一样,触及到窗户玻璃之处便会有暗黄浮现。 从这里,从我的床上,如果我打开睡意惺松的眼睛。打开自己尚未深睡的眼睛,天空中 就像一片冰雪之色,其中涌流着珍珠母暖色 果我用自己的感受来思考月光 事 就变得有些单调,使白色的光影渐渐暗淡下去,就像我的眼晴缓缓闭上时白光慎糊直至 停滞我经历若极其停滞的阶段。在这里,我并不是说我像大多数人那样,花费上一天又一刀 的时间写明信片去回应什么人写给我的快函。我也不是说我像其他一些人那样,可以轻易地 无限期推识一些可被证明有用于我的事情,或者是可以给子我快乐的事情。我对自己的误解 比这些要小得多。我是灵魂停滞了 我受生 种意志的悬置,与此同时 感情和思想却天 天在持健 我只能向别人表达自己,然后以语言,以行动,以习惯,在勃勃繁有者的灵魂 话里,通过他们向自己作自我表达 在这些影子般的时间里,我不能思想、感受或者愿望。我设法写下来的东西,只有数学 或者仅仅是笔的停顿。我一无所感,甚至我所爱之人的死亡,似乎也会远远离我而去,成为 件用外语发生的事件。我也一无所为,就像我在睡觉,我的语言、姿势以及举动仅仅是 种表面的呼吸, 官有节 于是日子和日子过去了,这些加起来的日子是我多少生命,我说不清楚。我最终把停滞 当成一件衣装脱落下的时候,我想我不会像自己的想象中那样赤裸地站若, 一些无形的外衣 将会一直包装者我,掩饰我真正灵魂的永远缺席。我突然想到这一切,我的思想、感受以及 驱望也许是一种停带的形式,是我更为个性化的用维方式和自己更为孰采的感资是厂个葛 志.的失落之处 x那个迷宫里我才真正成为自己 无论这是不是真理,我都会听其自然。无论上帝和女神是否存在,我都会交出实在的我, 听从任何送达而来的命运,听从任何提供与我的机会,对已经食言于我的许诺无限忠诚。 (1930,12,10) 我是传撇 我们把生活想象成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对于有一块园子的农民来说,园子就是他的 一切,是他的帝国。信撒有庞大帝国,仍嫌帝国狭窄,帝国就只是他的园子。小人物有一个 帝国。大人物只有一个园子。除了我们的感觉以外我们一无所有,这是他们的真实,却不能 被他们领悟,而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己生活的现实。 但所有这些都是虚 我做了很多梦,现在己经把梦做累了。但我并不厌倦梦。没有人厌倦梦,因为梦就是忘 却,而忘却不会成为我们的负担,忘却是我们完全保持清醒时无梦的沉睡。我在梦里得到了 一切。我已经醒了,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当过了多少次偿撒呵!这是何等精神意义上的 光荣!当信撒在一个海盗的宽宏大量下死里逃生以后,他长久和艰难地寻找这个人,速捕他 并且下令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拿破仑在圣·海伦娜岛上定下最后的意愿和遗嘱,他将 大笔遗产,留给 个曾经试图行刺威灵倾(滑铁卢之战的胜利者 译者注)的罪犯。如 灵魂的伟大,却与他们的惠斜眼疾的邻居差不多同日而语卜.·我己经不计其数地当过消 撒并且在梦里继续当下去! 不管我多少次当上了他撒,还没有喜欢上真正的消撒。我的真正帝国是我的梦,只因为 它们最后都夫细情于敌 我伪军队征战南北但无关紧要,不会有人死去。也没有城头的王 旗变幻。我从来 有 梦里军队的所 之处, 有旗帜飘入我梦中凝定的视野。在道拉多雷 大街上我不计数地成为他撒。作为他撒的我,至今生活在我的想象里,而真正的他撤们统统 早就死了,作为现实的道拉多雷斯大街,现在无从辨认他们。_我把一个空空的火柴盒,丢 入我高高窗户外的街头垃圾堆,然后坐在椅子里倾听。落下去的火柴盒送回了清晰的回声
蓝大不一样,触及到窗户玻璃之处便会有暗黄浮现。 从这里,从我的床上,如果我打开睡意惺松的眼睛.打开自己尚未深睡的眼睛,天空中 就像一片冰雪之色,其中涌流着珍珠母暖色的流丝。如果我用自己的感受来思考月光,事情 就变得有些单调,使白色的光影渐渐暗淡下去,就像我的眼睛缓缓闭上时白光模糊直至消失。 停滞我经历着极其停滞的阶段。在这里,我并不是说我像大多数人那样,花费上一天又一天 的时间写明信片去回应什么人写给我的快函。我也不是说我像其他一些人那样,可以轻易地 无限期推迟一些可被证明有用于我的事情,或者是可以给予我快乐的事情。我对自己的误解 比这些要小得多。我是灵魂停滞了。我受害于一种意志的悬置,与此同时,感情和思想却天 天在持续。我只能向别人表达自己,然后以语言,以行动,以习惯,在勃勃繁育着的灵魂生 活里,通过他们向自己作自我表达。 在这些影子般的时间里,我不能思想、感受或者愿望。我设法写下来的东西,只有数字 或者仅仅是笔的停顿。我一无所感,甚至我所爱之人的死亡,似乎也会远远离我而去,成为 一件用外语发生的事件。我也一无所为,就像我在睡觉,我的语言、姿势以及举动仅仅是一 种表面的呼吸,是一些器官有节奏的本能。 于是日子和日子过去了,这些加起来的日子是我多少生命,我说不清楚。我最终把停滞 当成一件衣装脱落下的时候,我想我不会像自己的想象中那样赤裸地站着,一些无形的外衣 将会一直包装着我,掩饰我真正灵魂的永远缺席。我突然想到这一切,我的思想、感受以及 愿望也许是一种停滞的形式,是我更为个性化的思维方式和自己更为熟悉的感资是厂个葛 志.的失落之处一一一一一一 rax 那个迷宫里我才真正成为自己。 无论这是不是真理,我都会听其自然。无论上帝和女神是否存在,我都会交出实在的我, 听从任何送达而来的命运,听从任何提供与我的机会,对已经食言于我的许诺无限忠诚。 (1930,12,10) 我是传撒 我们把生活想象成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对于有一块园子的农民来说,园子就是他的 一切,是他的帝国。信撒有庞大帝国,仍嫌帝国狭窄,帝国就只是他的园子。小人物有一个 帝国。大人物只有一个园子。除了我们的感觉以外我们一无所有,这是他们的真实,却不能 被他们领悟,而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己生活的现实。 但所有这些都是虚无。 我做了很多梦,现在已经把梦做累了。但我并不厌倦梦。没有人厌倦梦,因为梦就是忘 却,而忘却不会成为我们的负担,忘却是我们完全保持清醒时无梦的沉睡。我在梦里得到了 一切。我已经醒了,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当过了多少次偿撒呵!这是何等精神意义上的 光荣!当信撒在一个海盗的宽宏大量下死里逃生以后,他长久和艰难地寻找这个人,逮捕他 并且下令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拿破仑在圣·海伦娜岛上定下最后的意愿和遗嘱,他将一 大笔遗产,留给一个曾经试图行刺威灵顿(滑铁卢之战的胜利者——译者注)的罪犯。如此 灵魂的伟大,却与他们的患斜眼疾的邻居差不多同日而语卜.··我已经不计其数地当过消 撒并且在梦里继续当下去! 不管我多少次当上了他撒,还没有喜欢上真正的消撒。我的真正帝国是我的梦,只因为 它们最后都去烟悄无敌、,我伪军队征战南北但无关紧要,不会有人死去。也没有城头的王 旗变幻。我从来没有让梦里军队的所到之处,有旗帜飘入我梦中凝定的视野。在道拉多雷斯 大街上我不计数地成为他撒。作为他撒的我,至今生活在我的想象里,而真正的他撤们统统 早就死了,作为现实的道拉多雷斯大街,现在无从辨认他们。_我把一个空空的火柴盒,丢 入我高高窗户外的街头垃圾堆,然后坐在椅子里倾听。落下去的火柴盒送回了清晰的回声

让我知道大街的荒芜,这一事实似乎显示着某种意义。没有声音可以从整个城市的声音里分 离出来。是的,整个星期天城市的声音 这么多无法破##jHHg$ 人需要的现实世界,作为最为深连思想的起点,是何等的小:吃中饭晚了 一点点 用完了火柴然后把空火柴盒抛向街头,因为中饭吃得太晚以致稍感不适,除了可怜落日的许 诺以外空中什么也没有的星期天,还有我既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属于其他如此形而上问题的 生命。 但是,我当了多少次偿撤: (1930,6,27 下坠 踏着我梦想和成螽的脚步,从你的虚幻中下坠,下坠,而且成为我在这个世界中的替身 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你想要旅行么?要旅行的话,你只需要存在就行, 在我身体的列车里 在我的命运旅行途中如同一站接一站的一日复 日里,我探出头去看见了街道 广场,看见 了姿势和面容,它们总是相同, 一如它们总是相异。说到底,命运是越容所有景观的通道 如果我想象什么,我就能看见它。如果我旅行的话,我会看得到更多的什么吗?只右相 象的极端贫弱,才能为意在感受的旅行提供辩解 “通向E市的任何一条道路, 合把你引向界的终占”(19什纪苏格兰折学家托旦 斯昨莱尔语)但是 旦你把 界完 全看了个透,世界的终点就与你出发时的E市没有什 么两样。事实上,世界的终点以及世界的起点,只不过是我们有关世界的概念。仅仅是在我 们的内心里,景观才成其为景观。这就是为什么说我想象它们,我就是在创造它们。如果我 创造它们,它们就存在。如果它们存在,那么我看见它们就像我看见别的景观。所以干麻要 旅行呢?在马德里,在柏林,在波斯,在中国,在南极和北极,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有异于内 在的我?可以感受到我特别不同的感受? 生活全看我们是如何把它造就。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我们所看至 的,而是我们自己。孩子的智慧在我所见过的人当中,真正以心灵旅行的人是一个办公室的 小伙计,在我曾经一度供职的一家公司打过工。这个小家伙曾经收集着有关各个城市、各个 国家以及诸多旅游公司的小册子,有一些地图。其中一部分是从报纸上撕下来的,另一部分 是从某地或者其他地方讨来的。他剪下风景图片,外国服装的木刻,还有各种期刊杂志上小 艇和大船的油画 他代 些真实和虚假的公司访问一些旅游代理机构。 其中真实的一家 就是雇他打工的公司。他代表这些公同索要关于意大讨或者印度的小1. 文些个小册子提供在萄萄牙与澳大利亚之间航行的诸多细带。 他不仅仅是我所见到的最伟大的旅行者(因为他是最为真实的旅行家),还是我有幸国 到的最快乐的人之一 。我很抱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造就了他的纯真,但我不是真正地抱歉。 只是感到自己将有抱款的可能。我不会真正地抱款全因为在今天, 自从我结识他的短暂时期 以后, 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以后,他肯定已经长大成熟了,老成持重,办事牢靠 俗尽职 可能结了婚,是什么人养家糊口的靠山一 一N句话来说,已经成了半死者之一。现 在,完全知道怎么在心灵里旅行的他,甚至能用身体来旅行了。 一种记忆突然向我袭来:他曾经准确地知道哪一横列车必须赶上从巴黎至有微勒断特 胁·列车,哪一趟列车要穿越英格兰。在他对一些陌生地名的歪曲发音里,闪现者他伟大心 灵的光辉品质。他现在可能活得像一个半死者,但是也许有一天,当他垂垂老了的时候,他 会回忆起对布彻畅斯特的梦想相对于真正到达布彻勒斯特来说,不仅仅是更好,而且是更为 真实。 进一步说,也许这一切有另一种解释,也许他当时只不过是模仿别人而己。或者,也
让我知道大街的荒芜,这一事实似乎显示着某种意义。没有声音可以从整个城市的声音里分 离出来。是的,整个星期天城市的声音——这么多无法破##tjHHffg$e=。 一个人需要的现实世界,作为最为深连思想的起点,是何等的小:吃中饭晚了一点点, 用完了火柴然后把空火柴盒抛向街头,因为中饭吃得太晚以致稍感不适,除了可怜落日的许 诺以外空中什么也没有的星期天,还有我既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属于其他如此形而上问题的 生命。 但是,我当了多少次偿撤! (1930,6,27) 下坠 踏着我梦想和疲惫的脚步,从你的虚幻中下坠,下坠,而且成为我在这个世界中的替身。 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你想要旅行么?要旅行的话,你只需要存在就行。在我身体的列车里, 在我的命运旅行途中如同一站接一站的一日复一日里,我探出头去看见了街道和广场,看见 了姿势和面容,它们总是相同,一如它们总是相异。说到底,命运是越容所有景观的通道。 如果我想象什么,我就能看见它。如果我旅行的话,我会看得到更多的什么吗?只有想 象的极端贫弱,才能为意在感受的旅行提供辩解。 “通向 E 市的任何一条道路,都会把你引向世界的终点。”(19 世纪苏格兰哲学家托马 斯昨莱尔语)但是,一旦你把世界完全看了个透,世界的终点就与你出发时的 E 市没有什 么两样。事实上,世界的终点以及世界的起点,只不过是我们有关世界的概念。仅仅是在我 们的内心里,景观才成其为景观。这就是为什么说我想象它们,我就是在创造它们。如果我 创造它们,它们就存在。如果它们存在,那么我看见它们就像我看见别的景观。所以干嘛要 旅行呢?在马德里,在柏林,在波斯,在中国,在南极和北极,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有异于内 在的我?可以感受到我特别不同的感受? 生活全看我们是如何把它造就。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我们所看到 的,而是我们自己。孩子的智慧在我所见过的人当中,真正以心灵旅行的人是一个办公室的 小伙计,在我曾经一度供职的一家公司打过工。这个小家伙曾经收集着有关各个城市、各个 国家以及诸多旅游公司的小册子,有一些地图,其中一部分是从报纸上撕下来的,另一部分 是从某地或者其他地方讨来的。他剪下风景图片,外国服装的木刻,还有各种期刊杂志上小 艇和大船的油画。他代表一些真实和虚假的公司访问一些旅游代理机构,其中真实的一家, 就是雇他打工的公司。他代表这些公同索要关于意大讨或者印度的小 dljl.’────-一 这些个小册子提供在葡萄牙与澳大利亚之间航行的诸多细节。 他不仅仅是我所见到的最伟大的旅行者(因为他是最为真实的旅行家),还是我有幸遇 到的最快乐的人之一。我很抱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造就了他的纯真,但我不是真正地抱歉, 只是感到自己将有抱歉的可能。我不会真正地抱歉全因为在今天,自从我结识他的短暂时期 以后,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以后,他肯定已经长大成熟了,老成持重,办事牢靠,俗尽职守, 可能结了婚,是什么人养家糊口的靠山一一一一 N 一句话来说,已经成了半死者之一。现 在,完全知道怎么在心灵里旅行的他,甚至能用身体来旅行了。 一种记忆突然向我袭来:他曾经准确地知道哪一趟列车必须赶上从巴黎至有微勒斯特 胁·列车,哪一趟列车要穿越英格兰。在他对一些陌生地名的歪曲发音里,闪现着他伟大心 灵的光辉品质。他现在可能活得像一个半死者,但是也许有一天,当他垂垂老了的时候,他 会回忆起对布彻勒斯特的梦想相对于真正到达布彻勒斯特来说,不仅仅是更好,而且是更为 真实。 进一步说,也许这一切有另一种解释,也许他当时只不过是模仿别人而已。或者,也

Rliiry:to\13lorn9?tnysr3rw.xig'cag'- 一W人的愚笑之间存在着的石 鸿沟,我以为我们像孩子一样必定有一个守护神。这位守护神将自己的神明借给我们,然 后 也许不无哀伤地顺从 一种更高的法律,把我们抛弃,这也是雌性 它们成年后 方式。 于是,成为肥胖的猪锣就成为了我们的命运。我游历第八大洲有 一种关于知识的 问,我们通常定义为“学问”。也有一种关于理解的学问,我们称其为“文化”。但是,还有 一种关于感觉的学问。 汝种学问与人的牛活经验没有什么关系。生活经哈就像历史,不能给我们什么教益。自 正的体验包含两个方面:弱化一个人与现实自 个人对这种壁系的 析。以这种方 无论我们内 广 ,足以使 我们把这些事情找出来,并且知道如何去找。 什么是旅行?旅行有何用处? 一个落日,同另一个落日太像了,你无须到康上坦丁堡去 刻意地看一下某个落B。而旅行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自由感?我可以享乐于一次仅仅是从 里斯本到本弗卡的旅行,比起某一个人从里既本到中国的旅行来说,我的自由感可以更加骑 烈。因为在我看米 果自由 感不备于我的话 武无外 条道路 尔说, “造向N市的在条道路都时以把你引向世外的终点。但是,的N市的道路 如果随后领利到达了世界的终点,同样会引导我们径直返回N市。这就意味着,作为我们 起点的N市,一开始也是我们启程以求的“世界终点” 孔秋亚克(18世纪法国析学家一 一译者注)在一本名著作中 一开始就说:“无论我 们爬得多民医无论我们跌肯多深:我们都无缺选“出自己的感觉。”我们从来不能从自己体 内抽身而去。我们从来不能成为另外的人,除非运用我们对自己的想象性感觉,我们才能他 变。真正的景观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因为我们是它们的上帝。它们在我们眼里实际的样子 恰恰就是它们被造就的样子。我对世界七大洲的任何地方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真正去看过。 我游历我自己的第八大洲 存些人就悔人个大洋:但很少航游他自已的单调。我的航程比所有人的都要谣远。我 见过的高山多于地球上所有存在的高山。我走过的城市多于已经建起来的城市。我渡过的 可任 不可能的世界里奔流不总,在我沉。思的凝视下确凿无疑地奔流。如果旅行的话 我只能找到一个模糊不清的复制品,它复制着我无须旅行就己经看见了的东西。 其他旅行者访问一些国家时,所作所为就像无名的流浪者。而在我访问过的国家里,我 不仅仅右隐名旅行者所能感微到的暗自克悦,西且是统英钱l:c国王陛下,是生活在 那里的人民以及他们的习俗,是那些人民以及其他民族的整个历史。我看见了的那些景观利 那些房屋,都是上帝用我想象的材料创造出来的。我就是它们。 与死亡之约 我能够理解持续不断的惰性,仅仅在于我总是对自己单调无奇的生活听其自然、就像把 一些灰尘和赃物堆积在事物完全不可改变性的表面,缺少一种个人的洁身自好。 我们应该像对待白己的身体一样给命云洗洗操,像更换白己的衣装一样,来改变一下 我们的生活。 -不是为了保持我们要吃要睡的 一条小命,而是出于对我们自己无所作为的 敏,这就是正式叫作洁身自好的事情。 在很多人那里,一种洁身的缺乏并不是意志使然,而是一种不以为然的智识态度。对于 很多人来说,他们生活的乏味和雷同不是他们对自己的选择,也不是对无可选择之处境的自
许.Rljjry;to\l3lorn9?tny$r3rW,xi9’cag’──’──W 人的愚笨之间存在着的巨 大鸿沟,我以为我们像孩子一样必定有一个守护神。这位守护神将自己的神明借给我们,然 后,也许不无哀伤地顺从一种更高的法律,把我们抛弃,这也是雌性动物抛弃它们成年后代 的方式。于是,成为肥胖的猪锣就成为了我们的命运。我游历第八大洲有一种关于知识的学 问,我们通常定义为“学问”。也有一种关于理解的学问,我们称其为“文化”。但是,还有 一种关于感觉的学问。 这种学问与人的生活经验没有什么关系。生活经验就像历史,不能给我们什么教益。真 正的体验包含两个方面:弱化一个人与现实的联系,与此同时又强化一个人对这种联系的分 析。以这种方式,无论我们内心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人的感觉可以变得深入和广阔,足以使 我们把这些事情找出来,并且知道如何去找。 什么是旅行?旅行有何用处?一个落日,同另一个落日太像了,你无须到康上坦丁堡去 刻意地看一下某个落 B。而旅行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自由感?我可以享乐于一次仅仅是从 里斯本到本弗卡的旅行,比起某一个人从里既本到中国的旅行来说,我的自由感可以更加强 烈。因为在我看来,如果自由感不备于我的话,那么它就无处可寻。“任何一条道路,”卡莱 尔说,“通向 N 市的任何一条道路,都可以把你引向世界的终点。”但是,通向 N 市的道路, 如果随后顺利到达了世界的终点,同样会引导我们径直返回 N 市。这就意味着,作为我们 起点的 N 市,一开始也是我们启程以求的“世界终点”。 孔狄亚克(18 世纪法国哲学家——译者注)在一本著名著作中,一开始就说:“无论我 们爬得多民医无论我们跌肯多深;我们都无缺选“出自己的感觉。”我们从来不能从自己体 内抽身而去。我们从来不能成为另外的人,除非运用我们对自己的想象性感觉,我们才能他 变。真正的景观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因为我们是它们的上帝。它们在我们眼里实际的样子, 恰恰就是它们被造就的样子。我对世界七大洲的任何地方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真正去看过。 我游历我自己的第八大洲。 存些人规就悔卜个大洋;但很少航游他自己的单调。我的航程比所有人的都要遥远。我 见过的高山多于地球上所有存在的高山。我走过的城市多于已经建起来的城市。我渡过的大 河在一个不可能的世界里奔流不息,在我沉.思的凝视下确凿无疑地奔流。如果旅行的话, 我只能找到一个模糊不清的复制品,它复制着我无须旅行就已经看见了的东西。 其他旅行者访问一些国家时,所作所为就像无名的流浪者。而在我访问过的国家里,我 不仅仅有隐名旅行者所能感觉到的暗自喜悦,西且是统英钱 pl;irflcl 国王陛下,是生活在 那里的人民以及他们的习俗,是那些人民以及其他民族的整个历史。我看见了的那些景观和 那些房屋,都是上帝用我想象的材料创造出来的。我就是它们。 与死亡之约 我能够理解持续不断的惰性,仅仅在于我总是对自己单调无奇的生活听其自然、就像把 一些灰尘和赃物堆积在事物完全不可改变性的表面,缺少一种个人的洁身自好。 我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给命运洗洗澡,像更换自己的衣装一样,来改变一下 我们的生活——不是为了保持我们要吃要睡的一条小命,而是出于对我们自己无所作为的尊 敬,这就是正式叫作洁身自好的事情。 在很多人那里,一种洁身的缺乏并不是意志使然,而是一种不以为然的智识态度。对于 很多人来说,他们生活的乏味和雷同不是他们对自己的选择,也不是对无可选择之处境的自

然迎合,而是一种对自知之明的嗤之以鼻,一一种对理解力的本能讥潮。 有一些猪,不管它们怎样对自己的污秽感到厌恶,也不能使自己远离这种境况,然而奇 怪的 它们有同样感觉的极致,能够避开危险的小道以防恐怖事件发生。就像我 一样, 些靠天性活者的猪们不打算尝试一下从每天平庸的生活里逃离,在自己的软弱无力中昏昏欲 睡。它们是一些小鸟,只要蛇不在场便乐不可支:是一些苍蝇,对技头上随时准各袭来粘乎 平长舌的变色渐妈毫无察觉。 就这样,每一天我都沿自己俗套之树的特定一枝,招摇自己无意识的意识。我招摇 者跑在前面并不对 巴我等待的命运,还有我甚至不曾追赶的时光。只有 一件东西把我从单调 拯救出来,那就是我作出的有关简短笔记。我仅有的高兴,在于我的牢狱里还有透光的玻璃 在栏杆的这一边,在一大堆信函和宿命的尘土中,我写下了自己每一天与死亡签约时的签名。 我是说与死十整约么?不,这其至不是与死十签约。任何一个像我这样活若的人都不会 死去:他们来到客休在些枯氨只不过是停止生长。他占据的空间没有他也会存在下去,他走 过的街道在他无可寻觅时还将遗留下去,他住过的房子还将被不是他的人米居住。这就是我 们称之为虚无的一切。但这是我们的夸大其辞,这个否定性的悲剧甚至不能保证会得到什么 喝彩,因为我们无法肯定这就是虚无,因为我们的生活有多少,真知就同样只能生长多少。 我们是同时遮盖着窗户玻璃里面和外面的尘土,是命运的孙子和上帝的继子。 上帝娶了永远的暗夜之神为妻,而把暗夜之神弃之为嘉妇的乱神,才是我们真正的父亲 微像是 一种奇怪的观看方式,能够把我们大脑下意识里一些仅仅是粗略的印象,激发 成动人心弦的录观 常感觉到这 一点。我 ,虽然看 周围的 ,但两 空空。我只是看者人们所看着的一切,知道自己走在大街上,但并没有意识到这条街包括君 两边由人们建造出来的不同房屋。我走在一条大街上,从面包房那里飘来一股面包的浓香 也就从小城那一边的地带飘来了我的童年,飘来了另一家出现在我面前的面包房,那仙女的 王国是我们失去了的一切。我走在 一条大街上。从一家窄小店铺外的雄子上飘来了一缕突加 其来的水果香, 飘来了我在乡下短暂的岁月,飘来了我不再知道的岁月或者地方,那里 有果林和我心中的平宁欣慰,还有我作为一个孩子千真万确的一刻。我走在 一系大街上 乎意料地又有一阵木板箱的气味,从一个木箱打造者那里劈面而米:呵,C·韦尔德(19世 纪葡萄牙诗人,详见前注 一译者注),你出现在我的眼前,最终使我快乐,因为通过回忆, 我回到了文学的直实。不求理解我从来不求被他人理解。被理解类似于自我卖淫。我宁可被 人们严重地误解成非我的面目 宁可作为 一个人被其他人正派而自然地漠视。 比起办公室里的同事们把我看成特别不同的人来说没弃休么要篇让我长陆我崛让他们 的讥嘲不致于弄成这种味道。我想让他们行行好,把我看成是同他们一样的人。我想把他们 不再视我为异教这件事,永远钉死在十字架上。比起那些圣徒和隐士当中有案可查的殉难来 说,还有更加微不足道的殉难。世上有智力的苦刑,一如世上有身体和欲望。而另一些苦刑 包含着苦刑本身的妖烧诱人。正常正常对于我们来说像一个家,像日常生活中的一位母亲。 对伟大诗歌和崇高志向的高 群山作出 次长长的进入之后,在领略过出类技革和神奇莫测 的险峻风光之后,最甜蜜的事情当然是品尝生活中一切温暖,返回快乐的傻笑和玩笑充斥其 间的小酒店,混在这些人中间一起胡吹海喝,对我们受赐的宇宙心满意足,像他们一样目傻 气,恰如上帝把我们造就的模样 我们所微下的人还在艰难爬山,然而爬到山顶时,他们却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不会使我震惊的是,人们会说,比起一些生活和成就都只能 平平的其他人来说,我视之 为疯狂和愚笨的人要更好一些。他们一旦发作起来疯癫会不平常的猛烈:妄想狂会有 种超 乎绝大多数常人的推理能力:走火火魔的宗教狂热比任何煽动家(几乎)更能够吸引成群的 信徒,更能够给予追随者们一种煽动家从来给予不了的内在力量。但所有这些都证明不了什 么,只能证明疯狂就是疯狂。我宁可不知道美丽鲜花可以比附成一种荒野之地的胜利,因为
然迎合,而是一种对自知之明的嗤之以鼻,一种对理解力的本能讥嘲。 有一些猪,不管它们怎样对自己的污秽感到厌恶,也不能使自己远离这种境况,然而奇 怪的是,它们有同样感觉的极致,能够避开危险的小道以防恐怖事件发生。就像我一样,这 些靠天性活着的猪们不打算尝试一下从每天平庸的生活里逃离,在自己的软弱无力中昏昏欲 睡。它们是一些小鸟,只要蛇不在场便乐不可支;是一些苍蝇,对枝头上随时准备袭来粘乎 乎长舌的变色渐妈毫无察觉。 就这样,每一天我都沿着自己俗套之树的特定一枝,招摇着自己无意识的意识。我招摇 着跑在前面并不把我等待的命运,还有我甚至不曾追赶的时光。只有一件东西把我从单调中 拯救出来,那就是我作出的有关简短笔记。我仅有的高兴,在于我的牢狱里还有透光的玻璃, 在栏杆的这一边,在一大堆信函和宿命的尘土中,我写下了自己每一天与死亡签约时的签名。 我是说与死亡签约么?不,这甚至不是与死亡签约。任何一个像我这样活着的人都不会 死去:他们来到客休在些枯氨只不过是停止生长。他占据的空间没有他也会存在下去,他走 过的街道在他无可寻觅时还将遗留下去,他住过的房子还将被不是他的人来居住。这就是我 们称之为虚无的一切。但这是我们的夸大其辞,这个否定性的悲剧甚至不能保证会得到什么 喝彩,因为我们无法肯定这就是虚无,因为我们的生活有多少,真知就同样只能生长多少。 我们是同时遮盖着窗户玻璃里面和外面的尘土,是命运的孙子和上帝的继子。 上帝娶了永远的暗夜之神为妻,而把暗夜之神弃之为寡妇的乱神,才是我们真正的父亲。 嗅觉嗅觉像是一种奇怪的观看方式,能够把我们大脑下意识里一些仅仅是粗略的印象,激发 成动人心弦的景观。我经常感觉到这一点。我走到一条街上,虽然看着周围的一切,但两眼 空空。我只是看着人们所看着的一切,知道自己走在大街上,但并没有意识到这条街包括着 两边由人们建造出来的不同房屋。我走在一条大街上,从面包房那里飘来一股面包的浓香, 也就从小城那一边的地带飘来了我的童年,飘来了另一家出现在我面前的面包房,那仙女的 王国是我们失去了的一切。我走在一条大街上。从一家窄小店铺外的摊子上飘来了一缕突如 其来的水果香,也就飘来了我在乡下短暂的岁月,飘来了我不再知道的岁月或者地方,那里 有果林和我心中的平宁欣慰,还有我作为一个孩子千真万确的一刻。我走在一条大街上。出 乎意料地又有一阵木板箱的气味,从一个木箱打造者那里劈面而来:呵,C·韦尔德(19 世 纪葡萄牙诗人,详见前注——译者注),你出现在我的眼前,最终使我快乐,因为通过回忆, 我回到了文学的真实。不求理解我从来不求被他人理解。被理解类似于自我卖淫。我宁可被 人们严重地误解成非我的面目,宁可作为一个人被其他人正派而自然地漠视。 比起办公室里的同事们把我看成特别不同的人来说没弃休么要篇让我长陆我崛让他们 的讥嘲不致于弄成这种味道。我想让他们行行好,把我看成是同他们一样的人。我想把他们 不再视我为异教这件事,永远钉死在十字架上。比起那些圣徒和隐士当中有案可查的殉难来 说,还有更加微不足道的殉难。世上有智力的苦刑,一如世上有身体和欲望。而另一些苦刑, 包含着苦刑本身的妖烧诱人。正常正常对于我们来说像一个家,像日常生活中的一位母亲。 对伟大诗歌和崇高志向的高高群山作出一次长长的进入之后,在领略过出类技革和神奇莫测 的险峻风光之后,最甜蜜的事情当然是品尝生活中一切温暖,返回快乐的傻笑和玩笑充斥其 间的小酒店,混在这些人中间一起胡吹海喝,对我们受赐的宇宙心满意足,像他们一样冒傻 气,恰如上帝把我们造就的模样。 我们所撇下的人还在艰难爬山,然而爬到山顶时,他们却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不会使我震惊的是,人们会说,比起一些生活和成就都只能平平的其他人来说,我视之 为疯狂和愚笨的人要更好一些。他们一旦发作起来疯癫会不平常的猛烈;妄想狂会有一种超 乎绝大多数常人的推理能力;走火火魔的宗教狂热比任何煽动家(几乎)更能够吸引成群的 信徒,更能够给予追随者们一种煽动家从来给予不了的内在力量。但所有这些都证明不了什 么,只能证明疯狂就是疯狂。我宁可不知道美丽鲜花可以比附成一种荒野之地的胜利,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