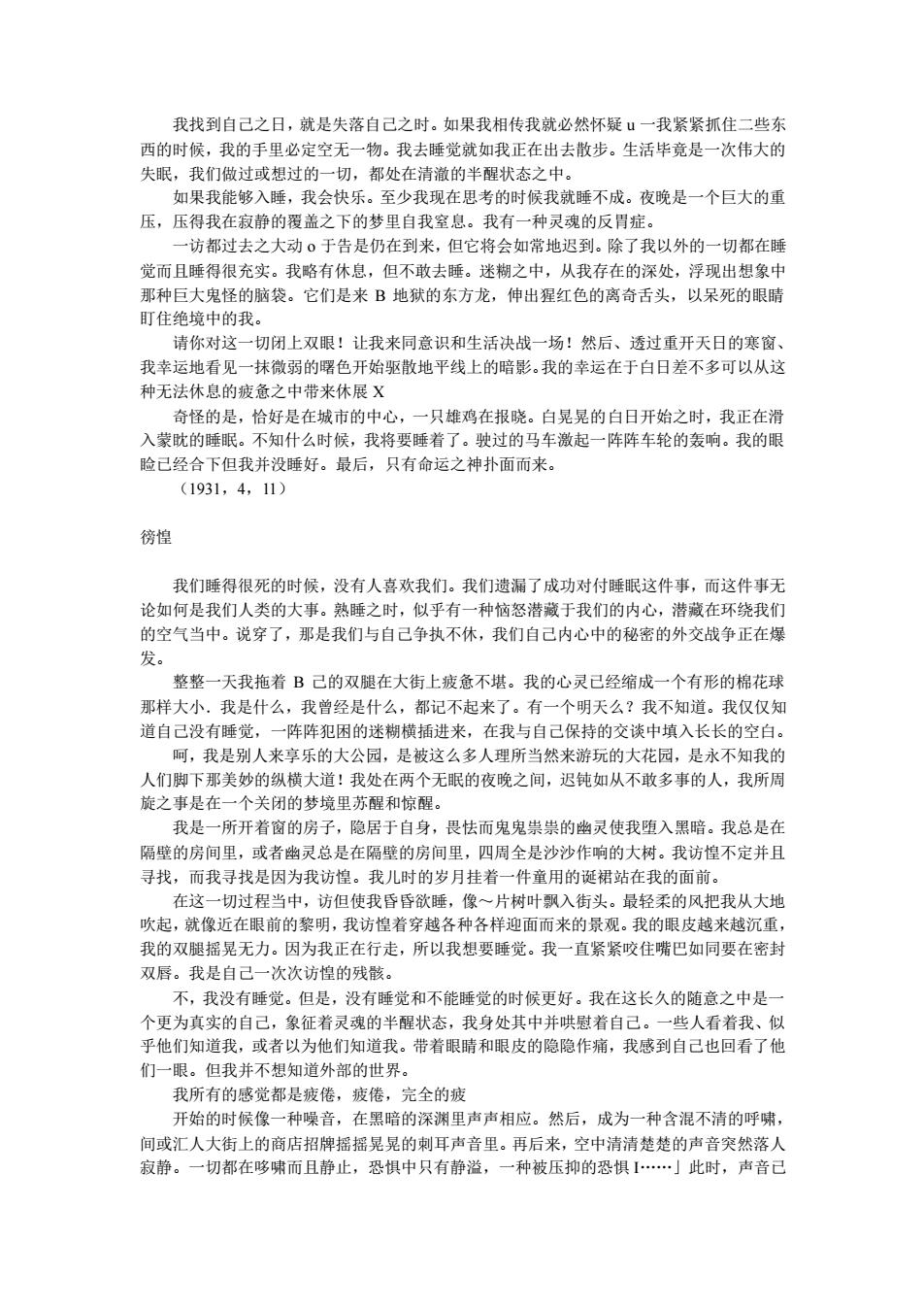
我找到自己之日,就是失落自己之时。如果我相传我就必然怀疑u一我紧紧抓住二些东 西的时候,我的手里必定空无一物。我去睡觉就如我正在出去散步。生活毕竞是一次伟大的 失眠,我们做过或想过的 切,都处在清澈的半醒状态之中 如果我能够入睡,我会快乐。至少我现在思考的时候我就睡不成, 夜晚是一个巨大的重 压,压得我在寂静的覆盖之下的梦里自我室总。我有一种灵魂的反胃症。 一访都时去之大动。于告是仍在到来,但它将会如常地识到。除了我以外的一切都在睡 觉而且睡得很充实。我略有休总,但不敢去睡。迷糊之中,从我存在的深处,浮现出想象中 那种巨大鬼怪的脑袋。它们是来B地狱的东方龙 伸出程红色的离奇舌头,以呆死的眼睛 盯住绝境中的我 请你对这一切闭上双眼:让我来同意识和生活决战一场:然后、透过重开天日的寒窗、 我幸运地看见一抹微弱的曙色开始驱散地平线上的暗影。我的幸运在于白日差不多可以从这 种无法休息的疲惫之中带来休展X 奇怪的是,恰好是在城市的中心 一只雄鸡在报晓。白晃晃的白日开始之时,我正在滑 入蒙耽的睡 不知什么时候,我将要睡若 驶过的马车激起 阵阵车轮的轰响。我的围 睑己经合下但我并没睡好。最后,只有命运之神扑面而来。 (1931,4,11) 徬惶 我们睡得很死的时候,没有人喜欢我们。我们遗漏了成功对付睡眼这件事,而这件事无 论如何是我们人类的大事。熟睡之时,似乎有一种恼怒潜藏于我们的内心,潜藏在环绕我们 的空气当中。说穿了,那是我们与自己争执不休,我们自己内心中的秘密的外交战争正在爆 发。 整整一天我拖若B已的双龈在大街上备不。我的心,灵已经缩成一个有形的棉花 那样大小。我是什么,我曾经是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有 一个明天么 我不知道。我仅仅知 道自己没有睡觉, 阵阵犯困的送湖横插进米,在我与自己保持的交谈中填入长长的空白: 呵,我是别人来享乐的大公园,是被这么多人理所当然来游玩的大花园,是永不知我的 人们脚下那美妙的纵横大道:我处在两个无眠的夜晚之间,迟纯如从不敢多事的人,我所周 旋之事是在一个关闭的梦境里苏醒和惊程。 我是一所开窗的房 子,隐居于自身,畏怯而鬼鬼祟祟的幽灵使我堕入黑暗。我总是在 隔壁的房间里,或者幽灵总是在隔壁的房间里,四周全是沙沙作响的大树。我访惶不定并且 寻找,而我寻找是因为我访惶。我儿时的岁月挂着一件童用的诞裙站在我的面前。 在这一切过程当中,访但使我昏昏欲睡,像~片树叶飘入街头。最轻柔的风把我从大地 吹起,就像近在眼前的黎明,我访怕着穿越各种各样迎面而来的景观。我的眼皮越来越沉重, 我的双腿摇晃无力。因为我正在行走,所以我想要睡觉。我一直紧紧咬住嘴巴如同要在密封 双唇 ,我是自己 次次访惶的残骸 不,我没有睡觉。但是,没有睡觉和不能睡觉的时候更好。我在这长久的随意之中是 个更为真实的自己,象征着灵魂的半醒状态,我身处其中并哄慰着自己。一些人看着我、似 乎他们知道我,或者以为他们知道我。带若眼晴和眼皮的隐隐作痛,我感到自己也回看了他 们一眼。但我并不想知道外部的世 我所有的感觉都是被倦。 疲倦 完全的 开始的时候像一种噪音,在黑暗的深渊里声声相应。然后,成为一种含混不清的呼啸 间或汇人大街上的商店招牌摇摇晃晃的刺耳声音里。再后来,空中清清楚楚的声音突然落人 寂静。一切都在哆啸而且静止,恐惧中只有静溢,一种被压抑的恐惧·」此时,声音已
我找到自己之日,就是失落自己之时。如果我相传我就必然怀疑 u 一我紧紧抓住二些东 西的时候,我的手里必定空无一物。我去睡觉就如我正在出去散步。生活毕竟是一次伟大的 失眠,我们做过或想过的一切,都处在清澈的半醒状态之中。 如果我能够入睡,我会快乐。至少我现在思考的时候我就睡不成。夜晚是一个巨大的重 压,压得我在寂静的覆盖之下的梦里自我窒息。我有一种灵魂的反胃症。 一访都过去之大动 o 于告是仍在到来,但它将会如常地迟到。除了我以外的一切都在睡 觉而且睡得很充实。我略有休息,但不敢去睡。迷糊之中,从我存在的深处,浮现出想象中 那种巨大鬼怪的脑袋。它们是来 B 地狱的东方龙,伸出猩红色的离奇舌头,以呆死的眼睛 盯住绝境中的我。 请你对这一切闭上双眼!让我来同意识和生活决战一场!然后、透过重开天日的寒窗、 我幸运地看见一抹微弱的曙色开始驱散地平线上的暗影。我的幸运在于白日差不多可以从这 种无法休息的疲惫之中带来休展 X 奇怪的是,恰好是在城市的中心,一只雄鸡在报晓。白晃晃的白日开始之时,我正在滑 入蒙眈的睡眠。不知什么时候,我将要睡着了。驶过的马车激起一阵阵车轮的轰响。我的眼 睑已经合下但我并没睡好。最后,只有命运之神扑面而来。 (1931,4,11) 徬惶 我们睡得很死的时候,没有人喜欢我们。我们遗漏了成功对付睡眠这件事,而这件事无 论如何是我们人类的大事。熟睡之时,似乎有一种恼怒潜藏于我们的内心,潜藏在环绕我们 的空气当中。说穿了,那是我们与自己争执不休,我们自己内心中的秘密的外交战争正在爆 发。 整整一天我拖着 B 己的双腿在大街上疲惫不堪。我的心灵已经缩成一个有形的棉花球 那样大小.我是什么,我曾经是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有一个明天么?我不知道。我仅仅知 道自己没有睡觉,一阵阵犯困的迷糊横插进来,在我与自己保持的交谈中填入长长的空白。 呵,我是别人来享乐的大公园,是被这么多人理所当然来游玩的大花园,是永不知我的 人们脚下那美妙的纵横大道!我处在两个无眠的夜晚之间,迟钝如从不敢多事的人,我所周 旋之事是在一个关闭的梦境里苏醒和惊醒。 我是一所开着窗的房子,隐居于自身,畏怯而鬼鬼祟祟的幽灵使我堕入黑暗。我总是在 隔壁的房间里,或者幽灵总是在隔壁的房间里,四周全是沙沙作响的大树。我访惶不定并且 寻找,而我寻找是因为我访惶。我儿时的岁月挂着一件童用的诞裙站在我的面前。 在这一切过程当中,访但使我昏昏欲睡,像~片树叶飘入街头。最轻柔的风把我从大地 吹起,就像近在眼前的黎明,我访惶着穿越各种各样迎面而来的景观。我的眼皮越来越沉重, 我的双腿摇晃无力。因为我正在行走,所以我想要睡觉。我一直紧紧咬住嘴巴如同要在密封 双唇。我是自己一次次访惶的残骸。 不,我没有睡觉。但是,没有睡觉和不能睡觉的时候更好。我在这长久的随意之中是一 个更为真实的自己,象征着灵魂的半醒状态,我身处其中并哄慰着自己。一些人看着我、似 乎他们知道我,或者以为他们知道我。带着眼睛和眼皮的隐隐作痛,我感到自己也回看了他 们一眼。但我并不想知道外部的世界。 我所有的感觉都是疲倦,疲倦,完全的疲 开始的时候像一种噪音,在黑暗的深渊里声声相应。然后,成为一种含混不清的呼啸, 间或汇人大街上的商店招牌摇摇晃晃的刺耳声音里。再后来,空中清清楚楚的声音突然落人 寂静。一切都在哆啸而且静止,恐惧中只有静溢,一种被压抑的恐惧 I.」此时,声音已

经完全消失」 只有风声,仅仅是风。我昏昏欲睡地注意到,门在怎样拉紧铰链,窗上的玻璃是怎样呻 吟着作出抗拒 我没有入睡,有一半的存在。 意识的沙沙声升浮到了表面。我睡意沉沉,但是无意识仍在纠貔着我。我没有睡。风 声.我醒来又滑回睡眠,似乎还没有睡着。有一种大声和可怕喧嚣的图景在我对自己的知 解之外。我小心翼翼地享用着入睡的可能性。我事实上在入睡,只是不知道我在那样做。在 切我们判定为噪音的东西 还有 种声音预告 切声音的终 我勉强听至 自己胃和心脏的声音时,黑暗在呼啸。运动是沉睡的形式如果我别无所长,我起码还存有自 由感觉中无穷无尽的新奇。 今天,走在阿尔玛达大街上,我突然注意到前面一个行人的背影:一个普通人的普通背 影,这位仍然的·过路青红刻k素茄复援,左手提着一个陈旧的手提箱,右手里的雨伞尖, 随着他的步子在人行道上 我突然对此人若有所感,侧然心动。我的侧然事关人类的普通性,事关 个正在上班途 中的一家之长的庸常日子,事关他幸福而驯良的家庭,事关他毫无疑义地靠悲哀和愉悦来成 就的生活,事关某种无思无虑生活状态的单纯,事关那一个衣冠背影的动物性自然。 我再一次打量那个人的背影,那个早现我如上思绪的窗口。 当你看到某个人在眼前沉睡,极其相同的感觉也会油然而生。人们睡者了,便成为了孩 子,也许这是因为 沉睡者无法作恶,甚至无 成知白 三的存在。靠自然的魔法 最罪恶的 最根深帝固的自大狂也可以在睡眠中露出圣洁之容。杀死一个孩子,与杀死一个熟睡中的人 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可以体察到的差别。 这是一个人沉睡了的背影。与我保持着同等速度并且走在前面的这个人,身体的每一部 分都在沉睡。他无意识地移动。他无意识地活者。他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沉睡不醒。生活的 切不过是一个梦,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所为, 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所愿,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月 知。作为命运水远的孩子,我们把自己的生活都睡掉了。就因为这样,当我带着这种感觉进 入思考,我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处于幼儿期的人类,对过着梦游一般生活的人们 体验到一片巨大无边的侧隐。 就在此刻 一种无法确定结论而且远虑闻如的纯粹博爱主义席卷而来,使我闲于侧隐 如同以上帝之眼俯瞰众生。以一种仅仅对于意识性活物的同情,我关注着每一个人。可怜的 人, 可怜的人类。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切到底是什么? 从我们肺部的一次简单呼吸,到城市的建立,到帝国疆域的确定,我把生活中的一切运 动、 一切能动之力都视为沉嫌的一种形式,视为一些梦,或者是一些不期而至的周期性短暂 停歌,介乎现实和下一种现实之间,介乎绝对意义中的一个日子和下一个日子之间。我像抽 象的母性市句,夜里偷务官巡所有好孩子都环孩子的床,对沉睡中的我这些孩子一视同 在我对他们的侧隐里 右 一种对无限存在性的宽厚 我的打量匆匆从前面那个背影移开,转向其他的人,那些大街上的行人。这些我跟随着 的背影,同样属于一些无意识的存在,同样在我的意识里激起荒诞而寒冷的侧隐。上班路上 闲谈的工厂姑娘们,上班途中大笑的青年职员们,来买归来的负重女仆们,跑开了当天第 超弟事的小伙子们 一所有这些人都像他:只不时是一些玩偶,被同一个隐形存在物手中的 拉线所操纵,只不过是被挂若不同面孔和不同肢体的一种无意识。他们做出了意识的所有外 表,但它们不是意识性存在物的意识,因此不是意识。无论他们聪明还是愚叁 事买上他们 同样愚蠢。无论他们年轻还是衰老,他们都共有若同样的年龄。无论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们都同属于非存在的性别。偷窥很有些日子了,我遇见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在某一个老地 方我天天不得不与之混在一起的人,取得了象征的意义,无论他们与我疏远还是交往,他们
经完全消失。 只有风声,仅仅是风。我昏昏欲睡地注意到,门在怎样拉紧铰链,窗上的玻璃是怎样呻 吟着作出抗拒。 我没有入睡,有一半的存在。 意识的沙沙声升浮到了表面。我睡意沉沉,但是无意识仍在纠缠着我。我没有睡。风 声.我醒来又滑回睡眠,似乎还没有睡着。有一种大声和可怕喧嚣的图景在我对自己的知 解之外。我小心翼翼地享用着入睡的可能性。我事实上在入睡,只是不知道我在那样做。在 一切我们判定为噪音的东西之外,总还有另外一种声音预告一切声音的终结。当我勉强听到 自己胃和心脏的声音时,黑暗在呼啸。运动是沉睡的形式如果我别无所长,我起码还存有自 由感觉中无穷无尽的新奇。 今天,走在阿尔玛达大街上,我突然注意到前面一个行人的背影:一个普通人的普通背 影,这位仍然的·过路青红刻 k 素茄复援,左手提着一个陈旧的手提箱,右手里的雨伞尖, 随着他的步子在人行道上一顿一顿。 我突然对此人若有所感,侧然心动。我的侧然事关人类的普通性,事关一个正在上班途 中的一家之长的庸常日子,事关他幸福而驯良的家庭,事关他毫无疑义地靠悲哀和愉悦来成 就的生活,事关某种无思无虑生活状态的单纯,事关那一个衣冠背影的动物性自然。 我再一次打量那个人的背影,那个呈现我如上思绪的窗口。 当你看到某个人在眼前沉睡,极其相同的感觉也会油然而生。人们睡着了,便成为了孩 子,也许这是因为沉睡者无法作恶,甚至无法感知自己的存在。靠着自然的魔法,最罪恶的、 最根深蒂固的自大狂也可以在睡眠中露出圣洁之容。杀死一个孩子,与杀死一个熟睡中的人, 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可以体察到的差别。 这是一个人沉睡了的背影。与我保持着同等速度并且走在前面的这个人,身体的每一部 分都在沉睡。他无意识地移动。他无意识地活着。他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沉睡不醒。生活的 一切不过是一个梦,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所为,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所愿,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所 知。作为命运永远的孩子,我们把自己的生活都睡掉了。就因为这样,当我带着这种感觉进 入思考,我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处于幼儿期的人类,对过着梦游一般生活的人们, 体验到一片巨大无边的恻隐。 就在此刻,一种无法确定结论而且远虑闻如的纯粹博爱主义席卷而来,使我困于恻隐, 如同以上帝之眼俯瞰众生。以一种仅仅对于意识性活物的同情,我关注着每一个人。可怜的 人,可怜的人类。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切到底是什么? 从我们肺部的一次简单呼吸,到城市的建立,到帝国疆域的确定,我把生活中的一切运 动、一切能动之力都视为沉睡的一种形式,视为一些梦,或者是一些不期而至的周期性短暂 停歇,介乎现实和下一种现实之间,介乎绝对意义中的一个日子和下一个日子之间。我像抽 象的母性市包,夜里偷务宣巡所有好孩子都坏孩子的床,对沉睡中的我这些孩子一视同仁。 在我对他们的恻隐里,有一种对无限存在性的宽厚。 我的打量匆匆从前面那个背影移开,转向其他的人,那些大街上的行人。这些我跟随着 的背影,同样属于一些无意识的存在,同样在我的意识里激起荒诞而寒冷的恻隐。上班路上 闲谈的工厂姑娘们,上班途中大笑的青年职员们,来买归来的负重女仆们,跑开了当天第一 超差事的小伙子们——所有这些人都像他:只不过是一些玩偶,被同一个隐形存在物手中的 拉线所操纵,只不过是被挂着不同面孔和不同肢体的一种无意识。他们做出了意识的所有外 表,但它们不是意识性存在物的意识,因此不是意识。无论他们聪明还是愚蠢,事实上他们 同样愚蠢。无论他们年轻还是衰老,他们都共有着同样的年龄。无论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们都同属于非存在的性别。偷窥很有些日子了,我遇见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在某一个老地 方我天天不得不与之混在一起的人,取得了象征的意义,无论他们与我疏远还是交往,他们

都会一起来构成隐秘的或预言式的书写,构成我生活虚幻的描摹。办公室成了一片纸页,人 们是纸上的词语。街道是一本书,相识者之间的寒暄,陌生者之间的遭遇,都是一些从不出 现在字典上 言说,然而我的理解勉强可以将其破 他们说话,他们交际,但这既不是他们自己在说话,也不是他们自己在交际,如同我说 的,他们是一些没有直接泄露出任何意思的词语,更确切地说,是让词义通过他们来澄露。 然而,以一种贫乏而模糊的视力,我仅仅能够大致弄明白他们是什么。那些窗户玻璃实 然出现在事物的表面,对于他们同时守护和播露的内在之物,显示起来将有所洗择」 我像一个听别人在谈论者色彩的人, 在知觉之外来理解这 有时候,走在大街上 我听到 私下里谈话的片 他们差不多总是关于另 一个女人 另一个男人,某个第三者的儿子,或者别的什么人的情人卜. ··单凭听到这些人类话语的 只鳞片爪,即便它们是最具意识的生命体所为,我也会被一种徒生厌恶的乏味以及一种在假 象中放逐的恐怖气昏脑袋,而且会突然认识到,自己是如何被别人狠狠地擦伤。我被地主和 其他佃户咒骂。因为我也是一个众多佃户中的一个,竟然可恶地透过仓库后面的窗子,从窗 栏中偷看了一下别人在雨中堆积于内院的垃 而那就是我的生活 潜在的宫殿 很多时候,我在帐本里持续记录若他人的帐目,还有自己缺失了的人生。当我从帐本里 抬起沉重的头,我感到一种生理上的恶心。这可能是因为我伏案太久,但不是帐目数字和清 阴所带来的问题。生活像一剂糟糕的药,使我佣出病来。然而,我从百大无边的澄明幻象中 看到,只要我真有力量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可以如此轻易地从沉闷中解脱。 我们通过行动来生活,也就是说通过意志来生活。我们这些人 天才或者乞丐们 本知道如何愿望的人,是一些分享着虚弱的弟兄。当我事实上仅仅是一个会计助理的时候, 我凭哪一点把自己叫作天才?C·韦尔德(1世纪葡萄牙诗人,见前注 -革者注)在疾生 面前宣称,自己是“诗人事尔德”,而不是作为商界职,员的“韦尔德先生”,这个时候的他 只不过是表现若酸腐的虚荣和无效的自夸。可怜的人,他从来就是“韦尔德先生”, 一个商 界职员而不是别的什么。诗人只有在死后才能诞生,因为只有在他死后,他的诗歌才会得至 欣赏 行动,是真正的智慧。我愿意成为我愿意成为的人。但是我必须愿望自己所愿望的东西 成功意味着己经成功,而不仅仅是潜在的成功。任何一大块土地都是宫殿的潜在可能,但是 如果还没建起来,宫殿在哪里?自我折腾我做者有关里斯本与卡斯凯什之间旅行的白日梦。 完去卡斯凯外那里为老板之自程的厂所房子付税。我急切地向往者来回各一个小时的旅行 让我有机会看看总是在改变着面容的伟大河流以及它的大西洋人海口。事实上 一路上我迷 失在抽象的思考里,我投出去的目光,并没有看见自己一直如此向往的河上风光。回来的 路上,我又迷失在对这种感受的分析之中。我不能描述旅行中哪怕最小的细节,以及我看见 过的最小片断。我的健忘和自我折腾只露下这些纸页,不知道比起各我折腾来流它们是好 些或者品师她一些 火车缓缓开进了车站,我已经到达了里斯本,还没有任何结论。棱上的琴声我第 次来 到里斯本的时候,曾经听到楼上飘来一个人在钢琴上弹泰音阶的声音,是一个我没有见到过 的小姑娘在作单调的钢琴练习。今天,通过一个我不能明了的内化过程,我居然发现如果我 走进心灵的最深处,这些重复的音阶仍然清晰可闻。弹奏者曾经是一个小姑娘,而现在叫作
都会一起来构成隐秘的或预言式的书写,构成我生活虚幻的描摹。办公室成了一片纸页,人 们是纸上的词语。街道是一本书,相识者之间的寒暄,陌生者之间的遭遇,都是一些从不出 现在字典上的言说,然而我的理解勉强可以将其破译。 他们说话,他们交际,但这既不是他们自己在说话,也不是他们自己在交际,如同我说 的,他们是一些没有直接泄露出任何意思的词语,更确切地说,是让词义通过他们来泄露。 然而,以一种贫乏而模糊的视力,我仅仅能够大致弄明白他们是什么。那些窗户玻璃突 然出现在事物的表面,对于他们同时守护和泄露的内在之物,显示起来将有所选择。 我像一个听别人在谈论着色彩的盲人,在知觉之外来理解这一切。 有时候,走在大街上,我听到一些私下里谈话的片断,他们差不多总是关于另一个女人, 另一个男人,某个第三者的儿子,或者别的什么人的情人卜.··单凭听到这些人类话语的 只鳞片爪,即便它们是最具意识的生命体所为,我也会被一种徒生厌恶的乏味以及一种在假 象中放逐的恐怖气昏脑袋,而且会突然认识到,自己是如何被别人狠狠地擦伤。我被地主和 其他佃户咒骂。因为我也是一个众多佃户中的一个,竟然可恶地透过仓库后面的窗子,从窗 栏中偷看了一下别人在雨中堆积于内院的垃圾,而那就是我的生活。 潜在的宫殿 很多时候,我在帐本里持续记录着他人的帐目,还有自己缺失了的人生。当我从帐本里 抬起沉重的头,我感到一种生理上的恶心。这可能是因为我伏案太久,但不是帐目数字和清 醒所带来的问题。生活像一剂糟糕的药,使我闹出病来。然而,我从巨大无边的澄明幻象中 看到,只要我真有力量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可以如此轻易地从沉闷中解脱。 我们通过行动来生活,也就是说通过意志来生活。我们这些人——天才或者乞丐们—— 本知道如何愿望的人,是一些分享着虚弱的弟兄。当我事实上仅仅是一个会计助理的时候, 我凭哪一点把自己叫作天才?C·韦尔德(l 世纪葡萄牙诗人,见前注——译者注)在医生 面前宣称,自己是“诗人韦尔德”,而不是作为商界职,员的“韦尔德先生”,这个时候的他, 只不过是表现着酸腐的虚荣和无效的自夸。可怜的人,他从来就是“韦尔德先生”,一个商 界职员而不是别的什么。诗人只有在死后才能诞生,因为只有在他死后,他的诗歌才会得到 欣赏。 行动,是真正的智慧。我愿意成为我愿意成为的人。但是我必须愿望自己所愿望的东西。 成功意味着已经成功,而不仅仅是潜在的成功。任何一大块土地都是宫殿的潜在可能,但是 如果还没建起来,宫殿在哪里?自我折腾我做着有关里斯本与卡斯凯什之间旅行的白日梦。 完去卡斯凯外那里为老板之自程的厂所房子付税。我急切地向往着来回各一个小时的旅行, 让我有机会看看总是在改变着面容的伟大河流以及它的大西洋人海口。事实上,一路上我迷 失在抽象的思考里,我投出去的目光,并没有看见自己一直如此向往的河上风光。回来的一 路上,我又迷失在对这种感受的分析之中。我不能描述旅行中哪怕最小的细节,以及我看见 过的最小片断。我的健忘和自我折腾只露下这些纸页,不知道比起各我折腾来流它们是好一 些或者是更糟一些。 火车缓缓开进了车站,我已经到达了里斯本,还没有任何结论。楼上的琴声我第一次来 到里斯本的时候,曾经听到楼上飘来一个人在钢琴上弹奏音阶的声音,是一个我没有见到过 的小姑娘在作单调的钢琴练习。今天,通过一个我不能明了的内化过程,我居然发现如果我 走进心灵的最深处,这些重复的音阶仍然清晰可闻。弹奏者曾经是一个小姑娘,而现在叫作

什么什么小姐,或者已经死了,在茂盛生长着森森柏树的白色墓地里长眠。 当时,我是一个孩子,现在我不是。在我的记忆里,虽然现在的声音与当时现实中的声 音一模一样,当它从幽潜之处升高的时候 仍然长期显现为同样缓缓的音阶 还有同样单调 的韵律。不论我是感觉它还是思考它的时候,我都难免一种复杂而痛苦的悲 我不会为自己失去童年而哭泣。但我为一切事情哭泣,因为它们与我的童年有关,因为 它们将要失去。用楼上偶尔重现的音阶重复来使我头痛的东西,是如此惊人的遥远和莫名的 钢琴之声,它是时间玄秘地飞逝 一它不是那种具体而且直接影响于我的飞逝,是虚无的全 部神秘性事实, 消失于音锤 次敲出的音符。这种音符不是什么音乐,倒不如说是怀 旧和向往的一种混合,潜藏在我记忆荒谬的深处。 它在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客厅里缓缓地升起,我甚至到今天也不知道的孩子,手指错落地 弹奏着同样已经消失了的重复音阶。我张望,我看见,我在眼中重构情景。一幕楼上公寓的 家庭生活图量,充满着一种它当年缺乏的激情,从我闲或的冥想中浮现出来 我猜想,虽然我仅仅是这一切的 个载体 虽然我感受到的向往既不真正属于我,也术 见得真有什么玄秘,但作为一段截取来的情感 它属于不可知道的第 三者 ,对于我来说,这 些情感是文学性的,就像维埃拉(葡萄牙17世纪伟大的语言家和古典散文作家之 译者 注)说的.是文学性的。我的伤害和痛苦来自自己想象的感受,它们仅仅存在于我的想象中 还有我对于他者思想或情感性的怀旧之中。这种怀旧留给我盈目的泪水 随者一种生成于世界深处的坚定,随者 一种著研究的形而 上坚守,那人练习钢琴音阶 的声音 一直上下回响 我 忆以至人骨 唤出了他 的古代街道 ,与今天的街道大同 小异。它们是死者通过不存在的透明之墙向我说话。它们是我对于做过或没有做过的一切的 澳邮员d武是深夜里奔涌伪激输水是静静房子里楼下的喧器。 在我的脑子里,我感受到一片尖啸。我想停止什么,想打碎什么,想中断双重无形的折 磨,中断这不可能录下来的弹奏,在我脑子里同时又是在他人房子里的弹奏。我想命令自己 的灵魂中止,逃出我的躯壳,离开我的身体飘然独行 听着这种音乐我会渐渐疯狂。 但至 最后我重归故我,带着我极其敏感的思绪,带着我薄纸般皮肤下明晰可见的满布神觉还有记 忆中的音阶,弹奏在这一台内化的、可恶的钢琴上。 就像我大脑里的某个部分己经不听指挥了,音阶一直在弹奏,从下面向我飘来,从上面 向我飘来,从我在里斯本的第一所房子里向我飘来 (1931.12.3) 活者使我迷醉 我梦境纷纷的时候,总是自己走到大街上去的时候,眼睛张开,却仍然安然无恙地被梦 培句意。我很得意,有那么多人无法察微我无魂的白动。我走过每天的生活,仍可以握住 我星空中太太的手。我走在街上的脚步 ,也可以与我梦中想象的种种模糊设计协调一致。我 还能在街上横冲直闯:不会跌改。我应该有所反应的时候决不会误事。我存在着。 我常常不必观察自己下一步的去处以避开汽车和行人,在这样的时候,我不必向任何人 问话也不必拐人近处的门道,我让自己更多地像一只纸船漂流在梦想的海洋上。我重访死去 的幻象,让这些幻象温暖若我关于早忌的增饿成觉,以及在卡车声中卷入生活的成觉 些卡车把菜送到市场上去 在这里,在生活之中,梦想成为 一个巨大的电影银幕。我走人贝克萨区的 一条梦境之街 走入其中的梦幻化现实,我的双眼被温柔地蒙上一道虚假记忆的白眼罩。我成为了一位航海 者,穿起无法知解的我。我占领了自己甚至从来没有造访过的地方。像一抹清新的微风,我 在这种催眠的状态中走着,引颈向前,大踏步走在不可能的存在之上
什么什么小姐,或者已经死了,在茂盛生长着森森柏树的白色墓地里长眠。 当时,我是一个孩子,现在我不是。在我的记忆里,虽然现在的声音与当时现实中的声 音一模一样,当它从幽潜之处升高的时候,仍然长期呈现为同样缓缓的音阶,还有同样单调 的韵律。不论我是感觉它还是思考它的时候,我都难免一种复杂而痛苦的悲伤。 我不会为自己失去童年而哭泣。但我为一切事情哭泣,因为它们与我的童年有关,因为 它们将要失去。用楼上偶尔重现的音阶重复来使我头痛的东西,是如此惊人的遥远和莫名的 钢琴之声,它是时间玄秘地飞逝——它不是那种具体而且直接影响于我的飞逝,是虚无的全 部神秘性事实,消失于音锤一次又一次敲出的音符。这种音符不是什么音乐,倒不如说是怀 旧和向往的一种混合,潜藏在我记忆荒谬的深处。 它在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客厅里缓缓地升起,我甚至到今天也不知道的孩子,手指错落地 弹奏着同样已经消失了的重复音阶。我张望,我看见,我在眼中重构情景。一幕楼上公寓的 家庭生活图景,充满着一种它当年缺乏的激情,从我困惑的冥想中浮现出来。 我猜想,虽然我仅仅是这一切的一个载体,虽然我感受到的向往既不真正属于我,也未 见得真有什么玄秘,但作为一段截取来的情感,它属于不可知道的第三者。对于我来说,这 些情感是文学性的,就像维埃拉(葡萄牙 17 世纪伟大的语言家和古典散文作家之——译者 注)说的,是文学性的。我的伤害和痛苦来自自己想象的感受,它们仅仅存在于我的想象中, 还有我对于他者思想或情感性的怀旧之中。这种怀旧留给我盈目的泪水。 随着一种生成于世界深处的坚定,随着一种苦苦研究的形而上坚守,那人练习钢琴音阶 的声音一直上下回响于我记忆以至人骨。它唤出了他人通过的古代街道,与今天的街道大同 小异。它们是死者通过不存在的透明之墙向我说话。它们是我对于做过或没有做过的一切的 澳邮员 d 武是深夜里奔涌伪激输水是静静房子里楼下的喧嚣。 在我的脑子里,我感受到一片尖啸。我想停止什么,想打碎什么,想中断双重无形的折 磨,中断这不可能录下来的弹奏,在我脑子里同时又是在他人房子里的弹奏。我想命令自己 的灵魂中止,逃出我的躯壳,离开我的身体飘然独行——听着这种音乐我会渐渐疯狂。但到 最后我重归故我,带着我极其敏感的思绪,带着我薄纸般皮肤下明晰可见的满布神觉还有记 忆中的音阶,弹奏在这一台内化的、可恶的钢琴上。 就像我大脑里的某个部分已经不听指挥了,音阶一直在弹奏,从下面向我飘来,从上面 向我飘来,从我在里斯本的第一所房子里向我飘来。 (1931,12,3) 活着使我迷醉 我梦境纷纷的时候,总是自己走到大街上去的时候,眼睛张开,却仍然安然无恙地被梦 境包藏。我很得意,有那么多人无法察觉我无魂的自动。我走过每天的生活,仍然可以握住 我星空中太太的手。我走在街上的脚步,也可以与我梦中想象的种种模糊设计协调一致。我 还能在街上横冲直闯:不会跌跤。我应该有所反应的时候决不会误事。我存在着。 我常常不必观察自己下一步的去处以避开汽车和行人,在这样的时候,我不必向任何人 问话也不必拐人近处的门道,我让自己更多地像一只纸船漂流在梦想的海洋上。我重访死去 的幻象,让这些幻象温暖着我关于早晨的增俄感觉,以及在卡车声中卷入生活的感觉——这 些卡车把菜送到市场上去。 在这里,在生活之中,梦想成为一个巨大的电影银幕。我走人贝克萨区的一条梦境之街, 走入其中的梦幻化现实,我的双眼被温柔地蒙上一道虚假记忆的白眼罩。我成为了一位航海 者,穿越无法知解的我。我占领了自己甚至从来没有造访过的地方。像一抹清新的微风,我 在这种催眠的状态中走着,引颈向前,大踏步走在不可能的存在之上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迷醉于各各不同的事情。有一件事足以迷醉我,那就是活着。我豪 饮自己流动的感受但决不会迷做一牧果眼下到了回去干活的时间,走向办公室的我恰如他 人·如果下没有这回事,我 :一决恰如他人。我不折不扣与他们 同。但在这个雷同的后面,我偷偷地把星星散布于自己个人的天空,在那里创造我的无限 模拟自己我总是生活在当前。我对于未来一无所知,也不再有一个过去。未来以千万种可能 性压迫者我,而过去以虚无的现实压迫者我。我既没有对未来的希望,也没有对过去的向往。 直到现在,生活与我愿望中它应有的方式如此经繁地相反:而我对它的所知':一直是 我 生能作出的 外部世界 生活只能为 劳的思里。我从来只不过是一个自己的残迹,自己的模拟。我过去的一切都并非我有心为之 其至与时夫某一一刻情成相联的怀旧成也不是。一个人的感受都是瞬间的,一日时去成为了 过去的一页,故事还在继续,但己经不是在这本书上。 水落碧潭的轻声,整齐草坪的聚绿 暮色中一·个公共花园 在这 为你给我的意识全部注入情感。我对生活的要求 过于得到一种感受,感到生活正在潮水般退到那些不可预见的黄昏中去,到其他孩子们在街 心幽暗花园中玩耍的声音中去。在头上,绿树高高的枝叶被古老的天空笼罩,而天空中的星 星刚刚开始重视。 (1930.6,13) 他身之感 独自思考使我自己同时成为了回声和深渊、一靠者对内心的深入,我分身无数、最开的 一光线的一点变化,一片枯叶的飘摇下落,从鲜花上测落下来的花瓣,墙那边的声 音或者说话者的脚步,与这些我假定自己在铜听若的一切在一起的,坏有向老农场半开的大 门, 一条走廊与月光下拥挤房舍相通的内院 所有这 一切,没 样属于我, 却受制于 种强烈愿望的死结,捆住了我敏感的思想。在这些各自的瞬间,我是他人。我在每一个界定 失误的印象里痛苦地使洛陷己。 我依靠不属于自己的这些印象而活着,挥霍着身分的放弃,身为自己的时候反而总有他 身之感。舞台我创造了自己各种不同的性格。我持续地创造它们。每一个梦想,一旦形成就 立即被另 一个来代替我做梦的人来体现 为了创造,我毁灭了自己。我将内心的生活外化得这样多,以至在内心中,现在我也只 能外化地存在。我是生活的舞台,有各种各样的演员登台面宜',演出看q门同的剧目已 秋天茫然的黄昏里,飘在辽阔天空中的一抹轻柔云彩,还有晚夏初秋时节一阵寒风苏醒,都 宣布了秋天的来临。树木还没有脱落它们的绿色或它们的叶子,也还没有依稀愁绪以伴随我 们任何有关外部世界的衰亡之感 这纯粹是因为,它反映着我们自己将来的衰亡。就像残 留的能量逐渐衰竭,某 ·类蛰伏之物还在尝试着最后的叁蠢欲动。呵,这些黄昏充满若如叫 痛苦的冷漠,秋天不是在世界里而是在我们内心中开始。 每一个秋天都让我们更接近我们最后的一个秋天,这一说也可用于刚刚过去的春天或夏 天,但秋天最能自然地提醒我们意识到一切事物的结束,提醒我们意识到美好季节里如此容 易忘却的事情。这还不是真正的秋天,空中还不见落叶的黄色或者天气的潮湿暗淡,而这种 景象最终要留给冬天。但是, 中愁思遥遥在望, 类似的哀伤也在人们的感觉神经里 整装上路,不论它多么模糊不清,人们感受着世间混杂的色彩,风中异样的音调,夜晚降临 之时一片古老的宁静,夜晚缓缓潜入宇宙不可回避的当下。 是的,我们都会要逝去,万事万物都会要逝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一个穿戴者感受和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迷醉于各各不同的事情。有一件事足以迷醉我,那就是活着。我豪 饮自己流动的感受但决不会迷做一牧果眼下到了回去干活的时间,走向办公室的我恰如他 人。如果眼下没有这回事,我就走到河边去看水流,再一决恰如他人。我不折不扣与他们雷 同。但在这个雷同的后面,我偷偷地把星星散布于自己个人的天空,在那里创造我的无限。 模拟自己我总是生活在当前。我对于未来一无所知,也不再有一个过去。未来以千万种可能 性压迫着我,而过去以虚无的现实压迫着我。我既没有对未来的希望,也没有对过去的向往。 直到现在,生活与我愿望中它应有的方式如此经繁地相反;而我对它的所知’;一直是 我对。于生活能够作出的假定。莫非将来它既不是我假定所在,也不是我的愿望所在,纯粹 是外部世界让我碰巧遭遇上的什么,甚至与我的意愿相违?重复我过去的生活只能是一种徒 劳的愿望。我从来只不过是一个自己的残迹,自己的模拟。我过去的一切都并非我有心为之, 甚至与过去某一刻情感相联的怀旧感也不是。一个人的感受都是瞬间的,一旦过去成为了翻 过去的一页,故事还在继续,但已经不是在这本书上。 城区树木简洁的暗影,水落碧潭的轻声,整齐草坪的翠绿——暮色中一个公共花园—— 在这一刻你对于我来说是整个宇宙,因为你给我的意识全部注入情感。我对生活的要求,莫 过于得到一种感受,感到生活正在潮水般退到那些不可预见的黄昏中去,到其他孩子们在街 心幽暗花园中玩耍的声音中去。在头上,绿树高高的枝叶被古老的天空笼罩,而天空中的星 星刚刚开始重视。 (1930,6,13) 他身之感 独自思考使我自己同时成为了回声和深渊、一靠着对内心的深入,我分身无数、最开的 一插曲——光线的一点变化,一片枯叶的飘摇下落,从鲜花上剥落下来的花瓣,墙那边的声 音或者说话者的脚步,与这些我假定自己在倾听着的一切在一起的,还有向老农场半开的大 门,一条走廊与月光下拥挤房舍相通的内院——所有这一切,没有一样属于我,却受制于某 种强烈愿望的死结,捆住了我敏感的思想。在这些各自的瞬间,我是他人。我在每一个界定 失误的印象里痛苦地使洛陷已·。 我依靠不属于自己的这些印象而活着,挥霍着身分的放弃,身为自己的时候反而总有他 身之感。舞台我创造了自己各种不同的性格。我持续地创造它们。每一个梦想,一旦形成就 立即被另一个来代替我做梦的人来体现。 为了创造,我毁灭了自己。我将内心的生活外化得这样多,以至在内心中,现在我也只 能外化地存在。我是生活的舞台,有各种各样的演员登台面 n 宜’,演出看 q 门同的剧目已 秋天茫然的黄昏里,飘在辽阔天空中的一抹轻柔云彩,还有晚夏初秋时节一阵寒风苏醒,都 宣布了秋天的来临。树木还没有脱落它们的绿色或它们的叶子,也还没有依稀愁绪以伴随我 们任何有关外部世界的衰亡之感——这纯粹是因为,它反映着我们自己将来的衰亡。就像残 留的能量逐渐衰竭,某一类蛰伏之物还在尝试着最后的蠢蠢欲动。呵,这些黄昏充满着如此 痛苦的冷漠,秋天不是在世界里而是在我们内心中开始。 每一个秋天都让我们更接近我们最后的一个秋天,这一说也可用于刚刚过去的春天或夏 天,但秋天最能自然地提醒我们意识到一切事物的结束,提醒我们意识到美好季节里如此容 易忘却的事情。这还不是真正的秋天,空中还不见落叶的黄色或者天气的潮湿暗淡,而这种 景象最终要留给冬天。但是,有一种愁思遥遥在望,一些类似的哀伤也在人们的感觉神经里 整装上路,不论它多么模糊不清,人们感受着世间混杂的色彩,风中异样的音调,夜晚降临 之时一片古老的宁静,夜晚缓缓潜入宇宙不可回避的当下。 是的,我们都会要逝去,万事万物都会要逝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一个穿戴着感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