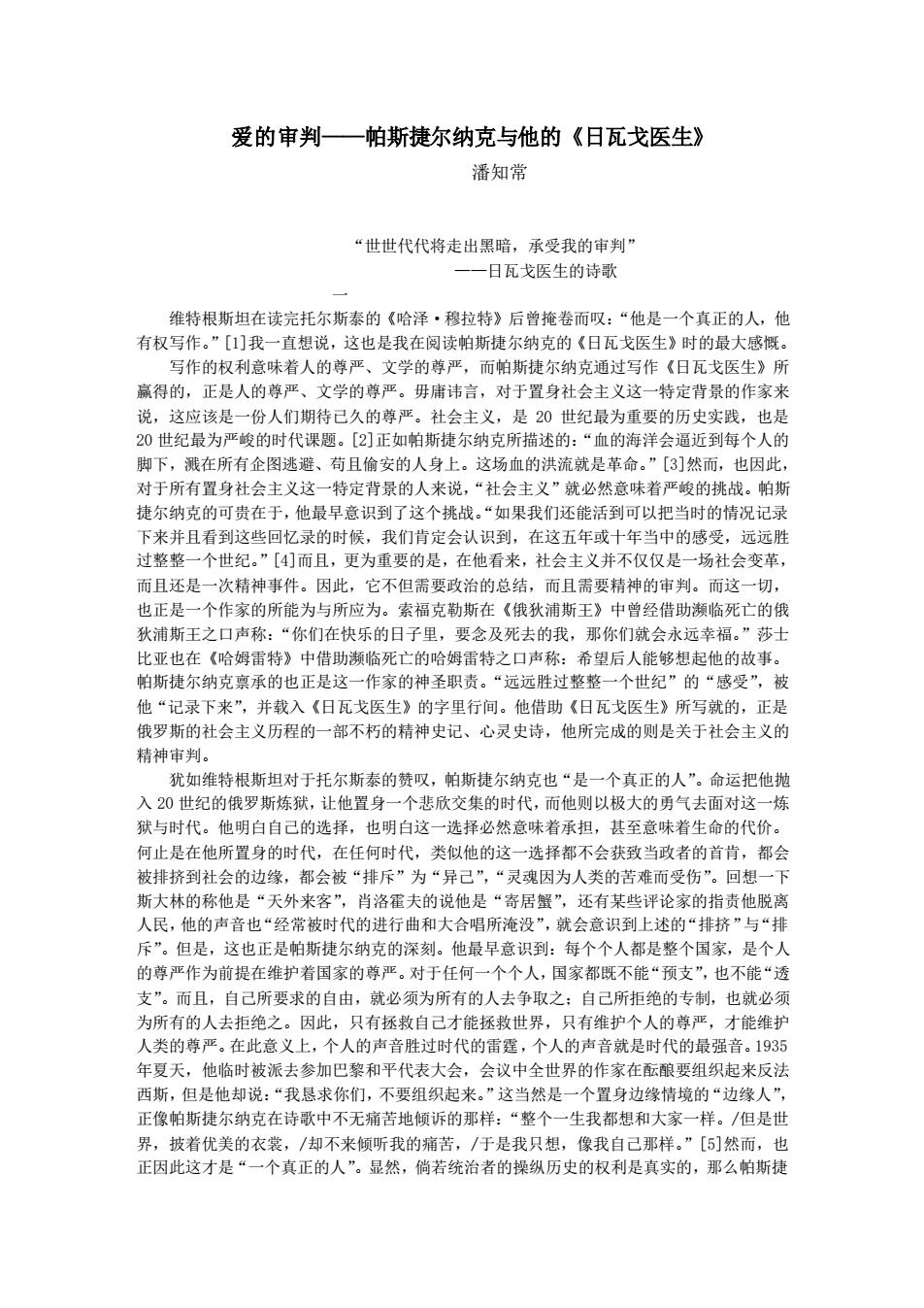
爱的审判一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 潘知常 “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 一日瓦戈医生的诗歌 维特根斯坦在读完托尔斯素的《哈泽·穆拉特》后曾掩卷而叹:“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 有权写作。”[]我一直想说,这也是我在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时的最大感慨。 写作的权利意味者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而帕斯捷尔纳克通过写作《日瓦戈医生》所 赢得的,正是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册唐讳言,对于置身社会主义这一特定背景的作家来 说,这应该是一份人们期待已久的尊严。社会主义,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历史实践,也是 20世纪最为严峻的时代课愚。[☑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描述的:血的海洋会通近到每个人的 脚下,溅在所有企图逃避、苟且偷安的人身上。这场血的洪流就是革命。”[3]然而,也因此, 对于所有置身社会主义这一特定背景的人来说,“社会主义”就必然意味着严峻的挑战。帕斯 捷尔纳克的可贵在于,他最早意识到了这个挑战。“如果我们还能活到可以把当时的情祝记录 下来并且看到这些回忆录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五年或十年当中的感受,远远 过整整一个世纪。”[4]而且,更为重要的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 场社会变 而且还是一次精神事件。因此,它不但需要政治的总结,而且需要精神的审判。而这一切, 也正是一个作家的所能为与所应为。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曾经借助濒临死亡的俄 狄浦斯王之口声称:“你们在快乐的日子里,要念及死去的我,那你们就会水远幸福。”莎士 比亚也在《哈姆雷特》中借助濒临死亡的哈姆雷特之口声称:希望后人能够想起他的故事。 帕斯捷尔纳克禀承的也正是这 作家的神圣职责 “远远胜过整整一个世 纪”的“感受”,被 他“记录下来”,并载入《日瓦戈医生》的字里行间。他借助《日瓦戈医生》所写就的,正是 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历程的一部不朽的精神史记、心灵史诗,他所完成的则是关于社会主义的 精神审判。 犹加维特根斯坦对于托尔斯素的裤叹,帕斯捷尔纳克也“是一个直正的人”。命运把他抛 入20世纪的俄罗斯炼狱,让他置身一个悲欣交集的时代,而他则以极大的勇气去面对这一炼 狱与时代。他明白自己的选择,也明白这一选择必然意味着承担,甚至意味着生命的代价 何止是在他所置身的时代,在任何时代,类似他的这一选择都不会获致当政者的首肯,都会 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都会被“排斥”为“异己”,“灵魂因为人类的苦难而受伤”。回想一下 斯大林的称他是“天外来客”,当洛霍夫的说他是“寄居蟹”,还有某些评论家的指责他脱离 人民,他的声音也“经常被时代的进行曲和大合唱所淹没”,就会意识到上述的“排挤”与“排 斥”。但是,这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深刻。他最早意识到: 每个个人都是整个国家,是个 的尊严作为前提在维护着国家的尊严。对于任何一个个人,国家都既不能“预支”,也不能“透 支”。而且,自己所要求的自由,就必须为所有的人去争取之:自己所拒绝的专制,也就必须 为所有的人去拒绝之。因此,只有拯救自己才能拯救世界,只有维护个人的尊严,才能维护 人类的尊严。在此意义上,个人的声音胜过时代的雷霆,个人的声音就是时代的最强音。1935 年夏天,他临时被派去参加巴黎和平代表大会 会议中 世界的作家在酝酿要组织起来反法 西斯,但是他却说:“我恳求你们,不要组织起来。”这当然是一个置身边缘情境的“边缘人 正像帕斯捷尔纳克在诗歌中不无痛苦地倾诉的那样:“整个一生我都想和大家一样。/但是世 界,披若优美的衣装,/却不来倾听我的痛苦,/于是我只想,像我自己那样。”[5]然而,也 正因此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显然,俏若统治者的操纵历史的权利是真实的,那么帕斯捷
爱的审判——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 潘知常 “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 ——日瓦戈医生的诗歌 一 维特根斯坦在读完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后曾掩卷而叹:“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 有权写作。”[1]我一直想说,这也是我在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时的最大感慨。 写作的权利意味着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而帕斯捷尔纳克通过写作《日瓦戈医生》所 赢得的,正是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毋庸讳言,对于置身社会主义这一特定背景的作家来 说,这应该是一份人们期待已久的尊严。社会主义,是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历史实践,也是 20 世纪最为严峻的时代课题。[2]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描述的:“血的海洋会逼近到每个人的 脚下,溅在所有企图逃避、苟且偷安的人身上。这场血的洪流就是革命。”[3]然而,也因此, 对于所有置身社会主义这一特定背景的人来说,“社会主义”就必然意味着严峻的挑战。帕斯 捷尔纳克的可贵在于,他最早意识到了这个挑战。“如果我们还能活到可以把当时的情况记录 下来并且看到这些回忆录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五年或十年当中的感受,远远胜 过整整一个世纪。”[4]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一场社会变革, 而且还是一次精神事件。因此,它不但需要政治的总结,而且需要精神的审判。而这一切, 也正是一个作家的所能为与所应为。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曾经借助濒临死亡的俄 狄浦斯王之口声称:“你们在快乐的日子里,要念及死去的我,那你们就会永远幸福。”莎士 比亚也在《哈姆雷特》中借助濒临死亡的哈姆雷特之口声称:希望后人能够想起他的故事。 帕斯捷尔纳克禀承的也正是这一作家的神圣职责。“远远胜过整整一个世纪”的“感受”,被 他“记录下来”,并载入《日瓦戈医生》的字里行间。他借助《日瓦戈医生》所写就的,正是 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历程的一部不朽的精神史记、心灵史诗,他所完成的则是关于社会主义的 精神审判。 犹如维特根斯坦对于托尔斯泰的赞叹,帕斯捷尔纳克也“是一个真正的人”。命运把他抛 入 20 世纪的俄罗斯炼狱,让他置身一个悲欣交集的时代,而他则以极大的勇气去面对这一炼 狱与时代。他明白自己的选择,也明白这一选择必然意味着承担,甚至意味着生命的代价。 何止是在他所置身的时代,在任何时代,类似他的这一选择都不会获致当政者的首肯,都会 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都会被“排斥”为“异己”,“灵魂因为人类的苦难而受伤”。回想一下 斯大林的称他是“天外来客”,肖洛霍夫的说他是“寄居蟹”,还有某些评论家的指责他脱离 人民,他的声音也“经常被时代的进行曲和大合唱所淹没”,就会意识到上述的“排挤”与“排 斥”。但是,这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深刻。他最早意识到:每个个人都是整个国家,是个人 的尊严作为前提在维护着国家的尊严。对于任何一个个人,国家都既不能“预支”,也不能“透 支”。而且,自己所要求的自由,就必须为所有的人去争取之;自己所拒绝的专制,也就必须 为所有的人去拒绝之。因此,只有拯救自己才能拯救世界,只有维护个人的尊严,才能维护 人类的尊严。在此意义上,个人的声音胜过时代的雷霆,个人的声音就是时代的最强音。1935 年夏天,他临时被派去参加巴黎和平代表大会,会议中全世界的作家在酝酿要组织起来反法 西斯,但是他却说:“我恳求你们,不要组织起来。”这当然是一个置身边缘情境的“边缘人”, 正像帕斯捷尔纳克在诗歌中不无痛苦地倾诉的那样:“整个一生我都想和大家一样。/但是世 界,披着优美的衣裳,/却不来倾听我的痛苦,/于是我只想,像我自己那样。”[5]然而,也 正因此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显然,倘若统治者的操纵历史的权利是真实的,那么帕斯捷

尔纳克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思想的权利就同样是真实的,而且是更加真实的。 作为自己所面对的一切的见证者与守夜人,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个人,伯斯捷尔纳克同样可 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下自己的名号 同样,也犹如维特根斯坦对于托尔斯泰的赞叹,帕斯捷尔纳克作为“ 一个真正的人”,也 “有权写作”。作为一个美学研究者。我一直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对于美学的痛斥而惭愧:“美 学并不存在。对我来说,似平美学不存在是对它的一种惩罚,因为它撒谎、妥协、迎合俗趣 屈尊俯就。因为它在对人一无所知的时候,胡扯专业问题。”[6]因为这无疑也是中国的美学 研究的通病 而帕斯捷尔纳克显然没有 、 迎合俗趣 屈尊俯就”, 沿右“相 专业问题 而是敏捷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 帕斯捷尔纳克念念 的是“还债 在逝1 前的一年,他还对一位美国诗人说:“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 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债。这种负债感在我缓慢的写作过程中变得一发不可遏制, 在那以前,我多年仅仅从事诗和国外作品的翻译,我有责任通过小说评述我们的时代 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饶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剖 小说, 美好和敏感的 面。那些岁月 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 不醒。但在百花盛开的时候,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 一定会复苏 .我不知道《日 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获得了彻底的成功,但即使它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仍然觉得比我 的早期诗歌具有更高的价值,内容更为丰富,更具备人道主义精神。”[7]在一封书信里,他 还进而提到了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有的人非常爱我(他们为数极少),我的心有负于他 们,.我是为他们而写的,好象是给他们写的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在另一封书信里他还说 这部小说是我偿还债务的一部分,证明我尽了自己的努力。 在这里,“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债”,“这种负债 感”,“我的心有负于他们”,“这部小说是我偿还债务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话语意味着帕斯 捷尔纳克对于自身责任的觉察。这是一种身为作家所必不可少的绝对责任,只要联想到“丧 钟在为每一个人而鸣”,我们就不难须悟这种绝对责任意煮味若什么。由此,尽管的断捷尔纳古 毫无怨尤地接受了世纪所给予他的 一切,但是他却同时又以无限的责任感回报若世纪所给了 他的一切。50年前的现实已经告诉我们,帕斯捷尔纳克因此而成为“诺贝尔 百年历史上 见的因永恒荣耀而招致终身灾难的作家,这意味着:那个世纪对于这一个人欠下了巨债而且 在他生前始终没有偿还,因此,那个世纪也没有因此而被牍回。这,实在是那个世纪的遗撼 也是那个世纪的耻辱。但是,这却并非帕斯捷尔纳克的遗憾与耻辱。因为,他已经完全尽到 了自己的责任 在他看来,革命固 是对现实的 但是美学却是拯救之拯救, 如果你在 美学的立场上质疑这场拯救现实的革命,事实上也就在精神上拯救了这场拯救现实的革命 这美学的拯救、精神的拯救,就是他自己所肩负的世纪巨债,也就是他自己所意识到并主动 肩负的绝对责任。写作,是他完成这一切的唯一可能,一个人对于一个世纪的巨债借此得以 德还, 一个人的自我也借此得以赎回,这,实在是一个人的光荣,一个人的辉煌。 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过,“《日瓦戈医生》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我想在其中刻画出俄罗 斯近45年的历史”。[8]不错,这确实是“真正的作品”。作为一个世界闻名的著名诗人, 斯捷尔纳克很早就意识到:“抒情诗已经不能表现我们经验的广博”。在提及几位诗人的自杀 时,他也一再为“生活已经变得过于沉重,过于复杂”,而自己尚未找到最恰当的形式和语言 去表达而苦闷,“写下去,过于艰难”。最终,他不惜从抒情转向了叙事,转而“用小说讲述 我们的时代”,并“重新创造 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在死后发表的自传性随笔《人与事》中, 帕斯捷尔纳克自陈说:“这里所写的东西 ,足以使人理 在我的个别事件中为何转 化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米。”[9]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前后的俄国社会生活,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国 内革命战争,20年代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卫国战争.当这一切纷纭错乱地汇聚而为前苏联
尔纳克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思想的权利就同样是真实的,而且是更加真实的。 作为自己所面对的一切的见证者与守夜人,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个人,帕斯捷尔纳克同样可 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下自己的名字。 同样,也犹如维特根斯坦对于托尔斯泰的赞叹,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也 “有权写作”。作为一个美学研究者。我一直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对于美学的痛斥而惭愧:“美 学并不存在。对我来说,似乎美学不存在是对它的一种惩罚,因为它撒谎、妥协、迎合俗趣、 屈尊俯就。因为它在对人一无所知的时候,胡扯专业问题。”[6]因为这无疑也是中国的美学 研究的通病。而帕斯捷尔纳克显然没有“撒谎、妥协、迎合俗趣、屈尊俯就”,也没有“胡扯 专业问题”,而是敏捷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帕斯捷尔纳克念念不忘的是“还债”。在逝世 前的一年,他还对一位美国诗人说:“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 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债。这种负债感在我缓慢的写作过程中变得一发不可遏制, 在那以前,我多年仅仅从事诗和国外作品的翻译,我有责任通过小说评述我们的时代——遥 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饶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 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 不醒。但在百花盛开的时候,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我不知道《日 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获得了彻底的成功,但即使它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仍然觉得比我 的早期诗歌具有更高的价值,内容更为丰富,更具备人道主义精神。”[7]在一封书信里,他 还进而提到了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有的人非常爱我(他们为数极少),我的心有负于他 们,.我是为他们而写的,好象是给他们写的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在另一封书信里他还说, “这部小说是我偿还债务的一部分,证明我尽了自己的努力。” 在这里,“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债”,“这种负债 感”,“我的心有负于他们”,“这部小说是我偿还债务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话语意味着帕斯 捷尔纳克对于自身责任的觉察。这是一种身为作家所必不可少的绝对责任,只要联想到“丧 钟在为每一个人而鸣”,我们就不难领悟这种绝对责任意味着什么。由此,尽管帕斯捷尔纳克 毫无怨尤地接受了世纪所给予他的一切,但是他却同时又以无限的责任感回报着世纪所给予 他的一切。50 年前的现实已经告诉我们,帕斯捷尔纳克因此而成为“诺贝尔”百年历史上罕 见的因永恒荣耀而招致终身灾难的作家,这意味着:那个世纪对于这一个人欠下了巨债而且 在他生前始终没有偿还,因此,那个世纪也没有因此而被赎回。这,实在是那个世纪的遗憾, 也是那个世纪的耻辱。但是,这却并非帕斯捷尔纳克的遗憾与耻辱。因为,他已经完全尽到 了自己的责任。在他看来,革命固然是对现实的拯救,但是美学却是拯救之拯救,如果你在 美学的立场上质疑这场拯救现实的革命,事实上也就在精神上拯救了这场拯救现实的革命。 这美学的拯救、精神的拯救,就是他自己所肩负的世纪巨债,也就是他自己所意识到并主动 肩负的绝对责任。写作,是他完成这一切的唯一可能,一个人对于一个世纪的巨债借此得以 偿还,一个人的自我也借此得以赎回,这,实在是一个人的光荣,一个人的辉煌。 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过,“《日瓦戈医生》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我想在其中刻画出俄罗 斯近 45 年的历史”。[8]不错,这确实是“真正的作品”。作为一个世界闻名的著名诗人,帕 斯捷尔纳克很早就意识到:“抒情诗已经不能表现我们经验的广博”。在提及几位诗人的自杀 时,他也一再为“生活已经变得过于沉重,过于复杂”,而自己尚未找到最恰当的形式和语言 去表达而苦闷,“写下去,过于艰难”。最终,他不惜从抒情转向了叙事,转而“用小说讲述 我们的时代”,并“重新创造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在死后发表的自传性随笔《人与事》中, 帕斯捷尔纳克自陈说:“这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为何转 化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9]1905 年俄国第一次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前后的俄国社会生活,1917 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国 内革命战争,20 年代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卫国战争.当这一切纷纭错乱地汇聚而为前苏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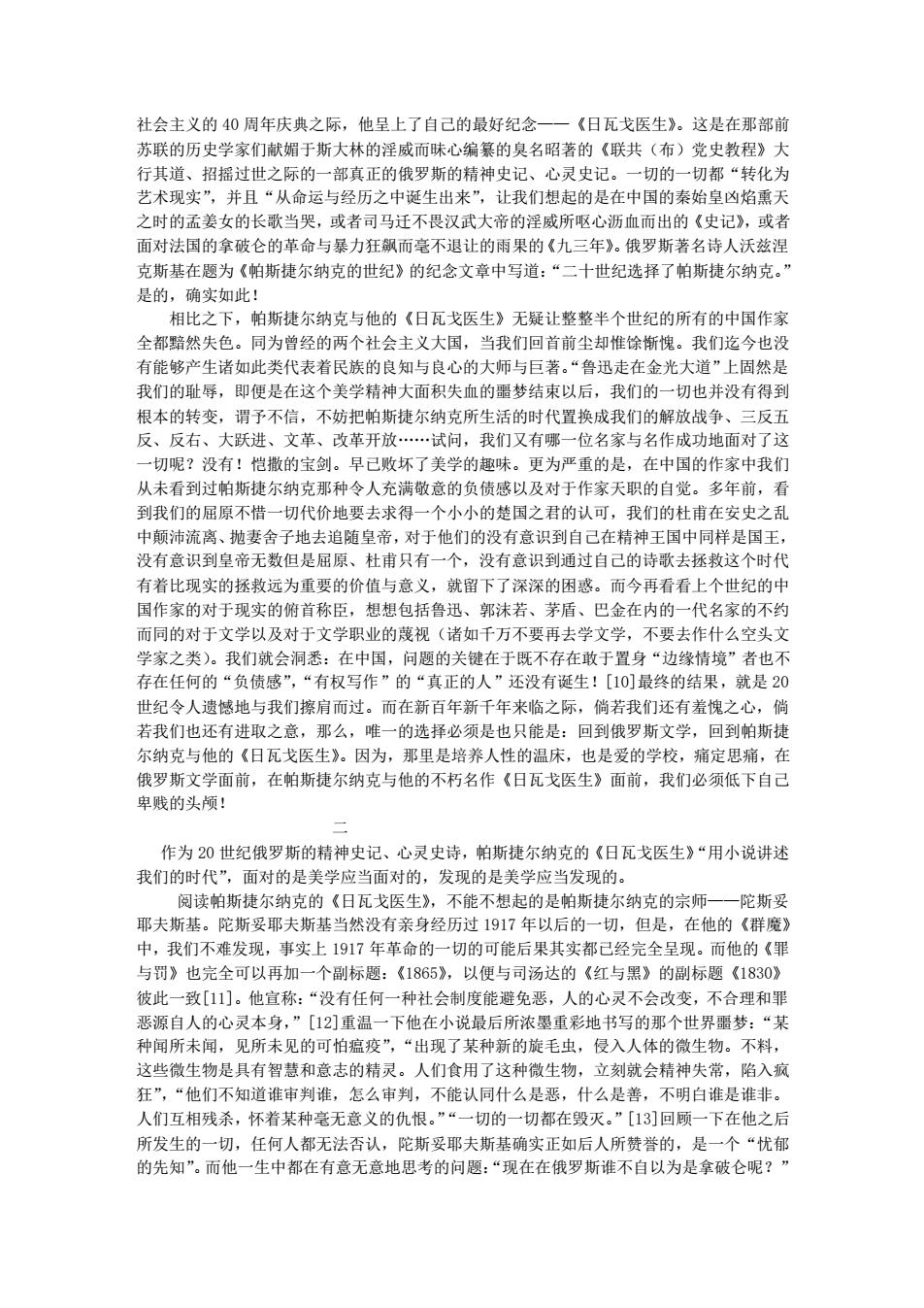
社会主义的40周年庆典之际,他呈上了自己的最好纪念一一《日瓦戈医生》。这是在那部前 苏联的历史学家们献媚于斯大林的淫威而味心编纂的臭名昭著的《联共(布)党史教程》大 行其道 招摇过世 际的一部真正的俄罗斯的精神史记、心灵史记。 切都4 转化为 艺术现实”,并且“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让我们想起的是在中国的秦始皇凶焰熏天 之时的孟姜女的长歌当哭,或者司马迁不畏汉武大帝的淫威所呕心沥血而出的《史记》,或者 面对法国的拿破仑的革命与暴力狂飙而毫不退让的雨果的《九三年》。俄罗斯著名诗人沃兹涅 克斯基在题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纪》的纪念文章中写道:“二十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 是的 确实如此 相比之下,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无疑让整整半个世纪的所有的中国作家 全都黯然失色。同为曾经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当我们回首前尘却惟徐惭愧。我们迄今也没 有能够产生诸如此类代表者民族的良知与良心的大师与巨著。“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固然是 我们的卧辱,即便是在这个美学结神大面积失血的册梦结束以后,我们的一切也并没有得到 根本的转变,谓予不信,不妨把帕斯捷尔纳克所生活的时代置换成我们的解放战争 三反五 反、反右、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 “试问,我们义有 位名家与名作成功地面对了这 一切呢?没有!恺撒的宝剑。早已败坏了美学的趣味。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国的作家中我们 从未看到过帕斯捷尔纳克那种令人充满敬意的负债感以及对于作家天职的自觉。多年前,看 到我们的届原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去求得一个小小的禁国之君的认可,我们的杜甫在安史之乱 中颠沛流离、抛妻舍子地去追随皇帝,对于他们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精神王国中同样是国王 没有意识到皇帝无数但 是屈原 杜甫只有 ,没有意识到通过自己的诗歌 拯救这个时代 有者比现实的拯救远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就留下了深深的困惑。而今再看看上个世纪的中 国作家的对于现实的俯首称臣,想想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在内的一代名家的不约 而同的对于文学以及对于文学职业的蔑视(诸如千万不要再去学文学,不要去作什么空头文 学家之类)。我们或会洞悉:在中国,问顾的关键在再不存在敢干身“边缘情墙”者也不 存在任何的“负债感”,“有权写作”的“真正的人”还没有诞生![10]最终的结果 就是20 世纪令人遗憾地与我们擦肩而过。而在新百年新千年来临之际,倘若我们还有羞愧之心,倘 若我们也还有进取之意,那么,唯一的选择必须是也只能是:回到俄罗斯文学,回到帕斯捷 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因为,那里是培养人性的温床,也是爱的学校,痛定思痛,在 俄罗斯文学面前,在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不朽名作《日瓦戈医生》面前,我们必须低下自己 鬼践的斗师! 作为20世纪俄罗斯的精神史记、心灵史诗,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用小说讲述 我们的时代”,面对的是美学应当面对的,发现的是美学应当发现的。 阅读柏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不能不想起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宗师 一密断好 耶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当然没有亲身经历过1917年以后的一切,但是,在他的《群魔》 中,我们不难发现,事实上1917年革命的 一切的可能后果其实都已经完全呈现。而他的《罪 与罚》也完全可以再加一个副标题:《1865》,以便与司汤达的《红与黑》的副标题《1830》 彼此一致[11]。他宣称:“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能避免恶,人的心灵不会改变,不合理和罪 恶源自人的心灵木身,”[12]重温一下他在小说最后所浓墨重彩地书写的那个世界蹈梦:“某 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可柏盘疫”,“出现了某种新的旋毛虫,侵入人体的微生物。不料 这些微生物是具有智慧和意志的精灵。人们食用了 这种微生物 立刻就会精神失常,陷入疯 “他们不知道谁审判谁,怎么审判 不能认同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不明白谁是谁非 人们互相残杀,怀若某种毫无意义的仇恨。” 一切的一切都在毁灭。”[13]回顾一下在他之后 所发生的一切,任何人都无法否认,陀斯妥耶夫斯基确实正如后人所赞誉的,是一个“忧椰 的先知”。而他一生中都在有意无意地思考的问题:“现在在俄罗斯谁不自以为是拿破仑呢?
社会主义的 40 周年庆典之际,他呈上了自己的最好纪念——《日瓦戈医生》。这是在那部前 苏联的历史学家们献媚于斯大林的淫威而昧心编纂的臭名昭著的《联共(布)党史教程》大 行其道、招摇过世之际的一部真正的俄罗斯的精神史记、心灵史记。一切的一切都“转化为 艺术现实”,并且“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让我们想起的是在中国的秦始皇凶焰熏天 之时的孟姜女的长歌当哭,或者司马迁不畏汉武大帝的淫威所呕心沥血而出的《史记》,或者 面对法国的拿破仑的革命与暴力狂飙而毫不退让的雨果的《九三年》。俄罗斯著名诗人沃兹涅 克斯基在题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纪》的纪念文章中写道:“二十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 是的,确实如此! 相比之下,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无疑让整整半个世纪的所有的中国作家 全都黯然失色。同为曾经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当我们回首前尘却惟馀惭愧。我们迄今也没 有能够产生诸如此类代表着民族的良知与良心的大师与巨著。“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固然是 我们的耻辱,即便是在这个美学精神大面积失血的噩梦结束以后,我们的一切也并没有得到 根本的转变,谓予不信,不妨把帕斯捷尔纳克所生活的时代置换成我们的解放战争、三反五 反、反右、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试问,我们又有哪一位名家与名作成功地面对了这 一切呢?没有!恺撒的宝剑。早已败坏了美学的趣味。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国的作家中我们 从未看到过帕斯捷尔纳克那种令人充满敬意的负债感以及对于作家天职的自觉。多年前,看 到我们的屈原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去求得一个小小的楚国之君的认可,我们的杜甫在安史之乱 中颠沛流离、抛妻舍子地去追随皇帝,对于他们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精神王国中同样是国王, 没有意识到皇帝无数但是屈原、杜甫只有一个,没有意识到通过自己的诗歌去拯救这个时代 有着比现实的拯救远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就留下了深深的困惑。而今再看看上个世纪的中 国作家的对于现实的俯首称臣,想想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在内的一代名家的不约 而同的对于文学以及对于文学职业的蔑视(诸如千万不要再去学文学,不要去作什么空头文 学家之类)。我们就会洞悉:在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既不存在敢于置身“边缘情境”者也不 存在任何的“负债感”,“有权写作”的“真正的人”还没有诞生![10]最终的结果,就是 20 世纪令人遗憾地与我们擦肩而过。而在新百年新千年来临之际,倘若我们还有羞愧之心,倘 若我们也还有进取之意,那么,唯一的选择必须是也只能是:回到俄罗斯文学,回到帕斯捷 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因为,那里是培养人性的温床,也是爱的学校,痛定思痛,在 俄罗斯文学面前,在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不朽名作《日瓦戈医生》面前,我们必须低下自己 卑贱的头颅! 二 作为 20 世纪俄罗斯的精神史记、心灵史诗,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用小说讲述 我们的时代”,面对的是美学应当面对的,发现的是美学应当发现的。 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不能不想起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宗师——陀斯妥 耶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当然没有亲身经历过 1917 年以后的一切,但是,在他的《群魔》 中,我们不难发现,事实上 1917 年革命的一切的可能后果其实都已经完全呈现。而他的《罪 与罚》也完全可以再加一个副标题:《1865》,以便与司汤达的《红与黑》的副标题《1830》 彼此一致[11]。他宣称:“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能避免恶,人的心灵不会改变,不合理和罪 恶源自人的心灵本身,”[12]重温一下他在小说最后所浓墨重彩地书写的那个世界噩梦:“某 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可怕瘟疫”,“出现了某种新的旋毛虫,侵入人体的微生物。不料, 这些微生物是具有智慧和意志的精灵。人们食用了这种微生物,立刻就会精神失常,陷入疯 狂”,“他们不知道谁审判谁,怎么审判,不能认同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不明白谁是谁非。 人们互相残杀,怀着某种毫无意义的仇恨。”“一切的一切都在毁灭。”[13]回顾一下在他之后 所发生的一切,任何人都无法否认,陀斯妥耶夫斯基确实正如后人所赞誉的,是一个“忧郁 的先知”。而他一生中都在有意无意地思考的问题:“现在在俄罗斯谁不自以为是拿破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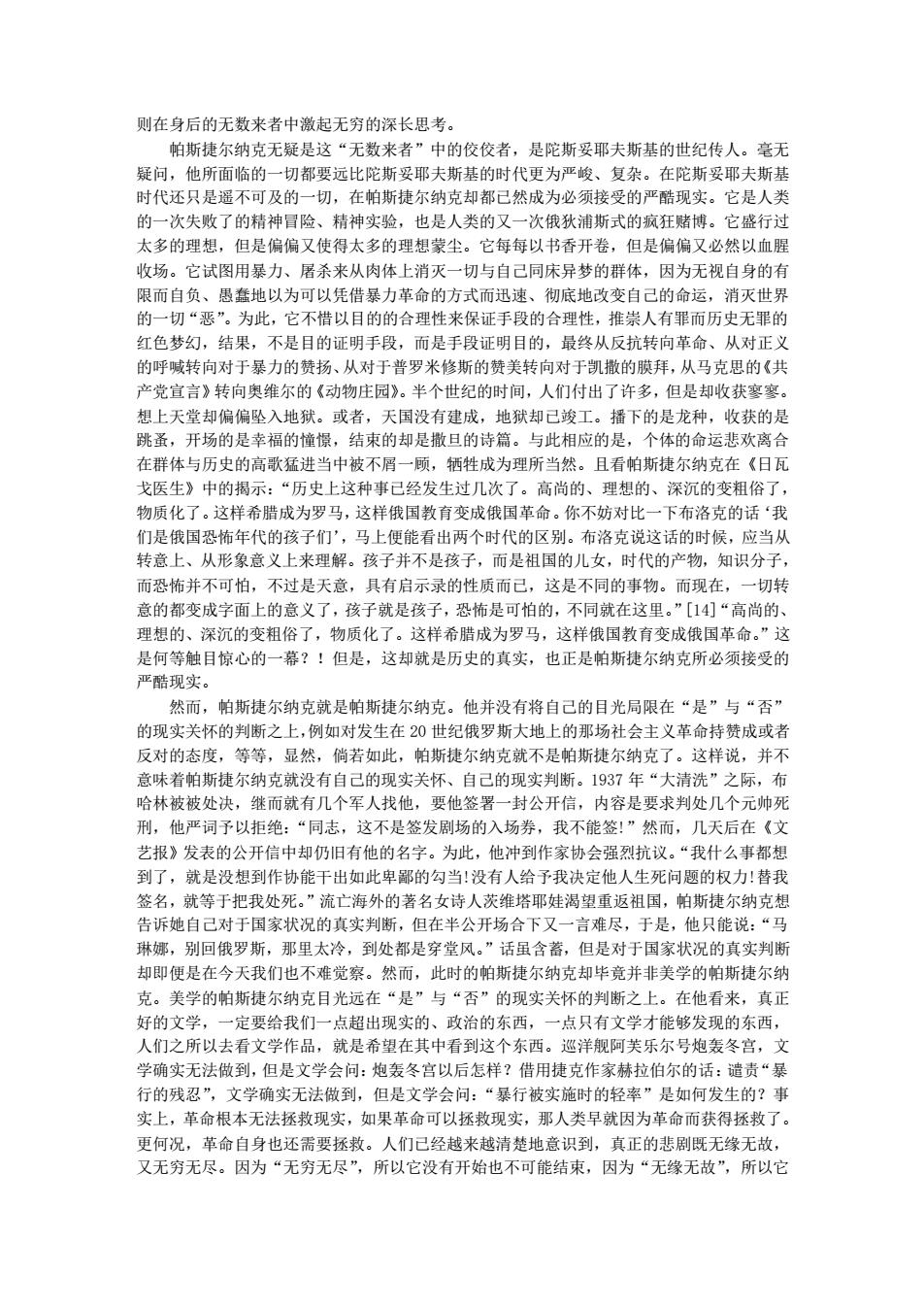
则在身后的无数来者中激起无穷的深长思考。 帕斯捷尔纳克无疑是这“无数来者”中的佼佼者,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世纪传人。毫无 疑问 他所面临的 切都要远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更为 复东 在陀斯妥耶夫斯 时代还只是遥不可及的一切,在帕斯捷尔纳克却都已然成为必级 接受的严酷现实。它是人类 的一次失败了的精神冒险、精神实验,也是人类的又一次俄狄浦斯式的疯狂赌博。它盛行过 太多的理想,但是偏偏又使得太多的理想蒙尘。它每每以书香开卷,但是偏偏又必然以血腥 收场。它试图用暴力、屠杀来从肉体上消灭一切与自己同床异梦的群体,因为无视自身的有 限而自负、愚地以为可以凭借暴力革命的方式而迅速 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的一切“恶” 为 它不惜以目的的合理性来保证手段的合理 红色梦幻,结果,不是目的证明手段,而是手段证明目的,最终从反抗转向革命、从对正义 的呼喊转向对于暴力的赞扬、从对于普罗米修斯的赞美转向对于凯撒的膜拜,从马克思的《共 产党宜言》转向奥维尔的《动物庄园》。半个世纪的时间,人们付出了许多,但是却收获宴宴 想上天堂却偏偏坠入地狱。或者,天国没有建成,地狱却已竣工。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 跳蚤,开场的是幸福的 束的却是撒旦的诗篇。 与此相应的是 木的 命运悲欢离 在群体与历史的高歌猛进当中被不屑一顾,牺牲成为理所当然。且看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 戈医生》中的揭示:“历史上这种事己经发生过几次了。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 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你不妨对比一下布洛克的话‘我 们是俄国恐栋年代的孩子们”,马上便能看出两个时代的区别。布洛古说这话的时候,应当从 转意上、从形象意义上来理解。孩子并不是孩子 而是祖国的儿女, 时代的产物知识分 而恐怖并不可怕,不过是天意,具有启示录的性质而已,这是不同的事物。而现在, 一切转 意的都变成字面上的意义了,孩子就是孩子,恐怖是可怕的,不同就在这里。”[14]“高尚的、 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有变成俄国革命。”这 是何等触目惊心的一幕?【但是,这却就是历史的真实,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所必须接受的 亚酷现实」 然而,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帕斯捷尔纳克。他并没有将自己的目光局限在 “是”与“否 的现实关怀的判断之上,例如对发生在20世纪俄罗斯大地上的那场社会主义革命持赞成或者 反对的态度,等等,显然,倘若如此,帕斯捷尔纳克就不是帕斯捷尔纳克了。这样说,并不 意味着帕斯捷尔纳克就没有自己的现实关怀、自己的现实判断。1937年“大清洗”之际,布 哈林被被处决,珠而就有几个军人找他,要他签署 封公开信,内容是要求判处几个元帅死 刑,他严词予以拒 “同志 这不是签发场的 入场券 ,我不能签!”然而,几天后在《文 艺报》发表的公开信中却仍旧有他的名字。为此,他冲到作家协会强烈抗议。“我什么事都想 到了,就是没想到作协能干出如此卑鄙的勾当!没有人给予我决定他人生死问题的权力!替我 签名,就等于把我处死。”流亡海外的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渴望重返祖国,帕斯捷尔纳克想 告诉她自己对于国家状况的真实判断,但在半公开场合下又一言难尽,于是,他只能说:“马 琳到同罗斯 那里太冷,到处都是穿堂风。”话虽含蓄,但是对于国家状况的真实判断 却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不难觉察。然而,此时的帕斯捷尔纳克却毕竟并非美学的帕斯捷尔 克。美学的帕斯捷尔纳克目光远在“是”与“否”的现实关怀的判断之上。在他看来,真正 好的文学, 一定要给我们一点超出现实的、政治的东西,一点只有文学才能够发现的东西, 人们之所以去看文学作品,就是希望在其中看到这个东西。巡洋舰阿芙乐尔号炮轰冬宫,文 学确实无法做到,但是文学会问:炮轰冬宫以后怎样?借用捷克作家赫拉伯尔的话:谴责“暴 行的残忍”,文学确实无法做到 但是文学会问: 录行被实施时的轻率” 是如何发生的?事 实上,革命根本无法拯救现实,如果革命可以拯救现实,那人类早就因为革命而获得拯救了。 更何况,革命自身也还需要拯教。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真正的悲剧既无缘无故, 又无穷无尽。因为“无穷无尽”,所以它没有开始也不可能结束,因为“无缘无故”,所以它
则在身后的无数来者中激起无穷的深长思考。 帕斯捷尔纳克无疑是这“无数来者”中的佼佼者,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世纪传人。毫无 疑问,他所面临的一切都要远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更为严峻、复杂。在陀斯妥耶夫斯基 时代还只是遥不可及的一切,在帕斯捷尔纳克却都已然成为必须接受的严酷现实。它是人类 的一次失败了的精神冒险、精神实验,也是人类的又一次俄狄浦斯式的疯狂赌博。它盛行过 太多的理想,但是偏偏又使得太多的理想蒙尘。它每每以书香开卷,但是偏偏又必然以血腥 收场。它试图用暴力、屠杀来从肉体上消灭一切与自己同床异梦的群体,因为无视自身的有 限而自负、愚蠢地以为可以凭借暴力革命的方式而迅速、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消灭世界 的一切“恶”。为此,它不惜以目的的合理性来保证手段的合理性,推崇人有罪而历史无罪的 红色梦幻,结果,不是目的证明手段,而是手段证明目的,最终从反抗转向革命、从对正义 的呼喊转向对于暴力的赞扬、从对于普罗米修斯的赞美转向对于凯撒的膜拜,从马克思的《共 产党宣言》转向奥维尔的《动物庄园》。半个世纪的时间,人们付出了许多,但是却收获寥寥。 想上天堂却偏偏坠入地狱。或者,天国没有建成,地狱却已竣工。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 跳蚤,开场的是幸福的憧憬,结束的却是撒旦的诗篇。与此相应的是,个体的命运悲欢离合 在群体与历史的高歌猛进当中被不屑一顾,牺牲成为理所当然。且看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 戈医生》中的揭示:“历史上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几次了。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 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你不妨对比一下布洛克的话‘我 们是俄国恐怖年代的孩子们’,马上便能看出两个时代的区别。布洛克说这话的时候,应当从 转意上、从形象意义上来理解。孩子并不是孩子,而是祖国的儿女,时代的产物,知识分子, 而恐怖并不可怕,不过是天意,具有启示录的性质而已,这是不同的事物。而现在,一切转 意的都变成字面上的意义了,孩子就是孩子,恐怖是可怕的,不同就在这里。”[14]“高尚的、 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这 是何等触目惊心的一幕?!但是,这却就是历史的真实,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所必须接受的 严酷现实。 然而,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帕斯捷尔纳克。他并没有将自己的目光局限在“是”与“否” 的现实关怀的判断之上,例如对发生在 20 世纪俄罗斯大地上的那场社会主义革命持赞成或者 反对的态度,等等,显然,倘若如此,帕斯捷尔纳克就不是帕斯捷尔纳克了。这样说,并不 意味着帕斯捷尔纳克就没有自己的现实关怀、自己的现实判断。1937 年“大清洗”之际,布 哈林被被处决,继而就有几个军人找他,要他签署一封公开信,内容是要求判处几个元帅死 刑,他严词予以拒绝:“同志,这不是签发剧场的入场券,我不能签!”然而,几天后在《文 艺报》发表的公开信中却仍旧有他的名字。为此,他冲到作家协会强烈抗议。“我什么事都想 到了,就是没想到作协能干出如此卑鄙的勾当!没有人给予我决定他人生死问题的权力!替我 签名,就等于把我处死。”流亡海外的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渴望重返祖国,帕斯捷尔纳克想 告诉她自己对于国家状况的真实判断,但在半公开场合下又一言难尽,于是,他只能说:“马 琳娜,别回俄罗斯,那里太冷,到处都是穿堂风。”话虽含蓄,但是对于国家状况的真实判断 却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不难觉察。然而,此时的帕斯捷尔纳克却毕竟并非美学的帕斯捷尔纳 克。美学的帕斯捷尔纳克目光远在“是”与“否”的现实关怀的判断之上。在他看来,真正 好的文学,一定要给我们一点超出现实的、政治的东西,一点只有文学才能够发现的东西, 人们之所以去看文学作品,就是希望在其中看到这个东西。巡洋舰阿芙乐尔号炮轰冬宫,文 学确实无法做到,但是文学会问:炮轰冬宫以后怎样?借用捷克作家赫拉伯尔的话:谴责“暴 行的残忍”,文学确实无法做到,但是文学会问:“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是如何发生的?事 实上,革命根本无法拯救现实,如果革命可以拯救现实,那人类早就因为革命而获得拯救了。 更何况,革命自身也还需要拯救。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真正的悲剧既无缘无故, 又无穷无尽。因为“无穷无尽”,所以它没有开始也不可能结束,因为“无缘无故”,所以它

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可是革命的愚蠢就在于:以为自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以为自己可以 找到某种外在的原因并且通过铲除这一外在的原因而获得最终的幸福。这样,终极的关怀就 被现实的关怀所僭代,这就是帕斯徒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借西玛之口所说的: “这儿把 某种肮脏的、无关紧要的次要东西抬到它所不应有的、并不属于它的高度。”[15] 结果,个人原罪被转换为社会原罪,人人争当激进时代的推波助澜的弄潮儿,个个要倒 传统时代的掘慕人。一项项社会启蒙工程、社会革命工程纷纷出笼,可是,就类似那座永远 也无法建成的巴比伦高塔:诸如此类的把人间建成天堂的革命都只有一种归宿,就是把人间 变成地狱。更何况 这 项项社会启蒙工程、社 革命工程还需要人类付出过高的甚至是不 可承受的代价!可是,当我们所有人的一生都变成这一项项社会启蒙工程、社会革命工程的 一砖一瓦或螺丝钉之时,这最终建成的幸福大厦又是为谁而建造、让谁来居住呢?这样的伟 大事业还能称之为“伟大”、称之为“事业”吗?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不朽著作《卡拉玛佐夫兄 弟》中的伊凡概然宣称:“我付不起这项伟大事业的票价”,这无疑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想 法,因此,必须替千千万万作 一项项社会启蒙工程 社会革命工程的 瓦或螺丝钉的 死难者们拒绝这张红色的“入场券”。在 个孩子的眼泪中,上帝的名誉都要大打折扣,何况 这只是人间的革命?! 帕斯捷尔纳克正是因此而走向了拯救之拯救,走向了对于社会主义的精神审判。他所瞩 目的,不再是历史的人,而是人的历史,不再是铁与火,而是血与泪,不再是英雄交响乐 而是悲枪奏鸣曲。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发现: 右些西方评论家把日有医生君成是时 苏维埃政权的人物 这种看法 不正确 ,因为他们没能够发 ,这部作品其实是对一切有 着的政权的反抗“。[16]这无疑是一种人性的反抗、美学的反抗。它并不斤斤计较于社会主义 的“好”或者“不好”,而只是去关注社会主义的人性根源,关注社会主义出现以后给人类 尤其是给俄罗斯人在精神上所带来的种种触目惊心的变化,人性在什么地方成功了?在什么 地方失败了?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补会主义究音绘人类带来了什么?留身补会主义的 背景,在什么地方离理想的人性更近, 在什么地方离理想的人性更远?人类因此而失去了行 么、又得到了什么 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中说:“文学只是一个便饭馆,不卖实山珍海味, 只卖一道菜,就是‘人性'。”[17]因此,你甚至可以发现,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非常简单的, 水远不会像生活那样让你服花绝乱,它永远紧盯的问题就只是一个:离理想的人性右多远? 或者,离理想的人性有多近?作家只和一个词朝夕相处,那就是“人性”:文学也永远只问 种得失,那就是“人性的尊网 雨果曾经高呼: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 绝对正 的人道主义!那就因为,在绝对正确的现实关怀的基础上,必须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终极关 怀。这试是雨果的反更:革命是绝对正义的吗?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的革命究意意义何在? 如果共和制度必须以钙牲个人的权利为代价,那么有没有更理想的共和制度?雨果的《九三 年》给我们的启示堪称深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也如此,透过社会主义的缤纷 图景,他看到的是社会主义背后的人性缺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他也意识到, “俄罗斯 灵魂是黑古隆冬的”,是一座地狱, 一座“由于不能再爱而受到的痛苦”而自铸的地狱。“恶 控制了人的机体,束缚着他的每一个行动,剥夺他同降落在灵魂中的黑暗进行斗争的任何 点想法和意愿,并且自觉地、心甘情愿地、怀若复仇的激情在内心中把黑暗当作光明”[18] 精神成了无根之物并失去了重量,生存进入了零度状态,衡量人性轻重的砝码不复存在,而 日再也找不到灵速的居之地 切不断以欲望的形式呈现 切都成为生中不能垂受 轻。那么,值此之际,美学何为?文学何为?帕斯捷尔纳克的答案,就是走向“爱” 这无 是走出地狱的唯一途径。社会主义背后的人性根原在于自我的出场与缺席。而以“社会主义 这一现实关怀来取代“自我的出场与缺席”这一终极关怀,则意味着这一人性根源的迷失。 事实上,任何的社会黑暗从根本上来说都来自于个人的“原罪”。这“原罪”既无可推卸也无
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可是革命的愚蠢就在于:以为自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以为自己可以 找到某种外在的原因并且通过铲除这一外在的原因而获得最终的幸福。这样,终极的关怀就 被现实的关怀所僭代,这就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借西玛之口所说的:“这儿把 某种肮脏的、无关紧要的次要东西抬到它所不应有的、并不属于它的高度。”[15] 结果,个人原罪被转换为社会原罪,人人争当激进时代的推波助澜的弄潮儿,个个要做 传统时代的掘墓人。一项项社会启蒙工程、社会革命工程纷纷出笼,可是,就类似那座永远 也无法建成的巴比伦高塔:诸如此类的把人间建成天堂的革命都只有一种归宿,就是把人间 变成地狱。更何况,这一项项社会启蒙工程、社会革命工程还需要人类付出过高的甚至是不 可承受的代价!可是,当我们所有人的一生都变成这一项项社会启蒙工程、社会革命工程的 一砖一瓦或螺丝钉之时,这最终建成的幸福大厦又是为谁而建造、让谁来居住呢?这样的伟 大事业还能称之为“伟大”、称之为“事业”吗?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不朽著作《卡拉玛佐夫兄 弟》中的伊凡慨然宣称:“我付不起这项伟大事业的票价”,这无疑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想 法,因此,必须替千千万万作为一项项社会启蒙工程、社会革命工程的一砖一瓦或螺丝钉的 死难者们拒绝这张红色的“入场券”。在一个孩子的眼泪中,上帝的名誉都要大打折扣,何况 这只是人间的革命?! 帕斯捷尔纳克正是因此而走向了拯救之拯救,走向了对于社会主义的精神审判。他所瞩 目的,不再是历史的人,而是人的历史,不再是铁与火,而是血与泪,不再是英雄交响乐, 而是悲怆奏鸣曲。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发现::"有些西方评论家把日瓦戈医生看成是对抗 苏维埃政权的人物。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他们没能够发现,这部作品其实是对一切存在 着的政权的反抗"。[16]这无疑是一种人性的反抗、美学的反抗。它并不斤斤计较于社会主义 的“好”或者“不好”,而只是去关注社会主义的人性根源,关注社会主义出现以后给人类, 尤其是给俄罗斯人在精神上所带来的种种触目惊心的变化,人性在什么地方成功了?在什么 地方失败了?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社会主义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置身社会主义的 背景,在什么地方离理想的人性更近,在什么地方离理想的人性更远?人类因此而失去了什 么、又得到了什么? 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中说:“文学只是一个便饭馆,不卖山珍海味, 只卖一道菜,就是‘人性’。”[17]因此,你甚至可以发现,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非常简单的, 永远不会像生活那样让你眼花缭乱,它永远紧盯的问题就只是一个:离理想的人性有多远? 或者,离理想的人性有多近?作家只和一个词朝夕相处,那就是“人性”;文学也永远只问一 种得失,那就是“人性的尊严”。雨果曾经高呼: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 的人道主义!那就因为,在绝对正确的现实关怀的基础上,必须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终极关 怀。这就是雨果的反思:革命是绝对正义的吗?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的革命究竟意义何在? 如果共和制度必须以牺牲个人的权利为代价,那么有没有更理想的共和制度?雨果的《九三 年》给我们的启示堪称深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也如此,透过社会主义的缤纷 图景,他看到的是社会主义背后的人性缺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他也意识到,“俄罗斯 灵魂是黑古隆冬的”,是一座地狱,一座“由于不能再爱而受到的痛苦”而自铸的地狱。“恶 控制了人的机体,束缚着他的每一个行动,剥夺他同降落在灵魂中的黑暗进行斗争的任何一 点想法和意愿,并且自觉地、心甘情愿地、怀着复仇的激情在内心中把黑暗当作光明”[18], 精神成了无根之物并失去了重量,生存进入了零度状态,衡量人性轻重的砝码不复存在,而 且再也找不到灵魂的栖居之地,一切不断以欲望的形式呈现,一切都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 轻。那么,值此之际,美学何为?文学何为?帕斯捷尔纳克的答案,就是走向“爱”,这无疑 是走出地狱的唯一途径。社会主义背后的人性根源在于自我的出场与缺席。而以“社会主义” 这一现实关怀来取代“自我的出场与缺席”这一终极关怀,则意味着这一人性根源的迷失。 事实上,任何的社会黑暗从根本上来说都来自于个人的“原罪”。这“原罪”既无可推卸也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