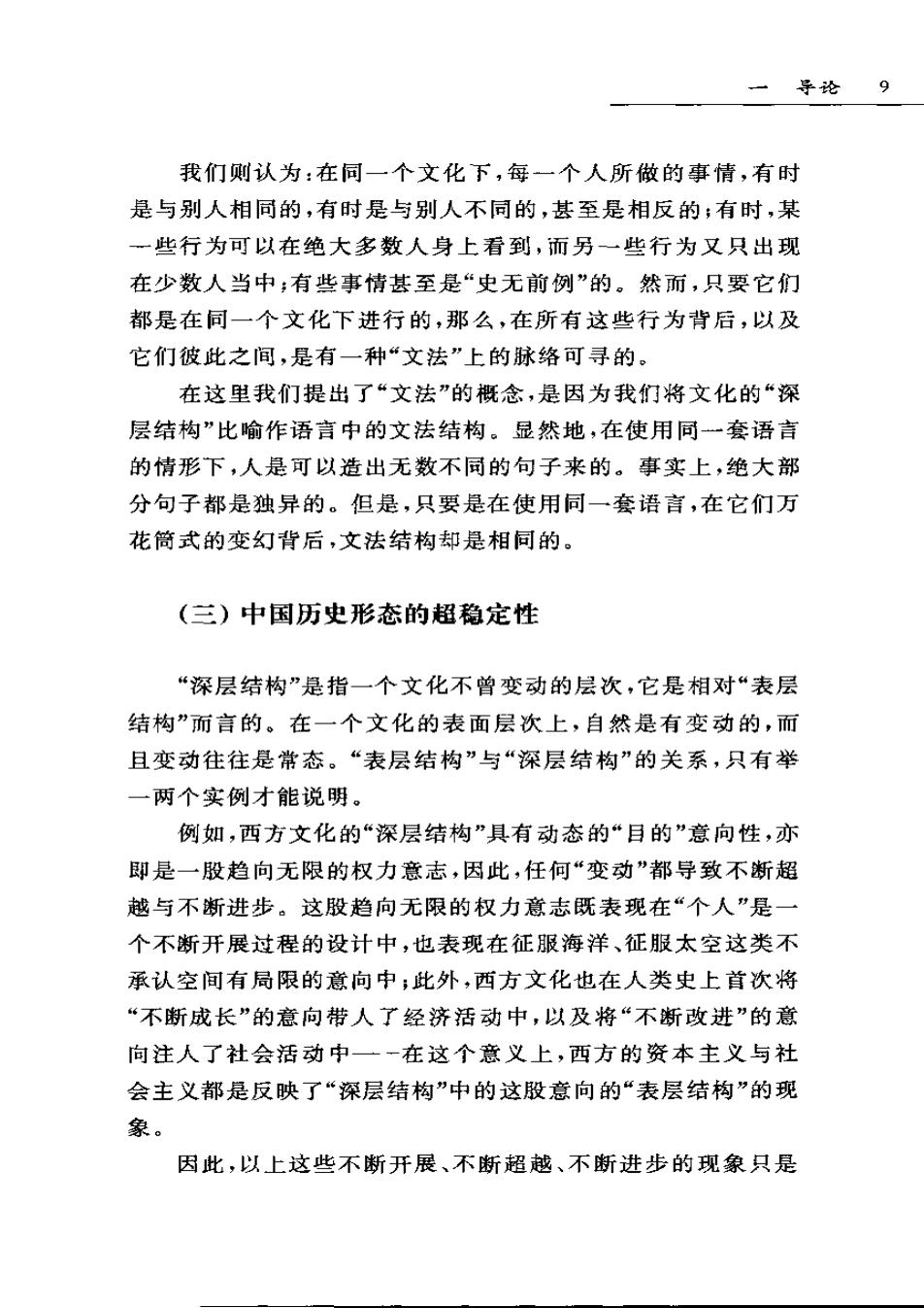
一导论 9 我们则认为:在同一个文化下,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有时 是与别人相同的,有时是与别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有时,某 一些行为可以在绝大多数人身上看到,而另一些行为又只出现 在少数人当中:有些事情甚至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只要它们 都是在同一个文化下进行的,那么,在所有这些行为背后,以及 它们彼此之间,是有一种“文法”上的脉络可寻的。 在这里我们提出了“文法”的概念,是因为我们将文化的“深 层结构”比喻作语言中的文法结构。显然地,在使用同一套语言 的情形下,人是可以造出无数不同的句子来的。事实上,绝大部 分句子都是独异的。但是,只要是在使用同一套语言,在它们万 花筒式的变幻背后,文法结构却是相同的。 (三)中国历史形态的超稳定性 “深层结构”是指一个文化不曾变动的层次,它是相对“表层 结构”而言的。在一个文化的表面层次上,自然是有变动的,而 且变动往往是常态。“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关系,只有举 一两个实例才能说明。 例如,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亦 即是一股趋向无限的权力意志,因此,任何“变动”都导致不断超 越与不断进步。这股趋向无限的权力意志既表现在“个人”是 个不断开展过程的设计中,也表现在征服海洋、征服太空这类不 承认空间有局限的意向中:此外,西方文化也在人类史上首次将 “不断成长”的意向带人了经济活动中,以及将“不断改进”的意 向注人了社会活动中一一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资本主义与社 会主义都是反映了“深层结构”中的这股意向的“表层结构”的现 象。 因此,以上这些不断开展、不斯超越、不断进步的现象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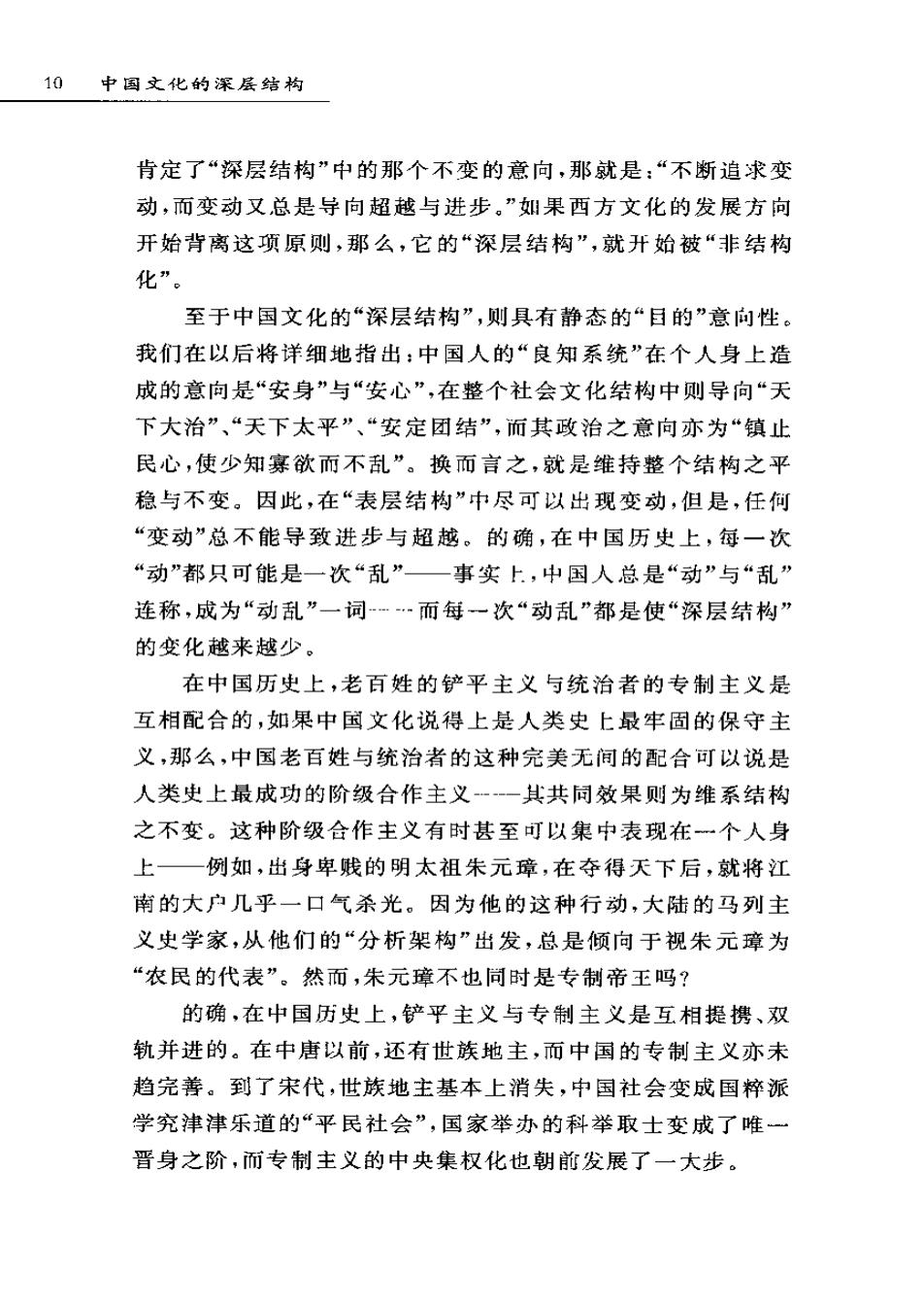
10中国文化的深层构 肯定了“深层结构”中的那个不变的意向,那就是:“不断追求变 动,而变动又总是导向超越与进步。”如果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向 开始背离这项原则,那么,它的“深层结构”,就开始被“非结构 化”。 至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则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 我们在以后将详细地指出:中国人的“良知系统”在个人身上造 成的意向是“安身”与“安心”,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则导向“天 下大治”、“天下太平”、“安定团结”,而其政治之意向亦为“镇止 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换而言之,就是维持整个结构之平 稳与不变。因此,在“表层结构”中尽可以出现变动,但是,任何 “变动”总不能导致进步与超越。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 “动”都只可能是一次“乱”一事实上,中国人总是“动”与“乱” 连称,成为“动乱”一词一.而每一次“动乱”都是使“深层结构” 的变化越来越少。 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的铲平主义与统治者的专制主义是 互相配合的,如果中国文化说得上是人类史上最牢固的保守主 义,那么,中国老百姓与统治者的这种完美无间的配合可以说是 人类史上最成功的阶级合作主义一其共同效果则为维系结构 之不变。这种阶级合作主义有时甚至可以集中表现在一个人身 上一例如,出身卑贱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夺得天下后,就将江 南的大户几乎一口气杀光。因为他的这种行动,大陆的马列主 义史学家,从他们的“分析架构”出发,总是倾向于视朱元璋为 “农民的代表”。然而,朱元璋不也同时是专制帝王吗?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铲平主义与专制主义是互相提携、双 轨并进的。在中唐以前,还有世族地主,而中国的专制主义亦未 趋完善。到了宋代,世族地主基本上消失,中国社会变成国粹派 学究津津乐道的“平民社会”,国家举办的科举取士变成了唯一 晋身之阶,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化也朝前发展了一大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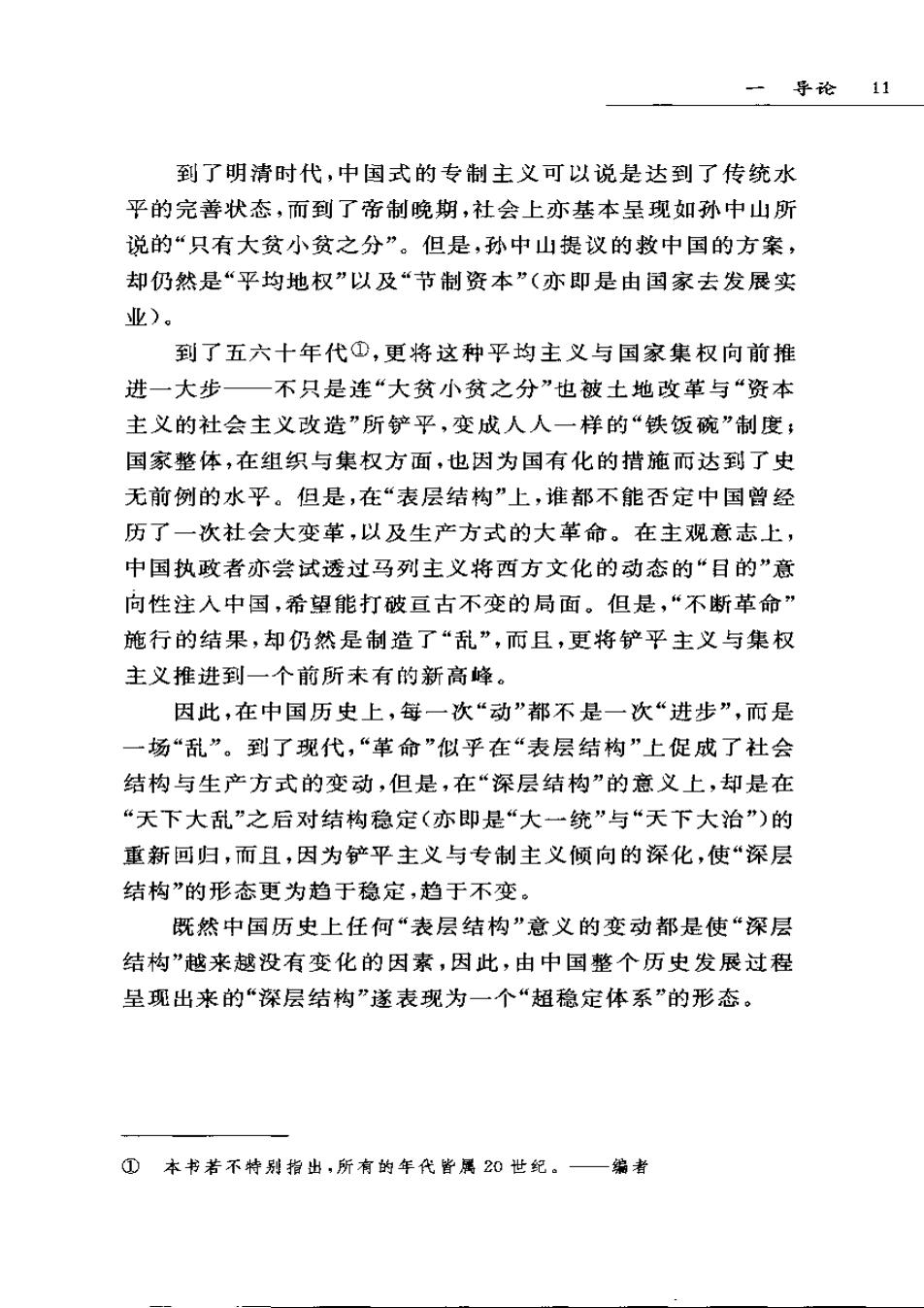
一导论11 到了明清时代,中国式的专制主义可以说是达到了传统水 平的完善状态,而到了帝制晚期,社会上亦基本呈现如孙中山所 说的“只有大贫小贫之分”。但是,孙中山提议的救中国的方案 却仍然是“平均地权”以及“节制资本”(亦即是由国家去发展实 业)。 到了五六十年代①,更将这种平均主义与国家集权向前推 进一大步一 一不只是连“大贫小贫之分”也被土地改革与“资本 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铲平,变成人人一样的“铁饭碗”制度: 国家整体,在组织与集权方面,也因为国有化的措施而达到了史 无前例的水平。但是,在“表层结构”上,堆都不能否定中国曾经 历了一次社会大变革,以及生产方式的大革命。在主观意志上, 中国执政者亦尝试透过马列主义将西方文化的动态的“目的”意 向性注入中国,希望能打破亘古不变的局面。但是,“不断革命 施行的结果,却仍然是制造了“乱”,而且,更将铲平主义与集权 主义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峰。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动”都不是一次“进步”,而是 一场“乱”。到了现代,“革命”似乎在“表层结构”上促成了社会 结构与生产方式的变动,但是,在“深层结构”的意义上,却是在 “天下大乱”之后对结构稳定(亦即是“大一统”与“天下大治”)的 重新回归,而且,因为铲平主义与专制主义倾向的深化,使“深层 结构”的形态更为趋于稳定,趋于不变。 既然中国历史上任何“表层结构”意义的变动都是使“深层 结构”越来越没有变化的因素,因此,由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 呈现出来的“深层结构”遂表现为一个“超稳定体系”的形态。 ①本书若不特群指出,所有的年代皆属20世纪。—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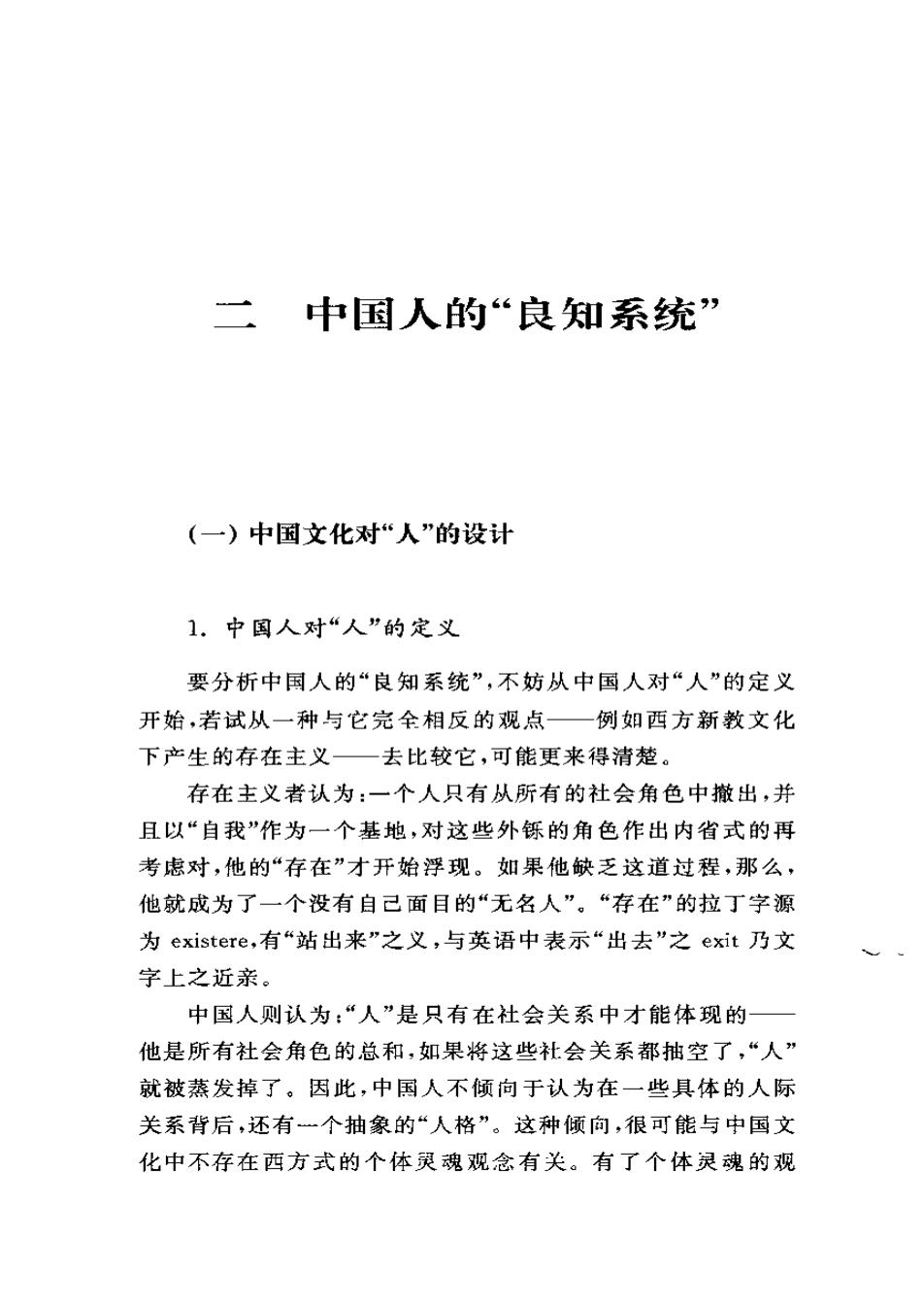
二中国人的“良知系统” (一)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 1.中国人对“人”的定义 要分析中国人的“良知系统”,不妨从中国人对“人”的定义 开始,若试从一种与它完全相反的观点—例如西方新教文化 下产生的存在主义一去比较它,可能更来得清楚。 存在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 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作出内省式的再 考虑对,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如果他缺乏这道过程,那么, 他就成为了一个没有自已面目的“无名人”。“存在”的拉丁字源 为existere,有“站出来”之义,与英语中表示“出去”之exit乃文 字上之近亲。 中国人则认为:“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 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 就被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 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这种倾向,很可能与中国文 化中不存在西方式的个体灵魂观念有关。有了个体灵魂的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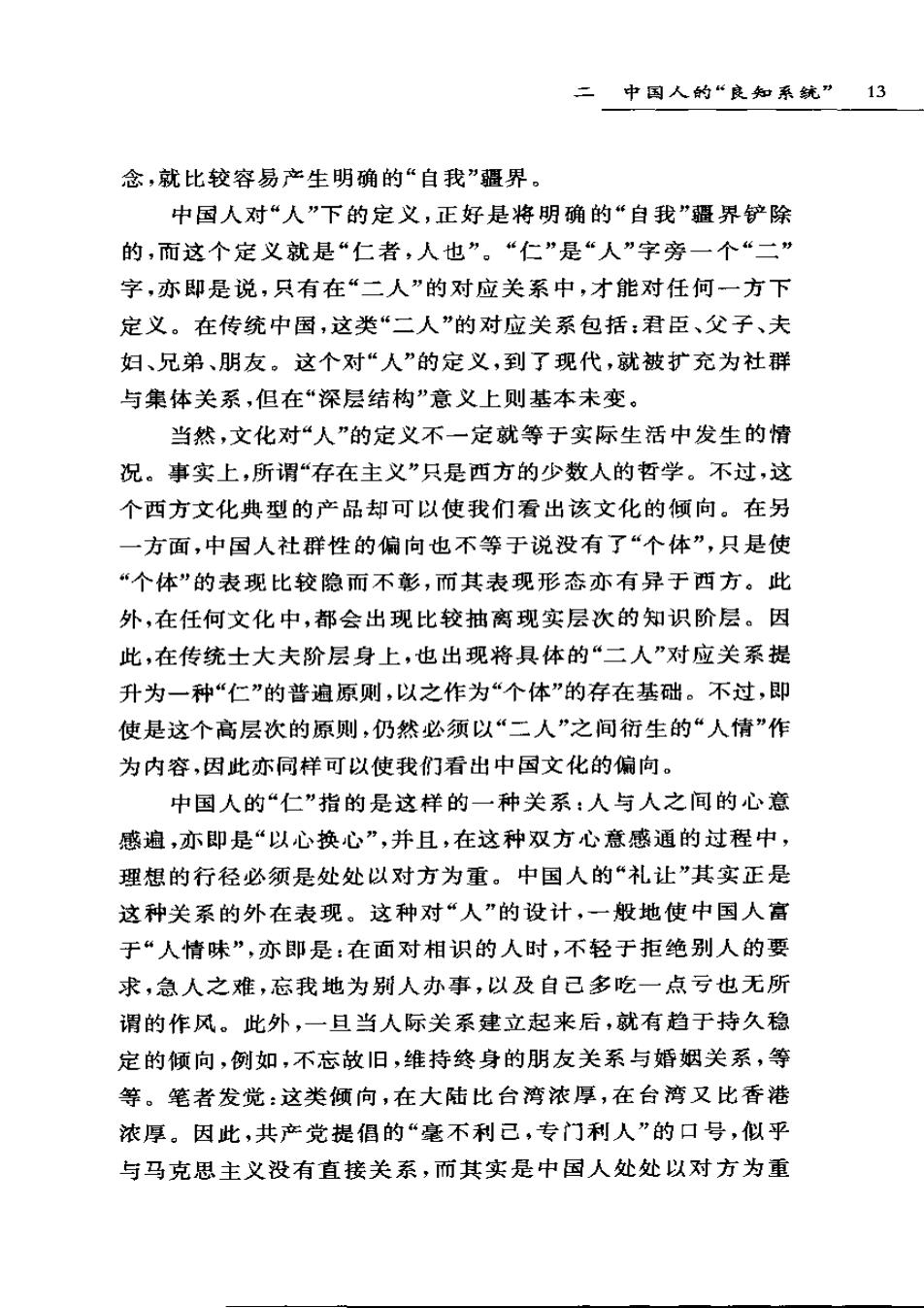
二中国人的“良知系统”13 念,就比较容易产生明确的“自我”疆界。 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 的,而这个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 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 定义。在传统中国,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 妇、兄弟、朋友。这个对“人”的定义,到了现代,就被扩充为社群 与集体关系,但在“深层结构”意义上则基本未变。 当然,文化对“人”的定义不一定就等于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情 况。事实上,所谓“存在主义”只是西方的少数人的哲学。不过,这 个西方文化典型的产品却可以使我们看出该文化的倾向。在另 一方面,中国人社群性的偏向也不等于说没有了“个体”,只是使 “个体”的表现比较隐而不彰,而其表现形态亦有异于西方。此 外,在任何文化中,都会出现比较抽离现实层次的知识阶层。因 此,在传统士大夫阶层身上,也出现将具体的“二人”对应关系提 升为一种“仁”的普遍原则,以之作为“个体”的存在基础。不过,即 使是这个高层次的原则,仍然必须以“二人”之间衍生的“人情”作 为内容,因此亦同样可以使我们看出中国文化的偏向。 中国人的“仁”指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心意 感遍,亦即是“以心换心”,并且,在这种双方心意感通的过程中, 理想的行径必须是处处以对方为重。中国人的“礼让”其实正是 这种关系的外在表现。这种对“人”的设计,一般地使中国人富 于“人情味”,亦即是:在面对相识的人时,不轻于拒绝别人的要 求,急人之难,忘我地为别人办事,以及自己多吃一点亏也无所 谓的作风。此外,一旦当人际关系建立起来后,就有趋于持久稳 定的倾向,例如,不忘故旧,维持终身的朋友关系与婚姻关系,等 等。笔者发觉:这类倾向,在大陆比台湾浓厚,在台湾又比香港 浓厚。因此,共产党提猖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似乎 与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关系,而其实是中国人处处以对方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