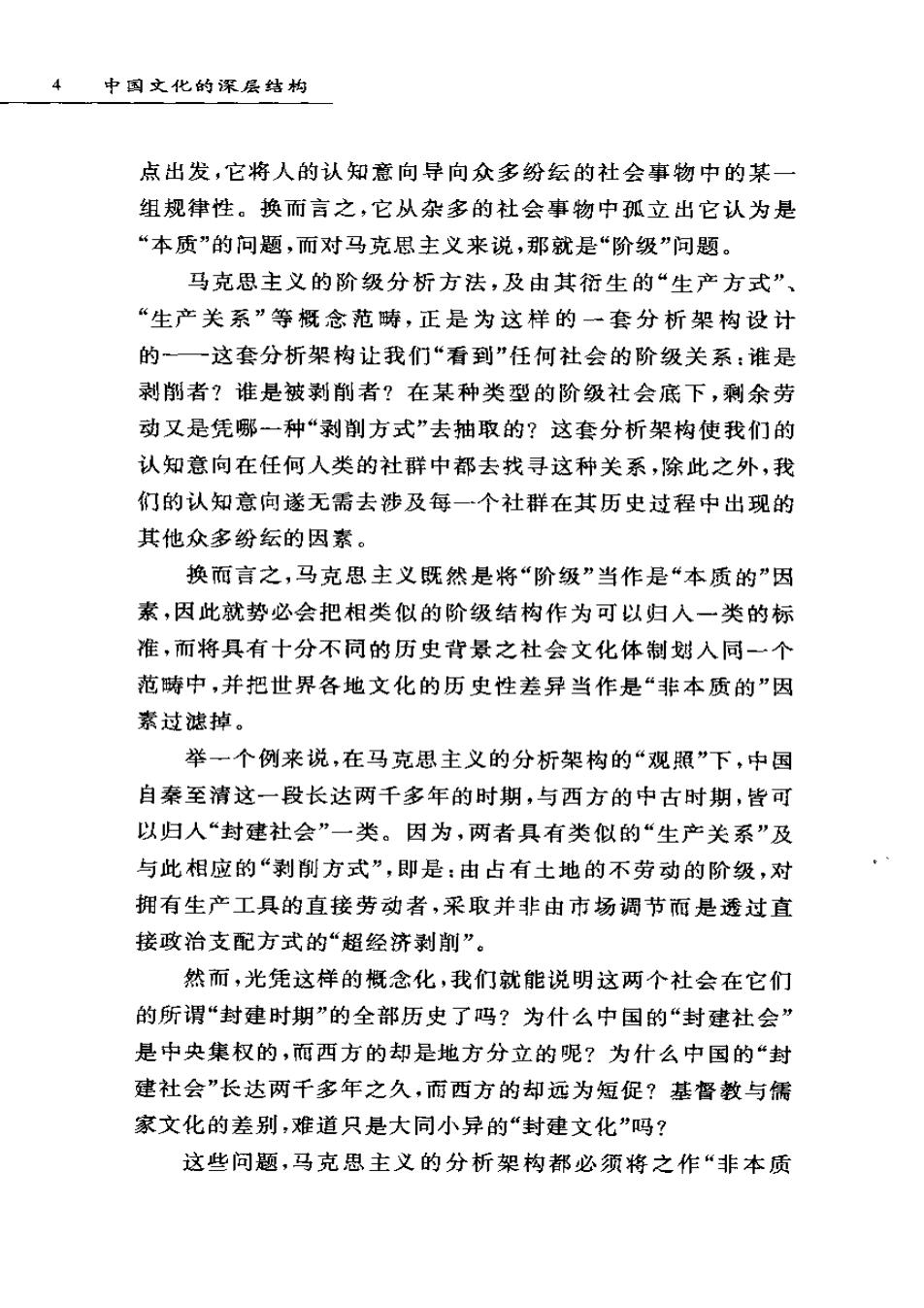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点出发,它将人的认知意向导向众多纷纭的社会事物中的某一 组规律性。换而言之,它从杂多的社会事物中孤立出它认为是 “本质”的问题,而对马克思主义来说,那就是“阶级”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及由其衍生的“生产方式” “生产关系”等概念范畴,正是为这样的一套分析架构设计 的一这套分析架构让我们“看到”任何社会的阶级关系:谁是 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在某种类型的阶级社会底下,剩余劳 动又是凭哪一种“剥削方式”去抽取的?这套分析架构使我们的 认知意向在任何人类的社群中都去找寻这种关系,除此之外,我 们的认知意向遂无需去涉及每一一个社群在其历史过程中出现的 其他众多纷纭的因素。 换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既然是将“阶级”当作是“本质的”因 素,因此就势必会把相类似的阶级结构作为可以归入一类的标 准,而将具有十分不同的历史背景之社会文化体制划入同一个 范畴中,并把世界各地文化的历史性差异当作是“非本质的”因 素过滤掉。 举一个例来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架构的“观照”下,中国 自秦至清这一段长达两千多年的时期,与西方的中古时期,皆可 以归人“封建社会”一类。因为,两者具有类似的“生产关系”及 与此相应的“剥削方式”,即是:由占有土地的不劳动的阶级,对 拥有生产工具的直接劳动者,采取并非由市场调节而是透过直 接政治支配方式的“超经济剥削”。 然而,光凭这样的概念化,我们就能说明这两个社会在它们 的所谓“封建时期”的全部历史了吗?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 是中央集权的,而西方的却是地方分立的呢?为什么中国的“封 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之久,而西方的却远为短促?基督教与儒 家文化的差别,难道只是大同小异的“封建文化”吗? 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架构都必须将之作“非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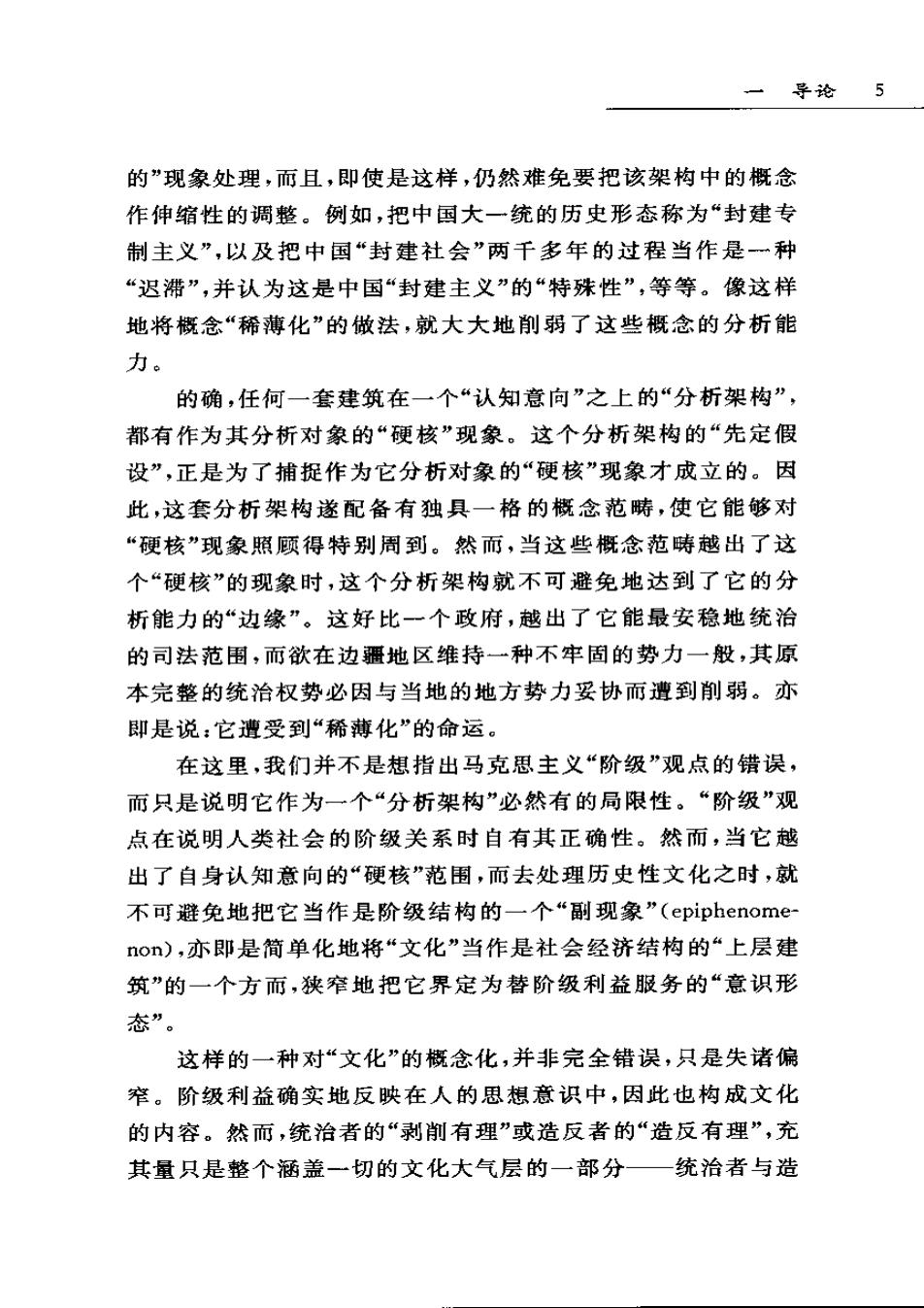
一导论5 的”现象处理,而且,即使是这样,仍然难免要把该架构中的概念 作伸缩性的调整。例如,把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形态称为“封建专 制主义”,以及把中国“封建社会”两干多年的过程当作是一种 “迟滞”,并认为这是中国“封建主义”的“特殊性”,等等。像这样 地将概念“稀薄化”的做法,就大大地削弱了这些概念的分析能 力。 的确,任何一套建筑在一个“认知意向”之上的“分析架构”, 都有作为其分析对象的“硬核”现象。这个分析架构的“先定假 设”,正是为了捕捉作为它分析对象的“硬核”现象才成立的。因 此,这套分析架构遂配备有独具一格的概念范畴,使它能够对 “硬核”现象照顾得特别周到。然而,当这些概念范畴越出了这 个“硬核”的现象时,这个分析架构就不可避免地达到了它的分 析能力的“边缘”。这好比一个政府,越出了它能最安稳地统治 的司法范围,而欲在边疆地区维持一种不牢固的势力一般,其原 本完整的统治权势必因与当地的地方势力妥协而遭到削弱。亦 即是说:它遭受到“稀薄化”的命运。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指出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错误, 而只是说明它作为一个“分析架构”必然有的局限性。“阶级”观 点在说明人类社会的阶级关系时自有其正确性。然而,当它越 出了自身认知意向的“硬核”范围,而去处理历史性文化之时,就 不可避免地把它当作是阶级结构的一个“副现象”(epiphenome- non),亦即是简单化地将“文化”当作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 筑”的一个方而,狭窄地把它界定为替阶级利益服务的“意识形 态”。 这样的一种对“文化”的概念化,并非完全错误,只是失诸偏 窄。阶级利益确实地反映在人的思想意识中,因此也构成文化 的内容。然而,统治者的“剥削有理”或造反者的“造反有理”,充 其量只是整个涵盖一切的文化大气层的一部分—统治者与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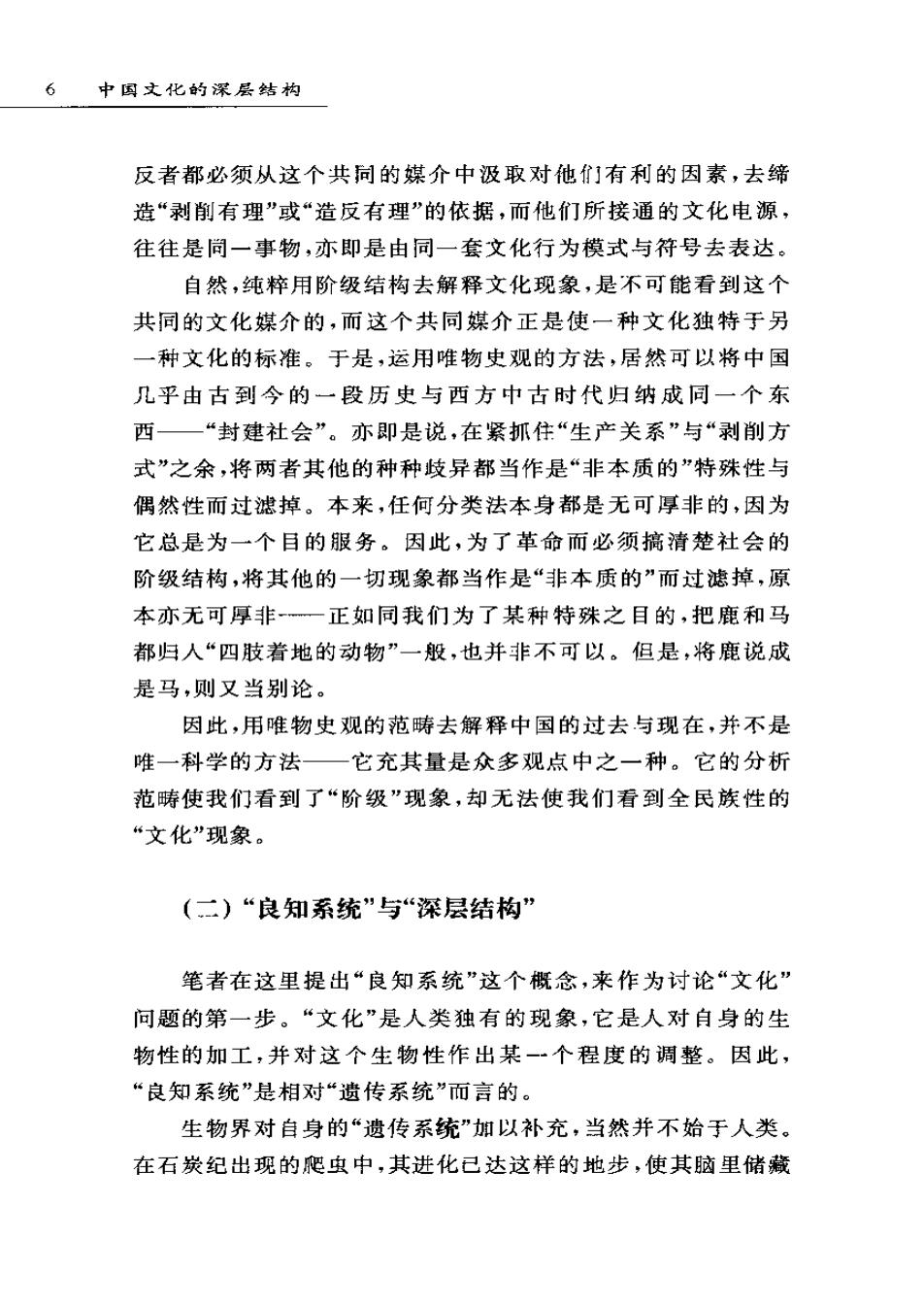
6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反者都必须从这个共同的媒介中汲取对他]有利的因素,去缔 造“剥削有理”或“造反有理”的依据,而他们所接通的文化电源, 往往是同一事物,亦即是由同一套文化行为模式与符号去表达。 自然,纯粹用阶级结构去解释文化现象,是不可能看到这个 共同的文化媒介的,而这个共同媒介正是使一种文化独特于另 一种文化的标准。于是,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居然可以将中国 几乎由古到今的一段历史与西方中古时代归纳成同一个东 西一“封建社会”。亦即是说,在紧抓住“生产关系”与“剥削方 式”之余,将两者其他的种种歧异都当作是“非本质的”特殊性与 偶然性而过滤掉。本来,任何分类法本身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 它总是为一个目的服务。因此,为了革命而必须搞清楚社会的 阶级结构,将其他的一切现象都当作是“非本质的”而过滤掉,原 本亦无可厚非一正如同我们为了某种特殊之目的,把鹿和马 都归人“四肢着地的动物”一般,也并非不可以。但是,将鹿说成 是马,则又当别论。 因此,用唯物史观的范畴去解释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并不是 唯一科学的方法一它充其量是众多观点中之一种。它的分析 范畴使我们看到了“阶级”现象,却无法使我们看到全民族性的 “文化”现象。 (二)“良知系统”与“深层结构” 笔者在这里提出“良知系统”这个概念,来作为讨论“文化” 问题的第一步。“文化”是人类独有的现象,它是人对自身的生 物性的加工,并对这个生物性作出某-一个程度的调整。因此, “良知系统”是相对“遗传系统”而言的。 生物界对自身的“遗传系统”加以补充,当然并不始于人类。 在石炭纪出现的爬虫中,其进化已达这样的地步,使其脑里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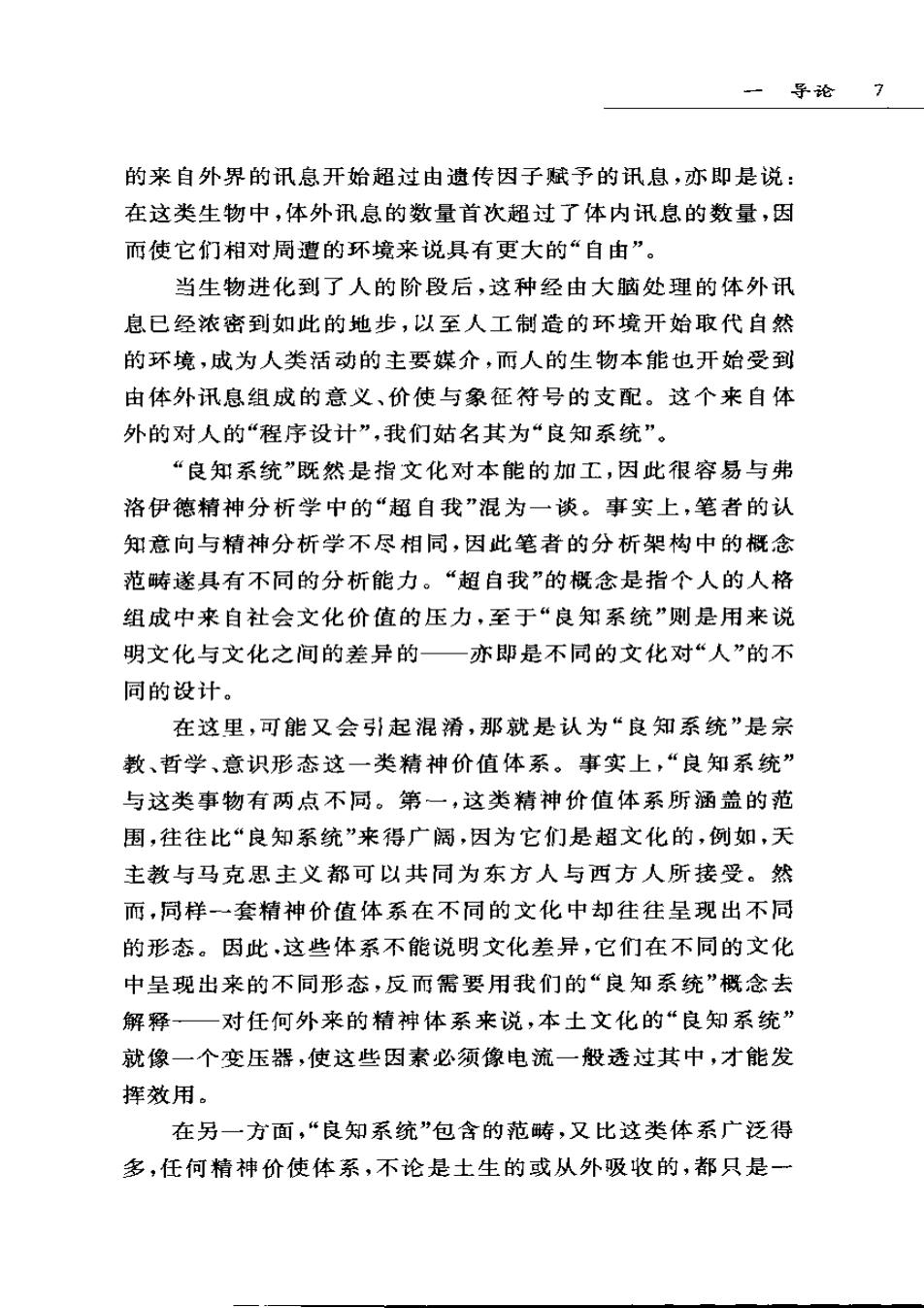
一导论 的来自外界的讯息开始超过由遗传因子赋予的讯息,亦即是说: 在这类生物中,体外讯息的数量首次超过了体内讯息的数量,因 而使它们相对周遭的环境来说具有更大的“自由”。 当生物进化到了人的阶段后,这种经由大脑处理的体外讯 息已经浓密到如此的地步,以至人工制造的环境开始取代自然 的环境,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媒介,而人的生物本能也开始受到 由体外讯息组成的意义、价使与象征符号的支配。这个来自体 外的对人的“程序设计”,我们姑名其为“良知系统”。 “良知系统”既然是指文化对本能的加工,因此很容易与弗 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超自我”混为一谈。事实上,笔者的认 知意向与精神分析学不尽相同,因此笔者的分析架构中的概念 范畴遂具有不同的分析能力。“超自我”的概念是指个人的人格 组成中来自社会文化价值的压力,至于“良知系统”则是用来说 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的一亦即是不同的文化对“人”的不 同的设计。 在这里,可能又会引起混滑,那就是认为“良知系统”是宗 教、哲学、意识形态这一类精神价值体系。事实上,“良知系统” 与这类事物有两点不同。第一,这类精神价值体系所涵盖的范 围,往往比“良知系统”来得广阔,因为它们是超文化的,例如,天 主教与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共同为东方人与西方人所接受。然 而,同样一套精神价值体系在不同的文化中却往往呈现出不同 的形态。因此,这些体系不能说明文化差异,它们在不同的文化 中呈现出来的不同形态,反而需要用我们的“良知系统”概念去 解释一对任何外来的精神体系来说,本土文化的“良知系统” 就像一个变压器,使这些因素必须像电流一般透过其中,才能发 挥效用。 在另一方面,“良知系统”包含的范畴,又比这类体系广泛得 多,任何精神价使体系,不论是土生的或从外吸收的,都只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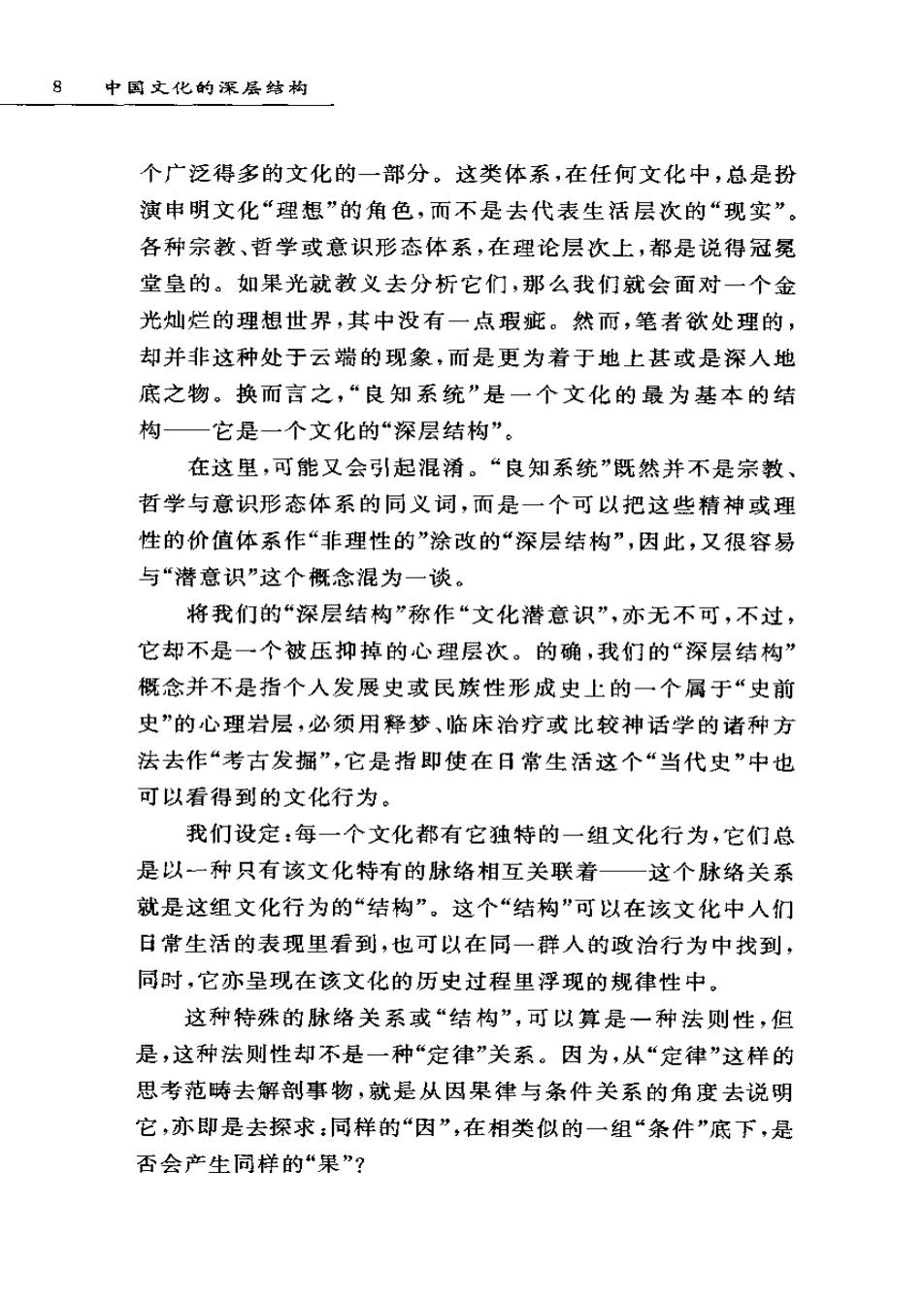
8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个广泛得多的文化的一部分。这类体系,在任何文化中,总是扮 演申明文化“理想”的角色,而不是去代表生活层次的“现实”。 各种宗教、哲学或意识形态体系,在理论层次上,都是说得冠冕 堂皇的。如果光就教义去分析它们,那么我们就会面对一个金 光灿烂的理想世界,其中没有一点瑕疵。然而,笔者欲处理的, 却并非这种处于云端的现象,而是更为着于地上甚或是深人地 底之物。换而言之,“良知系统”是一个文化的最为基本的结 构一它是一个文化的“深层结构”。 在这里,可能又会引起混淆。“良知系统”既然并不是宗教、 哲学与意识形态体系的同义词,而是一个可以把这些精神或理 性的价值体系作“非理性的”涂改的“深层结构”,因此,又很容易 与“潜意识”这个概念混为一谈。 将我们的“深层结构”称作“文化潜意识”,亦无不可,不过, 它却不是一个被压抑掉的心理层次。的确,我们的“深层结构 概念并不是指个人发展史或民族性形成史上的一个属于“史前 史”的心理岩层,必须用释梦、临床治疗或比较神话学的诸种方 法去作“考古发掘”,它是指即使在日常生活这个“当代史”中也 可以看得到的文化行为。 我们设定: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独特的一组文化行为,它们总 是以一种只有该文化特有的脉络相互关联着—这个脉络关系 就是这组文化行为的“结构”。这个“结构”可以在该文化中人们 日常生活的表现里看到,也可以在同一群人的政治行为中找到, 同时,它亦呈现在该文化的历史过程里浮现的规律性中。 这种特殊的脉络关系或“结构”,可以算是一种法则性,但 是,这种法则性却不是一种“定律”关系。因为,从“定律”这样的 思考范畴去解剖事物,就是从因果律与条件关系的角度去说明 它,亦即是去探求:同样的“因”,在相类似的一组“条件”底下,是 否会产生同样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