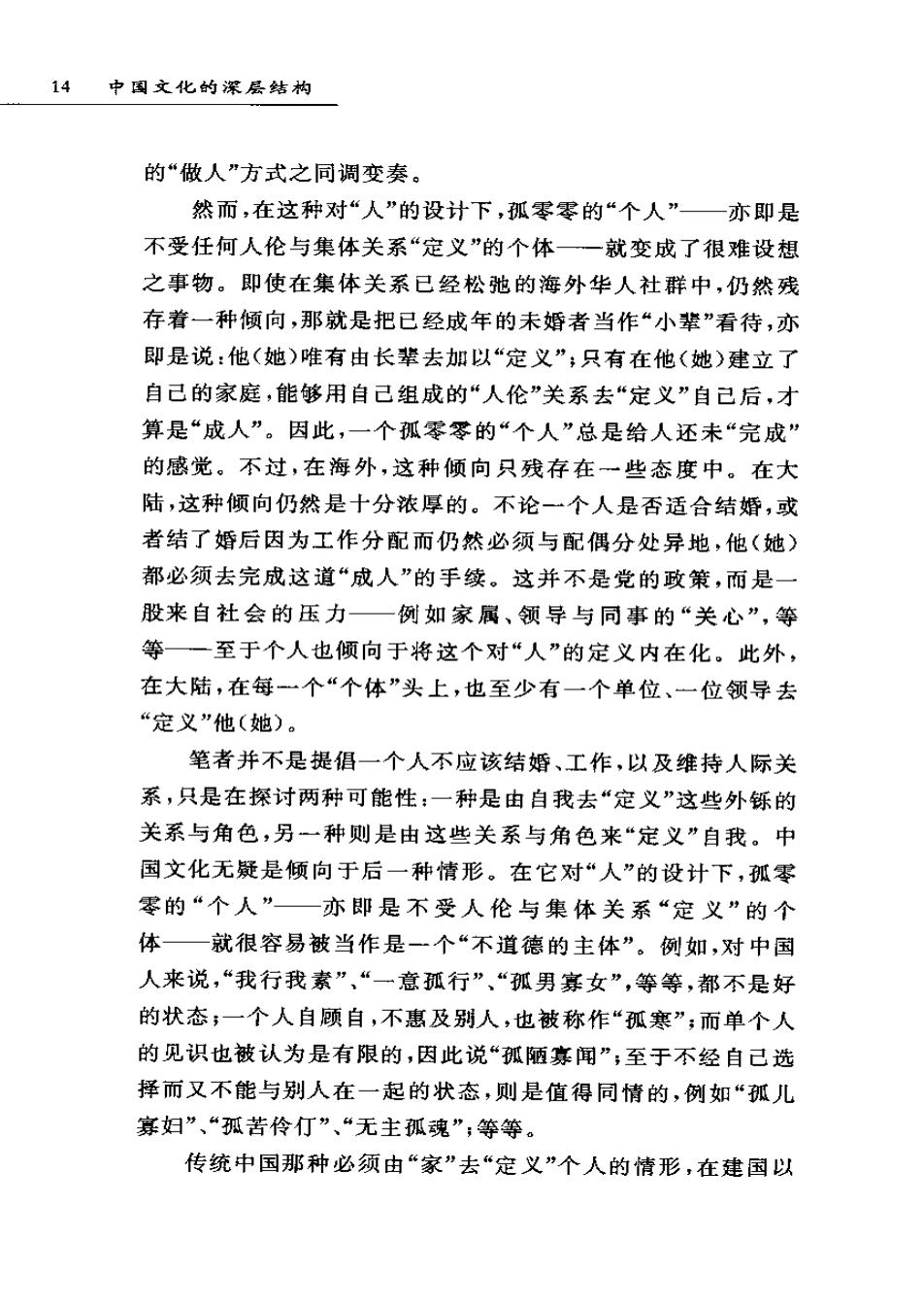
14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的“做人”方式之同调变奏。 然而,在这种对“人”的设计下,孤零零的“个人”一亦即是 不受任何人伦与集体关系“定义”的个体一一就变成了很难设想 之事物。即使在集体关系已经松弛的海外华人社群中,仍然残 存着一种倾向,那就是把已经成年的未婚者当作“小辈”看待,亦 即是说:他(她)唯有由长辈去加以“定义”:只有在他(她)建立了 自己的家庭,能够用自己组成的“人伦”关系去“定义”自己后,才 算是“成人”。因此,一个孤零零的“个人”总是给人还未“完成” 的感觉。不过,在海外,这种倾向只残存在一些态度中。在大 陆,这种倾向仍然是十分浓厚的。不论一个人是否适合结婚,或 者结了婚后因为工作分配而仍然必须与配偶分处异地,他(她) 都必须去完成这道“成人”的手续。这并不是党的政策,而是一 股来自社会的压力一例如家属、领导与同事的“关心”,等 等一至于个人也倾向于将这个对“人”的定义内在化。此外, 在大陆,在每一个“个体”头上,也至少有一个单位、一位领导去 “定义”他(她)。 笔者并不是提倡一个人不应该结婚、工作,以及维持人际关 系,只是在探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由自我去“定义”这些外铄的 关系与角色,另一种则是由这些关系与角色来“定义”自我。中 国文化无疑是倾向于后一种情形。在它对“人”的设计下,孤零 零的“个人”一—亦即是不受人伦与集体关系“定义”的个 体—就很容易被当作是一个“不道德的主体”。例如,对中国 人来说,“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孤男寡女”,等等,都不是好 的状态;一个人自顾自,不惠及别人,也被称作“孤寒”,而单个人 的见识也被认为是有限的,因此说“孤陋寡闻”;至于不经自己选 择而又不能与别人在一起的状态,则是值得同情的,例如“孤儿 寡妇”、“孤苦伶仃”、“无主孤魂”,等等。 传统中国那种必须由“家”去“定义”个人的情形,在建国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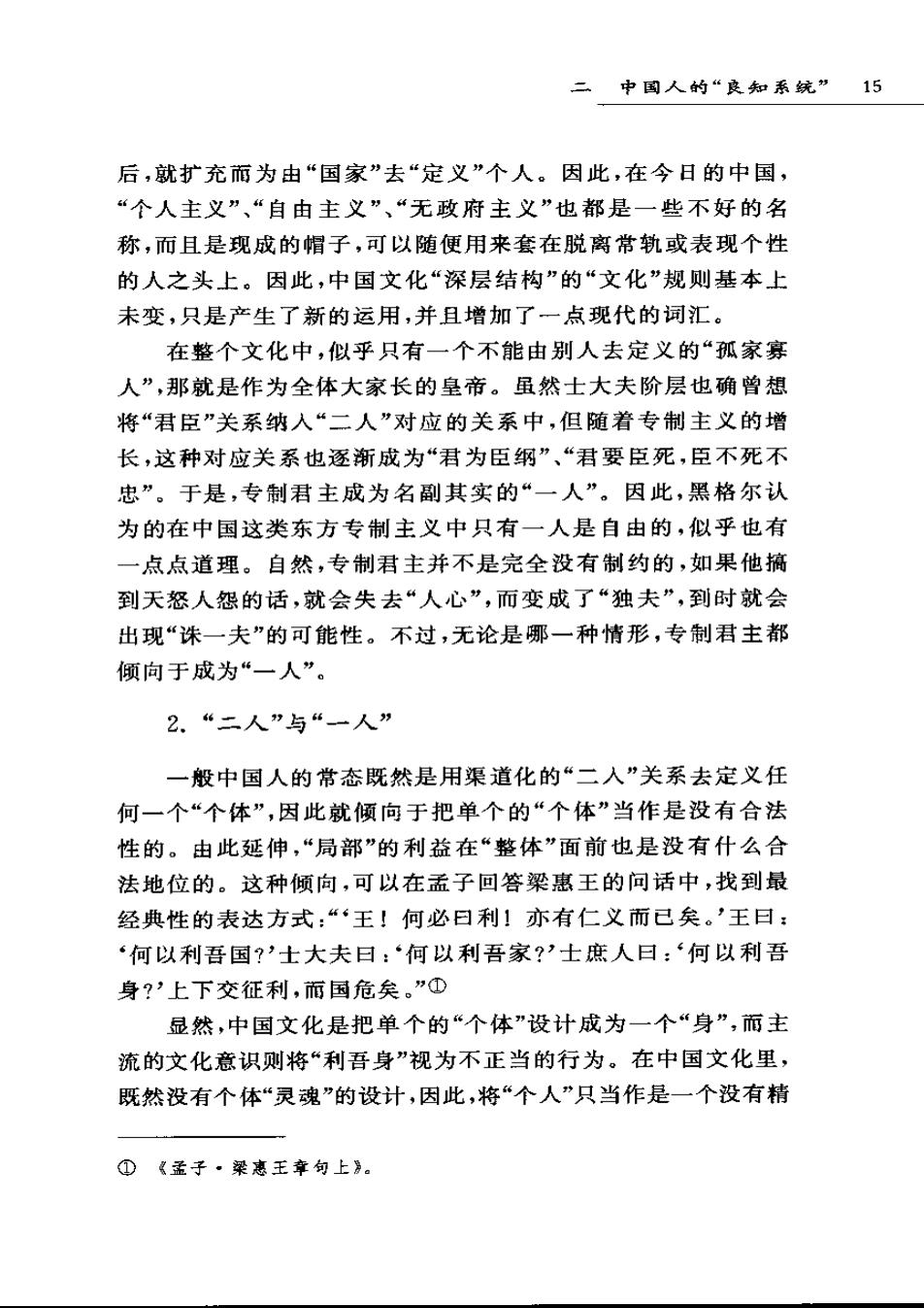
二中国人的“良知系统”15 后,就扩充而为由“国家”去“定义”个人。因此,在今日的中国,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也都是一些不好的名 称,而且是现成的帽子,可以随便用来套在脱离常轨或表现个性 的人之头上。因此,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文化”规则基本上 未变,只是产生了新的运用,并且增加了一点现代的词汇。 在整个文化中,似乎只有一个不能由别人去定义的“孤家寡 人”,那就是作为全体大家长的皇帝。虽然士大夫阶层也确曾想 将“君臣”关系纳人“二人”对应的关系中,但随着专制主义的增 长,这种对应关系也逐渐成为“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死不 忠”。于是,专制君主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人”。因此,黑格尔认 为的在中国这类东方专制主义中只有一人是自由的,似乎也有 一点点道理。自然,专制君主并不是完全没有制约的,如果他搞 到天怒人怨的话,就会失去“人心”,而变成了“独夫”,到时就会 出现“诛一夫”的可能性。不过,无论是哪一种情形,专制君主都 倾向于成为“一人”。 2.“二人”与“一人” 一般中国人的常态既然是用渠道化的“二入”关系去定义任 何一个“个体”,因此就倾向于把单个的“个体”当作是没有合法 性的。由此延伸,“局部”的利益在“整体”面前也是没有什么合 法地位的。这种倾向,可以在孟子回答梁惠王的问话中,找到最 经典性的表达方式:“王!何必日利1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日: ‘何以利吾国?’士大夫日:‘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日:‘何以利吾 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① 显然,中国文化是把单个的“个体”设计成为一个“身”,而主 流的文化意识则将“利吾身”视为不正当的行为。在中国文化里, 既然没有个体“灵魂”的设计,因此,将“个人”只当作是一个没有精 ①《孟子·梁惠王车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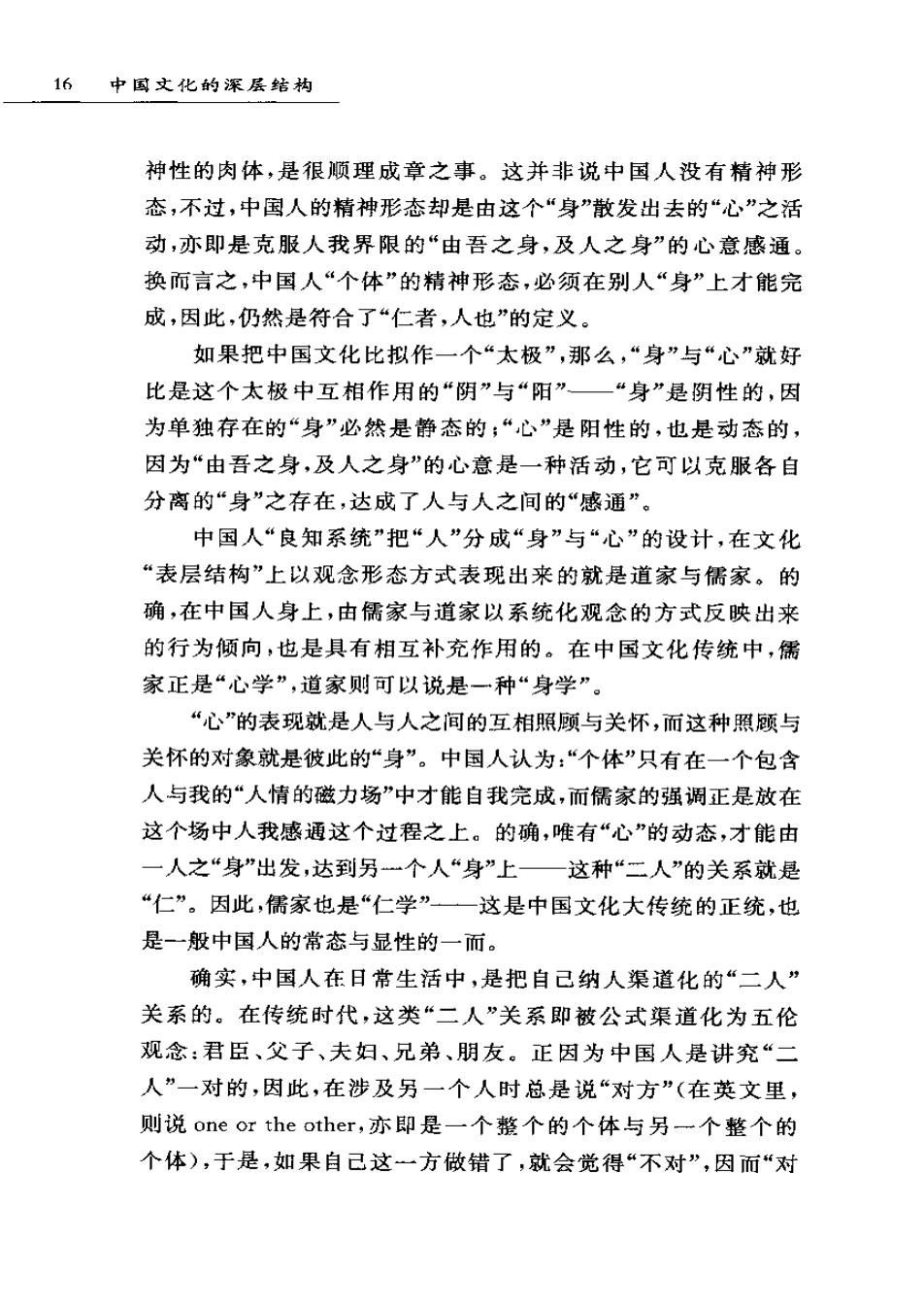
16 中国丈化的深层结构 神性的肉体,是很顺理成章之事。这并非说中国人没有精神形 态,不过,中国人的精神形态却是由这个“身”散发出去的“心”之活 动,亦即是克服人我界限的“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心意感通。 换而言之,中国人“个体”的精神形态,必须在别人“身”上才能完 成,因此,仍然是符合了“仁者,人也”的定义。 如果把中国文化比拟作一个“太极”,那么,“身”与“心”就好 比是这个太极中互相作用的“阴”与“阳”一“身”是阴性的,因 为单独存在的“身”必然是静态的,“心”是阳性的,也是动态的, 因为“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心意是一种活动,它可以克服各自 分离的“身”之存在,达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感通”。 中国人“良知系统”把“人”分成“身”与“心”的设计,在文化 “表层结构”上以观念形态方式表现出来的就是道家与儒家。的 确,在中国人身上,由儒家与道家以系统化观念的方式反映出来 的行为倾向,也是具有相互补充作用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儒 家正是“心学”,道家则可以说是一种“身学”。 “心”的表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照顾与关怀,而这种照顾与 关怀的对象就是彼此的“身”。中国人认为:“个体”只有在一个包含 人与我的“人情的磁力场”中才能自我完成,而儒家的强调正是放在 这个场中人我感通这个过程之上。的确,唯有“心”的动态,才能由 一人之“身”出发,达到另一个人“身”上一这种“二人”的关系就是 “仁”。因此,儒家也是“仁学”一这是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正统,也 是一般中国人的常态与显性的一而。 确实,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是把自己纳人渠道化的“二人” 关系的。在传统时代,这类“二人”关系即被公式渠道化为五伦 观念: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正因为中国人是讲究“二 人”一对的,因此,在涉及另一个人时总是说“对方”(在英文里, 则说one or the other,亦即是一个整个的个体与另一个整个的 个体),于是,如果自己这一方做错了,就会觉得“不对”,因而“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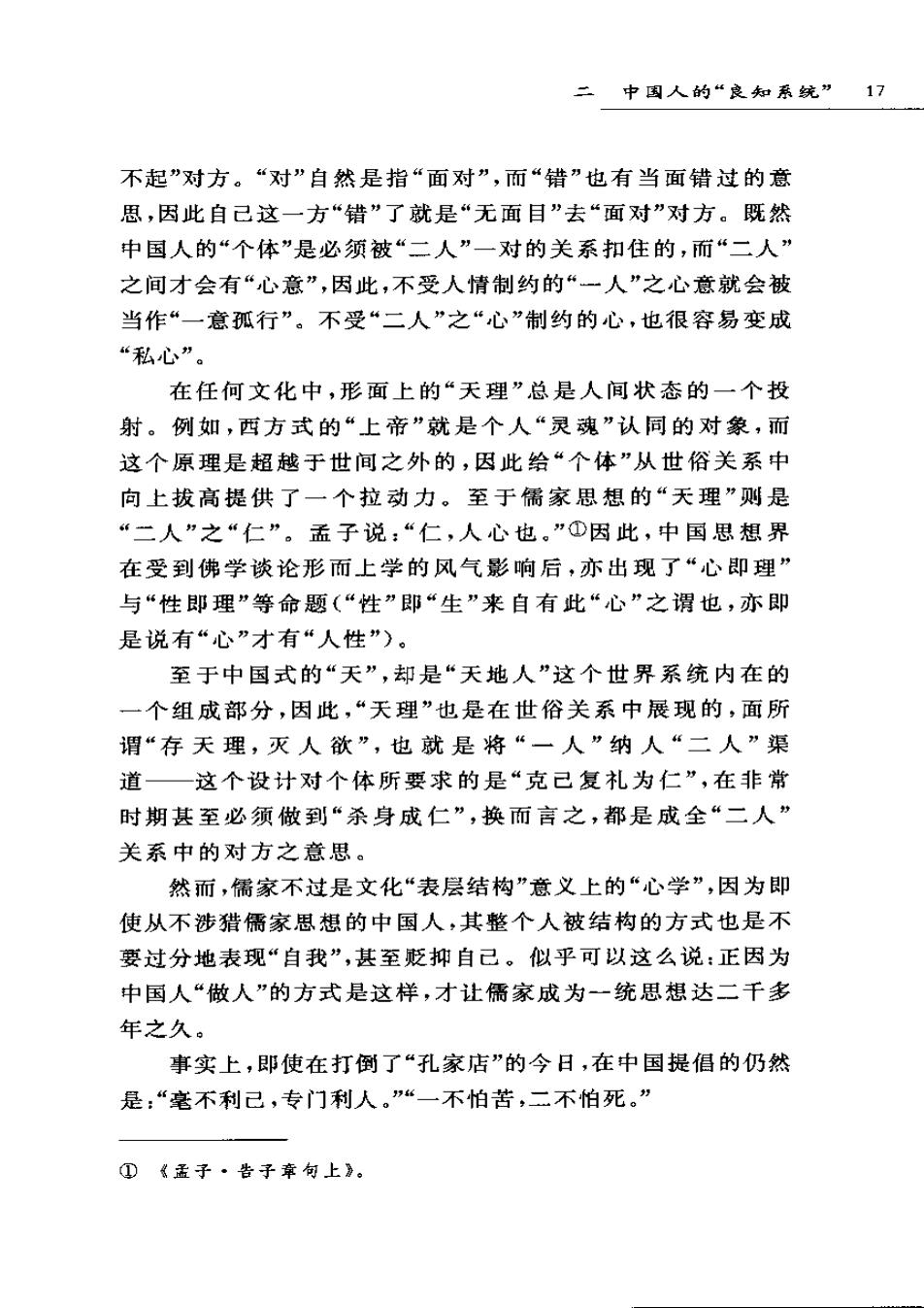
二中国人的“良知系统”17 不起”对方。“对”自然是指“面对”,而“错”也有当面错过的意 思,因此自己这一方“错”了就是“无面目”去“面对”对方。既然 中国人的“个体”是必须被“二人”一对的关系扣住的,而“二人” 之间才会有“心意”,因此,不受人情制约的“一人”之心意就会被 当作“一意孤行”。不受“二人”之“心”制约的心,也很容易变成 “私心”。 在任何文化中,形面上的“天理”总是人间状态的一个投 射。例如,西方式的“上帝”就是个人“灵魂”认同的对象,而 这个原理是超越于世间之外的,因此给“个体”从世俗关系中 向上拔高提供了一个拉动力。至于儒家思想的“天理”则是 “二人”之“仁”。孟子说:“仁,人心也。”①因此,中国思想界 在受到佛学谈论形而上学的风气影响后,亦出现了“心即理” 与“性即理”等命题(“性”即“生”来自有此“心”之谓也,亦即 是说有“心”才有“人性”)。 至于中国式的“天”,却是“天地人”这个世界系统内在的 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天理”也是在世俗关系中展现的,面所 谓“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将“一人”纳人“二人”渠 道一这个设计对个体所要求的是“克己复礼为仁”,在非常 时期甚至必须做到“杀身成仁”,换而言之,都是成全“二人” 关系中的对方之意思。 然而,儒家不过是文化“表层结构”意义上的“心学”,因为即 使从不涉猎儒家思想的中国人,其整个人被结构的方式也是不 要过分地表现“自我”,甚至贬抑自己。似乎可以这么说:正因为 中国人“做人”的方式是这样,才让儒家成为一统思想达二千多 年之久。 事实上,即使在打倒了“孔家店”的今日,在中国提倡的仍然 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①《孟子·告子率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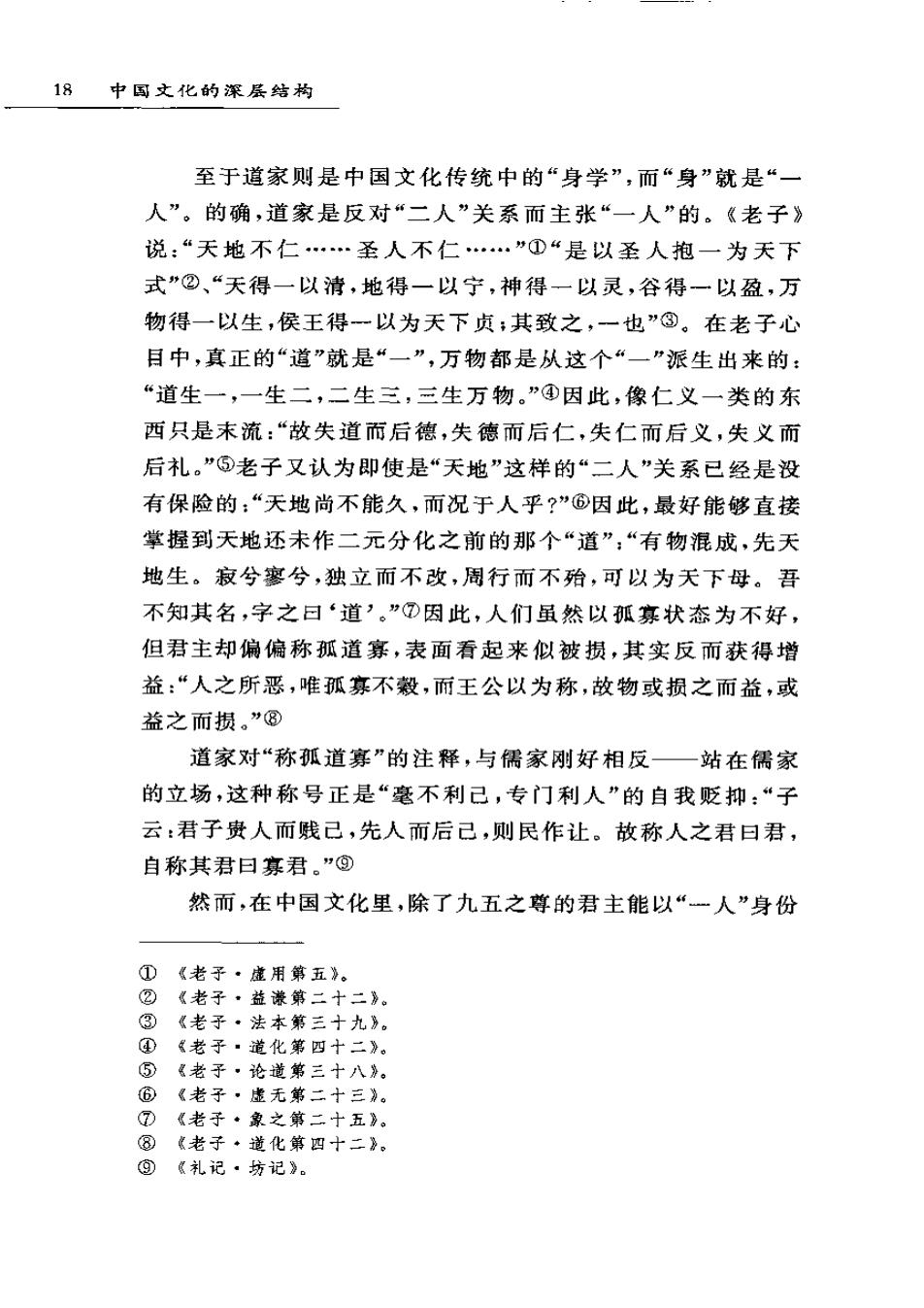
18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至于道家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身学”,而“身”就是“一 人”。的确,道家是反对“二人”关系而主张“一人”的。《老子》 说:“天地不仁.圣人不仁.”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 式”②、“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 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一也”③。在老子心 目中,真正的“道”就是“一”,万物都是从这个“一”派生出来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④因此,像仁义一类的东 西只是末流:“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 后礼。”⑤老子又认为即使是“天地”这样的“二人”关系已经是没 有保险的:“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⑥因此,最好能够直接 掌握到天地还未作二元分化之前的那个“道”,“有物混成,先天 地生。寂兮塞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 不知其名,字之日‘道’。”⑦因此,人们虽然以孤寡状态为不好, 但君主却偏偏称孤道寡,表面看起来似被损,其实反而获得增 益:“人之所恶,唯孤寡不毅,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 益之而损。”⑧ 道家对“称孤道寡”的注释,与儒家刚好相反一站在儒家 的立场,这种称号正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自我贬抑:“子 云:君子费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故称人之君曰君, 自称其君曰寡君。”⑨ 然而,在中国文化里,除了九五之尊的君主能以“一人”身份 ①《老子·崖用第五。 ②《老子·益谦第二十二》。 ③《老子·法本第三十九》。 ④《老子·道化第四十二》。 ⑤《老子·论道第三十八, 《老子·患无第二十三》。 ⑦《老子·象之第二十五》。 ⑧《老子·道化第四十二》, ⑨《礼记·坊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