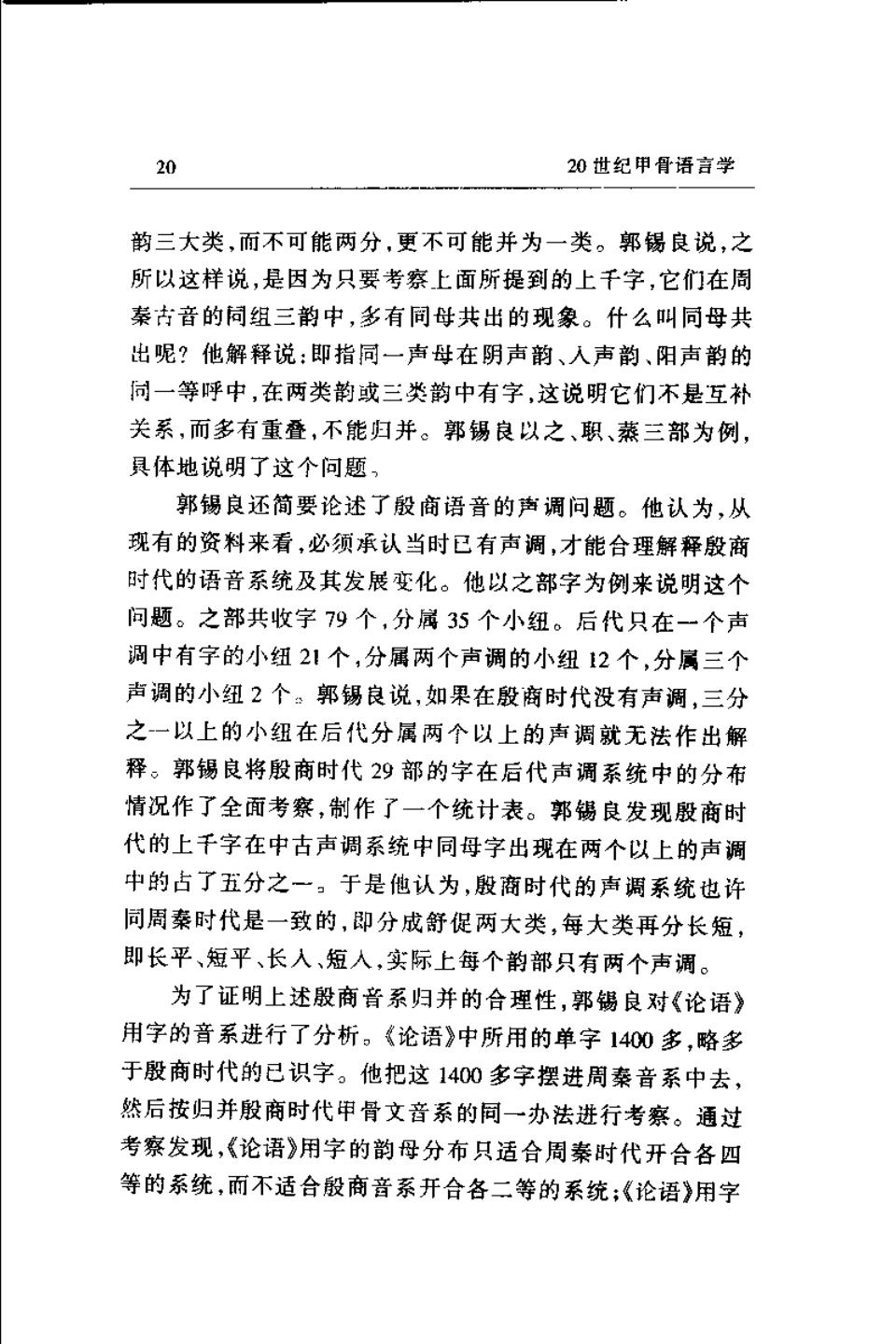
20 20世纪甲骨语言学 韵三大类,而不可能两分,更不可能并为一类。郭锡良说,之 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只要考察上面所提到的上千字,它们在周 秦古音的同组三韵中,多有同母共出的现象。什么叫同母共 出呢?他解释说:即指同一声母在阴声韵、入声韵、阳声韵的 同一等呼中,在两类韵或三类韵中有字,这说明它们不是互补 关系,而多有重叠,不能归并。郭锡良以之、职、蒸三部为例, 具体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郭锡良还简要论述了殷商语音的声调问题。他认为,从 现有的资料来看,必须承认当时已有声调,才能合理解释殷商 时代的语音系统及其发展变化。他以之部字为例来说明这个 问题。之部共收字79个,分属35个小纽。后代只在-一个声 调中有字的小纽2!个,分属两个声调的小纽2个,分属三个 声调的小纽2个郭锡良说,如果在殷商时代没有声调,三分 之一以上的小纽在后代分属两个以上的声调就无法作出解 释。郭锡良将殷商时代29部的字在后代声调系统中的分布 情况作了全面考察,制作了一个统计表。郭锡良发现殷商时 代的上千字在中古声调系统中同母字出现在两个以上的声调 中的古了五分之一。于是他认为,殷商时代的声调系统也许 同周秦时代是一致的,即分成舒促两大类,每大类再分长短, 即长平、短平、长入、短人,实际上每个韵部只有两个声调。 为了证明上述殷商音系归并的合理性,郭锡良对《论语》 用字的音系进行了分析。《论语》中所用的单字1400多,略多 于殷商时代的已识字。他把这1400多字摆进周秦音系中去, 然后按归并殷商时代甲骨文音系的同一办法进行考察。通过 考察发现,《论语》用字的韵母分布只适合周秦时代开合各四 等的系统,而不适合殷商音系开合各二等的系统;《论语》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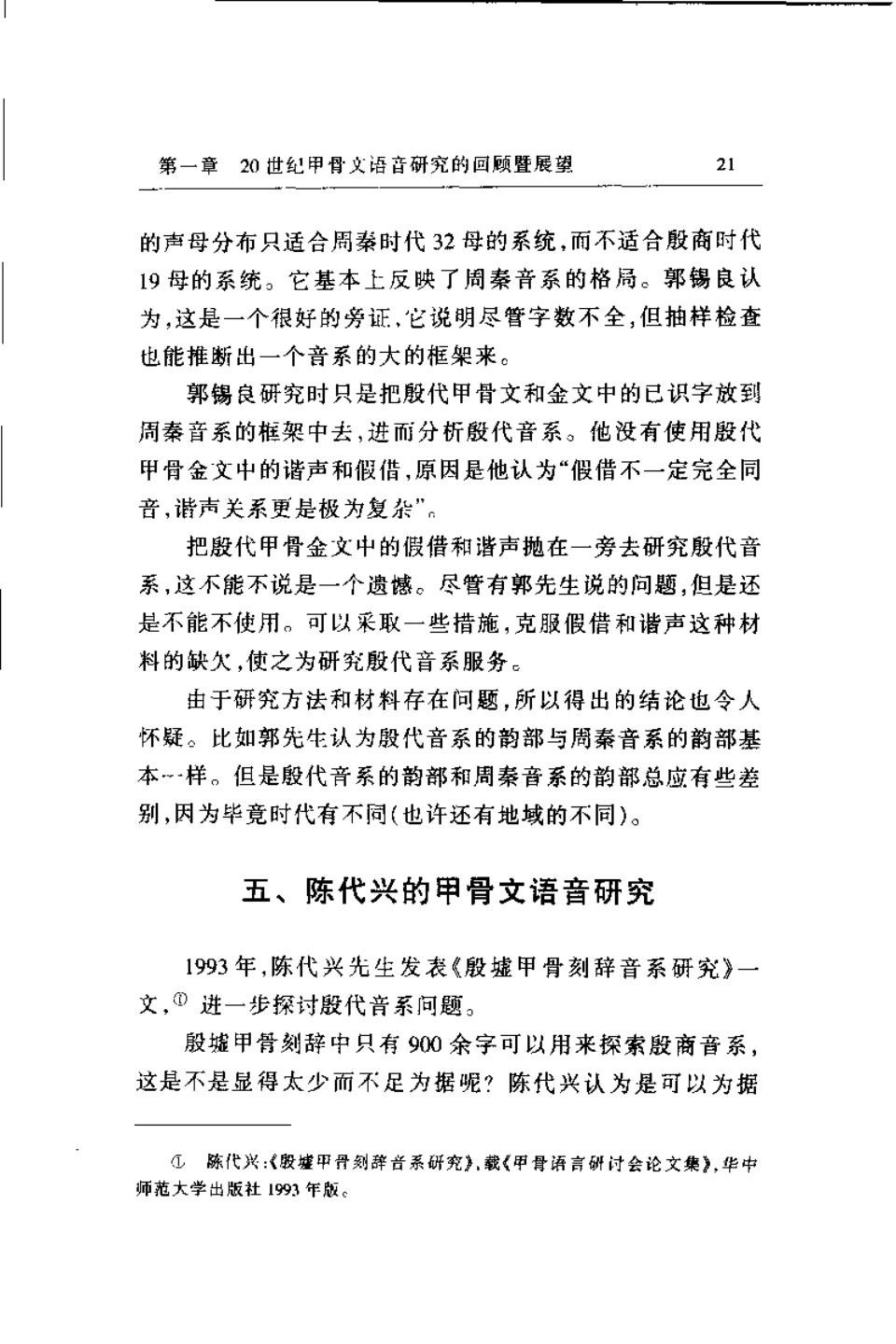
第一章20世甲骨文语音研究的回顾暨展望 21 的声母分布只适合周秦时代32母的系统,而不适合殷商时代 19母的系统。它基本上反映了周秦音系的格局。郭锡良认 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旁证,它说明尽管字数不全,但抽样检查 t也能推断出一个音系的大的框架来。 郭锡良研究时只是把殷代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已识字放到 周秦音系的框架中去,进而分析殷代音系。他没有使用殷代 甲骨金文中的谐声和假借,原因是他认为“假借不一定完全同 音,谐声关系更是极为复杂”。 把殷代甲骨金文中的假借和谐声抛在一旁去研究殷代音 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尽管有郭先生说的问题,但是还 是不能不使用。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克服假借和谐声这种材 料的缺欠,使之为研究殷代音系服务。 由于研究方法和材料存在问题,所以得出的结论也令人 怀疑。比如郭先生认为殷代音系的韵部与周秦音系的韵部基 本样。但是殷代音系的韵部和周秦音系的韵部总应有些差 别,因为毕竞时代有不同(也许还有地域的不同)。 五、陈代兴的甲骨文语音研究 1993年,陈代兴先生发表《殷墟甲骨刻辞音系研究》一 文,①进一步探讨殷代音系问题。 殷墟甲骨刻辞中只有900余字可以用来探索殷商音系, 这是不是显得太少而不足为据呢?陈代兴认为是可以为据 ①陈代兴:《股墟甲骨刻辞音系研究》,载《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华中 师范大学出版社93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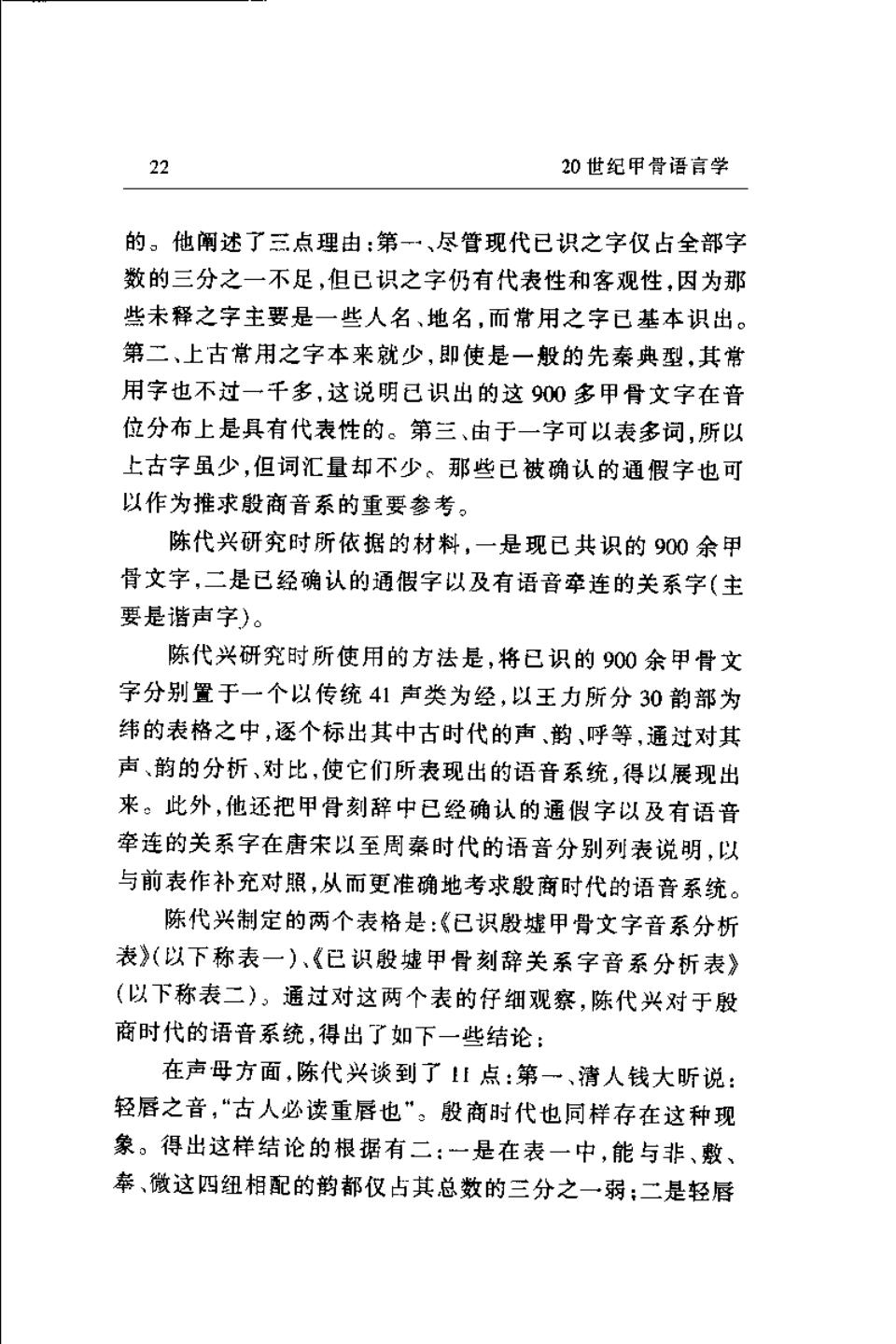
22 20世纪甲骨语言学 的。他阐述了二点理由:第一、尽管现代已识之字仅占全部字 数的三分之一不足,但已识之字仍有代表性和客观性,因为那 些未释之字主要是一些人名、地名,而常用之字已基本识出。 第二、上古常用之字本来就少,即使是一般的先秦典型,其常 用字也不过一千多,这说明已识出的这00多甲骨文字在音 位分布上是具有代表性的。第三、由于一字可以表多词,所以 上古字虽少,但词汇量却不少。那些已被确认的通假字也可 以作为推求殷商音系的重要参考。 陈代兴研究时所依据的材料,一是现已共识的900余甲 骨文字,二是已经确认的通假字以及有语音牵连的关系字(主 要是谐声字)。 陈代兴研究时所使用的方法是,将已识的900余甲骨文 字分别置于一个以传统41声类为经,以王力所分30韵部为 纬的表格之中,逐个标出其中古时代的声、韵、呼等,通过对其 声、韵的分析、对比,使它们所表现出的语音系统,得以展现出 来。此外,他还把甲骨刻辞中已经确认的通假字以及有语音 牵连的关系字在唐宋以至周秦时代的语音分别列表说明,以 与前表作补充对照,从而更准确地考求殷商时代的语音系统。 陈代兴制定的两个表格是:《已识殷墟甲骨文字音系分析 表》(以下称表一)、《已识殷墟甲骨刻辞关系字音系分析表》 (以下称表二),通过对这两个表的仔细观察,陈代兴对于殷 商时代的语音系统,得出了如下一些结论: 在声母方面,陈代兴谈到了f点:第一、清人钱大昕说: 轻唇之音,“古人必读重唇也”。殷商时代也同样存在这种现 象。得出这样结论的根据有二:一是在表一中,能与非、敷、 奉、微这四纽相配的韵都仅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一弱:二是轻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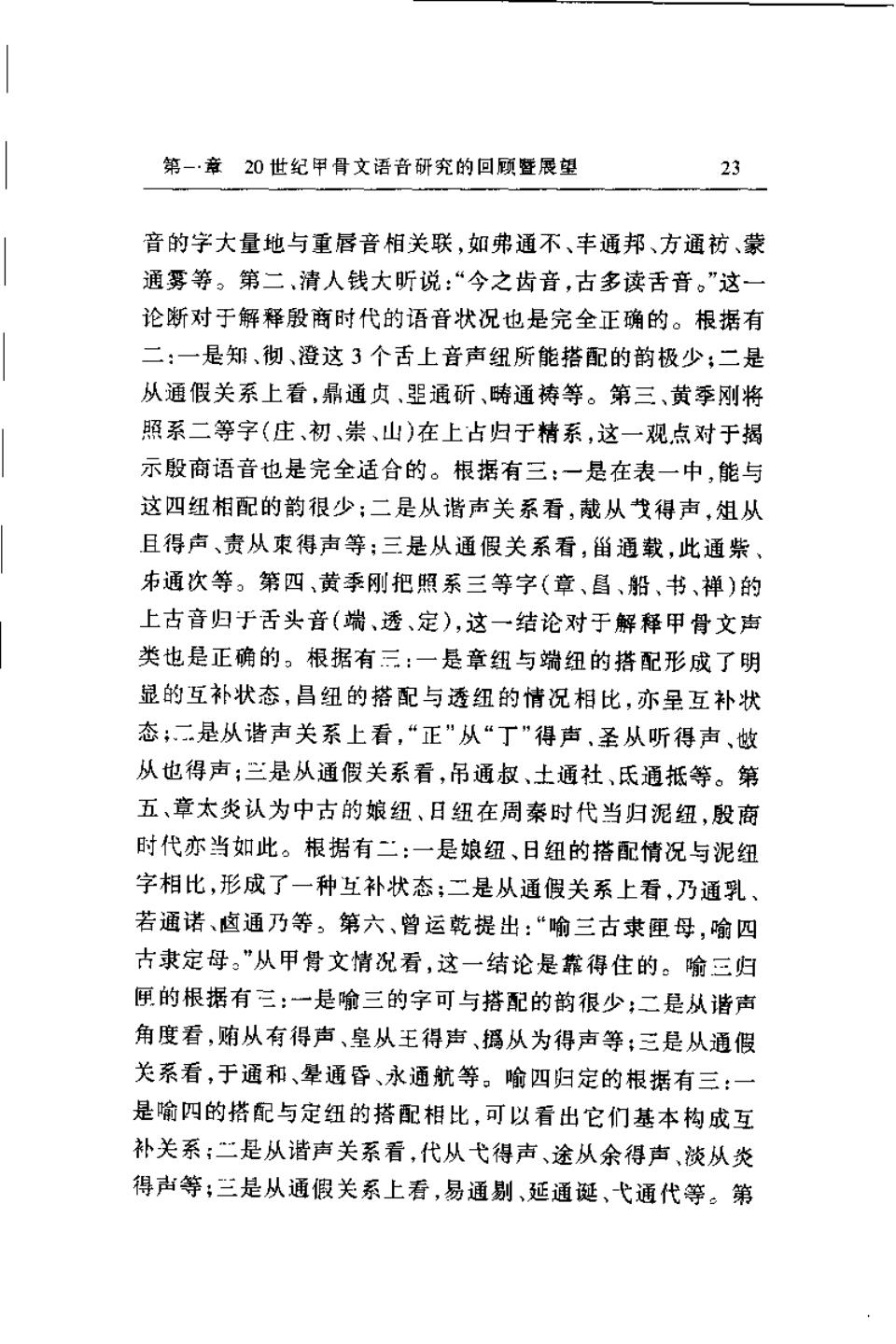
第-·章20世纪甲骨文语音研究的回顾暨展望 23 音的字大量地与重唇音相关联,如弗通不、丰通邦、方通祊、蒙 通雾等。第二、清人钱大昕说:“今之齿音,古多读舌音。”这一 论断对于解释殷商时代的语音状况也是完全正确的。根据有 二:一是知、彻、澄这3个舌上音声纽所能搭配的韵极少;二是 从通假关系上看,鼎通贞、里通斫、畴通祷等。第三、黄季刚将 照系二等字(庄、初、崇、山)在上占归于精系,这一观点对于揭 示殷商语音也是完全适合的。根据有三:一是在表一中,能与 这四纽相配的韵很少;二是从谐声关系看,裁从得声,俎从 且得声、责从束得声等:三是从通假关系看,甾通载,此通紫、 韦通次等。第四、黄季刚把照系三等字(章、昌、船、书、禅)的 上古音归于舌头音(端、透、定),这一结论对于解释甲骨文声 类也是正确的。根据有三:一是章纽与端纽的搭配形成了明 显的互补状态,昌纽的搭配与透纽的情况相比,亦呈互补状 态:是从谐声关系上看,“正”从“丁”得声,圣从听得声、做 从也得声;三是从通假关系看,吊通叔、士通社、氐通抵等。第 五、章太炎认为中古的娘纽、日纽在周秦时代当归泥纽,殷商 时代亦当如此。根据有二:一是娘纽、日纽的搭配情况与泥纽 字相比,形成了一种互补状态:二是从通假关系上看,乃通乳、 若通诺、卤通乃等,第六、曾运乾提出:“喻三古隶匣母,喻四 古隶定母。”从甲骨文情况看,这一结论是靠得住的。喻三归 匣的根据有三:一是喻三的字可与搭配的韵很少;二是从谐声 角度看,贿从有得声、皇从王得声、搦从为得声等:三是从通假 关系看,于通和、晕通昏、永通航等。喻四归定的根据有三:一 是喻四的搭配与定纽的搭配相比,可以看出它们基本构成互 补关系;二是从谐声关系看,代从弋得声、途从余得声、淡从炎 得声等;三是从通假关系上看,易通剔,延通诞、弋通代等。第

24 20世纪甲骨语言学 1 七、认为邪纽在甲骨文时代是一个独立的声纽。虽有些迹象 表明这个声纽很难独立,但是这个声纽中的-一些字有一些与 精系相谐的字,如“已”和“子”同形,假为“嗣”,这是可独立的 证据。第八、认定甲骨文时代没有送气清音的声纽出现。根 据是在表一中,溪纽字远远少于见纽字、滂纽字远远少于帮纽 字、清纽字远远少于精纽字、透纽字远远少于端纽字、敷纽字 大大少于非纽字、初纽字少于庄纽字、昌纽字少于章纽字。第 九、虽然群母字在甲骨文时代是很少的,可与搭配的韵只有7 个,但群纽还是存在的。可以将本属溪纽的字并人群纽,这样 就可以解决群纽字少的问题。第十、确认在甲骨文时代同一 发音部位的声纽开始发生分化,故可以相互通转。根据有二: 一是从谐声关系看,如以“己”为声符的,己属见纽、杞属溪纽、 跽属群纽;又如以“辟”为声符的,嬖属帮纽、辟属并纽。二是 从通假关系看,如“骨”通祸,骨属见纽,祸属匣纽,又如帝通 楠,帝在端纽,褅在定纽。第十一、甲骨文中存在复辅音声母, 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h],如“每”,假作“悔”与“晦”;二是 [ml],如“令”与“命”同字;三是[pl],如“鄙”从“㐭”得形,“㐭” 乃“廪”之初文;四是[p门,如“夫”从“大”得声,“夫”乃“大”之 异构;二是[ph],如“凤”以“凡”为声,又有加“兄”为声符的;六 是[hl],如“位”从“立”得声;七是[d],如“籤”通“后”;八是 [kd,如“唐”从“庚”得声;九是[k],如“各”假为“落”,“落”从 “洛”得声,“洛”从“各”得声;十是[],如“鱼”与“鲁”同义。 最后,陈代兴得出的殷商时代的声母系统及其构拟如下: (一)单辅音声母: ①牙音:见{k] 群{g] 疑[n] ②喉音:晓[h] 匣[Y]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