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经验对解决中日两国历史问题的启示及其局限 本文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2期,作者:徐秀丽,原题:《欧洲经验对解决中日历 史问题的启示及其局限》 一、欧洲历史问题和东亚历史问题的相似性 (一)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有极强的关联。 无论欧洲还是东亚,都有改善双边关系、营造新的区域关系的强烈愿望,历史问题的解决有 助于和平友好国际关系的建立,而和平友好的国际关系符合相关国家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 益。这一点是共同历史研究之所以可能的现实基础。 邻国是“搬不走的邻居”,无论是否喜欢,都得在地域上共存,而“恶邻”显然会制约一个 国家的发展,在当前日益全球化的人类发展趋势中更是如此。对于有过战争和冲突经历的国 家间关系来说,历史问题从来都不只是,或者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学术问题,它与现实中的 国际关系紧密相连,现实既可以柔化也可以激化历史问题。 德国与法国和波兰的教科书合作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冷战时期的欧洲,德法属于同一战略阵 营,其国家利益有极强的关连性,而且,两国的政治精英都对在欧洲框架内建立和平共存关 系抱有兴趣。这一背景使德法历史教科书合作得以顺利展开,两国共同参与的“教科书联合 委员会”(joint Textbook Commission)于1951年开始召集,《德法关于欧洲历史争议问题的 协定》(German-French Agreement on Controversial Questions of Europe an History)也于该年 达成。德法两国共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第1册于2006年夏季出版,这可以视作到目前为止 教科书国际合作的最高成就。①尽管法国是德国主要的受害国之一,尽管“协定”达成之后 出版的教科书远非完美,但两国间从未出现过严重的教科书争议,也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关于 历史问题的争议,这主要归因于两国现实利益和未来目标的一致。 德国与波兰的教科书合作比德法合作要晚得多,也要困难得多。冷战时代,西德与波兰分属 不同的战略阵营,边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波兰对其西部地区的德籍人口采取强硬手段, 等等。这些因素使波兰与西德的关系紧张而脆弱,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产生了相互了解 和合作的愿望和需求。在德波教科书委员会(German-Polish Textbook Commission)于1972 年组成之前,己经有一些学者、教师和宗教人士对此进行了相当的努力:当教科书委员会成 立时,大多数成员对相关讨论并不陌生。但这一合作真正取得进展,是在德国总理威利。勃 兰特实行“新东方政策”、《华沙条约》签订之后。合作的道路显然充满争议和困难,而且, 1976年出版的《联邦德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建议书》(Recommendations for History and Geography Textbooks in the FRG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 的第一印象仍然是各说各话。两国历史问题在1989年之后获得了全新的解决空间,1990 年代初期德波边界协定签署,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环境随之宽松,共识最终超越了分歧(虽 然也面临着新的问题)。② 中国和日本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议也与现实政治和外交关系息息相关。中日之间关于历史 问题的公开争议始于1980年代初期,1990年代之后日趋激化,这显然与中国经济的强劲
欧洲经验对解决中日两国历史问题的启示及其局限 本文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09 年第 2 期,作者:徐秀丽,原题:《欧洲经验对解决中日历 史问题的启示及其局限》 一、欧洲历史问题和东亚历史问题的相似性 (一)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有极强的关联。 无论欧洲还是东亚,都有改善双边关系、营造新的区域关系的强烈愿望,历史问题的解决有 助于和平友好国际关系的建立,而和平友好的国际关系符合相关国家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 益。这一点是共同历史研究之所以可能的现实基础。 邻国是“搬不走的邻居”,无论是否喜欢,都得在地域上共存,而“恶邻”显然会制约一个 国家的发展,在当前日益全球化的人类发展趋势中更是如此。对于有过战争和冲突经历的国 家间关系来说,历史问题从来都不只是,或者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学术问题,它与现实中的 国际关系紧密相连,现实既可以柔化也可以激化历史问题。 德国与法国和波兰的教科书合作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冷战时期的欧洲,德法属于同一战略阵 营,其国家利益有极强的关连性,而且,两国的政治精英都对在欧洲框架内建立和平共存关 系抱有兴趣。这一背景使德法历史教科书合作得以顺利展开,两国共同参与的“教科书联合 委员会”( joint Textbook Commission)于 1951 年开始召集,《德法关于欧洲历史争议问题的 协定》(German-French Agreement on Controversial Questions of Europe an History)也于该年 达成。德法两国共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第 1 册于 2006 年夏季出版,这可以视作到目前为止 教科书国际合作的最高成就。①尽管法国是德国主要的受害国之一,尽管“协定”达成之后 出版的教科书远非完美,但两国间从未出现过严重的教科书争议,也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关于 历史问题的争议,这主要归因于两国现实利益和未来目标的一致。 德国与波兰的教科书合作比德法合作要晚得多,也要困难得多。冷战时代,西德与波兰分属 不同的战略阵营,边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波兰对其西部地区的德籍人口采取强硬手段, 等等。这些因素使波兰与西德的关系紧张而脆弱,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产生了相互了解 和合作的愿望和需求。在德波教科书委员会(German-Polish Textbook Commission)于 1972 年组成之前,已经有一些学者、教师和宗教人士对此进行了相当的努力;当教科书委员会成 立时,大多数成员对相关讨论并不陌生。但这一合作真正取得进展,是在德国总理威利。勃 兰特实行“新东方政策”、《华沙条约》签订之后。合作的道路显然充满争议和困难,而且, 1976 年出版的《联邦德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建议书》(Recommendations for History and Geography Textbooks in the FRG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给读者 的第一印象仍然是各说各话。两国历史问题在 1989 年之后获得了全新的解决空间, 1990 年代初期德波边界协定签署,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环境随之宽松,共识最终超越了分歧(虽 然也面临着新的问题)。② 中国和日本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议也与现实政治和外交关系息息相关。中日之间关于历史 问题的公开争议始于 1980 年代初期, 1990 年代之后日趋激化,这显然与中国经济的强劲

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围际地帝提升、中日两国在风域政治和围际政治电角伍和影的力出现结 构性变动有密切的关系。③但是,由于两国共同利益和未来发展的一致性因素强大,最近十 余年来,虽然两国在历史问题上屡有争议 这种争议对两国相互关系尤其是对 民众的感情造 成极大的伤害,但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两国的交往,尤其是经济贸易领域的来往与合作。许 学者对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持乐观态度,有学者指出:“随着结构性的变动的延续和基本 趋势的明朗化,特别是在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真正建立,政治层面的问 颗能找到新的解决方法。”④新的政治框架出现,无疑会给两国间历史争议的解决带来有 利的环境,从中我们可以乐观地展望达成基本 共识的前景,也可以肯定,现在开展历史共同 研究、促进两国彻底 正当其时 总之,国际间历史问题争议的解决不是“悔罪”和“原谅”那么简单,它更多地是现实政治 经济关系的折射,但不能指望历史问题会“自行解决”,学者的努力、共同历史研究和教科 书合作的展开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本文所引施梅笛女士的两篇论文中都指出,共 同历史研究并不能充当达成历史共识的 但在有利的条件下, 形成指向相互理 解和共识的话语(dis-course),为双方提供沟通的渠道。这是欧洲经验给东亚历史研究的重 要启示。 (二)欧洲经验可以在合作策略上提供有益借鉴。 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开始国际间的历史共同研究和数科书合作,不但需要相关各方的诺 德和学识,而且需要智慧和策略。在这方面,欧洲的教科书合作在多方面值得借鉴,以下就 是若干例子。 1Claudia Schneider,The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 Issue -Viewed through the Prism of European Experienc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EastAsia。.感谢施梅笛女士提供该论文。该 教科书的第2册也已经出版。 ②H。C ack After the Wende:The Ge erman-Polish Textbook Project in Retrospect: Claudia Schneider, The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 Issue Viewed through th Prism of European Experienc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EastAsia: Professor Zernack的义 见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网站,www.gei。dea ③步平:《东亚地区能否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11月: Claudia schneider. The Jap e Hist in East Asian Perspective,The Annals of the An rican Acac emy of Politicaland Socia 2008) ④)步平:《历史认识如何跨越国境》,“历史教学与历史共识 东亚的比较视角”(德 国布伦瑞克,2008年10月)会议论文。 第一,政府采取相对超然的立场。 施梅笛女士指出,在德波被教科书合作中,就德方而言,国家干预事实上并不存在,负责 此事的是一个非国家机构 国际教科书研究所(1975年更名为Georg Eckert titute for nternational Te k Research GE1),而且历届德国政府确实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一并不试图或者说并不想对此过分介入:波兰的委员会从结构上说与国家权威联系更紧,但 其成员显然设法使自己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①但国家不干预,并不说明国家不支持。研究 表明,德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德波历史对话的各个阶段都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给予有 力支持,包括人事任命、财政支持、推动各州历史教科书接受教科书委员会的建议,以及采 一些表态性的举指 。G具 独立机构的合 研究活动保持自主,但它的经费很大 程度上来源于政府拨款,其活动得到高层的有力支持。它既不是一个政府组织,也不是纯粹 的私人机构,学者称其为“类公共”机构(“parapublic”institu-tion)。对德国政府而言,通 过G日的工作达到了双重目标:既显示了政府的支持,又不给学者施加民族主义压力。这种
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地位提升、中日两国在区域政治和国际政治中角色和影响力出现结 构性变动有密切的关系。③但是,由于两国共同利益和未来发展的一致性因素强大,最近十 余年来,虽然两国在历史问题上屡有争议,这种争议对两国相互关系尤其是对民众的感情造 成极大的伤害,但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两国的交往,尤其是经济贸易领域的来往与合作。许多 学者对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持乐观态度,有学者指出:“随着结构性的变动的延续和基本 趋势的明朗化,特别是在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真正建立,政治层面的问 题可能找到新的解决方法。”④新的政治框架出现,无疑会给两国间历史争议的解决带来有 利的环境,从中我们可以乐观地展望达成基本共识的前景,也可以肯定,现在开展历史共同 研究、促进两国彻底和解,正当其时。 总之,国际间历史问题争议的解决不是“悔罪”和“原谅”那么简单,它更多地是现实政治 经济关系的折射,但不能指望历史问题会“自行解决”,学者的努力、共同历史研究和教科 书合作的展开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本文所引施梅笛女士的两篇论文中都指出,共 同历史研究并不能充当达成历史共识的先锋,但在有利的条件下,它有助于形成指向相互理 解和共识的话语(dis-course),为双方提供沟通的渠道。这是欧洲经验给东亚历史研究的重 要启示。 (二)欧洲经验可以在合作策略上提供有益借鉴。 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开始国际间的历史共同研究和教科书合作,不但需要相关各方的道 德和学识,而且需要智慧和策略。在这方面,欧洲的教科书合作在多方面值得借鉴,以下就 是若干例子。 ①Claudia Schneider,The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 Issue——Viewed through the Prism of European Experienc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EastAsia。感谢施梅笛女士提供该论文。该 教科书的第 2 册也已经出版。 ②H。 C。 Klaus Zernack, After the Wende:The German-Polish Textbook Project in Retrospect; Claudia Schneider, The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 Issue——Viewed through the Prism of European Experienc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EastAsia; Professor Zernack 的文章 见 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 网站,www。gei。de。 ③步平:《东亚地区能否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中国图书评论》2007 年 11 月; Claudia Schneider,The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 Controversy i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and Social Science (2008 )。 ④步平:《历史认识如何跨越国境》,“历史教学与历史共识———东亚的比较视角”(德 国布伦瑞克, 2008 年 10 月)会议论文。 第一,政府采取相对超然的立场。 施梅笛女士指出,在德波教科书合作中,就德方而言,国家干预事实上并不存在,负责 此事的是一个非国家机构——国际教科书研究所(1975 年更名为 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 GEI),而且历届德国政府确实——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并不试图或者说并不想对此过分介入;波兰的委员会从结构上说与国家权威联系更紧,但 其成员显然设法使自己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①但国家不干预,并不说明国家不支持。研究 表明,德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德波历史对话的各个阶段都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给予有 力支持,包括人事任命、财政支持、推动各州历史教科书接受教科书委员会的建议,以及采 取一些表态性的举措。GEI 具有独立机构的合法地位,研究活动保持自主,但它的经费很大 程度上来源于政府拨款,其活动得到高层的有力支持。它既不是一个政府组织,也不是纯粹 的私人机构,学者称其为“类公共”机构(“parapublic”institu-tion)。对德国政府而言,通 过 GEI 的工作达到了双重目标:既显示了政府的支持,又不给学者施加民族主义压力。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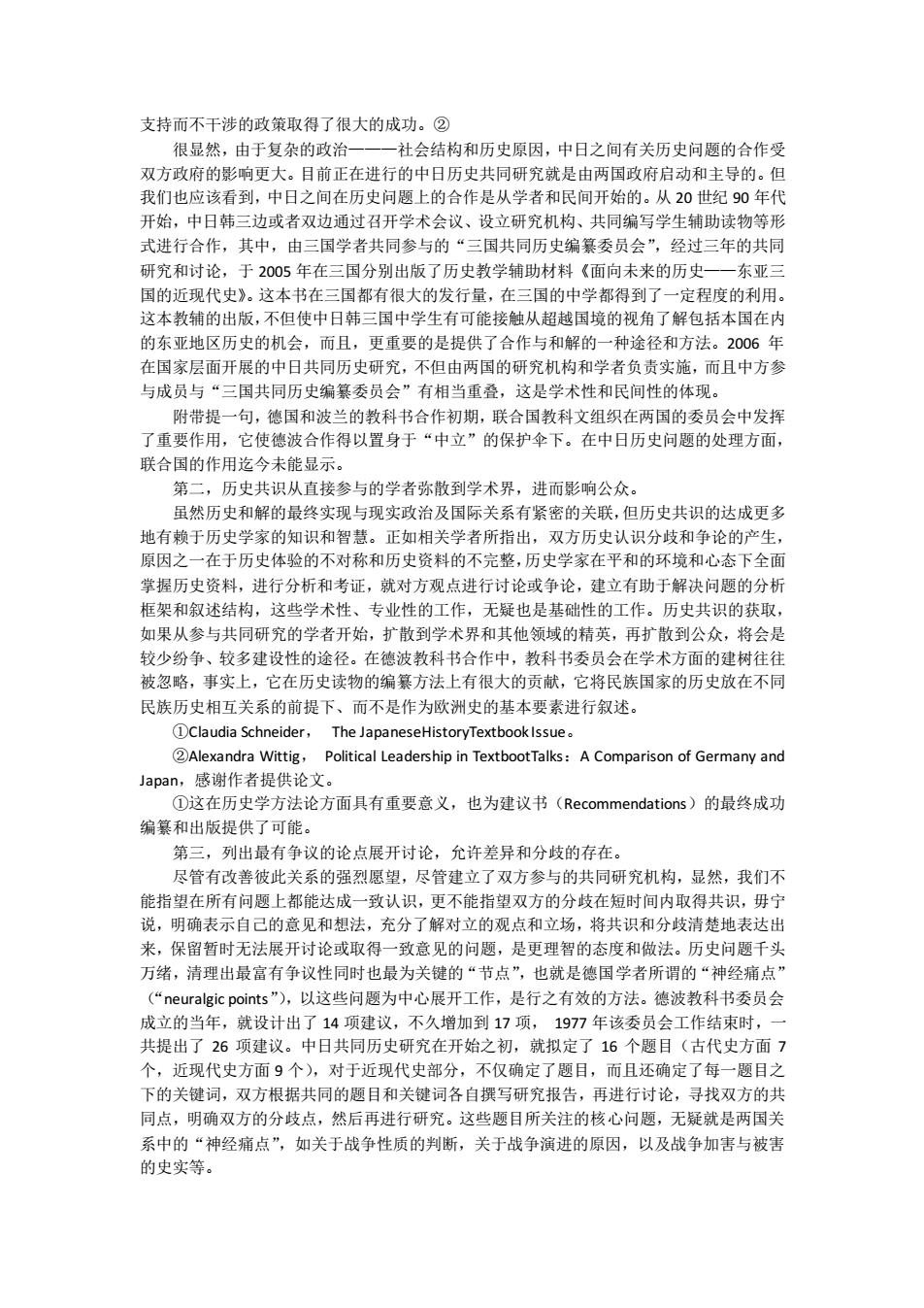
支持而不干涉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② 很显然,由于复杂的政治 社会结构和历史原因,中日之间有关历史问题的合作受 双方政府的影响更大。目前正在进行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就是由两国政府启动和主导的。但 我们也应该看到,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的合作是从学者和民间开始的。从20世纪90年代 开始,中日韩三边或者双边通过召开学术会议、设立研究机构、共同编写学生辅助读物等形 式进行合作,其中,由三国学者共同参与的“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经过三年的共同 研究和讨论,于2005年在三国分别出版了历史教学辅助材料《面向未来的历史 东亚 近现代史》。这本书在三国都有很大的 行最 的中 学都得到了 定程度的利用 这本教辅的出版,不但使中日韩三国中学生有可能接触从超越国境的视角了解包括本国在内 的东亚地区历史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合作与和解的一种途径和方法。2006年 在国家层面开展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不但由两国的研究机构和学者负责实施,而且中方参 与成员与“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有相当重叠,这是学术性和民间性的体现 附带提一句,德国和波兰的教科书合作初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两国的委员会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它使德波合作得以置身于 “中立 的保护伞下 在中日历史问题的处理方面 联合国的作用迄今未能显示。 第二,历史共识从直接参与的学者弥散到学术界,讲而影响公众。 虽然历史和解的最终实现与现实政治及国际关系有紧密的关联,但历史共识的达成更多 地有赖于历史学家的知识和智慧。正如相关学者所指出,双方历史认识分歧和争论的产生, 原因之一在于历史体验的 对称和历史资料的 元整 历中 在平 的 不境和心态下全面 掌握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考证,就对方观点进行讨论或争论,建立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分析 框架和叙述结构,这些学术性、专业性的工作,无疑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历史共识的获取, 如果从参与共同研究的学者开始,扩散到学术界和其他领域的精英,再扩散到公众,将会是 较少纷争、较多建设性的途径。在德波教科书合作中,教科书委员会在学术方面的建树往往 被忽路。电实上应在 历史读物的编方法上有很大的贡献 它将民族国家的历史放在不 民族历史相互关系的前提下、而不是作为欧洲史的基本要素进行叙述 (1Claudia Schneider, The JapaneseHistoryTextbookIssuea ②Alexandra wittie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TextbootTalks:A Comparison of Germany and apan,感谢作者提供论文。 D这在历史学方法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建议书(Recommendations)的最终成功 编篆和出版提供 可能 第三,列出最有争议的论点展开讨论,允许差异和分歧的存在。 尽管有改善彼此关系的强烈愿望,尽管建立了双方参与的共同研究机构,显然,我们不 能指望在所有间题上都能达成一致认识,更不能指望双方的分技在短时间内取得共识,毋宁 说,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充分了解对立的观点和立场,将共识和分歧清楚地表达出 来,保留暂时无法展开讨论或取得 动 见的问题, 是更理智的态度和做法 历史问题千头 万绪,清理出最富有争议性同时也最为关键的“节点”,也就是德国学者所谓的“神经痛点 (“neuralgic points"),以这些问题为中心展开工作,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德波教科书委员会 成立的当年,就设计出了14项建议,不久增加到17项,1977年该委员会工作结束时, 共根出了26项建议。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在开始之初,就拟定了16个题目(古代史方面 个。近图代中方面9个) 对于近现代史部分,不仅确定了题目,而且还确定了每 题目之 下的关键词,双方根据共同的题目和关健词各自撰写研究报告,再进行讨论,寻找双方的 同点,明确双方的分歧点,然后再进行研究。这些题目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无疑就是两国关 系中的“神经痛点”,如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关于战争演进的原因,以及战争加害与被害 的史实等
支持而不干涉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② 很显然,由于复杂的政治———社会结构和历史原因,中日之间有关历史问题的合作受 双方政府的影响更大。目前正在进行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就是由两国政府启动和主导的。但 我们也应该看到,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的合作是从学者和民间开始的。从 20 世纪 90 年代 开始,中日韩三边或者双边通过召开学术会议、设立研究机构、共同编写学生辅助读物等形 式进行合作,其中,由三国学者共同参与的“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经过三年的共同 研究和讨论,于 2005 年在三国分别出版了历史教学辅助材料《面向未来的历史——东亚三 国的近现代史》。这本书在三国都有很大的发行量,在三国的中学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利用。 这本教辅的出版,不但使中日韩三国中学生有可能接触从超越国境的视角了解包括本国在内 的东亚地区历史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合作与和解的一种途径和方法。2006 年 在国家层面开展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不但由两国的研究机构和学者负责实施,而且中方参 与成员与“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有相当重叠,这是学术性和民间性的体现。 附带提一句,德国和波兰的教科书合作初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两国的委员会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它使德波合作得以置身于“中立”的保护伞下。在中日历史问题的处理方面, 联合国的作用迄今未能显示。 第二,历史共识从直接参与的学者弥散到学术界,进而影响公众。 虽然历史和解的最终实现与现实政治及国际关系有紧密的关联,但历史共识的达成更多 地有赖于历史学家的知识和智慧。正如相关学者所指出,双方历史认识分歧和争论的产生, 原因之一在于历史体验的不对称和历史资料的不完整,历史学家在平和的环境和心态下全面 掌握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考证,就对方观点进行讨论或争论,建立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分析 框架和叙述结构,这些学术性、专业性的工作,无疑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历史共识的获取, 如果从参与共同研究的学者开始,扩散到学术界和其他领域的精英,再扩散到公众,将会是 较少纷争、较多建设性的途径。在德波教科书合作中,教科书委员会在学术方面的建树往往 被忽略,事实上,它在历史读物的编纂方法上有很大的贡献,它将民族国家的历史放在不同 民族历史相互关系的前提下、而不是作为欧洲史的基本要素进行叙述。 ①Claudia Schneider, The JapaneseHistoryTextbook Issue。 ②Alexandra Wittig,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TextbootTalks:A Comparison of Germany and Japan,感谢作者提供论文。 ①这在历史学方法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建议书(Recommendations)的最终成功 编纂和出版提供了可能。 第三,列出最有争议的论点展开讨论,允许差异和分歧的存在。 尽管有改善彼此关系的强烈愿望,尽管建立了双方参与的共同研究机构,显然,我们不 能指望在所有问题上都能达成一致认识,更不能指望双方的分歧在短时间内取得共识,毋宁 说,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充分了解对立的观点和立场,将共识和分歧清楚地表达出 来,保留暂时无法展开讨论或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是更理智的态度和做法。历史问题千头 万绪,清理出最富有争议性同时也最为关键的“节点”,也就是德国学者所谓的“神经痛点” (“neuralgic points”),以这些问题为中心展开工作,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德波教科书委员会 成立的当年,就设计出了 14 项建议,不久增加到 17 项, 1977 年该委员会工作结束时,一 共提出了 26 项建议。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在开始之初,就拟定了 16 个题目(古代史方面 7 个,近现代史方面 9 个),对于近现代史部分,不仅确定了题目,而且还确定了每一题目之 下的关键词,双方根据共同的题目和关键词各自撰写研究报告,再进行讨论,寻找双方的共 同点,明确双方的分歧点,然后再进行研究。这些题目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无疑就是两国关 系中的“神经痛点”,如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关于战争演进的原因,以及战争加害与被害 的史实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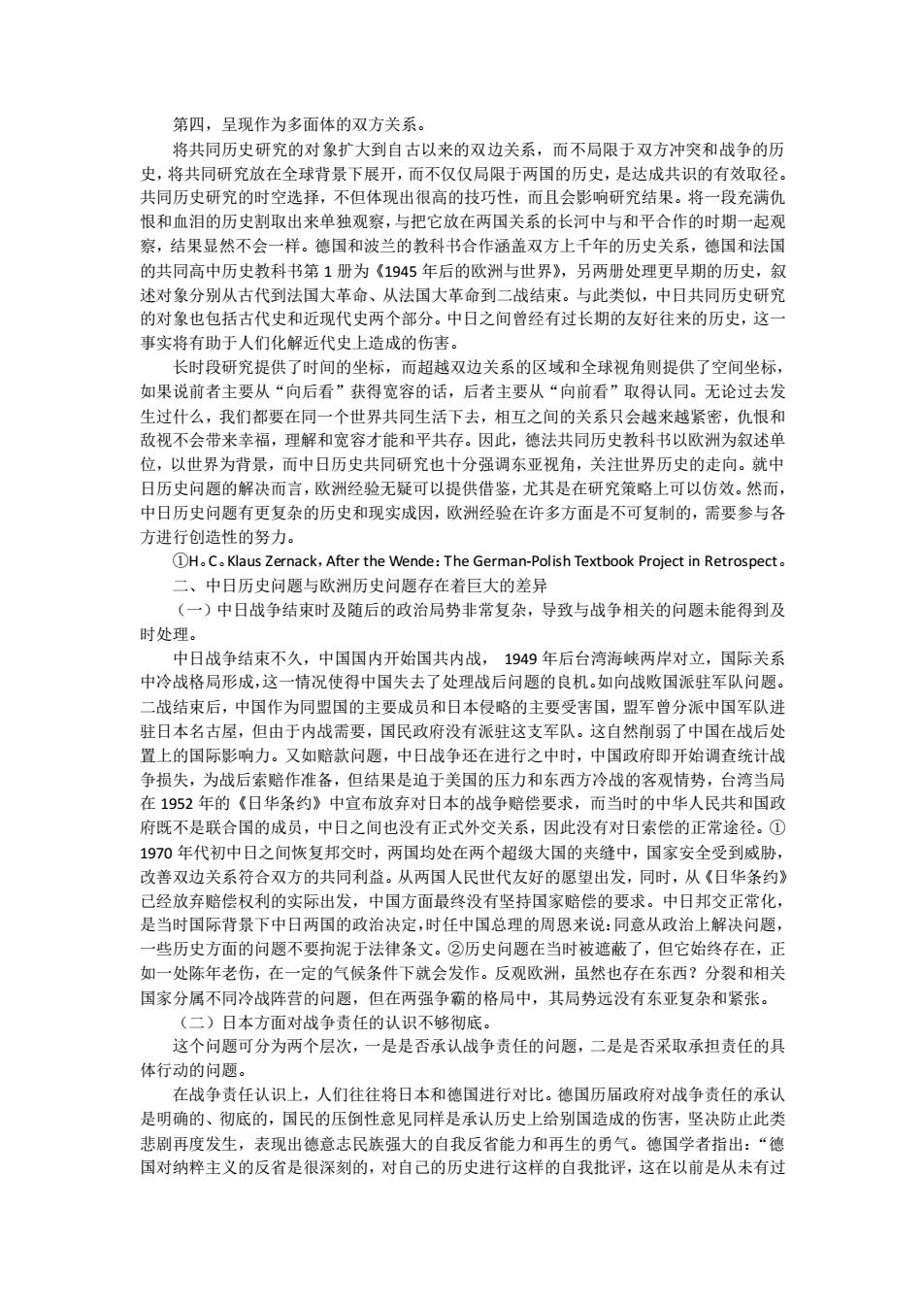
第四,县视作为多面体的双方关系。 将共同历史研究的对象扩大到自古以来的双边关系,而不局限于双方冲突和战争的历 史,将共同研究放在全球背景下展开 不仅仅局限于两国的历实 是达成共识的有效取{ 共同历史研究的时空选择, 不但体现出很高的技巧性,而且会影响研究结果。将一段充满仇 根和血泪的历史割取出来单独观察,与把它放在两国关系的长河中与和平合作的时期一起观 察,结果显然不会一样。德国和波兰的教科书合作涵盖双方上千年的历史关系,德国和法国 的共同高中历史教科书第1卧为《1945年后的欧洲与世界》,另两册处理更早期的历史,叙 述对象分别从古代到 法国大革命 从法国大革命到二战结束 。与此类似,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的对象也包括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部分。中日之间曾经有过长期的友好往来的历史,这 事实将有助于人们化解近代史上造成的伤害。 长时段研究提供了时间的坐标,而超械双边关系的区域和全球视角则提供了空间坐标! 如果说前者主要从“向后看”获得宽容的话,后者主要从“向前看”取得认同。无论过去发 生过什么,我们都要在同一个世界共同生活下去,相互之间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密,仇恨利 敌视不 会带米幸 理解和宽彩 才能和平共存 因此 德法 共同历史教科 以欧洲为叙 位,以世界为背景,而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也十分强调东亚视角,关注世界历史的走向。就中 日历史问题的解决而言,欧洲经验无疑可以提供借鉴,尤其是在研究策略上可以仿效。然而, 中日历史问题有更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成因,欧洲经验在许多方面是不可复制的,需要参与客 方进行创造性的努力。 ①HC.ka an-Polish Textbook Project in Retrospect 中日历史问题与欧洲历史问题存在者巨大的差异 《一)中日战争结束时及随后的政治局势非常复杂,导致与战争相关的问题未能得到及 时处理。 中日战争结束不久,中国国内开始国共内战,1949年后台湾海峡两岸对立,国际关系 中冷战格局形成,这一情况使得中国失去了处理战后问题的良机。如向战败国派驻军队问题。 二战结束后 ,中国作为同盟国的主要成员和日本侵略的主要受害国,盟军曾分派中国军队 驻日本名古屋,但由于内战需要,国民政府没有派驻这支军队。这自然削弱了中国在战后女 置上的国际影响力。又如赔款间题,中日战争还在进行之中时,中国政府即开始调查统计战 争损失,为战后索赔作准备,但结果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和东西方冷战的客观情势,台湾当局 在1952年的《日华条约》中言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府既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中日之间也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没有对日索偿的正常途径。Q 1970年代初中日之间恢复邦交时,两国均处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改善双边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出发,同时,从《日华条约》 己经放弃赔偿权利的实际出发,中国方面最终没有坚持国家赔偿的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 是当时国际背景下中日两国的政治决定,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说:同意从政治上解决间题 些历史方面的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②历史问题在当时被遮蔽 但它始终存在,正 处陈年老伤,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就会发作。反观欧洲,虽然也存在东西 分裂和相关 国家分属不同冷战阵营的问题,但在两强争霸的格局中,其局势远没有东亚复杂和紧张。 (二)日本方面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不够彻底。 这个问题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是否承认战争责任的问题,二是是否采取承担责任的具 体行动的问职 在战争责任认识上,人们往往将日本和德国进行对比。德国历届政府对战争贵任的承认 是明确的、彻底的,国民的压倒性意见同样是承认历史上给别国造成的伤害,坚决防止此类 悲剧再度发生,表现出德意志民族强大的自我反省能力和再生的勇气。德国学者指出:“德 国对纳粹主义的反省是很深刻的,对自己的历史进行这样的自我批评,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
第四,呈现作为多面体的双方关系。 将共同历史研究的对象扩大到自古以来的双边关系,而不局限于双方冲突和战争的历 史,将共同研究放在全球背景下展开,而不仅仅局限于两国的历史,是达成共识的有效取径。 共同历史研究的时空选择,不但体现出很高的技巧性,而且会影响研究结果。将一段充满仇 恨和血泪的历史割取出来单独观察,与把它放在两国关系的长河中与和平合作的时期一起观 察,结果显然不会一样。德国和波兰的教科书合作涵盖双方上千年的历史关系,德国和法国 的共同高中历史教科书第 1 册为《1945 年后的欧洲与世界》,另两册处理更早期的历史,叙 述对象分别从古代到法国大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到二战结束。与此类似,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的对象也包括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部分。中日之间曾经有过长期的友好往来的历史,这一 事实将有助于人们化解近代史上造成的伤害。 长时段研究提供了时间的坐标,而超越双边关系的区域和全球视角则提供了空间坐标, 如果说前者主要从“向后看”获得宽容的话,后者主要从“向前看”取得认同。无论过去发 生过什么,我们都要在同一个世界共同生活下去,相互之间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密,仇恨和 敌视不会带来幸福,理解和宽容才能和平共存。因此,德法共同历史教科书以欧洲为叙述单 位,以世界为背景,而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也十分强调东亚视角,关注世界历史的走向。就中 日历史问题的解决而言,欧洲经验无疑可以提供借鉴,尤其是在研究策略上可以仿效。然而, 中日历史问题有更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成因,欧洲经验在许多方面是不可复制的,需要参与各 方进行创造性的努力。 ①H。C。Klaus Zernack,After the Wende:The German-Polish Textbook Project in Retrospect。 二、中日历史问题与欧洲历史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一)中日战争结束时及随后的政治局势非常复杂,导致与战争相关的问题未能得到及 时处理。 中日战争结束不久,中国国内开始国共内战, 1949 年后台湾海峡两岸对立,国际关系 中冷战格局形成,这一情况使得中国失去了处理战后问题的良机。如向战败国派驻军队问题。 二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同盟国的主要成员和日本侵略的主要受害国,盟军曾分派中国军队进 驻日本名古屋,但由于内战需要,国民政府没有派驻这支军队。这自然削弱了中国在战后处 置上的国际影响力。又如赔款问题,中日战争还在进行之中时,中国政府即开始调查统计战 争损失,为战后索赔作准备,但结果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和东西方冷战的客观情势,台湾当局 在 1952 年的《日华条约》中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既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中日之间也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没有对日索偿的正常途径。① 1970 年代初中日之间恢复邦交时,两国均处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改善双边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出发,同时,从《日华条约》 已经放弃赔偿权利的实际出发,中国方面最终没有坚持国家赔偿的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 是当时国际背景下中日两国的政治决定,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说:同意从政治上解决问题, 一些历史方面的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②历史问题在当时被遮蔽了,但它始终存在,正 如一处陈年老伤,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就会发作。反观欧洲,虽然也存在东西?分裂和相关 国家分属不同冷战阵营的问题,但在两强争霸的格局中,其局势远没有东亚复杂和紧张。 (二)日本方面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不够彻底。 这个问题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是否承认战争责任的问题,二是是否采取承担责任的具 体行动的问题。 在战争责任认识上,人们往往将日本和德国进行对比。德国历届政府对战争责任的承认 是明确的、彻底的,国民的压倒性意见同样是承认历史上给别国造成的伤害,坚决防止此类 悲剧再度发生,表现出德意志民族强大的自我反省能力和再生的勇气。德国学者指出:“德 国对纳粹主义的反省是很深刻的,对自己的历史进行这样的自我批评,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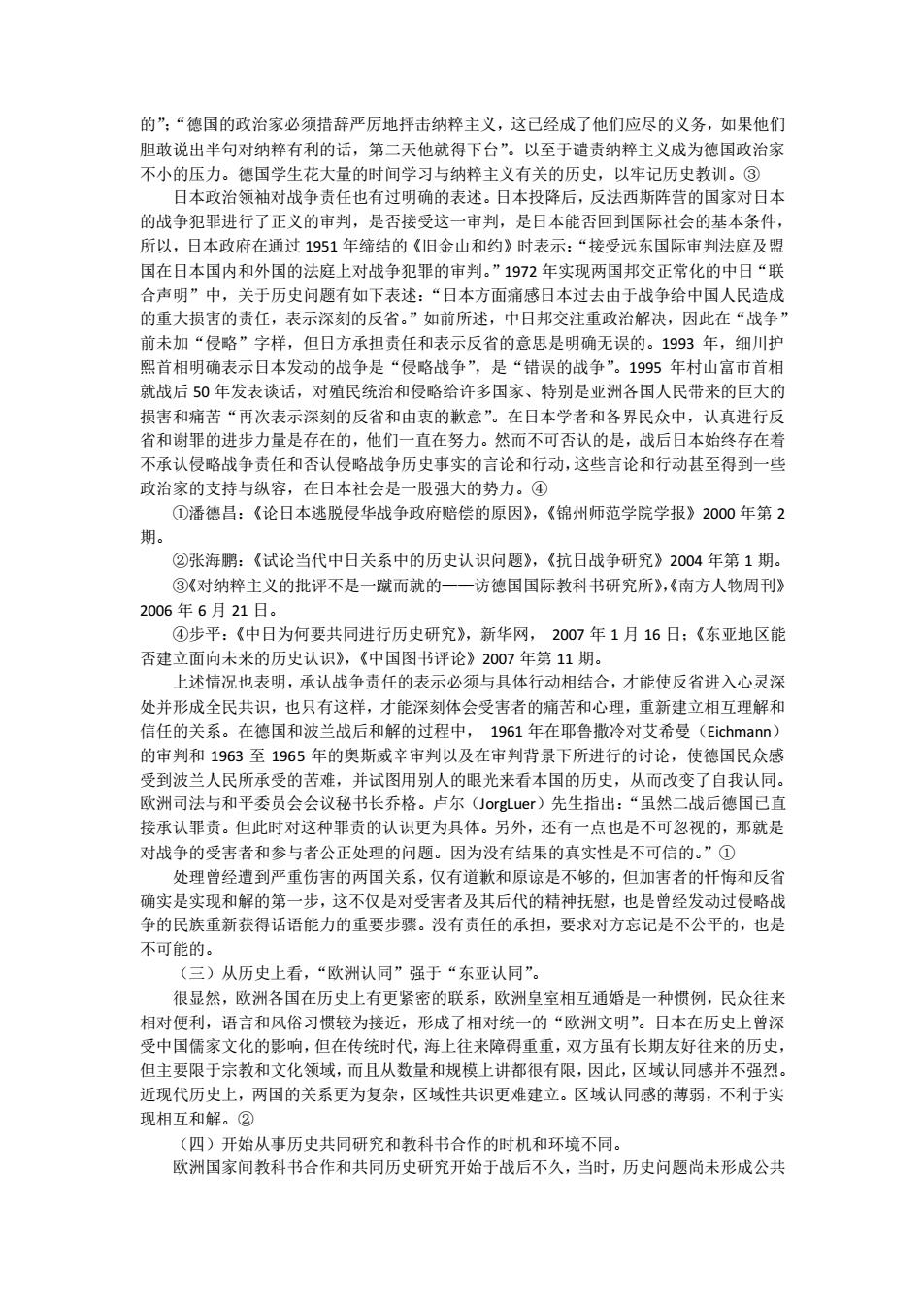
的”:“德国的政治家必须措辞严厉地抨击纳粹主义,这己经成了他们应尽的义务,如果他们 胆敢说出半句对纳粹有利的话,第二天他就得下台”。以至于谴责纳粹主义成为德国政治家 不小的压力。德国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与纳粹主义有关的历史。 以牢记历史教训 日本政治领袖对战争责任也有过明确的表述。日本投降后,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对日本 的战争犯罪进行了正义的审判,是否接受这一审判,是日本能否回到国际社会的基本条件, 所以,日本政府在通过1951年缔结的《旧金山和约》时表示:“接受远东国际审判法庭及盟 国在日本国内和外国的法庭上对战争犯罪的审判。”1972年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 声明”中 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 人民造成 的重大损害的发在历夫阅有解前运,中阳交重院,因比在德 前未加“侵略”字样,但日方承担责任和表示反省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1993年,细川护 熙首相明确表示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 就战后50年发表谈话,对殖民统治和侵路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 损害和痛苦“ 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在日本学者和各界民众中, 省和谢罪的进步力量是存在的,他们一直在努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战后日本始终存在者 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和行动,这些言论和行动甚至得到一些 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在日本社会是一股强大的势力。④ ①潘德吕:《论日本逃脱侵华战争政府赔货的原因》,《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 期。 ②张海鹏:《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 ③对纳粹主义的批评不是一藏而就的一 一访德国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南方人物周刊》 2006年6月21日。 ④步平:《中日为何要共同进行历史研究》,新华网,2007年1月16日:《东亚地区能 否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11期。 明,承认战争责任的表示必须与具体行动相结合,才能使反省进入心灵济 处并形成全民共识,也只有这样,才能深刻体会受害者的痛苦和心理,重新建立相互理解和 信任的关系。在德国和波兰战后和解的过程中,1961年在耶鲁撤冷对艾希曼(Eichmann) 的审判和1963至1965年的奥斯威辛审判以及在审判背景下所进行的讨论,使德国民众感 受到波兰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并试图用别人的眼光来看本国的历史,从而改变了自我认同 欧洲司法与和平委员会会议秘书长乔格。卢尔0 )先生指出:“虽然二战后德国已直 接承认罪责。但此 对这种罪责的认识更为具体。另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 那就 对战争的受害者和参与者公正处理的问题。因为没有结果的真实性是不可信的。”① 处理曾经遭到严重伤吉的两国关系,仅有道款和原谅是不够的,但加害者的杆悔和反省 确实是实现和解的第一步,这不仅是对受害者及其后代的精神抚慰,也是曾经发动过侵略战 争的民族重新获得话语能力的重要步骤。没有责任的承担,要求对方忘记是不公平的,也是 不可能的。 (三)从历史上看,“欧洲认同”强于“东亚认同”。 很显然,欧洲各国在历史上有更紧密的联系,欧洲皇室相互通婚是一种惯例,民众往来 相对便利,语言和风俗习惯较为接近,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欧洲文明”。日本在历史上曾深 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在传统时代,海上往来璋碍重重,双方虽有长期友好往来的历史, 但主要限于宗教和文化领域,而且从数量和规模上讲都很有限,因此,区域认同感并不强烈 近现代历史上,两国的关系更为复杂,区域性共识更难建立。区域认同感的薄弱, 不利于实 现相互和解。② (四)开始从事历史共同研究和教科书合作的时机和环境不同。 欧洲国家间教科书合作和共同历史研究开始于战后不久,当时,历史问题尚未形成公共
的”;“德国的政治家必须措辞严厉地抨击纳粹主义,这已经成了他们应尽的义务,如果他们 胆敢说出半句对纳粹有利的话,第二天他就得下台”。以至于谴责纳粹主义成为德国政治家 不小的压力。德国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与纳粹主义有关的历史,以牢记历史教训。③ 日本政治领袖对战争责任也有过明确的表述。日本投降后,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对日本 的战争犯罪进行了正义的审判,是否接受这一审判,是日本能否回到国际社会的基本条件, 所以,日本政府在通过 1951 年缔结的《旧金山和约》时表示:“接受远东国际审判法庭及盟 国在日本国内和外国的法庭上对战争犯罪的审判。”1972 年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 合声明”中,关于历史问题有如下表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 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如前所述,中日邦交注重政治解决,因此在“战争” 前未加“侵略”字样,但日方承担责任和表示反省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1993 年,细川护 熙首相明确表示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1995 年村山富市首相 就战后 50 年发表谈话,对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 损害和痛苦“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在日本学者和各界民众中,认真进行反 省和谢罪的进步力量是存在的,他们一直在努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 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和行动,这些言论和行动甚至得到一些 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在日本社会是一股强大的势力。④ ①潘德昌:《论日本逃脱侵华战争政府赔偿的原因》,《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 年第 2 期。 ②张海鹏:《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1 期。 ③《对纳粹主义的批评不是一蹴而就的——访德国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南方人物周刊》 2006 年 6 月 21 日。 ④步平:《中日为何要共同进行历史研究》,新华网, 2007 年 1 月 16 日;《东亚地区能 否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中国图书评论》2007 年第 11 期。 上述情况也表明,承认战争责任的表示必须与具体行动相结合,才能使反省进入心灵深 处并形成全民共识,也只有这样,才能深刻体会受害者的痛苦和心理,重新建立相互理解和 信任的关系。在德国和波兰战后和解的过程中, 1961 年在耶鲁撒冷对艾希曼(Eichmann) 的审判和 1963 至 1965 年的奥斯威辛审判以及在审判背景下所进行的讨论,使德国民众感 受到波兰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并试图用别人的眼光来看本国的历史,从而改变了自我认同。 欧洲司法与和平委员会会议秘书长乔格。卢尔(JorgLuer)先生指出:“虽然二战后德国已直 接承认罪责。但此时对这种罪责的认识更为具体。另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 对战争的受害者和参与者公正处理的问题。因为没有结果的真实性是不可信的。”① 处理曾经遭到严重伤害的两国关系,仅有道歉和原谅是不够的,但加害者的忏悔和反省 确实是实现和解的第一步,这不仅是对受害者及其后代的精神抚慰,也是曾经发动过侵略战 争的民族重新获得话语能力的重要步骤。没有责任的承担,要求对方忘记是不公平的,也是 不可能的。 (三)从历史上看,“欧洲认同”强于“东亚认同”。 很显然,欧洲各国在历史上有更紧密的联系,欧洲皇室相互通婚是一种惯例,民众往来 相对便利,语言和风俗习惯较为接近,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欧洲文明”。日本在历史上曾深 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在传统时代,海上往来障碍重重,双方虽有长期友好往来的历史, 但主要限于宗教和文化领域,而且从数量和规模上讲都很有限,因此,区域认同感并不强烈。 近现代历史上,两国的关系更为复杂,区域性共识更难建立。区域认同感的薄弱,不利于实 现相互和解。② (四)开始从事历史共同研究和教科书合作的时机和环境不同。 欧洲国家间教科书合作和共同历史研究开始于战后不久,当时,历史问题尚未形成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