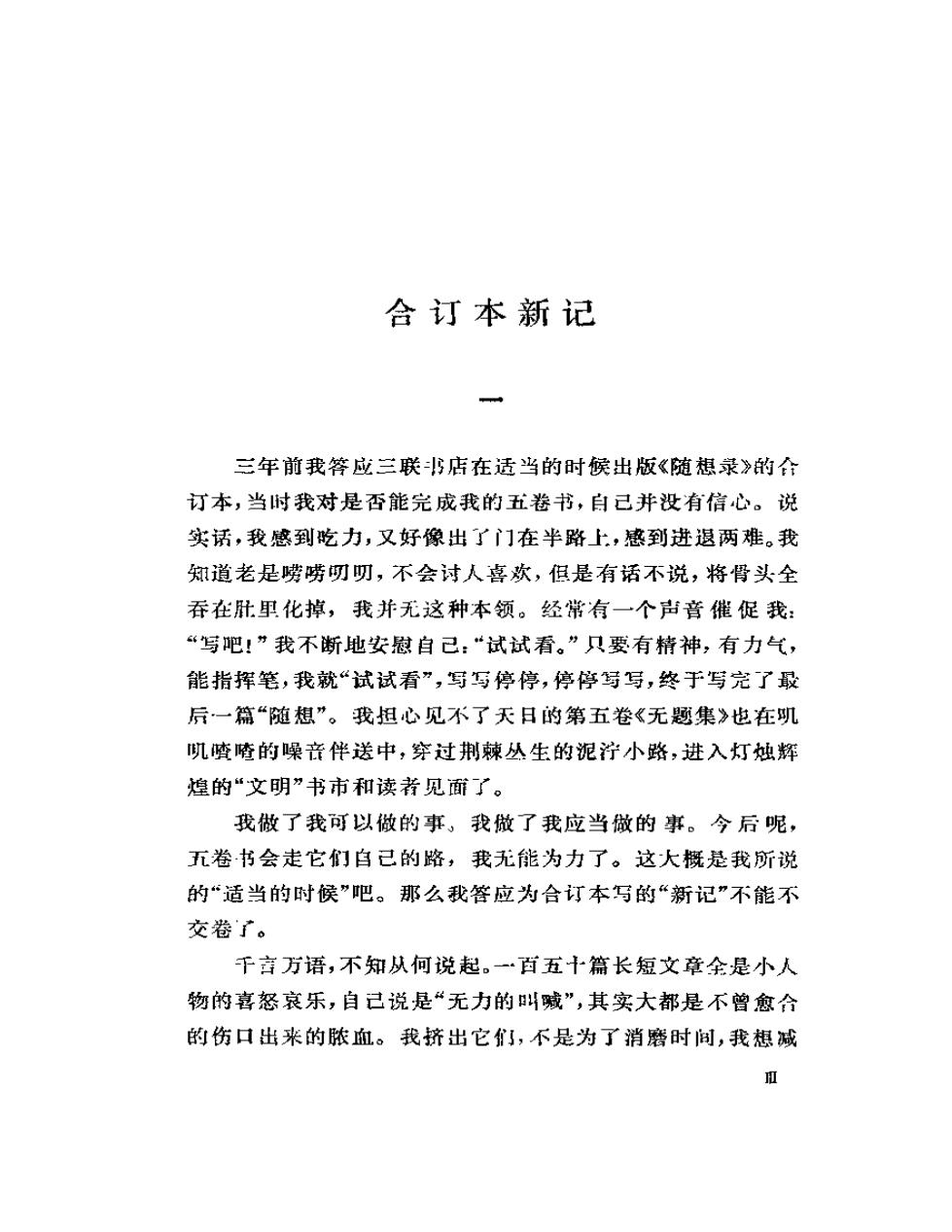
合订本新记 一 三年前我答应三联书店在适当的时候出版《随想录》的合 订本,当时我对是否能完成我的五卷书,自己并没有信心。说 实话,我感到吃力,又好像出了门在半路上,感到进退两难。我 知道老是唠叨叨,不会讨人喜欢,但是有话不说,将骨头全 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经常有一个声音催促我: “写吧!”我不断地安慰自己:“试试看。”只要有精神,有力气, 能指挥笔,我就“试试看”,写写停停,停停号写,终于写完了最 后·一篇“随想”。我担心见不了天日的第五卷《无题集》也在现 叽喳喳的噪音伴送中,穿过荆棘丛生的泥泞小路,进入灯烛辉 煌的“文明”书市和读者见面了。 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微了我应当做的事。今后呢, 五卷书会走它们自已的路,我无能为力了。这大概是我所说 的“适当的时候”吧。那么我答应为合订本写的“新记”不能不 交卷了。 千言方语,不知从何说起。·百五十篇长短文章全是小人 物的喜怒哀乐,自己说是“无力的叫喊”,其实大都是不曾愈合 的伤口出来的脓血。我挤出它J,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想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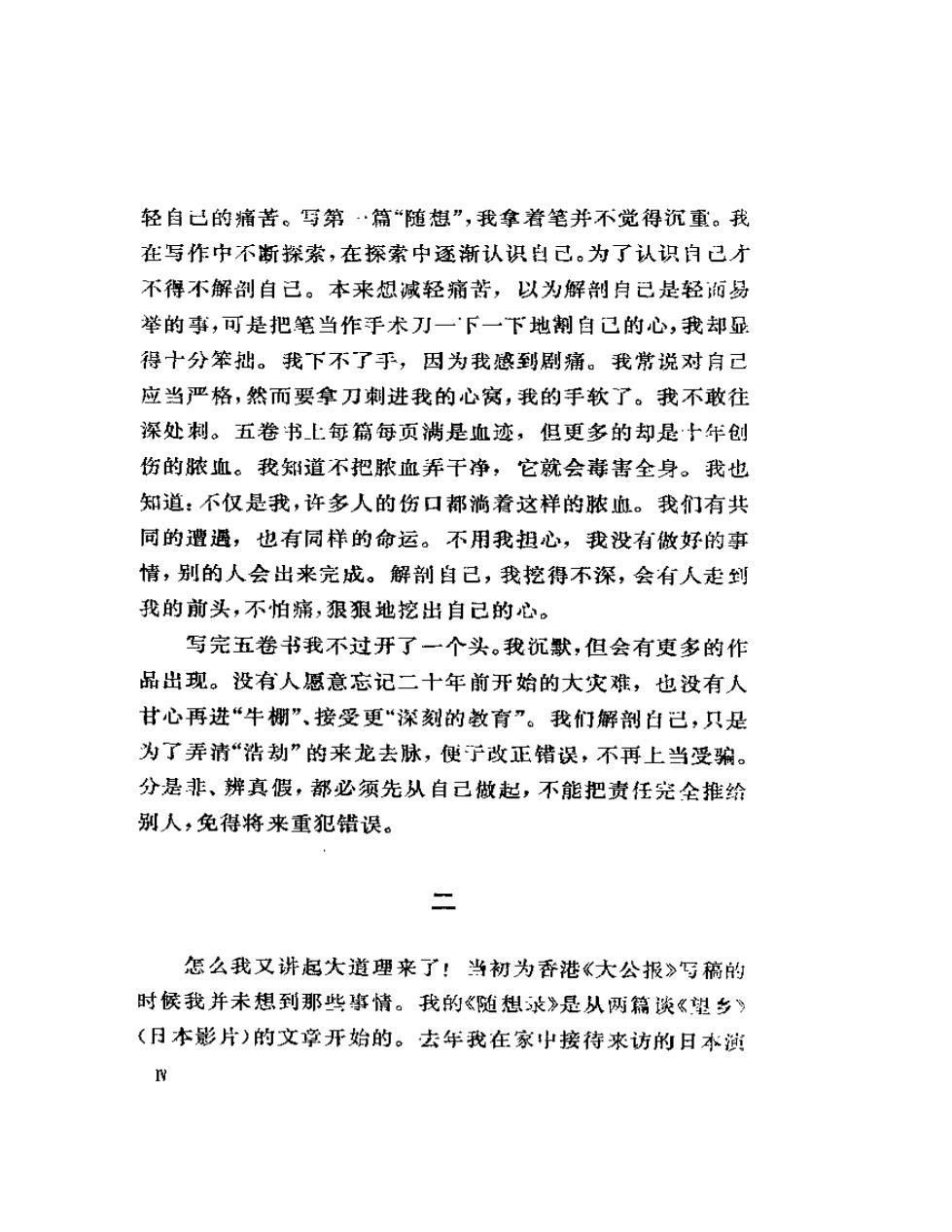
轻自已的痛苦。写第·篇“随想”,我拿着笔并不觉得沉重。我 在写作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逐渐认识自己。为了认识自己才 不得不解剖自已。本来想诚轻痛苦,以为解剖月已是轻间易 举的事,可是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制自己的心,我却显 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乎,因为我感到剧痛。我常说对自己 应当严格,然而要拿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手软了。我不敢往 深处刺。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上年创 伤的脓血。我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 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样的脓血。我们有共 同的遭遇,也有同样的命运。不用我担心,我没有做好的事 情,别的人会出来完成。解剖自已,我挖得不深,会有人走到 我的前头,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写完五卷书我不过开了一个头。我沉默,但会有更多的作 品出现。没有人思意忘记二十年前开始的大灾难,也没有人 甘心再进“牛棚”、接受更“深刻的教育”。我们解剖白已,只是 为了弄清“浩劫”的来龙去脉,使宁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 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 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 二 怎么我又讲起大道理来了!当初为香港《大公报》写稿的 时侯我并未想到那些事情。我的《随想最》是从两篇谈《望乡) (日本影片)的文章开始的。去年我在家中接待来访的日本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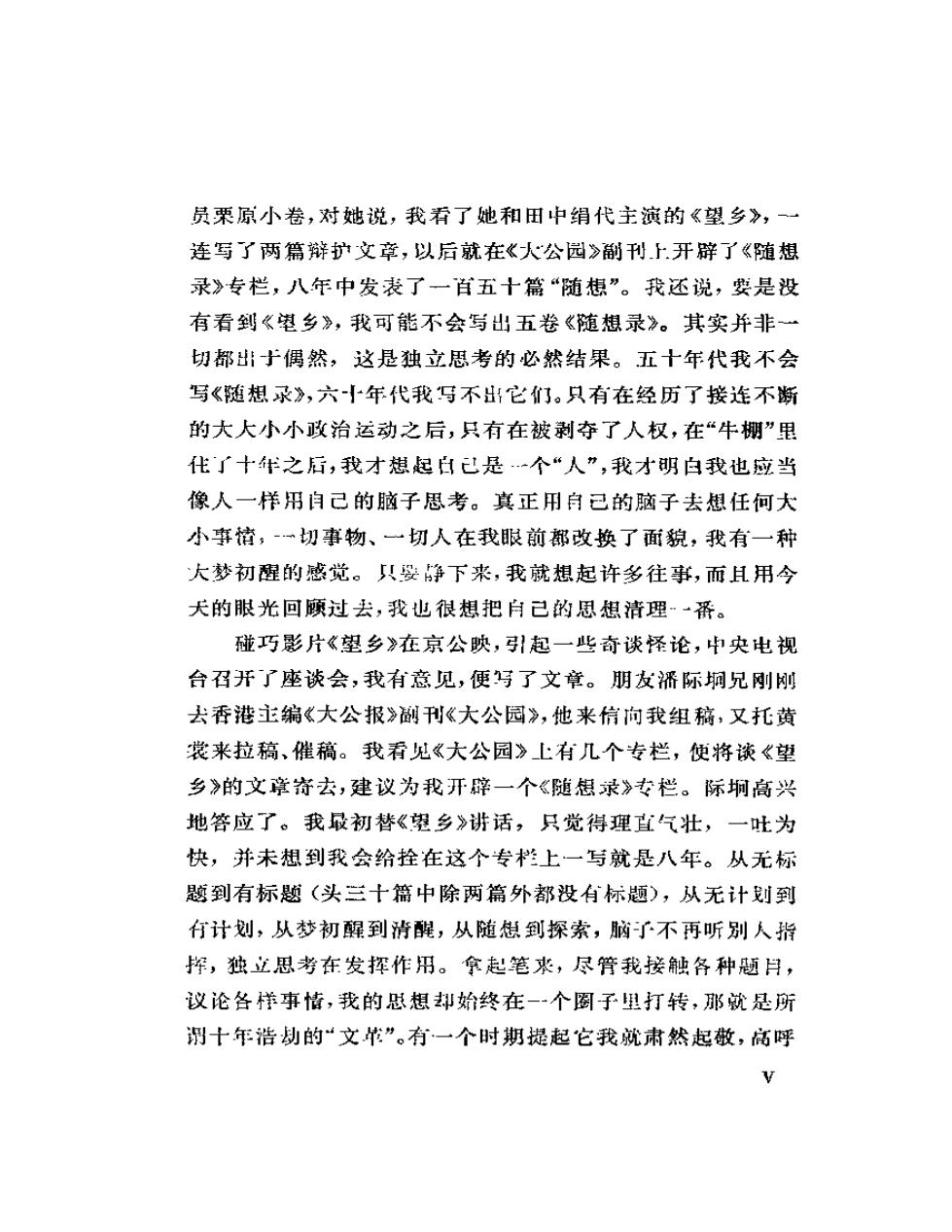
员栗原小卷,对她说,我看了她和田中绢代主演的《望乡》, 连写了两篇辩护文章,以后就在《大公园》御刊上开辟了《随想 录》专栏,八年中发表了一百五十篇“随想”。我还说,要是没 有看到《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其实并非一 切都:于偶然,这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五十年代我不会 写《随想录》,六小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 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甩 代了十作之后,我才想起白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 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真正用自已的脑子去想任何大 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换了面貌,我有一种 大梦初醒的感觉。只婴静下来,我就想起许多往事,而且用今 天的眼光回顾过去,我也很想把月己的思想清理一番。 碰巧影片《望乡》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谈怪论,中央电视 台召开了座谈会,我有意见,便写了文章。朋友潘际圳兄刚刚 去香港主编《大公报》测刊《大公园》,她来信向我组稿,又托黄 裳来拉稿、催稿。我看见《大公园》上有几个专栏,使将谈《望 乡》的文章寄去,建议为我开辟一个《随想录》专栏。际坰高兴 地答应了。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 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从无标 题到有标题(头三十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划到 行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醍,从随想到探索,脑了不再听别人指 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月, 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 渭十年浩劫的“文苹”。有一个时期提起它我就肃然起橄,高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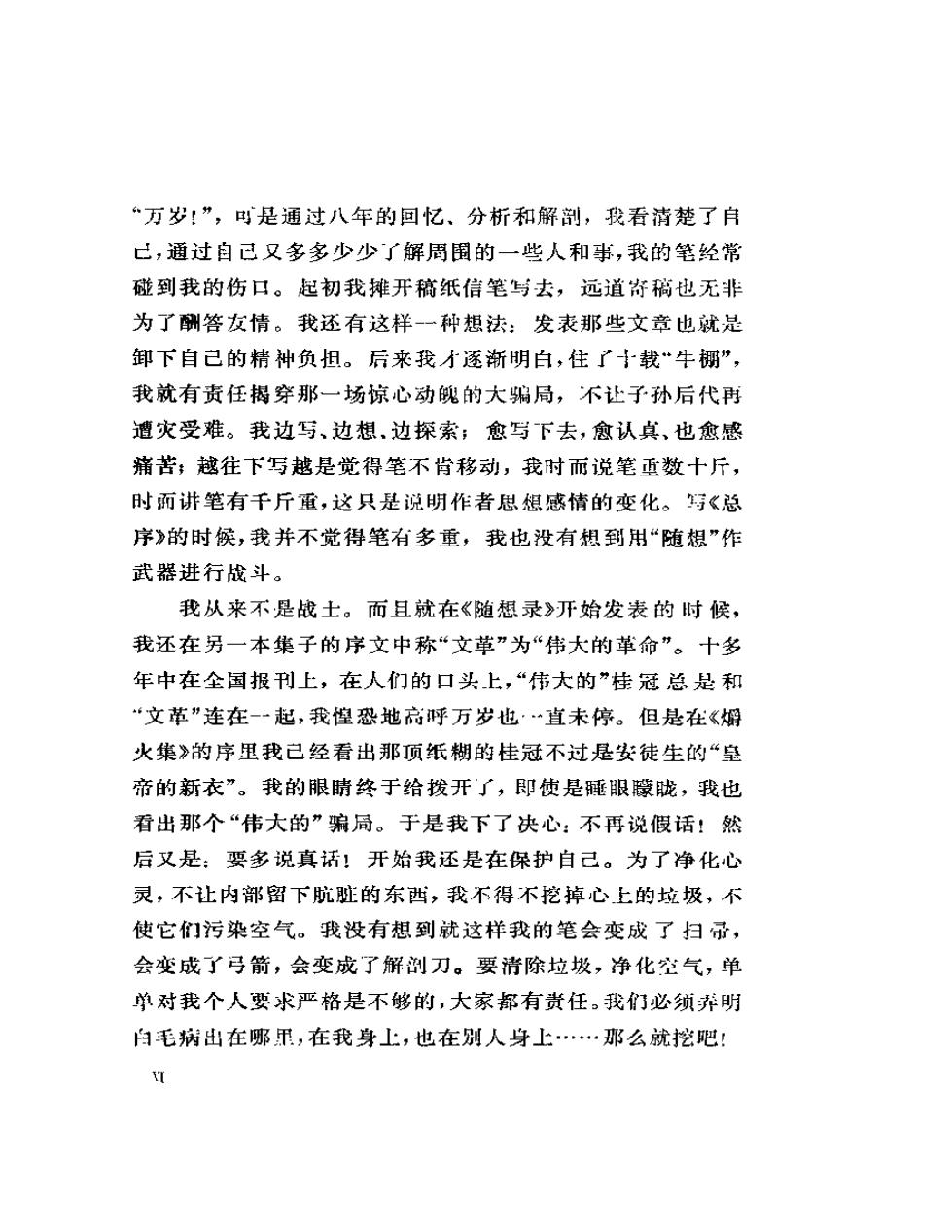
“万岁!”,是通过八年的回忆、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月 已,通过自已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围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笔经常 碰到我的伤口。起初我摊开稿纸信笔与去,远道寄稿也无非 为了酬答友情。我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发表那些文章也就是 卸下自己的精神负担。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住了十载“牛橱”, 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帆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 遭灾受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其、也愈感 痛苦:越往下写越是觉得笔不肯移动,我时而说笔重数十斤, 时而讲笔有干斤重,这只是说明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写《总 序》的时候,我并不觉得笔有多重,我也没有想到用“随想”作 武器进行战斗。 我从来不是战土。而且就在《随想录》开始发表的时候, 我还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称“文革”为“伟大的革命”。十多 年中在全国报刊上,在人们的口头上,“伟大的”桂冠总是和 “文革”连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万岁也.直未停。但是在《姆 火集》的序里我己经看出那顶纸糊的桂冠不过是安徒生的“皇 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终于给拨开了,即使是诞眼檬胧,我也 看出那个“伟大的”骗局。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然 后又是:要多说真话!开始我还是在保护自己。为了净化心 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 使它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变成了扫帝, 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要清除垃圾,净化空气,单 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必须弄明 白毛病出在哪用,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挖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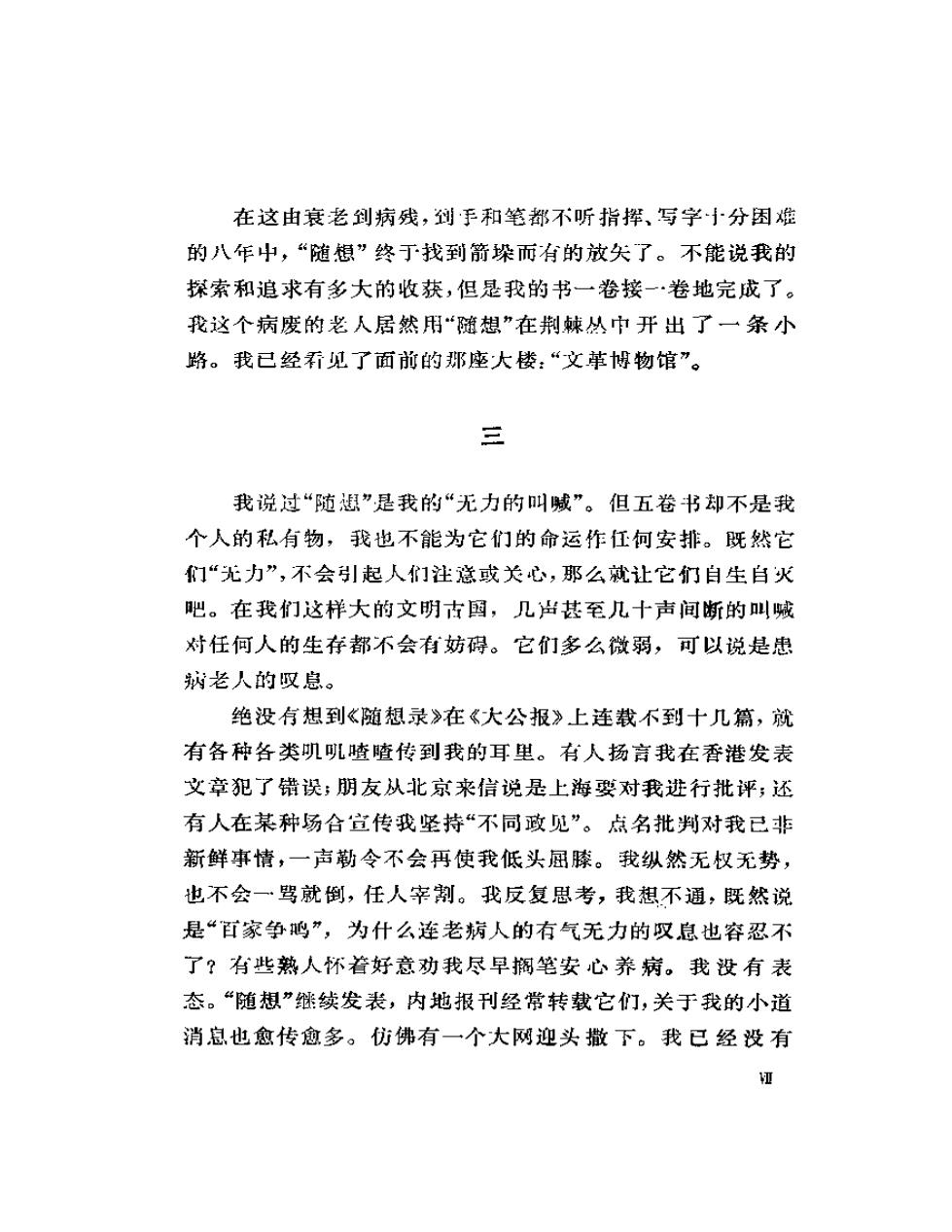
在这由衰老到病残,到手和笔都不听指挥、写字小分困难 的八年中,“随想”终于找到箭垛而有的放矢了。不能说我的 探索和追求有多大的收获,但是我的书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 我这个病废的老人居然用“随想”在荆棘丛巾开出了一条小 路。我已经看见了面前的那座大楼:“文革博物馆”。 三 我说过“随想”是我的“无力的叫喊”。但五爸书却不是我 个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为它们的命运作任何安排。既然它 们“无力”,不会引起人们注意或关心,那么就让它们自生自火 吧。在我们这样大的文明古国,几出基至几十声间断的叫喊 对任何人的生存都不会有妨碍。它们多么微弱,可以说是患 纳老人的叹息。 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 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 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 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 新鲜事情,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 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我反复思考,我想不通,既然说 是“百家争鸭”,为什么连老病人的有气无力的叹息也容忍不 了?有些熟人怀着好意劝我尽早搁笔安心养病。我没有表 态。“随想”继续发表,内地报刊经常转载它们,关于我的小道 消息也愈传愈多。衍佛有一个大网迎头撒下。我已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