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刻宋板注疏总目录 周易正义十卷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额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二十卷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七十卷汉毛公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春秋毅梁传注疏二十卷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九卷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十卷晋郭璞注,宋邪昺疏。 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右《十三经注疏》共四百十六卷。谨案《五代会要》:后唐 长兴三年,始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经书之刻木板,实始于 此。逮两宋刻本浸多,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即南宋岳珂《九经 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也。其书刻于宋南渡之后, 由元入明,递有修补,至明正德中,其板犹存。是以十行本为 诸本最古之册。此后有闽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 有明监板,乃明万历中用闽本重刻者。有汲古阁毛氏板,乃明 崇祯中用明监本重刻者。辗转翻刻,讹谬百出。明监板已毁, 今各省书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阁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识读,近 人修补更多讹舛。元家所藏十行宋本有十一经,虽无《仪礼〉

《尔雅),但有苏州北宋所刻之单疏板本,为贾公彦、邢昺之原 书,此二经更在十行本之前。元旧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虽 不专主十行本、单疏本,而大端实在此二本。嘉庆二十年,元 至江西,武宁卢氏宣旬读余《校勘记)而有慕于宋本,南昌给事 中黄氏中杰亦苦毛板之朽,因以元所藏十一经至南昌学堂重 刻之,且借校苏州黄氏丕烈所藏单疏二经重刻之,近盐巡道胡 氏稷亦从吴中购得十一经,其中有可补元戴本中所残缺者,于 是宋本注疏可以复行于世,岂独江西学中所私哉!刻书者最 患以臆见改古书,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误字,亦不使 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据《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 卷之末,俾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慎之至也。其经 文、注文有与明本不同,恐后人习读明本而反臆疑宋本之误, 故卢氏亦引校勘记载于卷后,慎之至也。窃谓士人读书,当从 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 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 矣。至于注疏诸义,亦有是有非。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甚 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之也。 二十一年秋,刻板初成,藏其板于南昌学,使士林书坊皆可就 而印之。学中因书成,请序于元。元谓圣贤之经,如日月经 天,江河行地,安敢以小言冠兹卷首,惟记刻书始末于目录之 后,复敬录《软定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各《提要)于各注疏之 前,俾束身修行之士,知我大清儒学远轶前代,由此潜心敦品、 博学笃行,以求古圣贤经传之本源,不为虚浮孤陋两途所误云 尔。 太子少保光禄大夫江西巡抚兼提督扬州阮元谨记

3 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后记 嘉庆二十有一年秋八月,南昌学堂重刊宋本《十三经注 疏》,成卷四百十六,并附录《校勘记》,为书万一千八有一十 叶。距始事于二十年仲春,历时十有九月,盖官于斯土与生是 邦者合其心力而为之者也,稷窃心慰焉。囊岁癸酉,稷承乏江 宁盐法道,适浙闽制府桐城方公维甸予告在籍,相与过从,讲 求政事之余,究研经义。时以各注疏本异同得失,参差互见, 近日坊间重刻汲古阁毛氏本,舛误滋多。计欲重刊之,而稷调 任江西,厥议遂寝。越明年甲戌,宫保阮公元来抚江右,稷向 读其所著《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心知其所藏宋本之善,欲请观 之。而莅政之初,公事旁午。逾岁初春,始获所愿。稷昔欲重 刊而志未逮者,又枰然动矣。武宁贡生卢宜旬,宫保门下士, 于稷夙有文字契,至是来谒,属董溉事,以宋本召工剞劂。而 一时贤士大夫乐与观成者,威鼓舞而赞襄之。于官则有今江 南苏松督粮道、前九江府知府方体,今江西督粮道、前广信府 知府王赓言,今南昌府知府张敦仁,暨南昌县知县陈煦、新建 县知县郑祖琛,署鄱阳县知县、候补知州周澍,浮梁县知县刘 丙,广丰县知县阿应麟,会昌县知县、候补知州曾晖春,二品荫 生仪征阮常生。于绅则有给事中黄中杰,御史卢浙,编修黄中 模,员外黄中栻,检讨罗允叔,举人余成教,贡生赵仪吉、袁泰 开、李桢,或输廉以助,或分经以校,续残补阙,证是存疑,而宫 保于退食余闲,详加勘定,且令庋其版于学中,俾四方读者皆 可就而印之,诚西江之盛事,而宫保嘉惠士林之至意也!宫保 既记其刻书始末于序目之后,稷亦喜夙愿之既副,为记其重刊

4 日月与校刊诸名氏于全书之末云。 江西盐法道分巡瑞袁临等处地方庐江胡稷谨记 重校宋本十三经注疏跋 宫保阮制军前抚江右时,出所藏宋十行本以嘉惠士林。 嘉庆丙子仲春开雕,阅十有九月,至丁丑仲秋板成,为卷四百 一十有六,为叶一万一千八百有奇。董其事者,武宁明经卢君 来庵也。嗣宫保升任两广制军,来庵以创始者乐于观成,板甫 就,急思印本呈制军,以慰其遗泽西江之意。局中襄事者未及 细校,故书一出,颇有淮风别雨之讹,览者憾之。后来庵游幕 湘南,以板移置府学明伦堂,远近购书者皆就印焉。时余司其 事,披览所及,心知有舛误处,而自揣见闻寡陋,藏书不富,未 敢轻为改易。今夏制军自粤邮书,以倪君模所校本一册寄示, 适奉新余君成教亦以所校本寄省。倪君所校计共九十三条, 余君所校计共三十八条,予因合二君所校之本,详加勘对,亲 为检查,督工逐条更正,是书益增美备。于此想见宫保尊经教 士之心,历十余年而不倦,隔数千里而不忘,而宇内好古之士 旁搜博采,相与正讹纠缪,岂非经学昌明之盛事哉!倘四方君 子更有考订所及补目前所未备者,随其所得,邮寄省垣,俾得 汇梓更正,亦皆有补于后学云。 道光丙戌岁仲冬月南昌府学教授盱江朱华临谨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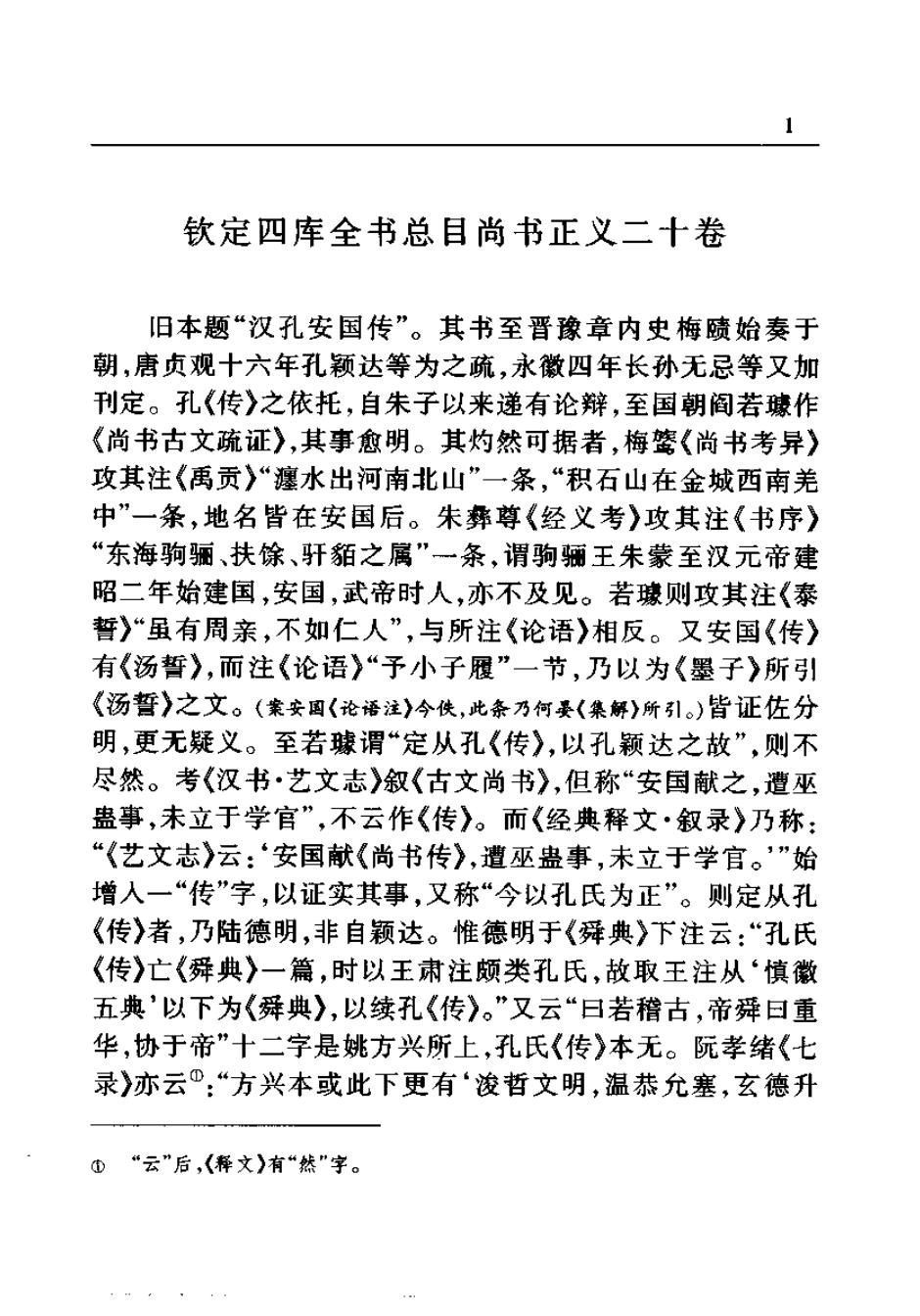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尚书正义二十卷 旧本题“汉孔安国传”。其书至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奏于 朝,唐贞观十六年孔颖达等为之疏,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又加 刊定。孔《传》之依托,自朱子以来递有论辩,至国朝阎若璩作 《尚书古文疏证),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据者,梅瓷《尚书考异》 攻其注《禹贡》“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条,“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 中”一条,地名皆在安国后。朱彝尊《经义考》攻其注《书序》 “东海驹骊、扶馀、开貊之属”一条,谓驹骊王朱蒙至汉元帝建 昭二年始建国,安国,武帝时人,亦不及见。若璩则攻其注《泰 誓〉“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与所注《论语》相反。又安国〈传》 有《汤誓》,而注《论语》“予小子履”一节,乃以为《墨子》所引 《汤誓》之文。(案安国《论语注》今佚,此条乃何要(集解》所引。)皆证佐分 明,更无疑义。至若骤谓“定从孔《传》,以孔颖达之故”,则不 尽然。考《汉书·艺文志》叙《古文尚书》,但称“安国献之,遭巫 蛊事,未立于学官”,不云作(传》。而《经典释文·叙录》乃称: “《艺文志》云:‘安国献《尚书传》,遭巫蛊事,未立于学官。”始 增人一“传”字,以证实其事,又称“今以孔氏为正”。则定从孔 《传》者,乃陆德明,非自颖达。惟德明于《舜典》下注云:“孔氏 《传》亡《舜典》一篇,时以王肃注颇类孔氏,故取王注从‘慎徽 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又云“日若稽古,帝舜日重 华,协于帝”十二字是姚方兴所上,孔氏《传》本无。阮孝绪〈七 录》亦云:“方兴本或此下更有‘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 “云”后,《释文》有“然”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