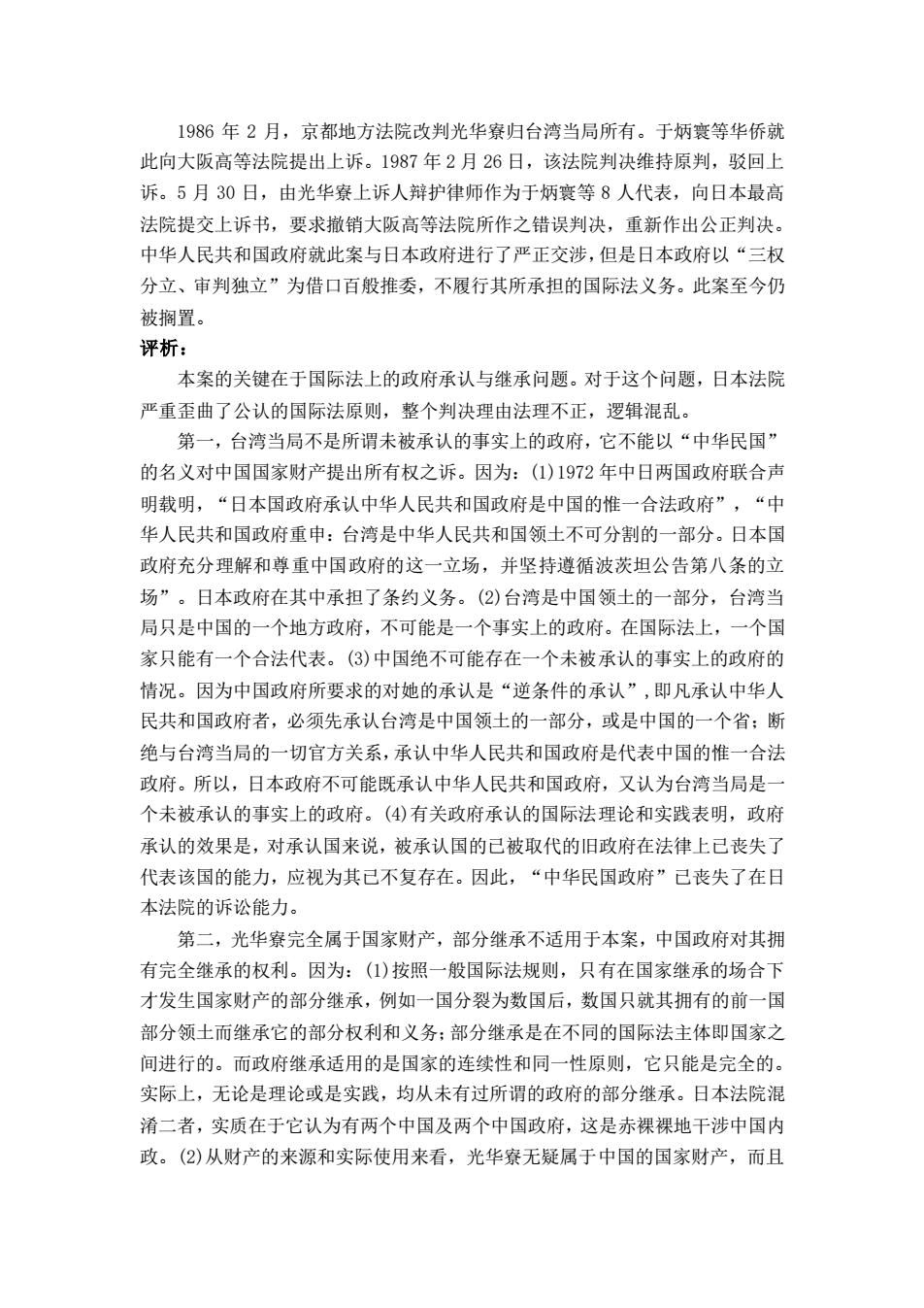
1986年2月,京都地方法院改判光华景归台湾当局所有。于纳寰等华侨就 此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987年2月26日,该法院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 诉。5月30日,由光华案上诉人辩护律师作为于炳寰等8人代表,向日本最高 法院提交上诉书,要求撤销大阪高等法院所作之错误判决,重新作出公正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此案与日本政府进行了严正交涉,但是日本政府以“三权 分立、审判独立”为借口百般推委,不履行其所承担的国际法义务。此案至今仍 被搁置。 评析: 本案的关键在于国际法上的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日本法院 严重歪曲了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整个判决理由法理不正,逻辑混乱。 第一,台湾当局不是所谓未被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它不能以“中华民国” 的名义对中国国家财产提出所有权之诉。因为:(1)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 明载明,“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 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 场”。日本政府在其中承担了条约义务。(②)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当 局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不可能是一个事实上的政府。在国际法上,一个国 家只能有一个合法代表。(3)中国绝不可能存在一个未被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的 情况。因为中国政府所要求的对她的承认是“逆条件的承认”,即凡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者,必须先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或是中国的一个省:断 绝与台湾当局的一切官方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 政府。所以,日本政府不可能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又认为台湾当局是 个未被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④)有关政府承认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表明,政府 承认的效果是,对承认国来说,被承认国的已被取代的旧政府在法律上已丧失了 代表该国的能力,应视为其已不复存在。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已丧失了在日 本法院的诉讼能力。 第二,光华寮完全属于国家财产,部分继承不适用于本案,中国政府对其拥 有完全继承的权利。因为:(1)按照一般国际法规则,只有在国家继承的场合下 才发生国家财产的部分继承,例如一国分裂为数国后,数国只就其拥有的前一国 部分领土而继承它的部分权利和义务:部分继承是在不同的国际法主体即国家之 间进行的。而政府继承适用的是国家的连续性和同一性原则,它只能是完全的。 实际上,无论是理论或是实践,均从未有过所谓的政府的部分继承。日本法院混 淆二者,实质在于它认为有两个中国及两个中国政府,这是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 政。(②)从财产的来源和实际使用来看,光华寮无疑属于中国的国家财产,而且
1986 年 2 月,京都地方法院改判光华寮归台湾当局所有。于炳寰等华侨就 此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987 年 2 月 26 日,该法院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 诉。5 月 30 日,由光华寮上诉人辩护律师作为于炳寰等 8 人代表,向日本最高 法院提交上诉书,要求撤销大阪高等法院所作之错误判决,重新作出公正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此案与日本政府进行了严正交涉,但是日本政府以“三权 分立、审判独立”为借口百般推委,不履行其所承担的国际法义务。此案至今仍 被搁置。 评析: 本案的关键在于国际法上的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日本法院 严重歪曲了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整个判决理由法理不正,逻辑混乱。 第一,台湾当局不是所谓未被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它不能以“中华民国” 的名义对中国国家财产提出所有权之诉。因为:(1)1972 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 明载明,“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 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 场”。日本政府在其中承担了条约义务。(2)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当 局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不可能是一个事实上的政府。在国际法上,一个国 家只能有一个合法代表。(3)中国绝不可能存在一个未被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的 情况。因为中国政府所要求的对她的承认是“逆条件的承认”,即凡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者,必须先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或是中国的一个省;断 绝与台湾当局的一切官方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 政府。所以,日本政府不可能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又认为台湾当局是一 个未被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4)有关政府承认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表明,政府 承认的效果是,对承认国来说,被承认国的已被取代的旧政府在法律上已丧失了 代表该国的能力,应视为其已不复存在。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已丧失了在日 本法院的诉讼能力。 第二,光华寮完全属于国家财产,部分继承不适用于本案,中国政府对其拥 有完全继承的权利。因为:(1)按照一般国际法规则,只有在国家继承的场合下 才发生国家财产的部分继承,例如一国分裂为数国后,数国只就其拥有的前一国 部分领土而继承它的部分权利和义务;部分继承是在不同的国际法主体即国家之 间进行的。而政府继承适用的是国家的连续性和同一性原则,它只能是完全的。 实际上,无论是理论或是实践,均从未有过所谓的政府的部分继承。日本法院混 淆二者,实质在于它认为有两个中国及两个中国政府,这是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 政。(2)从财产的来源和实际使用来看,光华寮无疑属于中国的国家财产,而且

中日恢复邦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机构也对它进行了有效的监督管理,中国 政府还曾拨款予以修缮。 第三,光华寮为私性财产,不属于政府继承范围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1) 将国家财产分为公性财产和私性财产,只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英美法系国家 和社会主义国家无此区分,而且大陆法系各国的规定也不尽一致。联合围国际委 员会关于国家继承的专题报告中亦有指出,大陆法系的做法不能令人满意。(②) 即使按大陆法系的做法,公性财产是指国家用以显示和行使主权或用来履行涉及 主权的一般义务的财产,这些义务包括国防、安全、促进卫生和教育以及国家发 展等。其中属于大陆法系的日本,认定私性财产的标准也是看该财产是否具有商 业性和赢利性。据此光华寮应是国家公性财产无疑。因为众所周知,它是因家 变卖财产所得公款购置并专用于教育目的的房产,不具有商业性和营利性。日本 法院将国家公性财产限定于用于外交和领事方面的财产的说法,在国际法上没有 任何根据,纯属杜撰。 日本政府在本案中所持的立场也是完全错误的。日本政府所谓其国内法规定 的“三权分立、审判独立”的借口不能成立,不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1)在国际法上,一国的任何机关均必须遵守该国或该国政府所代表该国缔结 的条约,遵守公认的国际法规范。《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7条明确规定,“一 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日本政府既然承担了不搞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条约义务,就应切实履行。日本法院也不能以“司法 独立”为借口不按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办事,否则日本政府有权监督、纠正。(2) 在因内法上,依各国通例,三权分立中的行政权属于政府,而外交权又属于行政 权的一个部分。日本政府对中国所作的承诺和所承担的条约义务,既是行使其行 政权的结果,也得到了具有立法权的日本国会的认可和同意,因此对日本法院具 有拘束力。如果法院一意孤行,日本政府有权予以纠正。美国国务院及司法部在 “湖广铁路债券案”中派员出庭支持中国政府的主张即是明证。(3)“三权分 立”亦包含“三权制衡”之义,司法独立决不等于司法机关可以为所欲为,司法 权应受行政权、立法权的制约,这是自明之理。因此,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日本 政府均有权进行行政干预。日本政府的不作为是违背其对中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 的。 间题: (1)如何评价日本法院对本案的判决?本案应该如何终结? (2)政府承认与继承的关系如何? 11、湖广铁路债券案一司法豁免权、国家债务继承
中日恢复邦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机构也对它进行了有效的监督管理,中国 政府还曾拨款予以修缮。 第三,光华寮为私性财产,不属于政府继承范围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1) 将国家财产分为公性财产和私性财产,只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英美法系国家 和社会主义国家无此区分,而且大陆法系各国的规定也不尽一致。联合国国际委 员会关于国家继承的专题报告中亦有指出,大陆法系的做法不能令人满意。(2) 即使按大陆法系的做法,公性财产是指国家用以显示和行使主权或用来履行涉及 主权的一般义务的财产,这些义务包括国防、安全、促进卫生和教育以及国家发 展等。其中属于大陆法系的日本,认定私性财产的标准也是看该财产是否具有商 业性和赢利性。据此,光华寮应是国家公性财产无疑。因为众所周知,它是国家 变卖财产所得公款购置并专用于教育目的的房产,不具有商业性和营利性。日本 法院将国家公性财产限定于用于外交和领事方面的财产的说法,在国际法上没有 任何根据,纯属杜撰。 日本政府在本案中所持的立场也是完全错误的。日本政府所谓其国内法规定 的“三权分立、审判独立”的借口不能成立,不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1)在国际法上,一国的任何机关均必须遵守该国或该国政府所代表该国缔结 的条约,遵守公认的国际法规范。《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7 条明确规定,“一 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日本政府既然承担了不搞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条约义务,就应切实履行。日本法院也不能以“司法 独立”为借口不按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办事,否则日本政府有权监督、纠正。(2) 在国内法上,依各国通例,三权分立中的行政权属于政府,而外交权又属于行政 权的一个部分。日本政府对中国所作的承诺和所承担的条约义务,既是行使其行 政权的结果,也得到了具有立法权的日本国会的认可和同意,因此对日本法院具 有拘束力。如果法院一意孤行,日本政府有权予以纠正。美国国务院及司法部在 “湖广铁路债券案”中派员出庭支持中国政府的主张即是明证。(3)“三权分 立”亦包含“三权制衡”之义,司法独立决不等于司法机关可以为所欲为,司法 权应受行政权、立法权的制约,这是自明之理。因此,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日本 政府均有权进行行政干预。日本政府的不作为是违背其对中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 的。 问题: (1)如何评价日本法院对本案的判决?本案应该如何终结? (2)政府承认与继承的关系如何? 11、湖广铁路债券案——司法豁免权、国家债务继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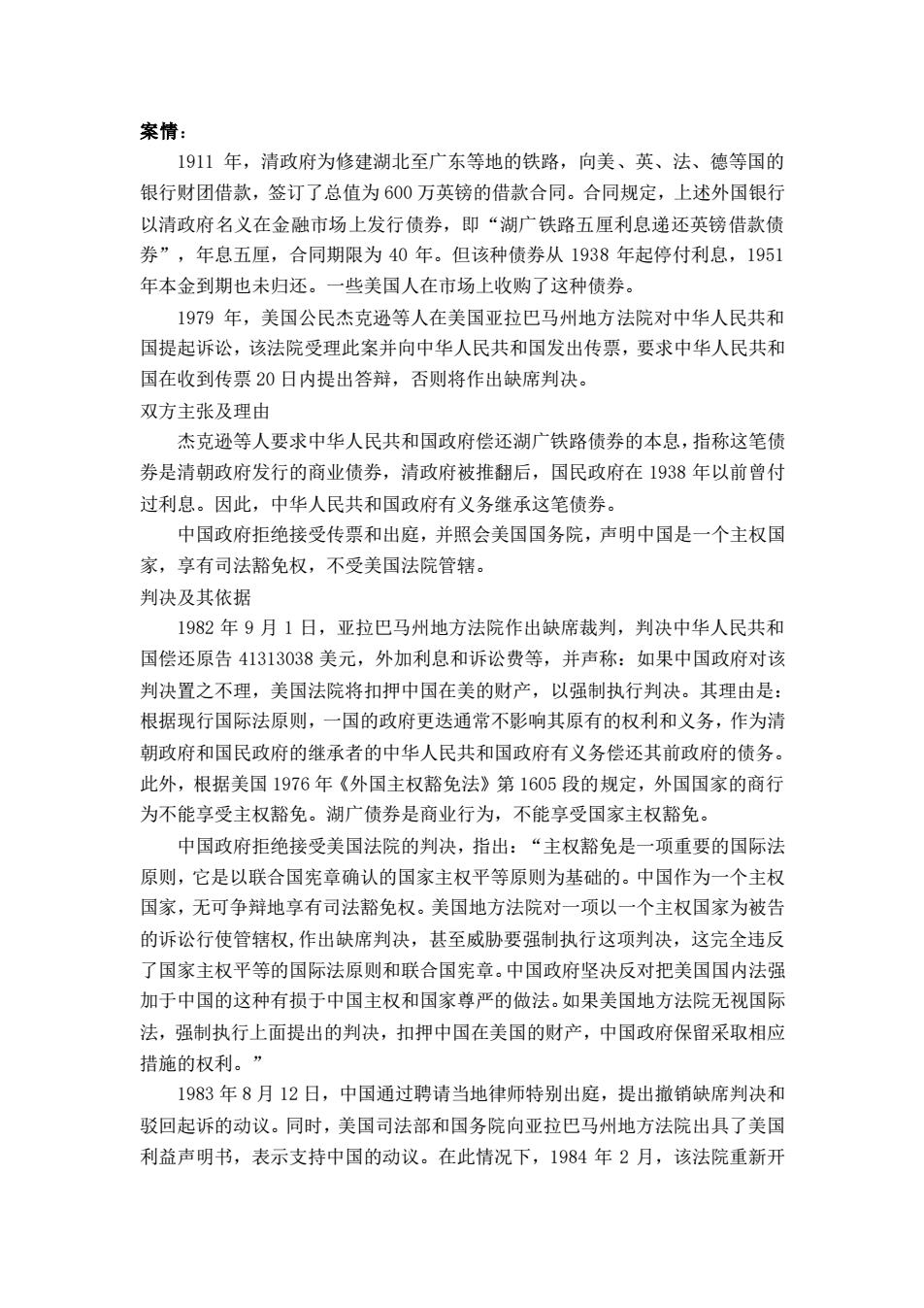
案情: 1911年,清政府为修建湖北至广东等地的铁路,向美、英、法、德等国的 银行财团借款,签订了总值为6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上述外国银行 以清政府名义在金种市场上发行债券,即“湖广铁路五厘利息递还英密借债 券”,年息五厘,合同期限为40年。但该种债券从1938年起停付利息,1951 年本金到期也未归还。一些美国人在市场上收购了这种债券。 1979年,美国公民杰克逊等人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提起诉讼,该法院受理此案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传票,要求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收到传票20日内提出答辩,否则将作出缺席判决。 双方主张及理由 杰克逊等人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还湖广铁路债券的本息,指称这笔债 券是清朝政府发行的商业债券,清政府被推翻后,国民政府在1938年以前曾付 过利息。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义务继承这笔债券。 中国政拒绝接受传票和出庭,并照会美固围务院,声明中围是一个主权压 家,享有司法豁免权,不受美国法院管辖。 判决及其依据 1982年9月1日,亚拉巴马州地方法院作出缺席裁判,判决中华人民共和 国偿还原告41313038美元,外加利息和诉讼费等,并声称:如果中国政府对该 判决置之不理,美国法院将扣押中国在美的财产,以强制执行判决。其理由是 根据现行国际法原则,一国的政府更迭通常不影响其原有的权利和义务,作为清 朝政府和国民政府的继承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义务偿还其前政府的债务 此外,根据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第1605段的规定,外国国家的商行 为不能享受主权豁免。湖广债券是商业行为,不能享受国家主权豁免 中国政府拒绝接受美国法院的判决,指出:“主权豁免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 原则,它是以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中国作为一个主权 国家,无可争辩地享有司法豁免权。美国地方法院对一项以一个主权国家为被告 的诉讼行使管辖权,作出缺席判决,甚至威胁要强制执行这项判决,这完全违反 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把美国国内法强 加于中国的这种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国家尊严的做法。如果美国地方法院无视国际 法,强制执行上面提出的判决,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财产,中国政府保留采取相应 措施的权利。” 1983年8月12日,中国通过聘请当地律师特别出庭,提出撤销缺席判决和 驳回起诉的动议。同时,美国司法部和国务院向亚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出具了美国 利益声明书,表示支持中国的动议。在此情况下,1984年2月,该法院重新开
案情: 1911 年,清政府为修建湖北至广东等地的铁路,向美、英、法、德等国的 银行财团借款,签订了总值为 600 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上述外国银行 以清政府名义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即“湖广铁路五厘利息递还英镑借款债 券”,年息五厘,合同期限为 40 年。但该种债券从 1938 年起停付利息,1951 年本金到期也未归还。一些美国人在市场上收购了这种债券。 1979 年,美国公民杰克逊等人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提起诉讼,该法院受理此案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传票,要求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收到传票 20 日内提出答辩,否则将作出缺席判决。 双方主张及理由 杰克逊等人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还湖广铁路债券的本息,指称这笔债 券是清朝政府发行的商业债券,清政府被推翻后,国民政府在 1938 年以前曾付 过利息。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义务继承这笔债券。 中国政府拒绝接受传票和出庭,并照会美国国务院,声明中国是一个主权国 家,享有司法豁免权,不受美国法院管辖。 判决及其依据 1982 年 9 月 1 日,亚拉巴马州地方法院作出缺席裁判,判决中华人民共和 国偿还原告 41313038 美元,外加利息和诉讼费等,并声称:如果中国政府对该 判决置之不理,美国法院将扣押中国在美的财产,以强制执行判决。其理由是: 根据现行国际法原则,一国的政府更迭通常不影响其原有的权利和义务,作为清 朝政府和国民政府的继承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义务偿还其前政府的债务。 此外,根据美国 1976 年《外国主权豁免法》第 1605 段的规定,外国国家的商行 为不能享受主权豁免。湖广债券是商业行为,不能享受国家主权豁免。 中国政府拒绝接受美国法院的判决,指出:“主权豁免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 原则,它是以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中国作为一个主权 国家,无可争辩地享有司法豁免权。美国地方法院对一项以一个主权国家为被告 的诉讼行使管辖权,作出缺席判决,甚至威胁要强制执行这项判决,这完全违反 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把美国国内法强 加于中国的这种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国家尊严的做法。如果美国地方法院无视国际 法,强制执行上面提出的判决,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财产,中国政府保留采取相应 措施的权利。” 1983 年 8 月 12 日,中国通过聘请当地律师特别出庭,提出撤销缺席判决和 驳回起诉的动议。同时,美国司法部和国务院向亚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出具了美国 利益声明书,表示支持中国的动议。在此情况下,1984 年 2 月,该法院重新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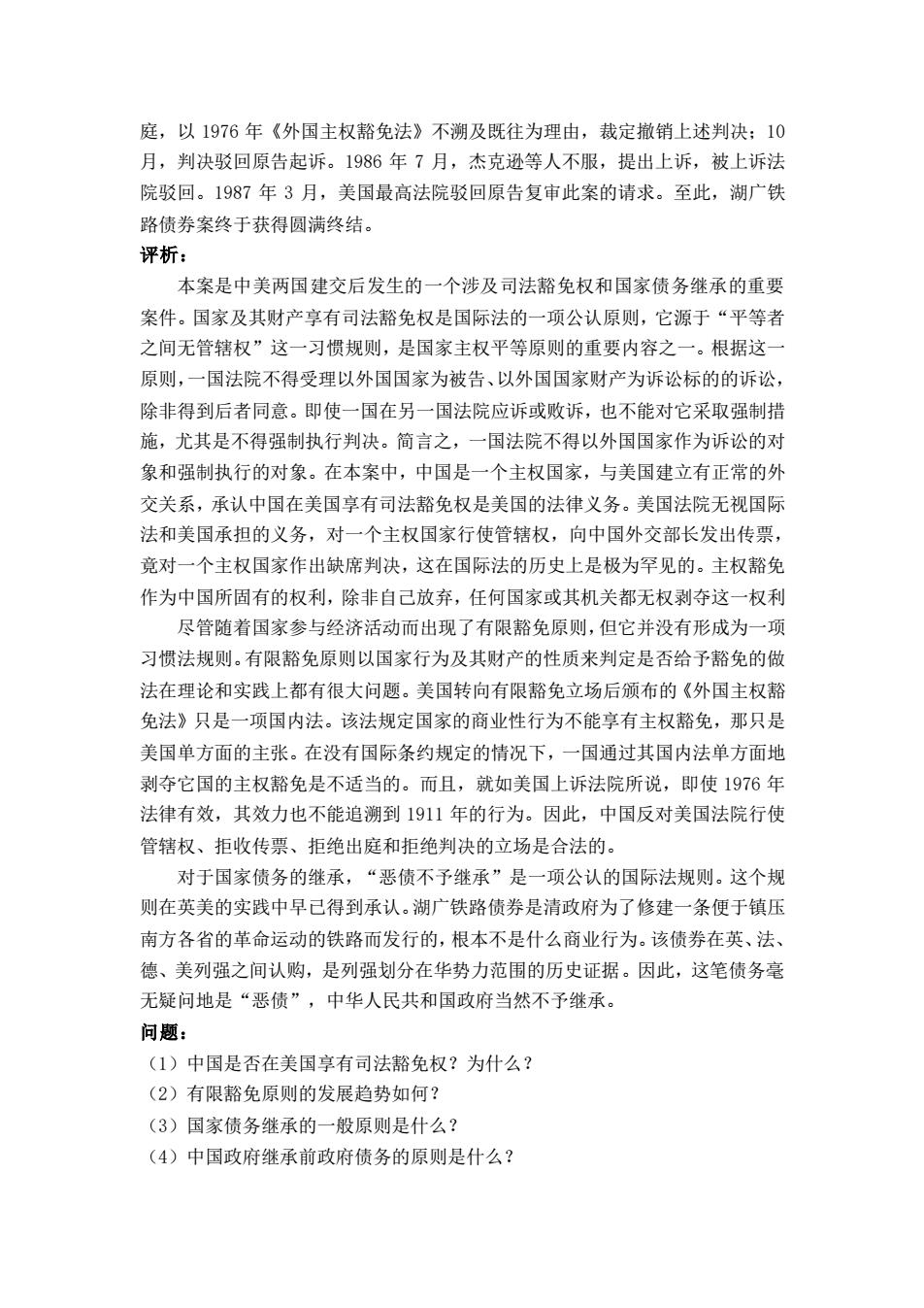
庭,以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不溯及既往为理由,裁定撤销上述判决:10 月,判决驳回原告起诉。1986年7月,杰克逊等人不服,提出上诉,被上诉法 院驳回。1987年3月,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原告复审此案的请求。至此,湖广铁 路债券案终于获得圆满终结。 评析: 本案是中美两国建交后发生的一个涉及司法豁免权和国家债务继承的重要 案件。国家及其财产享有司法豁免权是国际法的一项公认原则,它源于“平等者 之间无管辖权”这一习惯规则,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这 原则,一国法院不得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以外国国家财产为诉讼标的的诉讼, 除非得到后者同意。即使一国在另一国法院应诉或败诉,也不能对它采取强制措 施,尤其是不得强制执行判决。简言之,一国法院不得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的对 象和强制执行的对象。在本案中,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与美国建立有正常的外 交关系,承认中国在美国享有司法豁免权是美国的法律义务。美国法院无视国际 法和美国承担的义务,对一个主权国家行使管辖权,向中国外交部长发出传票, 竟对一个主权国家作出缺席判决,这在国际法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主权豁免 作为中国所固有的权利,除非自己放弃,任何国家或其机关都无权剥夺这一权利 尽管随着国家参与经济活动而出现了有限豁免原则,但它并没有形成为一项 习惯法规则。有限豁免原则以国家行为及其财产的性质来判定是否给予豁免的做 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问题。美国转向有限豁免立场后颁布的《外国主权豁 免法》只是一项国内法。该法规定国家的商业性行为不能享有主权豁免,那只是 美因单方面的主张。在没有国际条约规定的情况下,一国通过其国内法单方面地 剥夺它国的主权豁免是不适当的。而且,就如美国上诉法院所说,即使1976年 法律有效,其效力也不能追溯到1911年的行为。因此,中国反对美国法院行使 管辖权、拒收传票、拒绝出庭和拒绝判决的立场是合法的。 对于国家债务的继承,“恶债不予继承”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规则。这个规 则在英美的实践中早已得到承认。湖广铁路债券是清政府为了修建一条便于镇压 南方各省的革命运动的铁路而发行的,根本不是什么商业行为。该债券在英、法、 德、美列强之间认购,是列强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历史证据。因此,这笔债务毫 无疑问地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然不予继承。 问题: (1)中国是否在美国享有司法豁免权?为什么? (2)有限豁免原则的发展趋势如何? (3)国家债务继承的一般原则是什么? (4)中国政府继承前政府债务的原则是什么?
庭,以 1976 年《外国主权豁免法》不溯及既往为理由,裁定撤销上述判决;10 月,判决驳回原告起诉。1986 年 7 月,杰克逊等人不服,提出上诉,被上诉法 院驳回。1987 年 3 月,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原告复审此案的请求。至此,湖广铁 路债券案终于获得圆满终结。 评析: 本案是中美两国建交后发生的一个涉及司法豁免权和国家债务继承的重要 案件。国家及其财产享有司法豁免权是国际法的一项公认原则,它源于“平等者 之间无管辖权”这一习惯规则,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这一 原则,一国法院不得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以外国国家财产为诉讼标的的诉讼, 除非得到后者同意。即使一国在另一国法院应诉或败诉,也不能对它采取强制措 施,尤其是不得强制执行判决。简言之,一国法院不得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的对 象和强制执行的对象。在本案中,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与美国建立有正常的外 交关系,承认中国在美国享有司法豁免权是美国的法律义务。美国法院无视国际 法和美国承担的义务,对一个主权国家行使管辖权,向中国外交部长发出传票, 竟对一个主权国家作出缺席判决,这在国际法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主权豁免 作为中国所固有的权利,除非自己放弃,任何国家或其机关都无权剥夺这一权利 尽管随着国家参与经济活动而出现了有限豁免原则,但它并没有形成为一项 习惯法规则。有限豁免原则以国家行为及其财产的性质来判定是否给予豁免的做 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问题。美国转向有限豁免立场后颁布的《外国主权豁 免法》只是一项国内法。该法规定国家的商业性行为不能享有主权豁免,那只是 美国单方面的主张。在没有国际条约规定的情况下,一国通过其国内法单方面地 剥夺它国的主权豁免是不适当的。而且,就如美国上诉法院所说,即使 1976 年 法律有效,其效力也不能追溯到 1911 年的行为。因此,中国反对美国法院行使 管辖权、拒收传票、拒绝出庭和拒绝判决的立场是合法的。 对于国家债务的继承,“恶债不予继承”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规则。这个规 则在英美的实践中早已得到承认。湖广铁路债券是清政府为了修建一条便于镇压 南方各省的革命运动的铁路而发行的,根本不是什么商业行为。该债券在英、法、 德、美列强之间认购,是列强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历史证据。因此,这笔债务毫 无疑问地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然不予继承。 问题: (1)中国是否在美国享有司法豁免权?为什么? (2)有限豁免原则的发展趋势如何? (3)国家债务继承的一般原则是什么? (4)中国政府继承前政府债务的原则是什么?

12、诺特波姆案—国籍、外交保护 案情: 诺特波姆是德国人。1905年他离开德国,开始在危地马拉定居,并把危地 马拉作为其事业的中心。1939年10月,他去列支敦士登探望其兄弟时申请入籍。 按照列支敦士登国籍法,外国人入籍,必须己在该国居住至少3年,但在某些例 外情况下可以免除这个限制。诺特波姆交了一笔费用后获得该限制的豁免,从而 取得列支敦士登国籍。而按照德国国籍法,他同时丧失德国国籍。当时,德国已 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12月,危地马拉驻苏黎世总领事在诺特波姆的列支敦士登护照上签 证,准予其重返危地马拉。他返回危地马拉后,即向危政府申请将其登记簿上的 国籍由德国改为列支敦士登,并经过危政府批准。此后,他一直在危地马拉活动。 1941年12月,危地马拉向德国宣战,德国被列入散困。1943年11月,诺特被 姆被危警方以敌国侨民为由速捕,后被移交给美国。1944年12月,危地马拉当 局撤销了把他登记为列支敦士登公民的行政决定,随后扣押和没收了他在危地马 拉的财产。 1946年,诺特波姆获得释放,他向危地马拉驻美领事申请回危,遭到拒绝, 随后他赴列支敦士登定居。1946年2月,他又向危政府提出撤销1944年作出的 关于取消对他的国籍登记为列国籍的行政决定的请求,也遭到危拒绝。 1951年12月7日,列支敦士登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双方主张及理由 列政府认为,危地马拉当局将其国民诺特波姆逮捕、拘留、驱逐并且排除于 危国境外,以及扣押和没收他的财产,这是违反国际法的:拒绝为这些非法行为 赔偿,也是违反国际法的。 危政府首先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主张,理由是它接受法院管 辖权的声明己于1952年1月26日过期。同时,危指出,尽管列支敦士登己赋予 诺特波姆以列国籍,但危没有对此加以承认的义务。国籍是个人与国家联系的基 础,赋予国籍的前提是个人与国家之间有某种密切的联系。危地马拉并不认为在 本案中列支敦士登与诺特波姆之间有任何密切的联系,而国籍是外交保护的基 础,所以,列不能以国籍为由对诺特波姆提供外交保护,而国际诉讼是外交保护 的方式。因此,法院应驳回列的起诉。 判决及其依据 1953年11月,国际法院对初步反对主张作出裁决,判定对本案有管辖权
12、诺特波姆案——国籍、外交保护 案情: 诺特波姆是德国人。1905 年他离开德国,开始在危地马拉定居,并把危地 马拉作为其事业的中心。1939 年 10 月,他去列支敦士登探望其兄弟时申请入籍。 按照列支敦士登国籍法,外国人入籍,必须已在该国居住至少 3 年,但在某些例 外情况下可以免除这个限制。诺特波姆交了一笔费用后获得该限制的豁免,从而 取得列支敦士登国籍。而按照德国国籍法,他同时丧失德国国籍。当时,德国已 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 年 12 月,危地马拉驻苏黎世总领事在诺特波姆的列支敦士登护照上签 证,准予其重返危地马拉。他返回危地马拉后,即向危政府申请将其登记簿上的 国籍由德国改为列支敦士登,并经过危政府批准。此后,他一直在危地马拉活动。 1941 年 12 月,危地马拉向德国宣战,德国被列入敌国。1943 年 11 月,诺特波 姆被危警方以敌国侨民为由逮捕,后被移交给美国。1944 年 12 月,危地马拉当 局撤销了把他登记为列支敦士登公民的行政决定,随后扣押和没收了他在危地马 拉的财产。 1946 年,诺特波姆获得释放,他向危地马拉驻美领事申请回危,遭到拒绝, 随后他赴列支敦士登定居。1946 年 2 月,他又向危政府提出撤销 1944 年作出的 关于取消对他的国籍登记为列国籍的行政决定的请求,也遭到危拒绝。 1951 年 12 月 7 日,列支敦士登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双方主张及理由 列政府认为,危地马拉当局将其国民诺特波姆逮捕、拘留、驱逐并且排除于 危国境外,以及扣押和没收他的财产,这是违反国际法的;拒绝为这些非法行为 赔偿,也是违反国际法的。 危政府首先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主张,理由是它接受法院管 辖权的声明已于 1952 年 1 月 26 日过期。同时,危指出,尽管列支敦士登已赋予 诺特波姆以列国籍,但危没有对此加以承认的义务。国籍是个人与国家联系的基 础,赋予国籍的前提是个人与国家之间有某种密切的联系。危地马拉并不认为在 本案中列支敦士登与诺特波姆之间有任何密切的联系,而国籍是外交保护的基 础,所以,列不能以国籍为由对诺特波姆提供外交保护,而国际诉讼是外交保护 的方式。因此,法院应驳回列的起诉。 判决及其依据 1953 年 11 月,国际法院对初步反对主张作出裁决,判定对本案有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