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 人都带着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可能要说到的全部东西,想要表达 什么,就从?袋里掏出那个东西来。这种交际方式只有在童话或 幻想小说中才有可能。人类杜会的交际不能采用这种方式。且不 说那个口袋该有多大的容量,好多东西如水、火等还无法往里装, 而且更多的交际内容,比方“远近”、“喜欢”、“真理”等等,根本就不 是具体的东西,你想装也装不了。人类用来交际的不是实在的事 物,而是代表事物的符号。汉语的“字”、英语的“词”都是一种符 号。例如我说“火”或fire,人们听了就知道它代表“物体燃烧时发 出的光和焰”。语心中像“火”或fir这样的字或词都是现实现象 的符号。掌握符号,就是知道了符号所代表的是哪一类事物。这 正像商品交换中的货币那样,一个人如果有了货币就可以买到他 所需要的东西;与此相类似,一个人如果在脑子里储行了符号和符 号的组成规则,就可可以和别人交际,谈论各种事情。 语言符号的构造可以细分为音与义两个方面。“义”是现实现 象的转化或反映,但它必须和一定的语音形式相结合,不然就是一 片混沌、模糊的东西,人们难以掌握同样,声音也只有和·定的意 义相结合,才能生现出清晰的界限。只有声音链条的区分和意义 链条的区分相对应,这种音与义的结合才能组成一个符号。像汉 语的"火”字,uo是它的音,“物体燃烧时发出的光和焰”是它的 义,音和义相结合,就组成了汉语的一个符号。我」听没有学过的 外语,只听到一串乱槽糟的音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由于我 们不知道音与义结合的界限。将现实现象转化为意义,用声音来 表达,形城符号,这是人类为认知现实、改造现实而创造的一种最 有效的交际工月,因为它的容量最大、使用最简便、效果也最好。 语音是用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声音。发音器官每个人都有,随身携 带,人走到哪甲,它就能“跟”到哪甲,张嘴就能说,既不需要像大人 国里的人那样背着一个大口袋,也不需要任何其他专门的物质设 备(即使像旗语这种简单的交际工具,也还需要两根棍子、两块 布)。语言的运转最灵使,容量也最大,每一种语言从发音器官所 能够发出来的音中选择几十个音通过排列组合组成不同的音节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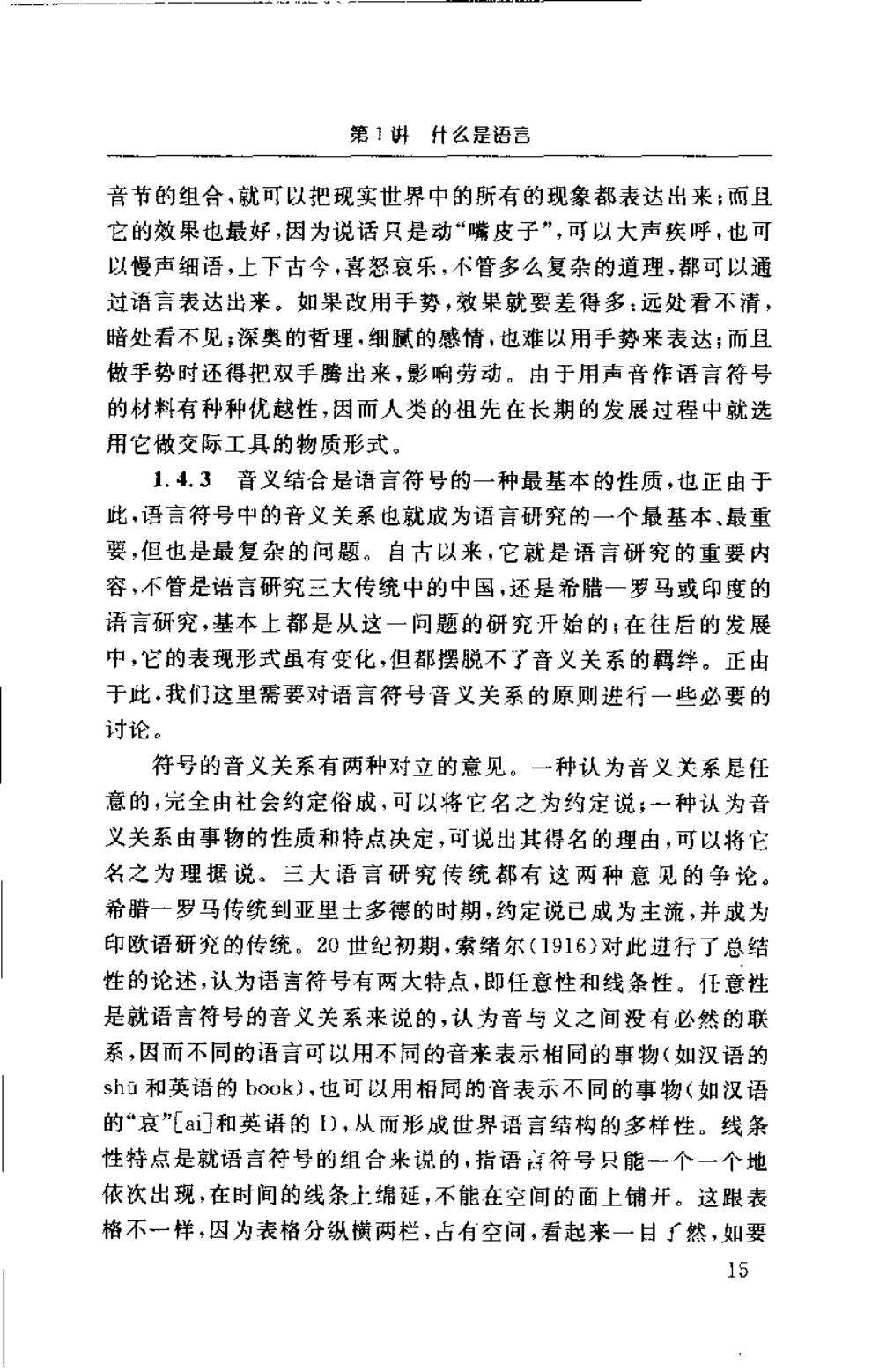
第1讲什么是语言 音节的组合,就可以把现实世界中的所有的现象都表达出来:而且 它的效果也最好,因为说话只是动“嘴皮子”,可以大声疾呼,也可 以慢声细语,上下古今,喜怒哀乐,不管多么复杂的道理,都可以通 过语言表达出来。如果改用手势,效果就要差得多:远处看不清, 暗处看不见;深奥的哲理,细腻的感情,也难以用手势来表达;而且 做手势时还得把双手腾出来,影响劳动。由于用声音作语言符号 的材料有种种优越性,因而人类的祖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就选 用它做交际工具的物质形式。 1.4.3音义结合是语言符号的一种最基本的性质,也正由于 此,语言符号中的音义关系也就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最基本、最重 要,但也是最复杂的问题。自古以来,它就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内 容,不管是诰言研究三大传统中的中国,还是希腊一罗马或印度的 语言研究,基本上都是从这一问题的研究开始的;在往后的发展 中,它的表现形式虽有变化,但都摆脱不了音义关系的羁绊。正由 于此,我们这里需要对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原则进行一些必要的 讨论。 符号的音义关系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音义关系是任 意的,完全由社会约定俗成,可以将它名之为约定说;一种认为音 义关系由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可说出其得名的理由,可以将它 名之为理据说。三大语言研究传统都有这两种意见的争论。 希腊一罗马传统到亚里士多德的时期,约定说已成为主流,并成为 印欧语研究的传统。20世纪初期,索绪尔(1916)对此进行了总结 性的论述,认为语言符号有两大特点,即任意性和线条性。征意性 是就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来说的,认为音与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 系,因而不同的语言可以用不同的音来表示相同的事物(如汉语的 shū和英语的book),也可以用相同的音表示不同的事物(如汉语 的“哀”[ai门和英语的【),从而形成世界语言结构的多样性。线条 性特点是就语言符号的组合来说的,指语符号只能一个一个地 依次出现,在时间的线条上绵延,不能在空间的面上铺开。这跟表 格不一样,囚为表格分纵横两栏,占有空间,看起来一日∫然,如要 15

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 将它说出来,就得经过一番改造的工夫,使之成为语言符号的线 条。一个世纪来,人们都将这两点看成为语言符号的根本性特点, 并将它归人“基本常识”的范畴。 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对印欧语来说,索绪尔的语言符号 任意性学说或许是对的,是“常识”,但对汉语来说,符号的音义关 系可能就会呈现出另一种样子。我们的先辈都强调概念得名的理 据。老子说名生于道,管子说“名生于实”(《九守》),是“物图有形, 形固有名”(《心术上》),汉语传统的这种“名”的理据性认识已渗透 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标志就是孔子的“名正言顺”的 理论。从先秦到清末民初,我们在这一点上似乎从来没有产生过 怀疑,利用文字提供的线索,“因声求义”。西学东渐,国人接受了 西方的语言学说,才強调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论,并且引 证先秦时期荀子《正名》篇里的一段话,即“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 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 成谓之实名”,证明我们早在二千年前就有符号任意性的学说。荀 子的这一论断没有错,但我们对它的理解好像是片面的、错误的, 因为荀子写《正名》篇的目的是反对“公孙龙、惠施之徒乱名改作, 以是为非”(见《荀子集解》的《正名》篇的题解),强调“王者制名”、 “知者分别为之制名”、“后王之成名”等等的“名”的约定裕成,的合 理性,不能、也不必“乱名改作”。至于人们用这一“约定俗成”说来 否定语言符号的理据性,那是由于我们的认识进人了一个误区,对 理据性的成因缺乏正确的理解造成的。理据,说的是概念得名的 理由,人们可以从中说出得名的根据,与约定性原则不是对立的。 为什么?根据汉语的理据性编码原则,我们发现,每一类现实现象 都具有多种多样的特征,每一种特征都有可能成为编码的理据,至 于语言社团选择哪一种特征作为编码的理据,那需要由杜会约定 俗成,因而同一类现象的得名,有的据声,如鸦、鸭、蟋蟀等:有的据 形,如蛔(体迂回而长)、牤、蟒(形体大)、蜘蛛(状其“短”):有的据 其色。如燕(鸟之白颈者)、熊(白鱼),等等。这种研究,古代的研究 姑且不论,而就清末民初的近现代来说,也大有人在,对汉语语源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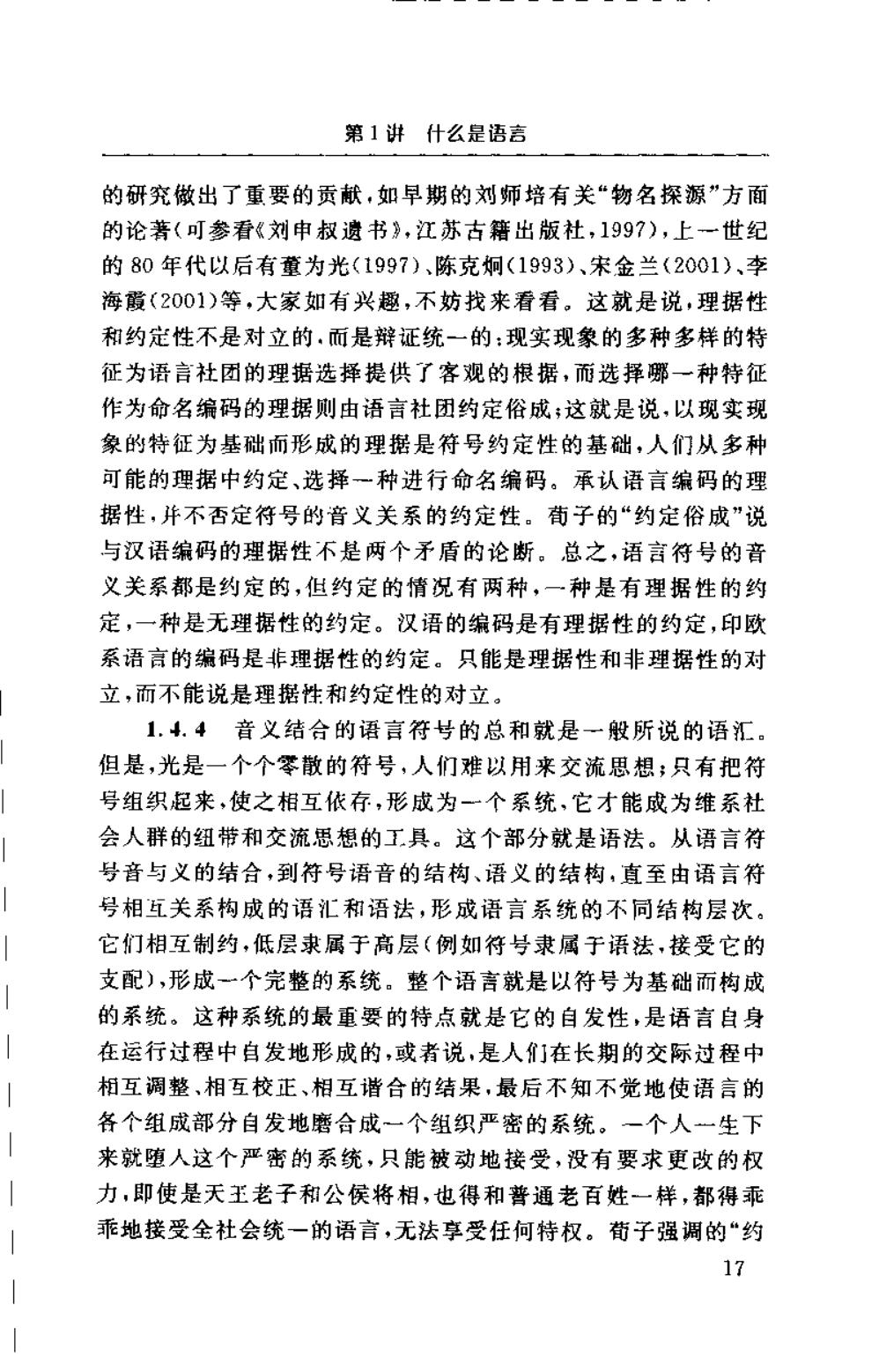
第1讲什么是语言 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早期的刘师培有关“物名探源”方面 的论著(可参看《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上一世纪 的80年代以后有重为光(1997),、陈克炯(1993)、宋金兰(2001)、李 海霞(2001)等,大家如有兴趣,不妨找来看看。这就是说,理据性 和约定性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现实现象的多种多样的特 征为语言杜团的理据选择提供了客观的根据,而选择哪一种特征 作为命名编码的理据则由语言社团约定俗成;这就是说,以现实现 象的特征为基础而形成的理据是符号约定性的基础,人们从多种 可能的理据中约定、选择一种进行命名编码。承认语言编码的理 据性,并不否定符号的音义关系的约定性。荀子的“约定俗成”说 与汉语编码的理据性不是两个矛盾的论断。总之,语言符号的音 义关系都是约定的,但约定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有理据性的约 定,一种是无理据性的约定。汉语的编码是有理据性的约定,印欧 系语言的编码是非理据性的约定。只能是理据性和非理据性的对 立,而不能说是理据性和约定性的对立。 1.4.4音义结合的语言符与的总和就是一般所说的语汇。 但是,光是一个个零辙的符号,人们难以用来交流思想;只有把符 号组织起来,使之相互依存,形成为一个系统,它才能成为维系杜 会人群的纽带和交流思想的工具。这个部分就是语法。从语言符 号音与义的结合,到符号语音的结构、语义的结构,直至由语言符 号相互关系构成的语汇和语法,形成语言系统的不同结构层次。 它们相互制约,低层隶属于高层(例如符号隶属于语法,接受它的 支配),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整个语言就是以符号为基础而构成 的系统。这种系统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自发性,是语言自身 在运行过程中自发地形成的,或者说,是人]在长期的交际过程中 相互调整,相互校正、相互谐合的结果,最后不知不觉地使语言的 各个组成部分自发地磨合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一个人一生下 来就堕人这个严密的系统,只能被动地接受,没有要求更改的权 力,即使是天王老子和公侯将相,也得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都得乖 乖地接受全社会统一的语言,无法享受任何特权。荀子强调的“约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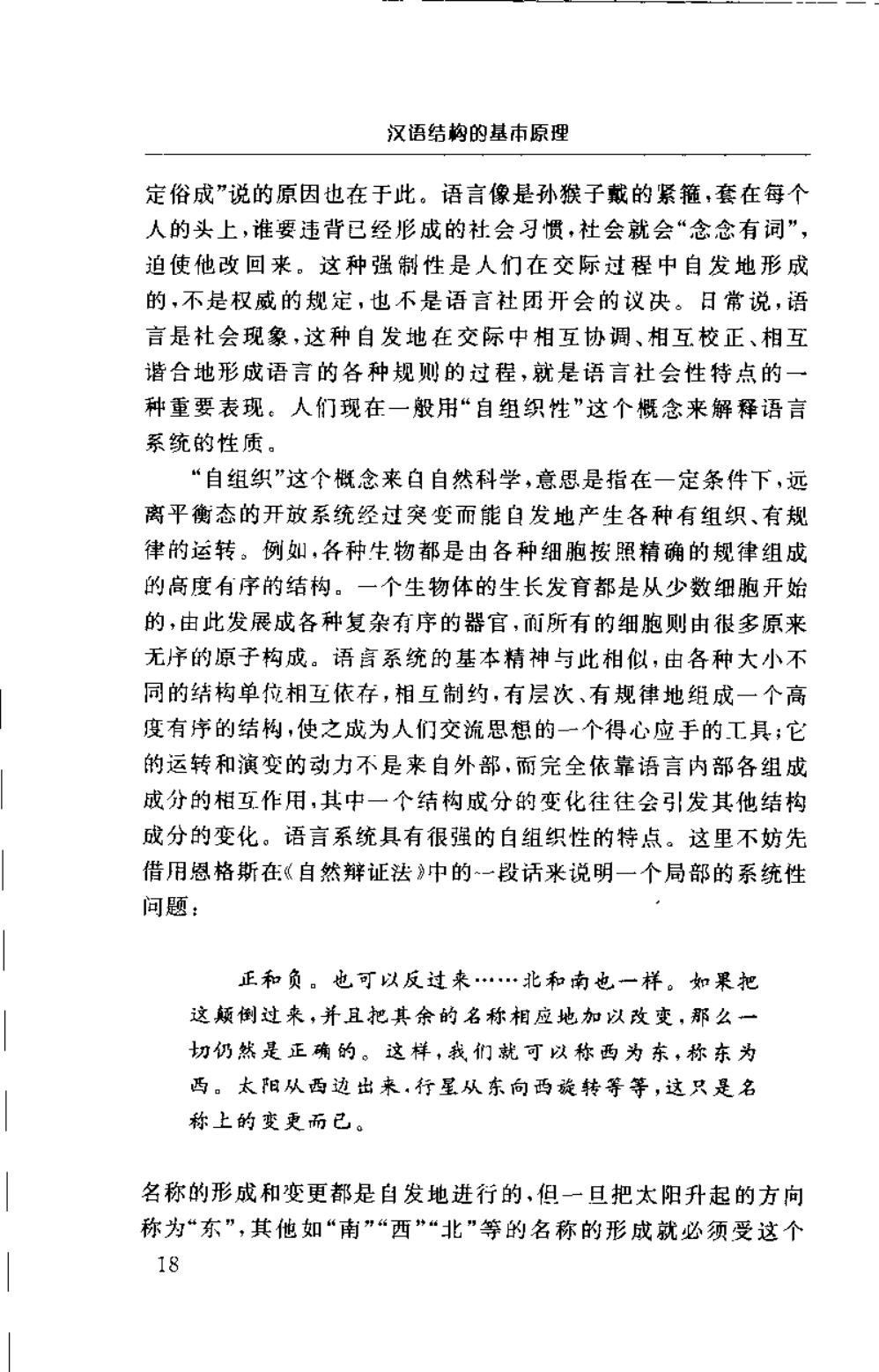
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 定俗成”说的原因也在于此。语言像是孙猴子戴的紧箍,套在每个 人的头上,谁要违背已经形成的社会习惯,社会就会“念念有词”, 迫使他改回来。这种强制性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自发地形成 的,不是权威的规定,也不是语言社团开会的议决。日常说,语 言是社会现象,这种自发地在交际中相互协调、相互校正、相互 谐合地形成语言的各种规则的过程,就是语言社会性特点的一 种重要表现。人们现在一般用“自组织性”这个概念来解释语言 系统的性质。 “自组织”这个概念来自自然科学,意思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远 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经过突变而能自发地产生各种有组织、有规 律的运转。例如,各种生物都是由各种细胞按照精确的规律组成 的高度有序的结构。一个生物体的生长发育都是从少数细胞开始 的,由此发展成各种复杂有序的器官,而所有的细胞则由很多原来 无序的原子构成。语音系统的基本精神与此相似,由各种大小不 同的结构单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有层次、有规律地组成一个高 度有序的结构,使之成为人们交流思想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它 的运转和演变的动力不是来自外部,而完全依靠语言内部各组成 成分的相互作用,其中一个结构成分的变化往往会引发其他结构 成分的变化。语言系统具有很强的自组织性的特点。这里不妨先 借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一个局部的系统性 问题: 正和负。也可以反过来…北和南也一样。如果把 这颜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相应地加以改变,那么一 切仍然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称西为东,称东为 西。太阳从西边出来,行星从东向西旅转等等,这只是名 称上的变更而已。 名称的形成和变更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但一旦把太阳升起的方向 称为“东”,其他如“南”“西”“北”等的名称的形成就必须受这个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