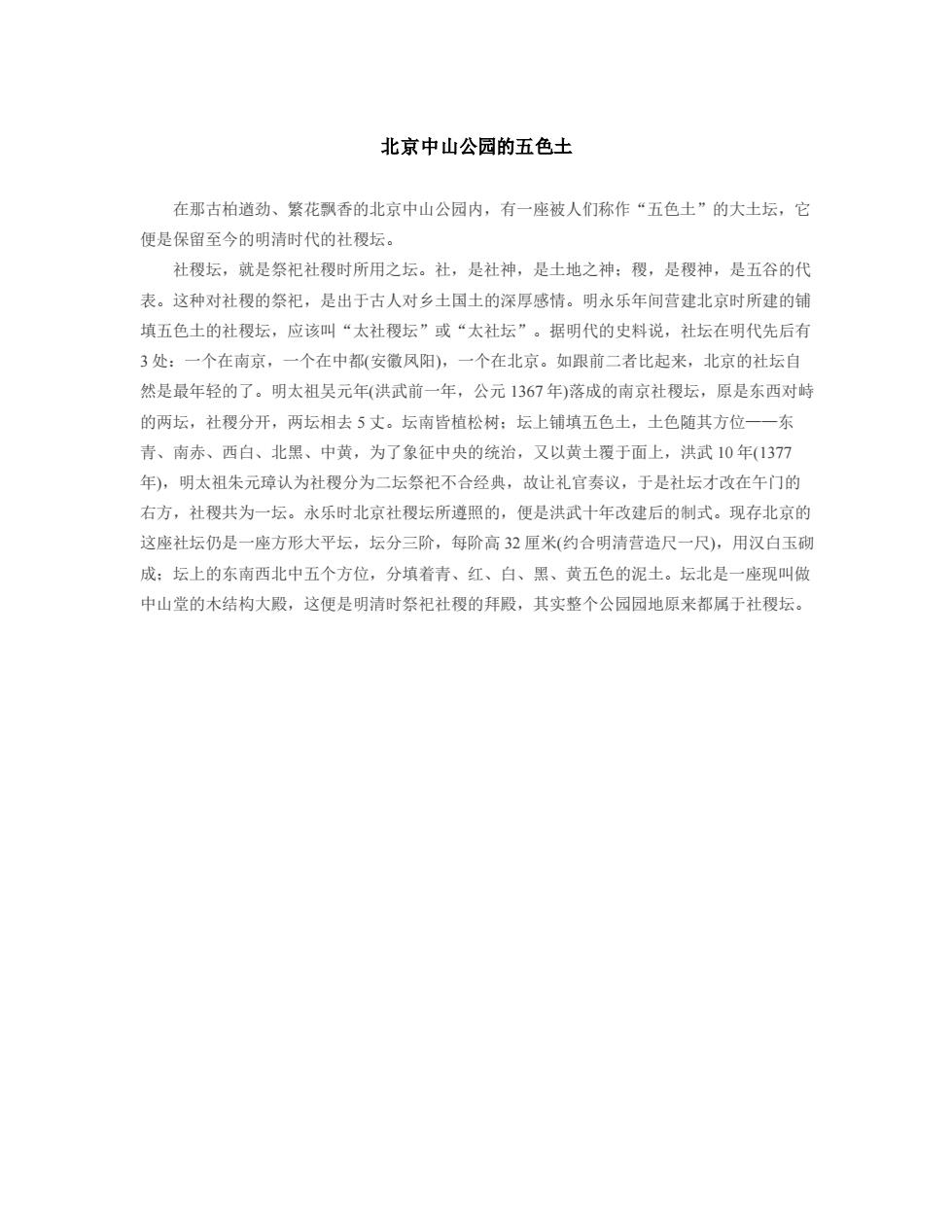
北京中山公园的五色土 在那古柏遒劲、繁花飘香的北京中山公园内,有一座被人们称作“五色土”的大土坛,它 便是保留至今的明清时代的社稷坛。 社稷坛,就是祭祀社稷时所用之坛。社,是社神,是土地之神:稷,是稷神,是五谷的代 表。这种对社稷的祭祀,是出于古人对乡土国土的深厚感情。明永乐年间营建北京时所建的铺 填五色土的社稷坛,应该叫“太社稷坛”或“太社坛”。据明代的史料说,社坛在明代先后有 3处:一个在南京,一个在中都(安徽凤阳),一个在北京。如跟前二者比起来,北京的社坛自 然是最年轻的了。明太祖吴元年(洪武前一年,公元1367年)落成的南京社稷坛,原是东西对峙 的两坛,社稷分开,两坛相去5丈。坛南皆植松树:坛上铺填五色土,土色随其方位一一东 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黄,为了象征中央的统治,又以黄土覆于面上,洪武10年(1377 年),明太祖朱元璋认为社稷分为二坛祭祀不合经典,故让礼官奏议,于是社坛才改在午门的 右方,社稷共为一坛。永乐时北京社稷坛所遵照的,便是洪武十年改建后的制式。现存北京的 这座社坛仍是一座方形大平坛,坛分三阶,每阶高32厘米(约合明清营造尺一尺),用汉白玉砌 成:坛上的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填着青、红、白、黑、黄五色的泥土。坛北是一座现叫做 中山堂的木结构大殿,这便是明清时祭祀社稷的拜殿,其实整个公园园地原来都属于社稷坛
北京中山公园的五色土 在那古柏遒劲、繁花飘香的北京中山公园内,有一座被人们称作“五色土”的大土坛,它 便是保留至今的明清时代的社稷坛。 社稷坛,就是祭祀社稷时所用之坛。社,是社神,是土地之神;稷,是稷神,是五谷的代 表。这种对社稷的祭祀,是出于古人对乡土国土的深厚感情。明永乐年间营建北京时所建的铺 填五色土的社稷坛,应该叫“太社稷坛”或“太社坛”。据明代的史料说,社坛在明代先后有 3 处:一个在南京,一个在中都(安徽凤阳),一个在北京。如跟前二者比起来,北京的社坛自 然是最年轻的了。明太祖吴元年(洪武前一年,公元 1367 年)落成的南京社稷坛,原是东西对峙 的两坛,社稷分开,两坛相去 5 丈。坛南皆植松树;坛上铺填五色土,土色随其方位——东 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黄,为了象征中央的统治,又以黄土覆于面上,洪武 10 年(1377 年),明太祖朱元璋认为社稷分为二坛祭祀不合经典,故让礼官奏议,于是社坛才改在午门的 右方,社稷共为一坛。永乐时北京社稷坛所遵照的,便是洪武十年改建后的制式。现存北京的 这座社坛仍是一座方形大平坛,坛分三阶,每阶高 32 厘米(约合明清营造尺一尺),用汉白玉砌 成;坛上的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填着青、红、白、黑、黄五色的泥土。坛北是一座现叫做 中山堂的木结构大殿,这便是明清时祭祀社稷的拜殿,其实整个公园园地原来都属于社稷坛

北京庙会小吃中“岁寒三友” 一般人谈到岁寒三友皆知为松、竹、梅也。但是早年的京华,每届隆冬,亦有所谓“岁寒 三友”,但非松、竹、梅,而指“‘半空儿’、冻柿子、海棠红”。 所谓“半空儿”,即果仁稀小的花生。那时一般干果行商,趸进大批花生,分别拣择其肥 瘠,按货论价。花生果空而不实者,值最低廉,贩商购得,炒得焦熟,以其香甜气味,售诸爱 好者,取名“半空儿”。寒冬小巷,常有小贩身背大麻袋,叫卖“半空儿,多给”。居民恒有 爱食此者,儿童因出少许钱可买一大堆,亦喜而购之。小贩虽背大麻包,却并不沉重,简单易 卖,很快售罄,满意而去。间亦有狡黠的摊贩,以“半空儿”掺入肥硕花生米中,论堆发售, 待顾客购得吃时方知上当。 中人D 北京 另一“友”为“冻柿子”。柿为秋熟果品。北京的西山、北山产量最丰。柿子初收上市, 小贩叫卖:“赛倭瓜的大柿子一涩了换啦!”及至霜降过后,叫卖改为:“喝了蜜啦一大 柿子!”就此两种吆喝声,便可晓得秋柿与冬柿之不同。柿初熟期,皮厚味涩,须经人工“漤” 过,则色红味甘,食之清脆。一遇霜降,柿已熟透,涩味全消,而肉质熟烂,成为蜜汁,所以 此时叫卖者以“喝蜜”来形容。到了冬令,经过严寒,柿子汁液冻结,用快刀切成薄片,食之 凉彻心脾,且有润燥、利大便之功。当时或有谓能祛除霉气者,不知此言是否科学。 第三友者是“海棠红”。所谓“海棠红”,实是冬天己届全红的海棠。这种海棠经过严寒, 冻得很坚实,街头小贩颇多贩卖,买主大多是孩童。此种海棠,手捏把柄,含入口内一咬,冷 透牙根。笔者幼时常乐于此道,每与同玩小孩,各持一枚咬之,冰得每人频频挤眼而笑。我们
北京庙会小吃中“岁寒三友” 一般人谈到岁寒三友皆知为松、竹、梅也。但是早年的京华,每届隆冬,亦有所谓“岁寒 三友”,但非松、竹、梅,而指“‘半空儿’、冻柿子、海棠红”。 所谓“半空儿”,即果仁稀小的花生。那时一般干果行商,趸进大批花生,分别拣择其肥 瘠,按货论价。花生果空而不实者,值最低廉,贩商购得,炒得焦熟,以其香甜气味,售诸爱 好者,取名“半空儿”。寒冬小巷,常有小贩身背大麻袋,叫卖“半空儿,多给”。居民恒有 爱食此者,儿童因出少许钱可买一大堆,亦喜而购之。小贩虽背大麻包,却并不沉重,简单易 卖,很快售罄,满意而去。间亦有狡黠的摊贩,以“半空儿”掺入肥硕花生米中,论堆发售, 待顾客购得吃时方知上当。 北京 另一“友”为“冻柿子”。柿为秋熟果品。北京的西山、北山产量最丰。柿子初收上市, 小贩叫卖:“赛倭瓜的大柿子——涩了换啦!”及至霜降过后,叫卖改为:“喝了蜜啦——大 柿子!”就此两种吆喝声,便可晓得秋柿与冬柿之不同。柿初熟期,皮厚味涩,须经人工“漤” 过,则色红味甘,食之清脆。一遇霜降,柿已熟透,涩味全消,而肉质熟烂,成为蜜汁,所以 此时叫卖者以“喝蜜”来形容。到了冬令,经过严寒,柿子汁液冻结,用快刀切成薄片,食之 凉彻心脾,且有润燥、利大便之功。当时或有谓能祛除霉气者,不知此言是否科学。 第三友者是“海棠红”。所谓“海棠红”,实是冬天已届全红的海棠。这种海棠经过严寒, 冻得很坚实,街头小贩颇多贩卖,买主大多是孩童。此种海棠,手捏把柄,含入口内一咬,冷 透牙根。笔者幼时常乐于此道,每与同玩小孩,各持一枚咬之,冰得每人频频挤眼而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