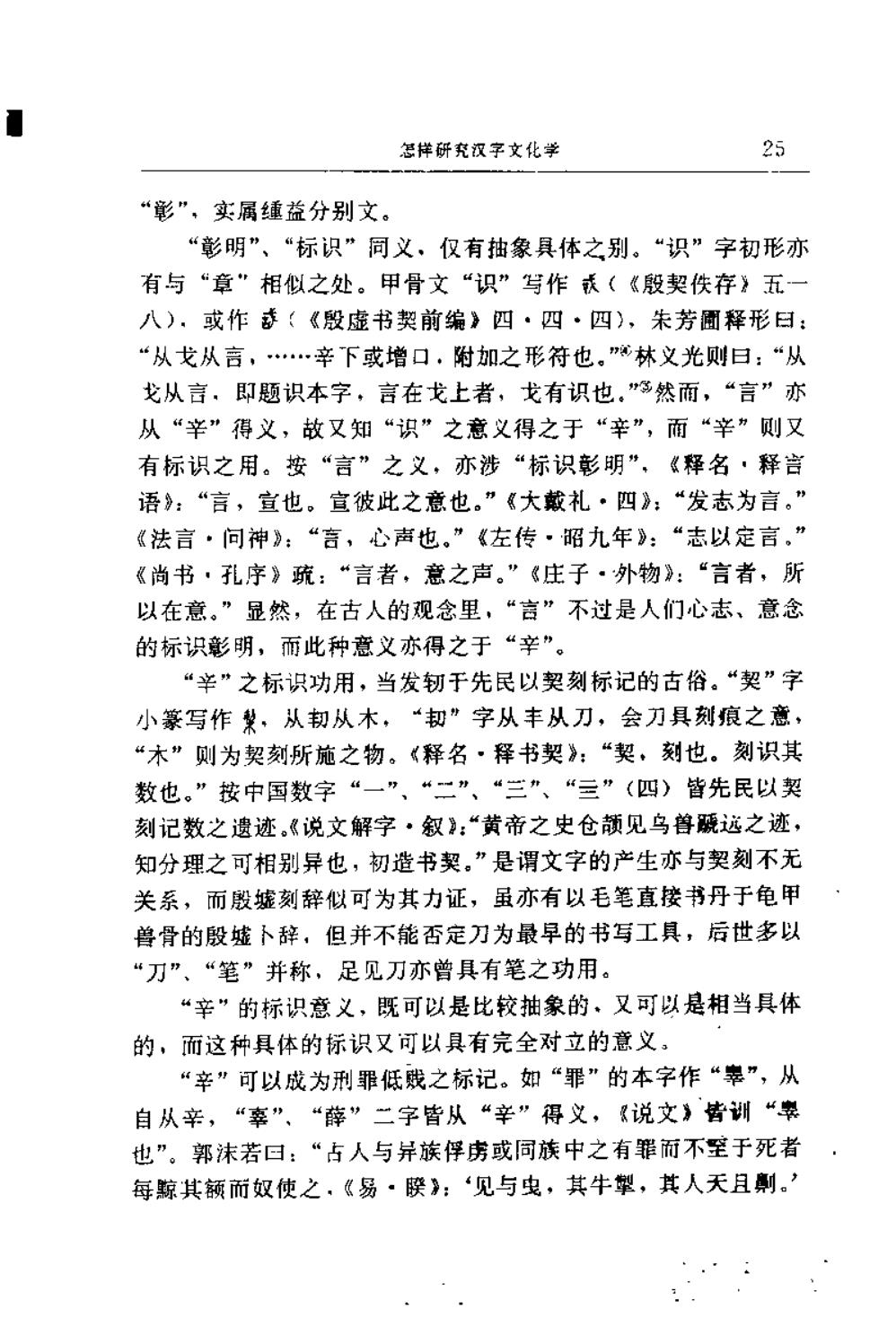
怎样研究汉字文化学 25 “彰”,实属重益分别文。 “彰明”、“标识”同义、仅有抽象具体之别。“识”字初形亦 有与“章”相似之处。甲骨文“识”写作获(《殷契佚存》五一 八),或作〔《殷虚书契前编》四·四·四),朱芳圃释形日: “从戈从言,…辛下或增口·附加之形符也。林义光则日:“从 戈从言,即题识本字,言在戈上者,戈有识也。”然而,“言”亦 从“¥”得义,故又知“识”之意义得之于“辛”,而“¥”侧又 有标识之用。按“言”之义,亦涉“标识彰明”,《释名·释言 语》:“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大戴礼·四》:“发志为言。” 《法言·问神》:“言,心声也。”《左传·昭九年》:“志以定言,” 《尚书·孔序》疏:“言者,意之声。”《庄子·外物》:“言者,所 以在意。”显然,在古人的观念里,“言”不过是人们心志、意念 的标识彰明,而此种意义亦得之于“辛”。 “辛”之标识功用,当发轫于先民以契刻标记的古俗。“契”字 小篆写作装,从㓞从木,“㓞”字从丰从刀,会刀具刻痕之意, “木”则为契刻所施之物。《释名·释书契》:“契、刻也。刻识其 数也。”按中国数字“一”、“二”、“三”、“三”(四》皆先民以契 刻记数之遗迹。《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顿见乌兽蹏远之迹, 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是谓文字的产生亦与契刻不无 关系,而殷墟刻辞似可为其力证,虽亦有以毛笔直接书丹于龟甲 兽骨的殷墟不辞,但并不能否定刀为最早的书写工具,后世多以 “刀”、“笔”并称,足见刀亦曾具有笔之功用。 “辛”的标识意义,既可以是比较抽象的、又可以是相当具体 的,而这种具体的标识又可以具有完全对立的意义, “辛”可以成为刑罪低戏之标记。如“罪”的本字作“睾”,从 自从辛,“辜”、“薛”二字皆从“辛”得义,《说文》皆训“架 也”。郭沫若回:“占人与异族俘虏或同族中之有罪而不至于死者 每黥其额而奴使之,《易·睽》:‘见与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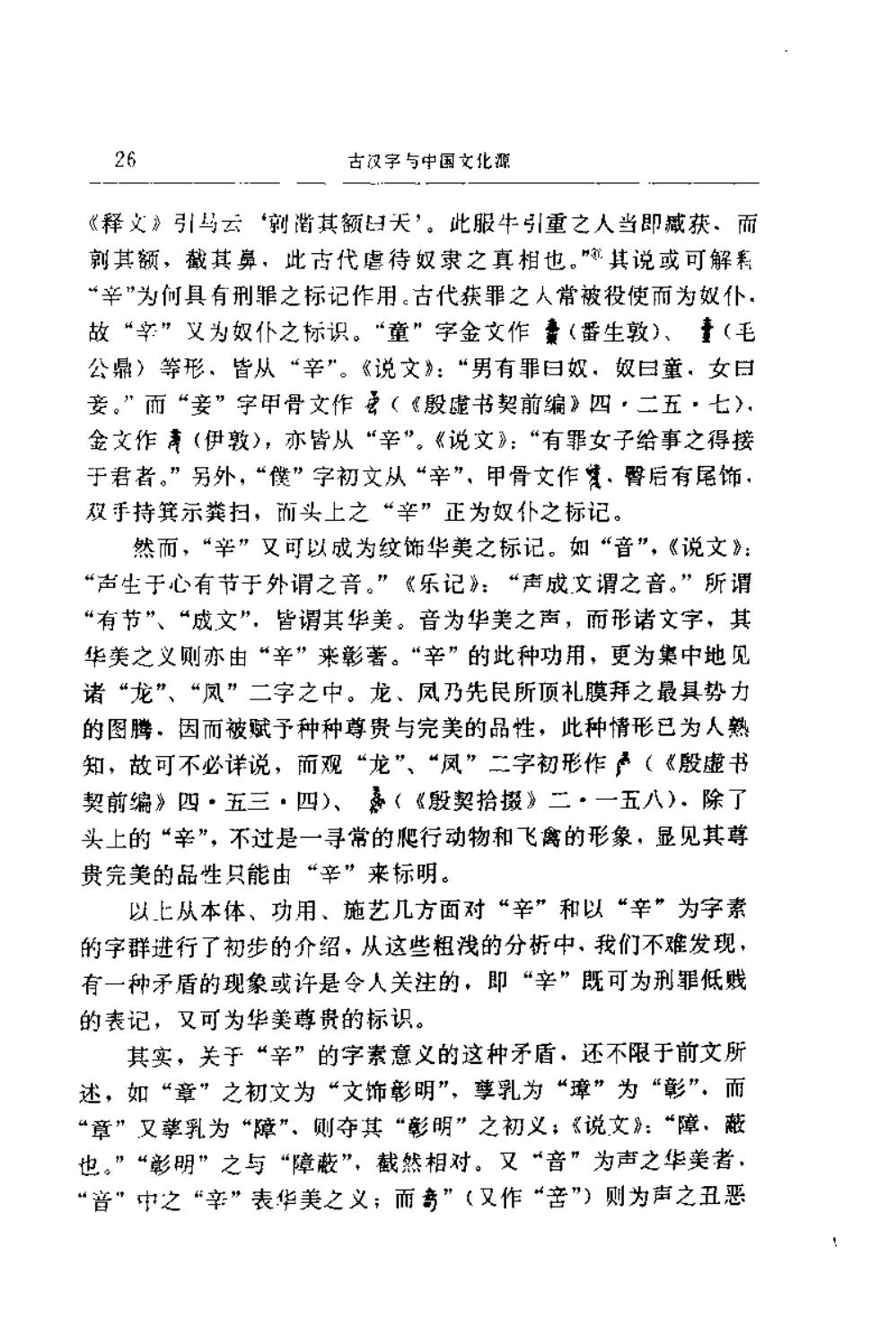
26 古汉字与中国文北源 《释义》引马云‘荆凿其额」天’。此服牛引重之人当即臧获、而 刺其额,截其鼻、此古代虐待奴隶之真相也。”心其说或可解 “辛”为何具有刑罪之标记作用。古代获罪之人常被役使而为奴仆, 故“竿”义为奴仆之标识。“童”字金文作囊(番生敦)、壹(毛 公鼎)等形、皆从“辛”。《说文》:“男有罪日奴、奴日童,女日 妾。”而“妾”字甲骨文作(《殷虚书契前编》四·二五·七), 金文作青(伊敦),亦皆从“辛”。《说文》:“有罪女子给事之得接 于君者。”另外,“僕”字初文从“辛”、甲骨文作、臀后有尾饰, 双手持箕示粪扫,而头上之“辛”正为奴仆之标记。 然而,“辛”又可以成为纹饰华美之标记。如“音”,《说文》: “声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乐记》:“声成文谓之音。”所谓 “有节”、“成文”,皆谓其华美。音为华美之声,而形诸文字,其 华美之义则亦由“辛”来彰著。“辛”的此种功用,更为集中地见 诸“龙”、“凤”二字之中。龙、凤乃先民所顶礼膜拜之最具势力 的图腾、因而被赋予种种尊贵与完美的品性,此种情形已为人熟 知,故可不必详说,而观“龙”、“风”二字初形作产(《殷虚书 契前编》四·五三·四)、喜(《殷契拾掇》二·一五八)、除了 头上的“辛”,不过是一寻常的爬行动物和飞禽的形象,显见其尊 贵完美的品性只能由“辛”来标明。 以上从本体、功用、施艺几方面对“辛”和以“辛”为字素 的字群进行了初步的介绍,从这些粗浅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 有一种矛盾的现象或许是令人关注的,即“辛”既可为刑罪低贱 的表记,又可为华美尊贵的标识。 其实,关于“辛”的字素意义的这种矛盾、还不限于前文所 述,如“章”之初文为“文饰彰明”,孳乳为“璋”为“彰”,而 “章”又孳乳为“障”、则夺其“彰明”之初义:《说文》:“障、蔽 也。”“彰明”之与“障蔽”,截然相对。又“音”为声之华美者, “音”中之“辛”表华美之义;而奇”(又作“苦”)则为声之丑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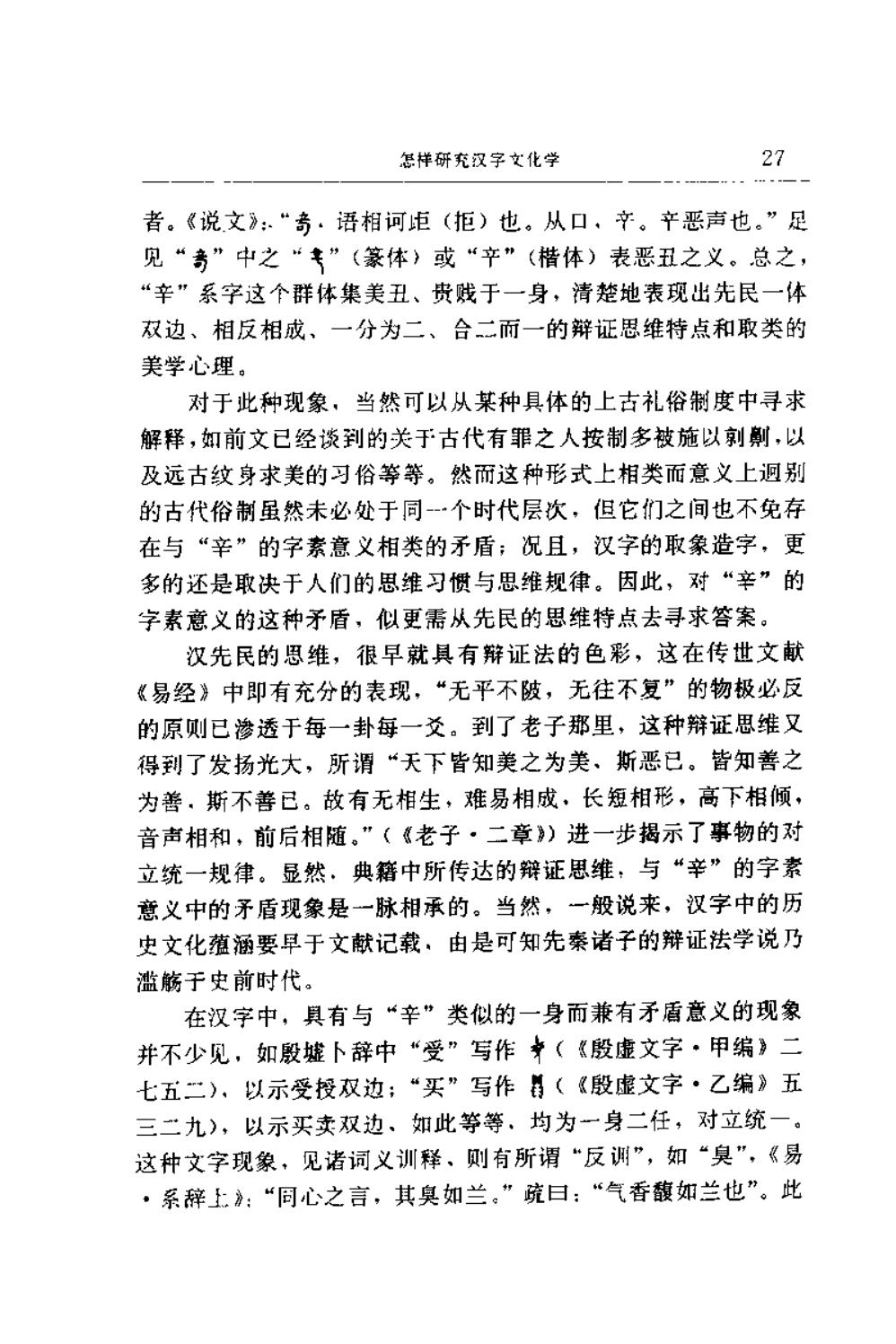
怎样研充汉字文化学 27 者。《说文》:“音·语相诃讵(拒)也。从口、产。辛恶声也。”足 见“音”中之“车”(篆体》或“辛”(楷体)表恶丑之义。总之, “辛”系字这个群体集美丑、贵贱于一身,清楚地表现出先民一体 双边、相反相成、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辩证思维特点和取类的 美学心理。 对于此种现象、当然可以从某种具体的上古礼俗制度中寻求 解释,如前文已经谈到的关于古代有罪之人按制多被施以刺劓,以 及远古纹身求美的习俗等等。然而这种形式上相类而意义上迥别 的古代俗制虽然未必处于同…个时代层次,但它们之间也不免存 在与“辛”的字素意义相类的矛盾;况且,汉字的取象造字,更 多的还是取决于人们的思维习惯与思维规律。因此,对“辛”的 字素意义的这种矛盾,似更需从先民的思维特点去寻求答案。 汉先民的恩维,很早就具有辩证法的色彩,这在传世文献 《易经》中即有充分的表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物极必反 的原则已渗透于每一卦每一爻。到了老子那里,这种辩证思维又 得到了发扬光大,所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 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稚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 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进一步揭示了事物的对 立统一规律。显然、典籍中所传达的辩证思维,与“辛”的字素 意义中的矛盾现象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一般说来,汉字中的历 史文化蕴涵要早于文献记载、由是可知先秦诸子的辩证法学说乃 滥觞于史前时代。 在汉字中,具有与“辛”类似的一身而兼有矛盾意义的现象 并不少见,如殷墟卜辞中“受”写作章(《殷虚文字·甲编》二 七五二)、以示受授双边;“买”写作书(《殷虚文字·乙编》五 三二九),以示买卖双边、如此等等、均为一身二任,对立统一。 这种文字现象,见诸词义训释、则有所谓“反训”,如“臭”,《易 ·系辞上》:“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疏日:“气香馥如兰也”。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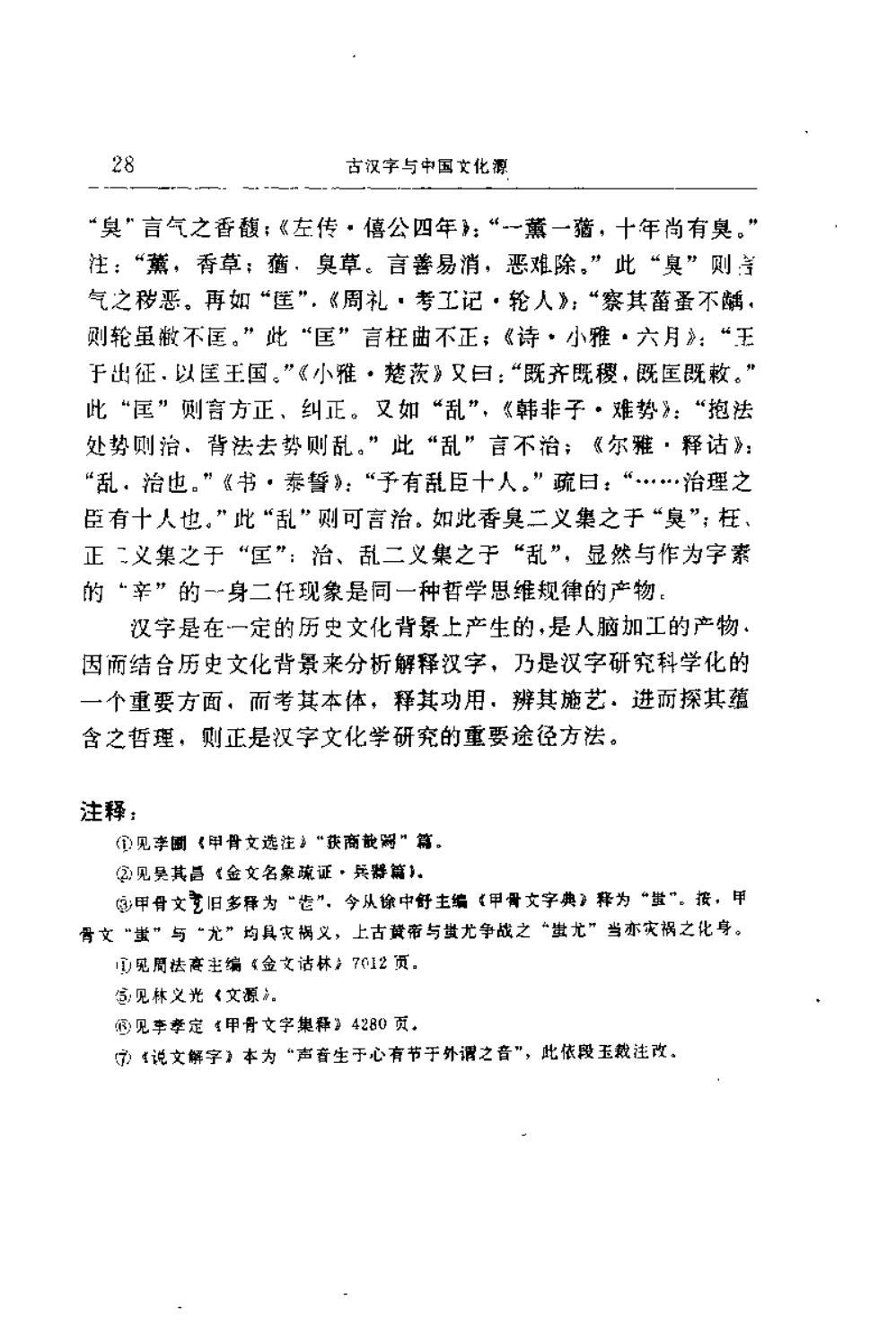
28 古汉字与中国文化源 “臭”言气之香馥:《左传·僖公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 注:“薰,香草:猶、臭草。言姜易消,恶难除,”此“臭”则羊 气之秽恶。再如“莲”,《周礼·考工记·轮人》:“察其菑蚤不龋 则轮虽撇不匡。”此“匡”言枉曲不正;《诗·小雅·六月》:“王 于出征,以匡王国。”《小雅·楚茨》又日:“既齐既稷,既匡既敕。” 此“匡”侧言方正、纠正。又如“乱”,《韩非子·难势》:“抱法 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此“乱”言不治;《尔雅·释诂》: “乱,治也。”《书·泰誓》:“予有乱臣十人。”疏日:“…治理之 臣有十人也。”此“乱”则可言治。如此香臭二义巢之于“臭”;枉、 正二义集之于“匡”:治、乱二义集之于“乱”,显然与作为字素 的“辛”的一身二任现象是同一种哲学思维规律的产物: 汉字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上产生的,是人脑加工的产物。 因而结合历史文化背景来分析解释汉字,乃是汉字研究科学化的 一个重要方面,而考其本体,释其功用、辨其施艺·进而探其蕴 含之哲理,则正是汉字文化学研究的重要途径方法。 注释: ①见李圃《甲骨文选注多“获商並网”篇。 ②见吴其昌《金文名象疏证·兵器篇》. ③甲骨文艺旧多释为“卷”、今从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释为“蚩”。按,甲 骨文“蚩”与“尤”均具灾祸义,上古黄帝与黄尤争战之“蚩尤”当亦灾祸之化身。 )见周法在主编《金文诘林立72页。 ⑤见林义光《文源。 ⑧见李幸定4甲骨文字集释》4280页。 ⑦《说文解字》本为“声者生于心有节于外裙之音”,此依段玉载注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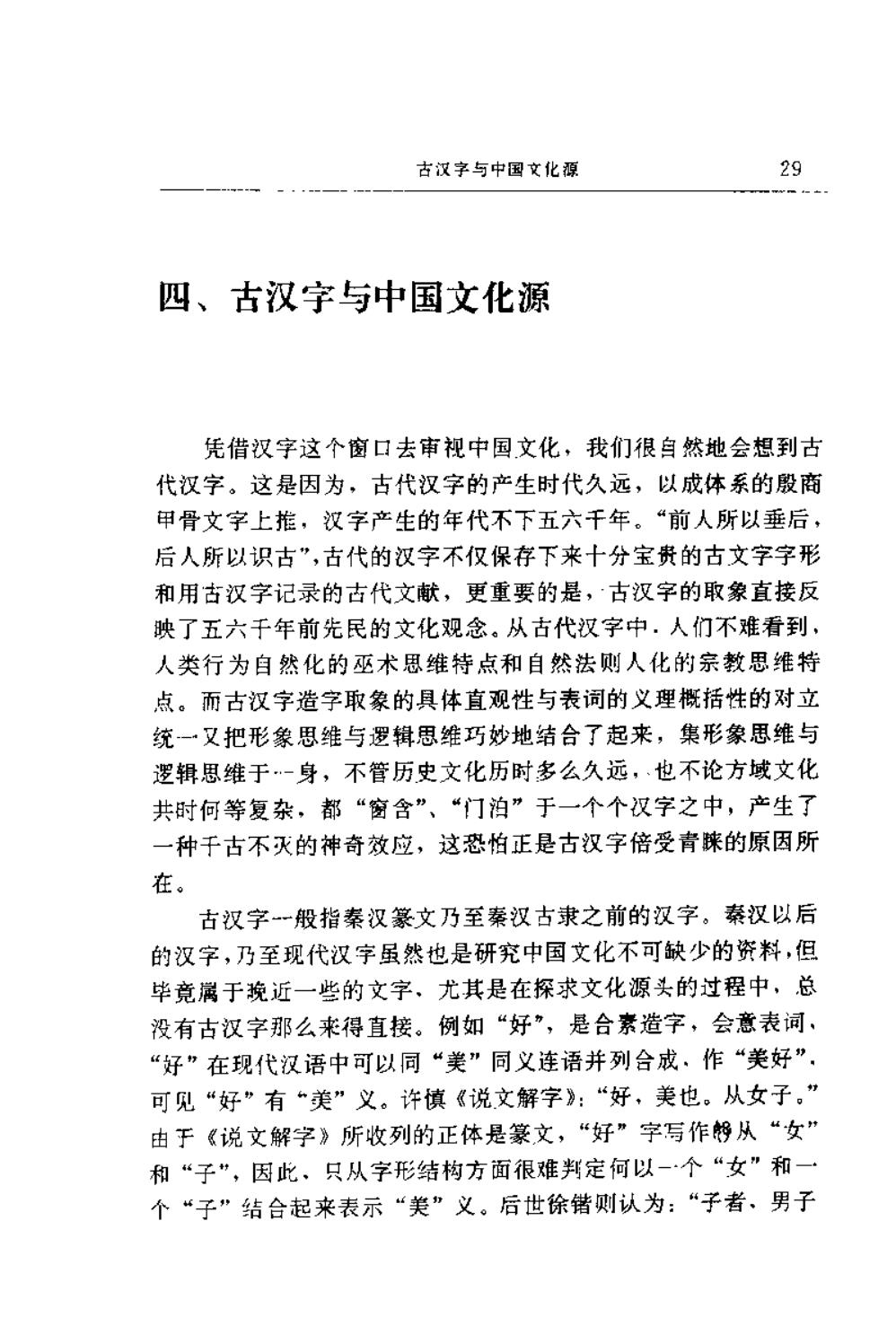
古汉字与中国文化源 29 四、古汉宇与中国文化源 凭借汉字这个窗口去审视中国文化,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古 代汉字。这是因为,古代汉字的产生时代久远,以成体系的殷商 甲骨文字上推,汉字产生的年代不下五六千年。“前人所以垂后, 后人所以识古”,古代的汉字不仅保存下来十分宝贵的古文字字形 和用古汉字记录的古代文献,更重要的是,·古汉字的取象直接反 映了五六干年前先民的文化观念。从古代汉字中·人们不难看到, 人类行为自然化的巫术恩维特点和自然法侧人化的宗教思维特 点。而古汉字造字取象的具体直观性与表词的义理概括性的对立 统·又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巧妙地结合了起来,集形象思维与 逻辑思维于-身,不管历史文化历时多么久远,也不论方域文化 共时何等复杂,都“窗含”、“门泊”于一个个汉字之中,产生了 一种干古不灭的神奇效应,这恐怕正是古汉字倍受青徕的原因所 在。 古汉字一般指秦汉篆文乃至秦汉古隶之前的汉字。秦汉以后 的汉字,乃至现代汉字虽然也是研究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资料,但 毕竞属于挽近一些的文字、尤其是在探求文化源头的过程中,总 没有古汉字那么来得直接。例如“好”,是合素造字,会意表词、 “好”在现代汉语中可以同“美”同义连语并列合成、作“美好”, 可见“好”有“美”义。许慎《说文解字》:“好,美也。从女子。” 由于《说文解字》所收列的正体是篆文,“好”字写作静从“女” 和“子”,因此、只从字形结构方面很难判定何以-·个“女”和一 个“子”结合起来表示“美”义。后世徐错则认为:“子者、男子